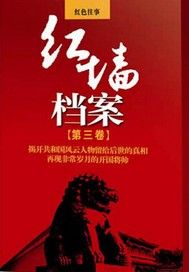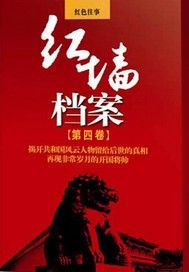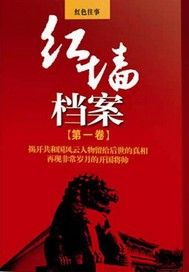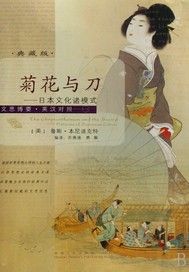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 第二节 融合中西文化
第二节 融合中西文化
蔡元培到校后,对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极为重视。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在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方面,曾进行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资产阶级新学的内容。但是这时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然把“法孔孟”定为教育宗旨,下令各校在编写修身、国文教科书时,必须“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妥慎改订,呈部审查。”这种“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使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新学又受到了压抑。虽然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很快破产了,但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所以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学校的教学思想仍很陈旧保守,课程设置也很落后,不少教员不学无术,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曾剀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严重束缚。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计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这就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他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学术和课程建设的取向上,主张“贯通中西”。他在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在谈到中国画也要吸取西洋画的优点时说:“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尔日耳曼诸民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隔绝,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只在他固有的范围内、固有的特色上进化,故‘文艺的中兴’,在中国今日才开始发展”。他认为要使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得到发展,就应该开放,善于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1916年秋,在他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就与汪精卫、李石曾联名致函国内有关人士,提出:“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元培等留法较久,考察颇详,见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儒先哲理类相契合;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他从这个思想出发,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外国科学成果,融合中西文化。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北大原来设有“中国哲学门”,一位学生曾建议改为“哲学系”,不局限于一国哲学,而要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这个建议和蔡元培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相一致,因而接受了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蔡元培是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的。以世界语为例,北大是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国璋(字芾仲)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语作为外国语学科之一,与国语算术及理科并重。蔡元培为了利于世界语学者作高深的研究,于1920年创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自兼会长,孙国璋为副。1922年俄国学者、盲诗人爱罗先珂受聘来校讲授世界语会话,孙专讲文法及读本,世界语班学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发起组织了北京世界语学会。是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语首先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这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世界语研究会开展纪念柴门霍甫诞辰的活动,在北大召开了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参加者达两千多人。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主张中国应普及世界语,以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会上通过的议案,要求在各级学校增加世界语课程,多方面推广世界语,并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由北大负责筹办的世界语专门学校,于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学校内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长,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周作人等。蔡元培提倡世界语,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程,是和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主张相一致的。
其次,认为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认为“人类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他既承认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又反对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强调学习外国,求得发展,又坚决反对“全盘欧化”,反对简单的模仿,生吞活剥外国的东西。他殷切地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时,要重在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为他人所同化。他对此作了意深词恳的剖祈: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长,补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級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儿辈英人、法人。支世界上能增加此几辈有学问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宁不甚善?无如失其我性为可惜也。往者学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缘之而益自发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十分感人而富有意义的。这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确为针砭时弊,金石之言。
但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当时在北大同样严重存在。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时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使对方语塞,无言以对。从这时起,开会时一律用中文,不再讲英语。在课堂上,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一些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后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后没有实现),但他没有单纯依赖外国,而是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学。1918年他聘请钟观光为北大理预科教授,担负采集我国植物标本的工作。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浙江镇海人。著名植物学家。蔡元培创立中国教育会和民初主持教育部时,曾与他共事。这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先后深入福建、广东、云南、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调查我国植物分布情况,历时五载,搜集和积累了许多珍贵植物标本与资料,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他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系正式成立后,钟观光仍留校继续整理标本,直至1927年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止。这时生物系已整理出植物标本八千多种,为教学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件事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和消化欧美国家的先进文化,根本是着眼于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再其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何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歩的发展。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种科学不仅指某一学科或研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人文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1921年6月,他到美国考察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曾阐述了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这对于改革学校的课程也有重要意义,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这时史的课程除中国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史,分别在四个年级讲授外,世界史有西洋史(分上古、中古和近世史),但东洋史还只有印度古代史和日本近世史。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第五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来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陈翰笙等人也在这时应聘来系介绍欧美新史学。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因而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当然,这主要是指这时新思潮对学术界的影响而言,对多数教授来说,其史学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1923年5月,北大考古学会成立,先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如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铜器,北京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肃敦煌古迹调查等,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有一定意义。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絞。”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扩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明确提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输出”。在他看来,国际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为前提,而“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因而要输出中国文明,让国际了解中国。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外,蔡元培还重视直接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经胡适等邀请来华后,蔡元培曾出面与杜威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商议,留他在北大讲授一年哲学。杜威除在北大讲学外,还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前后达两年多,遍历十一个省,大量散布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恶劣影响。蔡元培对杜威是谁崇的,但他并不赞同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如他在学与术的关系上重学理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立即得到应用,更难短期就有明显的效果,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科学研究的意义。这些观点有助于抵制实用主义思想对教育、科研领域的侵蚀。
继之,罗素、班乐卫、今西龙、杜里舒、阿士本、耶尔朔夫、福田德三等也曾应邀来校讲学或作学术讲演。1920年8月,北大特授与法国数学家班乐卫、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美国哲学家杜威、美驻华公使芮恩施以荣誉学位,蔡元培主持了授予仪式并发表演说。这是北大第一次授予外国学者以荣誉学位。
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亲自分别访问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华讲学。这一年3月8日,他在法国访晤居里夫人,当面邀请她来华讲学,居里夫人答:“此次不能柱,当于将来之暑假中谋之。”同年3月16日,他在德国偕原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琛访问爱因斯坦,“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如往中国演讲,应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1922年秋,爱因斯坦应邀到日本讲学,他表示愿同期来华,双方并商妥了来华讲学的条件。但由于中国方面拟以各团体联合名义发出联合邀请信,往返协商费时,致使爱因斯坦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未接到中方正式邀请信件,以为北大不打算践约,便延长了访日时间;直到12月22日,他方收到蔡元培寄去的信,才了解是误解,但日程已无法改变,致使这次访华无法实现。爱因斯坦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苦痛。”“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当时,北大曾为爱因斯坦访华作准备,于1922年11至12月举行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讲题有:《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主讲人丁燮林)、《相对各论》(何吟苜)、《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高叔钦)、《爱因斯坦之生平及其学说》(夏元瑰)、《非欧几里特的几何》(王士枢)、《相对通论》(文范村)、《相对论与哲学》(张竟生)。此外,北大当时还组织有相对学说讲演会和研究会,介绍和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蔡元培也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1918年5月,他曾呈请教育部咨商外交部,请于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于留学名额中增加北大人选。他提出过去北大有派选留学生成例,京师学堂期间,1903年曾派学生31名赴日留学;1906年曾分别资遣毕业生赴日留学游历;1907年复派师范毕业生八名赴英、法、美三国留学。自民国成立,国库奇绌,派生之举,因而停止。他认为“此不仅无以鼓励学生,亦且有碍学术发达,诚莫大之遗憾也。”
他在呈请中提出:“本校文、法、理、工四科每年毕业,约计十四班左右,每班以二人或一人计算,二十名之额,似难再减”。后得以派遣。他还很重视挑选准备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派往国外留学,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以便回校后开设新课,充实课程建设。
如史学系为培养师资,曾由学校选派本系毕业生姚士鳌、理科毕业生毛子水赴德学习史学和地理学。理科如汪敬熙、杨钟健、孙云铸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资送出国留学,后来他们都回北大担任教学工作。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在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方面,曾进行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资产阶级新学的内容。但是这时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然把“法孔孟”定为教育宗旨,下令各校在编写修身、国文教科书时,必须“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妥慎改订,呈部审查。”这种“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使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新学又受到了压抑。虽然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很快破产了,但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所以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学校的教学思想仍很陈旧保守,课程设置也很落后,不少教员不学无术,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曾剀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严重束缚。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计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这就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他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学术和课程建设的取向上,主张“贯通中西”。他在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在谈到中国画也要吸取西洋画的优点时说:“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尔日耳曼诸民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隔绝,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只在他固有的范围内、固有的特色上进化,故‘文艺的中兴’,在中国今日才开始发展”。他认为要使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得到发展,就应该开放,善于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1916年秋,在他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就与汪精卫、李石曾联名致函国内有关人士,提出:“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元培等留法较久,考察颇详,见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儒先哲理类相契合;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他从这个思想出发,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外国科学成果,融合中西文化。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北大原来设有“中国哲学门”,一位学生曾建议改为“哲学系”,不局限于一国哲学,而要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这个建议和蔡元培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相一致,因而接受了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蔡元培是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的。以世界语为例,北大是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国璋(字芾仲)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语作为外国语学科之一,与国语算术及理科并重。蔡元培为了利于世界语学者作高深的研究,于1920年创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自兼会长,孙国璋为副。1922年俄国学者、盲诗人爱罗先珂受聘来校讲授世界语会话,孙专讲文法及读本,世界语班学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发起组织了北京世界语学会。是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语首先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这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世界语研究会开展纪念柴门霍甫诞辰的活动,在北大召开了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参加者达两千多人。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主张中国应普及世界语,以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会上通过的议案,要求在各级学校增加世界语课程,多方面推广世界语,并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由北大负责筹办的世界语专门学校,于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学校内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长,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周作人等。蔡元培提倡世界语,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程,是和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主张相一致的。
其次,认为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认为“人类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他既承认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又反对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强调学习外国,求得发展,又坚决反对“全盘欧化”,反对简单的模仿,生吞活剥外国的东西。他殷切地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时,要重在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为他人所同化。他对此作了意深词恳的剖祈: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长,补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級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儿辈英人、法人。支世界上能增加此几辈有学问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宁不甚善?无如失其我性为可惜也。往者学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缘之而益自发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十分感人而富有意义的。这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确为针砭时弊,金石之言。
但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当时在北大同样严重存在。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时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使对方语塞,无言以对。从这时起,开会时一律用中文,不再讲英语。在课堂上,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一些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后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后没有实现),但他没有单纯依赖外国,而是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学。1918年他聘请钟观光为北大理预科教授,担负采集我国植物标本的工作。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浙江镇海人。著名植物学家。蔡元培创立中国教育会和民初主持教育部时,曾与他共事。这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先后深入福建、广东、云南、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调查我国植物分布情况,历时五载,搜集和积累了许多珍贵植物标本与资料,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他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系正式成立后,钟观光仍留校继续整理标本,直至1927年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止。这时生物系已整理出植物标本八千多种,为教学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件事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和消化欧美国家的先进文化,根本是着眼于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再其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何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歩的发展。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种科学不仅指某一学科或研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人文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1921年6月,他到美国考察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曾阐述了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这对于改革学校的课程也有重要意义,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这时史的课程除中国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史,分别在四个年级讲授外,世界史有西洋史(分上古、中古和近世史),但东洋史还只有印度古代史和日本近世史。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第五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来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陈翰笙等人也在这时应聘来系介绍欧美新史学。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因而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当然,这主要是指这时新思潮对学术界的影响而言,对多数教授来说,其史学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1923年5月,北大考古学会成立,先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如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铜器,北京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肃敦煌古迹调查等,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有一定意义。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絞。”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扩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明确提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输出”。在他看来,国际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为前提,而“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因而要输出中国文明,让国际了解中国。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外,蔡元培还重视直接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经胡适等邀请来华后,蔡元培曾出面与杜威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商议,留他在北大讲授一年哲学。杜威除在北大讲学外,还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前后达两年多,遍历十一个省,大量散布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恶劣影响。蔡元培对杜威是谁崇的,但他并不赞同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如他在学与术的关系上重学理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立即得到应用,更难短期就有明显的效果,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科学研究的意义。这些观点有助于抵制实用主义思想对教育、科研领域的侵蚀。
继之,罗素、班乐卫、今西龙、杜里舒、阿士本、耶尔朔夫、福田德三等也曾应邀来校讲学或作学术讲演。1920年8月,北大特授与法国数学家班乐卫、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美国哲学家杜威、美驻华公使芮恩施以荣誉学位,蔡元培主持了授予仪式并发表演说。这是北大第一次授予外国学者以荣誉学位。
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亲自分别访问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华讲学。这一年3月8日,他在法国访晤居里夫人,当面邀请她来华讲学,居里夫人答:“此次不能柱,当于将来之暑假中谋之。”同年3月16日,他在德国偕原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琛访问爱因斯坦,“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如往中国演讲,应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1922年秋,爱因斯坦应邀到日本讲学,他表示愿同期来华,双方并商妥了来华讲学的条件。但由于中国方面拟以各团体联合名义发出联合邀请信,往返协商费时,致使爱因斯坦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未接到中方正式邀请信件,以为北大不打算践约,便延长了访日时间;直到12月22日,他方收到蔡元培寄去的信,才了解是误解,但日程已无法改变,致使这次访华无法实现。爱因斯坦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苦痛。”“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当时,北大曾为爱因斯坦访华作准备,于1922年11至12月举行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讲题有:《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主讲人丁燮林)、《相对各论》(何吟苜)、《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高叔钦)、《爱因斯坦之生平及其学说》(夏元瑰)、《非欧几里特的几何》(王士枢)、《相对通论》(文范村)、《相对论与哲学》(张竟生)。此外,北大当时还组织有相对学说讲演会和研究会,介绍和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蔡元培也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1918年5月,他曾呈请教育部咨商外交部,请于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于留学名额中增加北大人选。他提出过去北大有派选留学生成例,京师学堂期间,1903年曾派学生31名赴日留学;1906年曾分别资遣毕业生赴日留学游历;1907年复派师范毕业生八名赴英、法、美三国留学。自民国成立,国库奇绌,派生之举,因而停止。他认为“此不仅无以鼓励学生,亦且有碍学术发达,诚莫大之遗憾也。”
他在呈请中提出:“本校文、法、理、工四科每年毕业,约计十四班左右,每班以二人或一人计算,二十名之额,似难再减”。后得以派遣。他还很重视挑选准备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派往国外留学,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以便回校后开设新课,充实课程建设。
如史学系为培养师资,曾由学校选派本系毕业生姚士鳌、理科毕业生毛子水赴德学习史学和地理学。理科如汪敬熙、杨钟健、孙云铸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资送出国留学,后来他们都回北大担任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