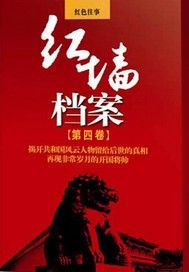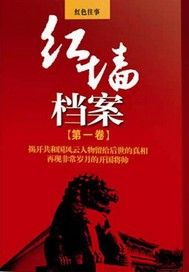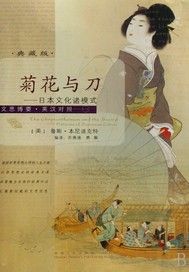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十二章 斑驳
这一日大清晨,高阳忽从一觉酣梦中醒来,睁目一瞧,只见绮窗碧纱,花影摇动,四周寂静无声。
高阳回头一见,见自己最贴身的侍女长荷并不在身旁,只是有青瞳、楚音在房中。她便问楚音道:“长荷到哪里去了?”
楚音含笑,半晌才悄声道:“回禀公主,长荷姐一大清早就被文夫人的丫头小萱叫走了。临去时,长荷姐她说这么早,公主是断断不会醒来的。她还说,并不要让人知道她去哪里了,说她立刻就会回来的。”
高阳听罢,颇觉诧异,默默地想道:“这真是从没有过的事。”想毕,发了半晌的怔,才对楚音道:“我要起来了。”
青瞳、楚音忙上前,伺候高阳起床梳洗。
梳洗完毕,雪妆将早餐端上来,高阳也不看,便教她端下去了。
楚音见高阳清晨一起来,洗梳完毕,便这样闷闷的一直坐在妆台前发怔。便笑道:“公主,要不要出去散一散心?”
青瞳见高阳仍端坐不动,便笑道:“公主,不知道长荷姐去文夫人她那里做什么去了?我看她去的好生神秘,定是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现在,我们就去文夫人屋里,看看长荷姐她在那里做什么,好是不好呢?”
高阳听罢青瞳这一席话,不觉好笑道:“怎么见得人家就有事?不是事事都可对人言的。”
楚音在一旁也笑劝道:“公主还是出去走走罢,省得发闷。夫人养的那只白鹦鹉越来越灵巧了,我保证它一见我们,便会向公主致礼儿的。”
高阳听了,这才站起身来,笑叹道:“去罢!反正有点闷。只是这一早便串门,有些叫人怪了。”
青瞳、楚音忙伺候高阳穿戴。
不久,高阳就率青瞳、楚音二人出门了。
原来,文夫人昨日到城中一个旧相识的姐妹,名叫贺月珩的人家中去贺寿,这贺月珩为太宗一重臣的如夫人。
那日,这位重臣在太宗千秋宴罢后,扶醉而归。不想他与正夫人闲话陛下欲再次与西京太守房玄龄联姻,将自己最宠爱之女高阳公主下嫁房玄龄二男房遗爱之事,偏被这贺月珩在无意中听见了。
这贺月珩与文夫人是多年的旧相识,说话多不避嫌。今见文夫人来,就忙将此事私下告知了她。
文夫人听了这些话,直蹙眉无语,她想不到高阳公主今后的命运,竟然就被她的父皇与他人在杯盘交错中这样决定了。
文夫人半晌才道:“按规矩,本朝公主多尚名士。这房二公子的文章及才干究竟何处出色了?让陛下看中了他?”
贺月珩听文夫人这一番话,不免含笑说道:“你这个晓初,也真是个‘双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释老书’的人了。这个房二公子,可不像房家那样世代书香门第人家出来的子弟,偏是那帮贵胄子弟中,好武、不喜文而闻名的,这‘文章出色’四字,又真从何谈起?”
文夫人听了,一时呆住了,半晌才道:“这房二公子口碑一般,又没有那种出类拔萃的才华,这如何使得?这如何使得?这不是委曲了我们这位公主!”
贺月珩苦笑道:“你以为光你觉得委曲?假如陛下真有此心将公主下嫁房府,普天下的人,都该为我们这位心高气傲的公主叫屈了。”
文夫人听罢,一时,焦虑满面,默然良久不语,半晌,才连连叹息道:“公主可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她的心性,我最是明白不过的了。如果是真有这样一桩姻缘,便是差大了,这如何是好?”
贺月珩见文夫人这般焦虑,忙道:“要说差,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试问论门第之显赫,除了房公家,在当今天下,还有何人能当得起?高阳公主是陛下最心爱的女儿,陛下当然要把公主下嫁到一个他最可仰赖的人家去。以月珩这个旁人看来,于君臣之道而言,天下最忠厚者,也非房大人莫属了。故这桩姻缘,于情于理,原无可厚非。”
文夫人听了贺月珩这一番话,不免长叹一声道:“于君臣之道而言,天下最忠厚者,当然是非房大人莫属了。可人家高阳公主与这君臣之道,究竟又有何种关联?今后的日子儿,终将是由公主自己来过,好歹便也只有人家自知了。素常我们公主最看重是人的性情及真实才华。对那些门第富贵什么的,反偏不放在眼中。富贵于她,真可谓等同浮云了。那种她能属意喜欢的人,便是一贫如洗的奴婢、僧道、贫尼也能为朋、为友;反之,则多是不屑一顾。陛下应该晓得我们的公主,她生就是这样的一副高傲脾性儿,而不该只看重门第这等虚物,而不顾及我们公主的心性了。”
贺月珩听文夫人这一说,也是半晌不语,后来也连连叹息道:“谁叫我们是女人来着?这都是命。话说转来,嫁谁娶谁,连天子的儿女,都是身由不得己,又遑论我们这些寻常人!试问与你一同入宫那百来号姐妹,现今安在?不过都是烟消云散了罢,又有几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哪一个女人又逃得了命运的编排?细思量,否则众人不会对‘命数’这样一些字眼,而奈何不得!”
贺月珩这一席话,直说得文夫人的全身心都凉了一个透彻。她忙告辞了往回赶。
等待文夫人到了宫中,可惜高阳已歇息了。
文夫人不便打搅她,自己心中倒是七上八下的,一夜未眠。
天一亮,文夫人不顾头痛,便令人将长荷从高阳的住处叫了出来。
长荷这里听了文夫人的话,边摇头,边叹息道:“按理来说,这一句话实在是不该由我们这些人说出来,这样寻常的人材,怎能入得人的眼目?这不是生生地毁了我们公主?”
文夫人默然半晌才道:“趁此事还没有成为定局之前,赶紧儿让公主去探个究竟才好。”
长荷听了,有些为难地说道:“只是,公主她一个女孩子家,如何问得这些事情?”
文夫人道:“这是有关终生的大事,如何又问不得?又不要直接去问,找个借口儿去问问总成罢?”
文夫人、长荷正说着。
她们忽然一抬头,只见高阳翩然入来,又见她身着一件薄银狐披裘,足穿鹿皮靴。头上乌云高绾,发间无多物,惟斜擦插一、二白鹭羽毛簪,显得高贵雅致。她身后还跟着青瞳、楚音二人。
高阳一进来,就见文夫人、长荷二人立即不言语。她便含笑问道:“你们在谈什么?竟连我也不让知道的么?”
文夫人、长荷忙站立起来,都笑迎道:“这么冷的天,公主还过来?快来坐着。”说罢,二人便帮她卸外衣。
高阳边入座,边笑道:“青瞳说你俩有秘密相商的,便偏要带我来探个究竟,我只能做一回恶客了。”
文夫人见瞒不过,忙将众侍女支开,又把自己听到的事,吞吞吐吐地告诉了高阳。
高阳听罢此事,只是支颐静坐。发怔半晌后,仍然难以置信地说道:“如何会呢?他的姐姐已经是嫁给我元嘉叔叔韩王为妃了,按辈分,我以‘婶’称之。现在,她的兄弟又要……,这岂不是咄咄的怪事情么?”
文夫人听了高阳的话,只是无言以答。
过了不久,高阳便再也坐立不住了,忙朝外对青瞳吩咐道:“让他们备车,我要立刻找父皇问一个究竟去。”
文夫人听高阳这一说,立刻点头赞同道:“公主,但愿这不过是空穴来风罢,弄清楚了,便是最好不过的。”
长荷、文夫人忙伺候高阳穿衣。
然后,车载高阳直奔太极宫的后宫而去。
恰逢贞观年间,天下基本还算太平无事,朝廷也是隔日方上朝,太宗今日正无需上朝。
太宗见高阳来了,不免心生欢喜道:“父皇正想要见阳儿,不想碰巧阳儿来了,看来,我们父女连心。”
高阳听了,不觉心中一惊,但又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含笑问道:“父皇有事找阳儿?”
太宗笑道:“无事,快过来陪父皇下局棋。”说罢,便在一镶象牙的金丝楠木棋盘前坐下。
宫人忙捧上棋子、汤茶上来,太宗挥手,让她们退下。
高阳这里听太宗说“无事”,便稍微安心。她一面拈棋在手,一面笑对太宗道:“下棋可以,只是父皇输了,阳儿想让父皇赏一件东西。”
太宗听了,不觉大笑道:“还未开战,阳儿便先设定局了。上次与阳儿下棋,父皇便输了,这次正思‘雪耻’呢。”
高阳也含笑道:“阳儿这一次,也照旧是当仁不让!”
太宗笑道:“鹿死谁手?还要拭目以待。”说罢,父女二人便开棋局。
高阳因疑团未破,不免心事丛丛,在棋局上,颇有些心不在焉。
半晌,太宗看着自己的棋势渐好,便看着高阳道:“阳儿,你为母后守孝已满,你也满十七了。”
高阳听罢,不觉拈一棋子在手,默然无语。
太宗叹息道:“在世的父母,也只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女完婚,后半生有所交待,方能安心的。现在,为父倒看好一个人。”
高阳听罢,一惊,忙道:“父皇,阳儿不愿成婚,只愿终生陪伴父皇。”
太宗笑道:“这真是孩子家的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没有一辈子都赖在宫中的道理的。再说,为父的终有走在儿女前头之日,那时阳儿又如何?莫非阳儿想作那终生不嫁的道姑不成?”
高阳仍然道:“阳儿就是不想出宫,只想在宫中终生伺奉父皇。”
太宗诧异地看着高阳问道:“这却是为何?为父的不懂了。”
高阳笑道:“父皇可曾还记得?阳儿十三岁时,便试骑过父皇一匹最心爱的银鬃马。因此马性烈,而人莫敢骑。阳儿不信,却偏要一试。在那时,父皇还说,阳儿就是世间一匹最难驯服的烈马,今后恐怕是难为人妻的。阳儿当即答道,阳儿才不愿为人之妻,要终生服侍父皇。父皇当即也说了,这正是求之不能之事了,只怕阳儿不肯。当时,阳儿还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句话了呢。现在,父皇岂肯忍让阳儿自食其言?而做不成君子!”
太宗听罢,大笑道:“言重了,这么久远的话,亏阳儿还记得!那时父皇只是说来与你玩笑的,莫要当真才好。再说阳儿现在已长成一个倩丽无比的大家闺秀了,如何为不得人妻?”
太宗说罢,又一笑道:“想想也觉好笑,父皇回宫还将阳儿的话,转说与你长孙母后听。那时,你母后还笑道,一般士人,如何擎受得起阳儿?人家阳儿从小就志向高远,恐怕夫婿不是一个才高八斗的人,就绝不会下嫁过去的。”
高阳听罢,忙笑嗔道:“父皇休得取笑阳儿!”
太宗忙笑道:“好!不提往事。当真天下统共才有一个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不过人家已于数百年前作古了。”
太宗见高阳拈棋低头看棋局不语,自己便也在棋盘里布下一子。
高阳出神半晌,也在其中布一子。
半晌,太宗又叹道:“现在,有大小千万件国事、家事,均压在父皇的心上,如果阳儿及你妹妹新城等人尚未婚嫁,为父的我将是寝食不安。其实,自你母后过世这些年来,父皇我也甚感寂寞,何尝不想把阳儿永留在身旁,以消暮年的寂寞?但女大当嫁,倒不能因为父皇舍不得,而误了阳儿的终身,这于情于理,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太宗见高阳仍低首不语,便又笑问道:“莫非怕人家的公子配不上阳儿?或是婚后受姑婆夫婿之约束,而不得自在了?”
半晌,高阳先点头,后又摇头道:“父皇,阳儿自顾不暇,又岂能为他人操浆持瓢?”
太宗笑道:“阳儿这真是推托之辞了。再说,如我们这样的人家,谁敢给阳儿气受?操浆持瓢这种事,如何会轮得上阳儿亲躬呢?自然有人会替你操持料理妥当的。”
一时,高阳心绪紊乱,不答一语。然后,她一直盯着棋局,仿佛从要这盘黑白混淆的迷局中闯出来,并且一定要战胜其父皇这一局棋,才能平息心内的挫败感。
过了半晌,太宗又笑道:“父皇曾在阳儿的故母之前有誓,要让阳儿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故父皇也定要把阳儿托付到一个在这世上让父皇最能安心的人家。这家主人为人忠心谦厚,又兼其孝道,其家风之严谨而远近闻名,大概他们家培养的儿女自不会有差。阳儿,你要不要猜猜他是谁?”
高阳听罢,心境越发绝望,俯首连道:“不猜!阳儿绝对不要猜的。”
太宗见状,笑道:“这阳儿还怕羞么?”说罢,在棋盘上,又顺手布了一子。
这时,太宗突然看见高阳的手又拈一棋子在手,然后,又见她抬头,望着自己的棋局道:“父皇只顾说阳儿的事,而顾不了自个儿的棋局,只怕这一回,父皇又是输定了!”
太宗一惊,望着棋盘,自负地笑说道:“怎会?方才阳儿的棋势,就还不太好呢。”
高阳将手中棋子,往棋盘中一搁,笑道:“孙子有言:‘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阳儿的这一盘棋,总该算得上是这个样子的了。”
太宗仔细辨了一下棋局,大笑道:“你父皇我今儿这才算得上是大意失荆州了!只好推枰认输了。可惜阳儿不生在战时,否则,方方面面都定是不亚于你平阳姑姑的。”
半晌,高阳才将话题一转,朝太宗微笑道:“阳儿的事,还请父皇千万、千万从长计议。这里父皇既然认输了,阳儿就想请父皇赐予孩儿一件东西,不知父皇肯不肯?”
太宗笑道:“是何种宝物?竟有舍不得送给我们阳儿之理?为父的这里除视这书架上晋人王右军的《兰亭集序》为至宝外,余者,就都随阳儿挑了。”
高阳忙笑道:“阳儿才不稀罕这些!阳儿只要父皇一幅亲书的飞白字体。我三兄最近赠了一个大金玉书厨与我。我欲还礼,他说,只要得一幅父皇的飞白字体即可。”
太宗听罢高阳说明的原由,不觉大笑道:“这个恪儿!他想要为父的字,为何自己不来求?反支着小妹跑差,也太不会怜惜人了。”
高阳笑道:“他说这字儿,目前也只有阳儿才要得出来。父皇,你千万莫让人家阳儿有辱使命才好哩。”
太宗听罢高阳的话,忙笑道:“好!好!阳儿的事,为父总是有求必应的。父皇过一二日写好了,便差人送来。阳儿要什么样的字?是励志劝学的?还是修身养性的?”
高阳想了一想,笑道:“不拘的。”
说罢,高阳便朝太宗的金丝楠木大书案走去。
高阳边走、边笑道:“阳儿看父皇闲暇兴来之时,常挥毫吟哦。父皇,你最近又有什么新作了?”
太宗一面也朝书案走去,一面笑道:“对了,这里有一首父皇的近作,是父皇过郊外草堂寺,去瞻仰罗什法师故迹后,有感而发的。阳儿,你且看一看父皇写得如何?”
太宗说罢,便将诗笺递给高阳。
高阳一面接诗笺,一面笑道:“这里就容阳儿拜读了。”说罢,就听她将这首《赞鸠摩罗什法师》轻声诵读道:“秦朝朗观圣人星,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文成金玉知不朽,口吐芬兰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诵罢,高阳沉思半晌,才对太宗道:“父皇的这首诗,可谓将鸠摩罗什法师这一生的行实都概括尽了。父皇这首诗的字,也是写得尽善尽美了。罗什法师功德之大,自是不用说的。只是,因我看见父皇这诗中有‘堪叹’二字,故阳儿想请教父皇一句,这逍遥园里的事,其中的是非对错,又该如何去评判呢?”
太宗想了一想,才笑道:“阳儿这一问,竟让父皇我一时难以回答了。按常理,鸠摩罗什法师身为佛门的一个修行人,就不该破了戒律,去娶妻生子。但父皇与姚兴一样,同样身为一国之君,自然会以为,如罗什法师这样聪明盖世之人,竟无后嗣去继承他的德馨与才能,这于国、于家,岂不是十分地可惜?故姚兴逼其纳妾生子一事,于情理而言,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此举,终究苦了法师本人,他不敢住僧坊,而且在逍遥园为弟子们讲经时,还常有‘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之叹。父皇自思,法师心中的烦闷,恐怕只那逍遥园中的明月青草可知了。而今父皇路过其故迹草堂寺,想故人安在?而那些曾看见法师含愁与抱怨的明月青草仍然青郁葱荣。故父皇我对此思之再三,也不免为之叹息不已。”
半晌,高阳方点头道:“父皇说得甚是。只是依阳儿看来,这古往今来的是非对错之理,竟然最是论不得了。且试想,谁又曾看见那‘不得已,而为之’这六字它后面的万般悲辛及无可奈何!”
不料高阳这句话,倒是说到太宗心上,这让他突然想起“玄武门之变”,心中不免隐约一痛。
为了掩饰这种心境,太宗大赞高阳的话,道:“这句话简直是完全在理!阳儿真不愧是个聪颖无比的孩子。今日父皇与阳儿谈得甚是投缘,故父皇我还要赏阳儿几件好东西。”
说罢,太宗回首吩咐内侍道:“把那冯学士临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拿过一卷来,朕要送高阳公主。”
太宗说完,又吩咐道:“还把书架上罗什法师译的那卷《成识论》也拿来。”
内侍忙应了,立即从书院书架上,将这些书取出来,并恭递给太宗。
太宗将《兰亭集序》的摹本递与高阳公主道:“这个虽为摹本,但父皇我敢说,它肯定也为世上罕有,阳儿应当善加爱护方好。”
继而,太宗又指着那卷《成识论》对高阳道:“据说那虔诚信佛,三次舍身为寺奴的梁武帝也对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卷《成识论》爱不释手。父皇公务繁忙,但大略一读,深感此经博大精深。阳儿有暇,倒也不妨一读。另外,罗什法师在地下,他如果有知阳儿这一句‘不得已,而为之’之语,该是何等的释怀!定会分外加佑阳儿的。”
高阳接过太宗所赠之书籍,及听见他所说之言后,不觉欢喜,将方才心头的不快,也暂放一边,忙对其父皇拜谢不迭。
太宗父女二人正说着,忽有内侍进来禀道:“陛下,梁国公房大人有要事,欲急禀陛下。”
太宗忙道:“即请他进来罢。”
高阳听了内侍的禀报后,不觉惊惶地打了一个寒颤,她便忙对太宗道:“父皇,恕阳儿这就告退罢。”
太宗笑对高阳道:“阳儿无需回避,见见房大人也好。”
高阳又道:“恕阳儿告退,且再见罢!父皇,阳儿去了。”
说罢,不待太宗发话,高阳便飞也似地从内殿侧门自去了。
太宗对高阳背影,含笑道:“人家是丑媳怕见公婆。阳儿倒是好端端的,又有何可惧哉?”
正是: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
高阳回头一见,见自己最贴身的侍女长荷并不在身旁,只是有青瞳、楚音在房中。她便问楚音道:“长荷到哪里去了?”
楚音含笑,半晌才悄声道:“回禀公主,长荷姐一大清早就被文夫人的丫头小萱叫走了。临去时,长荷姐她说这么早,公主是断断不会醒来的。她还说,并不要让人知道她去哪里了,说她立刻就会回来的。”
高阳听罢,颇觉诧异,默默地想道:“这真是从没有过的事。”想毕,发了半晌的怔,才对楚音道:“我要起来了。”
青瞳、楚音忙上前,伺候高阳起床梳洗。
梳洗完毕,雪妆将早餐端上来,高阳也不看,便教她端下去了。
楚音见高阳清晨一起来,洗梳完毕,便这样闷闷的一直坐在妆台前发怔。便笑道:“公主,要不要出去散一散心?”
青瞳见高阳仍端坐不动,便笑道:“公主,不知道长荷姐去文夫人她那里做什么去了?我看她去的好生神秘,定是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现在,我们就去文夫人屋里,看看长荷姐她在那里做什么,好是不好呢?”
高阳听罢青瞳这一席话,不觉好笑道:“怎么见得人家就有事?不是事事都可对人言的。”
楚音在一旁也笑劝道:“公主还是出去走走罢,省得发闷。夫人养的那只白鹦鹉越来越灵巧了,我保证它一见我们,便会向公主致礼儿的。”
高阳听了,这才站起身来,笑叹道:“去罢!反正有点闷。只是这一早便串门,有些叫人怪了。”
青瞳、楚音忙伺候高阳穿戴。
不久,高阳就率青瞳、楚音二人出门了。
原来,文夫人昨日到城中一个旧相识的姐妹,名叫贺月珩的人家中去贺寿,这贺月珩为太宗一重臣的如夫人。
那日,这位重臣在太宗千秋宴罢后,扶醉而归。不想他与正夫人闲话陛下欲再次与西京太守房玄龄联姻,将自己最宠爱之女高阳公主下嫁房玄龄二男房遗爱之事,偏被这贺月珩在无意中听见了。
这贺月珩与文夫人是多年的旧相识,说话多不避嫌。今见文夫人来,就忙将此事私下告知了她。
文夫人听了这些话,直蹙眉无语,她想不到高阳公主今后的命运,竟然就被她的父皇与他人在杯盘交错中这样决定了。
文夫人半晌才道:“按规矩,本朝公主多尚名士。这房二公子的文章及才干究竟何处出色了?让陛下看中了他?”
贺月珩听文夫人这一番话,不免含笑说道:“你这个晓初,也真是个‘双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释老书’的人了。这个房二公子,可不像房家那样世代书香门第人家出来的子弟,偏是那帮贵胄子弟中,好武、不喜文而闻名的,这‘文章出色’四字,又真从何谈起?”
文夫人听了,一时呆住了,半晌才道:“这房二公子口碑一般,又没有那种出类拔萃的才华,这如何使得?这如何使得?这不是委曲了我们这位公主!”
贺月珩苦笑道:“你以为光你觉得委曲?假如陛下真有此心将公主下嫁房府,普天下的人,都该为我们这位心高气傲的公主叫屈了。”
文夫人听罢,一时,焦虑满面,默然良久不语,半晌,才连连叹息道:“公主可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她的心性,我最是明白不过的了。如果是真有这样一桩姻缘,便是差大了,这如何是好?”
贺月珩见文夫人这般焦虑,忙道:“要说差,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试问论门第之显赫,除了房公家,在当今天下,还有何人能当得起?高阳公主是陛下最心爱的女儿,陛下当然要把公主下嫁到一个他最可仰赖的人家去。以月珩这个旁人看来,于君臣之道而言,天下最忠厚者,也非房大人莫属了。故这桩姻缘,于情于理,原无可厚非。”
文夫人听了贺月珩这一番话,不免长叹一声道:“于君臣之道而言,天下最忠厚者,当然是非房大人莫属了。可人家高阳公主与这君臣之道,究竟又有何种关联?今后的日子儿,终将是由公主自己来过,好歹便也只有人家自知了。素常我们公主最看重是人的性情及真实才华。对那些门第富贵什么的,反偏不放在眼中。富贵于她,真可谓等同浮云了。那种她能属意喜欢的人,便是一贫如洗的奴婢、僧道、贫尼也能为朋、为友;反之,则多是不屑一顾。陛下应该晓得我们的公主,她生就是这样的一副高傲脾性儿,而不该只看重门第这等虚物,而不顾及我们公主的心性了。”
贺月珩听文夫人这一说,也是半晌不语,后来也连连叹息道:“谁叫我们是女人来着?这都是命。话说转来,嫁谁娶谁,连天子的儿女,都是身由不得己,又遑论我们这些寻常人!试问与你一同入宫那百来号姐妹,现今安在?不过都是烟消云散了罢,又有几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哪一个女人又逃得了命运的编排?细思量,否则众人不会对‘命数’这样一些字眼,而奈何不得!”
贺月珩这一席话,直说得文夫人的全身心都凉了一个透彻。她忙告辞了往回赶。
等待文夫人到了宫中,可惜高阳已歇息了。
文夫人不便打搅她,自己心中倒是七上八下的,一夜未眠。
天一亮,文夫人不顾头痛,便令人将长荷从高阳的住处叫了出来。
长荷这里听了文夫人的话,边摇头,边叹息道:“按理来说,这一句话实在是不该由我们这些人说出来,这样寻常的人材,怎能入得人的眼目?这不是生生地毁了我们公主?”
文夫人默然半晌才道:“趁此事还没有成为定局之前,赶紧儿让公主去探个究竟才好。”
长荷听了,有些为难地说道:“只是,公主她一个女孩子家,如何问得这些事情?”
文夫人道:“这是有关终生的大事,如何又问不得?又不要直接去问,找个借口儿去问问总成罢?”
文夫人、长荷正说着。
她们忽然一抬头,只见高阳翩然入来,又见她身着一件薄银狐披裘,足穿鹿皮靴。头上乌云高绾,发间无多物,惟斜擦插一、二白鹭羽毛簪,显得高贵雅致。她身后还跟着青瞳、楚音二人。
高阳一进来,就见文夫人、长荷二人立即不言语。她便含笑问道:“你们在谈什么?竟连我也不让知道的么?”
文夫人、长荷忙站立起来,都笑迎道:“这么冷的天,公主还过来?快来坐着。”说罢,二人便帮她卸外衣。
高阳边入座,边笑道:“青瞳说你俩有秘密相商的,便偏要带我来探个究竟,我只能做一回恶客了。”
文夫人见瞒不过,忙将众侍女支开,又把自己听到的事,吞吞吐吐地告诉了高阳。
高阳听罢此事,只是支颐静坐。发怔半晌后,仍然难以置信地说道:“如何会呢?他的姐姐已经是嫁给我元嘉叔叔韩王为妃了,按辈分,我以‘婶’称之。现在,她的兄弟又要……,这岂不是咄咄的怪事情么?”
文夫人听了高阳的话,只是无言以答。
过了不久,高阳便再也坐立不住了,忙朝外对青瞳吩咐道:“让他们备车,我要立刻找父皇问一个究竟去。”
文夫人听高阳这一说,立刻点头赞同道:“公主,但愿这不过是空穴来风罢,弄清楚了,便是最好不过的。”
长荷、文夫人忙伺候高阳穿衣。
然后,车载高阳直奔太极宫的后宫而去。
恰逢贞观年间,天下基本还算太平无事,朝廷也是隔日方上朝,太宗今日正无需上朝。
太宗见高阳来了,不免心生欢喜道:“父皇正想要见阳儿,不想碰巧阳儿来了,看来,我们父女连心。”
高阳听了,不觉心中一惊,但又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含笑问道:“父皇有事找阳儿?”
太宗笑道:“无事,快过来陪父皇下局棋。”说罢,便在一镶象牙的金丝楠木棋盘前坐下。
宫人忙捧上棋子、汤茶上来,太宗挥手,让她们退下。
高阳这里听太宗说“无事”,便稍微安心。她一面拈棋在手,一面笑对太宗道:“下棋可以,只是父皇输了,阳儿想让父皇赏一件东西。”
太宗听了,不觉大笑道:“还未开战,阳儿便先设定局了。上次与阳儿下棋,父皇便输了,这次正思‘雪耻’呢。”
高阳也含笑道:“阳儿这一次,也照旧是当仁不让!”
太宗笑道:“鹿死谁手?还要拭目以待。”说罢,父女二人便开棋局。
高阳因疑团未破,不免心事丛丛,在棋局上,颇有些心不在焉。
半晌,太宗看着自己的棋势渐好,便看着高阳道:“阳儿,你为母后守孝已满,你也满十七了。”
高阳听罢,不觉拈一棋子在手,默然无语。
太宗叹息道:“在世的父母,也只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女完婚,后半生有所交待,方能安心的。现在,为父倒看好一个人。”
高阳听罢,一惊,忙道:“父皇,阳儿不愿成婚,只愿终生陪伴父皇。”
太宗笑道:“这真是孩子家的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没有一辈子都赖在宫中的道理的。再说,为父的终有走在儿女前头之日,那时阳儿又如何?莫非阳儿想作那终生不嫁的道姑不成?”
高阳仍然道:“阳儿就是不想出宫,只想在宫中终生伺奉父皇。”
太宗诧异地看着高阳问道:“这却是为何?为父的不懂了。”
高阳笑道:“父皇可曾还记得?阳儿十三岁时,便试骑过父皇一匹最心爱的银鬃马。因此马性烈,而人莫敢骑。阳儿不信,却偏要一试。在那时,父皇还说,阳儿就是世间一匹最难驯服的烈马,今后恐怕是难为人妻的。阳儿当即答道,阳儿才不愿为人之妻,要终生服侍父皇。父皇当即也说了,这正是求之不能之事了,只怕阳儿不肯。当时,阳儿还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句话了呢。现在,父皇岂肯忍让阳儿自食其言?而做不成君子!”
太宗听罢,大笑道:“言重了,这么久远的话,亏阳儿还记得!那时父皇只是说来与你玩笑的,莫要当真才好。再说阳儿现在已长成一个倩丽无比的大家闺秀了,如何为不得人妻?”
太宗说罢,又一笑道:“想想也觉好笑,父皇回宫还将阳儿的话,转说与你长孙母后听。那时,你母后还笑道,一般士人,如何擎受得起阳儿?人家阳儿从小就志向高远,恐怕夫婿不是一个才高八斗的人,就绝不会下嫁过去的。”
高阳听罢,忙笑嗔道:“父皇休得取笑阳儿!”
太宗忙笑道:“好!不提往事。当真天下统共才有一个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不过人家已于数百年前作古了。”
太宗见高阳拈棋低头看棋局不语,自己便也在棋盘里布下一子。
高阳出神半晌,也在其中布一子。
半晌,太宗又叹道:“现在,有大小千万件国事、家事,均压在父皇的心上,如果阳儿及你妹妹新城等人尚未婚嫁,为父的我将是寝食不安。其实,自你母后过世这些年来,父皇我也甚感寂寞,何尝不想把阳儿永留在身旁,以消暮年的寂寞?但女大当嫁,倒不能因为父皇舍不得,而误了阳儿的终身,这于情于理,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太宗见高阳仍低首不语,便又笑问道:“莫非怕人家的公子配不上阳儿?或是婚后受姑婆夫婿之约束,而不得自在了?”
半晌,高阳先点头,后又摇头道:“父皇,阳儿自顾不暇,又岂能为他人操浆持瓢?”
太宗笑道:“阳儿这真是推托之辞了。再说,如我们这样的人家,谁敢给阳儿气受?操浆持瓢这种事,如何会轮得上阳儿亲躬呢?自然有人会替你操持料理妥当的。”
一时,高阳心绪紊乱,不答一语。然后,她一直盯着棋局,仿佛从要这盘黑白混淆的迷局中闯出来,并且一定要战胜其父皇这一局棋,才能平息心内的挫败感。
过了半晌,太宗又笑道:“父皇曾在阳儿的故母之前有誓,要让阳儿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故父皇也定要把阳儿托付到一个在这世上让父皇最能安心的人家。这家主人为人忠心谦厚,又兼其孝道,其家风之严谨而远近闻名,大概他们家培养的儿女自不会有差。阳儿,你要不要猜猜他是谁?”
高阳听罢,心境越发绝望,俯首连道:“不猜!阳儿绝对不要猜的。”
太宗见状,笑道:“这阳儿还怕羞么?”说罢,在棋盘上,又顺手布了一子。
这时,太宗突然看见高阳的手又拈一棋子在手,然后,又见她抬头,望着自己的棋局道:“父皇只顾说阳儿的事,而顾不了自个儿的棋局,只怕这一回,父皇又是输定了!”
太宗一惊,望着棋盘,自负地笑说道:“怎会?方才阳儿的棋势,就还不太好呢。”
高阳将手中棋子,往棋盘中一搁,笑道:“孙子有言:‘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阳儿的这一盘棋,总该算得上是这个样子的了。”
太宗仔细辨了一下棋局,大笑道:“你父皇我今儿这才算得上是大意失荆州了!只好推枰认输了。可惜阳儿不生在战时,否则,方方面面都定是不亚于你平阳姑姑的。”
半晌,高阳才将话题一转,朝太宗微笑道:“阳儿的事,还请父皇千万、千万从长计议。这里父皇既然认输了,阳儿就想请父皇赐予孩儿一件东西,不知父皇肯不肯?”
太宗笑道:“是何种宝物?竟有舍不得送给我们阳儿之理?为父的这里除视这书架上晋人王右军的《兰亭集序》为至宝外,余者,就都随阳儿挑了。”
高阳忙笑道:“阳儿才不稀罕这些!阳儿只要父皇一幅亲书的飞白字体。我三兄最近赠了一个大金玉书厨与我。我欲还礼,他说,只要得一幅父皇的飞白字体即可。”
太宗听罢高阳说明的原由,不觉大笑道:“这个恪儿!他想要为父的字,为何自己不来求?反支着小妹跑差,也太不会怜惜人了。”
高阳笑道:“他说这字儿,目前也只有阳儿才要得出来。父皇,你千万莫让人家阳儿有辱使命才好哩。”
太宗听罢高阳的话,忙笑道:“好!好!阳儿的事,为父总是有求必应的。父皇过一二日写好了,便差人送来。阳儿要什么样的字?是励志劝学的?还是修身养性的?”
高阳想了一想,笑道:“不拘的。”
说罢,高阳便朝太宗的金丝楠木大书案走去。
高阳边走、边笑道:“阳儿看父皇闲暇兴来之时,常挥毫吟哦。父皇,你最近又有什么新作了?”
太宗一面也朝书案走去,一面笑道:“对了,这里有一首父皇的近作,是父皇过郊外草堂寺,去瞻仰罗什法师故迹后,有感而发的。阳儿,你且看一看父皇写得如何?”
太宗说罢,便将诗笺递给高阳。
高阳一面接诗笺,一面笑道:“这里就容阳儿拜读了。”说罢,就听她将这首《赞鸠摩罗什法师》轻声诵读道:“秦朝朗观圣人星,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文成金玉知不朽,口吐芬兰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诵罢,高阳沉思半晌,才对太宗道:“父皇的这首诗,可谓将鸠摩罗什法师这一生的行实都概括尽了。父皇这首诗的字,也是写得尽善尽美了。罗什法师功德之大,自是不用说的。只是,因我看见父皇这诗中有‘堪叹’二字,故阳儿想请教父皇一句,这逍遥园里的事,其中的是非对错,又该如何去评判呢?”
太宗想了一想,才笑道:“阳儿这一问,竟让父皇我一时难以回答了。按常理,鸠摩罗什法师身为佛门的一个修行人,就不该破了戒律,去娶妻生子。但父皇与姚兴一样,同样身为一国之君,自然会以为,如罗什法师这样聪明盖世之人,竟无后嗣去继承他的德馨与才能,这于国、于家,岂不是十分地可惜?故姚兴逼其纳妾生子一事,于情理而言,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此举,终究苦了法师本人,他不敢住僧坊,而且在逍遥园为弟子们讲经时,还常有‘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之叹。父皇自思,法师心中的烦闷,恐怕只那逍遥园中的明月青草可知了。而今父皇路过其故迹草堂寺,想故人安在?而那些曾看见法师含愁与抱怨的明月青草仍然青郁葱荣。故父皇我对此思之再三,也不免为之叹息不已。”
半晌,高阳方点头道:“父皇说得甚是。只是依阳儿看来,这古往今来的是非对错之理,竟然最是论不得了。且试想,谁又曾看见那‘不得已,而为之’这六字它后面的万般悲辛及无可奈何!”
不料高阳这句话,倒是说到太宗心上,这让他突然想起“玄武门之变”,心中不免隐约一痛。
为了掩饰这种心境,太宗大赞高阳的话,道:“这句话简直是完全在理!阳儿真不愧是个聪颖无比的孩子。今日父皇与阳儿谈得甚是投缘,故父皇我还要赏阳儿几件好东西。”
说罢,太宗回首吩咐内侍道:“把那冯学士临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拿过一卷来,朕要送高阳公主。”
太宗说完,又吩咐道:“还把书架上罗什法师译的那卷《成识论》也拿来。”
内侍忙应了,立即从书院书架上,将这些书取出来,并恭递给太宗。
太宗将《兰亭集序》的摹本递与高阳公主道:“这个虽为摹本,但父皇我敢说,它肯定也为世上罕有,阳儿应当善加爱护方好。”
继而,太宗又指着那卷《成识论》对高阳道:“据说那虔诚信佛,三次舍身为寺奴的梁武帝也对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卷《成识论》爱不释手。父皇公务繁忙,但大略一读,深感此经博大精深。阳儿有暇,倒也不妨一读。另外,罗什法师在地下,他如果有知阳儿这一句‘不得已,而为之’之语,该是何等的释怀!定会分外加佑阳儿的。”
高阳接过太宗所赠之书籍,及听见他所说之言后,不觉欢喜,将方才心头的不快,也暂放一边,忙对其父皇拜谢不迭。
太宗父女二人正说着,忽有内侍进来禀道:“陛下,梁国公房大人有要事,欲急禀陛下。”
太宗忙道:“即请他进来罢。”
高阳听了内侍的禀报后,不觉惊惶地打了一个寒颤,她便忙对太宗道:“父皇,恕阳儿这就告退罢。”
太宗笑对高阳道:“阳儿无需回避,见见房大人也好。”
高阳又道:“恕阳儿告退,且再见罢!父皇,阳儿去了。”
说罢,不待太宗发话,高阳便飞也似地从内殿侧门自去了。
太宗对高阳背影,含笑道:“人家是丑媳怕见公婆。阳儿倒是好端端的,又有何可惧哉?”
正是: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