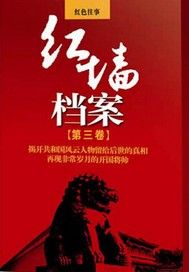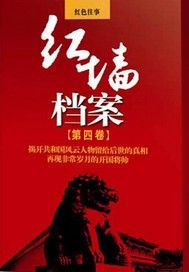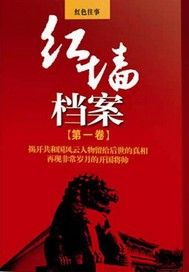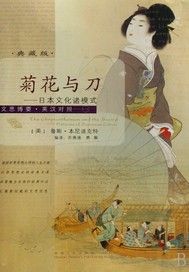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三十八章
老田、张颂臣、姜耀成都是很有特点和个性的人,颇富感染力和亲和力。与他们打了几天交道,阚式模就打心底里服了。他服他们的酒量,服他们的棋艺,服他们的谈吐和见识,服他们的豪爽性格和英雄气概,更服他们对时事大局、民族前途、国家兴亡命运等大事的见解与看法。渐渐地,他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开始变了,开始向着游击队一方靠近了。
阚式模的这一变化,人人见了都很高兴,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结义兄弟、二连连长高行渐。高行渐为人狠毒,阴险狡诈。他在江西时和红军打过不少仗,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怨,因此不愿意投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他曾经好几次找阚式模谈话,公开表达自己不愿意投靠游击队的主张。这时见阚式模和游击队越走越近,他心里不满,便暗暗地耍起了阴谋诡计。这天中午,他以庆贺自己四十五岁大寿为名,在他的二连连部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特地邀请阚式模和老田、张颂臣、姜耀成等人赴宴。这宴会名义上是庆生宴,实际上却是鸿门宴、逼宫宴,内里暗藏杀机,目的就是要借机杀掉老田、张颂臣、姜耀成和杨金根,彻底切断阚式模带领阚团投向游击队的路。
老田来阚团驻地没几天,跟高行渐没怎么打过交道,对他这个人了解不多,但对他举办的生日宴会却还是很有戒心的。临去赴宴之前,他特地把杨金根叫到一边,悄悄地叮嘱说:“对高行渐这个人,我们不熟悉,不能不有所戒备。他搞的那个宴会,你就别参加了吧!你留在外头,脑子活泛一点,多注意一下周边的情况。如果有事,或者发现了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你就赶紧去找阚副官和李长亭。这两个人还是比较可靠的。”
“是呀,人地生疏,情况复杂,戒备之心不能不有,我们确实要做好两手准备,”杨金根边说边点头,“对了,老田,这宴会你非得亲自参加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能不能找个理由把它推掉呢?张老板和姜老伯不是也要去嘛,让他们代表你敬杯酒,表达一下祝贺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老田摇摇头,轻声说:“阚式模去,我哪能不去呀!那会引起他们猜疑甚至不满的,对争取他们反正不利,明白吗?”
“非去不可的话,那就得格外小心了,尤其是要少喝酒,当心他下毒,”杨金根说,“对了,万一有事的话,我去哪里找阚副官和李连长呢?他们俩今天确定不参加宴会吗?”
老田用两目余光飞快地扫了扫四周,悄声说:“我问过李长亭和阚副官了。他们俩今天都有事,分不开身,不参加高行渐的宴会了。李长亭的事是带班值勤,多半会在一连连部或湘长公路附近。你去那里找他,准能找到。阚副官的事是带人巡视库房。我估计,他巡视的重点是军事装备库。因此,他不在军事装备库附近,便会在库房里面。”
叮嘱过杨金根后,老田又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地叮嘱了张颂臣和姜耀成几句,要他们少喝几杯酒,特别是要当心酒里有毒。
对老田的叮嘱,张颂臣不以为然。他大大咧咧地笑着说:“酒里下毒?借给他高行渐一百个胆,他也不敢!老田,你是不是小心得过了头呀?别忘了啊,咱们身边还有一个阚式模呢!阚式模可是咱们的保护神,关键时候能管用的。有他这位大哥在,高行渐那个当老弟的敢胡闹?哼,我看他没这个胆!”
“诸葛一生唯谨慎。张大哥,我看老田的想法对,多一分谨慎就多一分安全嘛,”姜耀成转脸看着张颂臣,一边说话,一边伸手摸摸下巴颏,“高行渐这人咱们不了解,天晓得他肚子里打的是什么算盘呀,对不对?我看呀,他把宴会放在他的连部办就值得怀疑。所以呀,咱们还是谨慎为妙。”
姜耀成的话显然动了老田的心。他眉头一紧,神情严肃地说:“是呀,高行渐怎么不把宴会摆在餐厅,却要摆在他的连部呢?哼,这事多少有些可疑之处,姜老伯说得对,咱们还是谨慎为佳,当心他‘项庄舞剑’!”
“什么‘项庄舞剑’!老田,我看你是太多心了。他是连长,在自己的连部举办宴会,这不也很正常嘛!嗨,算了,算了,你们要是实在害怕的话,那就去见一面,打个招呼,道声祝贺,然后就走人吧!我反正胆子大,什么也不怕,一个人留在宴会上和他们纠缠也没关系!”张颂臣说。他依旧大大咧咧,不大相信宴会上会出什么问题。
“我们见一面就走当然不行,酒还是要喝一杯的,”老田对张颂臣说。说完,他又转过脸来看着姜耀成,“姜老伯,小心使得万年船,咱们还是要做点预防。这样吧,咱们三个人分分工,我和张老板集中精力对付宴会,和他们纠缠,你就想办法早一点脱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
“哟、哟、哟,那不行,那不行,”姜耀成对着老田连连摇头,“咱们三个人中,数我的酒量最好,你们的酒量都不行。你和张大哥留下来对付宴会,那还不都得被他们灌倒了呀!算了吧,还是我留下来对付宴会,你和张大哥想办法尽早脱身吧!”
张颂臣撇撇嘴,笑了笑:“耀成老弟,不是老哥我自高自大,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不能走的。老田呢,他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也是不能走的。明摆着,老田是游击队的头,我是阚世模的恩人,都是宴会上的主客。你想想看,我们俩能抽身走人吗?我们俩要是走了,宴会上可就没有主客了,那阚式模该怎么想啊,高行渐又该怎么想啊?倒是你呢,情况和我们俩略略不同一点,完全可以去他娘一走了之。”
姜耀成抬头看看张颂臣,忽又低头沉吟:“是啊,大哥,你说的这情况我明白,可我心里不落忍啊!我这个最能喝酒的一走了之,却把你们两个不怎么能喝酒的留下来让他们灌酒,这、这不像话吧!”
“嗨,你哪是一走了之呢!刚才老田不是说了嘛,他是要你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的,那可是重大的责任啊,”张颂臣伸出手来,在姜耀成的肩头上拍了拍,然后又指了指自己衣服上的袖口,“好了,好了,别多虑了,我和老田又不是傻子,哪会那么容易让他们灌倒呢!嘿嘿,等会儿喝酒呀,我不拿嘴喝,就拿这只袖子喝,全他娘的往这只袖子里倒,看他娘的高行渐究竟能有多少酒倒进我这袖子里来!”
宴会上的明争暗斗还在酝酿,屋外的剑拔弩张却已经开始了。杨金根正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四个人迎面朝他走过来了。那四个人自称是阚团二连的战士,奉高行渐连长的命令来请他喝酒。杨金根是从来不喝酒的,当时便拱拱手,客客气气地回绝说:“对不起,我是滴酒不沾的,扫四位仁兄的兴了,请多原谅!”
“滴酒不沾?怎么可能呢?当兵的哪有不会喝酒的呀!”一个高个子士兵说。四个人的个头都比杨金根高,而这个高个子士兵的个头尤其高,差不多比杨金根高了一个脑袋。
杨金根仰头看了高个子士兵一眼,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说:“也许是天生的吧,我从小就不能喝酒,学都学不会。”
“喝酒都学不会?哼,我不信!”高个子士兵摇摇头,撇撇嘴。
站在高个子士兵旁边的,是一个年纪略大些的矮胖子。这时,他斜眼一瞟杨金根,开口说话了:“嗨,不会喝酒也没关系嘛,茶总会喝的吧?走吧,杨老弟,别借故推辞了,和我们一起去坐一坐,喝杯茶吧!坐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天,也不错呀,对不?”
杨金根抬眼看了看那个矮胖子,作古正经地说:“茶嘛,倒是可以喝的,不过这时候我不得空。这样吧,改天我请你们喝茶,行吗?今天嘛,我实在没时间,就只好对不住了。四位仁兄,请自便吧,恕小弟不能奉陪了!”
“坐在一起喝杯茶都不肯?哼、哼,看来你是存心要驳我们的面子喽!”矮胖子带着浓重的鼻音说。他的脸色开始变了,渐渐地由青变红。
“嚯嚯,仁兄误会了,误会了,不是小弟我存心要驳面子,而是真的有事分不开身,请多原谅,请多原谅!”杨金根抱拳作揖,抽身便走。
但杨金根想走,这时候也走不成了。那四个当兵的一拥而上,把他围在了垓心。杨金根拿眼扫了扫那四个当兵的,心里有些诧异,但却绝没有慌张。
“你们四位这是唱的哪一出呀?”杨金根淡然一笑。
矮胖子显然是个当头的,身上挎着盒子枪,脸上也带着一股子傲慢的官气。他一边拿眼扫向四周,指挥着其他几个当兵的,一边阴笑着说:“哪一出?《十字坡》呗!想借你的肉蒸几个人肉包子吃呀!嘿嘿,杨老弟,我们晓得你是条好汉,今天要你死也多少有些冤枉,但没办法,上命差遣,不得不为,你别怨恨我们哥儿几个哟!”
“哦,你们几个原来是想吃人肉包子,所以特地来找我麻烦的,”杨金根一边说,一边笑,“嗨,我还正愁没事干,打发不了这空闲日子呢,没想到你们哥儿几个倒主动送上门来陪我玩了!好吧,话都已经挑明了,那就来吧,还等什么呀?”
打斗很快就开始了。四个当兵的把杨金根围在中间,一个个伸拳踢腿,张牙舞爪,好不威风。高个子士兵劲头最足,先上。他从右侧开始进攻,一个箭步蹿了上来,猛地抓住了杨金根的右胳膊。紧跟着,一个嘴巴边上长着一道长长白疤瘌的士兵又从左侧开始进攻了,一上来便抓住了杨金根的左胳膊。杨金根的左右两只胳膊都被抓住了,情况似乎很不妙,但他自己却毫不在意,兀自若无其事地左看看,右看看,连连冷笑不止。高个子和白疤瘌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容易得手,因此脸上都开始泛出一丝洋洋自得的神色。但他们的得意劲实在是来得太早了,嘴巴还没来得及张开笑一笑,情况就突然变了。杨金根开始行动了,他身子往下一沉,再往后一缩,不知不觉间,整个人便一下子退到了高个子和白疤瘌的后面。紧跟着,他伸出一只手顶在高个子的后腰上,把另一只手按住白疤瘌的背部,然后两手一齐发力,高个子和白疤瘌便不由自主地往前冲,面对面地贴在一起了。两个大男人面对面地贴在一起,这样子显然既不雅观,又不好受。高个子的下巴颏磕在白疤瘌的脑门上了,白疤瘌疼得眼泪直流。白疤瘌的脑袋撞到高个子的胸部上了,高个子就像五脏六腑都被人掏掉了一般,好半天喘不过气来。
兵油子果然不一般,吃了亏就能长记性。这回轮到矮胖子和另一个士兵上了。那另一个士兵是个朝天鼻,两个鼻子眼没朝下,而是朝前,就像猪鼻子眼一般。矮胖子对朝天鼻使了个眼色,朝天鼻便对着杨金根扑上来了。他显然是吸取了高个子和白疤瘌的教训,虽然往前扑,却只不停地在杨金根的下三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撩拨,不肯靠近杨金根的身子。这动作很明显,目的在于引开杨金根的注意力,以便为其他人进行偷袭创造条件和机会。果然,没过多久,偷袭就开始了。进行偷袭的是矮胖子本人,他终于亲自动手了。只见他左腿往前一迈,身子急速旋转,右腿忽然一伸,脚尖猛地朝杨金根的裆下踢来。这是一招旋风腿,杨金根自然晓得。见矮胖子的脚尖急速踢来,他不仅不躲避,反倒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往下轻轻一捞。他这种捞法很独特,不显山不显水的,毫不引人注意,但却极有效,一下子便把矮胖子的那只脚捞在自己手中了。紧接着,他抓住矮胖子的脚掌猛地往前一送,矮胖子就站立不稳了,很快便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
两次进攻,两次都遭到了惨败,但矮胖子和他的同伴们却还不想放手。很快,他们又开始组织新的进攻了。不过,他们这一次进攻与上两次显然不同,既没有明确的分工,又没有精心的准备。矮胖子只是挤挤眼,呶呶嘴,算是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四个人便一起动手,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朝着杨金根狠狠地扑过来了。紧接着,他们就抱的抱腿,搂的搂腰,掐的掐脖子,死死地缠住了杨金根。这做法毫无章法,是上不得台面的,说白了不过就是流氓混混打群架,耍无赖。但这做法却对人多的一方有利,可以浑水摸鱼,趁乱取胜。杨金根没想到他们会采取这种流氓做法,事先不曾防备,因此动作慢了些,吃了一点亏。四个人一缠上身,他就明显处于不利局面了。他的手被人死死地抓住了,有劲使不出。他的腿被人牢牢地抱住了,有力踹不动。他的脖子被人紧紧地勒住了,连呼吸都畅快不起来。“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此时此刻,杨金根的心里就充满了被犬欺的感觉。
杨金根的心里虽然很不是滋味,但却没有着急,没有慌张。他是一个稳重人,沉得住气,甚至是越到急时还越有主意。他干脆手脚、身体都不动了,任凭矮胖子他们胡乱折腾。然而,他身体、手脚不动,心里却五时无刻不在紧张地思索着脱身的办法。他信心很足,觉得自己一定能够尽快地想出脱身的办法来。果然,他很快就想到办法了。他看到高个子的脑袋就在自己的头顶上方,下巴颏差不多挨着自己的脑门了,便悄悄地往下缩了缩身子,把全身力道凝聚到脑袋上,然后猛地使劲往上一顶。杨金根的这一顶力道极大,高个子的下巴颏和牙齿直接受到了沉重而猛烈的撞击,一阵阵巨大的疼痛立马袭上心头。高个子受不了了,不知不觉地松开了原本死死勒住杨金根脖子的那只手。
高个子的手一松开,杨金根的脖子就能活动自如,自由呼吸了。他感到了一阵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痛快,不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当此之时,稍有松懈,便可能会导致生命之忧的。因此,他片刻不敢停留,很快又开始了新的动作。高个子松手后,身体稍稍往后退了退。这就给杨金根留下了一些活动空间。杨金根的新动作,就是利用高个子留出的这一点点活动空间做文章。只见他两腿朝前猛地一蹬,双手使劲往后一拽,整个身子忽然往上一窜,然后又直直地往后倒了下去。很快,他便倒在地上了,四仰八叉,双眼望天。但这时杨金根倒在地上了,矮胖子、白疤瘌、朝天鼻也都倒在地上了。他们三个人原本是抱住杨金根的胳膊和大腿的。显然,他们的倒下完全是杨金根倒下时连带所致。杨金根运用借力打力的武术招式,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倒下时所形成的巨大惯性和重力,因而连带着把矮胖子、白疤瘌、朝天鼻他们三个人拖倒在地上了。
杨金根身体灵巧,一挺身就站起来了,但矮胖子他们却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杨金根拍拍身上的泥土,望着矮胖子他们笑了笑,不慌不忙地说:“四位仁兄,今天玩得还算痛快吧?要不要再玩玩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用的那招式也是入不得流的,胜之不武哟!不过,我这么做,也确实情有可原,迫不得已呀,谁叫你们用无赖流氓小混混打群架的方式来对付我呢!嘿嘿,咱们这就算扯平了吧,不打了,行不行呀?说实在的,就你们这能耐,别说四个人了,再来四个,也奈何不了我的。你们大概还不清楚吧,刚才我可是网开一面,没跟你们玩真的哟!要是玩真的,你们的小命只怕早就到阎家五爹那里报到去了,哪还有留在人间吃饭穿衣、拉屎撒尿的份儿呀!嗨,不说了,不说了,你们也可怜,人家要你们来杀我,你们就不得不来;可你们要想杀人吧,却又没那本事!算了,算了,我也晓得你们的苦处,不和你们为难了,你们爬起来走人吧!”
杨金根满以为自己很大度,矮胖子他们应该不会再纠缠了。因此,说完话,他转过身来,拔腿便走。但他刚刚迈开腿,还没走出三五步,矮胖子他们便一拥而上,把前后左右都堵住了。而且,他们每个人的手中还多了一样家伙——匕首。
“嚯嚯,想开溜?害怕了吧?”矮胖子一边说,一边晃晃手中的匕首。
杨金根扫一眼矮胖子,似笑不笑地说:“害怕?哼,我生来就胆大,至今还没搞清‘害怕’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呢!”
“不害怕,怎么要走呀?”高个子眯眯眼。
“那还不明白呀,觉得你们的这些小混混招式太低级,太下流,懒得跟你们玩了呗!”杨金根淡淡地一笑。
“懒得跟我们玩?哼,恐怕是害怕跟我们手中的这家伙玩吧?这家伙挺好的,很锋利,还是头次用,没见过血的呢!嘿嘿,没想到,它今天要在你身上派上用场了!”高个子眼睛盯着匕首,忽然把它往上一抛,然后又伸手接住。
“嘿嘿,你说的还真是没错,”杨金根看看高个子,“我还真是有些怕匕首呢!”
“瞧,说实话了吧,你小子果然是怕我们手中的匕首!”高个子哈哈大笑了,眉毛、眼睛、鼻子、嘴扯到了一起,一张脸皱皱巴巴的。
“不过,你搞清楚了啊,”杨金根盯着高个子,“我说怕匕首,可没说怕你们!我怕匕首,不是怕你们用匕首杀了我,而是怕我自己不小心用匕首误杀了你们,明白吗?”
“嘿嘿,你胡说,你胡说,”高个子晃动着手中的匕首,连声大喊,“匕首在我们手里拿着,你还能用来杀我们?哼,你没那本事!”
“是嘛,你不相信我有这本事?好吧,那你就等着吧,我可是不客气了啊,要动手了啊!”杨金根边说边挪动脚步,身子朝高个子站的那方向晃了晃。
杨金根这一动,高个子沉不住气了,脸色立时大变,两条腿也开始颤抖起来。他还以为杨金根真的是在瞄准他,要先拿他开刀呢!
其实,杨金根并没有真动。他只不过是做了个假动作而已。此时此刻,他并没有要和矮胖子他们真打真拼、一决生死的想法。矮胖子他们已经凶相毕露,誓要将他杀之而后快了,他为什么还没有和他们真打真拼、一决生死的想法呢?是害怕他们吗?当然不是!是害怕他们手中的匕首吗?当然也不是!他没这想法,完全是因为心中有所顾忌。
杨金根心中的顾忌是什么呢?这顾忌,来源于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处的特殊场合、特殊环境。问题很明显,他不是阚团的人,而是阚团请来的客人;并且,他还不是主要的客人,而只是主要客人的随从、护卫。因此,在这个环境里,他没有多少说话、行事的权利,必须处处受制约,事事听命于人,时时小心在意。四个人,四把匕首,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很容易打发,但他有权利打发吗?
望着矮胖子他们手中捏着的匕首,杨金根的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地琢磨起来了:“徒手搏斗,用力或轻或重,倒还能随意掌控,不至于轻易伤人性命。但若是用上匕首一类武器来,那还能随意掌控得住吗?枪炮无眼,匕首也是没长眼的呀!在搏斗中,他们要杀我,那是不可能的,但却难保我不会误杀他们呀!要是我一不留神,误杀了他们,或是让他们受了伤,见了血,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倘若因为自己的误杀而引起了阚团其他战士的愤怒,导致他们一拥而上,集体跟自己作对,自己能够对付得了吗?倘若因为自己而导致阚团跟游击队反目了,使得阚团反正的事泡了汤,那自己不是犯下滔天大罪了吗?倘若把事情闹大了,搞得不好收拾,自己怎么面对老田呀?怎么面对张老板和姜老伯呀?怎么回盘山去见老余和游击队的同伴们呀?”
这样一琢磨,杨金根终于下定决心了。他要以忍为上,一忍到底,通过躲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脱离是非之地。于是,他一纵身,跃上了旁边的一棵树。那树很高,也很大,有很多树杈。他就像玩单杠似的,先跃上一根树枝,再从那根树枝上爬到了一个树杈上。然后,他就坐在那树杈上不动了,静静地看着树下的四个人。
杨金根上树了,匕首够不着他了,矮胖子他们便着急了。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骂了起来,从杨金根的祖宗骂到杨金根本人,又从杨金根本人骂到游击队和共产党。杨金根却不管他们骂什么,只一门心思坐在树杈上不理不睬,闭目养神。
骂了一阵,矮胖子他们忽然不骂了,又纷纷低头弯腰,捡起了地上的石头。他们把大大小小的石头捡了起来,拿在手里,瞄准了树上的杨金根使劲砸,想把他砸下来。但他们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扔上去的石头既没多大准头,又没多大力道,哪能把杨金根那么灵活的人砸得下来!而且,他们一扔石头,反倒给杨金根提供了武器。杨金根顺手一捞,就把他们扔上来的石头捞在手里了。然后,他再拿着这些石头,照准矮胖子他们使劲扔。杨金根人在高处,石头由上往下扔,准头大,力道也大。结果,他扔的那些石头大半都砸到了矮胖子他们的身上,砸得他们鼻青脸肿,哭爹叫娘。
砸石头不管用了,矮胖子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从库房里找出几根长竹竿,每人发一根,然后就拿着这些长竹竿使劲往上戳,想把杨金根从树上戳下来。但这办法也没用,杨金根左一窜,右一跃,爬到了大树的最高处,长竹竿就全都够不着了。
办法都用尽了,杨金根却坐在树顶上稳如泰山。矮胖子着急了,搓着手,自言自语道:“这、这、这怎么办呢?哎呀——”
白疤瘌忽然走了过来,低头悄声说:“嗨,副排长,你不是带着枪嘛!有这玩意在,你还犯哪门子愁啊?给他一枪,不就得了?”
矮胖子原来是个副排长。他摸摸别在腰上的手枪,皱皱眉头说:“嗨,这办法我也不是没想过,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敢这么做呀!高连长叮嘱过,库房重地,附近又有日本人,枪是不能随意开的。再说,咱们离一连、三连都不远,也怕惊动他们呀,对不?他们人多,一旦枪声惊动了他们,那可就麻烦了——”
“哦,那倒也是,那倒也是,”白疤瘌连连点头,“那、那弹弓行不行呀?我倒是有几副好弹弓,平时拿着打鸟玩的,力量蛮足——”
白疤瘌这一说,矮胖子立马来了精神。他挤挤眼,把嘴巴贴到白疤瘌耳朵根子上说:“弹弓?哼,那玩意没准行。这样吧,你这就去拿弹弓,我们在树下守着,谨防他跑了!”
矮胖子和白疤瘌在树下鬼鬼祟祟,引起了杨金根的注意。他蹲在树杈上琢磨开了:“这两家伙耍什么名堂呢?该不是要去拿枪吧?他们要是用枪,那我就麻烦了。四条枪一齐放,我还不得被打成筛子?我死倒不要紧,可老田他们怎么办呢?老田可是叮嘱过我的呀,要我有事时就赶紧去找阚副官和李长亭。现如今还真是有事了,我怎么能傻呆呆地蹲在树杈上等着矮胖子他们开枪呢?高行渐那王八蛋的宴会肯定有阴谋。这会儿,老田他们只怕早就遇上麻烦了。不行,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得赶紧走,得赶紧找阚副官和李长亭去!”
一想起老田在宴会上可能遇到麻烦了,杨金根的心里就起急。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手一伸,脚一蹬,就飞快地在树上爬了起来。那棵树紧挨着一栋房子。他三下两下就爬到了临近那房子的一根树枝上。他抓住那树枝,身子像荡秋千那样往下一荡,两只脚就稳稳当当地落在屋顶上了。到了屋顶上就好办了。他的轻功好,在屋顶上奔跑如履平地。他直起身子,看了看四周的地形,然后就沿着屋脊一溜烟地跑了杨金根猜得没错,老田他们在宴会上早就遇到麻烦了。
麻烦是从喝酒开始的。高行渐派了五个大兵上场。那五个大兵都是酒量大得吓人的酒鬼。他们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大碗里都盛满了度数高得惊人的白酒。他们端着大碗酒沿着桌子转,逢人必敬,敬则必喝。谁要是不喝,他们就站在你身边不依不饶地劝,无休无止地说,甚至怪腔怪调地唱,搞得你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那些酒没有下毒,但由于度数很高,喝多了,人自然也就跟中毒差不多了。
阚式模酒量不小,酒胆也大。他是只要有人敬酒,就必喝无疑的,从来不会耍赖推酒。所以没多久,他就喝得多了,脸红耳热,醉眼迷离,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张颂臣虽说大大咧咧,不大相信宴会上有阴谋,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起了戒心。他打定了用袖子装酒的主意,有人敬酒,他就喝,但不往下咽,等人不注意时,再回头悄悄地吐到袖子里。这主意倒也起作用,高行渐敬了好几轮酒,他居然脸不红,耳不热,就跟没喝酒一般。但这办法虽然有效,却长久不了,因为那时是热天,张颂臣只穿着一件单衣,薄薄的一层棉布根本就存不住很多酒。
果然,没过多久,张颂臣的高招就不灵了。他衣袖里的酒不停地往下滴,滴到了一个敬酒大兵的脚上,那大兵立马叫喊起来:“张老板,你这袖子里怎么滴水呀?”
敬酒大兵的叫喊,引起了高行渐的注意。他走过来,扯起张颂臣的衣袖一看,当时就嚷嚷道:“哟,张老板,你那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也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呀?不行,不行,得罚,得罚,罚三大碗!不,得罚四大碗!”
高行渐当时就把那几个敬酒的大兵喊过来罚张颂臣喝酒。张颂臣没办法推辞了,只得一碗接一碗地喝了起来。
张颂臣的高招败露了,高行渐对老田和姜耀成喝酒的监督也更严了。没办法,他们俩也只得老老实实地喝起酒来。这形势自然是很不妙的。老田深感忧虑,悄悄地在桌子底下用脚捅了捅姜耀成。这意思很明显,是在催促姜耀成赶紧想办法逃离宴席。
姜耀成也觉得是该逃离宴席的时候了,脑子急速地转动起来。忽然间,一个大兵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鲜鱼汤端上了桌。姜耀成一见,立马计上心头。他拿起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小碗鲜鱼汤,就低头猛喝起来。那鱼汤很烫,姜耀成喝得很急,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了。
“哎呀,太好喝了,太好喝了,我生平最爱喝的就是鱼汤,而且还特别爱喝刚出锅的滚烫的鲜鱼汤!”姜耀成自顾自地喝着鱼汤,而且还边喝边说,一个劲地为鱼汤叫好。
喝了一阵鱼汤,姜耀成忽然停下来了,开始猛烈咳嗽。他抬起头,张着嘴,皱着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样子十分痛苦,似乎是鱼汤或者花椒等什么作料呛到气管里去了。一个大兵拿着一条毛巾走了过来。他见了,一把夺过那毛巾来,便急不可耐地往鼻子上捂。他一边用毛巾捂住鼻子,一边猛烈地咳嗽,一边还时不时地低下头,朝地下啐唾沫。这狼狈、肮脏的情况,谁都是不愿看的,人们纷纷扭转脸向着别处。趁着这功夫,姜耀成悄悄地松开毛巾一角,把一根牙签伸进鼻孔里捅了几下。这一来,他的鼻子便很快出大问题了,鲜血直流,喷嚏不断,唾沫横飞,狼狈不堪。
姜耀成这出戏实在演得太逼真了,瞒过了所有的人。顿时,宴会厅里喊的喊,叫的叫,人人手忙脚乱。高行渐张罗着要派人去喊医生。阚式模一挥手,把他阻住了。阚式模虽然酒喝得多,已经有些醉意,却还没有醉倒。他东倒西歪地走到姜耀成面前,伸手拍拍他的肩头,结结巴巴地说:“姜、姜老伯,别、别着急,肯定是胡、胡椒呛到鼻子眼里了,没、没什么大事的。你、你到外面去擦、擦把脸,洗一洗,把那粒胡、胡椒抠、抠出来,再、再去茅厮屋(厕所)里屙沱尿,就、就万、万事大、大吉了!”
阚世模说话了,其他人就不好说什么了。姜耀成就像遇上了大赦令,心里高兴不已。他一躬身站了起来,朝阚式模弯弯腰,又朝高行渐点点头,捂着鼻子就往外走。
见姜耀成往外走,高行渐连忙扒拉一下身边的一个大兵,低声喝道:“快去看住他,别让他跑了!他要是跑了,老子要你的命!”
厕所就在附近不远,那地方还很僻静。姜耀成一口气跑进厕所,转身躲到了门后。没多久,那大兵也跑来了。他站在门口欲进不进,不住地伸头张望。姜耀成见机得快,趁着他把脑袋伸进来张望时,便全身顶住门板,使狠劲猛地一推。这一下起作用了,那大兵“唉哟”一声,往后便倒。见那大兵倒在地上了,姜耀成忙从厕所里跑了出来,抱起一块大石头,对准他的脑袋,就狠狠地砸了下去。
接连挨了两次重力打击,那大兵晕过去了,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姜耀成朝他看了一眼,双手合十,默默念叨道:“惭愧,我姜耀成活到今天,也已六十有五了,还从来没跟人打过架呢,更别说杀人了。今日之事,实是迫不得已,只好请你原谅了!”
姜耀成默默地念叨了一番,又朝着那大兵鞠了几个躬,便转身走了。
杨金根还是没能摆脱矮胖子他们的纠缠。矮胖子他们熟悉地形,早就抄近路躲在一个地方了。那地方是杨金根的必经之路,非常隐蔽,杨金根看不到。因此,当杨金根一纵身从屋顶上跳下来时,很快便遇到了防不胜防的猛烈进攻。
首先发起进攻的是朝天鼻。他就躲在杨金根站的那个屋檐下,离杨金根非常近。杨金根一落地,脚还没站稳,朝天鼻就抡起一根粗大的木棍从左侧狠狠地扫了过来。那木棍扫着了杨金根的左腿膝盖。杨金根膝盖受伤,站立不稳,扑地便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发起进攻的是高个子。他就站在杨金根的右侧身后,挥舞着匕首扑了过来。杨金根正要起身,无奈腿受了伤,一时站不起来,结果被他刺中了一刀。那一刀刺进了右侧腰部,伤口很深,血流有如泉涌。两次受伤都很重,杨金根终于站不起来了。
见杨金根站不起来了,朝天鼻不觉大喜过望。他挥舞着那根粗大的木棍,又狠狠地扑了过来。这一回,杨金根有防备了。见木棍快近身了,他便伸出左手抓住,然后再使劲一拽,立马就把朝天鼻拽到了自己跟前。说时迟,那时快,杨金根右手一伸,叉开五指,忽地掐住了朝天鼻的脖子。这一下,朝天鼻就再也没有活路可走了。杨金根掐住他的脖子使劲一捏,再忽左忽右地拧几下,朝天鼻就不能动弹了。
杨金根在全力对付朝天鼻时,高个子就想乘机偷袭。他轻手轻脚、鬼头鬼脑地潜到杨金根身后,忽地一扬匕首,照准杨金根的后背就狠狠地戳了下来。他满意为自己的算计高明,杨金根不死也得重伤。但他的想法错了,杨金根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当匕首戳来,快要触及到后背时,杨金根忽然头一偏,身子一转,整个人就躲到朝天鼻的身后了。他用手捏住朝天鼻的脖子,把朝天鼻的躯体送到了高个子的匕首面前。高个子用力过猛,那匕首收不回来,整个地戳进了朝天鼻的后背。
眼见自己的匕首刺进了同伴朝天鼻的体内,高个子大吃一惊。他颓丧极了,正想拔出匕首再和杨金根决一死战时,情况忽然又变了。杨金根没等他拔出匕首,猛地一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杨金根的手劲大极了,高个子根本无力反抗。他折腾了几下,就再也折腾不起来了。杨金根终于用同一个方法干掉了两个敌人。
两处伤口都很疼,血也流得不少,但杨金根丝毫也不觉得难受。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他杀掉了两个敌人。“以两处伤口换两个敌人的性命,哼、哼,怎么说,这买卖也值!”他这样想着,不觉悄悄地乐了。
近处有一张门,门口有一道台阶。杨金根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地往前爬着,想爬到那台阶上歇一歇,脱下衣服,撕块布,包扎一下伤口。但就在这时,一粒石头子忽然飞来,打在了他的胸部上。那石头子不大,力道却不小,他的胸口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好像是弹弓打的,谁在打弹弓呢?”杨金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仰头向远处张望。很快,他就发现那打弹弓的人了。那人是白疤瘌。他正拿着弹弓洋洋得意呢。
“娘的,有你好看!”杨金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忽地一扬手,把手中捏着的那粒石头子扔了出去。那石头子飞得极快,刹那间就飞到了白疤瘌身边,一下子打中了他的右眼。这一下,白疤瘌的眼睛受伤不轻。他捂着眼睛哭爹叫娘,跌跌撞撞地跑了。
“嘿嘿,今天的买卖还行,打倒三个了!”杨金根乐了,脸上带着笑。但没过多久,他又收住笑,脸上显得十分严肃,嘴里也不住地自言自语起来:
“不对呀,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的,怎么这里只看见了三个呢?不是还有一个矮胖子嘛,他好像还是个头呢,这会儿躲到哪里去了?不行,我得慎重点,小心那王八蛋搞偷袭!”
杨金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眼四处张望。忽然,眼前一闪,路口跑过来一个人。他一惊,以为是矮胖子,连忙抄起那根粗木棍准备战斗。但就在这时候,那人突然停住不跑了,朝他喊了起来:“哟,金根,你怎么在这里呀?”
杨金根抬眼一看,原来那人是姜耀成。他又惊又喜,忙问:“姜大伯,你要去哪里呀?”
姜耀成小心翼翼地朝前后左右望了望,压低声音说:“老田他们有危险了,我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你怎么在这里待着呀?唉呀,你负伤了吧,流了那么多血!”
“我也是要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的,遇到了他们的截杀,所以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纠缠了老半天,”杨金根用手指指躺在地上的白疤瘌和高个子,“结果呢,他们完了,我自己也受伤了。唉,这伤看来还不轻,我这阵子站都站不起来了。得了,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老伯,你走吧,赶紧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
“我走?我走了,你怎么办?你可是伤得不轻啊,”姜耀成一边说,一边向杨金根靠近,“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把伤口包一包,再去找他们!”
“不、不、不,伤口不要紧,我自己能包,用不着你帮忙!你快走,别磨蹭!再磨蹭下去,老田他们就危险啦!”杨金根一边说,一边挥手。
姜耀成也晓得情况万分紧急,片刻耽误不得了。他转过身,边走边说道:“那好,我走了,你多保重,我过一会儿就来找你!”
姜耀成走了。但他刚走没多久,就遇到麻烦了。矮胖子来了,在路口堵上了他。姜耀成毕竟年纪大了,又没经过军事训练,哪里是矮胖子的对手。矮胖子拿着寒光闪烁的匕首,恶狠狠地扑向姜耀成,只三两招就把他逼得浑身大汗淋漓了。
路口的打斗声引起了杨金根的注意。他知道姜耀成遇上麻烦了,想去帮他解围,却又苦于自己站不起来,不觉急得心里直冒火,两只手不停地搓着,嘴里还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他娘的,这、这可怎么办呢?有劲使不上,干着急呀!”
杨金根真是一个智多星,再急的时候也能想得出主意来。突然,他不嚷嚷了,朝着打斗的方向喊了起来:“姜大伯,你快过来帮帮忙,我、我这伤口的血止不住了!唉哟,唉哟,他娘的,这伤口怎那疼啊?”
杨金根这是在用调虎离山计,目的在于通过招呼姜耀成而把矮胖子引过来,以便自己的一双手能够抓住或者打着矮胖子。姜耀成不知是计,还真以为杨金根的伤口止不住血呢。听到杨金根的喊声,他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了。矮胖子更搞不明白杨金根的心思。见姜耀成往杨金根的身边跑,他也就跟着跑过来了。见矮胖子跑到自己身边了,杨金根不觉大喜,手一伸,抓住他的一条胖腿便使劲一拽。杨金根这一拽,完全出乎矮胖子的意外。矮胖子毫无防备,立马仰面朝天地栽倒在地了。这时,杨金根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忽地两手一撑,身子高抬,朝着矮胖子压了过来,一下子便把他压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
矮胖子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身子被压住了,手脚却片刻未停。他和杨金根死死地纠缠在一起,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难分胜负。姜耀成见杨金根身上有伤,担心他吃亏,便想上来帮忙。但杨金根却不要他帮忙。他对着姜耀成连声大喊:“姜老伯,别管我,我能有办法的,你快走吧,救老田他们要紧!快走!快走!快走呀!”
矮胖子显然是想极力阻止姜耀成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因此,他拼命地挣扎着,一双手不停地乱打乱抓,甚至把手指戳进了杨金根的眼睛里。但他无论使多大的力气乱打乱抓,也无论抓哪里,打哪里,却总还是摆脱不了杨金根的控制。杨金根死死地抱住了矮胖子,就是不肯松手。他的眉毛紧紧地拧到了一起,牙关紧紧地咬着,双肩在不停地抖动,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流,一张脸几乎扭曲得认不出模样来了。显然,他在忍守着巨大的痛苦。那痛苦是一般人根本就无法忍受的,甚至是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的。
看到杨金根那样子,姜耀成受不了了,心里直想哭。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哭出来,强忍着眼泪,朝着李长亭的一连连部拼命地跑去了。
鸿门宴进行到最高潮了。高行渐用酒,几乎灌倒了宴会上所有的人。阚世模醉了,张颂臣醉了,阚式模带来的那些下属、卫兵也都醉了。醉了的人都在睡觉,有的趴在饭桌上,有的歪在椅子上,有的甚至躺倒在地上,七扭八歪,鼾声大作。
满屋里没有醉倒的只有几个人,那就是老田、高行渐以及高行渐的下属。高行渐的那几个下属都拿着匕首,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地守在门口和饭桌旁。
局面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高行渐也就开始明火执仗,公开露出强盗嘴脸了。他挪挪椅子,正面对着老田,鼻子眼里哼了哼:“嘿嘿,姓田的,今天这场戏,你没想到吧?”
老田在宴会开始时也喝了一些酒,但后来看出情况不对,就无论如何不肯喝了,高行渐也拿他没办法。他酒喝得少,因此头脑清醒。此时,他正襟危坐,眼睛望着远处。见高行渐对他说话,他便扫了一眼高行渐,不紧不慢地说:“是呀,来吃宴会的,却没想到看了一场戏!嗨,这世界呀,变化真快哟!”
高行渐神色一变,忽地高声嚷了起来:“变化太快?谁变了呀?老子变了吗?老子没变!老子从来就不同意投靠你们游击队的!”
“嚯嚯,不好意思,我的话可能没说清,高连长误会了,”老田笑笑,脸色平静如常,似乎丝毫也不在意高行渐那凶巴巴的样子和恶狠狠的言辞,“刚才我说世界变化太快,只是自己慨叹而已,并无明确所指,更没有指责你高连长的意思。高连长千万别误会啊!我们游击队的主张从来是一致的,你们投谁都可以,只要不跟日本鬼子走就行。不想投我们游击队,也不要紧嘛,我们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这一点,高连长尽可放心!高连长,现在是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我们应该齐心协力,一致抗日呀,对不对?只要那是一支抗日的部队,高连长愿意去投他,那也可以呀,我们支持!”
“是嘛,你这是真心实意?”
“当然是真心实意!”
“我们投国军,你也赞同?”
“赞同!”
“那我们要回江西呢?”
“可以呀,同样支持!”
“哼,说得好听!只怕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怎么不是真心话呢,我们的态度从来就是这样的嘛!”
“嘿嘿,真心话,鬼才信你的这些所谓真心话!你的真心话,就是要吞并我们阚团这支部队,”高行渐冷笑不止,“得了,得了,收起你的所谓真心话吧,老子忙得很,没时间听你的真心话了,跟你谈个正经事吧!”
老田眼一抬,望了望高行渐,一本正经地说:“好啊,既然有正经事要说,那就快说吧,我田默洗耳恭听就是了!”
高行渐抬起手,摸了摸自己那又短又大又红还长满疙瘩的鼻子,忽地向老田扫了一眼,慢吞吞地说:“跟你说实话吧,今天这出戏就是唱给你看的,目的嘛,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有合作的机会!”
老田笑了笑:“是嘛,想和我合作,那好啊!说吧,你想怎么合作呀?”
“怎么合作?这事简单,怎么合作都可以,只要你愿意,我愿意,咱们双方都愿意,事情不就行了嘛!我想啊,在当前,咱们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或者说主要有三条路可走。至于究竟怎么合作,那就得看你愿意选择哪一条路了!”
“哦,有三条路可走?那好吧,你说说看,具体都是哪三条路啊?”
“第一条路嘛,堪称最佳方案,”高行渐一边说,一边掰起了手指头,“具体来说,就是你我联手,立即发动兵变,控制阚团全部人马,并打下鬼子的军用仓库,用最好的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再伺机寻找新的驻地安营扎寨,扩充人马。第二条路嘛,就是你我联手,立即行动,秘密进军盘山,推翻那个姓余的,然后重组部队,由你当司令,我大哥当副司令,我来当参谋长。这条路嘛,也好走,算得上是不错的选择。第三条路嘛,就是由你出面,劝说我大哥回心转意,不投游击队,改投国军,并立即带部队东走平江,回江西另谋发展。这条路嘛,估计问题多一点,主要是我大哥的工作可能比较难做。但他很信服你和张老板,只要你们两个跟他好好说一说,他多半也会听的。当然,他万一不肯听,也不要紧,我有办法对付他。大不了,我把他软禁起来,裹挟着一起走不就行了。”
高行渐还在唾沫横飞地说个不停,老田却已眉头紧皱,脸色大变了。他冷不丁地打断高行渐的话,挥挥手说:“不行,不行,你这三条路都走不通!”
“走不通?怎么走不通?”高行渐瞪着大眼问。
“明摆着,你的这三条路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叛变!叛变是什么呀?是遭人唾骂,不齿于人类的丑恶行径!你想想,这样的事情我田默能做吗?”
高行渐愣住了,瞪大眼看着田默。愣了好一阵,他才回过神来,不冷不热地说:“我看你是个人才,有意跟你示好、靠近,没想到你却不知好歹!姓田的,事已至此,我是回不了头了,你也该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担忧啊!”
老田双手一摊,淡淡一笑:“前途、命运?国家残破如此,民族危亡在即,我田默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命运值得担忧啊?”
“难道命也不要了?”
“命?哼、哼,不瞒你说,我的命早就置之脑后了!”
“嚯嚯,那好,那你就做好准备吧,我成全你,亲自送你上西天!”
“上西天?行啊!来吧,我无须准备了,随时都可以动身!不过,在动身前,我还是要问你高连长一声:我死了,你还能活吗?”
“那就奇怪了,我能不能活跟你死有什么相关呢?”
“怎么不相关呢?明摆着,你只是二连的连长啊,无权代表阚团决定大事,对不对?我可不是你高行渐请来的客人,而是整个阚团请来的客人啊!你平白无故地把我这个阚团请来的客人一刀砍了,你那位大哥能饶得了你吗?一连、三连的士兵们能饶得了你吗?你自己的手下,二连的全体士兵能饶得了你吗?好吧,就说你这个当连长的有职有权,说了话,底下人不得不听,但你能保证他们在心底里绝对服你吗?倘若他们心里不服你,难道还会忠于你,心甘情愿地跟你走,为你卖命吗?”
“二连的人怎么不会为我卖命?哼,我在二连,那是有绝对权威的!不信,你问问他们!”高行渐手一抬,指了指站在一旁的士兵们。
老田一笑:“这时候问他们,那怎么能行呢?当着你的面,他们当然不敢说实话喽!高连长,你说你在二连有绝对权威,哼,这话真是自吹自擂、大言不惭哟,大概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谁都明白,人的权威不是靠职权人为树立起来的,而是靠做人行事,经过长久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你扪心自问吧,你的做人行事能使你确立起对二连全体士兵的绝对权威吗?你这一辈子做过足以确立绝对权威的事情吗?你的所作所为真的能够令人信服吗?高连长,我也不说别的了,只凭刚才你对我说的那一番话,特别是你说的那三条路,你就不是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男子汉、大丈夫……”
老田这一番话不软不硬,高行渐听了,不禁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士兵拿绳子捆老田。老田也不挣扎,任凭两个士兵拿着麻绳把自己捆在了椅子上。随即,高行渐又走了过来,用匕首顶住了老田的胸膛。
姜耀成跌跌撞撞地跑到一连连部,找到了李长亭。随即,李长亭又找到了阚副官。两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便急忙排兵布阵,由阚副官带一连包围二连营地,由李长亭带三连包围二连连部。他们还商定,行动要迅速,但也要高度保密,尽可能不动枪炮等武器,以免伤及无辜士兵和惊动日本鬼子。
李长亭很有经验,还没到二连连部,就派兵占领了制高点,控制了各交通要道。到二连连部门外后,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缴了岗哨和门卫的械,控制了关键地点和要害路口。随即,他又派兵把整个二连连部团团包围起来,并派人爬上屋顶,揭开几片屋瓦,对屋里的一切进行严密监视。
李长亭的这一切行动虽然十分谨慎、秘密,但却还是惊动了高行渐。高行渐抬头朝屋顶扫了一眼,突然把匕首往旁边的椅子上一放,迅速低头弯腰,从饭桌的一条腿上解下一根绳子来。他把那绳子捏在手里高高扬起,直起腰,对着门外大喊道:“李长亭,你来了是吧?嘿嘿,你来了,我不怕!你把全阚团的人都调来了,我也不怕!老子实话告诉你吧,我今天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包括死的准备。喂,你睁大眼好好看看吧,我手里拿的这根绳子是什么呀?嘿嘿,看不出这是什么吧?那好吧,我告诉你,这是炸药的引线!老子已经在这桌子底下安上炸药了。这炸药的威力可不小啊,足可以把这栋屋,连同屋里屋外的所有人,统统炸到天上去。你好好想想吧,是想死呢,还是想活?要想死呢,你就进来;要想活呢,那就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开!”
高行渐的这番举动,把李长亭镇住了。李长亭担心炸药爆炸会导致整个二连连部屋毁人亡,并引起日本驻军的注意,因而不得不有所顾忌。他愣了一下,便对士兵们挥挥手,示意他们往后退一退。然后,他走到门前,把脸贴在门框上,嘴巴对着门缝里喊了起来:“二哥,你别胡来啊!炸药一爆炸,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特别是伤着了大哥的性命,那可不是好玩的!真要是到了那时候,可就没办法挽回了,即便我要救你,可也救不了你喽,对不?咱们兄弟结义那么多年,同生死,共患难,感情深厚,胜过亲生,还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呀?你冷静点,听小弟一言,行吗?”
李长亭的话显然起了作用,高行渐不觉愣住了。他发了一会儿呆,便把引线往地上一扔,回身去拿放在旁边椅子上的那把匕首。那动作的意思很明显,是要重新拿起匕首来对付老田。高行渐手里没捏着炸药的引线了,这显然是个绝好的机会。老田看到这个机会了,心里不觉暗喜。他急忙一躬身站了起来,用脑袋对准高行渐的后腰猛地撞了过去。这一撞很有效,高行渐猝不及防,身子不觉往前一扑,顿时趴倒在地上了。但老田的身上绑着一把椅子,手、脚都无法自由行动。因此,在猛烈撞击高行渐的同时,他自己也不幸摔倒在地上了。
高行渐倒在地上了,却没有受重伤,身子依然灵活。他一翻身爬了起来,伸手就去抓那根引线,想引爆炸药。突然间,形势变得非常危急。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个人影忽地跃起,朝着高行渐猛扑过来,一下子就把他扑倒在地。这人影是张颂臣。实际上,他早就醒了。他深知自己年岁大了,难以和高行渐正面对垒,所以便假装睡觉,趴在桌上暗暗地寻找机会。这时见机会来了,他便趁机发起了进攻。
张颂臣扭住了高行渐,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高行渐的士兵们还来不及反应,李长亭便带着大队人马冲进来了。战斗很快结束,高行渐束手就擒。
阚式模的这一变化,人人见了都很高兴,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结义兄弟、二连连长高行渐。高行渐为人狠毒,阴险狡诈。他在江西时和红军打过不少仗,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怨,因此不愿意投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他曾经好几次找阚式模谈话,公开表达自己不愿意投靠游击队的主张。这时见阚式模和游击队越走越近,他心里不满,便暗暗地耍起了阴谋诡计。这天中午,他以庆贺自己四十五岁大寿为名,在他的二连连部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特地邀请阚式模和老田、张颂臣、姜耀成等人赴宴。这宴会名义上是庆生宴,实际上却是鸿门宴、逼宫宴,内里暗藏杀机,目的就是要借机杀掉老田、张颂臣、姜耀成和杨金根,彻底切断阚式模带领阚团投向游击队的路。
老田来阚团驻地没几天,跟高行渐没怎么打过交道,对他这个人了解不多,但对他举办的生日宴会却还是很有戒心的。临去赴宴之前,他特地把杨金根叫到一边,悄悄地叮嘱说:“对高行渐这个人,我们不熟悉,不能不有所戒备。他搞的那个宴会,你就别参加了吧!你留在外头,脑子活泛一点,多注意一下周边的情况。如果有事,或者发现了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你就赶紧去找阚副官和李长亭。这两个人还是比较可靠的。”
“是呀,人地生疏,情况复杂,戒备之心不能不有,我们确实要做好两手准备,”杨金根边说边点头,“对了,老田,这宴会你非得亲自参加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能不能找个理由把它推掉呢?张老板和姜老伯不是也要去嘛,让他们代表你敬杯酒,表达一下祝贺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老田摇摇头,轻声说:“阚式模去,我哪能不去呀!那会引起他们猜疑甚至不满的,对争取他们反正不利,明白吗?”
“非去不可的话,那就得格外小心了,尤其是要少喝酒,当心他下毒,”杨金根说,“对了,万一有事的话,我去哪里找阚副官和李连长呢?他们俩今天确定不参加宴会吗?”
老田用两目余光飞快地扫了扫四周,悄声说:“我问过李长亭和阚副官了。他们俩今天都有事,分不开身,不参加高行渐的宴会了。李长亭的事是带班值勤,多半会在一连连部或湘长公路附近。你去那里找他,准能找到。阚副官的事是带人巡视库房。我估计,他巡视的重点是军事装备库。因此,他不在军事装备库附近,便会在库房里面。”
叮嘱过杨金根后,老田又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地叮嘱了张颂臣和姜耀成几句,要他们少喝几杯酒,特别是要当心酒里有毒。
对老田的叮嘱,张颂臣不以为然。他大大咧咧地笑着说:“酒里下毒?借给他高行渐一百个胆,他也不敢!老田,你是不是小心得过了头呀?别忘了啊,咱们身边还有一个阚式模呢!阚式模可是咱们的保护神,关键时候能管用的。有他这位大哥在,高行渐那个当老弟的敢胡闹?哼,我看他没这个胆!”
“诸葛一生唯谨慎。张大哥,我看老田的想法对,多一分谨慎就多一分安全嘛,”姜耀成转脸看着张颂臣,一边说话,一边伸手摸摸下巴颏,“高行渐这人咱们不了解,天晓得他肚子里打的是什么算盘呀,对不对?我看呀,他把宴会放在他的连部办就值得怀疑。所以呀,咱们还是谨慎为妙。”
姜耀成的话显然动了老田的心。他眉头一紧,神情严肃地说:“是呀,高行渐怎么不把宴会摆在餐厅,却要摆在他的连部呢?哼,这事多少有些可疑之处,姜老伯说得对,咱们还是谨慎为佳,当心他‘项庄舞剑’!”
“什么‘项庄舞剑’!老田,我看你是太多心了。他是连长,在自己的连部举办宴会,这不也很正常嘛!嗨,算了,算了,你们要是实在害怕的话,那就去见一面,打个招呼,道声祝贺,然后就走人吧!我反正胆子大,什么也不怕,一个人留在宴会上和他们纠缠也没关系!”张颂臣说。他依旧大大咧咧,不大相信宴会上会出什么问题。
“我们见一面就走当然不行,酒还是要喝一杯的,”老田对张颂臣说。说完,他又转过脸来看着姜耀成,“姜老伯,小心使得万年船,咱们还是要做点预防。这样吧,咱们三个人分分工,我和张老板集中精力对付宴会,和他们纠缠,你就想办法早一点脱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
“哟、哟、哟,那不行,那不行,”姜耀成对着老田连连摇头,“咱们三个人中,数我的酒量最好,你们的酒量都不行。你和张大哥留下来对付宴会,那还不都得被他们灌倒了呀!算了吧,还是我留下来对付宴会,你和张大哥想办法尽早脱身吧!”
张颂臣撇撇嘴,笑了笑:“耀成老弟,不是老哥我自高自大,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不能走的。老田呢,他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也是不能走的。明摆着,老田是游击队的头,我是阚世模的恩人,都是宴会上的主客。你想想看,我们俩能抽身走人吗?我们俩要是走了,宴会上可就没有主客了,那阚式模该怎么想啊,高行渐又该怎么想啊?倒是你呢,情况和我们俩略略不同一点,完全可以去他娘一走了之。”
姜耀成抬头看看张颂臣,忽又低头沉吟:“是啊,大哥,你说的这情况我明白,可我心里不落忍啊!我这个最能喝酒的一走了之,却把你们两个不怎么能喝酒的留下来让他们灌酒,这、这不像话吧!”
“嗨,你哪是一走了之呢!刚才老田不是说了嘛,他是要你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的,那可是重大的责任啊,”张颂臣伸出手来,在姜耀成的肩头上拍了拍,然后又指了指自己衣服上的袖口,“好了,好了,别多虑了,我和老田又不是傻子,哪会那么容易让他们灌倒呢!嘿嘿,等会儿喝酒呀,我不拿嘴喝,就拿这只袖子喝,全他娘的往这只袖子里倒,看他娘的高行渐究竟能有多少酒倒进我这袖子里来!”
宴会上的明争暗斗还在酝酿,屋外的剑拔弩张却已经开始了。杨金根正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四个人迎面朝他走过来了。那四个人自称是阚团二连的战士,奉高行渐连长的命令来请他喝酒。杨金根是从来不喝酒的,当时便拱拱手,客客气气地回绝说:“对不起,我是滴酒不沾的,扫四位仁兄的兴了,请多原谅!”
“滴酒不沾?怎么可能呢?当兵的哪有不会喝酒的呀!”一个高个子士兵说。四个人的个头都比杨金根高,而这个高个子士兵的个头尤其高,差不多比杨金根高了一个脑袋。
杨金根仰头看了高个子士兵一眼,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说:“也许是天生的吧,我从小就不能喝酒,学都学不会。”
“喝酒都学不会?哼,我不信!”高个子士兵摇摇头,撇撇嘴。
站在高个子士兵旁边的,是一个年纪略大些的矮胖子。这时,他斜眼一瞟杨金根,开口说话了:“嗨,不会喝酒也没关系嘛,茶总会喝的吧?走吧,杨老弟,别借故推辞了,和我们一起去坐一坐,喝杯茶吧!坐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天,也不错呀,对不?”
杨金根抬眼看了看那个矮胖子,作古正经地说:“茶嘛,倒是可以喝的,不过这时候我不得空。这样吧,改天我请你们喝茶,行吗?今天嘛,我实在没时间,就只好对不住了。四位仁兄,请自便吧,恕小弟不能奉陪了!”
“坐在一起喝杯茶都不肯?哼、哼,看来你是存心要驳我们的面子喽!”矮胖子带着浓重的鼻音说。他的脸色开始变了,渐渐地由青变红。
“嚯嚯,仁兄误会了,误会了,不是小弟我存心要驳面子,而是真的有事分不开身,请多原谅,请多原谅!”杨金根抱拳作揖,抽身便走。
但杨金根想走,这时候也走不成了。那四个当兵的一拥而上,把他围在了垓心。杨金根拿眼扫了扫那四个当兵的,心里有些诧异,但却绝没有慌张。
“你们四位这是唱的哪一出呀?”杨金根淡然一笑。
矮胖子显然是个当头的,身上挎着盒子枪,脸上也带着一股子傲慢的官气。他一边拿眼扫向四周,指挥着其他几个当兵的,一边阴笑着说:“哪一出?《十字坡》呗!想借你的肉蒸几个人肉包子吃呀!嘿嘿,杨老弟,我们晓得你是条好汉,今天要你死也多少有些冤枉,但没办法,上命差遣,不得不为,你别怨恨我们哥儿几个哟!”
“哦,你们几个原来是想吃人肉包子,所以特地来找我麻烦的,”杨金根一边说,一边笑,“嗨,我还正愁没事干,打发不了这空闲日子呢,没想到你们哥儿几个倒主动送上门来陪我玩了!好吧,话都已经挑明了,那就来吧,还等什么呀?”
打斗很快就开始了。四个当兵的把杨金根围在中间,一个个伸拳踢腿,张牙舞爪,好不威风。高个子士兵劲头最足,先上。他从右侧开始进攻,一个箭步蹿了上来,猛地抓住了杨金根的右胳膊。紧跟着,一个嘴巴边上长着一道长长白疤瘌的士兵又从左侧开始进攻了,一上来便抓住了杨金根的左胳膊。杨金根的左右两只胳膊都被抓住了,情况似乎很不妙,但他自己却毫不在意,兀自若无其事地左看看,右看看,连连冷笑不止。高个子和白疤瘌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容易得手,因此脸上都开始泛出一丝洋洋自得的神色。但他们的得意劲实在是来得太早了,嘴巴还没来得及张开笑一笑,情况就突然变了。杨金根开始行动了,他身子往下一沉,再往后一缩,不知不觉间,整个人便一下子退到了高个子和白疤瘌的后面。紧跟着,他伸出一只手顶在高个子的后腰上,把另一只手按住白疤瘌的背部,然后两手一齐发力,高个子和白疤瘌便不由自主地往前冲,面对面地贴在一起了。两个大男人面对面地贴在一起,这样子显然既不雅观,又不好受。高个子的下巴颏磕在白疤瘌的脑门上了,白疤瘌疼得眼泪直流。白疤瘌的脑袋撞到高个子的胸部上了,高个子就像五脏六腑都被人掏掉了一般,好半天喘不过气来。
兵油子果然不一般,吃了亏就能长记性。这回轮到矮胖子和另一个士兵上了。那另一个士兵是个朝天鼻,两个鼻子眼没朝下,而是朝前,就像猪鼻子眼一般。矮胖子对朝天鼻使了个眼色,朝天鼻便对着杨金根扑上来了。他显然是吸取了高个子和白疤瘌的教训,虽然往前扑,却只不停地在杨金根的下三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撩拨,不肯靠近杨金根的身子。这动作很明显,目的在于引开杨金根的注意力,以便为其他人进行偷袭创造条件和机会。果然,没过多久,偷袭就开始了。进行偷袭的是矮胖子本人,他终于亲自动手了。只见他左腿往前一迈,身子急速旋转,右腿忽然一伸,脚尖猛地朝杨金根的裆下踢来。这是一招旋风腿,杨金根自然晓得。见矮胖子的脚尖急速踢来,他不仅不躲避,反倒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往下轻轻一捞。他这种捞法很独特,不显山不显水的,毫不引人注意,但却极有效,一下子便把矮胖子的那只脚捞在自己手中了。紧接着,他抓住矮胖子的脚掌猛地往前一送,矮胖子就站立不稳了,很快便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
两次进攻,两次都遭到了惨败,但矮胖子和他的同伴们却还不想放手。很快,他们又开始组织新的进攻了。不过,他们这一次进攻与上两次显然不同,既没有明确的分工,又没有精心的准备。矮胖子只是挤挤眼,呶呶嘴,算是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四个人便一起动手,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朝着杨金根狠狠地扑过来了。紧接着,他们就抱的抱腿,搂的搂腰,掐的掐脖子,死死地缠住了杨金根。这做法毫无章法,是上不得台面的,说白了不过就是流氓混混打群架,耍无赖。但这做法却对人多的一方有利,可以浑水摸鱼,趁乱取胜。杨金根没想到他们会采取这种流氓做法,事先不曾防备,因此动作慢了些,吃了一点亏。四个人一缠上身,他就明显处于不利局面了。他的手被人死死地抓住了,有劲使不出。他的腿被人牢牢地抱住了,有力踹不动。他的脖子被人紧紧地勒住了,连呼吸都畅快不起来。“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此时此刻,杨金根的心里就充满了被犬欺的感觉。
杨金根的心里虽然很不是滋味,但却没有着急,没有慌张。他是一个稳重人,沉得住气,甚至是越到急时还越有主意。他干脆手脚、身体都不动了,任凭矮胖子他们胡乱折腾。然而,他身体、手脚不动,心里却五时无刻不在紧张地思索着脱身的办法。他信心很足,觉得自己一定能够尽快地想出脱身的办法来。果然,他很快就想到办法了。他看到高个子的脑袋就在自己的头顶上方,下巴颏差不多挨着自己的脑门了,便悄悄地往下缩了缩身子,把全身力道凝聚到脑袋上,然后猛地使劲往上一顶。杨金根的这一顶力道极大,高个子的下巴颏和牙齿直接受到了沉重而猛烈的撞击,一阵阵巨大的疼痛立马袭上心头。高个子受不了了,不知不觉地松开了原本死死勒住杨金根脖子的那只手。
高个子的手一松开,杨金根的脖子就能活动自如,自由呼吸了。他感到了一阵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痛快,不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当此之时,稍有松懈,便可能会导致生命之忧的。因此,他片刻不敢停留,很快又开始了新的动作。高个子松手后,身体稍稍往后退了退。这就给杨金根留下了一些活动空间。杨金根的新动作,就是利用高个子留出的这一点点活动空间做文章。只见他两腿朝前猛地一蹬,双手使劲往后一拽,整个身子忽然往上一窜,然后又直直地往后倒了下去。很快,他便倒在地上了,四仰八叉,双眼望天。但这时杨金根倒在地上了,矮胖子、白疤瘌、朝天鼻也都倒在地上了。他们三个人原本是抱住杨金根的胳膊和大腿的。显然,他们的倒下完全是杨金根倒下时连带所致。杨金根运用借力打力的武术招式,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倒下时所形成的巨大惯性和重力,因而连带着把矮胖子、白疤瘌、朝天鼻他们三个人拖倒在地上了。
杨金根身体灵巧,一挺身就站起来了,但矮胖子他们却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杨金根拍拍身上的泥土,望着矮胖子他们笑了笑,不慌不忙地说:“四位仁兄,今天玩得还算痛快吧?要不要再玩玩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用的那招式也是入不得流的,胜之不武哟!不过,我这么做,也确实情有可原,迫不得已呀,谁叫你们用无赖流氓小混混打群架的方式来对付我呢!嘿嘿,咱们这就算扯平了吧,不打了,行不行呀?说实在的,就你们这能耐,别说四个人了,再来四个,也奈何不了我的。你们大概还不清楚吧,刚才我可是网开一面,没跟你们玩真的哟!要是玩真的,你们的小命只怕早就到阎家五爹那里报到去了,哪还有留在人间吃饭穿衣、拉屎撒尿的份儿呀!嗨,不说了,不说了,你们也可怜,人家要你们来杀我,你们就不得不来;可你们要想杀人吧,却又没那本事!算了,算了,我也晓得你们的苦处,不和你们为难了,你们爬起来走人吧!”
杨金根满以为自己很大度,矮胖子他们应该不会再纠缠了。因此,说完话,他转过身来,拔腿便走。但他刚刚迈开腿,还没走出三五步,矮胖子他们便一拥而上,把前后左右都堵住了。而且,他们每个人的手中还多了一样家伙——匕首。
“嚯嚯,想开溜?害怕了吧?”矮胖子一边说,一边晃晃手中的匕首。
杨金根扫一眼矮胖子,似笑不笑地说:“害怕?哼,我生来就胆大,至今还没搞清‘害怕’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呢!”
“不害怕,怎么要走呀?”高个子眯眯眼。
“那还不明白呀,觉得你们的这些小混混招式太低级,太下流,懒得跟你们玩了呗!”杨金根淡淡地一笑。
“懒得跟我们玩?哼,恐怕是害怕跟我们手中的这家伙玩吧?这家伙挺好的,很锋利,还是头次用,没见过血的呢!嘿嘿,没想到,它今天要在你身上派上用场了!”高个子眼睛盯着匕首,忽然把它往上一抛,然后又伸手接住。
“嘿嘿,你说的还真是没错,”杨金根看看高个子,“我还真是有些怕匕首呢!”
“瞧,说实话了吧,你小子果然是怕我们手中的匕首!”高个子哈哈大笑了,眉毛、眼睛、鼻子、嘴扯到了一起,一张脸皱皱巴巴的。
“不过,你搞清楚了啊,”杨金根盯着高个子,“我说怕匕首,可没说怕你们!我怕匕首,不是怕你们用匕首杀了我,而是怕我自己不小心用匕首误杀了你们,明白吗?”
“嘿嘿,你胡说,你胡说,”高个子晃动着手中的匕首,连声大喊,“匕首在我们手里拿着,你还能用来杀我们?哼,你没那本事!”
“是嘛,你不相信我有这本事?好吧,那你就等着吧,我可是不客气了啊,要动手了啊!”杨金根边说边挪动脚步,身子朝高个子站的那方向晃了晃。
杨金根这一动,高个子沉不住气了,脸色立时大变,两条腿也开始颤抖起来。他还以为杨金根真的是在瞄准他,要先拿他开刀呢!
其实,杨金根并没有真动。他只不过是做了个假动作而已。此时此刻,他并没有要和矮胖子他们真打真拼、一决生死的想法。矮胖子他们已经凶相毕露,誓要将他杀之而后快了,他为什么还没有和他们真打真拼、一决生死的想法呢?是害怕他们吗?当然不是!是害怕他们手中的匕首吗?当然也不是!他没这想法,完全是因为心中有所顾忌。
杨金根心中的顾忌是什么呢?这顾忌,来源于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处的特殊场合、特殊环境。问题很明显,他不是阚团的人,而是阚团请来的客人;并且,他还不是主要的客人,而只是主要客人的随从、护卫。因此,在这个环境里,他没有多少说话、行事的权利,必须处处受制约,事事听命于人,时时小心在意。四个人,四把匕首,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很容易打发,但他有权利打发吗?
望着矮胖子他们手中捏着的匕首,杨金根的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地琢磨起来了:“徒手搏斗,用力或轻或重,倒还能随意掌控,不至于轻易伤人性命。但若是用上匕首一类武器来,那还能随意掌控得住吗?枪炮无眼,匕首也是没长眼的呀!在搏斗中,他们要杀我,那是不可能的,但却难保我不会误杀他们呀!要是我一不留神,误杀了他们,或是让他们受了伤,见了血,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倘若因为自己的误杀而引起了阚团其他战士的愤怒,导致他们一拥而上,集体跟自己作对,自己能够对付得了吗?倘若因为自己而导致阚团跟游击队反目了,使得阚团反正的事泡了汤,那自己不是犯下滔天大罪了吗?倘若把事情闹大了,搞得不好收拾,自己怎么面对老田呀?怎么面对张老板和姜老伯呀?怎么回盘山去见老余和游击队的同伴们呀?”
这样一琢磨,杨金根终于下定决心了。他要以忍为上,一忍到底,通过躲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脱离是非之地。于是,他一纵身,跃上了旁边的一棵树。那树很高,也很大,有很多树杈。他就像玩单杠似的,先跃上一根树枝,再从那根树枝上爬到了一个树杈上。然后,他就坐在那树杈上不动了,静静地看着树下的四个人。
杨金根上树了,匕首够不着他了,矮胖子他们便着急了。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骂了起来,从杨金根的祖宗骂到杨金根本人,又从杨金根本人骂到游击队和共产党。杨金根却不管他们骂什么,只一门心思坐在树杈上不理不睬,闭目养神。
骂了一阵,矮胖子他们忽然不骂了,又纷纷低头弯腰,捡起了地上的石头。他们把大大小小的石头捡了起来,拿在手里,瞄准了树上的杨金根使劲砸,想把他砸下来。但他们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扔上去的石头既没多大准头,又没多大力道,哪能把杨金根那么灵活的人砸得下来!而且,他们一扔石头,反倒给杨金根提供了武器。杨金根顺手一捞,就把他们扔上来的石头捞在手里了。然后,他再拿着这些石头,照准矮胖子他们使劲扔。杨金根人在高处,石头由上往下扔,准头大,力道也大。结果,他扔的那些石头大半都砸到了矮胖子他们的身上,砸得他们鼻青脸肿,哭爹叫娘。
砸石头不管用了,矮胖子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从库房里找出几根长竹竿,每人发一根,然后就拿着这些长竹竿使劲往上戳,想把杨金根从树上戳下来。但这办法也没用,杨金根左一窜,右一跃,爬到了大树的最高处,长竹竿就全都够不着了。
办法都用尽了,杨金根却坐在树顶上稳如泰山。矮胖子着急了,搓着手,自言自语道:“这、这、这怎么办呢?哎呀——”
白疤瘌忽然走了过来,低头悄声说:“嗨,副排长,你不是带着枪嘛!有这玩意在,你还犯哪门子愁啊?给他一枪,不就得了?”
矮胖子原来是个副排长。他摸摸别在腰上的手枪,皱皱眉头说:“嗨,这办法我也不是没想过,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敢这么做呀!高连长叮嘱过,库房重地,附近又有日本人,枪是不能随意开的。再说,咱们离一连、三连都不远,也怕惊动他们呀,对不?他们人多,一旦枪声惊动了他们,那可就麻烦了——”
“哦,那倒也是,那倒也是,”白疤瘌连连点头,“那、那弹弓行不行呀?我倒是有几副好弹弓,平时拿着打鸟玩的,力量蛮足——”
白疤瘌这一说,矮胖子立马来了精神。他挤挤眼,把嘴巴贴到白疤瘌耳朵根子上说:“弹弓?哼,那玩意没准行。这样吧,你这就去拿弹弓,我们在树下守着,谨防他跑了!”
矮胖子和白疤瘌在树下鬼鬼祟祟,引起了杨金根的注意。他蹲在树杈上琢磨开了:“这两家伙耍什么名堂呢?该不是要去拿枪吧?他们要是用枪,那我就麻烦了。四条枪一齐放,我还不得被打成筛子?我死倒不要紧,可老田他们怎么办呢?老田可是叮嘱过我的呀,要我有事时就赶紧去找阚副官和李长亭。现如今还真是有事了,我怎么能傻呆呆地蹲在树杈上等着矮胖子他们开枪呢?高行渐那王八蛋的宴会肯定有阴谋。这会儿,老田他们只怕早就遇上麻烦了。不行,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得赶紧走,得赶紧找阚副官和李长亭去!”
一想起老田在宴会上可能遇到麻烦了,杨金根的心里就起急。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手一伸,脚一蹬,就飞快地在树上爬了起来。那棵树紧挨着一栋房子。他三下两下就爬到了临近那房子的一根树枝上。他抓住那树枝,身子像荡秋千那样往下一荡,两只脚就稳稳当当地落在屋顶上了。到了屋顶上就好办了。他的轻功好,在屋顶上奔跑如履平地。他直起身子,看了看四周的地形,然后就沿着屋脊一溜烟地跑了杨金根猜得没错,老田他们在宴会上早就遇到麻烦了。
麻烦是从喝酒开始的。高行渐派了五个大兵上场。那五个大兵都是酒量大得吓人的酒鬼。他们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大碗里都盛满了度数高得惊人的白酒。他们端着大碗酒沿着桌子转,逢人必敬,敬则必喝。谁要是不喝,他们就站在你身边不依不饶地劝,无休无止地说,甚至怪腔怪调地唱,搞得你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那些酒没有下毒,但由于度数很高,喝多了,人自然也就跟中毒差不多了。
阚式模酒量不小,酒胆也大。他是只要有人敬酒,就必喝无疑的,从来不会耍赖推酒。所以没多久,他就喝得多了,脸红耳热,醉眼迷离,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张颂臣虽说大大咧咧,不大相信宴会上有阴谋,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起了戒心。他打定了用袖子装酒的主意,有人敬酒,他就喝,但不往下咽,等人不注意时,再回头悄悄地吐到袖子里。这主意倒也起作用,高行渐敬了好几轮酒,他居然脸不红,耳不热,就跟没喝酒一般。但这办法虽然有效,却长久不了,因为那时是热天,张颂臣只穿着一件单衣,薄薄的一层棉布根本就存不住很多酒。
果然,没过多久,张颂臣的高招就不灵了。他衣袖里的酒不停地往下滴,滴到了一个敬酒大兵的脚上,那大兵立马叫喊起来:“张老板,你这袖子里怎么滴水呀?”
敬酒大兵的叫喊,引起了高行渐的注意。他走过来,扯起张颂臣的衣袖一看,当时就嚷嚷道:“哟,张老板,你那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也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呀?不行,不行,得罚,得罚,罚三大碗!不,得罚四大碗!”
高行渐当时就把那几个敬酒的大兵喊过来罚张颂臣喝酒。张颂臣没办法推辞了,只得一碗接一碗地喝了起来。
张颂臣的高招败露了,高行渐对老田和姜耀成喝酒的监督也更严了。没办法,他们俩也只得老老实实地喝起酒来。这形势自然是很不妙的。老田深感忧虑,悄悄地在桌子底下用脚捅了捅姜耀成。这意思很明显,是在催促姜耀成赶紧想办法逃离宴席。
姜耀成也觉得是该逃离宴席的时候了,脑子急速地转动起来。忽然间,一个大兵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鲜鱼汤端上了桌。姜耀成一见,立马计上心头。他拿起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小碗鲜鱼汤,就低头猛喝起来。那鱼汤很烫,姜耀成喝得很急,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了。
“哎呀,太好喝了,太好喝了,我生平最爱喝的就是鱼汤,而且还特别爱喝刚出锅的滚烫的鲜鱼汤!”姜耀成自顾自地喝着鱼汤,而且还边喝边说,一个劲地为鱼汤叫好。
喝了一阵鱼汤,姜耀成忽然停下来了,开始猛烈咳嗽。他抬起头,张着嘴,皱着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样子十分痛苦,似乎是鱼汤或者花椒等什么作料呛到气管里去了。一个大兵拿着一条毛巾走了过来。他见了,一把夺过那毛巾来,便急不可耐地往鼻子上捂。他一边用毛巾捂住鼻子,一边猛烈地咳嗽,一边还时不时地低下头,朝地下啐唾沫。这狼狈、肮脏的情况,谁都是不愿看的,人们纷纷扭转脸向着别处。趁着这功夫,姜耀成悄悄地松开毛巾一角,把一根牙签伸进鼻孔里捅了几下。这一来,他的鼻子便很快出大问题了,鲜血直流,喷嚏不断,唾沫横飞,狼狈不堪。
姜耀成这出戏实在演得太逼真了,瞒过了所有的人。顿时,宴会厅里喊的喊,叫的叫,人人手忙脚乱。高行渐张罗着要派人去喊医生。阚式模一挥手,把他阻住了。阚式模虽然酒喝得多,已经有些醉意,却还没有醉倒。他东倒西歪地走到姜耀成面前,伸手拍拍他的肩头,结结巴巴地说:“姜、姜老伯,别、别着急,肯定是胡、胡椒呛到鼻子眼里了,没、没什么大事的。你、你到外面去擦、擦把脸,洗一洗,把那粒胡、胡椒抠、抠出来,再、再去茅厮屋(厕所)里屙沱尿,就、就万、万事大、大吉了!”
阚世模说话了,其他人就不好说什么了。姜耀成就像遇上了大赦令,心里高兴不已。他一躬身站了起来,朝阚式模弯弯腰,又朝高行渐点点头,捂着鼻子就往外走。
见姜耀成往外走,高行渐连忙扒拉一下身边的一个大兵,低声喝道:“快去看住他,别让他跑了!他要是跑了,老子要你的命!”
厕所就在附近不远,那地方还很僻静。姜耀成一口气跑进厕所,转身躲到了门后。没多久,那大兵也跑来了。他站在门口欲进不进,不住地伸头张望。姜耀成见机得快,趁着他把脑袋伸进来张望时,便全身顶住门板,使狠劲猛地一推。这一下起作用了,那大兵“唉哟”一声,往后便倒。见那大兵倒在地上了,姜耀成忙从厕所里跑了出来,抱起一块大石头,对准他的脑袋,就狠狠地砸了下去。
接连挨了两次重力打击,那大兵晕过去了,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姜耀成朝他看了一眼,双手合十,默默念叨道:“惭愧,我姜耀成活到今天,也已六十有五了,还从来没跟人打过架呢,更别说杀人了。今日之事,实是迫不得已,只好请你原谅了!”
姜耀成默默地念叨了一番,又朝着那大兵鞠了几个躬,便转身走了。
杨金根还是没能摆脱矮胖子他们的纠缠。矮胖子他们熟悉地形,早就抄近路躲在一个地方了。那地方是杨金根的必经之路,非常隐蔽,杨金根看不到。因此,当杨金根一纵身从屋顶上跳下来时,很快便遇到了防不胜防的猛烈进攻。
首先发起进攻的是朝天鼻。他就躲在杨金根站的那个屋檐下,离杨金根非常近。杨金根一落地,脚还没站稳,朝天鼻就抡起一根粗大的木棍从左侧狠狠地扫了过来。那木棍扫着了杨金根的左腿膝盖。杨金根膝盖受伤,站立不稳,扑地便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发起进攻的是高个子。他就站在杨金根的右侧身后,挥舞着匕首扑了过来。杨金根正要起身,无奈腿受了伤,一时站不起来,结果被他刺中了一刀。那一刀刺进了右侧腰部,伤口很深,血流有如泉涌。两次受伤都很重,杨金根终于站不起来了。
见杨金根站不起来了,朝天鼻不觉大喜过望。他挥舞着那根粗大的木棍,又狠狠地扑了过来。这一回,杨金根有防备了。见木棍快近身了,他便伸出左手抓住,然后再使劲一拽,立马就把朝天鼻拽到了自己跟前。说时迟,那时快,杨金根右手一伸,叉开五指,忽地掐住了朝天鼻的脖子。这一下,朝天鼻就再也没有活路可走了。杨金根掐住他的脖子使劲一捏,再忽左忽右地拧几下,朝天鼻就不能动弹了。
杨金根在全力对付朝天鼻时,高个子就想乘机偷袭。他轻手轻脚、鬼头鬼脑地潜到杨金根身后,忽地一扬匕首,照准杨金根的后背就狠狠地戳了下来。他满意为自己的算计高明,杨金根不死也得重伤。但他的想法错了,杨金根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当匕首戳来,快要触及到后背时,杨金根忽然头一偏,身子一转,整个人就躲到朝天鼻的身后了。他用手捏住朝天鼻的脖子,把朝天鼻的躯体送到了高个子的匕首面前。高个子用力过猛,那匕首收不回来,整个地戳进了朝天鼻的后背。
眼见自己的匕首刺进了同伴朝天鼻的体内,高个子大吃一惊。他颓丧极了,正想拔出匕首再和杨金根决一死战时,情况忽然又变了。杨金根没等他拔出匕首,猛地一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杨金根的手劲大极了,高个子根本无力反抗。他折腾了几下,就再也折腾不起来了。杨金根终于用同一个方法干掉了两个敌人。
两处伤口都很疼,血也流得不少,但杨金根丝毫也不觉得难受。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他杀掉了两个敌人。“以两处伤口换两个敌人的性命,哼、哼,怎么说,这买卖也值!”他这样想着,不觉悄悄地乐了。
近处有一张门,门口有一道台阶。杨金根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地往前爬着,想爬到那台阶上歇一歇,脱下衣服,撕块布,包扎一下伤口。但就在这时,一粒石头子忽然飞来,打在了他的胸部上。那石头子不大,力道却不小,他的胸口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好像是弹弓打的,谁在打弹弓呢?”杨金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仰头向远处张望。很快,他就发现那打弹弓的人了。那人是白疤瘌。他正拿着弹弓洋洋得意呢。
“娘的,有你好看!”杨金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忽地一扬手,把手中捏着的那粒石头子扔了出去。那石头子飞得极快,刹那间就飞到了白疤瘌身边,一下子打中了他的右眼。这一下,白疤瘌的眼睛受伤不轻。他捂着眼睛哭爹叫娘,跌跌撞撞地跑了。
“嘿嘿,今天的买卖还行,打倒三个了!”杨金根乐了,脸上带着笑。但没过多久,他又收住笑,脸上显得十分严肃,嘴里也不住地自言自语起来:
“不对呀,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的,怎么这里只看见了三个呢?不是还有一个矮胖子嘛,他好像还是个头呢,这会儿躲到哪里去了?不行,我得慎重点,小心那王八蛋搞偷袭!”
杨金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眼四处张望。忽然,眼前一闪,路口跑过来一个人。他一惊,以为是矮胖子,连忙抄起那根粗木棍准备战斗。但就在这时候,那人突然停住不跑了,朝他喊了起来:“哟,金根,你怎么在这里呀?”
杨金根抬眼一看,原来那人是姜耀成。他又惊又喜,忙问:“姜大伯,你要去哪里呀?”
姜耀成小心翼翼地朝前后左右望了望,压低声音说:“老田他们有危险了,我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你怎么在这里待着呀?唉呀,你负伤了吧,流了那么多血!”
“我也是要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的,遇到了他们的截杀,所以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纠缠了老半天,”杨金根用手指指躺在地上的白疤瘌和高个子,“结果呢,他们完了,我自己也受伤了。唉,这伤看来还不轻,我这阵子站都站不起来了。得了,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老伯,你走吧,赶紧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
“我走?我走了,你怎么办?你可是伤得不轻啊,”姜耀成一边说,一边向杨金根靠近,“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把伤口包一包,再去找他们!”
“不、不、不,伤口不要紧,我自己能包,用不着你帮忙!你快走,别磨蹭!再磨蹭下去,老田他们就危险啦!”杨金根一边说,一边挥手。
姜耀成也晓得情况万分紧急,片刻耽误不得了。他转过身,边走边说道:“那好,我走了,你多保重,我过一会儿就来找你!”
姜耀成走了。但他刚走没多久,就遇到麻烦了。矮胖子来了,在路口堵上了他。姜耀成毕竟年纪大了,又没经过军事训练,哪里是矮胖子的对手。矮胖子拿着寒光闪烁的匕首,恶狠狠地扑向姜耀成,只三两招就把他逼得浑身大汗淋漓了。
路口的打斗声引起了杨金根的注意。他知道姜耀成遇上麻烦了,想去帮他解围,却又苦于自己站不起来,不觉急得心里直冒火,两只手不停地搓着,嘴里还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他娘的,这、这可怎么办呢?有劲使不上,干着急呀!”
杨金根真是一个智多星,再急的时候也能想得出主意来。突然,他不嚷嚷了,朝着打斗的方向喊了起来:“姜大伯,你快过来帮帮忙,我、我这伤口的血止不住了!唉哟,唉哟,他娘的,这伤口怎那疼啊?”
杨金根这是在用调虎离山计,目的在于通过招呼姜耀成而把矮胖子引过来,以便自己的一双手能够抓住或者打着矮胖子。姜耀成不知是计,还真以为杨金根的伤口止不住血呢。听到杨金根的喊声,他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了。矮胖子更搞不明白杨金根的心思。见姜耀成往杨金根的身边跑,他也就跟着跑过来了。见矮胖子跑到自己身边了,杨金根不觉大喜,手一伸,抓住他的一条胖腿便使劲一拽。杨金根这一拽,完全出乎矮胖子的意外。矮胖子毫无防备,立马仰面朝天地栽倒在地了。这时,杨金根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忽地两手一撑,身子高抬,朝着矮胖子压了过来,一下子便把他压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
矮胖子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身子被压住了,手脚却片刻未停。他和杨金根死死地纠缠在一起,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难分胜负。姜耀成见杨金根身上有伤,担心他吃亏,便想上来帮忙。但杨金根却不要他帮忙。他对着姜耀成连声大喊:“姜老伯,别管我,我能有办法的,你快走吧,救老田他们要紧!快走!快走!快走呀!”
矮胖子显然是想极力阻止姜耀成去找李长亭和阚副官。因此,他拼命地挣扎着,一双手不停地乱打乱抓,甚至把手指戳进了杨金根的眼睛里。但他无论使多大的力气乱打乱抓,也无论抓哪里,打哪里,却总还是摆脱不了杨金根的控制。杨金根死死地抱住了矮胖子,就是不肯松手。他的眉毛紧紧地拧到了一起,牙关紧紧地咬着,双肩在不停地抖动,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流,一张脸几乎扭曲得认不出模样来了。显然,他在忍守着巨大的痛苦。那痛苦是一般人根本就无法忍受的,甚至是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的。
看到杨金根那样子,姜耀成受不了了,心里直想哭。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哭出来,强忍着眼泪,朝着李长亭的一连连部拼命地跑去了。
鸿门宴进行到最高潮了。高行渐用酒,几乎灌倒了宴会上所有的人。阚世模醉了,张颂臣醉了,阚式模带来的那些下属、卫兵也都醉了。醉了的人都在睡觉,有的趴在饭桌上,有的歪在椅子上,有的甚至躺倒在地上,七扭八歪,鼾声大作。
满屋里没有醉倒的只有几个人,那就是老田、高行渐以及高行渐的下属。高行渐的那几个下属都拿着匕首,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地守在门口和饭桌旁。
局面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高行渐也就开始明火执仗,公开露出强盗嘴脸了。他挪挪椅子,正面对着老田,鼻子眼里哼了哼:“嘿嘿,姓田的,今天这场戏,你没想到吧?”
老田在宴会开始时也喝了一些酒,但后来看出情况不对,就无论如何不肯喝了,高行渐也拿他没办法。他酒喝得少,因此头脑清醒。此时,他正襟危坐,眼睛望着远处。见高行渐对他说话,他便扫了一眼高行渐,不紧不慢地说:“是呀,来吃宴会的,却没想到看了一场戏!嗨,这世界呀,变化真快哟!”
高行渐神色一变,忽地高声嚷了起来:“变化太快?谁变了呀?老子变了吗?老子没变!老子从来就不同意投靠你们游击队的!”
“嚯嚯,不好意思,我的话可能没说清,高连长误会了,”老田笑笑,脸色平静如常,似乎丝毫也不在意高行渐那凶巴巴的样子和恶狠狠的言辞,“刚才我说世界变化太快,只是自己慨叹而已,并无明确所指,更没有指责你高连长的意思。高连长千万别误会啊!我们游击队的主张从来是一致的,你们投谁都可以,只要不跟日本鬼子走就行。不想投我们游击队,也不要紧嘛,我们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这一点,高连长尽可放心!高连长,现在是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我们应该齐心协力,一致抗日呀,对不对?只要那是一支抗日的部队,高连长愿意去投他,那也可以呀,我们支持!”
“是嘛,你这是真心实意?”
“当然是真心实意!”
“我们投国军,你也赞同?”
“赞同!”
“那我们要回江西呢?”
“可以呀,同样支持!”
“哼,说得好听!只怕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怎么不是真心话呢,我们的态度从来就是这样的嘛!”
“嘿嘿,真心话,鬼才信你的这些所谓真心话!你的真心话,就是要吞并我们阚团这支部队,”高行渐冷笑不止,“得了,得了,收起你的所谓真心话吧,老子忙得很,没时间听你的真心话了,跟你谈个正经事吧!”
老田眼一抬,望了望高行渐,一本正经地说:“好啊,既然有正经事要说,那就快说吧,我田默洗耳恭听就是了!”
高行渐抬起手,摸了摸自己那又短又大又红还长满疙瘩的鼻子,忽地向老田扫了一眼,慢吞吞地说:“跟你说实话吧,今天这出戏就是唱给你看的,目的嘛,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有合作的机会!”
老田笑了笑:“是嘛,想和我合作,那好啊!说吧,你想怎么合作呀?”
“怎么合作?这事简单,怎么合作都可以,只要你愿意,我愿意,咱们双方都愿意,事情不就行了嘛!我想啊,在当前,咱们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或者说主要有三条路可走。至于究竟怎么合作,那就得看你愿意选择哪一条路了!”
“哦,有三条路可走?那好吧,你说说看,具体都是哪三条路啊?”
“第一条路嘛,堪称最佳方案,”高行渐一边说,一边掰起了手指头,“具体来说,就是你我联手,立即发动兵变,控制阚团全部人马,并打下鬼子的军用仓库,用最好的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再伺机寻找新的驻地安营扎寨,扩充人马。第二条路嘛,就是你我联手,立即行动,秘密进军盘山,推翻那个姓余的,然后重组部队,由你当司令,我大哥当副司令,我来当参谋长。这条路嘛,也好走,算得上是不错的选择。第三条路嘛,就是由你出面,劝说我大哥回心转意,不投游击队,改投国军,并立即带部队东走平江,回江西另谋发展。这条路嘛,估计问题多一点,主要是我大哥的工作可能比较难做。但他很信服你和张老板,只要你们两个跟他好好说一说,他多半也会听的。当然,他万一不肯听,也不要紧,我有办法对付他。大不了,我把他软禁起来,裹挟着一起走不就行了。”
高行渐还在唾沫横飞地说个不停,老田却已眉头紧皱,脸色大变了。他冷不丁地打断高行渐的话,挥挥手说:“不行,不行,你这三条路都走不通!”
“走不通?怎么走不通?”高行渐瞪着大眼问。
“明摆着,你的这三条路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叛变!叛变是什么呀?是遭人唾骂,不齿于人类的丑恶行径!你想想,这样的事情我田默能做吗?”
高行渐愣住了,瞪大眼看着田默。愣了好一阵,他才回过神来,不冷不热地说:“我看你是个人才,有意跟你示好、靠近,没想到你却不知好歹!姓田的,事已至此,我是回不了头了,你也该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担忧啊!”
老田双手一摊,淡淡一笑:“前途、命运?国家残破如此,民族危亡在即,我田默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命运值得担忧啊?”
“难道命也不要了?”
“命?哼、哼,不瞒你说,我的命早就置之脑后了!”
“嚯嚯,那好,那你就做好准备吧,我成全你,亲自送你上西天!”
“上西天?行啊!来吧,我无须准备了,随时都可以动身!不过,在动身前,我还是要问你高连长一声:我死了,你还能活吗?”
“那就奇怪了,我能不能活跟你死有什么相关呢?”
“怎么不相关呢?明摆着,你只是二连的连长啊,无权代表阚团决定大事,对不对?我可不是你高行渐请来的客人,而是整个阚团请来的客人啊!你平白无故地把我这个阚团请来的客人一刀砍了,你那位大哥能饶得了你吗?一连、三连的士兵们能饶得了你吗?你自己的手下,二连的全体士兵能饶得了你吗?好吧,就说你这个当连长的有职有权,说了话,底下人不得不听,但你能保证他们在心底里绝对服你吗?倘若他们心里不服你,难道还会忠于你,心甘情愿地跟你走,为你卖命吗?”
“二连的人怎么不会为我卖命?哼,我在二连,那是有绝对权威的!不信,你问问他们!”高行渐手一抬,指了指站在一旁的士兵们。
老田一笑:“这时候问他们,那怎么能行呢?当着你的面,他们当然不敢说实话喽!高连长,你说你在二连有绝对权威,哼,这话真是自吹自擂、大言不惭哟,大概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谁都明白,人的权威不是靠职权人为树立起来的,而是靠做人行事,经过长久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你扪心自问吧,你的做人行事能使你确立起对二连全体士兵的绝对权威吗?你这一辈子做过足以确立绝对权威的事情吗?你的所作所为真的能够令人信服吗?高连长,我也不说别的了,只凭刚才你对我说的那一番话,特别是你说的那三条路,你就不是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男子汉、大丈夫……”
老田这一番话不软不硬,高行渐听了,不禁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士兵拿绳子捆老田。老田也不挣扎,任凭两个士兵拿着麻绳把自己捆在了椅子上。随即,高行渐又走了过来,用匕首顶住了老田的胸膛。
姜耀成跌跌撞撞地跑到一连连部,找到了李长亭。随即,李长亭又找到了阚副官。两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便急忙排兵布阵,由阚副官带一连包围二连营地,由李长亭带三连包围二连连部。他们还商定,行动要迅速,但也要高度保密,尽可能不动枪炮等武器,以免伤及无辜士兵和惊动日本鬼子。
李长亭很有经验,还没到二连连部,就派兵占领了制高点,控制了各交通要道。到二连连部门外后,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缴了岗哨和门卫的械,控制了关键地点和要害路口。随即,他又派兵把整个二连连部团团包围起来,并派人爬上屋顶,揭开几片屋瓦,对屋里的一切进行严密监视。
李长亭的这一切行动虽然十分谨慎、秘密,但却还是惊动了高行渐。高行渐抬头朝屋顶扫了一眼,突然把匕首往旁边的椅子上一放,迅速低头弯腰,从饭桌的一条腿上解下一根绳子来。他把那绳子捏在手里高高扬起,直起腰,对着门外大喊道:“李长亭,你来了是吧?嘿嘿,你来了,我不怕!你把全阚团的人都调来了,我也不怕!老子实话告诉你吧,我今天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包括死的准备。喂,你睁大眼好好看看吧,我手里拿的这根绳子是什么呀?嘿嘿,看不出这是什么吧?那好吧,我告诉你,这是炸药的引线!老子已经在这桌子底下安上炸药了。这炸药的威力可不小啊,足可以把这栋屋,连同屋里屋外的所有人,统统炸到天上去。你好好想想吧,是想死呢,还是想活?要想死呢,你就进来;要想活呢,那就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开!”
高行渐的这番举动,把李长亭镇住了。李长亭担心炸药爆炸会导致整个二连连部屋毁人亡,并引起日本驻军的注意,因而不得不有所顾忌。他愣了一下,便对士兵们挥挥手,示意他们往后退一退。然后,他走到门前,把脸贴在门框上,嘴巴对着门缝里喊了起来:“二哥,你别胡来啊!炸药一爆炸,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特别是伤着了大哥的性命,那可不是好玩的!真要是到了那时候,可就没办法挽回了,即便我要救你,可也救不了你喽,对不?咱们兄弟结义那么多年,同生死,共患难,感情深厚,胜过亲生,还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呀?你冷静点,听小弟一言,行吗?”
李长亭的话显然起了作用,高行渐不觉愣住了。他发了一会儿呆,便把引线往地上一扔,回身去拿放在旁边椅子上的那把匕首。那动作的意思很明显,是要重新拿起匕首来对付老田。高行渐手里没捏着炸药的引线了,这显然是个绝好的机会。老田看到这个机会了,心里不觉暗喜。他急忙一躬身站了起来,用脑袋对准高行渐的后腰猛地撞了过去。这一撞很有效,高行渐猝不及防,身子不觉往前一扑,顿时趴倒在地上了。但老田的身上绑着一把椅子,手、脚都无法自由行动。因此,在猛烈撞击高行渐的同时,他自己也不幸摔倒在地上了。
高行渐倒在地上了,却没有受重伤,身子依然灵活。他一翻身爬了起来,伸手就去抓那根引线,想引爆炸药。突然间,形势变得非常危急。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个人影忽地跃起,朝着高行渐猛扑过来,一下子就把他扑倒在地。这人影是张颂臣。实际上,他早就醒了。他深知自己年岁大了,难以和高行渐正面对垒,所以便假装睡觉,趴在桌上暗暗地寻找机会。这时见机会来了,他便趁机发起了进攻。
张颂臣扭住了高行渐,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高行渐的士兵们还来不及反应,李长亭便带着大队人马冲进来了。战斗很快结束,高行渐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