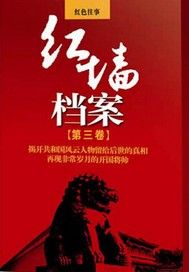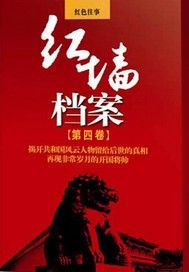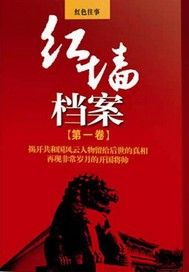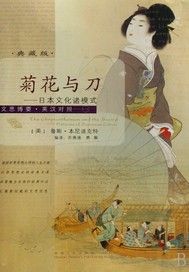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耀大娭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脑袋发沉,手脚发软,浑身上下就跟棉花一样,几乎一丁点劲儿都没有。忽然间,她听到了一阵喊娘的声音。那声音似乎很熟悉,却又小得可怜,分辨不清楚,仿佛是从遥远的天外传来。“哟,有人在喊娘?那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是谁呢?该不是鹤卿在喊我吧?”她费力地思索着,使劲睁开眼睛,终于看到了趴在自己身边的儿子姜鹤卿。
一见姜鹤卿,耀大娭毑不觉吓出一声冷汗。她连忙惊呼:“唉哟,儿子呀,你怎么从隔断里跑出来啦?那多危险呀!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还不得抓起来砍脑壳?”
“没事的。鬼子已经来搜查过了,刚走,”姜鹤卿笑笑,“鬼子也放松些了,每天只来搜查一次,今天肯定不会再来了。你老人家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那也不行!那也得进隔断里躲着!不能出来!晓得不?”耀大娭毑使劲大喊。但她再使劲,声音却还是小得只够她自己听见。
“好,好,我过一阵就去隔断里躲起来,这总行了吧?”姜鹤卿说完,又笑了笑。
看着儿子的脸,耀大娭毑有些怀疑。她暗自琢磨道:“鹤卿的样子好怪啊,明明是在笑,脸上却又挂着泪水!他怎么啦?”
琢磨了一阵,耀大娭毑终于憋不住了。她盯着姜鹤卿的眼睛问:“鹤卿,你、你怎么啦?哭什么呀?”
“我哪哭了呀?见到娘,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姜鹤卿抬起手背擦了擦脸,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娘,你看,我这不是在笑嘛!”
耀大娭毑欠欠身子,想坐起来。姜鹤卿连忙伸手按住了她的肩头,柔声细语地说:“娘,你老人家身子还没恢复过来,这会子不能起床,快躺下吧!”
“我、我怎么啦?对了,我、我这是在哪里啊?”耀大娭毑纳闷地问,眼睛忽左忽右地看,满脸疑惑不解的神色。
“娘,你老人家这是在家里呀!你看,这屋不就是你老人家一直住的那间嘛!这床,这被子,这枕头,这椅子,这桌子,还有这小板凳,不都是你老人家一直用的嘛!”姜鹤卿伸出一只手,边说边指点。
耀大娭毑歪着脑袋,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了看四周,叹口气说:“嗯,是在家里,是在家里,我终于回、回家了!”
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耀大娭毑似乎明白自己是在家里了,两只眼盯着房顶,好一阵没言声。但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又陷入糊涂了,偏过脸来,瞪大眼睛问道:“对啦,我不是去长沙城里了嘛,怎么又回家了呀?”
“是呀,你老人家是去长沙了呀,在长沙待了十多天呐,前天才回来的。”姜鹤卿微微笑着,轻声回答道。
“前天才回来?我、我前天回来的?鹤卿,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你把娘搞糊涂了!”耀大娭毑满脸茫然。她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想坐起来。
“别、别起来,快躺下,快躺下!你老人家这会子不能起来的。有话躺着说不也一样嘛,何必非要起来呢,”姜鹤卿伸手按了按耀大娭毑的肩头,又拿起她的手轻轻地塞进被窝里,重新掖紧了被头,“是呀,你老人家是前天回来的,自己一个人走路从长沙走回来的。估计你老人家是一路上没吃上饭,饿虚了身子,又走了一天路,累垮了,到半路还遇上了狂风暴雨,连累带饿,还带受凉挨冻,结果实在撑不住,晕倒在界石镇上了。后来,还是易杂货救了你老人家呢!”
“谁?谁救了我?”耀大娭毑睁眼问道。
“易杂货呀!就是界石镇西头开杂货铺的易老倌,脸上有麻子的那个,”姜鹤卿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你老人家忘了?他约莫四五十岁年纪,单单瘦瘦的身材,经常挑着一副杂货担子来村里收荒货的,还收过咱们家一个大瓷胆瓶呐!他家挨那棵大樟树不远,正好看见你老人家跌倒在雨地里了。当时,他便冒着狂风暴雨把你老人家背到他家里去了。晚上,雨停了,他又叫上儿子,两个人用床铺板抬着你老人家送到家里来了。”
“哦,易杂货,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哪!鹤卿啊,这恩咱们不可不报,”耀大娭毑盯着儿子的眼睛,语气凝重地吩咐道,“你今晚上就去他家,带十块光洋,拿一只阉鸡、一只麻鸭,再到镇上称十斤不带骨头的好猪肉。”
姜鹤卿撇撇嘴,笑着说:“你老人家疼我是假的。明知道鬼子正急着要抓我呢,却还要我今晚去界石镇。那不是要把我送给鬼子吗?”
“哦,对、对、对,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不过,易杂货的恩是肯定得报的,要不就过些日子吧。唉哟,真的是老了,脑子不行了,什么都记不住了,”耀大娭毑皱了皱眉头,忽然又眼珠子一瞪,喊了起来,“对了,白虎呢?怎么没看见白虎呀?”
姜鹤卿眼皮一抬,忙问:“白虎?白虎是谁呀?”
“小狗呀!我从茅草塘曾老婆子家带回来的。对了,那天那么冷,风雨又那么大,它多半冻死了吧?”说着说着,耀大娭毑的眼睛又发红了。
“没冻死,它还好着呢。”姜鹤卿笑笑。
“哦,那太好了!它呢?快抱来我看看!”耀大娭毑精神一震。
姜鹤卿伸手一指,说:“它不就在你老人家床底下趴着嘛!”
“是嘛?”耀大娭毑惊呼一声,连忙歪过头来,想侧转身子往床底下看。
但耀大娭毑已虚弱极了,那身子似有千斤重,哪侧转得过来呀?她动了动,肩头还没转过来,便又身子一倒,倒回去了。姜鹤卿见状,连忙把那小狗抱起来,放到母亲身旁。
经过几天调理,耀大娭毑的体力倒是恢复一些了,能起来坐坐,也能下床在屋里走几步,但神志状况却越来越糟糕,成天糊里糊涂的,嘴巴还不停地念叨着水玉和济勋的名字,以至白天黑夜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
看到母亲这样子,姜鹤卿着急得很。他自己出不去,便托堂兄姜鹤坤遍天下去请有名的郎中。姜鹤坤把远近十多里有名的郎中都请来了,但他们却都治不好耀大娭毑的病。郎中们的看法很一致,都说耀大娭毑的病,表象上看是内伤饥饿、外感风寒,而根子却是忧虑过度,心力交瘁,五脏六腑俱伤,因此不是医药所能治的。有些郎中说得更绝:风寒之病可医,心神之病难治,医家是无能为了,就看天命、造化吧!
郎中们这样说,姜鹤卿自然更急了。从耀大娭毑不停叨唠的断断续续话语中,他大概齐地弄明白了这十多天母亲在长沙城里所经历的事情,知道老人家的病因就在于水玉和济勋两个人的失踪。于是,他也顾不得鬼子什麽时候要来搜查了,动不动就从隔断里爬了出来,跑到母亲床前守着。他掰开了揉碎了地对母亲进行劝解,说吉人自有天相,济勋、水玉都不会出任何事,要她别操空心。但耀大娭毑的满腔心事又岂是儿子几句话所能化解的呢?她人躺在家里歇着,脑子却依然还在长沙城里奔驰,睁眼闭眼都是水玉和济勋的身影,开口闭口也都是水玉和济勋在梁家附近走失的那些事情。
到了回家后的第八天、第九天,耀大娭毑更是一时一刻都安静不下来了。她一会儿掰着手指头,嘴里不断地念叨:“嗯,第八天了,还有两天,济木就带水玉和济勋回来了”,“嗯,第九天了,还有一天,水玉和济勋就回家了”,“嗯,水玉和济勋明天就到家了”;一会儿又对着儿子鹤卿大喊:“鹤卿,把水玉的床铺拾掇好,多铺点新草,把被窝铺盖拿出去晒一晒,弄干净点”;过了一会儿,她又闹着要下床,说是济木带着水玉、济勋回来了,已经过了界石镇,快到石板塘堤上了,自己无论如何要去接一接。她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搅得全家和左邻右舍的心都不安了。
耀大娭毑最要好的朋友,头一个就是景满贞。闹起倔脾气来,她谁的话都不听,唯独景满贞的话还能听得进去。所以,当她闹得不可开交时,姜鹤卿就只好求助景满贞。
到了回家后的第十天,耀大娭毑折腾得更厉害了。一大清早,天刚麻麻亮,她就闹着要下床,愣说济木带着水玉和济勋已经到了石板塘的塘堤上了,她得去接一接。姜鹤卿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实在没辙了,只好跑到景满贞家的台阶上,隔着窗户把她从睡梦中喊醒。
景满贞披上衣服,连茅房都没来得及去,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
一见景满贞,耀大娭毑就喊了起来:“满贞,你来得正好,快,快扶我起来!”
“哟,英莲姐,这一大早要起来干什么呀?这大屋里还没一个人起来呐!”景满贞紧赶几步走上前,扶住了耀大娭毑。
“济木带着水玉、济勋回来了,都快到石板塘了。你说,我能不去接一接吗?”耀大娭毑气喘吁吁地说。
“什么?济木他们到石板塘了?哪有这回事呀?我们家耀宗刚到屋,他是昨天晚上从长沙动身的。他临行前去看过济木,济木对他说要等今天天亮后才动身。你这会儿去接,哪能接到呀?估计他们还没到捞刀河呐,你上哪儿接去?”景满贞说完,朝姜鹤卿挤了挤眼。显然,她是对耀大娭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噢,他们今早上才动身?那是,那是,这会子到不了捞刀河。好吧,那我就再睡一阵,过会子再去接他们。来、来,满贞,你也上床睡吧,挨着我,挨着我!”耀大娭毑边说,边往床里头挪身子,好把床边上的地方腾给景满贞。
“这就对了嘛,咱们睡一觉再去接,免得在路上空等。嘻、嘻,英莲姐,你这被窝里的味道好闻,连屁都是香的。说真的,英莲姐,我就最喜欢跟你钻一个被窝。”景满贞笑嘻嘻的,一迈腿上了床,紧挨着耀大娭毑躺下。
景满贞撒的谎还真起作用,耀大娭毑搂着她睡了一个好觉。只可惜这一觉时间不够长,还没到半晌午,耀大娭毑便醒了。她醒了,就再也不肯在床上躺着了。她闹着要下床,要到外头去,要亲自到大路上去迎接济木、济勋和水玉。景满贞故伎重演,一会儿撒谎说济木他们刚到茶亭寺,一会儿撒谎说济木他们正在半路上吃饭,一会儿又撒谎说济木他们快到界石镇了。但她的这些谎言编得再好,耀大娭毑却横竖不肯听了。姜鹤卿和景满贞都无计可施了,他们只得一边一个架住耀大娭毑的胳膊往大路上走。
事情也真巧,三个人刚走到石板路的北头,还没到石板塘,一抬头忽然看见了塘堤上的姜济木。只见他跌跌撞撞地迎面狂奔而来,冲下塘堤,跑到跟前,一下子跪倒在地,对着耀大娭毑大声哭喊道:“奶奶,你、你这是怎么啦?得什么病了呀?”
耀大娭毑这时候突然变了,变得就跟好人一样,头脑异常清醒。她一把抓住姜济木的脑袋,让他的脸朝上仰着,正对着自己的脸,然后死死地逼视着他的眼睛大声说道:“我没事,你不用管!你就回答我一件事:怎么就一个人回来啦?济勋呢?水玉呢?”
“奶奶,我没用,我没用,我没找到济勋弟!”姜济木泪流满面,嗓子沙哑得厉害。
“难道一点消息都没有?”耀大娭毑声音异常严厉。
“没、没、没有!”姜济木的声音颤抖着,小得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耀大娭毑微微晃动了一下身子,接着又逼问道:“那水玉呢?”
姜济木忽闪着眼睛,朝姜鹤卿看了看,又朝景满贞看了看,好一会儿没言声。
姜济木的举动显然激怒了耀大娭毑。她弯曲着右手中指和食指猛敲姜济木的脑门,厉声大喝:“你、你怎么不说话呀?水玉怎么啦?水玉到底怎么啦?说!快说!”
“水、水玉也没找到,但、但找到了她的……”话说了一半,姜济木又突然停下来了,一双眼睛怯怯地看着耀大娭毑。
耀大娭毑更火了,破口大骂道:“你这砍颈的东西怎么啦?拉屎拉半截!快说呀,你找到水玉什么啦?”
“奶奶,你别着急啊,”姜济木从挎兜里掏出一双花布鞋来递给耀大娭毑,“我、我找到了这双鞋,像是水玉的。但、但也许是我看错了,这鞋可、可能不是水玉的。”
耀大娭毑从姜济木手中接过那双鞋,只拿到眼前晃了晃,就立马说道:“没错,这鞋是水玉的,还是临走前我给她做的呐。济木,你、你是在哪里找到这双鞋的?”
姜济木又不说话了,眼睛瞥了瞥姜鹤卿,又瞥了瞥景满贞。
“你看,你看,话说了一半又不说了,尽屙半截屎!快说呀,水玉这双鞋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耀大娭毑声音很高,根本不像重病在身的人。
“在、在河边,就、就是梁家附近那段江堤下边的一块大、大石头上。”姜济木话没说完,眼泪已哗哗地流了下来。
“哦,这鞋是在河边捡到的?这么说,水玉那孩子投、投水啦?啊,我可怜的孙女!”耀大娭毑突然嚎啕大哭,但她只哭了一声,便头一歪,昏晕过去了。
耀大娭毑的病情急转直下,一连五六天水米不进。郎中们看了,都直摇手。
得知耀大娭毑病情加重的消息,左邻右舍、亲朋戚友纷纷前来探视。这天上午,姜耀宗回来了。他刚一到家,撂下行囊,便急急忙忙地来看耀大娭毑。姜耀宗的回来,带来了张颂臣、姜耀成等人的问候,还带来了梁家原来的那些老邻居——张老婆子、齐家婶子、贾家大姐、刘老太太等人的问候。
听到了老朋友们的问候,耀大娭毑的心情略略好受了一些,但依旧苦着一副脸,不停地长吁短叹。姜耀宗剥了一个橘子给她,她不肯吃。姜耀宗递给她一块蛋糕,她也不肯吃。姜耀宗问她想吃点什么,她又摇了摇头。姜耀宗急了,张口就埋怨道:“唉哟,老嫂子呃,你的心思也太重了吧!这也不吃,那也不喝,那不是等死吗?”
“是呀,我就是在等死,”耀大娭毑叹口气,泪水直流,“孩子们死了,是我害的。你说,我还能活下去吗?”
姜耀宗一惊,连忙说:“哟,这我就不懂了,怎么是你害的呢?”
“怎么不是我害的呢?明摆着的嘛,我要不带他们去长沙,不把他们的身世当面告诉他们,他们能跑吗?”耀大娭毑不断地伸手抹眼泪。
“呵呵,那就好笑了,”姜耀宗似笑非笑,“你不把他们的身世说出来,眼看着他们嫡亲兄妹通婚,犯人伦大错,那就好了吗?”
耀大娭毑一时语塞,表情木木的。过了好一阵,她才缓过神来,小声说:“那总也比让他们去死好啊,对不?”
“不对!我宁肯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死,也不能眼看着他们肮肮脏脏地活着,”姜耀宗勃然大怒,情绪激昂,语音铿锵,“兄妹通婚,一根肠子里爬出来的做夫妻,那叫什么?那不是犯错,而是犯罪!那样做,祖宗牌位里头是写不进去的!那样做,我们姜家,包括所有活着的族人,也包括所有的祖宗和子孙后代,都会要羞死的!老嫂子呃,你告诉他们实情,那是对的!他们自己想不通,要跳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你无关!他们真要是自杀了,你也别想他们了,算你自己瞎了眼,白疼他们一场了呗!这么明白的道理,他们都明白不了;这么点芝麻小事,他们都想不开;为了兄妹之间本不应该有的那点情,闹得昏头胀脑,投河上吊,那还是个人吗?这样的人不死,留在世上有什么用呀?”
姜耀宗脾气好,平时不大说狠话,这一次却出乎意料,话说得异常激昂慷慨。
听了姜耀宗这一番话,耀大娭毑不觉脸红心跳,头脑清醒多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耀宗,你说得对,我想通了。他们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唉,从今以后啊,我也不想他们了,就当从来就没有过他们好了。”
“呵呵,嫂子,你还真以为他们死了?”姜耀宗笑了笑。大概是狠话说完了,火气发光了,他这时候的脾气小多了,说话的语气平静了许多。
“济勋还不好说,水玉肯定是死了,”耀大娭毑眼眶一红,眼泪又差点流了出来,“她的鞋都找到了嘛,是在江边上找到的。明摆着,她投水了呀!”
“投水就一定能死成吗?”
“那当然喽!她投的不是小水塘,而是大河呀!那么深的水,她还能不死?”
“我看未必!那地方,我去看了,水不深!”
“是呀,江边上的水是不深,这我知道。但江中间的水深呀,对不?她诚心要寻死,当然会往江中间走喽,还能老站在江边上不动?”
“她即便是到了江中间,那也死不成!”
“那为什么?”
“江中间来来往往的船那么多,人见了,还能不救?”
“人救?哼,我看没人会救。阳世间都这样子了,人人自顾不暇,谁还有那好心眼跳到那么深的江水里去救人呀?”
“不,好人还是不少。我就亲眼看见过好多人跳河,结果都被船上的人救起来了。说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过一个人投河死成了的!”
“真的?”耀大娭毑一声大叫,眼光突然发亮,盯向姜耀宗。但仅仅过了一会儿,她的眼光就从姜耀宗的脸上移开,渐渐地黯淡下来了。
“怎么?你不信?”
“信是信,但水玉肯定没被救起来!”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
“当然喽!她要是被救起来了,就一定会回家,对不对?可是,我和济木在她家住了那么久,都没见她回来呀!”
“嗨,嫂子呃,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水玉怎么会回家呢?”
“怎么不会回家呢?”
“她父母都死了,还回家干什么?等孙棒子抓她呀?”
“哦,你是说她是在知道父母已经死了的消息以后投河的?”
“那肯定是这样的喽!你想想噢,”姜耀宗一边说,一边掰起了手指头,“水玉那天离开家是天快亮的时候,对不?孙棒子带兵到她家来抓人是一大清早,对不?这中间时间很短,最多也就一两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她根本就来不及回家,因为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情绪平静下来,对不?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她也许想通了,情绪平静下来了,想回家了,但这时却已迟了,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她父母已经被抓走了。她很聪明,肯定晓得孙棒子在家里埋伏了重兵。她当然是不会甘心自己的清白之身被孙棒子玷污的,于是一怒之下便跑到江边投水了。”
“依你这么说,那水玉就不一定晓得她父母死在牢里和后来我们游行示威的事喽?”
“游行示威的事,她是肯定不知道的。她要是知道的话,当时就会现身,而且会积极参加。这是为她和她父母报仇的事,她哪能不参加呢?至于她父母惨死在牢里的事,估计她也不知道。明摆着,她父母亲被关在哪个牢里,她不一定晓得。而且,她即便是晓得父母关在哪个牢里,她也肯定不会去探视。她很聪明,当然不会不明白孙棒子抓她父母是在用钓鱼之计,目的在于抓她。如果她去探监,不仅救不了父母,反倒会害了自己。我估计呀,水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心思。”
“哦,另外一种心思?那是什么心思呀?”
“我估计呀,水玉投水自杀,不一定完全是为情所困,自己想不开,而很可能还存着一份救父母亲的心思。她很清楚,孙棒子之所以抓她父母,目的是为了得到她。因此她就想喽:我不死,孙棒子就老存着得到我的幻想,不放我父母,要逼我就范;那要是我死了,孙棒子晓得无论怎么做也得不到我了,不就会放了父母吗?她这么一想,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自杀的冲动喽,对不?”
“耀宗,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多了。看来,水玉肯定是跳河了,但会不会被人救起来,那就得看她自己的命运喽!那济勋呢?他会不会是也跳了河呀?”
“济勋不会,肯定不会!水玉跳河,是确实有原因的。孙棒子要抓她,还把她父母关进牢里了,这是她跳河的两大诱因。济勋哪有这些诱因呀?没有这些诱因,他跳河自杀干什么?疯了啊?被鬼打昏了脑壳啊?”
“那会不会是他看见水玉跳河了,于是也就跟着跳下去了呢?”
“不会的!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明摆着,到现在还找不着他的人影呀!”
“那孩子心气高,”姜耀宗抬手摸摸下巴颏,“我估计呀,他是找事做去了,过些日子就会买一大堆东西回来看你的。老嫂子呃,你等着吧!”
和姜耀宗说了好一阵话,耀大娭毑的精神好多了。姜鹤卿见母亲见好,就问她想吃什么,要不要熬点粥喝。耀大娭毑想了想,说:“到时候跟着一起吃点饭就行了,粥就别另外熬了。要是有现成的好开水,就沏碗茶吃吧,只是没盐没豆子了哦!”
那年月,盐最金贵。姜家这几年连着出事,既要筹备盖房,又要延医治病,还要进长沙城寻人,耀大娭毑先前攒下的一点积蓄早就花光了,哪还有钱买盐吃?所以,一家人差不多有好几个月没粘过盐味了。姜鹤卿在家里翻了半天,竟然没寻出一丁点盐来。没办法,他只得去景满贞家借盐了。但他刚出门,迎面便碰上了姜鹤慧。
姜鹤慧是姜鹤卿的堂妹妹,在鹤字辈中年纪最小,比姜鹤卿还小两三岁。她是姜耀柏的女儿。姜耀柏后来生意衰败了,就把她和她的两个哥哥及其家人从陕西西安送回了湖南老家。但她虽是姜耀柏的女儿,脾气性情却大不相同。她是一个非常诚实、厚道、善良的人,为人谦和,特别乐于助人,和耀大娭毑的关系也极好。耀大娭毑得病以后,她就天天来帮忙做事,有时还整天整夜地守在病床边。
姜鹤慧听姜鹤卿说要去景满贞家借盐,便忙打阻说:“你别跑了吧!我们家有盐,炒黄豆也是现成的,我现在就打转回去拿点来!”
姜鹤慧回自己家拿盐和黄豆去了,姜鹤卿便忙着烧开水、拿茶叶、磨姜汁,做沏茶的准备。但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却还没见姜鹤慧回来。他实在等不及了,便跑到景满贞家拿了一点盐和黄豆回来,沏好了一碗姜盐豆子茶,双手捧着,递到耀大娭毑嘴边。
耀大娭毑好长时间没喝过姜盐豆子茶了。她聚精会神地盯着那碗茶看,看了老半天,才微微低头抿了一口。这一口喝下去,她立刻眉开眼笑了,情不自禁地嚷嚷道:“好吃!好吃!还是咱们老家的茶好吃!哎呀,就可惜缺点芝麻和桂花!”
喝完一碗茶,耀大娭毑的精神又好了些。她靠着床头半躺着,眼睛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蓝天,一只手指头伸进嘴里剔着牙缝里的茶叶,神情显得安详适意。过了一会儿,牙缝里的茶叶剔出来了,她一边弹手指,把茶叶弹到地上,一边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阎王爷那里有没有姜盐豆子芝麻桂花茶吃,要是有,可就太好了!”
姜鹤慧手里拿着一小瓶盐和一小碗炒熟的黄豆匆匆忙忙地跑来了。她眼圈红红的,脸上还带着泪痕。姜鹤卿一见,便埋怨道:“哎哟,我的姑娭毑,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八成是你哥不让拿盐来吧?嗨,也难怪,这年月盐也实在太贵了,比得上黄金,谁舍得往外拿呢?”
“不,我哥没不舍得!”姜鹤慧说。
“我不信!你哥是个吝啬鬼,能让你拿盐出来?他多半骂你了吧,要不你为什么哭了呢?”姜鹤卿说。
“我哥没骂我!我拿盐出来,是背着他的,他根本就没看见!”
“那就奇怪了,你哭什么呢?”
姜鹤慧不说话了,低着头,不停地用手背擦眼睛。这一切,耀大娭毑都看在眼里了。她把姜鹤慧拽到自己身边坐下,轻声问:“鹤慧,好闺女,家里出什么事啦?能告诉伯妈吗?”
“没、没什么事!”姜鹤慧头压得更低了。
耀大娭毑伸手把姜鹤慧拉近了些,抚摸着她的肩头说:“怎么能没事呢?你心里头那么难受,那肯定是有事呀,对不?孩子,别藏着掖着了,快跟伯妈说实话吧!不说出来,你难受,伯妈也难受呀!”
“那、那好,我说出来,你老人家千万别着急啊,”姜鹤慧擤了一把鼻涕,哽咽着说,“我大哥家的老三济芬和二哥家的老二济芳被土匪劫持了!”
耀大娭毑大吃一惊,忙问:“哟,被土匪劫持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就、就、就刚才!”姜鹤慧泪如泉涌。
“济芬、济芳不都是姑娘家嘛,最多也就十二三岁吧?平常看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会突然被土匪劫持呢?”
“嗨,这、这也得怪、怪她们自己,”姜鹤慧又擤了一把鼻涕,控制了一下情绪,“她们在家里待不住,老想上大山里去看看,说了几次也不听。今天一大早,她们也没跟大人打声招呼,就拽上我二哥家的老二济崇悄悄地出门走了。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踢石头子玩,刚进山就看见路边坐着几个衣服特别破旧、浑身又黑又脏的男人。济芬最爱干净,见那几个人脏兮兮的,样子很难看,觉得恶心,便小声骂了一句‘臭要饭的’。谁知这一骂就骂出麻烦来了。那几个男人当时就冲上来,抓住三个孩子又打又骂。打完了,骂完了,他们又抓住三个孩子往山里头走。走到常家洞附近时,他们又忽然把济崇放了,要他回来给家里报信,说是要拿一千块光洋去盘山寺赎人。他们还说,如果三天之内见不到一千块光洋,他们就要把两个女孩子留在山里当压寨夫人。我刚才回家时,赶上济崇也刚到屋,正在说遇上土匪的事呢。我听得心里又慌又乱,所以就忘了拿盐的事,耽误了你老人家吃茶的事,真不好意思!”
“嗨,什么‘耽误’不‘耽误’的,我吃茶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打紧?你别在意,”耀大娭毑说,“对了,鹤慧,济崇是男孩子吧?今年多大了?有十五六吗?”
“是呀,济崇是男孩子,今年满十六了,四月份的生日。”
“难怪土匪放了他呢,他们觉得十六七的男孩留在身边既没用还碍事嘛。济崇要是个女孩,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只怕就更糟了。哎哟,我的娘呃,这土匪也太猖獗了,大白天竟敢劫持人!鹤卿,”耀大娭毑转头看着姜鹤卿,“你快去找鹤坤,把这事对他说说,要他赶紧商量救人的事。你对他说,就说是我的意思,土匪是不可信的,跟他们讲不得客气,拿钱赎人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的,只能动武,派人直接去盘山寺救人。土匪狮子大开口,要一千光洋。如今这世道,谁家拿得出一千光洋啊?再说喽,就是拿得出一千,也不能给!这帮土匪实在太可恶了,白昼劫人,为害一方,我们哪能容忍啊?干脆,咱们趁着救人的机会把那帮子土匪灭了吧,也算是为地方上做件好事。不过,要去救人,动作就要快,最好是今天晚上就去,千万耽误不得。要是拖久了,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或是把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可就麻烦了!”
姜鹤坤新近刚被大家选为族长。他正在家里拾弄猪栏屋,满手满脚都是猪粪,浑身上下臭烘烘的。他还不知道土匪劫持孩子的事呢。姜鹤卿把事情一讲,他吃惊地说:“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呀?那鹤喜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姜鹤卿笑笑说:“那还用问,他们不好意思呗!”
“嗯,兴许是,”姜鹤坤点点头,“也没准他们觉得我这个族长是新上来的,不管用,所以就不来找我了。不过,他们不来找我,我就得去找他们了。这事太大,族里不管不行!”
“那你打算怎么管呢?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娘的意思是动武。她说对土匪不能信,更讲不得客气。”姜鹤卿说。
姜鹤坤抬眼看着远方的照壁山,斩钉截铁地说:“老人家的意见是对的。跟土匪没得客气可讲,只有打这一条路。别说没钱喽,就是有钱,也不能给他们。他们动不动就下山抢钱抢东西,动不动就把人劫持到山上去,搞得地方上民不聊生,人心惶惶,这还得了?这次要是容忍他们了,给他们钱了,他们下次还来村里劫持人,那怎么办呀?祸根不除,为害无穷。不行,这仗非打不可。但是,这仗不打就不打,打就一定要打胜。而要打胜,就一定要做好准备。至少我们得先摸摸情况吧?比如说:盘山寺的地形怎么样啊;要打的话,先从哪里开始进攻啊;土匪总共有几个人啊,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啊,手中有没有真枪实弹啊;孩子抓走后情况怎么样啊;她们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啊。这些情况,我们都得先摸清楚。只有摸清了情况,我们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没错,是得先摸清情况,”姜鹤卿说,“那,坤哥,要不我先到盘山寺附近跑一趟,探探路,摸摸情况?”
姜鹤坤把眼神从照壁山上移回来,低头沉思,好半天才说:“你去?那不行吧?鬼子正盯着你呐,要是你被他们抓走了,我大娘还不得把我吃了?”
姜鹤卿笑笑,不慌不忙地说:“有个情况你还不晓得吧?我那未过门的堂客就在骆家坳。骆家坳就在盘山脚下,离盘山寺很近。她常去盘山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我去找找她,打听打听情况,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呵呵,你堂客就在土匪窝里,”姜鹤坤看着姜鹤卿,眯起眼睛,诡秘地一笑,“哼,我还真以为你是急公好义呢,原来里头有这层关系!探路是假,找堂客亲热是真吧?”
“嗨,这时候哪有心思开玩笑呀,都屎到P股门了,”姜鹤卿一脸正经,“快拿主意吧,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那既是这样,你就跑一趟呗!但你是你娘老子的心头肉,她会放心你去吗?”
“不要紧的,不跟她说实话就是了。”姜鹤卿说。
“好,你去吧!千万注意安全啊,别让鬼子发现了!最好是从山里走,从树林子里穿,绕开大路,明白吗?”
“明白,出不了事的!我现在就走!你去我家里,撒个慌,稳住我娘!”
中午饭后,各家的男子汉就都来正堂屋开会了。姜鹤坤把事情一说,大家立刻炸开了锅,七嘴八舌,什么意见都有。有人嚷嚷:“事情都这样了,还开什么狗屁会呀?瞎耽误工夫!还不赶紧抄家伙上山救人去?”有人慢腾腾地说:“事情没那么邪乎吧?盘山寺也就七八个小毛贼,能有那大胆抓住人不放?没准也就是吓唬吓唬鹤喜,要他出点血罢了!”也有人幸灾乐祸,不阴不阳地叨唠道:“该!这就是天报应!谁叫耀柏叔那么贪心,私占公户建房盖屋呢?要依我说,这事就不该管,听他自作自受!”
说话的人中,有不少是反对动武的。他们反对动武,原因当然有多方面。有些人是因为胆子小,不敢动刀动枪,害怕伤到自己。有些人是因为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想法,不愿意为别人管闲事、卖力气。还有些人则是缺乏信心,不相信族里这些人真能办成到土匪窝里救人的大事。
反对动武的这几种想法,姜济胜无一不有。一进正堂屋,他就把和自己走得近的几个小年轻拉到一起,找一个犄角旮旯蹲了下来,无边无涯地说起了风凉话。起初,他那些风凉话还只是小声议论,当听到有人说“这事就不该管,听他自作自受”时,他的风凉话就立刻变成大声嚷嚷了。他扯开嗓门对着堂屋里吆喝道:“没错,这事就是不该管!明摆着,这事咱们没法管呀,对不对?土匪是什么人?他们是天天在山里摸爬滚打惯了的,地形熟,会走山路,个个武功出众,还有真刀真枪。咱们呢?咱们能跟他们比吗?咱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呀,天天就和泥巴打交道,从来没练过武,别说真刀真枪喽,就是木棍子都不会使。就咱们这能耐,打得过土匪吗?我不是吓唬你们,咱们要真是上山和土匪打,别说救出那两个小姑娘了,不被土匪戳死就算便宜!搞得不好的话,只怕脑袋都得搬家!咱们可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父母谁管呀?老婆谁管呀?孩子谁管呀?人生在世呀,就得认命。事情让谁赶上了,谁就得认命,不要牵扯别人,别人也没必要为他去送命。要依我说,这上山救人的话就别再说了,那是他娘的没用的屁话!耀柏家的这档子事就听其自然吧!他要是有钱呢,就拿钱去赎人。他要是没钱呢,就把女孩留在山上当压寨夫人算了!当压寨夫人也没什么不好嘛,天天不用做事,没准还能吃香的喝辣的呐!”
姜济胜一说话,他身旁的那几个小年轻就跟着起哄。一时间,反对上山救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占了上风。
姜鹤扬早就憋不住了。他猛地站了起来,对着姜济胜大吼道:“济胜,你那话才叫做屁话呢!什么‘认命’不‘认命’哪?什么‘牵扯别人’、‘为别人送命’哪?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出了事不应该帮把手吗?按照你这逻辑,大家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那好吧,将来你们家出了事,我们也都不管,看你怎么办?”
“对,鹤扬叔说得太对了,”姜耀希的孙子济民挥着拳头说,“要是济胜大哥他堂客被土匪抢走了,我们就不管,让她给土匪当压寨夫人算了。她堂客可是咱们村的头号美人哪,长得漂亮极了,土匪要是抢了,准保还没到晚上就得玩得稀巴烂。”
姜鹤季在鞋底子上嗑了嗑旱烟袋,慢腾腾地说:“是呀,济胜,你真的太不像话了。济芬、济芳那俩孩子才多大呀,你就说让她们当压寨夫人算了。亏你还是她们俩的大哥呢,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你还是个男子汉吗?你爸平常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我真不明白,耀松大伯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孙子,真是丢人现眼哪!”
“济胜啊,你也太看低咱们农民了。农民怎么啦?农民就玩不过土匪?你数数看,哪朝哪代的天下不是咱农民打下的?刘备还织过履、贩过席、种过菜呢!太平天国的那些大将们哪个不是农民呀?农民要是连几个小毛贼土匪都对付不了,那也就不是好农民了。我也不是说大话,别说那山上只有七八个土匪,就是再多十个八个,咱们也能对付得了。大家都没真刀实枪地干过,但却都不怕,你怎么就那么胆小害怕呢?难道你特别,生来就是软骨头?”姜鹤扬冷嘲热讽地说,说完还轻蔑地朝地下啐了一口唾沫。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朝着姜济胜开火,姜济胜和他那一伙子就都哑巴了。于是乎,主张上山救人的这一派又占了上风。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门外忽然传来了喊叫声。那是姜耀典。他担心儿子鹤仲、鹤季跟着上山救人会有危险,便戳着根拐棍出来,站在南大门的门廊里,对着正堂屋大喊:“鹤仲、鹤季,你们两个赶紧回来,我还有要紧事等着你们做呢!”
姜耀典大喊大叫了好半天,姜鹤仲和姜鹤季兄弟却都不理睬。姜鹤坤觉得不大好,便扫了一眼姜鹤仲和姜鹤季说:“要不你们兄弟把一个回去看看吧!”
“我来吧,”姜鹤季站起来,走到门口,扯开嗓门对姜耀典大声说了起来,“爷老子,大家说了,你要再大喊大叫的话,族里就不管我鹤康哥和鹤鹏弟的事了,看你怎么办?”
姜鹤季这句话真起作用,姜耀典不出声了,头一扭,戳着拐杖回去了。
议论好半天了,该收尾了,姜鹤坤站了起来,边走边措辞,想说几句。正在这时,景满贞和姜鹤慧忽然推门进来了。景满贞一进门,就对着姜鹤坤嚷嚷起来:“鹤坤,上山救人的事,别落下我和鹤慧,我们俩也去!”
“哎哟,二娘,这是男人们的事,你、你们就别来瞎掺合啦!”姜鹤坤说。
景满贞眼睛一瞪,大声嚷道:“什么话?上山救人还分男女?小瞧你二娘是不是?你二娘不比你差,不信上来试试!”
景满贞这一说,满堂屋人都大笑起来:“好,快来看吧,母子俩比武喽!母子俩比武喽!”
姜鹤慧也笑了。笑了一阵,她便款款地走到堂屋中间,做了个请肃静的手势,看了姜鹤坤一眼,然后朝前后左右的人群各鞠一躬,轻声说:“大家为我们家的事操心了,我代表我大哥、二哥及我们全家所有的人谢谢了!鹤坤哥,各位哥哥,刚才满贞婶子说我们两个也要上山救人,这不是瞎掺合,而是我们的真心实意。我们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去,去了也有好处。我们去了,没准还能成为秘密武器,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呢!”
“哟嗬,鹤慧,你是什么秘密武器呀?”大家纷纷起哄,堂屋里热热闹闹。
“那当然喽,这事很明白嘛,”姜鹤慧说,“我那两个侄女刚从陕西来湖南不久,听不大懂湖南话,跟大家也都不熟。因而如果需要她们配合的话,她们就可能配合不好,难免耽误事。如果我和满贞婶子同去的话呢,情况就可能会好得多,因为我会说陕西话,我又是个女人,两个孩子跟我又很熟,她们都能听我的,沟通起来会比较容易嘛。”
“嗯,有道理,有道理,”姜鹤坤点点头说,“秘密武器,那你就和我娘一起去吧!不过,我把话说在头里,得绝对服从我指挥哟!”
景满贞和姜鹤慧的激情感染了大家,满堂屋的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加上山救人的战斗。姜鹤坤见大家热情高涨,心里很高兴,便想趁热打铁,把上山的人选定下来。他正要宣布人选,门口突然进来了姜鹤卿,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人三十出头年纪,个头高大,身强体壮。
见来人了,姜鹤坤忙上前招呼。姜鹤卿一伸手,指指身后的人说:“坤哥,他叫骆根宝,是骆家坳的,我姐夫!”
姜鹤卿话音刚落,几个小伙子就喊起来了:“哟,鹤卿叔,你不就三个姐夫嘛,怎么今天又来了一个姐夫呀?怎么回事,快说说!”
姜鹤卿腼腆,脸爱发红。见大家起哄,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脸不觉红了起来。姜鹤坤见状,连忙替他解围。“别起哄了,商量正事要紧!”姜鹤坤边说边向大家挥了挥手。
紧接着,姜鹤坤又招呼骆根宝到堂屋中间坐下,请他介绍盘山寺的情况。骆根宝倒也是个大方随便的人。他略略客气了几句,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原来,盘山不太高,也不太大,但异常陡峭险峻。山峰东、南两面都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北面有一条长达十数里的深涧构成天然屏障,只有西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峰顶。那羊肠小道也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围绕着山峰盘旋而上,分三盘六坡二十一弯,关卡障碍有很多处,处处易守难攻。
山半腰有一个寺庙,那就是盘山寺。盘山寺很小,只有一个山门、一个大殿、两间配殿。大殿的后头,还有一排矮小的平房,那是做住房、厨房以及堆放柴火杂物用的。寺庙的山门紧邻那条通往峰顶的羊肠小道。羊肠小道的另一侧,就是那条险峻万分的天然屏障山涧了。
盘山寺里原来有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土匪们来了以后,便把他们赶出去了。那两个和尚从此便真正成了“出家人”,无家可归,只得到处流浪了。
土匪总共有八个,多为外地人,年纪多在三十岁左右,而且多数都是叫花子出身。为首的姓金,不知名字,土匪们都叫他金大脑袋。这人个头不小,身体也壮实,有些武功,一手棍法使得不错。土匪中还有一个叫金猫的,个头不高,人很消瘦,长得就跟猴子似的,但其貌虽不扬,武功却不弱,尤其轻功了得,在山上奔跑如履平地。除了金大脑袋和金猫之外,土匪中就再没有什么武功好的了。
土匪们占据盘山寺不久,还没有搞到什么枪支弹药一类的武器。他们使的多数都是棍棒,偶尔也有用大刀和梭镖的。但那些大刀和梭镖也多半是样子货,有的材料不真,有的棒头太轻,有的还陈旧得生了锈。因此,总的来说,他们的势力并不强,没有太大的战斗力。
骆根宝详细介绍了盘山寺和土匪们的情况,临末了还对姜鹤坤说:“你们人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就多派几个人和你们一起干。不说多了,我们村一二十个壮小伙子还是派得出来的,而且个个都是猎户,身手好,地形熟!”
姜鹤坤一听,连忙紧紧握住骆根宝的手说:“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我们村的人手倒是不少,会武功的也有几个,估计对付那几个小蟊贼也足够了,可就是地形不大熟,夜里头看不清地形地势,走那三盘六坡二十一弯可能会有些犯晕。要不你就派几个路熟的给我们带带路吧,其余的人就不麻烦了!”
骆根宝低头看着地面,沉思有顷,说:“坤哥,我们村离盘山寺近,平常受土匪的侵害最多,早就有心灭掉他们了。你们这次上山打他们,其实也是在为我们村做好事。所以呀,我们村多派几个人参加也是应当的。要不这么吧,我派几个身手好、地形熟的给你们带路,然后我自己再带几个人协助你们进攻,听你的指挥,行吗?”
“那好吧,你回去安排人,”姜鹤坤对骆根宝说,“我们晚饭后就动身,到你们村口会齐!”
送走骆根宝,姜鹤坤就开始选派人手。他这个瞧瞧,那个看看,斟酌了好半天,最后才选定了十六个人。但这十六个人中,有姜鹤卿,却没有姜济木。这一来,姜济木不高兴了,耀大娭毑也不高兴了。
姜济木不高兴,是因为他自己想去。耀大娭毑不高兴,是因为她不想让小儿子姜鹤卿去。她既担心小儿子姜鹤卿夜里走山路时不小心跌倒伤了脚,又害怕他跟土匪搏斗时伤了身子。她想得很细,一个人没完没了地瞎琢磨:“刀枪可是没长眼睛的呀!要是土匪玩命地打,一枪戳来,正好戳中了鹤卿的眼睛,或是戳中了鹤卿的胸口,那该怎么办?”她越想越怕,想着想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耀大娭毑的心思,让姜鹤坤知道了。姜鹤坤连忙作出决定:姜鹤卿也不上山救人了,留在家里照顾病重的母亲。
姜鹤卿和姜济木都不参加上山救人的战斗了。这事显然有些不妥。果然,村里很快就有人议论开了,说是耀大娭毑有私心。
耀大娭毑没有听到人们的议论,但她也觉察出自己好像有些不对。她把姜鹤坤喊来,对他说:“我们家一个都不去,那肯定不行。要不就让济木去吧,鹤卿留下来照顾我!”
姜鹤卿这时正好就在旁边。他忙插话说:“娘,你老人家这样做就不对了!我是叔叔,年纪长些,武功又好,济木是侄子,年纪比我小,武功又不如我,你不让我去,让他去,心不是也太偏了吗?人家该怎么看这事呀?”
“那、那怎么办呢?”耀大娭毑急得直搓手。
“有什么不好办的?我和济木都去不就行了嘛!两个人都去,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呢!”姜鹤卿说。
耀大娭毑手一挥,说:“嗨,算了,算了,那就两个人都去吧!”
一见姜鹤卿,耀大娭毑不觉吓出一声冷汗。她连忙惊呼:“唉哟,儿子呀,你怎么从隔断里跑出来啦?那多危险呀!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还不得抓起来砍脑壳?”
“没事的。鬼子已经来搜查过了,刚走,”姜鹤卿笑笑,“鬼子也放松些了,每天只来搜查一次,今天肯定不会再来了。你老人家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那也不行!那也得进隔断里躲着!不能出来!晓得不?”耀大娭毑使劲大喊。但她再使劲,声音却还是小得只够她自己听见。
“好,好,我过一阵就去隔断里躲起来,这总行了吧?”姜鹤卿说完,又笑了笑。
看着儿子的脸,耀大娭毑有些怀疑。她暗自琢磨道:“鹤卿的样子好怪啊,明明是在笑,脸上却又挂着泪水!他怎么啦?”
琢磨了一阵,耀大娭毑终于憋不住了。她盯着姜鹤卿的眼睛问:“鹤卿,你、你怎么啦?哭什么呀?”
“我哪哭了呀?见到娘,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姜鹤卿抬起手背擦了擦脸,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娘,你看,我这不是在笑嘛!”
耀大娭毑欠欠身子,想坐起来。姜鹤卿连忙伸手按住了她的肩头,柔声细语地说:“娘,你老人家身子还没恢复过来,这会子不能起床,快躺下吧!”
“我、我怎么啦?对了,我、我这是在哪里啊?”耀大娭毑纳闷地问,眼睛忽左忽右地看,满脸疑惑不解的神色。
“娘,你老人家这是在家里呀!你看,这屋不就是你老人家一直住的那间嘛!这床,这被子,这枕头,这椅子,这桌子,还有这小板凳,不都是你老人家一直用的嘛!”姜鹤卿伸出一只手,边说边指点。
耀大娭毑歪着脑袋,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了看四周,叹口气说:“嗯,是在家里,是在家里,我终于回、回家了!”
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耀大娭毑似乎明白自己是在家里了,两只眼盯着房顶,好一阵没言声。但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又陷入糊涂了,偏过脸来,瞪大眼睛问道:“对啦,我不是去长沙城里了嘛,怎么又回家了呀?”
“是呀,你老人家是去长沙了呀,在长沙待了十多天呐,前天才回来的。”姜鹤卿微微笑着,轻声回答道。
“前天才回来?我、我前天回来的?鹤卿,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你把娘搞糊涂了!”耀大娭毑满脸茫然。她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想坐起来。
“别、别起来,快躺下,快躺下!你老人家这会子不能起来的。有话躺着说不也一样嘛,何必非要起来呢,”姜鹤卿伸手按了按耀大娭毑的肩头,又拿起她的手轻轻地塞进被窝里,重新掖紧了被头,“是呀,你老人家是前天回来的,自己一个人走路从长沙走回来的。估计你老人家是一路上没吃上饭,饿虚了身子,又走了一天路,累垮了,到半路还遇上了狂风暴雨,连累带饿,还带受凉挨冻,结果实在撑不住,晕倒在界石镇上了。后来,还是易杂货救了你老人家呢!”
“谁?谁救了我?”耀大娭毑睁眼问道。
“易杂货呀!就是界石镇西头开杂货铺的易老倌,脸上有麻子的那个,”姜鹤卿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你老人家忘了?他约莫四五十岁年纪,单单瘦瘦的身材,经常挑着一副杂货担子来村里收荒货的,还收过咱们家一个大瓷胆瓶呐!他家挨那棵大樟树不远,正好看见你老人家跌倒在雨地里了。当时,他便冒着狂风暴雨把你老人家背到他家里去了。晚上,雨停了,他又叫上儿子,两个人用床铺板抬着你老人家送到家里来了。”
“哦,易杂货,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哪!鹤卿啊,这恩咱们不可不报,”耀大娭毑盯着儿子的眼睛,语气凝重地吩咐道,“你今晚上就去他家,带十块光洋,拿一只阉鸡、一只麻鸭,再到镇上称十斤不带骨头的好猪肉。”
姜鹤卿撇撇嘴,笑着说:“你老人家疼我是假的。明知道鬼子正急着要抓我呢,却还要我今晚去界石镇。那不是要把我送给鬼子吗?”
“哦,对、对、对,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不过,易杂货的恩是肯定得报的,要不就过些日子吧。唉哟,真的是老了,脑子不行了,什么都记不住了,”耀大娭毑皱了皱眉头,忽然又眼珠子一瞪,喊了起来,“对了,白虎呢?怎么没看见白虎呀?”
姜鹤卿眼皮一抬,忙问:“白虎?白虎是谁呀?”
“小狗呀!我从茅草塘曾老婆子家带回来的。对了,那天那么冷,风雨又那么大,它多半冻死了吧?”说着说着,耀大娭毑的眼睛又发红了。
“没冻死,它还好着呢。”姜鹤卿笑笑。
“哦,那太好了!它呢?快抱来我看看!”耀大娭毑精神一震。
姜鹤卿伸手一指,说:“它不就在你老人家床底下趴着嘛!”
“是嘛?”耀大娭毑惊呼一声,连忙歪过头来,想侧转身子往床底下看。
但耀大娭毑已虚弱极了,那身子似有千斤重,哪侧转得过来呀?她动了动,肩头还没转过来,便又身子一倒,倒回去了。姜鹤卿见状,连忙把那小狗抱起来,放到母亲身旁。
经过几天调理,耀大娭毑的体力倒是恢复一些了,能起来坐坐,也能下床在屋里走几步,但神志状况却越来越糟糕,成天糊里糊涂的,嘴巴还不停地念叨着水玉和济勋的名字,以至白天黑夜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
看到母亲这样子,姜鹤卿着急得很。他自己出不去,便托堂兄姜鹤坤遍天下去请有名的郎中。姜鹤坤把远近十多里有名的郎中都请来了,但他们却都治不好耀大娭毑的病。郎中们的看法很一致,都说耀大娭毑的病,表象上看是内伤饥饿、外感风寒,而根子却是忧虑过度,心力交瘁,五脏六腑俱伤,因此不是医药所能治的。有些郎中说得更绝:风寒之病可医,心神之病难治,医家是无能为了,就看天命、造化吧!
郎中们这样说,姜鹤卿自然更急了。从耀大娭毑不停叨唠的断断续续话语中,他大概齐地弄明白了这十多天母亲在长沙城里所经历的事情,知道老人家的病因就在于水玉和济勋两个人的失踪。于是,他也顾不得鬼子什麽时候要来搜查了,动不动就从隔断里爬了出来,跑到母亲床前守着。他掰开了揉碎了地对母亲进行劝解,说吉人自有天相,济勋、水玉都不会出任何事,要她别操空心。但耀大娭毑的满腔心事又岂是儿子几句话所能化解的呢?她人躺在家里歇着,脑子却依然还在长沙城里奔驰,睁眼闭眼都是水玉和济勋的身影,开口闭口也都是水玉和济勋在梁家附近走失的那些事情。
到了回家后的第八天、第九天,耀大娭毑更是一时一刻都安静不下来了。她一会儿掰着手指头,嘴里不断地念叨:“嗯,第八天了,还有两天,济木就带水玉和济勋回来了”,“嗯,第九天了,还有一天,水玉和济勋就回家了”,“嗯,水玉和济勋明天就到家了”;一会儿又对着儿子鹤卿大喊:“鹤卿,把水玉的床铺拾掇好,多铺点新草,把被窝铺盖拿出去晒一晒,弄干净点”;过了一会儿,她又闹着要下床,说是济木带着水玉、济勋回来了,已经过了界石镇,快到石板塘堤上了,自己无论如何要去接一接。她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搅得全家和左邻右舍的心都不安了。
耀大娭毑最要好的朋友,头一个就是景满贞。闹起倔脾气来,她谁的话都不听,唯独景满贞的话还能听得进去。所以,当她闹得不可开交时,姜鹤卿就只好求助景满贞。
到了回家后的第十天,耀大娭毑折腾得更厉害了。一大清早,天刚麻麻亮,她就闹着要下床,愣说济木带着水玉和济勋已经到了石板塘的塘堤上了,她得去接一接。姜鹤卿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实在没辙了,只好跑到景满贞家的台阶上,隔着窗户把她从睡梦中喊醒。
景满贞披上衣服,连茅房都没来得及去,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
一见景满贞,耀大娭毑就喊了起来:“满贞,你来得正好,快,快扶我起来!”
“哟,英莲姐,这一大早要起来干什么呀?这大屋里还没一个人起来呐!”景满贞紧赶几步走上前,扶住了耀大娭毑。
“济木带着水玉、济勋回来了,都快到石板塘了。你说,我能不去接一接吗?”耀大娭毑气喘吁吁地说。
“什么?济木他们到石板塘了?哪有这回事呀?我们家耀宗刚到屋,他是昨天晚上从长沙动身的。他临行前去看过济木,济木对他说要等今天天亮后才动身。你这会儿去接,哪能接到呀?估计他们还没到捞刀河呐,你上哪儿接去?”景满贞说完,朝姜鹤卿挤了挤眼。显然,她是对耀大娭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噢,他们今早上才动身?那是,那是,这会子到不了捞刀河。好吧,那我就再睡一阵,过会子再去接他们。来、来,满贞,你也上床睡吧,挨着我,挨着我!”耀大娭毑边说,边往床里头挪身子,好把床边上的地方腾给景满贞。
“这就对了嘛,咱们睡一觉再去接,免得在路上空等。嘻、嘻,英莲姐,你这被窝里的味道好闻,连屁都是香的。说真的,英莲姐,我就最喜欢跟你钻一个被窝。”景满贞笑嘻嘻的,一迈腿上了床,紧挨着耀大娭毑躺下。
景满贞撒的谎还真起作用,耀大娭毑搂着她睡了一个好觉。只可惜这一觉时间不够长,还没到半晌午,耀大娭毑便醒了。她醒了,就再也不肯在床上躺着了。她闹着要下床,要到外头去,要亲自到大路上去迎接济木、济勋和水玉。景满贞故伎重演,一会儿撒谎说济木他们刚到茶亭寺,一会儿撒谎说济木他们正在半路上吃饭,一会儿又撒谎说济木他们快到界石镇了。但她的这些谎言编得再好,耀大娭毑却横竖不肯听了。姜鹤卿和景满贞都无计可施了,他们只得一边一个架住耀大娭毑的胳膊往大路上走。
事情也真巧,三个人刚走到石板路的北头,还没到石板塘,一抬头忽然看见了塘堤上的姜济木。只见他跌跌撞撞地迎面狂奔而来,冲下塘堤,跑到跟前,一下子跪倒在地,对着耀大娭毑大声哭喊道:“奶奶,你、你这是怎么啦?得什么病了呀?”
耀大娭毑这时候突然变了,变得就跟好人一样,头脑异常清醒。她一把抓住姜济木的脑袋,让他的脸朝上仰着,正对着自己的脸,然后死死地逼视着他的眼睛大声说道:“我没事,你不用管!你就回答我一件事:怎么就一个人回来啦?济勋呢?水玉呢?”
“奶奶,我没用,我没用,我没找到济勋弟!”姜济木泪流满面,嗓子沙哑得厉害。
“难道一点消息都没有?”耀大娭毑声音异常严厉。
“没、没、没有!”姜济木的声音颤抖着,小得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耀大娭毑微微晃动了一下身子,接着又逼问道:“那水玉呢?”
姜济木忽闪着眼睛,朝姜鹤卿看了看,又朝景满贞看了看,好一会儿没言声。
姜济木的举动显然激怒了耀大娭毑。她弯曲着右手中指和食指猛敲姜济木的脑门,厉声大喝:“你、你怎么不说话呀?水玉怎么啦?水玉到底怎么啦?说!快说!”
“水、水玉也没找到,但、但找到了她的……”话说了一半,姜济木又突然停下来了,一双眼睛怯怯地看着耀大娭毑。
耀大娭毑更火了,破口大骂道:“你这砍颈的东西怎么啦?拉屎拉半截!快说呀,你找到水玉什么啦?”
“奶奶,你别着急啊,”姜济木从挎兜里掏出一双花布鞋来递给耀大娭毑,“我、我找到了这双鞋,像是水玉的。但、但也许是我看错了,这鞋可、可能不是水玉的。”
耀大娭毑从姜济木手中接过那双鞋,只拿到眼前晃了晃,就立马说道:“没错,这鞋是水玉的,还是临走前我给她做的呐。济木,你、你是在哪里找到这双鞋的?”
姜济木又不说话了,眼睛瞥了瞥姜鹤卿,又瞥了瞥景满贞。
“你看,你看,话说了一半又不说了,尽屙半截屎!快说呀,水玉这双鞋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耀大娭毑声音很高,根本不像重病在身的人。
“在、在河边,就、就是梁家附近那段江堤下边的一块大、大石头上。”姜济木话没说完,眼泪已哗哗地流了下来。
“哦,这鞋是在河边捡到的?这么说,水玉那孩子投、投水啦?啊,我可怜的孙女!”耀大娭毑突然嚎啕大哭,但她只哭了一声,便头一歪,昏晕过去了。
耀大娭毑的病情急转直下,一连五六天水米不进。郎中们看了,都直摇手。
得知耀大娭毑病情加重的消息,左邻右舍、亲朋戚友纷纷前来探视。这天上午,姜耀宗回来了。他刚一到家,撂下行囊,便急急忙忙地来看耀大娭毑。姜耀宗的回来,带来了张颂臣、姜耀成等人的问候,还带来了梁家原来的那些老邻居——张老婆子、齐家婶子、贾家大姐、刘老太太等人的问候。
听到了老朋友们的问候,耀大娭毑的心情略略好受了一些,但依旧苦着一副脸,不停地长吁短叹。姜耀宗剥了一个橘子给她,她不肯吃。姜耀宗递给她一块蛋糕,她也不肯吃。姜耀宗问她想吃点什么,她又摇了摇头。姜耀宗急了,张口就埋怨道:“唉哟,老嫂子呃,你的心思也太重了吧!这也不吃,那也不喝,那不是等死吗?”
“是呀,我就是在等死,”耀大娭毑叹口气,泪水直流,“孩子们死了,是我害的。你说,我还能活下去吗?”
姜耀宗一惊,连忙说:“哟,这我就不懂了,怎么是你害的呢?”
“怎么不是我害的呢?明摆着的嘛,我要不带他们去长沙,不把他们的身世当面告诉他们,他们能跑吗?”耀大娭毑不断地伸手抹眼泪。
“呵呵,那就好笑了,”姜耀宗似笑非笑,“你不把他们的身世说出来,眼看着他们嫡亲兄妹通婚,犯人伦大错,那就好了吗?”
耀大娭毑一时语塞,表情木木的。过了好一阵,她才缓过神来,小声说:“那总也比让他们去死好啊,对不?”
“不对!我宁肯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死,也不能眼看着他们肮肮脏脏地活着,”姜耀宗勃然大怒,情绪激昂,语音铿锵,“兄妹通婚,一根肠子里爬出来的做夫妻,那叫什么?那不是犯错,而是犯罪!那样做,祖宗牌位里头是写不进去的!那样做,我们姜家,包括所有活着的族人,也包括所有的祖宗和子孙后代,都会要羞死的!老嫂子呃,你告诉他们实情,那是对的!他们自己想不通,要跳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你无关!他们真要是自杀了,你也别想他们了,算你自己瞎了眼,白疼他们一场了呗!这么明白的道理,他们都明白不了;这么点芝麻小事,他们都想不开;为了兄妹之间本不应该有的那点情,闹得昏头胀脑,投河上吊,那还是个人吗?这样的人不死,留在世上有什么用呀?”
姜耀宗脾气好,平时不大说狠话,这一次却出乎意料,话说得异常激昂慷慨。
听了姜耀宗这一番话,耀大娭毑不觉脸红心跳,头脑清醒多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耀宗,你说得对,我想通了。他们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唉,从今以后啊,我也不想他们了,就当从来就没有过他们好了。”
“呵呵,嫂子,你还真以为他们死了?”姜耀宗笑了笑。大概是狠话说完了,火气发光了,他这时候的脾气小多了,说话的语气平静了许多。
“济勋还不好说,水玉肯定是死了,”耀大娭毑眼眶一红,眼泪又差点流了出来,“她的鞋都找到了嘛,是在江边上找到的。明摆着,她投水了呀!”
“投水就一定能死成吗?”
“那当然喽!她投的不是小水塘,而是大河呀!那么深的水,她还能不死?”
“我看未必!那地方,我去看了,水不深!”
“是呀,江边上的水是不深,这我知道。但江中间的水深呀,对不?她诚心要寻死,当然会往江中间走喽,还能老站在江边上不动?”
“她即便是到了江中间,那也死不成!”
“那为什么?”
“江中间来来往往的船那么多,人见了,还能不救?”
“人救?哼,我看没人会救。阳世间都这样子了,人人自顾不暇,谁还有那好心眼跳到那么深的江水里去救人呀?”
“不,好人还是不少。我就亲眼看见过好多人跳河,结果都被船上的人救起来了。说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过一个人投河死成了的!”
“真的?”耀大娭毑一声大叫,眼光突然发亮,盯向姜耀宗。但仅仅过了一会儿,她的眼光就从姜耀宗的脸上移开,渐渐地黯淡下来了。
“怎么?你不信?”
“信是信,但水玉肯定没被救起来!”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
“当然喽!她要是被救起来了,就一定会回家,对不对?可是,我和济木在她家住了那么久,都没见她回来呀!”
“嗨,嫂子呃,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水玉怎么会回家呢?”
“怎么不会回家呢?”
“她父母都死了,还回家干什么?等孙棒子抓她呀?”
“哦,你是说她是在知道父母已经死了的消息以后投河的?”
“那肯定是这样的喽!你想想噢,”姜耀宗一边说,一边掰起了手指头,“水玉那天离开家是天快亮的时候,对不?孙棒子带兵到她家来抓人是一大清早,对不?这中间时间很短,最多也就一两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她根本就来不及回家,因为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情绪平静下来,对不?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她也许想通了,情绪平静下来了,想回家了,但这时却已迟了,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她父母已经被抓走了。她很聪明,肯定晓得孙棒子在家里埋伏了重兵。她当然是不会甘心自己的清白之身被孙棒子玷污的,于是一怒之下便跑到江边投水了。”
“依你这么说,那水玉就不一定晓得她父母死在牢里和后来我们游行示威的事喽?”
“游行示威的事,她是肯定不知道的。她要是知道的话,当时就会现身,而且会积极参加。这是为她和她父母报仇的事,她哪能不参加呢?至于她父母惨死在牢里的事,估计她也不知道。明摆着,她父母亲被关在哪个牢里,她不一定晓得。而且,她即便是晓得父母关在哪个牢里,她也肯定不会去探视。她很聪明,当然不会不明白孙棒子抓她父母是在用钓鱼之计,目的在于抓她。如果她去探监,不仅救不了父母,反倒会害了自己。我估计呀,水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心思。”
“哦,另外一种心思?那是什么心思呀?”
“我估计呀,水玉投水自杀,不一定完全是为情所困,自己想不开,而很可能还存着一份救父母亲的心思。她很清楚,孙棒子之所以抓她父母,目的是为了得到她。因此她就想喽:我不死,孙棒子就老存着得到我的幻想,不放我父母,要逼我就范;那要是我死了,孙棒子晓得无论怎么做也得不到我了,不就会放了父母吗?她这么一想,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自杀的冲动喽,对不?”
“耀宗,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多了。看来,水玉肯定是跳河了,但会不会被人救起来,那就得看她自己的命运喽!那济勋呢?他会不会是也跳了河呀?”
“济勋不会,肯定不会!水玉跳河,是确实有原因的。孙棒子要抓她,还把她父母关进牢里了,这是她跳河的两大诱因。济勋哪有这些诱因呀?没有这些诱因,他跳河自杀干什么?疯了啊?被鬼打昏了脑壳啊?”
“那会不会是他看见水玉跳河了,于是也就跟着跳下去了呢?”
“不会的!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明摆着,到现在还找不着他的人影呀!”
“那孩子心气高,”姜耀宗抬手摸摸下巴颏,“我估计呀,他是找事做去了,过些日子就会买一大堆东西回来看你的。老嫂子呃,你等着吧!”
和姜耀宗说了好一阵话,耀大娭毑的精神好多了。姜鹤卿见母亲见好,就问她想吃什么,要不要熬点粥喝。耀大娭毑想了想,说:“到时候跟着一起吃点饭就行了,粥就别另外熬了。要是有现成的好开水,就沏碗茶吃吧,只是没盐没豆子了哦!”
那年月,盐最金贵。姜家这几年连着出事,既要筹备盖房,又要延医治病,还要进长沙城寻人,耀大娭毑先前攒下的一点积蓄早就花光了,哪还有钱买盐吃?所以,一家人差不多有好几个月没粘过盐味了。姜鹤卿在家里翻了半天,竟然没寻出一丁点盐来。没办法,他只得去景满贞家借盐了。但他刚出门,迎面便碰上了姜鹤慧。
姜鹤慧是姜鹤卿的堂妹妹,在鹤字辈中年纪最小,比姜鹤卿还小两三岁。她是姜耀柏的女儿。姜耀柏后来生意衰败了,就把她和她的两个哥哥及其家人从陕西西安送回了湖南老家。但她虽是姜耀柏的女儿,脾气性情却大不相同。她是一个非常诚实、厚道、善良的人,为人谦和,特别乐于助人,和耀大娭毑的关系也极好。耀大娭毑得病以后,她就天天来帮忙做事,有时还整天整夜地守在病床边。
姜鹤慧听姜鹤卿说要去景满贞家借盐,便忙打阻说:“你别跑了吧!我们家有盐,炒黄豆也是现成的,我现在就打转回去拿点来!”
姜鹤慧回自己家拿盐和黄豆去了,姜鹤卿便忙着烧开水、拿茶叶、磨姜汁,做沏茶的准备。但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却还没见姜鹤慧回来。他实在等不及了,便跑到景满贞家拿了一点盐和黄豆回来,沏好了一碗姜盐豆子茶,双手捧着,递到耀大娭毑嘴边。
耀大娭毑好长时间没喝过姜盐豆子茶了。她聚精会神地盯着那碗茶看,看了老半天,才微微低头抿了一口。这一口喝下去,她立刻眉开眼笑了,情不自禁地嚷嚷道:“好吃!好吃!还是咱们老家的茶好吃!哎呀,就可惜缺点芝麻和桂花!”
喝完一碗茶,耀大娭毑的精神又好了些。她靠着床头半躺着,眼睛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蓝天,一只手指头伸进嘴里剔着牙缝里的茶叶,神情显得安详适意。过了一会儿,牙缝里的茶叶剔出来了,她一边弹手指,把茶叶弹到地上,一边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阎王爷那里有没有姜盐豆子芝麻桂花茶吃,要是有,可就太好了!”
姜鹤慧手里拿着一小瓶盐和一小碗炒熟的黄豆匆匆忙忙地跑来了。她眼圈红红的,脸上还带着泪痕。姜鹤卿一见,便埋怨道:“哎哟,我的姑娭毑,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八成是你哥不让拿盐来吧?嗨,也难怪,这年月盐也实在太贵了,比得上黄金,谁舍得往外拿呢?”
“不,我哥没不舍得!”姜鹤慧说。
“我不信!你哥是个吝啬鬼,能让你拿盐出来?他多半骂你了吧,要不你为什么哭了呢?”姜鹤卿说。
“我哥没骂我!我拿盐出来,是背着他的,他根本就没看见!”
“那就奇怪了,你哭什么呢?”
姜鹤慧不说话了,低着头,不停地用手背擦眼睛。这一切,耀大娭毑都看在眼里了。她把姜鹤慧拽到自己身边坐下,轻声问:“鹤慧,好闺女,家里出什么事啦?能告诉伯妈吗?”
“没、没什么事!”姜鹤慧头压得更低了。
耀大娭毑伸手把姜鹤慧拉近了些,抚摸着她的肩头说:“怎么能没事呢?你心里头那么难受,那肯定是有事呀,对不?孩子,别藏着掖着了,快跟伯妈说实话吧!不说出来,你难受,伯妈也难受呀!”
“那、那好,我说出来,你老人家千万别着急啊,”姜鹤慧擤了一把鼻涕,哽咽着说,“我大哥家的老三济芬和二哥家的老二济芳被土匪劫持了!”
耀大娭毑大吃一惊,忙问:“哟,被土匪劫持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就、就、就刚才!”姜鹤慧泪如泉涌。
“济芬、济芳不都是姑娘家嘛,最多也就十二三岁吧?平常看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会突然被土匪劫持呢?”
“嗨,这、这也得怪、怪她们自己,”姜鹤慧又擤了一把鼻涕,控制了一下情绪,“她们在家里待不住,老想上大山里去看看,说了几次也不听。今天一大早,她们也没跟大人打声招呼,就拽上我二哥家的老二济崇悄悄地出门走了。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踢石头子玩,刚进山就看见路边坐着几个衣服特别破旧、浑身又黑又脏的男人。济芬最爱干净,见那几个人脏兮兮的,样子很难看,觉得恶心,便小声骂了一句‘臭要饭的’。谁知这一骂就骂出麻烦来了。那几个男人当时就冲上来,抓住三个孩子又打又骂。打完了,骂完了,他们又抓住三个孩子往山里头走。走到常家洞附近时,他们又忽然把济崇放了,要他回来给家里报信,说是要拿一千块光洋去盘山寺赎人。他们还说,如果三天之内见不到一千块光洋,他们就要把两个女孩子留在山里当压寨夫人。我刚才回家时,赶上济崇也刚到屋,正在说遇上土匪的事呢。我听得心里又慌又乱,所以就忘了拿盐的事,耽误了你老人家吃茶的事,真不好意思!”
“嗨,什么‘耽误’不‘耽误’的,我吃茶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打紧?你别在意,”耀大娭毑说,“对了,鹤慧,济崇是男孩子吧?今年多大了?有十五六吗?”
“是呀,济崇是男孩子,今年满十六了,四月份的生日。”
“难怪土匪放了他呢,他们觉得十六七的男孩留在身边既没用还碍事嘛。济崇要是个女孩,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只怕就更糟了。哎哟,我的娘呃,这土匪也太猖獗了,大白天竟敢劫持人!鹤卿,”耀大娭毑转头看着姜鹤卿,“你快去找鹤坤,把这事对他说说,要他赶紧商量救人的事。你对他说,就说是我的意思,土匪是不可信的,跟他们讲不得客气,拿钱赎人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的,只能动武,派人直接去盘山寺救人。土匪狮子大开口,要一千光洋。如今这世道,谁家拿得出一千光洋啊?再说喽,就是拿得出一千,也不能给!这帮土匪实在太可恶了,白昼劫人,为害一方,我们哪能容忍啊?干脆,咱们趁着救人的机会把那帮子土匪灭了吧,也算是为地方上做件好事。不过,要去救人,动作就要快,最好是今天晚上就去,千万耽误不得。要是拖久了,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或是把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可就麻烦了!”
姜鹤坤新近刚被大家选为族长。他正在家里拾弄猪栏屋,满手满脚都是猪粪,浑身上下臭烘烘的。他还不知道土匪劫持孩子的事呢。姜鹤卿把事情一讲,他吃惊地说:“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呀?那鹤喜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姜鹤卿笑笑说:“那还用问,他们不好意思呗!”
“嗯,兴许是,”姜鹤坤点点头,“也没准他们觉得我这个族长是新上来的,不管用,所以就不来找我了。不过,他们不来找我,我就得去找他们了。这事太大,族里不管不行!”
“那你打算怎么管呢?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娘的意思是动武。她说对土匪不能信,更讲不得客气。”姜鹤卿说。
姜鹤坤抬眼看着远方的照壁山,斩钉截铁地说:“老人家的意见是对的。跟土匪没得客气可讲,只有打这一条路。别说没钱喽,就是有钱,也不能给他们。他们动不动就下山抢钱抢东西,动不动就把人劫持到山上去,搞得地方上民不聊生,人心惶惶,这还得了?这次要是容忍他们了,给他们钱了,他们下次还来村里劫持人,那怎么办呀?祸根不除,为害无穷。不行,这仗非打不可。但是,这仗不打就不打,打就一定要打胜。而要打胜,就一定要做好准备。至少我们得先摸摸情况吧?比如说:盘山寺的地形怎么样啊;要打的话,先从哪里开始进攻啊;土匪总共有几个人啊,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啊,手中有没有真枪实弹啊;孩子抓走后情况怎么样啊;她们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啊。这些情况,我们都得先摸清楚。只有摸清了情况,我们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没错,是得先摸清情况,”姜鹤卿说,“那,坤哥,要不我先到盘山寺附近跑一趟,探探路,摸摸情况?”
姜鹤坤把眼神从照壁山上移回来,低头沉思,好半天才说:“你去?那不行吧?鬼子正盯着你呐,要是你被他们抓走了,我大娘还不得把我吃了?”
姜鹤卿笑笑,不慌不忙地说:“有个情况你还不晓得吧?我那未过门的堂客就在骆家坳。骆家坳就在盘山脚下,离盘山寺很近。她常去盘山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我去找找她,打听打听情况,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呵呵,你堂客就在土匪窝里,”姜鹤坤看着姜鹤卿,眯起眼睛,诡秘地一笑,“哼,我还真以为你是急公好义呢,原来里头有这层关系!探路是假,找堂客亲热是真吧?”
“嗨,这时候哪有心思开玩笑呀,都屎到P股门了,”姜鹤卿一脸正经,“快拿主意吧,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那既是这样,你就跑一趟呗!但你是你娘老子的心头肉,她会放心你去吗?”
“不要紧的,不跟她说实话就是了。”姜鹤卿说。
“好,你去吧!千万注意安全啊,别让鬼子发现了!最好是从山里走,从树林子里穿,绕开大路,明白吗?”
“明白,出不了事的!我现在就走!你去我家里,撒个慌,稳住我娘!”
中午饭后,各家的男子汉就都来正堂屋开会了。姜鹤坤把事情一说,大家立刻炸开了锅,七嘴八舌,什么意见都有。有人嚷嚷:“事情都这样了,还开什么狗屁会呀?瞎耽误工夫!还不赶紧抄家伙上山救人去?”有人慢腾腾地说:“事情没那么邪乎吧?盘山寺也就七八个小毛贼,能有那大胆抓住人不放?没准也就是吓唬吓唬鹤喜,要他出点血罢了!”也有人幸灾乐祸,不阴不阳地叨唠道:“该!这就是天报应!谁叫耀柏叔那么贪心,私占公户建房盖屋呢?要依我说,这事就不该管,听他自作自受!”
说话的人中,有不少是反对动武的。他们反对动武,原因当然有多方面。有些人是因为胆子小,不敢动刀动枪,害怕伤到自己。有些人是因为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想法,不愿意为别人管闲事、卖力气。还有些人则是缺乏信心,不相信族里这些人真能办成到土匪窝里救人的大事。
反对动武的这几种想法,姜济胜无一不有。一进正堂屋,他就把和自己走得近的几个小年轻拉到一起,找一个犄角旮旯蹲了下来,无边无涯地说起了风凉话。起初,他那些风凉话还只是小声议论,当听到有人说“这事就不该管,听他自作自受”时,他的风凉话就立刻变成大声嚷嚷了。他扯开嗓门对着堂屋里吆喝道:“没错,这事就是不该管!明摆着,这事咱们没法管呀,对不对?土匪是什么人?他们是天天在山里摸爬滚打惯了的,地形熟,会走山路,个个武功出众,还有真刀真枪。咱们呢?咱们能跟他们比吗?咱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呀,天天就和泥巴打交道,从来没练过武,别说真刀真枪喽,就是木棍子都不会使。就咱们这能耐,打得过土匪吗?我不是吓唬你们,咱们要真是上山和土匪打,别说救出那两个小姑娘了,不被土匪戳死就算便宜!搞得不好的话,只怕脑袋都得搬家!咱们可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父母谁管呀?老婆谁管呀?孩子谁管呀?人生在世呀,就得认命。事情让谁赶上了,谁就得认命,不要牵扯别人,别人也没必要为他去送命。要依我说,这上山救人的话就别再说了,那是他娘的没用的屁话!耀柏家的这档子事就听其自然吧!他要是有钱呢,就拿钱去赎人。他要是没钱呢,就把女孩留在山上当压寨夫人算了!当压寨夫人也没什么不好嘛,天天不用做事,没准还能吃香的喝辣的呐!”
姜济胜一说话,他身旁的那几个小年轻就跟着起哄。一时间,反对上山救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占了上风。
姜鹤扬早就憋不住了。他猛地站了起来,对着姜济胜大吼道:“济胜,你那话才叫做屁话呢!什么‘认命’不‘认命’哪?什么‘牵扯别人’、‘为别人送命’哪?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出了事不应该帮把手吗?按照你这逻辑,大家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那好吧,将来你们家出了事,我们也都不管,看你怎么办?”
“对,鹤扬叔说得太对了,”姜耀希的孙子济民挥着拳头说,“要是济胜大哥他堂客被土匪抢走了,我们就不管,让她给土匪当压寨夫人算了。她堂客可是咱们村的头号美人哪,长得漂亮极了,土匪要是抢了,准保还没到晚上就得玩得稀巴烂。”
姜鹤季在鞋底子上嗑了嗑旱烟袋,慢腾腾地说:“是呀,济胜,你真的太不像话了。济芬、济芳那俩孩子才多大呀,你就说让她们当压寨夫人算了。亏你还是她们俩的大哥呢,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你还是个男子汉吗?你爸平常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我真不明白,耀松大伯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孙子,真是丢人现眼哪!”
“济胜啊,你也太看低咱们农民了。农民怎么啦?农民就玩不过土匪?你数数看,哪朝哪代的天下不是咱农民打下的?刘备还织过履、贩过席、种过菜呢!太平天国的那些大将们哪个不是农民呀?农民要是连几个小毛贼土匪都对付不了,那也就不是好农民了。我也不是说大话,别说那山上只有七八个土匪,就是再多十个八个,咱们也能对付得了。大家都没真刀实枪地干过,但却都不怕,你怎么就那么胆小害怕呢?难道你特别,生来就是软骨头?”姜鹤扬冷嘲热讽地说,说完还轻蔑地朝地下啐了一口唾沫。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朝着姜济胜开火,姜济胜和他那一伙子就都哑巴了。于是乎,主张上山救人的这一派又占了上风。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门外忽然传来了喊叫声。那是姜耀典。他担心儿子鹤仲、鹤季跟着上山救人会有危险,便戳着根拐棍出来,站在南大门的门廊里,对着正堂屋大喊:“鹤仲、鹤季,你们两个赶紧回来,我还有要紧事等着你们做呢!”
姜耀典大喊大叫了好半天,姜鹤仲和姜鹤季兄弟却都不理睬。姜鹤坤觉得不大好,便扫了一眼姜鹤仲和姜鹤季说:“要不你们兄弟把一个回去看看吧!”
“我来吧,”姜鹤季站起来,走到门口,扯开嗓门对姜耀典大声说了起来,“爷老子,大家说了,你要再大喊大叫的话,族里就不管我鹤康哥和鹤鹏弟的事了,看你怎么办?”
姜鹤季这句话真起作用,姜耀典不出声了,头一扭,戳着拐杖回去了。
议论好半天了,该收尾了,姜鹤坤站了起来,边走边措辞,想说几句。正在这时,景满贞和姜鹤慧忽然推门进来了。景满贞一进门,就对着姜鹤坤嚷嚷起来:“鹤坤,上山救人的事,别落下我和鹤慧,我们俩也去!”
“哎哟,二娘,这是男人们的事,你、你们就别来瞎掺合啦!”姜鹤坤说。
景满贞眼睛一瞪,大声嚷道:“什么话?上山救人还分男女?小瞧你二娘是不是?你二娘不比你差,不信上来试试!”
景满贞这一说,满堂屋人都大笑起来:“好,快来看吧,母子俩比武喽!母子俩比武喽!”
姜鹤慧也笑了。笑了一阵,她便款款地走到堂屋中间,做了个请肃静的手势,看了姜鹤坤一眼,然后朝前后左右的人群各鞠一躬,轻声说:“大家为我们家的事操心了,我代表我大哥、二哥及我们全家所有的人谢谢了!鹤坤哥,各位哥哥,刚才满贞婶子说我们两个也要上山救人,这不是瞎掺合,而是我们的真心实意。我们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去,去了也有好处。我们去了,没准还能成为秘密武器,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呢!”
“哟嗬,鹤慧,你是什么秘密武器呀?”大家纷纷起哄,堂屋里热热闹闹。
“那当然喽,这事很明白嘛,”姜鹤慧说,“我那两个侄女刚从陕西来湖南不久,听不大懂湖南话,跟大家也都不熟。因而如果需要她们配合的话,她们就可能配合不好,难免耽误事。如果我和满贞婶子同去的话呢,情况就可能会好得多,因为我会说陕西话,我又是个女人,两个孩子跟我又很熟,她们都能听我的,沟通起来会比较容易嘛。”
“嗯,有道理,有道理,”姜鹤坤点点头说,“秘密武器,那你就和我娘一起去吧!不过,我把话说在头里,得绝对服从我指挥哟!”
景满贞和姜鹤慧的激情感染了大家,满堂屋的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加上山救人的战斗。姜鹤坤见大家热情高涨,心里很高兴,便想趁热打铁,把上山的人选定下来。他正要宣布人选,门口突然进来了姜鹤卿,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人三十出头年纪,个头高大,身强体壮。
见来人了,姜鹤坤忙上前招呼。姜鹤卿一伸手,指指身后的人说:“坤哥,他叫骆根宝,是骆家坳的,我姐夫!”
姜鹤卿话音刚落,几个小伙子就喊起来了:“哟,鹤卿叔,你不就三个姐夫嘛,怎么今天又来了一个姐夫呀?怎么回事,快说说!”
姜鹤卿腼腆,脸爱发红。见大家起哄,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脸不觉红了起来。姜鹤坤见状,连忙替他解围。“别起哄了,商量正事要紧!”姜鹤坤边说边向大家挥了挥手。
紧接着,姜鹤坤又招呼骆根宝到堂屋中间坐下,请他介绍盘山寺的情况。骆根宝倒也是个大方随便的人。他略略客气了几句,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原来,盘山不太高,也不太大,但异常陡峭险峻。山峰东、南两面都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北面有一条长达十数里的深涧构成天然屏障,只有西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峰顶。那羊肠小道也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围绕着山峰盘旋而上,分三盘六坡二十一弯,关卡障碍有很多处,处处易守难攻。
山半腰有一个寺庙,那就是盘山寺。盘山寺很小,只有一个山门、一个大殿、两间配殿。大殿的后头,还有一排矮小的平房,那是做住房、厨房以及堆放柴火杂物用的。寺庙的山门紧邻那条通往峰顶的羊肠小道。羊肠小道的另一侧,就是那条险峻万分的天然屏障山涧了。
盘山寺里原来有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土匪们来了以后,便把他们赶出去了。那两个和尚从此便真正成了“出家人”,无家可归,只得到处流浪了。
土匪总共有八个,多为外地人,年纪多在三十岁左右,而且多数都是叫花子出身。为首的姓金,不知名字,土匪们都叫他金大脑袋。这人个头不小,身体也壮实,有些武功,一手棍法使得不错。土匪中还有一个叫金猫的,个头不高,人很消瘦,长得就跟猴子似的,但其貌虽不扬,武功却不弱,尤其轻功了得,在山上奔跑如履平地。除了金大脑袋和金猫之外,土匪中就再没有什么武功好的了。
土匪们占据盘山寺不久,还没有搞到什么枪支弹药一类的武器。他们使的多数都是棍棒,偶尔也有用大刀和梭镖的。但那些大刀和梭镖也多半是样子货,有的材料不真,有的棒头太轻,有的还陈旧得生了锈。因此,总的来说,他们的势力并不强,没有太大的战斗力。
骆根宝详细介绍了盘山寺和土匪们的情况,临末了还对姜鹤坤说:“你们人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就多派几个人和你们一起干。不说多了,我们村一二十个壮小伙子还是派得出来的,而且个个都是猎户,身手好,地形熟!”
姜鹤坤一听,连忙紧紧握住骆根宝的手说:“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我们村的人手倒是不少,会武功的也有几个,估计对付那几个小蟊贼也足够了,可就是地形不大熟,夜里头看不清地形地势,走那三盘六坡二十一弯可能会有些犯晕。要不你就派几个路熟的给我们带带路吧,其余的人就不麻烦了!”
骆根宝低头看着地面,沉思有顷,说:“坤哥,我们村离盘山寺近,平常受土匪的侵害最多,早就有心灭掉他们了。你们这次上山打他们,其实也是在为我们村做好事。所以呀,我们村多派几个人参加也是应当的。要不这么吧,我派几个身手好、地形熟的给你们带路,然后我自己再带几个人协助你们进攻,听你的指挥,行吗?”
“那好吧,你回去安排人,”姜鹤坤对骆根宝说,“我们晚饭后就动身,到你们村口会齐!”
送走骆根宝,姜鹤坤就开始选派人手。他这个瞧瞧,那个看看,斟酌了好半天,最后才选定了十六个人。但这十六个人中,有姜鹤卿,却没有姜济木。这一来,姜济木不高兴了,耀大娭毑也不高兴了。
姜济木不高兴,是因为他自己想去。耀大娭毑不高兴,是因为她不想让小儿子姜鹤卿去。她既担心小儿子姜鹤卿夜里走山路时不小心跌倒伤了脚,又害怕他跟土匪搏斗时伤了身子。她想得很细,一个人没完没了地瞎琢磨:“刀枪可是没长眼睛的呀!要是土匪玩命地打,一枪戳来,正好戳中了鹤卿的眼睛,或是戳中了鹤卿的胸口,那该怎么办?”她越想越怕,想着想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耀大娭毑的心思,让姜鹤坤知道了。姜鹤坤连忙作出决定:姜鹤卿也不上山救人了,留在家里照顾病重的母亲。
姜鹤卿和姜济木都不参加上山救人的战斗了。这事显然有些不妥。果然,村里很快就有人议论开了,说是耀大娭毑有私心。
耀大娭毑没有听到人们的议论,但她也觉察出自己好像有些不对。她把姜鹤坤喊来,对他说:“我们家一个都不去,那肯定不行。要不就让济木去吧,鹤卿留下来照顾我!”
姜鹤卿这时正好就在旁边。他忙插话说:“娘,你老人家这样做就不对了!我是叔叔,年纪长些,武功又好,济木是侄子,年纪比我小,武功又不如我,你不让我去,让他去,心不是也太偏了吗?人家该怎么看这事呀?”
“那、那怎么办呢?”耀大娭毑急得直搓手。
“有什么不好办的?我和济木都去不就行了嘛!两个人都去,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呢!”姜鹤卿说。
耀大娭毑手一挥,说:“嗨,算了,算了,那就两个人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