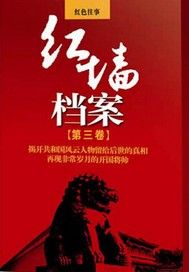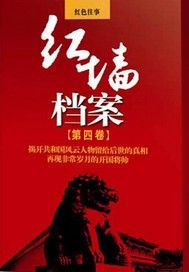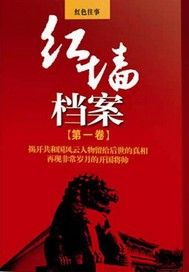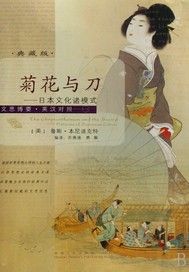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二十三章
耀大娭毑觉得,这次游行示威活动搞得如此沸沸扬扬,差不多全城全省都家喻户晓了,梁水玉再怎么躲着藏着也该知道了。而她知道了,也一定会很快跑回家来的。所以,游行示威一结束,她就守在梁家不出门了。
耀大娭毑坚信梁水玉会回来。然而,两天过去了,梁水玉没回来;七、八天过去了,梁水玉还是没回来。“这、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莫非她跑到外地去了?莫非她遭到鬼子的毒手了?莫、莫非她出其他什么事情了?”
耀大娭毑不敢再往下想了。她原本打算在见到孙女梁水玉以后,就赶紧带着她一起回乡下去的。梁水玉老也不回来,她便在梁家待不下去了。耀大娭毑心里最着急上火的,是小儿子姜鹤卿。临离开家来长沙的时候,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叮嘱过姜鹤卿,要他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好待在隔断里别出来。同时,她也反复嘱托过景满贞,要她把姜鹤卿当亲儿子管,管紧管严,管得死死的。
耀大娭毑度日如年,实在待不下去了。这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她就叫孙子姜济木起床了。姜济木睡得死,叫了几次也叫不醒,她就揪他的耳朵,打他的P股。
“济木,奶奶在这里实在待不住了,家里好多事情都还等着奶奶回去做呢!奶奶今天要回去,现在就走!”耀大娭毑把嘴巴贴在孙子的耳朵根子上大声说。
“是嘛,今天回家?那好啊!”姜济木听说要回去,连忙一翻身坐了起来。他还以为奶奶是要带他一起回家呢。
耀大娭毑伸手按住姜济木的肩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天还早,你别起来,接着睡吧!奶奶一个人走,你不走!”
姜济木急了,一边揉眼,一边大声嚷嚷:“你老人家要一个人回去?那怎么行!你老人家知道码头在哪里吗?知道船票怎么买吗?”
“我干什么非要知道码头在哪里、船票怎么买呀?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哪能坐船呢?要回去,也只能是走路喽!”耀大娭毑说。
“走路回去?那我更不放心了,”姜济木一翻身下床,抓住衣服就往身上套,“回家的那条路,你老人家还从来没走过的,走错了、找不到家了怎么办?”
“唉呀,你这孩子也太小瞧奶奶了。湘长官道,笔直的一条路,谁不会走呀?没走过,问一问不就会走了吗?嘴巴底下就是路嘛!”耀大娭毑撇撇嘴。
“奶奶,我、我还是跟你一起走吧!路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的岗哨呢,要是把你老人家抓走了,那、那该怎么办?”姜济木嘟嘟囔囔。
“嗨,这你就大错特错啦,”耀大娭毑拍着巴掌说,“我一个人走,鬼子倒不会抓,要是你在身边,那可就危险了。明摆着,鬼子不会抓我的。我一个老太婆,他们抓我干什么?没用呀,对不?他们抓我还嫌麻烦呢。要派人看着,要给我饭吃,我要上茅房,他们还得派人跟着,那多麻烦呀。他们能自找麻烦抓我吗?不会的!可你就不同了。你是大小伙子,有力气,能修碉堡,能挖工事,能搬枪抬炮搞运输,能干很多的事。鬼子缺劳力,见了你,还能不抓?你被抓走了,我能站在旁边干瞪眼看着不管吗?不能吧?那我肯定得跟他们拼老命的!这样一来,那咱们两个可就都完蛋了!所以呀,你无论如何不能跟我一起走,明白吗?再说,我走了,你也走了,那谁来找济勋和水玉呢?水玉回家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孩子呀,你是奶奶的乖孙子,就听奶奶一句话吧,别走了!你留下来,在这屋里住着,等一等水玉和济勋。另外,张老板城里的米行也快开业了,他也离不开你呀,对不?”
耀大娭毑这几句话起了作用,姜济木明白自己确实不能走了。他一P股坐到床边,嘟囔道:“路、路不会走,倒、倒是可以问。可那么远的路,差、差不多有一百里,你、你老人家行吗?万一路上出了事,那、那该如何是好呀?”
“哎哟,能出什么事呀?你别瞎操心好不好?大小伙子一点也不利落,老婆婆妈妈的,”耀大娭毑训斥道,“济木,奶奶可给你说好了噢,找水玉和济勋的事可就完全交给你一个人了。找到了他们俩,你就一起带回。没找到济勋,只找到了水玉,也要赶紧带回家。万一谁都没找到,那也得及时和我通信息,明白了吗?和你说好了吧,从今天算起,到第十天头上,不管怎样你都得回家一趟,把个信给我。”
耀大娭毑转身就走。但她刚刚走到门口,还没来得及跨门槛,姜济木突然又喊起来了:“奶奶,奶奶,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老人家说。”
“什么事?”耀大娭毑站住了,回头问。
“是……是……,是这样……”姜济木红着脸,吱吱呜呜。
“哟,怎么扭扭捏捏呀,”耀大娭毑好奇地打量着孙子,“莫不是你小子把小颖搞上床了吧?怎么样啊,肚子没搞大吧?”
“没、没、没,”姜济木满脸通红,“你老人家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哦,没这事呀,那你慌什么啊?”
“这、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有话就快说!”
姜济木低着头,眼睛看着地,结结巴巴地小声说:“那、那年鬼子打田营镇,进、进了小颖家,把、把她和她娘都那、那个了!”
“哦!”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打来,耀大娭毑懵了。她眼睛瞪得老大,直直地盯着前方,仅仅吐了一个“哦”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姜济木愣愣地站着,斜眼瞟了一下耀大娭毑,颤抖着声音说:“明、明摆着,这事不、不是小颖的错,怪不得她。你老人家就谅、谅解她,让、让她和我相、相好吧!反正这一辈子,我是永、永远也离不开她了!”
好半天,耀大娭毑才缓过神来。她低头看着地,缓缓地说:“这事不是她的错,我没怪她的意思。这你放心。但婚姻大事实在太大了,不能草率,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说完话,耀大娭毑拔腿就走。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走出屋门,姜济木直直地站在当地发愣,心里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
城里的一段路,耀大娭毑走得倒还比较顺利,但出了城可就很不顺利了。日本鬼子在城郊接合部的交通要道设置了很多岗哨,其中有一个关键路口被封死了,过往行人一概不放行,除非持有宪兵队颁发的特别通行证。那路口是从长沙去往湘北县的必经之地。这一来,耀大娭毑着急了。她一个乡下来的老太婆,长沙城里没一个说得上话的熟人,去哪里找宪兵队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呢?她好说歹说都没用。说多了,鬼子还要拿枪托砸她。没办法,她只得忍气吞声往回走了。
往回走了里把多路,耀大娭毑偶尔一回头,突然发现左边的小路上有七八个人正神色慌张地往一个小山上跑。“哟,那拨人干嘛往山上跑呀?莫非那山上有小路可以绕过鬼子的岗哨?”她这样想着,便灵机一动,转身走上了左边的小路。
山上果然有条小路可以绕过鬼子的岗哨。那七八个人都是年轻妇女,一大清早进城卖茶鸡蛋的,这时候卖完了茶鸡蛋回家。她们提的提篮子,背的背包袱,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一边匆匆忙忙地往山上爬。耀大娭毑悄悄地跟在她们后面,也往小山上爬。爬到半山腰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不好,鬼子追来了,快跑!”耀大娭毑回头一望,一眼便看见有三个鬼子端着枪跟在后面追。
鬼子跑得飞快,离得越来越近了。他们端着枪,嘴里呜哩哇啦地乱喊乱叫,朝着山上的人群猛追过来,样子凶恶极了。过了没多久,他们还朝着人群开起了枪。随着凄厉的枪声不断响起,子弹跟着人群擦身而过。这一来,大家更害怕了,腿发软,心发虚,手忙脚乱,浑身直打哆嗦。还有几个人完全慌了神,干脆趴在地上不走了。见情况十分危急,耀大娭毑连忙对着她们大喊起来:“唉哟,这时候哪能停下来呀?鬼子正愁找不到花姑娘呢,要是被他们抓到了,还不都得被他们糟蹋?快跑!快跑呀!”耀大娭毑这一声大喊起了作用,趴在地上不动的那些人又都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七扭八歪地往前跑了。
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时,耀大娭毑又喊了起来:“大家别往一条路上挤,那样容易被鬼子抓住!大家快散开,朝左右两边跑,快进山里,找树林子躲起来!”说完,她就拽起一个小姑娘的手跑进了左边的树林子。
左边的树林子非常茂密,到处是没过头顶的灌木丛和齐腰深的茅草。耀大娭毑见日本鬼子快到了,根本来不及往远处跑,便连忙在近边找了一处特别茂密的茅草丛藏了起来。那茅草丛的周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林,正好挡住了前面的那条小路。
日本鬼子端着枪,呜哩哇啦地怪叫着扑过来了。那乌黑的枪管、亮闪闪的刺刀、黄颜色的军裤都看得清清楚楚。小姑娘吓坏了,脸上没一点血色,两只小手也冰凉冰凉的,浑身哆嗦得像打摆子。耀大娭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捏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眼睛却一刻也不停地盯着灌木丛外面的那条小路。
三个鬼子从小路上匆匆跑过,呜哩哇啦的怪叫声、“咚咚咚”的皮鞋声、拉动枪栓时的“喀嚓”声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过了一阵,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声音终于去远了,听不到了。忽然间,茅草丛周边显得异常宁静。那宁静令人窒息,令人恐怖。
小姑娘把脑袋埋在耀大娭毑怀里,身子不停地瑟瑟发抖。耀大娭毑伸手略略抬起她的头,看着她的小脸蛋,小声说:“别害怕,鬼子往那边跑了!”
“哦,是嘛?往那边跑啦?唉哟,我的娘呃,吓死我了!”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小声说,话音还带着颤抖。
“孩子呀,你多大啦?”
“十六,过年就十七了!”
“叫什么名字?”
“张玉珊。人都叫我小珊。”
“小珊,嗯,这名字好听。就你一个人出来的?”
“不,还有我二婶、三婶!”
“她们跑散了?”
“刚才还在一起的,这会子不知道躲哪去了,没准在那边吧!”
“你们都是进城卖茶鸡蛋的?”
“是呀,我们每天一大早进城,到这时候就往回转。”
“每天都要从这山上绕道走吗?那多危险呀!”
“不,以前都是走大路,不从这山上绕道。”
“以前走大路?以前那路口鬼子没设岗哨吗?”
“那路口早就有岗哨了,但以前让走,只是查得比较严罢了。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不让走了。”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我命苦啊,让走的时候没赶上,不让走的时候却偏偏赶上了。那、那你家在哪里住?”
“穆家陇,就在山那边,”小珊用手一指前边,“离这不远,走过山下的这道陇,从前头那座山翻过去,再走一两里路就到了。”
“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能!这条路我挺熟的,以前老走。有时扯猪草,我还来这山里呐。这山里,还有那山脚下,猪草特别多。”
“噢,你老去城里卖茶鸡蛋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去呢?你娘也真是的,忍心让你一个姑娘家在外跑,她怎么不跟着?”
“我娘病了,病得很重,我爸要留在家里照顾她。家里急着用钱买药给我娘治病,所以我每天都要跟着二婶、三婶进城卖茶鸡蛋。”
“哦,可怜的孩子!要不,等会儿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送,我能行。奶奶,谢谢你!”
说着,小珊站起来就要走,耀大娭毑连忙伸手按住。“现在哪能走呀?孩子,鬼子还没过去呢!”她轻声说。
两人正悄悄地说着话,忽然听见前边的山腰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叫声。那哭叫声很大很急,异常凄厉、悲惨,犹如撕心裂肺一般。紧接着,山腰里又传来了鬼子的淫笑声。那淫笑声忽大忽小,里面还夹杂着呼哧带喘的声音。耀大娭毑心头一惊,不由得眉头紧皱,两行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唉,不知道是哪个姐妹被糟蹋了?日本鬼子真他娘的没人性,禽兽不如啊!”她暗地里骂了起来。
在茅草丛里又躲了一阵,才见那三个日本鬼子提着裤子、端着枪、哼着日本小调七扭八歪地走过来了。他们顺着来时走过的那条小路,从耀大娭毑和小珊藏身的灌木丛前走过,匆匆地下山去了。
直到日本鬼子走远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耀大娭毑才牵着小珊的手从茅草丛里钻了出来。一出来,她们便直奔前边的山腰。果然,在那山腰的茅草丛里,她们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面色惨白,神情呆滞,大腿间流着鲜血,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一见那女人,小珊就哭了。她扑倒在地,抱着那女人的身子边哭边喊:“三婶,三婶,你、你怎么啦?”
“小珊,我、我不活了,我、我活不成了呀,”三婶嘶哑着嗓音有气无力地说,“你帮我带句话给你三叔吧,让他好好待孩子,别打孩子,把孩子养大成人,为我报仇!——我那可怜的孩子呀,娘还没给你喂够奶,就走了!你别怨娘啊,娘是迫不得已的,娘是被日本鬼子害死的!你、你要为娘报仇啊!”
耀大娭毑连忙帮三婶擦净身子,穿好衣服,扶她起来坐着。她一边用手帮她梳理头发,一边轻声说:“她三婶啊,你这想法可就不对了。既然受了日本鬼子欺负,那就得想法子报仇雪恨喽,怎能大仇不报就寻死呢?那多冤啊!人活在这世上要刚强些,不能太软弱,明白吗?什么事都要往开里想,往大里想,想远一点,不能一根筋跟自己过不去。动不动就寻死,那咱们中国的人还不得都死绝了?而今这世道,受日本鬼子欺负的女人可就多了去了,哪是就你一个呢?光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呢。望城岭知道不?那地方有个姓李的姑娘,前不久被七个日本鬼子轮奸了。涝溪桥附近有个五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上个月初二被四个日本鬼子轮奸了。邵家大屋有个孕妇早两天被五个日本鬼子抓住轮奸了,结果导致流产,出了好多血。可她们都没寻死,都活下来了。她们为什么不寻死呀?因为她们晓得要报仇,因为她们晓得寻死对自己只有坏处没好处。老话讲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话说得多在理呀。人活下来,才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人要是死了,可就他娘的什么都没了。人死了,什么都没了,还怎么报仇啊?所以啊,要报仇,人就不能死。再说喽,人的死活是一个人的事吗?不是呀!那还得牵扯好多人呢。比如说你吧,你要是真死啦,你家里头可就不好办了。头一层,你儿子就没娘了。人家都有娘,他没娘。你说,他那心里头是什么滋味?第二层,你老公就没堂客了。他没堂客了,这一辈子打单身,那日子好过吗?再一层,你亲娘亲爷就没你这闺女了,过年过节你没法去看他们,将来他们死后你也没法去磕头拜祭烧纸钱。那他们该多孤单啊!你说,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还有一层,你死了,你公公婆婆也就没你这个儿媳妇了,那你说还能为他们端茶递水尽孝道吗?我也不说远的了,单是这四层,你就不能死,明白吗?死还不容易?前头就有口塘,你往那塘里一跳不就行了?可那真是最笨最蠢的做法呀,会给爷娘、孩子和家里所有的亲人们带来无边无尽痛苦的。她三婶呀,你好好想想吧,你可真的是死不得喽!”
没过多久,小珊她二婶也急急忙忙地找来了。三个人轮着做工作,掰开来揉碎了地说,过了好一阵,小珊她三婶才渐渐平静下来。耀大娭毑见状,连忙对小珊她二婶打了一个手势,两个人一边一个,搀起小珊她三婶就走。
过了陇,下了山,就看得见大路了。三个人都对耀大娭毑说:“老人家,你就从这里上大路吧,我们也快到家了!”
耀大娭毑这时却站着不动了。她把小珊拽到一边问:“你三叔对你三婶好吗?”
小珊低着头,小声说:“挺好的,只是……”
“只是脾气比较急,说话粗鲁,是不?”耀大娭毑说。
“嗯!”小珊点点头。
“哦,原来是这样,”耀大娭毑低声说,“那我还是送你们到家吧!”
两个人正小声说话,小珊她二婶慢慢腾腾地走过来了。她头一低,把嘴巴凑近耀大娭毑的耳朵,悄声说:“你老人家担心我三妹想不开,是不?放心吧,她那人挺开朗的。再说还有我们俩在呢,没事!”
耀大娭毑头一抬,看着小珊她二婶说:“我不是不放心你妹,而是不放心她男人。他男人要是个心宽、懂事、明理的人呢,这事就好办了。她男人要是个一根筋,心眼小,认死理、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呢,这事就还真的有点麻烦。倘若她男人不明事理,莽莽撞撞地说出几句不中听的话来,那她三婶还能活下去吗?”
果然,小珊她三叔脾气急,说话粗鲁。一听说老婆被鬼子奸污了,他便火冒三丈,对着她嚷嚷起来:“你还有脸回来?怎么不去死呢?当时你就该一头撞死在鬼子身上呀!”
耀大娭毑急忙上前,拽住小珊她三叔的手就往屋外走。走到外头地坪里,她站住了,冷冷地对小珊她三叔说:“小伙子,你去拿把菜刀吧!有多的话,拿两把更好!”
“要菜刀干什么?”小珊她三叔问。
“别问,你去拿就是了!”耀大娭毑说。
小珊她三叔转身进屋,一会儿就从屋里出来了,一手捏着一把菜刀。耀大娭毑看他一眼,对他说:“走吧,快跟我走!”
“走?往哪里走?你老人家要带我去哪里呀?”小珊她三叔满头雾水,站着不动。
“去哪里?当然是去找日本鬼子拼命喽!你刚才不是埋怨你堂客没一头撞死在日本鬼子身上吗?看来,你是一个有志气、不怕死的,能跟日本鬼子拼命。那好吧,我这就带你找那三个日本鬼子拼命去,我见过他们,认得。”
小珊她三叔愣住了,脸红脖子粗地站在那里不言语。
“快跟我走呀!这会子去,还来得及,追得上,那三个鬼子肯定没走远。要是再耽误一点工夫,可就不好办了,他们走远了,追不上了!”耀大娭毑说。
小珊她三叔还是不动,愣愣地站在原地。
耀大娭毑发脾气了,盯着小珊她三叔,狠狠地骂了起来:“怎么?你不敢去啦?害怕啦?你不是要堂客往鬼子身上撞吗,那你自己怎么不去撞呀?噢,闹半天,你他娘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窝里狠,一个没用的东西呀!有气只往堂客们身上使,不敢对别人发,这叫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呀?”
小珊她三叔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子。
“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你知道吗?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担待的,是要为堂客们主事的,撑腰的,打气的。堂客们在外头受了欺负,男子汉大丈夫要为她抹平伤口,要为她消除怨气,要为她报仇雪恨。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懂吗?可你倒好,女人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本来就不想活了,你却不仅不体谅她,不安慰她,不为她报仇,反倒还要伤她的心,出口就说混帐话,要她去死!你他娘的这不是往她的伤口上撒盐吗?你说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呀?不明事理,动不动就犯浑,对堂客们使气,你他娘的简直猪狗不如呀!她三婶瞎了眼,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嫁了你这么一个不懂事的混帐东西,真是倒她娘的三辈子血霉!”
小珊她三叔良心发现,忽然跪倒在地,捶胸顿足地边哭边说:“老人家,你骂得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不如呀!”
“哭管什么用啊?快回去安慰你女人,她不容易!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他娘的就麻烦了,懂吗?”耀大娭毑大声吼道。
突然,小珊她三叔猛地站了起来,把菜刀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耀大娭毑一愣,忙大声喊道:“你干什么去?快给我回来!”
“我、我找我二哥去!”小珊她三叔说。
“找你二哥?找你二哥干什么?想找你二哥一起去杀鬼子,是吗?你们两个人就能报得了仇吗?糊涂!”耀大娭毑不停地大声嚷嚷。
小珊她二婶不知什么时候站到耀大娭毑身边了。她扒拉一下耀大娭毑肩头,低声说:“让他去吧!她二哥是抗日游击队的队长!”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可就太好了!”耀大娭毑恍然大悟,心里高兴极了,不觉连声说了好几个“那就好”。
从小珊她们村出来,就是一条田间小路。耀大娭毑走在小路上,心里很高兴。她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好,救了小珊她三婶一条命,因此颇有一点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感觉。但她正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件事忽然涌上心头:“小珊她三婶没有错,她三叔应该谅解他,心疼她,跟从前一样好好待她,那小颖呢?小颖那么小的时候就被鬼子玷污了,是多么的不幸啊!她遭受了那么大的不幸,我是不是也应该谅解她、心疼她、体贴她呀?”
耀大娭毑一边走,一边想,忽然自责起来了。她觉得自己临出门时对孙子济木说的那番话有点不对劲,心里懊恼不已。“不行!我这做法不对,要赶紧改!下次见济木时,一定要跟他说清,就说自己对小颖没别的看法,很同情她,特别喜欢她,完全同意他们两个做一家子。唉,也不晓得房子哪天能盖起来。要是房子盖起来了,就让他们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耀大娭毑这样想。
离开小珊她们村,走不到两三里地,耀大娭毑就上了大路。大路上没有岗哨了,但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日伪军。那些日伪军有的坐着大卡车,有的坐着装甲车,有的开着摩托车,还有的背着各式各样的枪支在大路上走,一个个张牙舞爪,耀武扬威。
大路上根本看不见老百姓。身边老有日本鬼子,看不见老百姓,耀大娭毑心里有点发怵,但却没有慌张。“不怕!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一个死!”她这样想着为自己壮胆子,昂头挺胸、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大约走了五六十里地,来到了一个名叫潘家塘的地方。那地方好像有日伪军的仓库,路边到处都是高大而又看不见窗户的圆筒形建筑,站岗的日伪军士兵也特别多。耀大娭毑觉得情况有些特殊,怕惹麻烦,就想躲开那地方。她朝四处望了望,见大路西侧有条田间小路可以绕过那地方,便连忙从大路上走下来,往那田间小路走。但她还没走到田间小路,忽然跑过来两个伪军,拦在了前面。
“干什么的?”一个高个子伪军拿枪对着耀大娭毑大声吼道。
耀大娭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弯下腰,低下头,捂着肚子,装出一副病得不轻的模样,有气无力地哼哼说:“唉哟,唉哟,我病了,肚子疼死了,想去那田里屙屎!老总,行行好,让我去吧!不然,屙在这地方,你们也怕臭呀,对不?”
“真他娘的倒臭霉,碰上个拉稀的,”高个子伪军皱起眉头,用手捂着鼻子,“喂,你得的什么病呀?”
“什么病?唉哟,老总,什么病我也说不清。我们家里的人都病了,得的都是这种病,拉稀屎,肚子疼得厉害,还发烧,浑身没劲。有人说没准是黄热病,天知道是不是呢?反正大热天里得这病的很多,而且这病还很厉害,得了就好不了。唉哟,唉哟,唉哟,这阵子肚子疼得更厉害了,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要屙裤子里啦!”耀大娭毑一边哼哼,一边捂着肚子往地下蹲,好像实在受不了,要就地解大便的样子。
“唉哟,老太婆,在这地方屙屎,那可是不行的!你快走吧,快走吧!”高个子伪军士兵说完,就拉着另一个伪军一溜烟跑了。
耀大娭毑觉得自己装病的计谋很高明。看着那两个伪军士兵慌慌张张逃跑的身影,她乐了。但她乐得实在太早了。她刚刚转过身来,往前走了不到半里地,拐弯处就突然伸出一根黑呼呼的枪管来,对准了她。
拿枪对准耀大娭毑的,是一个半大不大的伪军士兵,个头很矮,满脸稚气,鼻子眼里还流着鼻涕。他用手紧握枪杆,把脸紧贴在枪托上,一只眼睛眯着,一只眼睛半睁半闭地瞄着准星,对着耀大娭毑大声喊叫道:“干什么的?”
耀大娭毑毫无防备,不觉吓了一跳。她往后退了两步,立马装出一副笑脸来,小声说道:“唉哟,孩子呀,你可是把奶奶吓着了!”
“谁、谁、谁是你的孩、孩子?别、别瞎说八、八道!”那小伪军士兵口吃,话说得不利落。他往前跨进一步,使劲拉动了一下枪栓。
“呵呵,你这毛头孩子,话还说不利落呢,就想开枪杀人?胆子也忒大了吧?人是那么好杀的?我命不该绝,你开枪打死了我,阎王老子要派小鬼来抓你的,知道吗?”耀大娭毑边说边笑。她不往后退了,反倒迎着那小伪军士兵的枪管朝前走了一步。
耀大娭毑这一往前走,反倒把那小伪军士兵吓着了。他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后退,一边使劲地拉动枪栓,一边对着耀大娭毑拼命大叫:“你、你、你别往前走、走了哦,我、我可是真、真要开、开枪了!”
小伪军士兵那样子很认真,不像是装模作样吓唬人。这一来,耀大娭毑不能不好好琢磨了。她想:“这家伙还是个孩子,思想不成熟,容易盲目蛮干。倘若他真的开枪了,给我一粒子弹吃,我不就莫名其妙地死在这里啦?不行,跟他说理是说不清的,跟他瞎糊弄也是糊弄不过去的,得认真琢磨琢磨,想个高招来对付他了。”
耀大娭毑不说话了。她往后退了两步,站在路边,低头沉思起来。正在这时,眼前身影一晃,拐弯处突然又冒出来了一个人。那人个头高挑,身形单瘦,三十上下年纪,腰间还挎着一支盒子枪。
小伪军士兵一见那人,猛地收起枪,脚跟一碰,抬手敬了一个军礼,口里说道:“报告长官,我抓了一个间谍!”
“间谍?是嘛?呵呵,”那被叫做长官的伪军笑了笑,抬起手一挥,“你去吧,这间谍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小伪军士兵使劲地缩了一下鼻子,扛着枪走了。看着他那远去的瘦小身影,耀大娭毑不觉又动起了心思:“嗨,命运真不好。小当兵的走了,大当官的又来了。还不如那小当兵的在这里好呢。他毕竟岁数小,主意不多,好对付一些呀。这个当官的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年纪大,经验多,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鬼主意肯定少不了。唉,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呢?看样子,这一关只怕是过不去了,凶多吉少啊!”
耀大娭毑正低头想心思,那伪军军官缓缓地迈着步子走过来了。他看了一眼耀大娭毑,微微笑着问:“你老人家是附近的人吧?”
“是呀!”耀大娭毑斜眼打量了一下伪军军官。
“怎么不走大路,却转到这小道上来了呢?”
“那有什么不同呢?小路、大路不都是让人走的路嘛!”
“呵呵,那还是有不同的,”伪军军官笑了笑,“你走大路,显得光明正大,没人会怀疑你。但你要是放着大路不走,非要钻旁边的小道,那人家可就要起疑心了,怀疑你是做间谍的,明白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耀大娭毑脸上堆起了笑容,“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说清。其实,我到这地方来,不是为了走小路的,而是……”
伪军军官忽然打断耀大娭毑的话,抢着说:“而是为了解手的,对不?”
“是呀,是呀!我觉得不好意思说,所以就没说出来。”
“嗨,很正当的嘛,那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呢?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屙屎屙尿呀?老人家,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是、是、是,是这个理,是这个理,”耀大娭毑说,一双笑眯眯的眼盯着伪军军官看,“我看你这个人呀,倒是挺好的,对我们老百姓和颜悦色,通情达理,不像给日本人做事的嘛!对了,你那么好的人,又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为什么跟日本人走在一起呀?”
伪军军官脸一红,掉转头朝旁边看,不好意思地说:“嗨,世界上的好多事,都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呀。我走这条路也是身不由己的!”
“噢,身不由己!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这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我原来是国军的。跟鬼子作战时,由于粮饷和弹药不济,我们团吃了大败仗,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团长为了给弟兄们谋条活路,便带着全团投降了鬼子。”
“哦,原来是这样,”耀大娭毑沉吟,“看样子,你这几年大概干得还算不错喽,好像是当官了嘛!”
“什么不错?日本鬼子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伪军军官忽然气愤起来,脸色变得铁青,“我干了那么长时间,当牛做马,也才当了个连长。”
“哦,连长?连长这官也不小了吧?下头有千把人?”
“不,没那么多,也就百八十个。”
“干得不顺,那就不干了呗,走他娘!”
“走?往哪里走呀?”
“带着你的人还去国军呗!”
“国军都跑光了,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那就去找游击队呗!游击队应该好找呀,照壁山里就有。你手下有那么多人,他们肯定会欢迎的!”
“找游击队?老人家,你是不知道,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伪军军官一声长叹,“首先一点,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游击队在哪里,找他们就犹如大海捞针。其次,你即便晓得他们在哪里,也没法去投靠。明摆着,没个熟人带路,帮忙引见一下,他们哪会轻易相信我们、收留我们呢?你老人家想想,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
“嗯,实情倒真是这样,”耀大娭毑点点头,“那能不能这样呢?干脆不管手下人算了,自己一个人,衣服一脱,枪一扔,回家种地养堂客孩子去!”
“唉哟,老人家,你可是太天真、太幼稚了。自己一个人跑回家?哼,只怕你人还没到家,他们就已在你家门口堵着了。真要是那样做的话,别说自己活不成,就是老婆、孩子也肯定得死,甚至老父老母和兄弟姐妹全家都得死光!”
“哟,这不成,那不成,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喽?跟日本人干,肯定是不成的呀!”
“这我明白!看来只能慢慢想办法了。”
“你赶紧想办法脱离日本人吧!要快点,别慢慢了!”
“谢谢你老人家提醒,我会的!”
“那就好!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李,叫李长亭。”
“哦,咱们俩五百年前是一家。”
“噢,你老人家也姓李?”
“是呀,我娘家姓李,婆家姓姜,就在界石镇东边的石板塘住。”
“石板塘?哦,我晓得。那咱们两家离得还真是不远。我呀,就在山那边李家冲住。不过,李家冲是我姨家,不是我老家。我是江西人,因为跟着部队打仗,到湖南这边来了,回不去江西了,便把全家老小都搬到姨妈家来了。所以呀,现在也就算是湖南人吧。李家冲那个村子,你老人家晓得不?”
“晓得,晓得!对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家里人还多着呢,堂客、孩子、老父、老母。这还只是我本人的家,我姨妈家的人就更多了,老老少少加在一起,得有三四十口。”
“哦,家里人还真是不少。有空的话,来我们石板塘坐坐!”
“呃,有空一定去。你老人家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找我。我呀,在这里还有点权力,是看守仓库的三连连长。”
又走了七八里路,就快到界石镇了。这时,路上的日伪军明显少了起来,耀大娭毑的一颗心渐渐放松下来。但这时,她的心放松了,肚子却又饿得不行了,身上没劲了。
原来,她身上的钱早就一文不剩了,梁家米缸里剩下的那一点点杂粮也早就吃光了,祖孙两个这些天全是靠邻居们东家送一点西家送一点蹭饭吃度日。头天晚上,隔壁齐家婶子送来了一碗红薯粥和两张杂粮饼子,但耀大娭毑既没吃,也没带,她全都留给孙子了。“东西本来就不多,一碗粥,两张薄薄的饼子,济木一个人吃还不够呢。算了吧,我就不吃了,也不带了,全都留给他吧。湘长官道一条大路,路边上的人家准少不了,哪里找不到一点吃的呢?”耀大娭毑当时这样想。所以,她便饿着肚子出了门。
但她没想到,湘长官道是日本鬼子重点控制、重兵把守的交通运输线,来往的日军多,沿线的居民实在不堪骚扰,早就纷纷搬到外乡或深山老林里去了,以致一路上的民居大都变成了空房,根本就找不到人,找谁要吃的去?耀大娭毑见村就进,见门就敲,走了好几十里路,却居然一户人家都没找到。她早就饿得不行了,饥肠辘辘,头晕眼花,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得提不起来,迈不开步子。没办法,她只得在路边上捡了两根树枝当拐杖,一手拿一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蹭。耀大娭毑拿着两根拐杖慢慢地往前蹭,又蹭了几里路,终于来到了一个名叫茅草塘的地方。这地方离界石镇已经很近了。看到那地方的一山一水,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茅草塘这地方,她实在太熟悉不过了。二十年前,她去谭家园请陈愈来家看茅坡那块地基时,就曾经到过这里。那天,她给陈愈老头拿了一只麻鸭当礼物。但当她走到塘堤上,把用绳子捆得死死的麻鸭放在路边,自己走到塘堤下的树丛中去小解时,那只麻鸭却神奇地挣开绳子跑了,飞到茅草塘里去了。当时,眼见那鸭子在水塘中间仰头望天、洋洋得意地呱呱大叫,她急得直跳脚,干搓着手不知所措。后来,还是这茅草塘附近的曾老婆子一家人拿着长竹竿一齐上阵,轰的轰,赶的赶,费了好大的劲,才帮她把那鸭子捉了上来。
“曾家老婆子应该还在世吧,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呢。要不上她家去找点吃的?唉呀,我的娘,找人要饭吃,一辈子没做过这种事,这脸面也丢得太大了!”耀大娭毑边琢磨,边朝曾老婆子家的屋顶望了望。
曾老婆子的家在茅草塘对岸的山洼里,与大路之间还有一小段距离,地形比较隐蔽。耀大娭毑沿着塘堤一直走,约摸走了二三百步,转弯钻进一片小树林子,再从那树林子里钻出来,走进一条小路,拐两个弯就到了。还好,曾老婆子家里有人。耀大娭毑用手一推,那门就“吱呀”一声开了。
“是哪一个哦?”屋里传来了老太婆的喊声。
耀大娭毑推开门,一眼便看到了靠墙猫腰坐着的曾老婆子。多年不见,曾老婆子都老得没人样了,身子骨又小又瘦,满头白发乱糟糟的,脸上布满了沟沟坎坎和黄黑色的老年斑,两只手就跟宰杀过后的鸡爪子似的,又白又干枯,一点血色都没有。见曾老婆子这模样,耀大娭毑不觉一阵心酸,差一点没哭出来。她忍了忍,对曾老婆子喊道:“哟,曾姐,不认得我了吧?我是石板塘姜家的李英莲呀,到过你们家的!那年我路过茅草塘时,跑了一只麻鸭,还是你老人家带着儿女们帮忙捉住的呢,还记得不?”
“噢,原来是姜家李大妹子呀!你瞧我这老眼昏花的,连你都不认得了,真正是不行了哟,要进棺材了哟!看你一手撑根棍子,我还以为是个要饭的叫花子呐!咯、咯、咯……”曾老婆子“咯咯咯”地一阵大笑,摸着墙边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要饭的叫花子”这句话,曾老婆子是无心说,耀大娭毑却是有心听。她是个极其要强的人,从来不肯低头求人的,这一辈子何曾张口找人要过饭吃呀!她不觉低下头,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嘴巴张开闭上地反复了好几次,这才小声嗫嚅着说道:“你老人家还真没说错,我还就是个叫花子,到你家来就是要讨碗饭吃的!”
曾老婆子一愣,似信不信地说:“哟,李大妹子,你真是来要饭吃的呀?怎、怎么啦?你、你们家落难了?是那帮该挨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祸害的吧?”
“嗨,说来话长!”耀大娭毑把棍子靠墙放好,挨着门边的椅子坐下,又长叹了一口气,这才把自己家里的大致情况和十多天来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唉呀,难怪你没精打采的,原来是饿着肚子走了七八十里路,把精力耗尽了呀。正好,我刚做得饭,还没来得及吃呢,你要不嫌弃,咱姐俩就一起吃吧。我正发愁没人做个伴呐,憋闷死了。你来得正好,咱老姐俩边吃边说话,扯扯谈,”曾老婆子咧着嘴,满脸的皱纹都扯到了一起,“不过,你别嫌弃我家的饭不好吃啊!我这饭可不是什么正经的饭,就一点儿粥,一点儿红薯,还没一点儿菜,你将就着吃吧!”
“嗨,不瞒你老人家说,我这阵子呀,饿得都快死了,大概连死尸都吃得下,哪还有挑饭吃的份!只要是能吃的,你随便给我一口,我就知足了。对了,你儿子、儿媳他们呢?住亲戚家去了,还是躲山里去啦?”耀大娭毑边说边打量。
“躲山里去了,就在大青山那边,”曾老婆子一扬头,透过窗户眼瞄了瞄远处的大青山,忽又迅即低下头来,压低嗓门,样子显得神神秘秘,“那山里洞多,树多,大石头也多,藏起个把人来,鬼都找不到。儿子们非要我也跟着去,还要拿轿子抬我去,我死活不肯。我上那山里干什么去呀?反正也这把老骨头了,死得过了,还怕日本鬼子怎么的?你说是不是?对了,你们家的人也都躲到山里去了吧?”
“没有。我们那地方跟你老人家这地方还有些不同呢。我们那里离大路远,离山近,进不进山倒也无所谓。反正看见鬼子来了,临时往山里跑也来得及。”
“是、是、是,你们那里安全些,安全些。我们这里可就不行了哟,大门口就有鬼子。有一次,我儿媳妇在茅厮屋(厕所)里屙屎,一个鬼子就在窗户外头看着,真够吓人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儿媳妇胆子还真大。她屎也不屙了,尿也不屙了,伸手从缸里抓起一把石灰来,就往窗户外头扔。这一把石灰扔出去倒真起了作用,那鬼子的眼睛被石灰迷住了,吓得他唔呀哇呀地大喊大叫着跑了。咯咯咯,咯咯咯……”
“是嘛?哟,你儿媳妇胆子可真够大的!”耀大娭毑不觉也笑了。
“唉哟,你看我这老糊涂!尽顾着跟你说话,连吃饭的事都忘了!你还饿着肚子呢,”曾老婆子扶住桌子边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往厨房走,“大妹子啊,你等等啊,我这就给你拿饭去!”
曾老婆子踮着小脚颤颤巍巍地进了厨房。紧接着,厨房里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好一阵,曾老婆子才又颤颤巍巍地从厨房里出来了。她手上端着一个小茶盘。那小茶盘里放着两小碗稀稀的米粥和两只煮熟的小红薯。估计这就是曾老婆子一天的全部饭食了。她把小茶盘放在桌子上,眯起眼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两小碗粥,挑了一碗稍多一点的递给耀大娭毑。然后,她又眯起眼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两只煮熟的小红薯,挑了一只稍大一点的递给耀大娭毑。
耀大娭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连招呼也来不及打一声,接过那只红薯张嘴就咬,只三下五下便连皮带须根吃了个净光净。
那红薯实在是太小了,吃进肚子里一点影响都没有。耀大娭毑抹抹嘴,旋即又端起了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但她的嘴张开,刚碰上碗边,不觉又合上了。原来,她看见从旁边的屋子里头拱出来了两只小狗仔。那两只小狗仔特别小,一色洁白的短绒毛,憨头憨脑,非常可爱。
“刚生的吧?”耀大娭毑端着粥碗问。
“是呀,大前天刚生的。”曾老婆子说。
“就这两只?”耀大娭毑问。
“可不是就这两只了,”曾老婆子喝口粥,伸出舌头舔舔嘴巴,“嗨,原来是有六只的,前天夜里死掉一只,昨天夜里又死了三只。”
“哟,怎么死啦?狗婆没奶?”耀大娭毑问。
“嗨,这个时候人都快饿死了,狗当然没东西吃喽。狗没东西吃,哪还会有奶呢?这些天,狗婆大概是饿疯了,见空子就往外钻,管都管不住。大前天晌午时,我一不留神,忘了关屋门,狗婆便溜出去找食吃了,结果被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打死吃肉了。这些小狗仔刚生下来,还没学会吃饭呐,又没娘了,吃不上奶,还能不死?结果那几只没能熬过两天就死了。这两只呀,肯定也活不成,都得饿死,多半就是这一两天的事。这世道呀,真他娘的叫人恨,连狗都命苦!”曾老婆子叹了一口长气。
两只小狗仔拱到耀大娭毑身边来了,依偎在她的脚尖躺着。她把粥碗放回到桌子上,缓缓地弯下腰,伸出双手慢慢地捧住一只小狗仔,轻轻地放在两膝间。她低下头,默默地看着那小狗仔,用手轻轻地捋着它的毛,眼睛里满含着温热的泪水。那小狗仔也像懂事似的,微微地仰起头,瞪着圆圆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她。
耀大娭毑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小狗仔,轻轻地抚摸着小狗仔,心里头满是慈祥和爱怜之意,仿佛躺在膝间的不是小狗仔,而是她自己的小孙子。她看着,摸着,脑子里忽地涌上一个想法:小狗仔没有奶吃,能不能改喝粥呢?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放进粥碗里,沾上一点粥后,又塞进小狗仔的嘴里。那小狗仔大概饿极了,见自己嘴里突然多了一个东西,便也不问青红皂白,使劲咬住吮吸起来。
见小狗仔吮吸手指,耀大娭毑一阵惊喜,不觉对曾老婆子喊了起来:“曾姐,小狗仔死不了啦,能喝粥了!”
“是嘛?小狗仔能喝粥啦?那、那可就太好了!哎哟,这几天看着它们没奶吃,饿着肚子等死,我这心里头哟,七上八下的,可难受呢。这下好了,有办法救它们了。李大妹子呃,你心肠好,是个大善人,救了它们,将来肯定会有好报的,”曾老婆子显得异常兴奋。她一把拖过桌子上那个盛放针头线脑的小竹筐来,从里面翻腾出一小块纱布,忙不迭地递给耀大娭毑,“来,用纱布试试,纱布蘸得多,比手指好用!”
耀大娭毑接过纱布,放进粥碗里浸泡一会儿,拿出来捏成手指般大小的一根长条,然后再塞进小狗仔的嘴里。那小狗仔见塞进嘴里的不是手指,起初有些诧异,瞪大眼睛盯着耀大娭毑看,但看了没多久就拼命地吮吸起来了。这办法真管用,效率比手指快得多。没多一会儿,两只小狗仔就都喂饱了。
吃饱了的小狗崽躺在耀大娭毑的怀里睡着了。看着它们那四仰八叉、呼呼大睡的怪样子,她很欣慰,情不自禁地微微笑了起来。
曾老婆子大概看出了耀大娭毑喜欢狗,作古正经地说:“这两只小狗,你都拿走吧!我们家没吃的,留着它们,早晚都得死!”
耀大娭毑鼻子一酸,眼泪又差点流了出来。她犹豫了一下说:“带两只是不行,我抱不动,要不就拿走一只吧!”
“好,拿走一只算一只,好歹救它一条命,”曾老婆子语音低沉,脸色十分凝重,“你挑吧!挑大的!你左手边那一只好像大一点!”
耀大娭毑笑笑:“嗨,我就拿这只小一点的吧!那只大一点的,就给你老人家留着。”
“行、行、行,拿哪只都行,拿哪只都行!”曾老婆子说。
耀大娭毑脱下外衣,把那只小一点的狗放在衣服里,一边包一边说:“要不我给这两只小狗起个名字吧,也算是留个纪念。留下的这一只是个母的,就起个女名,叫做白玉。我带走的这一只是个公的,就叫做白虎。你老人家看,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白玉、白虎,这两名字都好听,”曾老婆子张着没牙的嘴,“呵呵”乐了,“要是哪天白虎长大了,我还没去见阎王,你能把它带来让我看看,那就太好了!”
“好,将来我一定带白虎来见你老人家!小白虎,咱们走喽,跟老奶奶再见喽!”耀大娭毑把包着小狗的衣服往后背一搭,抬腿就走。
两只小狗仔喂饱了,耀大娭毑却一口米粥都没喝上。她只吃了一只小小的红薯。但那只红薯虽然小,却还是管点用。她愣是仗着那只小红薯的作用,又走了十多里路。眼看着离家不远了,只有七八里路了,连屹立在界石镇村口的那棵大樟树也隐隐约约地看得见了,她心里渐渐地轻松起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初夏天雷雨更是常见。就在这时,天上忽然乌云密布,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如注。耀大娭毑正在半途中,四周都是地势低洼的水稻田,急切之间哪里躲雨去?没多一会儿,她便浑身透湿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就连巡逻的日本鬼子也都急急忙忙地跑进屋里躲起来了。耀大娭毑朝四周望了望,见找不到躲雨的地方,也就索性不再找了。她横下心来,顶着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不管不顾地往前走。
世界完全被黑暗吞没了,到处都是乌蒙蒙的,黑沉沉的。远处的山、近处的房屋,就连路边的杂草、灌木,一切全都看不见了。一阵一阵突如其来的电闪,像刺刀一样不时地撕裂夜空,把眼前密集的雨线、路上白花花的雨水照得贼亮。伴随着电闪,雷鸣也疯狂发作。那雷声大得出奇,就像巨大的炸药包突然在头顶爆炸似的,震得人耳朵直发聋,头皮直发麻。雨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风助雨势,雨助风威。凶猛无比的狂风裹挟着成千上万根雨线迎面扑来,像一根根尖利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地上的一切。
洞庭湖滨的气候就是怪,出大太阳的时候,三九天穿单褂还热;一旦刮起北风、下起大雨来,三伏天也穿得住棉袄。耀大娭毑上了年纪,又饿虚了,担惊受怕地走了上百里路,哪还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摧残突袭。身上的一点点热呼气早就被冷雨狂风抽吸得一丝不剩了,她感到浑身寒意四起,侵入肌骨,心里又冷又怕,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大雨还在下,丝毫没有停歇的趋势。耀大娭毑把抱着小狗的衣服紧紧地捂在胸口上,低着头,弯着腰,顶着狂风暴雨,进两步退一步地往前蹭,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蹭。就这样,她又往前蹭了两里多路。
渐渐地挨近界石镇村口了,眼看着那棵高大而远近闻名的大樟树就在跟前了,耀大娭毑心里一阵高兴,想紧赶几步,尽快走到那大樟树底下避避雨。然而,她心里想快,两只脚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她心里一急,猛一使劲迈腿,忽然眼前一黑,身子往前一倾,不觉栽倒在地。这以后,她就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耀大娭毑坚信梁水玉会回来。然而,两天过去了,梁水玉没回来;七、八天过去了,梁水玉还是没回来。“这、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莫非她跑到外地去了?莫非她遭到鬼子的毒手了?莫、莫非她出其他什么事情了?”
耀大娭毑不敢再往下想了。她原本打算在见到孙女梁水玉以后,就赶紧带着她一起回乡下去的。梁水玉老也不回来,她便在梁家待不下去了。耀大娭毑心里最着急上火的,是小儿子姜鹤卿。临离开家来长沙的时候,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叮嘱过姜鹤卿,要他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好待在隔断里别出来。同时,她也反复嘱托过景满贞,要她把姜鹤卿当亲儿子管,管紧管严,管得死死的。
耀大娭毑度日如年,实在待不下去了。这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她就叫孙子姜济木起床了。姜济木睡得死,叫了几次也叫不醒,她就揪他的耳朵,打他的P股。
“济木,奶奶在这里实在待不住了,家里好多事情都还等着奶奶回去做呢!奶奶今天要回去,现在就走!”耀大娭毑把嘴巴贴在孙子的耳朵根子上大声说。
“是嘛,今天回家?那好啊!”姜济木听说要回去,连忙一翻身坐了起来。他还以为奶奶是要带他一起回家呢。
耀大娭毑伸手按住姜济木的肩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天还早,你别起来,接着睡吧!奶奶一个人走,你不走!”
姜济木急了,一边揉眼,一边大声嚷嚷:“你老人家要一个人回去?那怎么行!你老人家知道码头在哪里吗?知道船票怎么买吗?”
“我干什么非要知道码头在哪里、船票怎么买呀?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哪能坐船呢?要回去,也只能是走路喽!”耀大娭毑说。
“走路回去?那我更不放心了,”姜济木一翻身下床,抓住衣服就往身上套,“回家的那条路,你老人家还从来没走过的,走错了、找不到家了怎么办?”
“唉呀,你这孩子也太小瞧奶奶了。湘长官道,笔直的一条路,谁不会走呀?没走过,问一问不就会走了吗?嘴巴底下就是路嘛!”耀大娭毑撇撇嘴。
“奶奶,我、我还是跟你一起走吧!路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的岗哨呢,要是把你老人家抓走了,那、那该怎么办?”姜济木嘟嘟囔囔。
“嗨,这你就大错特错啦,”耀大娭毑拍着巴掌说,“我一个人走,鬼子倒不会抓,要是你在身边,那可就危险了。明摆着,鬼子不会抓我的。我一个老太婆,他们抓我干什么?没用呀,对不?他们抓我还嫌麻烦呢。要派人看着,要给我饭吃,我要上茅房,他们还得派人跟着,那多麻烦呀。他们能自找麻烦抓我吗?不会的!可你就不同了。你是大小伙子,有力气,能修碉堡,能挖工事,能搬枪抬炮搞运输,能干很多的事。鬼子缺劳力,见了你,还能不抓?你被抓走了,我能站在旁边干瞪眼看着不管吗?不能吧?那我肯定得跟他们拼老命的!这样一来,那咱们两个可就都完蛋了!所以呀,你无论如何不能跟我一起走,明白吗?再说,我走了,你也走了,那谁来找济勋和水玉呢?水玉回家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孩子呀,你是奶奶的乖孙子,就听奶奶一句话吧,别走了!你留下来,在这屋里住着,等一等水玉和济勋。另外,张老板城里的米行也快开业了,他也离不开你呀,对不?”
耀大娭毑这几句话起了作用,姜济木明白自己确实不能走了。他一P股坐到床边,嘟囔道:“路、路不会走,倒、倒是可以问。可那么远的路,差、差不多有一百里,你、你老人家行吗?万一路上出了事,那、那该如何是好呀?”
“哎哟,能出什么事呀?你别瞎操心好不好?大小伙子一点也不利落,老婆婆妈妈的,”耀大娭毑训斥道,“济木,奶奶可给你说好了噢,找水玉和济勋的事可就完全交给你一个人了。找到了他们俩,你就一起带回。没找到济勋,只找到了水玉,也要赶紧带回家。万一谁都没找到,那也得及时和我通信息,明白了吗?和你说好了吧,从今天算起,到第十天头上,不管怎样你都得回家一趟,把个信给我。”
耀大娭毑转身就走。但她刚刚走到门口,还没来得及跨门槛,姜济木突然又喊起来了:“奶奶,奶奶,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老人家说。”
“什么事?”耀大娭毑站住了,回头问。
“是……是……,是这样……”姜济木红着脸,吱吱呜呜。
“哟,怎么扭扭捏捏呀,”耀大娭毑好奇地打量着孙子,“莫不是你小子把小颖搞上床了吧?怎么样啊,肚子没搞大吧?”
“没、没、没,”姜济木满脸通红,“你老人家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哦,没这事呀,那你慌什么啊?”
“这、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有话就快说!”
姜济木低着头,眼睛看着地,结结巴巴地小声说:“那、那年鬼子打田营镇,进、进了小颖家,把、把她和她娘都那、那个了!”
“哦!”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打来,耀大娭毑懵了。她眼睛瞪得老大,直直地盯着前方,仅仅吐了一个“哦”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姜济木愣愣地站着,斜眼瞟了一下耀大娭毑,颤抖着声音说:“明、明摆着,这事不、不是小颖的错,怪不得她。你老人家就谅、谅解她,让、让她和我相、相好吧!反正这一辈子,我是永、永远也离不开她了!”
好半天,耀大娭毑才缓过神来。她低头看着地,缓缓地说:“这事不是她的错,我没怪她的意思。这你放心。但婚姻大事实在太大了,不能草率,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说完话,耀大娭毑拔腿就走。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走出屋门,姜济木直直地站在当地发愣,心里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
城里的一段路,耀大娭毑走得倒还比较顺利,但出了城可就很不顺利了。日本鬼子在城郊接合部的交通要道设置了很多岗哨,其中有一个关键路口被封死了,过往行人一概不放行,除非持有宪兵队颁发的特别通行证。那路口是从长沙去往湘北县的必经之地。这一来,耀大娭毑着急了。她一个乡下来的老太婆,长沙城里没一个说得上话的熟人,去哪里找宪兵队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呢?她好说歹说都没用。说多了,鬼子还要拿枪托砸她。没办法,她只得忍气吞声往回走了。
往回走了里把多路,耀大娭毑偶尔一回头,突然发现左边的小路上有七八个人正神色慌张地往一个小山上跑。“哟,那拨人干嘛往山上跑呀?莫非那山上有小路可以绕过鬼子的岗哨?”她这样想着,便灵机一动,转身走上了左边的小路。
山上果然有条小路可以绕过鬼子的岗哨。那七八个人都是年轻妇女,一大清早进城卖茶鸡蛋的,这时候卖完了茶鸡蛋回家。她们提的提篮子,背的背包袱,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一边匆匆忙忙地往山上爬。耀大娭毑悄悄地跟在她们后面,也往小山上爬。爬到半山腰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不好,鬼子追来了,快跑!”耀大娭毑回头一望,一眼便看见有三个鬼子端着枪跟在后面追。
鬼子跑得飞快,离得越来越近了。他们端着枪,嘴里呜哩哇啦地乱喊乱叫,朝着山上的人群猛追过来,样子凶恶极了。过了没多久,他们还朝着人群开起了枪。随着凄厉的枪声不断响起,子弹跟着人群擦身而过。这一来,大家更害怕了,腿发软,心发虚,手忙脚乱,浑身直打哆嗦。还有几个人完全慌了神,干脆趴在地上不走了。见情况十分危急,耀大娭毑连忙对着她们大喊起来:“唉哟,这时候哪能停下来呀?鬼子正愁找不到花姑娘呢,要是被他们抓到了,还不都得被他们糟蹋?快跑!快跑呀!”耀大娭毑这一声大喊起了作用,趴在地上不动的那些人又都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七扭八歪地往前跑了。
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时,耀大娭毑又喊了起来:“大家别往一条路上挤,那样容易被鬼子抓住!大家快散开,朝左右两边跑,快进山里,找树林子躲起来!”说完,她就拽起一个小姑娘的手跑进了左边的树林子。
左边的树林子非常茂密,到处是没过头顶的灌木丛和齐腰深的茅草。耀大娭毑见日本鬼子快到了,根本来不及往远处跑,便连忙在近边找了一处特别茂密的茅草丛藏了起来。那茅草丛的周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林,正好挡住了前面的那条小路。
日本鬼子端着枪,呜哩哇啦地怪叫着扑过来了。那乌黑的枪管、亮闪闪的刺刀、黄颜色的军裤都看得清清楚楚。小姑娘吓坏了,脸上没一点血色,两只小手也冰凉冰凉的,浑身哆嗦得像打摆子。耀大娭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捏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眼睛却一刻也不停地盯着灌木丛外面的那条小路。
三个鬼子从小路上匆匆跑过,呜哩哇啦的怪叫声、“咚咚咚”的皮鞋声、拉动枪栓时的“喀嚓”声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过了一阵,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声音终于去远了,听不到了。忽然间,茅草丛周边显得异常宁静。那宁静令人窒息,令人恐怖。
小姑娘把脑袋埋在耀大娭毑怀里,身子不停地瑟瑟发抖。耀大娭毑伸手略略抬起她的头,看着她的小脸蛋,小声说:“别害怕,鬼子往那边跑了!”
“哦,是嘛?往那边跑啦?唉哟,我的娘呃,吓死我了!”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小声说,话音还带着颤抖。
“孩子呀,你多大啦?”
“十六,过年就十七了!”
“叫什么名字?”
“张玉珊。人都叫我小珊。”
“小珊,嗯,这名字好听。就你一个人出来的?”
“不,还有我二婶、三婶!”
“她们跑散了?”
“刚才还在一起的,这会子不知道躲哪去了,没准在那边吧!”
“你们都是进城卖茶鸡蛋的?”
“是呀,我们每天一大早进城,到这时候就往回转。”
“每天都要从这山上绕道走吗?那多危险呀!”
“不,以前都是走大路,不从这山上绕道。”
“以前走大路?以前那路口鬼子没设岗哨吗?”
“那路口早就有岗哨了,但以前让走,只是查得比较严罢了。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不让走了。”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我命苦啊,让走的时候没赶上,不让走的时候却偏偏赶上了。那、那你家在哪里住?”
“穆家陇,就在山那边,”小珊用手一指前边,“离这不远,走过山下的这道陇,从前头那座山翻过去,再走一两里路就到了。”
“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能!这条路我挺熟的,以前老走。有时扯猪草,我还来这山里呐。这山里,还有那山脚下,猪草特别多。”
“噢,你老去城里卖茶鸡蛋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去呢?你娘也真是的,忍心让你一个姑娘家在外跑,她怎么不跟着?”
“我娘病了,病得很重,我爸要留在家里照顾她。家里急着用钱买药给我娘治病,所以我每天都要跟着二婶、三婶进城卖茶鸡蛋。”
“哦,可怜的孩子!要不,等会儿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送,我能行。奶奶,谢谢你!”
说着,小珊站起来就要走,耀大娭毑连忙伸手按住。“现在哪能走呀?孩子,鬼子还没过去呢!”她轻声说。
两人正悄悄地说着话,忽然听见前边的山腰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叫声。那哭叫声很大很急,异常凄厉、悲惨,犹如撕心裂肺一般。紧接着,山腰里又传来了鬼子的淫笑声。那淫笑声忽大忽小,里面还夹杂着呼哧带喘的声音。耀大娭毑心头一惊,不由得眉头紧皱,两行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唉,不知道是哪个姐妹被糟蹋了?日本鬼子真他娘的没人性,禽兽不如啊!”她暗地里骂了起来。
在茅草丛里又躲了一阵,才见那三个日本鬼子提着裤子、端着枪、哼着日本小调七扭八歪地走过来了。他们顺着来时走过的那条小路,从耀大娭毑和小珊藏身的灌木丛前走过,匆匆地下山去了。
直到日本鬼子走远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耀大娭毑才牵着小珊的手从茅草丛里钻了出来。一出来,她们便直奔前边的山腰。果然,在那山腰的茅草丛里,她们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面色惨白,神情呆滞,大腿间流着鲜血,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一见那女人,小珊就哭了。她扑倒在地,抱着那女人的身子边哭边喊:“三婶,三婶,你、你怎么啦?”
“小珊,我、我不活了,我、我活不成了呀,”三婶嘶哑着嗓音有气无力地说,“你帮我带句话给你三叔吧,让他好好待孩子,别打孩子,把孩子养大成人,为我报仇!——我那可怜的孩子呀,娘还没给你喂够奶,就走了!你别怨娘啊,娘是迫不得已的,娘是被日本鬼子害死的!你、你要为娘报仇啊!”
耀大娭毑连忙帮三婶擦净身子,穿好衣服,扶她起来坐着。她一边用手帮她梳理头发,一边轻声说:“她三婶啊,你这想法可就不对了。既然受了日本鬼子欺负,那就得想法子报仇雪恨喽,怎能大仇不报就寻死呢?那多冤啊!人活在这世上要刚强些,不能太软弱,明白吗?什么事都要往开里想,往大里想,想远一点,不能一根筋跟自己过不去。动不动就寻死,那咱们中国的人还不得都死绝了?而今这世道,受日本鬼子欺负的女人可就多了去了,哪是就你一个呢?光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呢。望城岭知道不?那地方有个姓李的姑娘,前不久被七个日本鬼子轮奸了。涝溪桥附近有个五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上个月初二被四个日本鬼子轮奸了。邵家大屋有个孕妇早两天被五个日本鬼子抓住轮奸了,结果导致流产,出了好多血。可她们都没寻死,都活下来了。她们为什么不寻死呀?因为她们晓得要报仇,因为她们晓得寻死对自己只有坏处没好处。老话讲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话说得多在理呀。人活下来,才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人要是死了,可就他娘的什么都没了。人死了,什么都没了,还怎么报仇啊?所以啊,要报仇,人就不能死。再说喽,人的死活是一个人的事吗?不是呀!那还得牵扯好多人呢。比如说你吧,你要是真死啦,你家里头可就不好办了。头一层,你儿子就没娘了。人家都有娘,他没娘。你说,他那心里头是什么滋味?第二层,你老公就没堂客了。他没堂客了,这一辈子打单身,那日子好过吗?再一层,你亲娘亲爷就没你这闺女了,过年过节你没法去看他们,将来他们死后你也没法去磕头拜祭烧纸钱。那他们该多孤单啊!你说,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还有一层,你死了,你公公婆婆也就没你这个儿媳妇了,那你说还能为他们端茶递水尽孝道吗?我也不说远的了,单是这四层,你就不能死,明白吗?死还不容易?前头就有口塘,你往那塘里一跳不就行了?可那真是最笨最蠢的做法呀,会给爷娘、孩子和家里所有的亲人们带来无边无尽痛苦的。她三婶呀,你好好想想吧,你可真的是死不得喽!”
没过多久,小珊她二婶也急急忙忙地找来了。三个人轮着做工作,掰开来揉碎了地说,过了好一阵,小珊她三婶才渐渐平静下来。耀大娭毑见状,连忙对小珊她二婶打了一个手势,两个人一边一个,搀起小珊她三婶就走。
过了陇,下了山,就看得见大路了。三个人都对耀大娭毑说:“老人家,你就从这里上大路吧,我们也快到家了!”
耀大娭毑这时却站着不动了。她把小珊拽到一边问:“你三叔对你三婶好吗?”
小珊低着头,小声说:“挺好的,只是……”
“只是脾气比较急,说话粗鲁,是不?”耀大娭毑说。
“嗯!”小珊点点头。
“哦,原来是这样,”耀大娭毑低声说,“那我还是送你们到家吧!”
两个人正小声说话,小珊她二婶慢慢腾腾地走过来了。她头一低,把嘴巴凑近耀大娭毑的耳朵,悄声说:“你老人家担心我三妹想不开,是不?放心吧,她那人挺开朗的。再说还有我们俩在呢,没事!”
耀大娭毑头一抬,看着小珊她二婶说:“我不是不放心你妹,而是不放心她男人。他男人要是个心宽、懂事、明理的人呢,这事就好办了。她男人要是个一根筋,心眼小,认死理、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呢,这事就还真的有点麻烦。倘若她男人不明事理,莽莽撞撞地说出几句不中听的话来,那她三婶还能活下去吗?”
果然,小珊她三叔脾气急,说话粗鲁。一听说老婆被鬼子奸污了,他便火冒三丈,对着她嚷嚷起来:“你还有脸回来?怎么不去死呢?当时你就该一头撞死在鬼子身上呀!”
耀大娭毑急忙上前,拽住小珊她三叔的手就往屋外走。走到外头地坪里,她站住了,冷冷地对小珊她三叔说:“小伙子,你去拿把菜刀吧!有多的话,拿两把更好!”
“要菜刀干什么?”小珊她三叔问。
“别问,你去拿就是了!”耀大娭毑说。
小珊她三叔转身进屋,一会儿就从屋里出来了,一手捏着一把菜刀。耀大娭毑看他一眼,对他说:“走吧,快跟我走!”
“走?往哪里走?你老人家要带我去哪里呀?”小珊她三叔满头雾水,站着不动。
“去哪里?当然是去找日本鬼子拼命喽!你刚才不是埋怨你堂客没一头撞死在日本鬼子身上吗?看来,你是一个有志气、不怕死的,能跟日本鬼子拼命。那好吧,我这就带你找那三个日本鬼子拼命去,我见过他们,认得。”
小珊她三叔愣住了,脸红脖子粗地站在那里不言语。
“快跟我走呀!这会子去,还来得及,追得上,那三个鬼子肯定没走远。要是再耽误一点工夫,可就不好办了,他们走远了,追不上了!”耀大娭毑说。
小珊她三叔还是不动,愣愣地站在原地。
耀大娭毑发脾气了,盯着小珊她三叔,狠狠地骂了起来:“怎么?你不敢去啦?害怕啦?你不是要堂客往鬼子身上撞吗,那你自己怎么不去撞呀?噢,闹半天,你他娘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窝里狠,一个没用的东西呀!有气只往堂客们身上使,不敢对别人发,这叫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呀?”
小珊她三叔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子。
“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你知道吗?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担待的,是要为堂客们主事的,撑腰的,打气的。堂客们在外头受了欺负,男子汉大丈夫要为她抹平伤口,要为她消除怨气,要为她报仇雪恨。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懂吗?可你倒好,女人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本来就不想活了,你却不仅不体谅她,不安慰她,不为她报仇,反倒还要伤她的心,出口就说混帐话,要她去死!你他娘的这不是往她的伤口上撒盐吗?你说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呀?不明事理,动不动就犯浑,对堂客们使气,你他娘的简直猪狗不如呀!她三婶瞎了眼,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嫁了你这么一个不懂事的混帐东西,真是倒她娘的三辈子血霉!”
小珊她三叔良心发现,忽然跪倒在地,捶胸顿足地边哭边说:“老人家,你骂得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不如呀!”
“哭管什么用啊?快回去安慰你女人,她不容易!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他娘的就麻烦了,懂吗?”耀大娭毑大声吼道。
突然,小珊她三叔猛地站了起来,把菜刀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耀大娭毑一愣,忙大声喊道:“你干什么去?快给我回来!”
“我、我找我二哥去!”小珊她三叔说。
“找你二哥?找你二哥干什么?想找你二哥一起去杀鬼子,是吗?你们两个人就能报得了仇吗?糊涂!”耀大娭毑不停地大声嚷嚷。
小珊她二婶不知什么时候站到耀大娭毑身边了。她扒拉一下耀大娭毑肩头,低声说:“让他去吧!她二哥是抗日游击队的队长!”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可就太好了!”耀大娭毑恍然大悟,心里高兴极了,不觉连声说了好几个“那就好”。
从小珊她们村出来,就是一条田间小路。耀大娭毑走在小路上,心里很高兴。她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好,救了小珊她三婶一条命,因此颇有一点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感觉。但她正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件事忽然涌上心头:“小珊她三婶没有错,她三叔应该谅解他,心疼她,跟从前一样好好待她,那小颖呢?小颖那么小的时候就被鬼子玷污了,是多么的不幸啊!她遭受了那么大的不幸,我是不是也应该谅解她、心疼她、体贴她呀?”
耀大娭毑一边走,一边想,忽然自责起来了。她觉得自己临出门时对孙子济木说的那番话有点不对劲,心里懊恼不已。“不行!我这做法不对,要赶紧改!下次见济木时,一定要跟他说清,就说自己对小颖没别的看法,很同情她,特别喜欢她,完全同意他们两个做一家子。唉,也不晓得房子哪天能盖起来。要是房子盖起来了,就让他们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耀大娭毑这样想。
离开小珊她们村,走不到两三里地,耀大娭毑就上了大路。大路上没有岗哨了,但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日伪军。那些日伪军有的坐着大卡车,有的坐着装甲车,有的开着摩托车,还有的背着各式各样的枪支在大路上走,一个个张牙舞爪,耀武扬威。
大路上根本看不见老百姓。身边老有日本鬼子,看不见老百姓,耀大娭毑心里有点发怵,但却没有慌张。“不怕!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一个死!”她这样想着为自己壮胆子,昂头挺胸、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大约走了五六十里地,来到了一个名叫潘家塘的地方。那地方好像有日伪军的仓库,路边到处都是高大而又看不见窗户的圆筒形建筑,站岗的日伪军士兵也特别多。耀大娭毑觉得情况有些特殊,怕惹麻烦,就想躲开那地方。她朝四处望了望,见大路西侧有条田间小路可以绕过那地方,便连忙从大路上走下来,往那田间小路走。但她还没走到田间小路,忽然跑过来两个伪军,拦在了前面。
“干什么的?”一个高个子伪军拿枪对着耀大娭毑大声吼道。
耀大娭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弯下腰,低下头,捂着肚子,装出一副病得不轻的模样,有气无力地哼哼说:“唉哟,唉哟,我病了,肚子疼死了,想去那田里屙屎!老总,行行好,让我去吧!不然,屙在这地方,你们也怕臭呀,对不?”
“真他娘的倒臭霉,碰上个拉稀的,”高个子伪军皱起眉头,用手捂着鼻子,“喂,你得的什么病呀?”
“什么病?唉哟,老总,什么病我也说不清。我们家里的人都病了,得的都是这种病,拉稀屎,肚子疼得厉害,还发烧,浑身没劲。有人说没准是黄热病,天知道是不是呢?反正大热天里得这病的很多,而且这病还很厉害,得了就好不了。唉哟,唉哟,唉哟,这阵子肚子疼得更厉害了,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要屙裤子里啦!”耀大娭毑一边哼哼,一边捂着肚子往地下蹲,好像实在受不了,要就地解大便的样子。
“唉哟,老太婆,在这地方屙屎,那可是不行的!你快走吧,快走吧!”高个子伪军士兵说完,就拉着另一个伪军一溜烟跑了。
耀大娭毑觉得自己装病的计谋很高明。看着那两个伪军士兵慌慌张张逃跑的身影,她乐了。但她乐得实在太早了。她刚刚转过身来,往前走了不到半里地,拐弯处就突然伸出一根黑呼呼的枪管来,对准了她。
拿枪对准耀大娭毑的,是一个半大不大的伪军士兵,个头很矮,满脸稚气,鼻子眼里还流着鼻涕。他用手紧握枪杆,把脸紧贴在枪托上,一只眼睛眯着,一只眼睛半睁半闭地瞄着准星,对着耀大娭毑大声喊叫道:“干什么的?”
耀大娭毑毫无防备,不觉吓了一跳。她往后退了两步,立马装出一副笑脸来,小声说道:“唉哟,孩子呀,你可是把奶奶吓着了!”
“谁、谁、谁是你的孩、孩子?别、别瞎说八、八道!”那小伪军士兵口吃,话说得不利落。他往前跨进一步,使劲拉动了一下枪栓。
“呵呵,你这毛头孩子,话还说不利落呢,就想开枪杀人?胆子也忒大了吧?人是那么好杀的?我命不该绝,你开枪打死了我,阎王老子要派小鬼来抓你的,知道吗?”耀大娭毑边说边笑。她不往后退了,反倒迎着那小伪军士兵的枪管朝前走了一步。
耀大娭毑这一往前走,反倒把那小伪军士兵吓着了。他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后退,一边使劲地拉动枪栓,一边对着耀大娭毑拼命大叫:“你、你、你别往前走、走了哦,我、我可是真、真要开、开枪了!”
小伪军士兵那样子很认真,不像是装模作样吓唬人。这一来,耀大娭毑不能不好好琢磨了。她想:“这家伙还是个孩子,思想不成熟,容易盲目蛮干。倘若他真的开枪了,给我一粒子弹吃,我不就莫名其妙地死在这里啦?不行,跟他说理是说不清的,跟他瞎糊弄也是糊弄不过去的,得认真琢磨琢磨,想个高招来对付他了。”
耀大娭毑不说话了。她往后退了两步,站在路边,低头沉思起来。正在这时,眼前身影一晃,拐弯处突然又冒出来了一个人。那人个头高挑,身形单瘦,三十上下年纪,腰间还挎着一支盒子枪。
小伪军士兵一见那人,猛地收起枪,脚跟一碰,抬手敬了一个军礼,口里说道:“报告长官,我抓了一个间谍!”
“间谍?是嘛?呵呵,”那被叫做长官的伪军笑了笑,抬起手一挥,“你去吧,这间谍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小伪军士兵使劲地缩了一下鼻子,扛着枪走了。看着他那远去的瘦小身影,耀大娭毑不觉又动起了心思:“嗨,命运真不好。小当兵的走了,大当官的又来了。还不如那小当兵的在这里好呢。他毕竟岁数小,主意不多,好对付一些呀。这个当官的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年纪大,经验多,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鬼主意肯定少不了。唉,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呢?看样子,这一关只怕是过不去了,凶多吉少啊!”
耀大娭毑正低头想心思,那伪军军官缓缓地迈着步子走过来了。他看了一眼耀大娭毑,微微笑着问:“你老人家是附近的人吧?”
“是呀!”耀大娭毑斜眼打量了一下伪军军官。
“怎么不走大路,却转到这小道上来了呢?”
“那有什么不同呢?小路、大路不都是让人走的路嘛!”
“呵呵,那还是有不同的,”伪军军官笑了笑,“你走大路,显得光明正大,没人会怀疑你。但你要是放着大路不走,非要钻旁边的小道,那人家可就要起疑心了,怀疑你是做间谍的,明白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耀大娭毑脸上堆起了笑容,“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说清。其实,我到这地方来,不是为了走小路的,而是……”
伪军军官忽然打断耀大娭毑的话,抢着说:“而是为了解手的,对不?”
“是呀,是呀!我觉得不好意思说,所以就没说出来。”
“嗨,很正当的嘛,那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呢?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屙屎屙尿呀?老人家,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是、是、是,是这个理,是这个理,”耀大娭毑说,一双笑眯眯的眼盯着伪军军官看,“我看你这个人呀,倒是挺好的,对我们老百姓和颜悦色,通情达理,不像给日本人做事的嘛!对了,你那么好的人,又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为什么跟日本人走在一起呀?”
伪军军官脸一红,掉转头朝旁边看,不好意思地说:“嗨,世界上的好多事,都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呀。我走这条路也是身不由己的!”
“噢,身不由己!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这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我原来是国军的。跟鬼子作战时,由于粮饷和弹药不济,我们团吃了大败仗,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团长为了给弟兄们谋条活路,便带着全团投降了鬼子。”
“哦,原来是这样,”耀大娭毑沉吟,“看样子,你这几年大概干得还算不错喽,好像是当官了嘛!”
“什么不错?日本鬼子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伪军军官忽然气愤起来,脸色变得铁青,“我干了那么长时间,当牛做马,也才当了个连长。”
“哦,连长?连长这官也不小了吧?下头有千把人?”
“不,没那么多,也就百八十个。”
“干得不顺,那就不干了呗,走他娘!”
“走?往哪里走呀?”
“带着你的人还去国军呗!”
“国军都跑光了,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那就去找游击队呗!游击队应该好找呀,照壁山里就有。你手下有那么多人,他们肯定会欢迎的!”
“找游击队?老人家,你是不知道,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伪军军官一声长叹,“首先一点,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游击队在哪里,找他们就犹如大海捞针。其次,你即便晓得他们在哪里,也没法去投靠。明摆着,没个熟人带路,帮忙引见一下,他们哪会轻易相信我们、收留我们呢?你老人家想想,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
“嗯,实情倒真是这样,”耀大娭毑点点头,“那能不能这样呢?干脆不管手下人算了,自己一个人,衣服一脱,枪一扔,回家种地养堂客孩子去!”
“唉哟,老人家,你可是太天真、太幼稚了。自己一个人跑回家?哼,只怕你人还没到家,他们就已在你家门口堵着了。真要是那样做的话,别说自己活不成,就是老婆、孩子也肯定得死,甚至老父老母和兄弟姐妹全家都得死光!”
“哟,这不成,那不成,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喽?跟日本人干,肯定是不成的呀!”
“这我明白!看来只能慢慢想办法了。”
“你赶紧想办法脱离日本人吧!要快点,别慢慢了!”
“谢谢你老人家提醒,我会的!”
“那就好!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李,叫李长亭。”
“哦,咱们俩五百年前是一家。”
“噢,你老人家也姓李?”
“是呀,我娘家姓李,婆家姓姜,就在界石镇东边的石板塘住。”
“石板塘?哦,我晓得。那咱们两家离得还真是不远。我呀,就在山那边李家冲住。不过,李家冲是我姨家,不是我老家。我是江西人,因为跟着部队打仗,到湖南这边来了,回不去江西了,便把全家老小都搬到姨妈家来了。所以呀,现在也就算是湖南人吧。李家冲那个村子,你老人家晓得不?”
“晓得,晓得!对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家里人还多着呢,堂客、孩子、老父、老母。这还只是我本人的家,我姨妈家的人就更多了,老老少少加在一起,得有三四十口。”
“哦,家里人还真是不少。有空的话,来我们石板塘坐坐!”
“呃,有空一定去。你老人家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找我。我呀,在这里还有点权力,是看守仓库的三连连长。”
又走了七八里路,就快到界石镇了。这时,路上的日伪军明显少了起来,耀大娭毑的一颗心渐渐放松下来。但这时,她的心放松了,肚子却又饿得不行了,身上没劲了。
原来,她身上的钱早就一文不剩了,梁家米缸里剩下的那一点点杂粮也早就吃光了,祖孙两个这些天全是靠邻居们东家送一点西家送一点蹭饭吃度日。头天晚上,隔壁齐家婶子送来了一碗红薯粥和两张杂粮饼子,但耀大娭毑既没吃,也没带,她全都留给孙子了。“东西本来就不多,一碗粥,两张薄薄的饼子,济木一个人吃还不够呢。算了吧,我就不吃了,也不带了,全都留给他吧。湘长官道一条大路,路边上的人家准少不了,哪里找不到一点吃的呢?”耀大娭毑当时这样想。所以,她便饿着肚子出了门。
但她没想到,湘长官道是日本鬼子重点控制、重兵把守的交通运输线,来往的日军多,沿线的居民实在不堪骚扰,早就纷纷搬到外乡或深山老林里去了,以致一路上的民居大都变成了空房,根本就找不到人,找谁要吃的去?耀大娭毑见村就进,见门就敲,走了好几十里路,却居然一户人家都没找到。她早就饿得不行了,饥肠辘辘,头晕眼花,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得提不起来,迈不开步子。没办法,她只得在路边上捡了两根树枝当拐杖,一手拿一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蹭。耀大娭毑拿着两根拐杖慢慢地往前蹭,又蹭了几里路,终于来到了一个名叫茅草塘的地方。这地方离界石镇已经很近了。看到那地方的一山一水,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茅草塘这地方,她实在太熟悉不过了。二十年前,她去谭家园请陈愈来家看茅坡那块地基时,就曾经到过这里。那天,她给陈愈老头拿了一只麻鸭当礼物。但当她走到塘堤上,把用绳子捆得死死的麻鸭放在路边,自己走到塘堤下的树丛中去小解时,那只麻鸭却神奇地挣开绳子跑了,飞到茅草塘里去了。当时,眼见那鸭子在水塘中间仰头望天、洋洋得意地呱呱大叫,她急得直跳脚,干搓着手不知所措。后来,还是这茅草塘附近的曾老婆子一家人拿着长竹竿一齐上阵,轰的轰,赶的赶,费了好大的劲,才帮她把那鸭子捉了上来。
“曾家老婆子应该还在世吧,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呢。要不上她家去找点吃的?唉呀,我的娘,找人要饭吃,一辈子没做过这种事,这脸面也丢得太大了!”耀大娭毑边琢磨,边朝曾老婆子家的屋顶望了望。
曾老婆子的家在茅草塘对岸的山洼里,与大路之间还有一小段距离,地形比较隐蔽。耀大娭毑沿着塘堤一直走,约摸走了二三百步,转弯钻进一片小树林子,再从那树林子里钻出来,走进一条小路,拐两个弯就到了。还好,曾老婆子家里有人。耀大娭毑用手一推,那门就“吱呀”一声开了。
“是哪一个哦?”屋里传来了老太婆的喊声。
耀大娭毑推开门,一眼便看到了靠墙猫腰坐着的曾老婆子。多年不见,曾老婆子都老得没人样了,身子骨又小又瘦,满头白发乱糟糟的,脸上布满了沟沟坎坎和黄黑色的老年斑,两只手就跟宰杀过后的鸡爪子似的,又白又干枯,一点血色都没有。见曾老婆子这模样,耀大娭毑不觉一阵心酸,差一点没哭出来。她忍了忍,对曾老婆子喊道:“哟,曾姐,不认得我了吧?我是石板塘姜家的李英莲呀,到过你们家的!那年我路过茅草塘时,跑了一只麻鸭,还是你老人家带着儿女们帮忙捉住的呢,还记得不?”
“噢,原来是姜家李大妹子呀!你瞧我这老眼昏花的,连你都不认得了,真正是不行了哟,要进棺材了哟!看你一手撑根棍子,我还以为是个要饭的叫花子呐!咯、咯、咯……”曾老婆子“咯咯咯”地一阵大笑,摸着墙边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要饭的叫花子”这句话,曾老婆子是无心说,耀大娭毑却是有心听。她是个极其要强的人,从来不肯低头求人的,这一辈子何曾张口找人要过饭吃呀!她不觉低下头,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嘴巴张开闭上地反复了好几次,这才小声嗫嚅着说道:“你老人家还真没说错,我还就是个叫花子,到你家来就是要讨碗饭吃的!”
曾老婆子一愣,似信不信地说:“哟,李大妹子,你真是来要饭吃的呀?怎、怎么啦?你、你们家落难了?是那帮该挨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祸害的吧?”
“嗨,说来话长!”耀大娭毑把棍子靠墙放好,挨着门边的椅子坐下,又长叹了一口气,这才把自己家里的大致情况和十多天来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唉呀,难怪你没精打采的,原来是饿着肚子走了七八十里路,把精力耗尽了呀。正好,我刚做得饭,还没来得及吃呢,你要不嫌弃,咱姐俩就一起吃吧。我正发愁没人做个伴呐,憋闷死了。你来得正好,咱老姐俩边吃边说话,扯扯谈,”曾老婆子咧着嘴,满脸的皱纹都扯到了一起,“不过,你别嫌弃我家的饭不好吃啊!我这饭可不是什么正经的饭,就一点儿粥,一点儿红薯,还没一点儿菜,你将就着吃吧!”
“嗨,不瞒你老人家说,我这阵子呀,饿得都快死了,大概连死尸都吃得下,哪还有挑饭吃的份!只要是能吃的,你随便给我一口,我就知足了。对了,你儿子、儿媳他们呢?住亲戚家去了,还是躲山里去啦?”耀大娭毑边说边打量。
“躲山里去了,就在大青山那边,”曾老婆子一扬头,透过窗户眼瞄了瞄远处的大青山,忽又迅即低下头来,压低嗓门,样子显得神神秘秘,“那山里洞多,树多,大石头也多,藏起个把人来,鬼都找不到。儿子们非要我也跟着去,还要拿轿子抬我去,我死活不肯。我上那山里干什么去呀?反正也这把老骨头了,死得过了,还怕日本鬼子怎么的?你说是不是?对了,你们家的人也都躲到山里去了吧?”
“没有。我们那地方跟你老人家这地方还有些不同呢。我们那里离大路远,离山近,进不进山倒也无所谓。反正看见鬼子来了,临时往山里跑也来得及。”
“是、是、是,你们那里安全些,安全些。我们这里可就不行了哟,大门口就有鬼子。有一次,我儿媳妇在茅厮屋(厕所)里屙屎,一个鬼子就在窗户外头看着,真够吓人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儿媳妇胆子还真大。她屎也不屙了,尿也不屙了,伸手从缸里抓起一把石灰来,就往窗户外头扔。这一把石灰扔出去倒真起了作用,那鬼子的眼睛被石灰迷住了,吓得他唔呀哇呀地大喊大叫着跑了。咯咯咯,咯咯咯……”
“是嘛?哟,你儿媳妇胆子可真够大的!”耀大娭毑不觉也笑了。
“唉哟,你看我这老糊涂!尽顾着跟你说话,连吃饭的事都忘了!你还饿着肚子呢,”曾老婆子扶住桌子边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往厨房走,“大妹子啊,你等等啊,我这就给你拿饭去!”
曾老婆子踮着小脚颤颤巍巍地进了厨房。紧接着,厨房里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好一阵,曾老婆子才又颤颤巍巍地从厨房里出来了。她手上端着一个小茶盘。那小茶盘里放着两小碗稀稀的米粥和两只煮熟的小红薯。估计这就是曾老婆子一天的全部饭食了。她把小茶盘放在桌子上,眯起眼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两小碗粥,挑了一碗稍多一点的递给耀大娭毑。然后,她又眯起眼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两只煮熟的小红薯,挑了一只稍大一点的递给耀大娭毑。
耀大娭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连招呼也来不及打一声,接过那只红薯张嘴就咬,只三下五下便连皮带须根吃了个净光净。
那红薯实在是太小了,吃进肚子里一点影响都没有。耀大娭毑抹抹嘴,旋即又端起了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但她的嘴张开,刚碰上碗边,不觉又合上了。原来,她看见从旁边的屋子里头拱出来了两只小狗仔。那两只小狗仔特别小,一色洁白的短绒毛,憨头憨脑,非常可爱。
“刚生的吧?”耀大娭毑端着粥碗问。
“是呀,大前天刚生的。”曾老婆子说。
“就这两只?”耀大娭毑问。
“可不是就这两只了,”曾老婆子喝口粥,伸出舌头舔舔嘴巴,“嗨,原来是有六只的,前天夜里死掉一只,昨天夜里又死了三只。”
“哟,怎么死啦?狗婆没奶?”耀大娭毑问。
“嗨,这个时候人都快饿死了,狗当然没东西吃喽。狗没东西吃,哪还会有奶呢?这些天,狗婆大概是饿疯了,见空子就往外钻,管都管不住。大前天晌午时,我一不留神,忘了关屋门,狗婆便溜出去找食吃了,结果被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打死吃肉了。这些小狗仔刚生下来,还没学会吃饭呐,又没娘了,吃不上奶,还能不死?结果那几只没能熬过两天就死了。这两只呀,肯定也活不成,都得饿死,多半就是这一两天的事。这世道呀,真他娘的叫人恨,连狗都命苦!”曾老婆子叹了一口长气。
两只小狗仔拱到耀大娭毑身边来了,依偎在她的脚尖躺着。她把粥碗放回到桌子上,缓缓地弯下腰,伸出双手慢慢地捧住一只小狗仔,轻轻地放在两膝间。她低下头,默默地看着那小狗仔,用手轻轻地捋着它的毛,眼睛里满含着温热的泪水。那小狗仔也像懂事似的,微微地仰起头,瞪着圆圆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她。
耀大娭毑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小狗仔,轻轻地抚摸着小狗仔,心里头满是慈祥和爱怜之意,仿佛躺在膝间的不是小狗仔,而是她自己的小孙子。她看着,摸着,脑子里忽地涌上一个想法:小狗仔没有奶吃,能不能改喝粥呢?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放进粥碗里,沾上一点粥后,又塞进小狗仔的嘴里。那小狗仔大概饿极了,见自己嘴里突然多了一个东西,便也不问青红皂白,使劲咬住吮吸起来。
见小狗仔吮吸手指,耀大娭毑一阵惊喜,不觉对曾老婆子喊了起来:“曾姐,小狗仔死不了啦,能喝粥了!”
“是嘛?小狗仔能喝粥啦?那、那可就太好了!哎哟,这几天看着它们没奶吃,饿着肚子等死,我这心里头哟,七上八下的,可难受呢。这下好了,有办法救它们了。李大妹子呃,你心肠好,是个大善人,救了它们,将来肯定会有好报的,”曾老婆子显得异常兴奋。她一把拖过桌子上那个盛放针头线脑的小竹筐来,从里面翻腾出一小块纱布,忙不迭地递给耀大娭毑,“来,用纱布试试,纱布蘸得多,比手指好用!”
耀大娭毑接过纱布,放进粥碗里浸泡一会儿,拿出来捏成手指般大小的一根长条,然后再塞进小狗仔的嘴里。那小狗仔见塞进嘴里的不是手指,起初有些诧异,瞪大眼睛盯着耀大娭毑看,但看了没多久就拼命地吮吸起来了。这办法真管用,效率比手指快得多。没多一会儿,两只小狗仔就都喂饱了。
吃饱了的小狗崽躺在耀大娭毑的怀里睡着了。看着它们那四仰八叉、呼呼大睡的怪样子,她很欣慰,情不自禁地微微笑了起来。
曾老婆子大概看出了耀大娭毑喜欢狗,作古正经地说:“这两只小狗,你都拿走吧!我们家没吃的,留着它们,早晚都得死!”
耀大娭毑鼻子一酸,眼泪又差点流了出来。她犹豫了一下说:“带两只是不行,我抱不动,要不就拿走一只吧!”
“好,拿走一只算一只,好歹救它一条命,”曾老婆子语音低沉,脸色十分凝重,“你挑吧!挑大的!你左手边那一只好像大一点!”
耀大娭毑笑笑:“嗨,我就拿这只小一点的吧!那只大一点的,就给你老人家留着。”
“行、行、行,拿哪只都行,拿哪只都行!”曾老婆子说。
耀大娭毑脱下外衣,把那只小一点的狗放在衣服里,一边包一边说:“要不我给这两只小狗起个名字吧,也算是留个纪念。留下的这一只是个母的,就起个女名,叫做白玉。我带走的这一只是个公的,就叫做白虎。你老人家看,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白玉、白虎,这两名字都好听,”曾老婆子张着没牙的嘴,“呵呵”乐了,“要是哪天白虎长大了,我还没去见阎王,你能把它带来让我看看,那就太好了!”
“好,将来我一定带白虎来见你老人家!小白虎,咱们走喽,跟老奶奶再见喽!”耀大娭毑把包着小狗的衣服往后背一搭,抬腿就走。
两只小狗仔喂饱了,耀大娭毑却一口米粥都没喝上。她只吃了一只小小的红薯。但那只红薯虽然小,却还是管点用。她愣是仗着那只小红薯的作用,又走了十多里路。眼看着离家不远了,只有七八里路了,连屹立在界石镇村口的那棵大樟树也隐隐约约地看得见了,她心里渐渐地轻松起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初夏天雷雨更是常见。就在这时,天上忽然乌云密布,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如注。耀大娭毑正在半途中,四周都是地势低洼的水稻田,急切之间哪里躲雨去?没多一会儿,她便浑身透湿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就连巡逻的日本鬼子也都急急忙忙地跑进屋里躲起来了。耀大娭毑朝四周望了望,见找不到躲雨的地方,也就索性不再找了。她横下心来,顶着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不管不顾地往前走。
世界完全被黑暗吞没了,到处都是乌蒙蒙的,黑沉沉的。远处的山、近处的房屋,就连路边的杂草、灌木,一切全都看不见了。一阵一阵突如其来的电闪,像刺刀一样不时地撕裂夜空,把眼前密集的雨线、路上白花花的雨水照得贼亮。伴随着电闪,雷鸣也疯狂发作。那雷声大得出奇,就像巨大的炸药包突然在头顶爆炸似的,震得人耳朵直发聋,头皮直发麻。雨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风助雨势,雨助风威。凶猛无比的狂风裹挟着成千上万根雨线迎面扑来,像一根根尖利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地上的一切。
洞庭湖滨的气候就是怪,出大太阳的时候,三九天穿单褂还热;一旦刮起北风、下起大雨来,三伏天也穿得住棉袄。耀大娭毑上了年纪,又饿虚了,担惊受怕地走了上百里路,哪还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摧残突袭。身上的一点点热呼气早就被冷雨狂风抽吸得一丝不剩了,她感到浑身寒意四起,侵入肌骨,心里又冷又怕,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大雨还在下,丝毫没有停歇的趋势。耀大娭毑把抱着小狗的衣服紧紧地捂在胸口上,低着头,弯着腰,顶着狂风暴雨,进两步退一步地往前蹭,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蹭。就这样,她又往前蹭了两里多路。
渐渐地挨近界石镇村口了,眼看着那棵高大而远近闻名的大樟树就在跟前了,耀大娭毑心里一阵高兴,想紧赶几步,尽快走到那大樟树底下避避雨。然而,她心里想快,两只脚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她心里一急,猛一使劲迈腿,忽然眼前一黑,身子往前一倾,不觉栽倒在地。这以后,她就什么事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