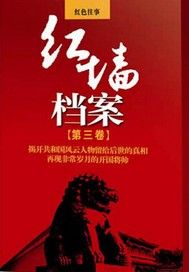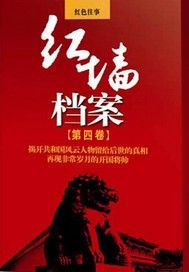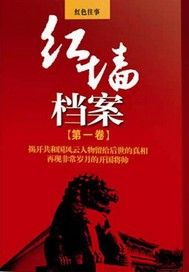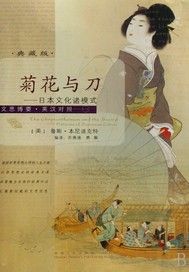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谜底揭穿了,梁水玉就是耀大娭毑的亲孙女、姜济勋的亲妹妹、小名珠儿的姜济珠。兄妹不能通婚,这事是没得任何商量的。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他们那已经升温到炙热的情感迅速冷却下来而又不至产生其他麻烦呢?再者,事情说破后,水玉她们家就没有搪塞孙棒子的理由了,水玉怎样才能躲开孙棒子的无理纠缠而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呢?对这些事,耀大娭毑和水玉她爸妈都觉得非常伤脑筋。人就是这样,越是至亲的亲人有事在身,就越容易把事情往最坏里想。他们老担心这样做会伤济勋的心,那样做又会使得水玉的面子不好看。他们甚至担心,一旦事情说穿,济勋和水玉都会抹不开情面,结果亲兄妹反倒成了仇家,一辈子不相往来。他们总想找一个最妥当最安全的办法来做到两全其美,万无一失。他们就这样左思右想,凝思苦索,结果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都快到丑时了,最终的办法却还是没能定下来。
阵阵江风从树顶上扫过,吹得树叶簌簌作响。耀大娭毑抬头看看天,一片树叶忽然落了下来,掉在她的脸上。她摇摇头,抖落掉树叶,又扭扭腰,伸伸胳膊,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过了半夜,天气就转凉了。她衣服穿得单薄,早就感到有些凉意了。这时一股带着浓重水气的江风吹来,直往衣袖里、脖领里钻,她不觉浑身起了好多鸡皮疙瘩。“哟,还真有些冷呐!”耀大娭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伸拳蹬腿,围着那树活动身子。
“你老人家冷了吧?要不先回屋里暖和暖和?”水玉她妈看着耀大娭毑,小声说。
“不了,不了!何必费那事呢?咱们还是赶紧把事情定下来吧,”耀大娭毑说。话里明显带着点怕冷的颤音,“时间确实有点晚了,咱们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再拖下去,被鬼子的巡逻队发现了,可就不得了喽。再说,我也累了,困了,想睏觉(睡觉)了。要不这么办吧,我拿主意,你们听我的。事情万分紧急,绝对不能过夜,现在咱们就把水玉和济勋叫醒,分头跟他们谈。济勋嘛,我来谈。水玉呢,你们两个找她谈。治大病要用猛药,谈大事要讲狠话。他们两个从相识到相交,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感情好得黏糊在一起了,也就难舍难分了。现在呀,他们正是深陷泥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看呀,在这节骨眼上,不讲几句狠话,他们是不会很快清醒的。所以,咱们谈这事的时候,话一定要说得干脆,说得利落,斩钉截铁,绝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要从头至尾说得清清楚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也一定要说透说深,说得明明白白,说得他们真正打心底里信服。你们两口子再想想,看还有别的想法没有?”
“没啦,没啦!你老人家想得这样周到,我们哪还有别的想法呀,就照你老人家的意思办吧!”水玉她爸妈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你们没意见,那就去叫醒孩子们吧!”耀大娭毑说。
“好的,我这就去叫醒孩子,”水玉她妈边说边起身,“对了,你老人家还没吩咐呢,两个孩子是都叫到这里来吗?”
“不、不、不,两个孩子哪能在一起谈呢,”耀大娭毑连连摇手,“碍着面子呀,对不?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嘛,咱们分开谈。你们和水玉就在屋里谈吧,把济勋喊出来就行了。”
“那好吧,你老人家略等等,我去喊济勋过来,”水玉她妈说。说完,她又回头走了过来,脱下身上的外衣扔给耀大娭毑,“你老人家快披上这件衣服吧,外头有点凉!”
“呵呵,我也不客气了,这阵子还真是有点凉呢!”耀大娭毑接过衣服,连忙穿上。
水玉她爸也起身了,站在一旁等水玉她妈。水玉她妈朝水玉她爸扫了一眼,正转身要走,耀大娭毑一挥手,又把她留了下来。
“等、等,我还有个事要说。这个家,你们是住不得了,得赶紧走!”耀大娭毑说。
“走?往哪里走呀?我们家一无亲戚可投,二无朋友可靠,眼下真正是走投无路了!”水玉她妈说,话音很凄凉。
“怎么会走投无路呢?眼下不就有一条路嘛!”耀大娭毑满脸都是笑。
“眼下就有路?哪里有路呀?”水玉她妈不解地问。
“嗨,我们乡下呀,”耀大娭毑拖着长音说,“难道你不把我当亲戚、朋友吗?”
水玉她爸妈相互对视一眼,齐声说:“哪好意思给你老人家添麻烦呀!”
“哟,添麻烦?水玉她妈,你这说法多生分呀!亲朋之间,帮帮忙难道不是应该的?平常素不相识的人见一面都是缘分,更何况咱们两家之间还有水玉这根线牵着呢!对了,”耀大娭毑微微笑着,显得非常诚恳,“咱们刚才不是说好了的嘛,我让济勋给你当儿子的。怎么刚过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忘了这档子事啦!该不是反悔了吧?”
“没有,没有,”水玉她妈边笑边摇手,“收那么好的一个儿子,我当然求之不得喽,哪里还会反悔呢?”
“那好,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就是亲戚,就是最亲最亲的亲戚,”耀大娭毑轻轻地拍着手,笑得满脸开花,“是亲戚可就得常走动,别生分哟!我可是给你们说好了哦,孙棒子那王八蛋肯定会要继续无理纠缠的,没准还会带枪来抢人呢!这个家,你们可真是待不得了,有危险的!干脆,你们都跟我去乡下吧,到我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咱们明天就走,行不行?你们要是相信我的话,那就别啰嗦,稍稍收拾一下东西,带几件换洗衣服,明天一早动身,带着水玉跟我们一起去乡下。咱们呀,赶早不赶晚,乘天亮以前的头班轮船走。我们家呀,也很穷,但饭总还是有得吃的,只要你们不挑剔就行!”
水玉她妈忙小声打哈哈:“哎哟哟,看你老人家说的!带我们一起走,那是你老人家看得起我们,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哪还能挑剔呀!只要你老人家给口饭吃,让我们留口气,不饿死,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水玉她爸妈回屋不久,姜济勋和姜济木兄弟两个就来到大空场的樟树底下了。姜济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东倒西歪地走了过来,P股往地上一蹲,扯开嗓子就嚷:“奶奶,什么事那么急呀,非得这时候说?我还没睡醒呐,一个梦都没做完!”
“是嘛,正做梦呀?梦见什么啦?”耀大娭毑和颜悦色,话里充满了慈爱。
“梦见和水玉在一起”姜济勋揉揉眼睛。
耀大娭毑一惊,连忙打断孙子的话,急急地问:“哦,和水玉在一起,在一起干什么呀?”
“在一起瞎玩呗,还能干什么?”姜济勋嘟囔道,头都没抬。
“噢,在一起玩,没干什么,那、那就好,那就好。”耀大娭毑似乎心里想着别的事,话说得零零碎碎。
姜济勋猛地抬起头来,眼睛盯着耀大娭毑:“不让人安生睡觉,把人从床上拽起来,究竟有什么事呀?”
“当然是有天大的急事喽!没有天大的急事,我三更半夜里叫你起来干什么?鬼打起呀?抽风呀?嗨,我问你哦,”耀大娭毑说,声音不大,语气却很重,“你还记得你曾经有过一个小妹妹吗?”
“你老人家是说那个叫做‘夜哭猪’的珠儿吧?事情嘛,我还勉强记得,晓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妹妹。但她的样子,我可就真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她不是被我妈带走了嘛,当时还只有两岁多呐,只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姜济勋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不,她没死,她、她还活着!”耀大娭毑哽咽着说,声音很低沉。她仰头看着星空,泪珠围着眼眶转。
见奶奶突然哭了,姜济勋大吃一惊。他猛地抬起头来,怪模怪样地看着耀大娭毑,大声问:“奶奶,你、你怎么啦?是想起珠儿来了?嗨,事情都快过去二十年了,还想她干什么?她肯定早死了,不可能还活着的!”
“怎么不可能活着?她就是还活着,如今就在长沙城里呢!”耀大娭毑抬手擦擦眼泪。
“是嘛,珠儿还活着?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姜济勋就像是挨了雷击似的,突然从地上蹦了起来,睡意顿时烟消云散。
耀大娭毑依旧眼泪围着眼珠转。她撩起衣角擦了擦眼睛,静静地说:“我当然知道喽,因为我见到她了!”
“哟,你老人家见到珠儿啦?她在哪里?快告诉我吧,我现在就去看她!”姜济勋凑到奶奶跟前火急火燎地说。
耀大娭毑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远处黑黝黝的屋顶,缓缓地说:“你也见过她了!你见到她比我还早得多呐!”
“是嘛,我也见过珠儿啦?那、那怎么可能呢!这些日子,我根本就没见过别的什么人呀!这、这、这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呀?奶奶,你把我搞糊涂了!”姜济勋大声喊道,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态。
耀大娭毑忽地从远处的屋顶收回眼神,低着头,看着地面,声音很低神态却很严厉地问:“你知道珠儿是谁吗?”
“我、我哪能知道珠儿是谁呢!奶奶,你老人家就别跟孙子打哑谜了,快点告诉我吧,珠儿究竟是谁呀?她在哪里呀?”姜济勋急得火烧眉毛,不自觉地围着矮凳转起圈来。
“实话告诉你吧,她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耀大娭毑神情严肃,语速很慢,语音低沉,几乎是一字一顿,“其实,你这些日子,天天都见着她,天天都和她在一起呢!她、她、她就是梁家的水玉姑娘!”
耀大娭毑的话犹如一声霹雳,把姜济勋打懵了。他忽地停止转圈,站在当地发愣,眼睛直直地盯着夜空,半天不言声。
“水玉是珠儿,这、这怎么可能呢?这、这是不可能的呀!”姜济勋仿佛神经失常,没完没了地喃喃自语。
“怎么不可能?实话说吧,这事我早就怀疑上了,”耀大娭毑走到姜济勋面前,轻轻地扶着他的肩头,将他按在凳子上坐好,“从水玉刚进咱们家门那时候起,我就怀疑上了。她和你长得那么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她又还有‘夜哭猪’的外号,这难道是巧合吗?天底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呀!这次我来长沙,其实就是找梁家证实这件事的。刚才我找水玉她爸妈聊了聊,问题就彻底弄明白了。没错,水玉就是珠儿,就是你的亲妹妹济珠。十七年前你妈来长沙时,由于带着珠儿不方便,找不到事情做,没有饭吃,饿得半夜里晕倒在梁家门口,被水玉她妈救了。后来,你妈觉得水玉她妈一家子都是好人,便把珠儿送给了她们家。孩子呀,这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奶奶没骗你。奶奶也没必要骗你呀,对不?”
姜济勋低着头,用手使劲抠着头皮,就像要把那满头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统统拔起来似的。他完全被奶奶的话震惊了,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事实。突然间,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盯着远处那一大片黑黝黝的屋顶,用嘶哑的嗓音问道:“那、那、那我妈呢?她去哪里了?现在还有音信吗,还能找到她吗?”
耀大娭毑挪挪凳子,坐得离姜济勋更近了些,伸手摸摸他的头,柔声细语地说:“水玉她妈说,你妈把珠儿留给梁家后,就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她当然是找事做去了,她要吃饭呀,要养活自己呀,对不?她究竟做什么事去了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她也许给人家当保姆去了,也许进厂当女工去了,也许另找人家了。这都是没准的事。水玉她妈还说,你妈临走时曾经撂下话,要水玉她妈把珠儿改个名字,并搬几次家,离开那些老邻居,免得后来人多嘴杂,说漏了珠儿的事,让珠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水玉她妈晓得你妈是诚心诚意为梁家好,便也就听信了她的话,真的搬了家,并把珠儿的名字改成了水玉。家搬了,地址变了,孩子的名字也改了,你妈即便想找珠儿,也就找不到了。水玉她妈还说,她后来还回原来的住地去过几次,问那些老邻居们见没见过你妈,知不知道你妈的消息。那些老邻居都说,你妈自打走了以后便再也没回来过,谁也不晓得她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估摸呀,你妈多半还在人世,只是我们没她的音信,找不到她罢了!”
“妈!妈!我的妈呀!你在哪里?儿子想你呀!儿子的命怎那么苦呀!”姜济勋一阵号啕大哭,突然站起来,一转身,朝着湘江边上猛跑。
“哟,奶奶,济、济勋怎么跑啦?”姜济木指着姜济勋的背影对耀大娭毑说。
“愣着干什么?死心眼!快!快追!快追呀!”耀大娭毑对着姜济木一声大吼。
茫茫夜色中,湘江边上有三个人影在往北奔跑。跑在最前头的是姜济勋,紧跟在他后头的是姜济木,跑在最后面的是耀大娭毑。其实,耀大娭毑那跑的样子已经不是跑了,甚至连走都说不上,简直快变成爬了,东倒西歪,七扭八拐,真让人怀疑会不会一下子栽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也难怪,六十岁出头的老太婆了,怎能跑得过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呢!
姜济勋脑袋往后仰着,胸脯往前挺着,两只胳膊不断地向上挥舞,两条腿玩命似地使劲拨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速度快极了。那样子根本不像正常人,简直就是个发了狂的疯子。姜济木的身体比姜济勋强壮得多,体格更加高大魁梧,两条腿也更加坚韧有力,要追上姜济勋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但他架不住还要照看远远落在后头的耀大娭毑,时不时地要回头看一眼她,喊一声“奶奶,你慢点”,因而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渐渐地,他和姜济勋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了。
见姜济勋越跑越远,耀大娭毑急了。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断断续续地对着姜济木大声叫喊:“济、济木,你、你管我干、干什么?快、快追他呀!快、快去截、截住他,千、千万别让他往、往河里跑!”
“噢,好吧,奶奶,那我就不管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就在这里歇着吧,我回头过来找你老人家!”姜济木说完,猛加一把劲,速度骤然提升。
姜济木的速度很快,眼看就要追上姜济勋了。但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前边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棚户区,姜济勋身子一转,钻进那棚户区里不见了。棚户区里乱糟糟的,到处是低矮简陋的小平房,到处是弯曲狭窄的小巷子,到处是堆满了杂物的犄角旮旯。姜济勋进到那里头,就像是钻进了姜子牙当年摆设的八卦迷魂阵,自身都找不到出去的路,别人哪里还找得到他的影子。
“糟糕,这里头那么乱,奶奶要是跑进来,可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回去找奶奶!”姜济木琢磨道。他心里惦记着奶奶,连忙顺着原路退了出来。
姜济木刚从棚户区里跑出来,恰巧耀大娭毑也一瘸一拐地走到了。
“怎、怎么啦?你、你没找到你、你弟弟?”耀大娭毑低着头,弯着腰,用手抚摸着胸口,气喘吁吁地问。
“没、没找到!那里头到处都是小巷子,乱七八糟、黑咕隆咚的,哪、哪、哪还看得见人呀!”姜济木喘着粗气说。
“你、你怎么不、不往里头追呀?”耀大娭毑又问。
“往里头追?那里头乱着呢,真要是追进去,只怕我自己都出不来了!”姜济木抬起手,不断地擦脑门上的汗。
歇了一阵子,耀大娭毑总算缓过一口气,活过来了。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用手一指大堤上面的一个大土堆说:“走,咱们上那里看看吧!那里地势高,站在那里朝下头看,兴许能看得出一点那棚户区里边的名堂来。”
棚户区设在江边上,地势远低于江堤上的那个大土堆。所以,站在大土堆上朝下一望,整个棚户区的全景便尽收眼底。耀大娭毑一看那棚户区便傻眼了。
“唉哟,我的娘,这棚户区好大好乱啊,里头藏起个把人来,哪找得到呀!且不说现在是夜里,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就是大白天也不好找啊,”耀大娭毑盯着那棚户区,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一大片棚子,少说也得有好几百间吧?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乱七八糟,而且还尽是犄角旮旯,往哪里找去?算了吧,先不找了,天亮了再说!”
“天亮再说?奶奶,那要是耽误久了,济勋会不会出事?”姜济木低声嗫嚅道。
“济勋出事?他能出什么事?你莫非是怕他投河自杀?他哪会那么做呢!傻小子,放心吧,他不会投河自杀的!不就是恋人变成了兄妹嘛,又不是爹死娘嫁人的事,哪至于投河自杀呢!他要真是因为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想不开,寻死觅活的,那也就算我鬼打昏了脑壳,瞎了眼,白疼他了!”耀大娭毑既像是在对姜济木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咱们这会儿上哪去?”姜济木问。
“上哪去?自然是先回梁家喽!我刚才已经和水玉她爸妈商量好了,”耀大娭毑嘴里说着话,眼睛却依旧盯着棚户区,“天不亮,咱们就走,带着他们一家三口子一起走。让她们去咱们乡下,在咱们家住一阵子,躲一躲孙棒子那恶魔。我估计这几天孙棒子会来梁家找麻烦的,赶紧躲开他吧,免得夜长梦多,你说是不?”
“是,是,你老人家考虑周全!”姜济木连连点头。
耀大娭毑带着姜济木马不停蹄地赶到梁家,却没有看见水玉。屋里只有水玉她爸妈,两口子满脸苦相,正在相对抹眼泪。一看这情况,耀大娭毑便明白一切了。她挨着水玉她妈坐下,扶着她的肩头,轻声问:“水玉跑了?”
“我刚把话说完,她、她就开开门一溜烟跑了。真是个不懂事的东西,要人操心劳神!”水玉她妈边哭边说,眼泪大把大把地往下流。
“没去找找?”耀大娭毑问。
“嗨,哪能不去找呢,可、可哪找得到她呀!出门前后左右都是小巷子,东南西北处处连通,天知道她往哪个方向跑了,”水玉她爸皱皱眉头,叹了口气,“再说,黑天黑夜的,到处都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兵,街上危险着呐!要是碰上那帮乌龟王八蛋,那还真不知道会出什么漏子呐!所以呀,我找了一阵便回来了。”
听水玉她爸说“到处都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兵”,耀大娭毑心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她暗地里琢磨道:“是呀,要是碰上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兵,那该怎么办?水玉这孩子呀,也真是不懂事,明明白白的事情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看来,水玉不回来,乡下还暂时不能回去了,先忙着找人要紧。”
耀大娭毑正想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水玉她爸却先开口了。他看了看耀大娭毑,用商量的口吻说:“老人家,水玉没着落,我们还真是没法跟您一起走。怎么着也得先把她找到,对不对?要不你老人家带着济木、济勋他们先回乡下去吧!”
“嗨,我们也没法走了!”耀大娭毑苦笑一声。
“哟,你老人家怎么没法走呀?”水玉她爸问。
耀大娭毑满脸愁云,叹息一声说:“我那孙子也是个不晓事的,他也想不通,一溜烟跑了,跑得不知去向!”
“喔,济勋也跑了?”水玉她爸妈几乎同时惊呼。
“是呀,济勋是沿着河边跑的。他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追。他在前边使劲地跑,我们就紧跟在后头拼命地追。但追了老半天,我们祖孙两个累得贼死,心都快跳出来了,却还是没能追上。眼看着他一转身跑进北头那片棚户区里去了,等我们赶到时,就不见了踪影。也不知道那瘟神究竟躲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头去了。那么大的人了,还是不让人省心,真是前世做的孽,该遭报应呀!”
“你老人家也别太着急,等天亮了,我们再一起去找。济勋和水玉应该就在这附近,不会跑远,更不会出太大的事。明摆着,他们两个的事并不大,说穿了也就行了,顶多暂时有点难为情,心里不舒服,一两天也就过去了,绝不至于想不通,要寻死觅活。我看呀,你老人家和济木就先别走了,安心在我们家住着吧。天亮了,咱们就一起去找孩子。等找到他们了,咱们再一起走,回你老人家那乡下去,行吗?”水玉她爸说,还是商量的口气。
“嗨,有什么行不行的呢,事情也就只能这样了喽。只是还要给你们两位添麻烦,真正不好意思,”耀大娭毑朝水玉她爸点点头,又朝水玉她妈看了看,“要不咱们分头找吧。我还去河边找,让济木跟你在周边的巷子里找!”
水玉她妈忙伸手拉拉耀大娭毑的衣襟,接下茬说:“哟,看你老人家说的,那有什么麻烦呀?你老人家是贵客,我们请都请不来的呢。只是没什么好招待,你老人家多原谅就是了。至于天亮后找孩子的事,我看还不如这样做比较好,让济木跟他叔到巷子里去找,我跟你老人家一起去河边吧。那地方太大,你老人家一个人跑不过来的。”
“没事,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河边地方虽大,却不难找,一眼就能望得到头。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孩子也可能会自己回来的,家里没人哪行啊!”耀大娭毑说。
天刚亮,四个人就开始分头行动了。水玉她爸去街东边,姜济木去街西边,耀大娭毑去河边,水玉她妈留在家里“守株待兔”。
耀大娭毑的目标很明确,认准姜济勋就藏在棚户区里。所以,一出梁家大门,她便直奔那片棚户区。但目标虽明确,要找到人却还真不容易。首先是那片棚户区很大,有近千间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棚子,住了好几百户人家,而且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要把每家每户都找到,都问遍,谈何容易!其次是那片棚户区太杂乱,巷子短小狭窄,且分布毫无规律可循,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还有很多走不通的死路和犄角旮旯,以致生人很难辨清方向,极容易顾此失彼,造成遗漏。还有一点是最麻烦的。那就是:棚户区的居民五方杂处,住的都是安徽、江苏一带的船工及其家属。他们不是本地人,根本听不懂耀大娭毑说的湘北话;而耀大娭毑很少接触过安徽、江苏人,自然也听不懂他们的话。这对耀大娭毑找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还常常闹出笑话,搞得她莫名其妙,啼笑皆非。
有一次,耀大娭毑向一个老头打听姜济勋的下落,说要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老头一听,乐呵呵的,便把她带到一个雇工成群聚集的地方去了。那些雇工见耀大娭毑来了,便一齐围了上来,纷纷问要人做什么活,一天给多少钱。原来,那老头听错了耀大娭毑的话,把“小伙子”听成了“小伙计”,误以为她是要找做工的“小伙计”。
还有一次,耀大娭毑找到一个老太婆,说要找人。那老太婆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她,忽然问:“要找男的还是女的?”她回答说:“要找男的。”那老太婆又问:“哦,要找男的是吧?那你是自己找还是替别人找呀?”她回答说:“当然是我自己找喽!”那老太婆咧开嘴乐了,呵呵笑着说:“那好,跟我来吧!”于是,那老太婆便不再说话,径自在前头走,领她到一户人家去了。那人家只有一个老头,见她来了,神情异常高兴,眼睛顿时便射出异样的光芒来。耀大娭毑一看那情况,便知道是发生误会了,连忙解释。结果,费了好大的劲,说了一大堆话,大家的误会才消除。原来,那老太婆听错了耀大娭毑的话,误以为她是寡妇,要找个老公嫁人。
耀大娭毑在棚户区里找了整整一天,累得半死,却什么信息也没得到。到傍晚时,她不得不拖着沉重的两条腿回梁家了。但她刚刚走到梁家门口,正要上前敲门,隔壁屋里突然伸出来一只手,一下子拽住了她的衣袖。她回头一看,拽她衣袖的原来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似乎是梁家的邻居。
“快,快进来,快进来!”那老太婆一边使眼色,一边低声喊叫。她的声音很急,几乎是命令式的口吻。
耀大娭毑心知有异,连忙一闪身进了屋。她刚一进屋,那老太婆便“呯”的一声把屋门关上了。
“你是梁家的亲戚?”老太婆问。
耀大娭毑看了看那老太婆,嗫嚅道:“嗯,就说是吧。不过,不是很亲,是远房的。请问,你老人家是?”
“噢,你问我呀?老身是梁家的邻居,平时和水玉她妈走得很近的,姓张。估摸我比你大几岁,你就叫我张嫂得了,要不就叫张姐也行,”老太婆故意压低声音急急地说,“你呀,得亏让我看见了,要不得出大事的!”
“出大事?出什么大事呀?”耀大娭毑吃惊地问。
“梁家出事啦!两口子都被灵官庙里的那帮汉奸伪军狗腿子抓走了!”张老太婆声音压得很低,神色十分慌张。
“哟,梁家两口子都被抓走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耀大娭毑心里陡然一惊。
“今早上抓走的,来了好些伪军狗腿子,个个都背着长枪,还上了刺刀,把梁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就我们家这门口都派上了好几个岗哨盯着呢!”张老太婆显然心有余悸,声音依旧压得很低。
“哦,那、那帮人凭什么要抓梁家的人呀?”耀大娭毑问。
“凭什么?这年头,他们抓人还需要理由?哼,就那帮丧尽天理良心的鬼子汉奸,天天想着法子祸害咱们老百姓,什么事不能兴个由头抓人呀,”张老太婆恨得咬牙切齿,“那帮子伪军来梁家抓人,名义上说是抓游击队。他们说梁家是游击队的窝点,昨晚上他家来游击队了。但老百姓谁不知道,他们这只是打了个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水玉那姑娘。水玉那小丫头长得漂亮,被伪军头子孙棒子看上了,非要娶回家里做小不可。梁家两口子都是好人家,当然不会同意啦,前些日子就把水玉藏起来了,让孙棒子见不着人,找不着人。这一下,就把孙棒子惹恼了,愣给梁家扣上了一个窝藏游击队的罪名。”
“那、那水玉呢?她没被抓走?”耀大娭毑问。
“没,水玉没抓着。据说那小丫头昨晚上回来了,后来又走了。得亏她走了,要不准得抓走被糟蹋不可。”张老太婆说。
“噢,原来是这么回子事,”耀大娭毑叹了口气,不停地搓着手,“这么说,我这会子还真是去不得梁家喽?”
“那哪能去呢!他们家这会儿到处都埋伏着汉奸狗腿子,专等着水玉姑娘回家,也专等着梁家的知情人上钩,”张老太婆悄声说,“你一去,那还不是自投罗网!”
“张姐,谢谢你老人家提醒。今天这事,要不是你老人家帮忙,我只怕早就被他们抓走了,”耀大娭毑轻声说,“不过,我和梁家虽说不上很亲,但也是平素常来往的,水玉她妈对我挺讲情义。如今他们家出事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你老人家说对不?我寻思想去看看他们,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只是搞不清他们如今关在哪里。”
“嗨,什么谢不谢的,我不也是顺手的事嘛,”张老太婆眨巴着眼说,“孙棒子那帮汉奸王八蛋伪军是驻扎在灵官庙里头。我估摸,水玉她爸妈多半也是被关在灵官庙里头。你要看他们,只怕还得往那里头去找。不过,那里头住着好些兵呢,到处都有背着枪站岗放哨的,你要去找水玉她爸妈,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哟!那帮子汉奸伪军,良心都是让狗吃了的,对咱老百姓可狠呐!他们让不让你进去,还真难说。你自己倒是要多留心啊,说话口气放软和点,千万别太冲啦,明白吗?”
“呃,明白,明白,我加倍小心就是。张姐呀,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耀大娭毑边说边往外走。
耀大娭毑的脚刚刚迈出门槛,还没来得及粘上街面,张老太婆又突然一伸手拽住她的衣袖,把她拽回来了。
“喂,我想起来了,灵官庙后头有一排小平房,比较低矮,是后来加盖的,上头插着铁丝网,看样子像关人的地方。我看呀,水玉她爸妈多半是关在那里头,你就上那里头去找找看吧!”张老太婆低声嘱咐道。
按照张老太婆的指引,耀大娭毑往左拐了两条小巷子,再往前走了里把路,很快就找到了灵官庙。果然,张老太婆猜得没错,灵官庙后头那排低矮的平房就是一个专门关人的临时监狱。那平房是东西排列,两头各有一道门,但东头的门上着锁,只有西头的门半开半掩。门外两侧各有一个端着枪的卫兵站岗,门里一侧的树底下还坐着一个腰挎盒子枪的。耀大娭毑一看那阵势,心里便明白一切了。
“哼,外头这两个站岗的只是摆设,求他们没用。里头树底下坐着的那个腰挎盒子枪的,才是真正管事的。老娘得把动作搞大点,把他引出来。”耀大娭毑这样想。她扫了一眼门口外头那两个站岗的卫兵,便挺直身子,迈开大步,旁若无人地径直朝大门走去。但她还没走近大门,便被左侧的卫兵拦住了。那卫兵年纪很轻,个子很高,站在耀大娭毑面前,差不多高出她两个脑袋。
“干什么的?老东西!你不要命啦?再不站住,老子开枪毙了你!”高个子卫兵一声大喊,接着又猛地一拉枪栓,把枪口直接对准了耀大娭毑的胸口。
卫兵的喊声很大,动作很凶猛,样子很吓人。要是别的女人,只怕早就被吓得胆颤心惊,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耀大娭毑个头虽矮小,胆大却是出了名的。她见过大世面,根本不在乎这个。她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依旧笑笑嘻嘻、平平静静的神态,就好像身边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她低头看着那卫兵手中紧握的枪,从握枪的手到枪托,从枪托到枪身,再从枪身一直到乌黑的枪口,都看了一个遍。而后,她又慢慢地抬起头来,直视着那卫兵的眼睛,用极低沉的语气缓缓地说:
“小伙子呀,别把枪口对着老太婆好吗?不是我老太婆害怕你那枪口,而是实实在在用不着这样做啊。我老太婆的年纪大概跟你爷爷、奶奶差不多吧?都六十好几了,骨头都能当鼓槌使了,身上也早就没什么力气了,又没带任何家伙,真正手无寸铁,你何苦用那枪口吓唬我呢!看你样子,身体蛮壮实的,像个有力气有能耐的人,为什么不拿着这枪到战场上去杀日本鬼子呢?你去杀日本鬼子,保卫了国家,那是做好事,大家也敬佩你是个中国人呀,对不?当然喽,上战场杀日本鬼子,也会要负伤,也会要流血,甚至也可能会丢性命,但那总比你现在强呀!你看看你现在,拿着枪为日本鬼子卖命,为汉奸头子卖命,昧着良心做事,天天被人戳着后脊梁骨骂,被老白姓恨得牙根痒痒的,那多没意思呀!你爷爷奶奶、父母家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们高兴你这样做吗?我想,他们多半还不知道你做的事吧?他们要是知道你在做这些事,那脸可就没处搁了,人还不得羞愧死呀?小伙子呀,你以为日本鬼子长久得了吗?实话告诉你吧,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久不了的!我听街上好些人都在议论,说日本鬼子是丧家犬,快完蛋了。他们在中国老打败仗,在全世界各地也都不得人心。小伙子呀,我劝你放聪明点,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千万别再一个心思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头子当枪使啦,那样会不得好死的!”
耀大娭毑本来不想说这么多的,但她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收不住了。高个子卫兵骂她是“老东西”,扬言要枪毙她,还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胸膛,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刺激太大了。她活到现在,都六十好几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实在是忍无可忍。然而,她话虽说得多,语气也很硬,但却句句在理。那高个子卫兵大概良心还没有完全让狗吃掉,听了她的话,也似乎觉得自己有些理亏,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手里端着枪不知所措,扭扭捏捏的,老大不自在。
耀大娭毑的算计没错,她有意识地把动作搞大了,就真把门里头那个跨盒子枪的引出来了。只见那人背着双手,踱着方步慢慢地走出大门,对着高个子卫兵说道:“孙长子,把枪收起,让老人家进来!”
对个子高大的男人,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一般都叫做“大个子”或“大高个”,而长沙、湘北等地的湖南人有些特别,他们一般不叫“大个子”或“大高个”,而是叫做“长子”。那个高个子卫兵姓孙,个头长得很高大,所以“孙长子”便成了他的外号了。孙长子见腰挎盒子枪的人向自己打招呼,连忙收起枪,转身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随即一声大喊道:“是,孙副官!”耀大娭毑见机快,见高个子卫兵让开了路,便连忙抬起脚迈进院门。她原以为那姓孙的副官会要对她狠狠训斥和严格盘查的,然而那姓孙的副官却并没有这样做。他只简单地问了问耀大娭毑的来意,便面无表情地领着她往院子中间走。
走到第四间屋子门首,姓孙的副官停了下来。他朝左右看了看,掏出钥匙打开屋门,指着屋里头,小声对耀大娭毑说:“老人家,你进去吧,梁家两口子就在屋里。说话抓紧点,别待时间太长了!”
屋角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豆粒大小的灯火有气无力地向周围播撒着昏黄暗淡的光线,愈显得整个房间的气氛凄苦惨烈,了无生气。耀大娭毑费了好大的劲才看清,水玉她爸躺在靠墙的地上,水玉她妈盘腿坐在他的身边。
“你、你们两个吃苦了!”耀大娭毑一阵哽咽,三脚两步地走上前,紧紧握住了水玉她妈伸过来的手。
水玉她妈没有说话,只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着,豆大的泪珠一滴接一滴地滴落在耀大娭毑的手背上。
水玉她爸直溜溜地躺着,手、脚、身子没有丝毫动静,只有嘴巴里还在不时地吐出痛苦的呻吟声。耀大娭毑一见那样子,便鼻子发酸,直想哭出声来。她强忍眼泪,看着水玉她妈问道:“狗娘养的汉奸狗腿子对老梁动刑啦?”
水玉她妈还是没有说话,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打得真够重的呀,狗娘养的王八蛋!”耀大娭毑一边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水玉她爸,一边咬着牙根说,那声音虽低沉,却满含着怒气。
“可、可不是嘛,都、都、都快让他们打死了!”水玉她妈终于开口了,话声里满是悲凄的哭音。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带包子来了,就在东头街口那家店里买的,还热着呢。来、来、来,趁热吃一口吧。你吃你的,老梁我来喂。这时候最要紧的呀,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什么事都比不上吃饭重要。吃了饭,身上有劲,好跟他们斗。要是不吃东西,饿坏了自己,可就更趁了那帮王八羔子汉奸卖国贼的意啦,明白吗?”耀大娭毑把手里的荷叶包放在地上,解开荷叶,从中拿出一个包子递到水玉她妈手里。
水玉她妈接过包子,却没往嘴里塞。她看了看包子,轻声说:“多谢你老人家的心意了,但我这会儿哪吃得下呀!不瞒你老人家说,我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得、得、得,快别说那不硬气的话了。这时候,哪能那么想呢!水玉她爸伤那么重,还得你来照顾呢,对不?水玉也还在外头盼着你回去呢,是不?关几天就会放出去的,哪至于严重到要自杀的份儿呢!你呀,这么点事就经不起,要自杀,那天底下的人还不都得死绝了?”耀大娭毑急急地说。
水玉她妈忽然不哭了,一本正经地说:“老人家,我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姓孙的那汉奸二鬼子如今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要把我们家水玉弄到手不可。为了逼我们家水玉现身露面,他不仅把我们两口子抓进了监狱,而且还给我们安了一个杀头的罪名,说我们私通游击队,窝藏游击队,家里有武器,有弹药什么的。你老人家想想,我们两口子能让他痛痛快快得到水玉吗?他要是得不到我们家水玉,那我们两口子还有活路可走吗?你瞧瞧他那心肠多狠毒呀,愣把我们家老梁往死里打,打成了内脏里出血的重伤,连肋骨都打折了三根。看这样子,我们家老梁是活不成了,最多也就是三两天的事。我们家老梁要是走了,我、我活着还、还有什么意思呀!”
“哎哟,他们打那么重呀?肋骨都折了!这帮子混蛋王八蛋,”耀大娭毑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我请个郎中来看看吧?”
水玉她妈连连摇头,带着哭音说:“你老人家千万别费那事了,花钱不说,他们也不会让郎中进门的。再说,郎中来了也没用,老梁这伤实在太重了,根本就没法治了。下午,他们也派来了一个郎中,但那郎中看了看,却只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叹气,连个方子都没开就一甩手走了。对老梁呀,别抱什么希望了,还是照管水玉要紧。你老人家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老人家托付水玉的事情呐!”
“咳呀,瞧你说的,水玉也是我的亲孙女呀,对不?照看她那不也是我自己的份内事嘛,哪用得着‘托付’两个字啊!这事你尽管放心,有老身在,水玉准能找得到的。这几天,我带着济木再抓紧时间找找就是了,无论如何也得把她找到!”耀大娭毑说。
水玉她妈又摇了摇头,盯着耀大娭毑说:“这会儿找不找得到水玉倒不要紧了,关键是要赶紧通知她,让她千万别回家,千万别到这牢房里来看我们!明摆着,孙棒子现在用的,是引鱼上钩的计谋。他把我们关进牢里,就是要用我们来引水玉上钩的。所以呀,我现在最着急的,倒不是找水玉,而是要想办法把眼前的情势告诉水玉,让她明白面前的危险,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高飞!”
水玉她妈的话说到了要害处,耀大娭毑听了,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是呀,眼前的情势真的是太危险了。孙棒子把水玉他爸妈抓起来,关进牢里,用的就是引鱼上钩的计。倘若水玉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地跑回了家,或者冒冒失失地到牢里来探望她父母,那不是正好中了孙棒子的阴谋诡计吗?他们可以就势抓住水玉,以她父母的性命和自由相威胁,逼她就范呀!不行,这情况太紧急了,得赶快想个办法通知水玉,让她火速逃走。但、但现在根本就搞不清楚水玉在哪里,想个什么法子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目前的情况通知到她,让她明白身边的危险和家里人的想法呢?”想到这里,耀大娭毑不禁双眉紧蹙,陷入了沉思。
耀大娭毑正在沉思,门口人影一闪,孙副官忽然进来了。他一进门,便急急地低声招呼耀大娭毑快走,说是门卫要换岗了,再不走,就会被新来的岗哨发觉。耀大娭毑晓得这事的利害关系,连忙简单嘱咐了水玉她妈几句,起身就走。一出牢门,她就朝东走,想从进来时的那个门出去,这时孙副官拽住了她。
“不能走那边,”孙副官低声说,“来,大娘,跟我来!”
孙副官拽着耀大娭毑的衣袖一路小跑,从牢房前面的一个小门出去,进了灵官寺的后院,再从灵官寺的后院一直往左走,然后再往右一拐,没走几步路便到了一个圆洞门。出了那圆洞门,孙副官不走了。他用手一指前边说:“前面十字路口往左拐,就是你老人家来时的那条小巷子。大娘,你快走吧!”
孙副官不仅没有刁难,反倒温言细语,处处关照,这令耀大娭毑感到意外。她扫了一眼孙副官,和颜悦色地说:“没想到,你倒是个好人,跟门口那个卫兵大不一样。好,小伙子,多行行善吧,会有好报的!”
“好人?这世道无路可走,好人都快逼成坏人了。你老人家高看我,我很高兴,”孙副官轻声说,“你老人家说得对,为人在世是应该多行善,做好事。好人做不成,我就多做做好事吧。不过,门口那个卫兵本质也不坏,心肠挺善的,只是年纪太轻,还不太懂事罢了。你老人家放心,我会多说说他的。”
“噢,那也许是我错看他了。不要紧,我不记恨他。你姓孙,他也姓孙,你们俩是不是一家子呀?”耀大娭毑问。
“我们营长也姓孙,外号叫做孙棒子。不过,跟你老人家说实话,”孙副官朝前后左右瞧了瞧,说话声压得特别低,“我们三个都姓孙,都是一个族里的,有点沾亲带故,但不是一家子,更不是一个心眼。孙棒子是无恶不作,我和那个卫兵却是迫不得已才当伪军的。我们家欠了孙棒子一大笔债,三辈子都还不清,家里又有妻儿老小,一家人都指着我挣钱吃饭,不出来挣点钱,这日子怎么过呀?孙长子,也就是那个卫兵,他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只怕比我还要苦些。你老人家可千万莫把我们三个人一起看啊!”
“你是个好人,孙棒子是无可救药的坏人,你们不是一路的,这我晓得。但你长期和他混在一起,终归也不是个事啊,对不?日本鬼子长不了啦,孙棒子也长不了啦,你得赶紧另谋生路啊!”耀大娭毑说。
“是呀,你老人家说得对,鬼子的日子不多了,伪军的差当不得了,我得赶紧离开他们,另谋生路。谢谢你老人家的好意提醒!时候不早了,这地方有危险,久留不得,你老人家赶快走吧!”孙副官悄声说。说完,他又小心翼翼地朝前后左右看了看。
离开灵官寺,耀大娭毑就直奔梁家后面的那个大空场子。还没到大空场子,她就远远地看见大樟树的底下坐着自己的孙子姜济木。
辛辛苦苦地跑了一整天,姜济木一点收获都没有。直到天快黑了,他才不得不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梁家。但他还没到梁家门首便发现了意外:门外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屋里也没有点灯,却有人在低声说话。那话音粗声粗气,很野蛮,不是梁家人说的,却像兵痞子的口吻。他心知情况有异,怕出危险,便连忙一侧身,迅疾地转了个弯,钻进旁边的小过道,一路小跑溜到大空场子来了。
一见奶奶的面,姜济木便问有弟弟姜济勋的消息没有。耀大娭毑没有回答孙子的提问,却冷着脸反问道:“喂,你晓得你们米行张老板住在哪里吗?”
姜济木愣了一下,说:“哟,你老人家怎么打听这个呀?要找张老板吗?找他干什么?济勋不会去他那里的!”
耀大娭毑急了,眼睛珠子一瞪,大声吼道:“哎呀,你就快说吧,到底晓不晓得你们张老板的住处呀?”
“张老板的住处,我当然晓得喽,”姜济木伸手挠挠后脑勺,“他有两个住处呢,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区。你老人家问的是哪一个?”
“那他现在是住在哪里?城里,还是郊区?”
“郊区!”
“郊区?郊区哪里呀?那地方,你晓得吗?”
“晓得呀,就在城郊捞刀河附近,我还去过那里呢。奶奶,你打听我们张老板的住处干什么呀,莫非济勋去他家啦?”姜济木一脸好奇的神气。
“走,你快带我去见张老板,我有件天大的事要和他商量!其他事,咱们路上再说吧!”耀大娭毑说完,拔腿就走。
阵阵江风从树顶上扫过,吹得树叶簌簌作响。耀大娭毑抬头看看天,一片树叶忽然落了下来,掉在她的脸上。她摇摇头,抖落掉树叶,又扭扭腰,伸伸胳膊,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过了半夜,天气就转凉了。她衣服穿得单薄,早就感到有些凉意了。这时一股带着浓重水气的江风吹来,直往衣袖里、脖领里钻,她不觉浑身起了好多鸡皮疙瘩。“哟,还真有些冷呐!”耀大娭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伸拳蹬腿,围着那树活动身子。
“你老人家冷了吧?要不先回屋里暖和暖和?”水玉她妈看着耀大娭毑,小声说。
“不了,不了!何必费那事呢?咱们还是赶紧把事情定下来吧,”耀大娭毑说。话里明显带着点怕冷的颤音,“时间确实有点晚了,咱们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再拖下去,被鬼子的巡逻队发现了,可就不得了喽。再说,我也累了,困了,想睏觉(睡觉)了。要不这么办吧,我拿主意,你们听我的。事情万分紧急,绝对不能过夜,现在咱们就把水玉和济勋叫醒,分头跟他们谈。济勋嘛,我来谈。水玉呢,你们两个找她谈。治大病要用猛药,谈大事要讲狠话。他们两个从相识到相交,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感情好得黏糊在一起了,也就难舍难分了。现在呀,他们正是深陷泥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看呀,在这节骨眼上,不讲几句狠话,他们是不会很快清醒的。所以,咱们谈这事的时候,话一定要说得干脆,说得利落,斩钉截铁,绝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要从头至尾说得清清楚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也一定要说透说深,说得明明白白,说得他们真正打心底里信服。你们两口子再想想,看还有别的想法没有?”
“没啦,没啦!你老人家想得这样周到,我们哪还有别的想法呀,就照你老人家的意思办吧!”水玉她爸妈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你们没意见,那就去叫醒孩子们吧!”耀大娭毑说。
“好的,我这就去叫醒孩子,”水玉她妈边说边起身,“对了,你老人家还没吩咐呢,两个孩子是都叫到这里来吗?”
“不、不、不,两个孩子哪能在一起谈呢,”耀大娭毑连连摇手,“碍着面子呀,对不?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嘛,咱们分开谈。你们和水玉就在屋里谈吧,把济勋喊出来就行了。”
“那好吧,你老人家略等等,我去喊济勋过来,”水玉她妈说。说完,她又回头走了过来,脱下身上的外衣扔给耀大娭毑,“你老人家快披上这件衣服吧,外头有点凉!”
“呵呵,我也不客气了,这阵子还真是有点凉呢!”耀大娭毑接过衣服,连忙穿上。
水玉她爸也起身了,站在一旁等水玉她妈。水玉她妈朝水玉她爸扫了一眼,正转身要走,耀大娭毑一挥手,又把她留了下来。
“等、等,我还有个事要说。这个家,你们是住不得了,得赶紧走!”耀大娭毑说。
“走?往哪里走呀?我们家一无亲戚可投,二无朋友可靠,眼下真正是走投无路了!”水玉她妈说,话音很凄凉。
“怎么会走投无路呢?眼下不就有一条路嘛!”耀大娭毑满脸都是笑。
“眼下就有路?哪里有路呀?”水玉她妈不解地问。
“嗨,我们乡下呀,”耀大娭毑拖着长音说,“难道你不把我当亲戚、朋友吗?”
水玉她爸妈相互对视一眼,齐声说:“哪好意思给你老人家添麻烦呀!”
“哟,添麻烦?水玉她妈,你这说法多生分呀!亲朋之间,帮帮忙难道不是应该的?平常素不相识的人见一面都是缘分,更何况咱们两家之间还有水玉这根线牵着呢!对了,”耀大娭毑微微笑着,显得非常诚恳,“咱们刚才不是说好了的嘛,我让济勋给你当儿子的。怎么刚过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忘了这档子事啦!该不是反悔了吧?”
“没有,没有,”水玉她妈边笑边摇手,“收那么好的一个儿子,我当然求之不得喽,哪里还会反悔呢?”
“那好,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就是亲戚,就是最亲最亲的亲戚,”耀大娭毑轻轻地拍着手,笑得满脸开花,“是亲戚可就得常走动,别生分哟!我可是给你们说好了哦,孙棒子那王八蛋肯定会要继续无理纠缠的,没准还会带枪来抢人呢!这个家,你们可真是待不得了,有危险的!干脆,你们都跟我去乡下吧,到我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咱们明天就走,行不行?你们要是相信我的话,那就别啰嗦,稍稍收拾一下东西,带几件换洗衣服,明天一早动身,带着水玉跟我们一起去乡下。咱们呀,赶早不赶晚,乘天亮以前的头班轮船走。我们家呀,也很穷,但饭总还是有得吃的,只要你们不挑剔就行!”
水玉她妈忙小声打哈哈:“哎哟哟,看你老人家说的!带我们一起走,那是你老人家看得起我们,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哪还能挑剔呀!只要你老人家给口饭吃,让我们留口气,不饿死,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水玉她爸妈回屋不久,姜济勋和姜济木兄弟两个就来到大空场的樟树底下了。姜济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东倒西歪地走了过来,P股往地上一蹲,扯开嗓子就嚷:“奶奶,什么事那么急呀,非得这时候说?我还没睡醒呐,一个梦都没做完!”
“是嘛,正做梦呀?梦见什么啦?”耀大娭毑和颜悦色,话里充满了慈爱。
“梦见和水玉在一起”姜济勋揉揉眼睛。
耀大娭毑一惊,连忙打断孙子的话,急急地问:“哦,和水玉在一起,在一起干什么呀?”
“在一起瞎玩呗,还能干什么?”姜济勋嘟囔道,头都没抬。
“噢,在一起玩,没干什么,那、那就好,那就好。”耀大娭毑似乎心里想着别的事,话说得零零碎碎。
姜济勋猛地抬起头来,眼睛盯着耀大娭毑:“不让人安生睡觉,把人从床上拽起来,究竟有什么事呀?”
“当然是有天大的急事喽!没有天大的急事,我三更半夜里叫你起来干什么?鬼打起呀?抽风呀?嗨,我问你哦,”耀大娭毑说,声音不大,语气却很重,“你还记得你曾经有过一个小妹妹吗?”
“你老人家是说那个叫做‘夜哭猪’的珠儿吧?事情嘛,我还勉强记得,晓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妹妹。但她的样子,我可就真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她不是被我妈带走了嘛,当时还只有两岁多呐,只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姜济勋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不,她没死,她、她还活着!”耀大娭毑哽咽着说,声音很低沉。她仰头看着星空,泪珠围着眼眶转。
见奶奶突然哭了,姜济勋大吃一惊。他猛地抬起头来,怪模怪样地看着耀大娭毑,大声问:“奶奶,你、你怎么啦?是想起珠儿来了?嗨,事情都快过去二十年了,还想她干什么?她肯定早死了,不可能还活着的!”
“怎么不可能活着?她就是还活着,如今就在长沙城里呢!”耀大娭毑抬手擦擦眼泪。
“是嘛,珠儿还活着?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姜济勋就像是挨了雷击似的,突然从地上蹦了起来,睡意顿时烟消云散。
耀大娭毑依旧眼泪围着眼珠转。她撩起衣角擦了擦眼睛,静静地说:“我当然知道喽,因为我见到她了!”
“哟,你老人家见到珠儿啦?她在哪里?快告诉我吧,我现在就去看她!”姜济勋凑到奶奶跟前火急火燎地说。
耀大娭毑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远处黑黝黝的屋顶,缓缓地说:“你也见过她了!你见到她比我还早得多呐!”
“是嘛,我也见过珠儿啦?那、那怎么可能呢!这些日子,我根本就没见过别的什么人呀!这、这、这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呀?奶奶,你把我搞糊涂了!”姜济勋大声喊道,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态。
耀大娭毑忽地从远处的屋顶收回眼神,低着头,看着地面,声音很低神态却很严厉地问:“你知道珠儿是谁吗?”
“我、我哪能知道珠儿是谁呢!奶奶,你老人家就别跟孙子打哑谜了,快点告诉我吧,珠儿究竟是谁呀?她在哪里呀?”姜济勋急得火烧眉毛,不自觉地围着矮凳转起圈来。
“实话告诉你吧,她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耀大娭毑神情严肃,语速很慢,语音低沉,几乎是一字一顿,“其实,你这些日子,天天都见着她,天天都和她在一起呢!她、她、她就是梁家的水玉姑娘!”
耀大娭毑的话犹如一声霹雳,把姜济勋打懵了。他忽地停止转圈,站在当地发愣,眼睛直直地盯着夜空,半天不言声。
“水玉是珠儿,这、这怎么可能呢?这、这是不可能的呀!”姜济勋仿佛神经失常,没完没了地喃喃自语。
“怎么不可能?实话说吧,这事我早就怀疑上了,”耀大娭毑走到姜济勋面前,轻轻地扶着他的肩头,将他按在凳子上坐好,“从水玉刚进咱们家门那时候起,我就怀疑上了。她和你长得那么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她又还有‘夜哭猪’的外号,这难道是巧合吗?天底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呀!这次我来长沙,其实就是找梁家证实这件事的。刚才我找水玉她爸妈聊了聊,问题就彻底弄明白了。没错,水玉就是珠儿,就是你的亲妹妹济珠。十七年前你妈来长沙时,由于带着珠儿不方便,找不到事情做,没有饭吃,饿得半夜里晕倒在梁家门口,被水玉她妈救了。后来,你妈觉得水玉她妈一家子都是好人,便把珠儿送给了她们家。孩子呀,这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奶奶没骗你。奶奶也没必要骗你呀,对不?”
姜济勋低着头,用手使劲抠着头皮,就像要把那满头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统统拔起来似的。他完全被奶奶的话震惊了,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事实。突然间,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盯着远处那一大片黑黝黝的屋顶,用嘶哑的嗓音问道:“那、那、那我妈呢?她去哪里了?现在还有音信吗,还能找到她吗?”
耀大娭毑挪挪凳子,坐得离姜济勋更近了些,伸手摸摸他的头,柔声细语地说:“水玉她妈说,你妈把珠儿留给梁家后,就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她当然是找事做去了,她要吃饭呀,要养活自己呀,对不?她究竟做什么事去了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她也许给人家当保姆去了,也许进厂当女工去了,也许另找人家了。这都是没准的事。水玉她妈还说,你妈临走时曾经撂下话,要水玉她妈把珠儿改个名字,并搬几次家,离开那些老邻居,免得后来人多嘴杂,说漏了珠儿的事,让珠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水玉她妈晓得你妈是诚心诚意为梁家好,便也就听信了她的话,真的搬了家,并把珠儿的名字改成了水玉。家搬了,地址变了,孩子的名字也改了,你妈即便想找珠儿,也就找不到了。水玉她妈还说,她后来还回原来的住地去过几次,问那些老邻居们见没见过你妈,知不知道你妈的消息。那些老邻居都说,你妈自打走了以后便再也没回来过,谁也不晓得她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估摸呀,你妈多半还在人世,只是我们没她的音信,找不到她罢了!”
“妈!妈!我的妈呀!你在哪里?儿子想你呀!儿子的命怎那么苦呀!”姜济勋一阵号啕大哭,突然站起来,一转身,朝着湘江边上猛跑。
“哟,奶奶,济、济勋怎么跑啦?”姜济木指着姜济勋的背影对耀大娭毑说。
“愣着干什么?死心眼!快!快追!快追呀!”耀大娭毑对着姜济木一声大吼。
茫茫夜色中,湘江边上有三个人影在往北奔跑。跑在最前头的是姜济勋,紧跟在他后头的是姜济木,跑在最后面的是耀大娭毑。其实,耀大娭毑那跑的样子已经不是跑了,甚至连走都说不上,简直快变成爬了,东倒西歪,七扭八拐,真让人怀疑会不会一下子栽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也难怪,六十岁出头的老太婆了,怎能跑得过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呢!
姜济勋脑袋往后仰着,胸脯往前挺着,两只胳膊不断地向上挥舞,两条腿玩命似地使劲拨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速度快极了。那样子根本不像正常人,简直就是个发了狂的疯子。姜济木的身体比姜济勋强壮得多,体格更加高大魁梧,两条腿也更加坚韧有力,要追上姜济勋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但他架不住还要照看远远落在后头的耀大娭毑,时不时地要回头看一眼她,喊一声“奶奶,你慢点”,因而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渐渐地,他和姜济勋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了。
见姜济勋越跑越远,耀大娭毑急了。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断断续续地对着姜济木大声叫喊:“济、济木,你、你管我干、干什么?快、快追他呀!快、快去截、截住他,千、千万别让他往、往河里跑!”
“噢,好吧,奶奶,那我就不管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就在这里歇着吧,我回头过来找你老人家!”姜济木说完,猛加一把劲,速度骤然提升。
姜济木的速度很快,眼看就要追上姜济勋了。但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前边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棚户区,姜济勋身子一转,钻进那棚户区里不见了。棚户区里乱糟糟的,到处是低矮简陋的小平房,到处是弯曲狭窄的小巷子,到处是堆满了杂物的犄角旮旯。姜济勋进到那里头,就像是钻进了姜子牙当年摆设的八卦迷魂阵,自身都找不到出去的路,别人哪里还找得到他的影子。
“糟糕,这里头那么乱,奶奶要是跑进来,可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回去找奶奶!”姜济木琢磨道。他心里惦记着奶奶,连忙顺着原路退了出来。
姜济木刚从棚户区里跑出来,恰巧耀大娭毑也一瘸一拐地走到了。
“怎、怎么啦?你、你没找到你、你弟弟?”耀大娭毑低着头,弯着腰,用手抚摸着胸口,气喘吁吁地问。
“没、没找到!那里头到处都是小巷子,乱七八糟、黑咕隆咚的,哪、哪、哪还看得见人呀!”姜济木喘着粗气说。
“你、你怎么不、不往里头追呀?”耀大娭毑又问。
“往里头追?那里头乱着呢,真要是追进去,只怕我自己都出不来了!”姜济木抬起手,不断地擦脑门上的汗。
歇了一阵子,耀大娭毑总算缓过一口气,活过来了。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用手一指大堤上面的一个大土堆说:“走,咱们上那里看看吧!那里地势高,站在那里朝下头看,兴许能看得出一点那棚户区里边的名堂来。”
棚户区设在江边上,地势远低于江堤上的那个大土堆。所以,站在大土堆上朝下一望,整个棚户区的全景便尽收眼底。耀大娭毑一看那棚户区便傻眼了。
“唉哟,我的娘,这棚户区好大好乱啊,里头藏起个把人来,哪找得到呀!且不说现在是夜里,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就是大白天也不好找啊,”耀大娭毑盯着那棚户区,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一大片棚子,少说也得有好几百间吧?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乱七八糟,而且还尽是犄角旮旯,往哪里找去?算了吧,先不找了,天亮了再说!”
“天亮再说?奶奶,那要是耽误久了,济勋会不会出事?”姜济木低声嗫嚅道。
“济勋出事?他能出什么事?你莫非是怕他投河自杀?他哪会那么做呢!傻小子,放心吧,他不会投河自杀的!不就是恋人变成了兄妹嘛,又不是爹死娘嫁人的事,哪至于投河自杀呢!他要真是因为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想不开,寻死觅活的,那也就算我鬼打昏了脑壳,瞎了眼,白疼他了!”耀大娭毑既像是在对姜济木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咱们这会儿上哪去?”姜济木问。
“上哪去?自然是先回梁家喽!我刚才已经和水玉她爸妈商量好了,”耀大娭毑嘴里说着话,眼睛却依旧盯着棚户区,“天不亮,咱们就走,带着他们一家三口子一起走。让她们去咱们乡下,在咱们家住一阵子,躲一躲孙棒子那恶魔。我估计这几天孙棒子会来梁家找麻烦的,赶紧躲开他吧,免得夜长梦多,你说是不?”
“是,是,你老人家考虑周全!”姜济木连连点头。
耀大娭毑带着姜济木马不停蹄地赶到梁家,却没有看见水玉。屋里只有水玉她爸妈,两口子满脸苦相,正在相对抹眼泪。一看这情况,耀大娭毑便明白一切了。她挨着水玉她妈坐下,扶着她的肩头,轻声问:“水玉跑了?”
“我刚把话说完,她、她就开开门一溜烟跑了。真是个不懂事的东西,要人操心劳神!”水玉她妈边哭边说,眼泪大把大把地往下流。
“没去找找?”耀大娭毑问。
“嗨,哪能不去找呢,可、可哪找得到她呀!出门前后左右都是小巷子,东南西北处处连通,天知道她往哪个方向跑了,”水玉她爸皱皱眉头,叹了口气,“再说,黑天黑夜的,到处都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兵,街上危险着呐!要是碰上那帮乌龟王八蛋,那还真不知道会出什么漏子呐!所以呀,我找了一阵便回来了。”
听水玉她爸说“到处都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兵”,耀大娭毑心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她暗地里琢磨道:“是呀,要是碰上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巡逻兵,那该怎么办?水玉这孩子呀,也真是不懂事,明明白白的事情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看来,水玉不回来,乡下还暂时不能回去了,先忙着找人要紧。”
耀大娭毑正想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水玉她爸却先开口了。他看了看耀大娭毑,用商量的口吻说:“老人家,水玉没着落,我们还真是没法跟您一起走。怎么着也得先把她找到,对不对?要不你老人家带着济木、济勋他们先回乡下去吧!”
“嗨,我们也没法走了!”耀大娭毑苦笑一声。
“哟,你老人家怎么没法走呀?”水玉她爸问。
耀大娭毑满脸愁云,叹息一声说:“我那孙子也是个不晓事的,他也想不通,一溜烟跑了,跑得不知去向!”
“喔,济勋也跑了?”水玉她爸妈几乎同时惊呼。
“是呀,济勋是沿着河边跑的。他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追。他在前边使劲地跑,我们就紧跟在后头拼命地追。但追了老半天,我们祖孙两个累得贼死,心都快跳出来了,却还是没能追上。眼看着他一转身跑进北头那片棚户区里去了,等我们赶到时,就不见了踪影。也不知道那瘟神究竟躲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头去了。那么大的人了,还是不让人省心,真是前世做的孽,该遭报应呀!”
“你老人家也别太着急,等天亮了,我们再一起去找。济勋和水玉应该就在这附近,不会跑远,更不会出太大的事。明摆着,他们两个的事并不大,说穿了也就行了,顶多暂时有点难为情,心里不舒服,一两天也就过去了,绝不至于想不通,要寻死觅活。我看呀,你老人家和济木就先别走了,安心在我们家住着吧。天亮了,咱们就一起去找孩子。等找到他们了,咱们再一起走,回你老人家那乡下去,行吗?”水玉她爸说,还是商量的口气。
“嗨,有什么行不行的呢,事情也就只能这样了喽。只是还要给你们两位添麻烦,真正不好意思,”耀大娭毑朝水玉她爸点点头,又朝水玉她妈看了看,“要不咱们分头找吧。我还去河边找,让济木跟你在周边的巷子里找!”
水玉她妈忙伸手拉拉耀大娭毑的衣襟,接下茬说:“哟,看你老人家说的,那有什么麻烦呀?你老人家是贵客,我们请都请不来的呢。只是没什么好招待,你老人家多原谅就是了。至于天亮后找孩子的事,我看还不如这样做比较好,让济木跟他叔到巷子里去找,我跟你老人家一起去河边吧。那地方太大,你老人家一个人跑不过来的。”
“没事,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河边地方虽大,却不难找,一眼就能望得到头。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孩子也可能会自己回来的,家里没人哪行啊!”耀大娭毑说。
天刚亮,四个人就开始分头行动了。水玉她爸去街东边,姜济木去街西边,耀大娭毑去河边,水玉她妈留在家里“守株待兔”。
耀大娭毑的目标很明确,认准姜济勋就藏在棚户区里。所以,一出梁家大门,她便直奔那片棚户区。但目标虽明确,要找到人却还真不容易。首先是那片棚户区很大,有近千间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棚子,住了好几百户人家,而且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要把每家每户都找到,都问遍,谈何容易!其次是那片棚户区太杂乱,巷子短小狭窄,且分布毫无规律可循,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还有很多走不通的死路和犄角旮旯,以致生人很难辨清方向,极容易顾此失彼,造成遗漏。还有一点是最麻烦的。那就是:棚户区的居民五方杂处,住的都是安徽、江苏一带的船工及其家属。他们不是本地人,根本听不懂耀大娭毑说的湘北话;而耀大娭毑很少接触过安徽、江苏人,自然也听不懂他们的话。这对耀大娭毑找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还常常闹出笑话,搞得她莫名其妙,啼笑皆非。
有一次,耀大娭毑向一个老头打听姜济勋的下落,说要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老头一听,乐呵呵的,便把她带到一个雇工成群聚集的地方去了。那些雇工见耀大娭毑来了,便一齐围了上来,纷纷问要人做什么活,一天给多少钱。原来,那老头听错了耀大娭毑的话,把“小伙子”听成了“小伙计”,误以为她是要找做工的“小伙计”。
还有一次,耀大娭毑找到一个老太婆,说要找人。那老太婆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她,忽然问:“要找男的还是女的?”她回答说:“要找男的。”那老太婆又问:“哦,要找男的是吧?那你是自己找还是替别人找呀?”她回答说:“当然是我自己找喽!”那老太婆咧开嘴乐了,呵呵笑着说:“那好,跟我来吧!”于是,那老太婆便不再说话,径自在前头走,领她到一户人家去了。那人家只有一个老头,见她来了,神情异常高兴,眼睛顿时便射出异样的光芒来。耀大娭毑一看那情况,便知道是发生误会了,连忙解释。结果,费了好大的劲,说了一大堆话,大家的误会才消除。原来,那老太婆听错了耀大娭毑的话,误以为她是寡妇,要找个老公嫁人。
耀大娭毑在棚户区里找了整整一天,累得半死,却什么信息也没得到。到傍晚时,她不得不拖着沉重的两条腿回梁家了。但她刚刚走到梁家门口,正要上前敲门,隔壁屋里突然伸出来一只手,一下子拽住了她的衣袖。她回头一看,拽她衣袖的原来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似乎是梁家的邻居。
“快,快进来,快进来!”那老太婆一边使眼色,一边低声喊叫。她的声音很急,几乎是命令式的口吻。
耀大娭毑心知有异,连忙一闪身进了屋。她刚一进屋,那老太婆便“呯”的一声把屋门关上了。
“你是梁家的亲戚?”老太婆问。
耀大娭毑看了看那老太婆,嗫嚅道:“嗯,就说是吧。不过,不是很亲,是远房的。请问,你老人家是?”
“噢,你问我呀?老身是梁家的邻居,平时和水玉她妈走得很近的,姓张。估摸我比你大几岁,你就叫我张嫂得了,要不就叫张姐也行,”老太婆故意压低声音急急地说,“你呀,得亏让我看见了,要不得出大事的!”
“出大事?出什么大事呀?”耀大娭毑吃惊地问。
“梁家出事啦!两口子都被灵官庙里的那帮汉奸伪军狗腿子抓走了!”张老太婆声音压得很低,神色十分慌张。
“哟,梁家两口子都被抓走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耀大娭毑心里陡然一惊。
“今早上抓走的,来了好些伪军狗腿子,个个都背着长枪,还上了刺刀,把梁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就我们家这门口都派上了好几个岗哨盯着呢!”张老太婆显然心有余悸,声音依旧压得很低。
“哦,那、那帮人凭什么要抓梁家的人呀?”耀大娭毑问。
“凭什么?这年头,他们抓人还需要理由?哼,就那帮丧尽天理良心的鬼子汉奸,天天想着法子祸害咱们老百姓,什么事不能兴个由头抓人呀,”张老太婆恨得咬牙切齿,“那帮子伪军来梁家抓人,名义上说是抓游击队。他们说梁家是游击队的窝点,昨晚上他家来游击队了。但老百姓谁不知道,他们这只是打了个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水玉那姑娘。水玉那小丫头长得漂亮,被伪军头子孙棒子看上了,非要娶回家里做小不可。梁家两口子都是好人家,当然不会同意啦,前些日子就把水玉藏起来了,让孙棒子见不着人,找不着人。这一下,就把孙棒子惹恼了,愣给梁家扣上了一个窝藏游击队的罪名。”
“那、那水玉呢?她没被抓走?”耀大娭毑问。
“没,水玉没抓着。据说那小丫头昨晚上回来了,后来又走了。得亏她走了,要不准得抓走被糟蹋不可。”张老太婆说。
“噢,原来是这么回子事,”耀大娭毑叹了口气,不停地搓着手,“这么说,我这会子还真是去不得梁家喽?”
“那哪能去呢!他们家这会儿到处都埋伏着汉奸狗腿子,专等着水玉姑娘回家,也专等着梁家的知情人上钩,”张老太婆悄声说,“你一去,那还不是自投罗网!”
“张姐,谢谢你老人家提醒。今天这事,要不是你老人家帮忙,我只怕早就被他们抓走了,”耀大娭毑轻声说,“不过,我和梁家虽说不上很亲,但也是平素常来往的,水玉她妈对我挺讲情义。如今他们家出事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你老人家说对不?我寻思想去看看他们,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只是搞不清他们如今关在哪里。”
“嗨,什么谢不谢的,我不也是顺手的事嘛,”张老太婆眨巴着眼说,“孙棒子那帮汉奸王八蛋伪军是驻扎在灵官庙里头。我估摸,水玉她爸妈多半也是被关在灵官庙里头。你要看他们,只怕还得往那里头去找。不过,那里头住着好些兵呢,到处都有背着枪站岗放哨的,你要去找水玉她爸妈,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哟!那帮子汉奸伪军,良心都是让狗吃了的,对咱老百姓可狠呐!他们让不让你进去,还真难说。你自己倒是要多留心啊,说话口气放软和点,千万别太冲啦,明白吗?”
“呃,明白,明白,我加倍小心就是。张姐呀,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耀大娭毑边说边往外走。
耀大娭毑的脚刚刚迈出门槛,还没来得及粘上街面,张老太婆又突然一伸手拽住她的衣袖,把她拽回来了。
“喂,我想起来了,灵官庙后头有一排小平房,比较低矮,是后来加盖的,上头插着铁丝网,看样子像关人的地方。我看呀,水玉她爸妈多半是关在那里头,你就上那里头去找找看吧!”张老太婆低声嘱咐道。
按照张老太婆的指引,耀大娭毑往左拐了两条小巷子,再往前走了里把路,很快就找到了灵官庙。果然,张老太婆猜得没错,灵官庙后头那排低矮的平房就是一个专门关人的临时监狱。那平房是东西排列,两头各有一道门,但东头的门上着锁,只有西头的门半开半掩。门外两侧各有一个端着枪的卫兵站岗,门里一侧的树底下还坐着一个腰挎盒子枪的。耀大娭毑一看那阵势,心里便明白一切了。
“哼,外头这两个站岗的只是摆设,求他们没用。里头树底下坐着的那个腰挎盒子枪的,才是真正管事的。老娘得把动作搞大点,把他引出来。”耀大娭毑这样想。她扫了一眼门口外头那两个站岗的卫兵,便挺直身子,迈开大步,旁若无人地径直朝大门走去。但她还没走近大门,便被左侧的卫兵拦住了。那卫兵年纪很轻,个子很高,站在耀大娭毑面前,差不多高出她两个脑袋。
“干什么的?老东西!你不要命啦?再不站住,老子开枪毙了你!”高个子卫兵一声大喊,接着又猛地一拉枪栓,把枪口直接对准了耀大娭毑的胸口。
卫兵的喊声很大,动作很凶猛,样子很吓人。要是别的女人,只怕早就被吓得胆颤心惊,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耀大娭毑个头虽矮小,胆大却是出了名的。她见过大世面,根本不在乎这个。她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依旧笑笑嘻嘻、平平静静的神态,就好像身边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她低头看着那卫兵手中紧握的枪,从握枪的手到枪托,从枪托到枪身,再从枪身一直到乌黑的枪口,都看了一个遍。而后,她又慢慢地抬起头来,直视着那卫兵的眼睛,用极低沉的语气缓缓地说:
“小伙子呀,别把枪口对着老太婆好吗?不是我老太婆害怕你那枪口,而是实实在在用不着这样做啊。我老太婆的年纪大概跟你爷爷、奶奶差不多吧?都六十好几了,骨头都能当鼓槌使了,身上也早就没什么力气了,又没带任何家伙,真正手无寸铁,你何苦用那枪口吓唬我呢!看你样子,身体蛮壮实的,像个有力气有能耐的人,为什么不拿着这枪到战场上去杀日本鬼子呢?你去杀日本鬼子,保卫了国家,那是做好事,大家也敬佩你是个中国人呀,对不?当然喽,上战场杀日本鬼子,也会要负伤,也会要流血,甚至也可能会丢性命,但那总比你现在强呀!你看看你现在,拿着枪为日本鬼子卖命,为汉奸头子卖命,昧着良心做事,天天被人戳着后脊梁骨骂,被老白姓恨得牙根痒痒的,那多没意思呀!你爷爷奶奶、父母家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们高兴你这样做吗?我想,他们多半还不知道你做的事吧?他们要是知道你在做这些事,那脸可就没处搁了,人还不得羞愧死呀?小伙子呀,你以为日本鬼子长久得了吗?实话告诉你吧,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久不了的!我听街上好些人都在议论,说日本鬼子是丧家犬,快完蛋了。他们在中国老打败仗,在全世界各地也都不得人心。小伙子呀,我劝你放聪明点,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千万别再一个心思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头子当枪使啦,那样会不得好死的!”
耀大娭毑本来不想说这么多的,但她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收不住了。高个子卫兵骂她是“老东西”,扬言要枪毙她,还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胸膛,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刺激太大了。她活到现在,都六十好几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实在是忍无可忍。然而,她话虽说得多,语气也很硬,但却句句在理。那高个子卫兵大概良心还没有完全让狗吃掉,听了她的话,也似乎觉得自己有些理亏,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手里端着枪不知所措,扭扭捏捏的,老大不自在。
耀大娭毑的算计没错,她有意识地把动作搞大了,就真把门里头那个跨盒子枪的引出来了。只见那人背着双手,踱着方步慢慢地走出大门,对着高个子卫兵说道:“孙长子,把枪收起,让老人家进来!”
对个子高大的男人,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一般都叫做“大个子”或“大高个”,而长沙、湘北等地的湖南人有些特别,他们一般不叫“大个子”或“大高个”,而是叫做“长子”。那个高个子卫兵姓孙,个头长得很高大,所以“孙长子”便成了他的外号了。孙长子见腰挎盒子枪的人向自己打招呼,连忙收起枪,转身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随即一声大喊道:“是,孙副官!”耀大娭毑见机快,见高个子卫兵让开了路,便连忙抬起脚迈进院门。她原以为那姓孙的副官会要对她狠狠训斥和严格盘查的,然而那姓孙的副官却并没有这样做。他只简单地问了问耀大娭毑的来意,便面无表情地领着她往院子中间走。
走到第四间屋子门首,姓孙的副官停了下来。他朝左右看了看,掏出钥匙打开屋门,指着屋里头,小声对耀大娭毑说:“老人家,你进去吧,梁家两口子就在屋里。说话抓紧点,别待时间太长了!”
屋角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豆粒大小的灯火有气无力地向周围播撒着昏黄暗淡的光线,愈显得整个房间的气氛凄苦惨烈,了无生气。耀大娭毑费了好大的劲才看清,水玉她爸躺在靠墙的地上,水玉她妈盘腿坐在他的身边。
“你、你们两个吃苦了!”耀大娭毑一阵哽咽,三脚两步地走上前,紧紧握住了水玉她妈伸过来的手。
水玉她妈没有说话,只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着,豆大的泪珠一滴接一滴地滴落在耀大娭毑的手背上。
水玉她爸直溜溜地躺着,手、脚、身子没有丝毫动静,只有嘴巴里还在不时地吐出痛苦的呻吟声。耀大娭毑一见那样子,便鼻子发酸,直想哭出声来。她强忍眼泪,看着水玉她妈问道:“狗娘养的汉奸狗腿子对老梁动刑啦?”
水玉她妈还是没有说话,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打得真够重的呀,狗娘养的王八蛋!”耀大娭毑一边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水玉她爸,一边咬着牙根说,那声音虽低沉,却满含着怒气。
“可、可不是嘛,都、都、都快让他们打死了!”水玉她妈终于开口了,话声里满是悲凄的哭音。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带包子来了,就在东头街口那家店里买的,还热着呢。来、来、来,趁热吃一口吧。你吃你的,老梁我来喂。这时候最要紧的呀,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什么事都比不上吃饭重要。吃了饭,身上有劲,好跟他们斗。要是不吃东西,饿坏了自己,可就更趁了那帮王八羔子汉奸卖国贼的意啦,明白吗?”耀大娭毑把手里的荷叶包放在地上,解开荷叶,从中拿出一个包子递到水玉她妈手里。
水玉她妈接过包子,却没往嘴里塞。她看了看包子,轻声说:“多谢你老人家的心意了,但我这会儿哪吃得下呀!不瞒你老人家说,我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得、得、得,快别说那不硬气的话了。这时候,哪能那么想呢!水玉她爸伤那么重,还得你来照顾呢,对不?水玉也还在外头盼着你回去呢,是不?关几天就会放出去的,哪至于严重到要自杀的份儿呢!你呀,这么点事就经不起,要自杀,那天底下的人还不都得死绝了?”耀大娭毑急急地说。
水玉她妈忽然不哭了,一本正经地说:“老人家,我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姓孙的那汉奸二鬼子如今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要把我们家水玉弄到手不可。为了逼我们家水玉现身露面,他不仅把我们两口子抓进了监狱,而且还给我们安了一个杀头的罪名,说我们私通游击队,窝藏游击队,家里有武器,有弹药什么的。你老人家想想,我们两口子能让他痛痛快快得到水玉吗?他要是得不到我们家水玉,那我们两口子还有活路可走吗?你瞧瞧他那心肠多狠毒呀,愣把我们家老梁往死里打,打成了内脏里出血的重伤,连肋骨都打折了三根。看这样子,我们家老梁是活不成了,最多也就是三两天的事。我们家老梁要是走了,我、我活着还、还有什么意思呀!”
“哎哟,他们打那么重呀?肋骨都折了!这帮子混蛋王八蛋,”耀大娭毑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我请个郎中来看看吧?”
水玉她妈连连摇头,带着哭音说:“你老人家千万别费那事了,花钱不说,他们也不会让郎中进门的。再说,郎中来了也没用,老梁这伤实在太重了,根本就没法治了。下午,他们也派来了一个郎中,但那郎中看了看,却只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叹气,连个方子都没开就一甩手走了。对老梁呀,别抱什么希望了,还是照管水玉要紧。你老人家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老人家托付水玉的事情呐!”
“咳呀,瞧你说的,水玉也是我的亲孙女呀,对不?照看她那不也是我自己的份内事嘛,哪用得着‘托付’两个字啊!这事你尽管放心,有老身在,水玉准能找得到的。这几天,我带着济木再抓紧时间找找就是了,无论如何也得把她找到!”耀大娭毑说。
水玉她妈又摇了摇头,盯着耀大娭毑说:“这会儿找不找得到水玉倒不要紧了,关键是要赶紧通知她,让她千万别回家,千万别到这牢房里来看我们!明摆着,孙棒子现在用的,是引鱼上钩的计谋。他把我们关进牢里,就是要用我们来引水玉上钩的。所以呀,我现在最着急的,倒不是找水玉,而是要想办法把眼前的情势告诉水玉,让她明白面前的危险,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高飞!”
水玉她妈的话说到了要害处,耀大娭毑听了,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是呀,眼前的情势真的是太危险了。孙棒子把水玉他爸妈抓起来,关进牢里,用的就是引鱼上钩的计。倘若水玉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地跑回了家,或者冒冒失失地到牢里来探望她父母,那不是正好中了孙棒子的阴谋诡计吗?他们可以就势抓住水玉,以她父母的性命和自由相威胁,逼她就范呀!不行,这情况太紧急了,得赶快想个办法通知水玉,让她火速逃走。但、但现在根本就搞不清楚水玉在哪里,想个什么法子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目前的情况通知到她,让她明白身边的危险和家里人的想法呢?”想到这里,耀大娭毑不禁双眉紧蹙,陷入了沉思。
耀大娭毑正在沉思,门口人影一闪,孙副官忽然进来了。他一进门,便急急地低声招呼耀大娭毑快走,说是门卫要换岗了,再不走,就会被新来的岗哨发觉。耀大娭毑晓得这事的利害关系,连忙简单嘱咐了水玉她妈几句,起身就走。一出牢门,她就朝东走,想从进来时的那个门出去,这时孙副官拽住了她。
“不能走那边,”孙副官低声说,“来,大娘,跟我来!”
孙副官拽着耀大娭毑的衣袖一路小跑,从牢房前面的一个小门出去,进了灵官寺的后院,再从灵官寺的后院一直往左走,然后再往右一拐,没走几步路便到了一个圆洞门。出了那圆洞门,孙副官不走了。他用手一指前边说:“前面十字路口往左拐,就是你老人家来时的那条小巷子。大娘,你快走吧!”
孙副官不仅没有刁难,反倒温言细语,处处关照,这令耀大娭毑感到意外。她扫了一眼孙副官,和颜悦色地说:“没想到,你倒是个好人,跟门口那个卫兵大不一样。好,小伙子,多行行善吧,会有好报的!”
“好人?这世道无路可走,好人都快逼成坏人了。你老人家高看我,我很高兴,”孙副官轻声说,“你老人家说得对,为人在世是应该多行善,做好事。好人做不成,我就多做做好事吧。不过,门口那个卫兵本质也不坏,心肠挺善的,只是年纪太轻,还不太懂事罢了。你老人家放心,我会多说说他的。”
“噢,那也许是我错看他了。不要紧,我不记恨他。你姓孙,他也姓孙,你们俩是不是一家子呀?”耀大娭毑问。
“我们营长也姓孙,外号叫做孙棒子。不过,跟你老人家说实话,”孙副官朝前后左右瞧了瞧,说话声压得特别低,“我们三个都姓孙,都是一个族里的,有点沾亲带故,但不是一家子,更不是一个心眼。孙棒子是无恶不作,我和那个卫兵却是迫不得已才当伪军的。我们家欠了孙棒子一大笔债,三辈子都还不清,家里又有妻儿老小,一家人都指着我挣钱吃饭,不出来挣点钱,这日子怎么过呀?孙长子,也就是那个卫兵,他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只怕比我还要苦些。你老人家可千万莫把我们三个人一起看啊!”
“你是个好人,孙棒子是无可救药的坏人,你们不是一路的,这我晓得。但你长期和他混在一起,终归也不是个事啊,对不?日本鬼子长不了啦,孙棒子也长不了啦,你得赶紧另谋生路啊!”耀大娭毑说。
“是呀,你老人家说得对,鬼子的日子不多了,伪军的差当不得了,我得赶紧离开他们,另谋生路。谢谢你老人家的好意提醒!时候不早了,这地方有危险,久留不得,你老人家赶快走吧!”孙副官悄声说。说完,他又小心翼翼地朝前后左右看了看。
离开灵官寺,耀大娭毑就直奔梁家后面的那个大空场子。还没到大空场子,她就远远地看见大樟树的底下坐着自己的孙子姜济木。
辛辛苦苦地跑了一整天,姜济木一点收获都没有。直到天快黑了,他才不得不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梁家。但他还没到梁家门首便发现了意外:门外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屋里也没有点灯,却有人在低声说话。那话音粗声粗气,很野蛮,不是梁家人说的,却像兵痞子的口吻。他心知情况有异,怕出危险,便连忙一侧身,迅疾地转了个弯,钻进旁边的小过道,一路小跑溜到大空场子来了。
一见奶奶的面,姜济木便问有弟弟姜济勋的消息没有。耀大娭毑没有回答孙子的提问,却冷着脸反问道:“喂,你晓得你们米行张老板住在哪里吗?”
姜济木愣了一下,说:“哟,你老人家怎么打听这个呀?要找张老板吗?找他干什么?济勋不会去他那里的!”
耀大娭毑急了,眼睛珠子一瞪,大声吼道:“哎呀,你就快说吧,到底晓不晓得你们张老板的住处呀?”
“张老板的住处,我当然晓得喽,”姜济木伸手挠挠后脑勺,“他有两个住处呢,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区。你老人家问的是哪一个?”
“那他现在是住在哪里?城里,还是郊区?”
“郊区!”
“郊区?郊区哪里呀?那地方,你晓得吗?”
“晓得呀,就在城郊捞刀河附近,我还去过那里呢。奶奶,你打听我们张老板的住处干什么呀,莫非济勋去他家啦?”姜济木一脸好奇的神气。
“走,你快带我去见张老板,我有件天大的事要和他商量!其他事,咱们路上再说吧!”耀大娭毑说完,拔腿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