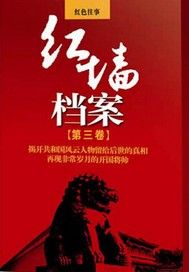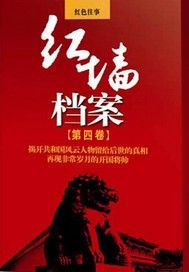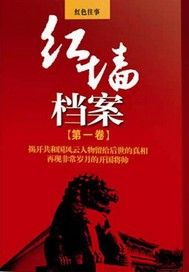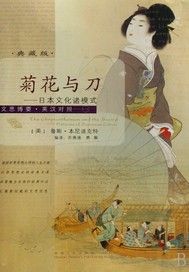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三十节 司徒雷登
如果说真有一位美国人,他既爱美国又爱中国的话,那么,就不能不推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许有些人不会相信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引用燕大校友张绍强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开场白: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爱国向不后人,立即宣布罢课,南下请愿。因而引起校内外国教授们的激烈反对。中国教授初持中立态度,继司徒雷登也有人出头站在学生一边。校内闹得不可开交,南下请愿团照旧南下,留在校内的学生也仍坚持和那些外国教授对立,不准任何人开课。
出现这些情况,学校当局连电在美国募捐的司徒校务长,促他早日返华解决学潮。司徒返校之日,也是南下请愿团北上返校之时。当司徒到校之后,立即召开大会,全校学生和中外教授,齐集本校大礼堂,听司徒讲话。外国教授总以为司徒必然站在他们一边;学生也以为司徒毕竟是一位外国人,不会赞成罢课的。可是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司徒此时站在讲台上,默不作声约二三分钟之久,才开口讲话。他说道:“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说这话时,他脚尖一再踮起,态度真诚,声调恳切,眼中潮润着,泪水似乎就要掉下来。大家听后,无论中外教授和学生,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满天乌云一风而散,次日学生照常上课,学生与教授之间,平静无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中国的杭州,他父亲是常驻杭州的传教士。11岁那年,司徒被送回美国,寄养于姨妈家中,并在美国念书,直至大学毕业。
司徒念了好几个大学,最后在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学校要他作出对未来事业的决定,他那时并不喜欢中国,他曾自白说:“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到钟楼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钟声,直至翌日清晨5点才慢慢入睡,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厌恶到中国去当传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里并非是我所想象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老百姓当猴戏一样地对待,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过一种遁世隐居者的生活。我童年时代就看到爸爸所过的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更使我体会到这种生活之枯燥无味。相反的,我若留在弗吉尼亚,有朋友,有欢乐,真是天上与地下之比。”他进一步说:“我天生就不喜欢传教士,然而人们在当时都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耶稣信徒,他就应到国外去做一个传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应召。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他觉得个人的一切应当听从上帝的安排,因此终于愉快地走了传教士的道路,而且正是到他所本来不喜欢的落后的中国去。
他在神学院时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名叫莫菲特,他们两人都同时被指定去中国。他们决定在出发以前成亲,以便双双对对地去中国,但当时他们连女朋友也没有,怎么能结婚呢?青年人有一股傻劲,他们俩发誓,既然已情如手足,那么,他们也应当去与一对姐妹结婚。司徒雷登说:“我在新奥尔良有一家远房亲戚,他家有4个女儿,我们去那儿每人挑一个。”莫菲特大喜,欣然同意。1904年11月,他俩到了新奥尔良,那四姐妹果真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女儿一样,对他们欢迎备至。但谁挑谁呢?司徒雷登心中暗选了两位,他想:“我一定要让莫菲特先挑,因为我绝不能挑走莫菲特所属意的姑娘。万一莫菲特挑走了我属意的姑娘,我还可有一后备的。”但莫菲特也是一名君子,他一定要司徒雷登先挑,两人争执不下,只好由上帝决定,以硬币一枚来决定先后。结果,莫菲特先挑,他挑上了二妹凯特。正好,司徒属意的是大姐艾琳,没有冲突,而是各得其所。
11月17日,两对小夫妻就在新奥尔良举行了婚礼,双双启程赴中国。司徒雷登被留在杭州传教,莫菲特则被派往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们两人又是各得其所。
司徒雷登与艾琳谈恋爱的日子虽然很短,甚至可以说简直没有谈恋爱的阶段,但婚后的生活却十分美满。据司徒雷登说,他的结婚有点像中国式的结婚,是命中注定的。不同的是,在中国是由父母之命决定,而他的婚姻是由上帝决定的。
1907年,司徒雷登帮助长老会在杭州兴办了“育英学院”。该校成为“之江大学”的前身。翌年,他受聘执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他怀着强烈的兴趣,钻研宗教经文、历史和哲学,并且出版了《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和《希—英—汉字典》。
其时,北京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有意联袂,且已在城东南的一处逼仄之地凑成临时校舍,挂出一块“北京大学”的牌子。据当时的教工回忆,学校经费拮据,人员短缺,“教职员连打字姑娘都算在内,只有二十三人”,学生不足一百人,图书仅数万册,“图书馆则斗室二间,实验室则一楼一底二间,生理化均在其中了”。由于人事、机构名称争执不下,该校校务陷入僵局。1918年12月,“北京大学”董事会决定聘请司徒雷登为该校校长。
“我接受的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司徒雷登事后回忆说。
司徒雷登广征时贤之见。因国立北京大学这时已负盛名,这所教会学校已不宜再用“北京大学”为校名。最后,它采用了“燕京大学”的校名。这是1919年。这意味着燕京大学的正式诞生。接着,他又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设立女部。燕大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授课的大学之一。
1922年至1936年,司徒雷登连续10次赴美募捐,给燕大开辟了广阔的财源。
1921年,司徒雷登靠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的四郊,勘察新校址。他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北京西郊海淀的一块地皮。
他在自传中说:
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
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任何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不幸,正当燕大位居海淀的校舍落成之际,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了。他在自传中记道:“她生孩子时身体受了损害,一直未康复,是个半残废。她最关心的是不要让她那虚弱多病的身体影响我的工作,她与我的母亲和睦相处,互为补充,相依为命,生活得犹如一个人一样。6月6日,正当燕大搬入新校舍之际,她去世了。灵柩下葬在新校园附近的新燕大公墓里,她的坟墓是公墓中的第一座。”
司徒雷登再也没有续弦。他说,他与艾琳恩爱弥笃,如胶似漆。他绝对不能再同另外一个女子生活在一起,想到与艾琳的亲密无间的情谊而再去想与另外的女人发生感情,那是不可思议的,这将是对他的灵魂的一种侮辱。从此,司徒雷登一直过独身生活,直至去世。他说:“燕大成了我的大家庭,学生们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而我也确实对他们有父辈之情。”
史静寰博士谈司徒雷登时说:“燕大在3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燕大与其他大学相比,有着比较宽松的内部环境和活跃的政治气氛。燕大的图书馆内藏有不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公开向学生出借,有些还被指定为教学参考书。这种学习为今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基础。黄华、杨刚、龚普生等都曾谈到这一点。学生在校内刊物上发表攻击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苏区情况的文章并不犯忌。甚至学生可以公开批评美国的侵略政策。1935年年底为司徒祝寿时,学生们说:‘司徒先生虽然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他所企慕的是全人类的博爱和和平,要使司徒先生能得更大的快乐,我们只有拼着牺牲我们的头颅与热血去为祖国奋斗。’”
司徒雷登北上就任燕大校长之时,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一运动所介绍的新思想和采取的新文体(白话文)使中国文字宣传工作发生重大改变。这一运动所引起的全民族特别是知识界对宣传媒介的重视,更使报纸杂志的出版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司徒雷登从这种形势中看到了中国对新闻、出版等有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及燕大作为教会学校所可能进行的工作。他上任后不久即向托事部建议,组建燕大新闻系,但这一建议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后托事部虽然授权司徒雷登在燕大增设新闻系,但明确告诉他,托事部没有为新闻系提供经费的义务。这种“无米之炊”的局面并未使司徒雷登放弃自己的主张。1924年,燕大正式开始创办新闻专业的尝试。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后代白瑞华(R。S。Britton)和另一美国人聂士芬(Vernon Nash)合作进行这一工作。他们在燕大开设了最早的新闻学课。这时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也不过刚刚存在15年。但是不久,白瑞华因身体原因回国治病。1927年,聂士芬也回美国深造,并为新闻系的正式建立进行筹款工作。1927—1929年,尚未成型的新闻系被迫中止其工作。聂士芬在美国的筹款工作进行得相当活跃。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兼教育家、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和院长惠廉士(W。Williams)曾于20年代初来中国访问,对在中国建立新闻教育基地的主张最为赞同。他亲自出任为燕大新闻系筹款的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影响下密苏里大学新闻界人士踊跃捐款,很快就筹到6.5万美元。除此之外,他还促成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燕大新闻系结成姐妹学校。由密苏里大学帮助燕大新闻系创建工作。两校订立交换教授与学生的协议。1929年,聂士芬回到燕大,燕大新闻系的各项工作得以恢复。由于经费及师资有限,新闻系不以培养非常专业化的新闻工作人员为目标,而是偏重于使学生接受广泛的知识和有关报业的基本原理及技术训练。因此,新闻系学生一般都从其他系选修3/4的课程,只有1/4的新闻专业课。新闻系的教学很注意实践。30年代,新闻系学生曾出版了自己的实习报纸:《燕京新闻》。日军占领北平时,很多杂志报纸被迫停刊。燕大利用自己的美国国旗得以继续维持。燕大新闻系出版的《平西报》曾在一个时期内是北平唯一的一张西文报纸。
新闻系开办以后成为燕大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根据1932—1933年度的调查,新建的新闻系已有学生52名,超过政治学系(51名)。在全校各专业学生人数上名列第四。到30年代末,新闻系已成为全校学生最多的大系。1930年,新闻系只有一名毕业生,1935年的毕业生数是15名。到40年代,全国各大报几乎都有燕大的毕业生。由于较高的英文水平,燕大毕业生在国际新闻工作中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
燕大很快成了一所有名望的教会大学,其学术上的成就得到社会承认。早在20年代末,美国加州大学在以毕业生升入美国院校的成绩为标准所进行的远东各大学质量调查中就将燕大列为甲级。以后燕大也一直是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响的教会学校之一。燕大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中,培养六七千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特别是在教育、新闻、外交、政治等领域,燕大学生更占有特殊地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地处北平的国立大学相继迁往大后方。鉴于当时美国是中立国,日军不会轻易地干预美国的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决定留在原地办学,为日占区的青年提供求学机会。在这期间,司徒雷登千方百计保护从事抗日活动的学生。他多次借口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日军及新民会进入校园内搜捕抗日分子和共产党人。1939年元旦,燕大学生试图刺杀汉奸周作人,可是行动失败。司徒雷登不久就发现了参与刺杀行动的学生,在他的保护下,日伪当局始终未能抓捕到他们。
燕大有些进步学生和教师想离开学校投身抗日斗争,司徒雷登总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帮助。司徒雷登曾明确指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其离开沦陷区,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要给予支持。无论是去国统区,还是去解放区,都要给予帮助。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送行。在一次欢送会上,他说他希望燕大学生,不论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在这几年时间里,不少学生就是在司徒雷登的协助下,去了重庆、昆明,或是翻越西山,到了解放区。
在燕大数学系任教的英籍教师赖朴吾(E。Ralph Lapwood)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于1939年夏离开燕大,与路易·艾黎一起经过解放区到达四川,从事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前线为目的的“工业合作协会”工作。这件事在燕大影响很大,有些学生就想到那里工作。于是,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去见司徒雷登,请他想想办法。司徒雷登主动提出应该资助学生南下,并且建议学生先去上海,然后由在上海男女青年会工作的燕大校友帮助他们转往内地。有十多个男女同学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走的。
对于教职员工的反日行动或想去抗日根据地访问,司徒雷登也给予帮助。英籍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先生秘密地为华北共产党游击队提供通信器材和医疗设备,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司徒雷登曾多次把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借给他使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迈可夫妇也是乘坐司徒雷登的小汽车,取道西山前往解放区的。作为无线电专家,林迈可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工作了八九年,与抗日军民同甘共苦,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英国。
1936年6月,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只身独闯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之前,曾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秘密长谈。虽说没有人知道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他们的谈话与斯诺的陕北之行有关,而且斯诺此行是得到司徒雷登校长支持的。斯诺从陕北回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司徒雷登的住宅临湖轩多次为燕大和清华的教师及学生代表放映他摄制的反映苏区情况的影片和幻灯片。燕京大学的校刊《燕京周刊》首先连续发表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一书,于1937年10月在美国出版。该书第一次客观、公正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在斯诺陕北之行的影响下,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萌发了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想法,并于1937年两次组织考察团,沿斯诺走过的道路访问延安。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寇封闭了燕京大学,并囚禁了司徒。一直到日本投降,司徒才获得自由,并立即进行燕京复校工作。但1946年7月4日,马歇尔将军请司徒前往南京美国驻华使馆出席美国独立纪念活动,并当面请其出任驻华大使。于是,他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名政治明星。
司徒雷登曾多次见过蒋介石,他们是“主内朋友”,很谈得拢。司徒在1946年也在重庆见过毛泽东,当时他曾夸耀他有不少学生在延安为共产党效劳。但司徒与蒋、毛的个人友谊并不能帮助国共谈判。国共谈判是注定要失败的,谁也没有能力回天。所以,像马歇尔一样,司徒最后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
其时有一个细节。当1949年年初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在国民党要求下,各国驻华使馆纷纷迁往广州,只有美国使馆没有搬走。傅泾波曾劝司徒以个人名义去北京与共产党摸底,看看是否还有迂回余地。司徒虽有此心,但他囿于外交纪律,终于不敢采取行动。
同年8月,司徒奉国务院召回之令,从南京回美。回美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2007年7月,《环球时报》记者王君如访问了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并作了以下报道:
司徒雷登1949年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三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待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到,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交往缘于傅的父亲。傅泾波的父亲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认识了司徒雷登,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曾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谋过差事,但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干了半年多就辞职了。随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傅泾波夫妇膝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们对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顺。大女儿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她自己则贷了20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点内疚,因为他当时正去艾奥瓦州看望三女儿傅海澜了。他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在司徒雷登身边,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孙中山,好像还认识孙中山。在他的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2008年11月17日,在习近平的协助下,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将军,终于得以带着司徒雷登的骨灰把它埋葬在杭州的安贤园,实现了司徒归葬中国的宿梦。
萧淑熙叶道纯整理
2001年12月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爱国向不后人,立即宣布罢课,南下请愿。因而引起校内外国教授们的激烈反对。中国教授初持中立态度,继司徒雷登也有人出头站在学生一边。校内闹得不可开交,南下请愿团照旧南下,留在校内的学生也仍坚持和那些外国教授对立,不准任何人开课。
出现这些情况,学校当局连电在美国募捐的司徒校务长,促他早日返华解决学潮。司徒返校之日,也是南下请愿团北上返校之时。当司徒到校之后,立即召开大会,全校学生和中外教授,齐集本校大礼堂,听司徒讲话。外国教授总以为司徒必然站在他们一边;学生也以为司徒毕竟是一位外国人,不会赞成罢课的。可是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司徒此时站在讲台上,默不作声约二三分钟之久,才开口讲话。他说道:“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说这话时,他脚尖一再踮起,态度真诚,声调恳切,眼中潮润着,泪水似乎就要掉下来。大家听后,无论中外教授和学生,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满天乌云一风而散,次日学生照常上课,学生与教授之间,平静无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中国的杭州,他父亲是常驻杭州的传教士。11岁那年,司徒被送回美国,寄养于姨妈家中,并在美国念书,直至大学毕业。
司徒念了好几个大学,最后在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学校要他作出对未来事业的决定,他那时并不喜欢中国,他曾自白说:“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到钟楼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钟声,直至翌日清晨5点才慢慢入睡,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厌恶到中国去当传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里并非是我所想象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老百姓当猴戏一样地对待,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过一种遁世隐居者的生活。我童年时代就看到爸爸所过的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更使我体会到这种生活之枯燥无味。相反的,我若留在弗吉尼亚,有朋友,有欢乐,真是天上与地下之比。”他进一步说:“我天生就不喜欢传教士,然而人们在当时都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耶稣信徒,他就应到国外去做一个传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应召。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他觉得个人的一切应当听从上帝的安排,因此终于愉快地走了传教士的道路,而且正是到他所本来不喜欢的落后的中国去。
他在神学院时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名叫莫菲特,他们两人都同时被指定去中国。他们决定在出发以前成亲,以便双双对对地去中国,但当时他们连女朋友也没有,怎么能结婚呢?青年人有一股傻劲,他们俩发誓,既然已情如手足,那么,他们也应当去与一对姐妹结婚。司徒雷登说:“我在新奥尔良有一家远房亲戚,他家有4个女儿,我们去那儿每人挑一个。”莫菲特大喜,欣然同意。1904年11月,他俩到了新奥尔良,那四姐妹果真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女儿一样,对他们欢迎备至。但谁挑谁呢?司徒雷登心中暗选了两位,他想:“我一定要让莫菲特先挑,因为我绝不能挑走莫菲特所属意的姑娘。万一莫菲特挑走了我属意的姑娘,我还可有一后备的。”但莫菲特也是一名君子,他一定要司徒雷登先挑,两人争执不下,只好由上帝决定,以硬币一枚来决定先后。结果,莫菲特先挑,他挑上了二妹凯特。正好,司徒属意的是大姐艾琳,没有冲突,而是各得其所。
11月17日,两对小夫妻就在新奥尔良举行了婚礼,双双启程赴中国。司徒雷登被留在杭州传教,莫菲特则被派往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们两人又是各得其所。
司徒雷登与艾琳谈恋爱的日子虽然很短,甚至可以说简直没有谈恋爱的阶段,但婚后的生活却十分美满。据司徒雷登说,他的结婚有点像中国式的结婚,是命中注定的。不同的是,在中国是由父母之命决定,而他的婚姻是由上帝决定的。
1907年,司徒雷登帮助长老会在杭州兴办了“育英学院”。该校成为“之江大学”的前身。翌年,他受聘执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他怀着强烈的兴趣,钻研宗教经文、历史和哲学,并且出版了《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和《希—英—汉字典》。
其时,北京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有意联袂,且已在城东南的一处逼仄之地凑成临时校舍,挂出一块“北京大学”的牌子。据当时的教工回忆,学校经费拮据,人员短缺,“教职员连打字姑娘都算在内,只有二十三人”,学生不足一百人,图书仅数万册,“图书馆则斗室二间,实验室则一楼一底二间,生理化均在其中了”。由于人事、机构名称争执不下,该校校务陷入僵局。1918年12月,“北京大学”董事会决定聘请司徒雷登为该校校长。
“我接受的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司徒雷登事后回忆说。
司徒雷登广征时贤之见。因国立北京大学这时已负盛名,这所教会学校已不宜再用“北京大学”为校名。最后,它采用了“燕京大学”的校名。这是1919年。这意味着燕京大学的正式诞生。接着,他又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设立女部。燕大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授课的大学之一。
1922年至1936年,司徒雷登连续10次赴美募捐,给燕大开辟了广阔的财源。
1921年,司徒雷登靠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的四郊,勘察新校址。他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北京西郊海淀的一块地皮。
他在自传中说:
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
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任何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不幸,正当燕大位居海淀的校舍落成之际,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了。他在自传中记道:“她生孩子时身体受了损害,一直未康复,是个半残废。她最关心的是不要让她那虚弱多病的身体影响我的工作,她与我的母亲和睦相处,互为补充,相依为命,生活得犹如一个人一样。6月6日,正当燕大搬入新校舍之际,她去世了。灵柩下葬在新校园附近的新燕大公墓里,她的坟墓是公墓中的第一座。”
司徒雷登再也没有续弦。他说,他与艾琳恩爱弥笃,如胶似漆。他绝对不能再同另外一个女子生活在一起,想到与艾琳的亲密无间的情谊而再去想与另外的女人发生感情,那是不可思议的,这将是对他的灵魂的一种侮辱。从此,司徒雷登一直过独身生活,直至去世。他说:“燕大成了我的大家庭,学生们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而我也确实对他们有父辈之情。”
史静寰博士谈司徒雷登时说:“燕大在3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燕大与其他大学相比,有着比较宽松的内部环境和活跃的政治气氛。燕大的图书馆内藏有不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公开向学生出借,有些还被指定为教学参考书。这种学习为今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基础。黄华、杨刚、龚普生等都曾谈到这一点。学生在校内刊物上发表攻击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苏区情况的文章并不犯忌。甚至学生可以公开批评美国的侵略政策。1935年年底为司徒祝寿时,学生们说:‘司徒先生虽然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他所企慕的是全人类的博爱和和平,要使司徒先生能得更大的快乐,我们只有拼着牺牲我们的头颅与热血去为祖国奋斗。’”
司徒雷登北上就任燕大校长之时,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一运动所介绍的新思想和采取的新文体(白话文)使中国文字宣传工作发生重大改变。这一运动所引起的全民族特别是知识界对宣传媒介的重视,更使报纸杂志的出版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司徒雷登从这种形势中看到了中国对新闻、出版等有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及燕大作为教会学校所可能进行的工作。他上任后不久即向托事部建议,组建燕大新闻系,但这一建议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后托事部虽然授权司徒雷登在燕大增设新闻系,但明确告诉他,托事部没有为新闻系提供经费的义务。这种“无米之炊”的局面并未使司徒雷登放弃自己的主张。1924年,燕大正式开始创办新闻专业的尝试。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后代白瑞华(R。S。Britton)和另一美国人聂士芬(Vernon Nash)合作进行这一工作。他们在燕大开设了最早的新闻学课。这时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也不过刚刚存在15年。但是不久,白瑞华因身体原因回国治病。1927年,聂士芬也回美国深造,并为新闻系的正式建立进行筹款工作。1927—1929年,尚未成型的新闻系被迫中止其工作。聂士芬在美国的筹款工作进行得相当活跃。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兼教育家、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和院长惠廉士(W。Williams)曾于20年代初来中国访问,对在中国建立新闻教育基地的主张最为赞同。他亲自出任为燕大新闻系筹款的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影响下密苏里大学新闻界人士踊跃捐款,很快就筹到6.5万美元。除此之外,他还促成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燕大新闻系结成姐妹学校。由密苏里大学帮助燕大新闻系创建工作。两校订立交换教授与学生的协议。1929年,聂士芬回到燕大,燕大新闻系的各项工作得以恢复。由于经费及师资有限,新闻系不以培养非常专业化的新闻工作人员为目标,而是偏重于使学生接受广泛的知识和有关报业的基本原理及技术训练。因此,新闻系学生一般都从其他系选修3/4的课程,只有1/4的新闻专业课。新闻系的教学很注意实践。30年代,新闻系学生曾出版了自己的实习报纸:《燕京新闻》。日军占领北平时,很多杂志报纸被迫停刊。燕大利用自己的美国国旗得以继续维持。燕大新闻系出版的《平西报》曾在一个时期内是北平唯一的一张西文报纸。
新闻系开办以后成为燕大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根据1932—1933年度的调查,新建的新闻系已有学生52名,超过政治学系(51名)。在全校各专业学生人数上名列第四。到30年代末,新闻系已成为全校学生最多的大系。1930年,新闻系只有一名毕业生,1935年的毕业生数是15名。到40年代,全国各大报几乎都有燕大的毕业生。由于较高的英文水平,燕大毕业生在国际新闻工作中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
燕大很快成了一所有名望的教会大学,其学术上的成就得到社会承认。早在20年代末,美国加州大学在以毕业生升入美国院校的成绩为标准所进行的远东各大学质量调查中就将燕大列为甲级。以后燕大也一直是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响的教会学校之一。燕大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中,培养六七千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特别是在教育、新闻、外交、政治等领域,燕大学生更占有特殊地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地处北平的国立大学相继迁往大后方。鉴于当时美国是中立国,日军不会轻易地干预美国的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决定留在原地办学,为日占区的青年提供求学机会。在这期间,司徒雷登千方百计保护从事抗日活动的学生。他多次借口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日军及新民会进入校园内搜捕抗日分子和共产党人。1939年元旦,燕大学生试图刺杀汉奸周作人,可是行动失败。司徒雷登不久就发现了参与刺杀行动的学生,在他的保护下,日伪当局始终未能抓捕到他们。
燕大有些进步学生和教师想离开学校投身抗日斗争,司徒雷登总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帮助。司徒雷登曾明确指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其离开沦陷区,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要给予支持。无论是去国统区,还是去解放区,都要给予帮助。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送行。在一次欢送会上,他说他希望燕大学生,不论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在这几年时间里,不少学生就是在司徒雷登的协助下,去了重庆、昆明,或是翻越西山,到了解放区。
在燕大数学系任教的英籍教师赖朴吾(E。Ralph Lapwood)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于1939年夏离开燕大,与路易·艾黎一起经过解放区到达四川,从事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前线为目的的“工业合作协会”工作。这件事在燕大影响很大,有些学生就想到那里工作。于是,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去见司徒雷登,请他想想办法。司徒雷登主动提出应该资助学生南下,并且建议学生先去上海,然后由在上海男女青年会工作的燕大校友帮助他们转往内地。有十多个男女同学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走的。
对于教职员工的反日行动或想去抗日根据地访问,司徒雷登也给予帮助。英籍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先生秘密地为华北共产党游击队提供通信器材和医疗设备,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司徒雷登曾多次把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借给他使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迈可夫妇也是乘坐司徒雷登的小汽车,取道西山前往解放区的。作为无线电专家,林迈可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工作了八九年,与抗日军民同甘共苦,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英国。
1936年6月,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只身独闯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之前,曾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秘密长谈。虽说没有人知道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他们的谈话与斯诺的陕北之行有关,而且斯诺此行是得到司徒雷登校长支持的。斯诺从陕北回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司徒雷登的住宅临湖轩多次为燕大和清华的教师及学生代表放映他摄制的反映苏区情况的影片和幻灯片。燕京大学的校刊《燕京周刊》首先连续发表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一书,于1937年10月在美国出版。该书第一次客观、公正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在斯诺陕北之行的影响下,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萌发了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想法,并于1937年两次组织考察团,沿斯诺走过的道路访问延安。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寇封闭了燕京大学,并囚禁了司徒。一直到日本投降,司徒才获得自由,并立即进行燕京复校工作。但1946年7月4日,马歇尔将军请司徒前往南京美国驻华使馆出席美国独立纪念活动,并当面请其出任驻华大使。于是,他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名政治明星。
司徒雷登曾多次见过蒋介石,他们是“主内朋友”,很谈得拢。司徒在1946年也在重庆见过毛泽东,当时他曾夸耀他有不少学生在延安为共产党效劳。但司徒与蒋、毛的个人友谊并不能帮助国共谈判。国共谈判是注定要失败的,谁也没有能力回天。所以,像马歇尔一样,司徒最后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
其时有一个细节。当1949年年初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在国民党要求下,各国驻华使馆纷纷迁往广州,只有美国使馆没有搬走。傅泾波曾劝司徒以个人名义去北京与共产党摸底,看看是否还有迂回余地。司徒虽有此心,但他囿于外交纪律,终于不敢采取行动。
同年8月,司徒奉国务院召回之令,从南京回美。回美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2007年7月,《环球时报》记者王君如访问了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并作了以下报道:
司徒雷登1949年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三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待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到,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交往缘于傅的父亲。傅泾波的父亲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认识了司徒雷登,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曾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谋过差事,但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干了半年多就辞职了。随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傅泾波夫妇膝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们对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顺。大女儿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她自己则贷了20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点内疚,因为他当时正去艾奥瓦州看望三女儿傅海澜了。他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在司徒雷登身边,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孙中山,好像还认识孙中山。在他的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2008年11月17日,在习近平的协助下,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将军,终于得以带着司徒雷登的骨灰把它埋葬在杭州的安贤园,实现了司徒归葬中国的宿梦。
萧淑熙叶道纯整理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