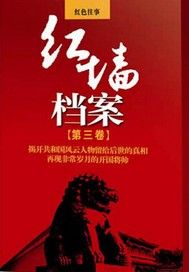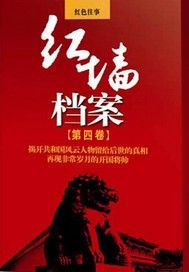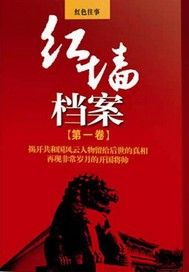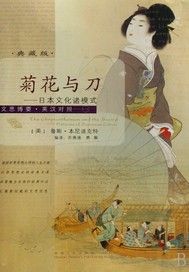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一节 比较宗教学研究
如果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铸就汤氏文化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并从整体上强化了他向传统折返的选择意识,那么汤氏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便是耸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央大厦,在具体研究领域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展示传统文化因革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汤用彤以汉唐佛教史为研究中心的学术道路,立意于斯,起步也于斯。
印度佛法东渐,于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儒、道乃至民间习俗交汇、拒斥和互相渗透中,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损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它虽从未占据统治地位,但京都重镇、市井乡里、名山大川,无处不寺院林立,缁衣云集;翻译佛典,经论爰述,浩如烟海;上自王公贵胄,下至贩夫翁妪,口称阿弥陀佛者比比皆是,虔心向佛者也不乏其人;如来真身,十室之邑,必有一席香火之奉。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鼎足而立,构成了世界宗教文化的三元色彩。然而由于中国僧徒素乏历史观念,即使佛门大德,也对自身的发展缺乏系统的认识。更由于禅宗不立文字、道断语言的修行方式,尤其难能对佛教文化进展的里程进行系统的整理。其间,虽然自梁慧皎著《高僧传》,后经唐道宣、宋赞宁、明如惺相继有历代高僧传记资料传世,于经、律、论三藏外,补上了史的阙失,但它们均依梁传体例,多为个人传记材料,且奇诡怪异,前生来世充斥于字里行间,“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本来的佛教往史被涂抹得妖祥杂兴,类同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和魂飞魄降的神话传说。加之《封神演义》、《西游记》的艺术夸张与民间鬼神崇拜的契合,几乎使佛教文化与超生送死、地狱天堂的民间信仰趋于一途。因此仍可以说,20世纪之前佛教史的研究始终未能登上学术的殿堂,即使在寺院的藏经楼中也难得占一席之地。
时至19世纪末叶,由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兴衰振敝的需要,佛教文化沿着自身发展的道路,重新出现了盛唐以后的勃兴局面。对佛教义理新的诠释,引起学者们对佛教史籍如痴如狂的求索,以及对经典真伪开始了锲而不舍的考证。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佛教往史研究的连带兴趣。上述由政治转向学术、由哲理扩展到史学领域的佛教文化研究,既是近世文化黄金时代的表征,也与科学史学兴起相同步。
20世纪初,寺僧、居士,尤其是侧身于中西文化交争的学者,其中不少人属意于佛教兴衰变迁之迹的研究,为史学领域增添了异样的光彩。维新派的臣子、反清革命的志士、新文化运动各壁垒中佼佼者与佛门四众中那些博雅好古之士,对佛教输入、发展的历史资料详征博引,条分缕析,甚至借资东籍,求诸欧西,开始在佛教史领域中纵横捭阖。诸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蒋维乔、欧阳渐、释太虚以及胡适之一辈,俱以乾嘉流风遗韵,钩稽靡密,从不同角度考订中国佛教植根与发展的佚事,或辨识一经一典的真伪与成书年代,间或探寻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冲突中发生和转化的轨迹。然而这些研究均散漫零落,于个别史料或某一经籍辨述过详,甚而有三纸无驴之嫌,于宏观的历史研究仅得补缺而已。梁启超虽于20世纪初即有志于《中国佛教史》的著述,而且精心结撰各种论文三十余篇。然而毕竟功亏一篑,留下了西西弗斯(Sisyphus)之憾。而且其常带感情的笔锋也难免使其语涉武断。汤氏之前真正能称得上佛教史著述的仅蒋维乔、黄忏华二氏之书。然而诚如前言,黄著多取旧传史料,蒋著依日人撰述改写增补而成。他们的功在将历代中国佛教往史予以系统整理,但无甚创见而缺乏独立研究的价值是严重的缺憾。1938年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问世,该书综合全史,有所陈述,中国佛教史才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了学术舞台。它既立足于史料的精详缜密,并以史为鉴,欲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又非纯依陈迹之搜讨,实以心性体会与佛教文化的精髓同情默应,客观公正地评价过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它既铺排着历史的真实,又不乏中肯的评价,因此也就无愧于“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的盛誉了。
有人说,汤氏的佛教史研究是“考证研究体”,其意在区别蒋、黄二氏记述体的两部佛教史著述。其实近代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无不受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梁启超诸人誉之以“科学实证法”,即此风影响的具体表现。在佛教文化研究中,此风也弥散在整个学术领域,梁启超、章太炎、欧阳渐、太虚诸人的《大乘起信论》、《四十二章经》,汉明帝永平求法等考证以及胡适的《神会和尚传》,均是这一“科学实证法”在治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实践。蒋、黄二氏的《中国佛教史》尽管是陈述形式,但其间也充斥着大量考据的学问。至于“研究”则更无特指的含义。但“考证研究体”的内涵还是突出了汤氏佛教史研究与其他人不同的特点:与蒋、黄不同的是以考证为基础的多维比较,与梁、胡不同的是系统的历史诠释。因此,准确地说汤氏佛教史研究应当是“考证比较诠释体”。
就方法而言,汤氏一再说明他的佛教史研究是凭借考证之学而展开的。这显然得力于乾嘉治学的流风遗韵。他又是受过系统西方文化教育的中国学人,因而西方科学史学、社会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治学方法也可信手拈来。故其研究中又多用系统的比较方法。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自不必重复,只其强调“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所谓“言约旨远”、“见道深弘”,自然要对它的现实意义“有所陈述”了。可见,汤氏中国佛教史研究不仅提供了“可信的材料”,“提出了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一般线索”,“揭露中国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现象”,同时也建设了一整套社会科学的系统治学方法。当然它所体现和印证因革转化的文化观念,更是汤氏通览全史、有所陈述的“深弘之道”。
事实上,前章所述同情默应、心性体会是就方法而言的指导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治学过程中对客体的深刻理解。这既是传统人文主义的精神,也是学术道路上的选择前提,或者说是选择的可能性。而广搜精求、多维比较则是“选择”的实施,即在大量史料中,通过不同方位的比较与考订而选择出历史的真迹。故其方法可集中概括为比较与考证两个方面,而逻辑的阐释则是以比较和考证为基础的。汤氏在《隋唐佛学的特点》的一次演讲中指明,历史研究有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在《隋唐佛教史稿》一书的绪言中又强调“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这两种方法的说明,显然把其治斯学的方法具体化也进一步系统化了。所谓纵的叙述,就是以可信的历史文献,从社会发展的纵轴上,阐述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及逻辑发展的必然性。横的叙述则是就同一时代不同地域各种宗风的历史断面的比较和诠释,表现地域文化的差异、宗派间的冲突与渗透,进而把握不同文化的特殊性、普遍性以及时代转型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不仅汤氏并览今古、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且其考证、比较与诠释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同样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成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享“价值至高”的盛誉。其后至今治斯学者,无不取之为蓝本而只能在其原有的间架上有所增益。
据此,本章就比较、考证、诠释三个方面对汤氏中国佛教史研究予以系统的透析,力图展现汤氏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全部风貌。同时还拟以专章同梁启超、蒋维乔、胡适佛教史研究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借以说明汤氏学术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在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原本就是对世界古今人文精神的选择和集大成。从希波格拉底到柏拉图洎至亚里士多德,由孔孟到朱、王,自释迦旁涉基督,还有卢梭因感情扩张的个人主义、培根视知识为权力的科学主义等,都是其思想上的借鉴之处。他尤其尊尚传统,视佛、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为“四圣”,每提及他们的人文学说,则情不自禁地称他们四人为“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之人物”。这是对不同文化优良传统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实际上也是在比较中完成的。白氏在建设他新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对古今东西文化均有所扬弃。他既比较了传统和现代,比较了神学和科学,比较了印欧和中美等文化观念的优劣异同,而且在强调研究佛教往史以吸取其精义的时候,又多角度地同基督、伊斯兰乃至儒、道、墨思想进行了比较,有选择地吸收了各宗教义中的人文精神而形成了他的人文主义。尽管这种比较是表层的,但作为科学思想建设的一种方法,不可能不影响汤氏以后的治学途径。事实上,科学的比较法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尤其是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应用。
所谓比较宗教学就是对个别宗教的历史、社会心理以及与其他宗教相关内容进行比较,以揭示宗教的内容与本质的实证宗教学。它是从18世纪比较解剖学、比较心理学的领域中延伸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用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创始人缪勒(Mǖller,F。M)的话说就是“只知道一种宗教的人什么宗教也不了解”,说明比较的方法对于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其实,19世纪对宗教史的考察就是建立在对不同宗教价值观比较的基础上。因此从广义上说,宗教史研究就是比较宗教学研究。汤氏的哲学、史学论文已经驾轻就熟地使用起这种科学比较法了。
当然,这并非说“比较”就完全是舶来品,其实,清初的朴学大师、乾嘉时期的汉学家所应用的考据之学同样寓比较于其中。清末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就是重实证的考据之学,它同样含有比较、扬弃的内容。汤用彤佛教史研究更多地,也可以说系统地采用了比较法和比较宗教学研究,这虽然是对西方文化选择吸收的结果,但无疑也与传统的灌注有关,更得力于乾嘉汉学的治学功底。
所谓系统的比较,显然不是传统中采用的零星的或平面式的比较,而是有组织的、多维的或者说是整体多方位的比较。它包括时序上的前后比较以探源索流、自身发展变化的纵深比较以得其精髓,以及宗派间的风尚、教外各家的异同乃至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空间聚散离合、冲突渗透的多方位比较以观其会通和转化。后者又是在时间和地域、内容和形式、本质精神与理论框架等不同层面的比较中实现的。通过上述系统的比较,揭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不同文化的对峙以及在接触中的拒斥、吸引、渗透和互相推动的特征,以寻找文化变迁的脉络。
一、佛道思想的比较看佛教的传入与佛道思想的调和
汤氏学术从不囿于单一的领域,其佛教史研究亦然。他总是把佛教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兴衰的变迁之迹放置在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佛教初传之时,他经过一系列的考证,确认“在西汉,佛法当已由北天竺传布中亚各国。其时汉武锐意开辟西域,远谋与乌孙、大宛、大夏交通……佛法必因是而益得东侵之便利。中印文化之结合即系于此……武帝之雄图实与佛法东来以极大助力”,“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而大月氏则为东汉时佛法东传的重镇。其时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已“由独任清虚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而且道教亦方萌芽,所以佛教传入必附庸方术才能得以流行,因而形成所谓佛道式的佛教。这些便是汤氏揭示的佛法东渐及其在中国这块文化厚土上植根、发芽,同时引起中国传统思想震荡并开始转化的社会背景,也是他进行佛道思想比较的客观前提。
事实上,汉武之际,尚雄强刚勇之风而尊儒术;另一方面汉武帝希冀长生久视之术,黄老之学则由盛而衰,谶纬之说亦代之而起。至纪元初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托名黄帝,道家方士亦以周之史官为教主,于是黄老之术与道教方术并行不悖。光武诸子均好鬼神方术,当时民俗甚至儒门学说均尚阴阳五行之事。崇尚清虚的佛教自然容易和它们实现多方面的认同。而且,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时也刚刚破土而出。初入的佛教,初创的道教以及取代黄老之学而新起的黄老之术“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于是便在接触中转相资益、并驾前行了。汤氏就是在这一文化大环境中认识佛教传入,并比较它们的思想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结果的。汤用彤根据汉代佛法之流布,列《佛道》专章,从生死观、道德观、修行方法、宗教仪式、经文教理、布道形式等方面比较了佛道乃至儒家的思想。
1938年,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于长沙付梓时,汤用彤曾指出,佛法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僧人学者无不具宗教情绪,“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必不能得其真”。所以他说:“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而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本土,探讨起来实在也非易事。因为这既不能不依靠那些真伪难辨、莫衷一是的“陈迹”,也难以“同情默应”之情去作心性的体会。佛法虽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甚巨,但其初来时势力甚微,且被人视作异族信仰,故史籍缺载。其后又揣测附会,神化己说,因而盘根错节,使后世学者“实难确定”。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强调“入华年代之确定,固非首要问题”,故“不宜强为之解”;另一方面又指出“治佛教史,尤当致意于变迁兴衰之迹”。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在考证比较中探索佛法输入、植根、孕育以至生成的机遇和条件,找出其发生发展的脉络。
首先,汤用彤以其所具的乾嘉考据之学的功力,对无稽散漫、精芜混杂的史籍和传说条分缕析,否定了汉明帝以前佛教入华的各种传说,即使如《魏书·释老志》所载,汉武帝时为“佛教流通之渐”,其时印度未有塑佛像之事等五证而“虚妄可知”。大致确定佛入中土当在汉明帝永平年中。同时他还指出“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但汉明帝求法亦“应有相当的根据”,而“非向壁虚造”,把佛教传入华夏视作由微而著的渐渍过程。至于后世必定以作始之功归之明帝,实在是出于自张其军,为僧伽增色的需要而已。
佛教传入中土的大环境确定之后,何以佛教能在此时输入?输入后的文化能否在新的环境中植根、发芽?这才是汤氏力图说明的,他选择的主要是比较文化或者说是比较宗教学方法。可以这样认为:考证是为了确定事实,比较则既为了辨析事实的真伪,也在于追溯变迁的缘由。
在这里,汤氏取争议较多的《四十二章经》为研究对象,并针对梁启超的“伪书晚出”之说,从内容到形式阐明佛教传入的契机,及其初传时的文化冲突与调和。
《四十二章经》即《佛说二十四章经》。相传在中国最早的寺院和译经道场白马寺译出,也是第一本汉译佛典。《高僧传》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历代三宝记》有言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携梵文贝叶经入华,禅居白马寺,于寺内清凉台共同译出此经,明帝敕令藏于兰台石室(皇家图书馆)。《高僧传》作者慧皎也认为是他们二人共译,后尚行江左,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此经出世甚晚,而为中国人托名伪撰。梁启超即持此论,认为它“乃撰本而非译本”。汤氏则从此经源出西土,刘宋时已有两种译本,后又经历代改窜,特别就经的性质诸方面,说明《四十二章经》译于月氏,送至中夏,乃佛法植入的一个表征。不仅为佛法初传时期进一步提供了确证,更由其思想内容与当时社会思潮相合,阐明了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
他指出:“古本《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既未申大乘之圆义,更不涉老庄之玄致”,后世之修加,实在是“唐以后宗门教下之妄人,依据当日流行之旨趣,以彰大其服膺之宗义”。由此他进一步比较了《四十二章经》与当时文化习俗:
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几全为小乘)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而其相合之故有二。首因人心相同,其所信之理每相似。次则汉代道术,必渐受佛教之影响,致采用其教义……经义与道术可相附会,而佛教在汉代已列入道术之林,此经因而为社会最流行之经典。故桓帝时,襄楷……引此与《太平经》及谶纬之说杂陈,且于西来之法与中夏之学,未尝加以区分也。
汤氏不仅利用自己语言文字之长,取巴利文本与汉译佛典作比较,令人无可非议地信服《四十二章经》源出西土;更重要的是从认识发生的心理过程,追究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在社会心理上的认同,以及文化接触中影响的双向性,即佛教对道术的附会,道术又取佛教义理而用之。他还特意指明,初传时期的佛教,不仅与道家方术,而且与杂取儒、道、阴阳的谶纬之说兼收并用了。这也正是汤氏关于文化移植的第一阶段,看见表面相同而调合。其实这里同样也包含有文化传播(即汤氏所谓的播化)的意思。
事实上,佛教传入时期,黄老思想为上流社会所崇尚,阴阳道术则为民间俗情,当时社会祭祀祈福大行其道。故佛教传入不仅要与道术趋合,而且还要受黄老思想的吸引或拒斥。因此,佛法必须适时地进行自身改造,以满足华夏民族心理乃至整个文化的需要,才能在一个新的地域植根或在华夏文化之树上嫁接而得新果。汤用彤同样注意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对初接触的中印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
汤氏在《汉代佛法之流布》一章中,不厌其烦地说明中印文化接触过程中的趋合现象。一方面是:
光武诸子,类好鬼神方术。
光武及明帝,虽一代明君,均信谶纬。沛王辅亦善图谶。楚王、济南王均谓常造作图书。当时皇室风尚若此。
当时俗情儒术均重阴阳五行之说,鬼神方术,厌胜避忌,甚嚣尘上。
还有如楚王英斋戒祭祀,桓帝亦好神仙之事,甚至上溯《史记》已有“鼎湖仙去”之说。
另一方面则是:
(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故俊异之声早被。
北之巨子昙柯迦罗则向善星术,南之领袖康僧会则多知图谶。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仅视佛教为一种方术或者直接“羼以神仙道术之言。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而佛教之所以能在初传时期,其势力逐渐得以扩张,也“不能不谓因其为一种祭祀方术,而投一时风尚也”。
当然,初传时期的佛教,很难以原来意义上的佛教视之,自然也非后起之典型的中国佛教。汤氏在比较时即断然指出:“故方士求仙捷径,最初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与之趋合的汉代佛教“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由此不难看出,不同文化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因适应新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理论的需要必然要进行自身改造,本土文化则常在不改变自己特质的前提下,吸收会通外来文化以实现自身的转化。这正是汤氏比较性阐释的用意所在。
无疑,道士方术,或者说黄老之术并不完全代表黄老之学,更不反映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全部。内容上的趋合较形式上的趋合更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会通。佛法清静无为、省欲去奢的理论尤其与黄老之学同气。汉初黄老之学虽为人君南面之术,但清静无为的思想显然与佛家空无旨趣能一拍即合。即如道教,也多讲修心养性、无为而治。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以天地万物受之“元气”即受之虚无的自然,言阴阳、配五行、陈教诫之辞,治国治道“其所言上接黄老、推尊谶纬”在思想上同样能引导佛教的顺化,所以在山东及东海沿岸诸地,道教佛教同步流行,尤能显示思想上的认同对于文化调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佛法在思想内容和行为方式上与当时的学术、道术相结合,又是百姓崇奉佛教的原因。如此辗转推助,佛教植入、生发,传统因之得以转化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为了说明佛、道(包括黄老之学的道家,辟谷养气、长生久视的道术和道教)思想的认同对于佛教传入的吸附作用,汤用彤进一步在宗教旨意、仪轨和经说异同诸方面对汉代佛道予以微观的剖析和比较。
一曰精灵起灭。汤氏指出:
释迦教义,自始即不为华人所了解。当东汉之世,鬼神之说至为炽盛。佛教谈三世因果,遂亦误认为鬼道之一,内教外道,遂并行不悖矣。
此说包括两个方面,即神不灭和果报之说。被汉代推为至尊的儒家思想,虽然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说,但仍讲“敬鬼神而远之”的话。而在整个大传统中,精灵不灭、魂升魄降之类的信仰却是根深蒂固的。汉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至桓帝时,边韶更据“浴神不死”之理,沿用阴阳二气之义,提出“蝉蜕渡世”的精灵不灭论。其时佛家不得不将无我轮回的缘起理论暂搁一旁,而以魂灵轮回呼应当时的习尚,这大概是本来具有的鲜明辩证思维的因缘说长期被人误解为天堂地狱、神佛畜生轮回之迷信思想的缘起了。
与神不灭思想相应的便是因果报应之说。《易》有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便是传统中的“承负”之说。这本来与佛说果报有些类同,因而更容易被善于攀合的中国传统心理糅为一体了。《牟子理惑论》有“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太平经》更以“承负”之说为根本义理之一,大讲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总之道禀气以生而永存,佛尚神灵而有三世;道以老子叠为圣者作师,佛谓释迦过去本生,历无量数劫;道有承负之说,流及子孙,佛有果报之理,应至三世。总之改造后的佛家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也就与之珠联璧合了。
二曰省欲去奢。
此则佛道异同比较尤为审慎。汤氏认为在摒除嗜欲方面,“固亦中外学说常有也”。这反映人类文化较普遍的特征,而佛道于此道更有相通之处。
无论道家还是道教,都以道法自然为准绳而贵尚无为。今译佛家涅槃,汉时即译无为。黄老之学本尚清静无为,道教则强调“不淫其性,返璞归真”。无为则摒除嗜欲,不淫其性乃不放纵个人性情也。道教追求的保性命之真是以“荡意平心”为入道之途的。它强调精神内守,不为外物所诱。汤氏引《淮南子·精神训》“五色乱目目不明,五声哗耳耳不聪”说明道家传统同样视嗜欲为失性命之真的根本而持节欲去奢之精神。而省欲去奢原本即是佛教教化的基本方式和通达觉悟之境的主要道路,当时传入的《四十二章经》“全书宗旨,在奖励梵行……教人克伐爱欲,尤所常见”。汤氏轻易列举了十来条关于此方面的内容,说明汉代佛教“视财色为爱欲之根”与传统精神几可等量齐观。
另外,汤氏在此还指出了佛道的差异。他说:“沙门不近女色,中国道术所无(且汉时方士已有房中术)。”在民间甚至还有采阴补阳、夫妇双修之事。但这些在汤用彤看来也是“甚为时人所惊奇”的。襄楷认为佛教不近女色便是道教的“守一”,即如皇帝“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也有悖于黄老之学,说明当时社会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去奢节欲的精神。汤氏还引述了《淮南子》“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丑也”,借以证明当时克欲去奢的风尚。这一点实际上与佛教的不净观如出一辙,传统文化受西来思想影响亦可知也。后世道教全真派的戒律多取诸佛门,无疑为汤氏文化调和、推助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印证。
三曰仁慈好施。
儒家讲博施济众,道家则重己贵生,字面虽与佛家布施戒杀相类,其义实相去甚远。前者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内容,后者显然由爱己出发。中国人向以三牲为祭,所以汉代佛教传入前,戒杀乐施在中国罕见。由此观之,传统与慈悲为怀、好生恶杀的佛教大相异趣。“汉代方士,不闻戒杀”,“至若布施,则亦为治黄白术者所不言”。至于乐善好施之士,显然是佛教广为流传之后的事了。然而“仁善好施”作为一种教化,在随佛入华之时,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拒斥,应当视为武帝时穷兵黩武,以及其后士族豪门穷奢极欲,鲸吞兼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馈。这点尽管汤氏未予说明,但他还是举出后汉时蜀中高士折象“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谓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用以说明“东汉奉黄老者,固亦有戒杀乐施者”。当然,单纯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佛教传入时在传统中的顺化,所以他又专取《太平经》与佛教进行比较,指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亦颇窃取佛教之学说”。他说《太平经》“颇重仁道”,“常言乐施好生,则尤与佛家契合”,足见道家甚至整个传统与佛法的趋合。当然,佛教更要受传统的影响而发生变异。比如《太平经》以五阴为元气,此中国传统的元气论亦为佛家所取而作为汉代佛教的根本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汤氏引《六度集经》中《察微王经》借用的元气观:“元气强者为地,软者为水,暖者为火,动者为风”,佛家的四大在传统的吸附下,便被“元气”兼包并容了。
四曰讲经注经。
汤用彤说:“汉代儒家讲经立都讲。晋时佛家讲经,亦闻有都讲。似系采汉人经师讲经成法。但此制自亦有释典之根据,未必是因袭儒家法度。”为此他考察了佛家典籍,证明“佛家在汉魏间已有都讲,则都讲诵经发问之制,疑始于佛徒也”。尽管都讲之制是佛家因袭儒家还是儒家效法佛家不能得到确论,然而两相比较,同样显示了文化调和的痕迹。
另外还有如黄老之学为君子人之术、浮图乃延祚之方等,实反映了佛教初传时中印文化互相影响的真实情况。简单地说,由外来文化方面看,佛法因植入的需要而趋附传统,依傍黄老、道术以求发展。就传统而言,一方面因中西交通开辟,佛法继续东来,而不能不受新思想的影响,再则因译事未兴,国人仅得其思想之概貌及释迦教人行事之大端,推测附会,视之为与传统相合的道术,西来之人也顺水推船、推广其教,所以汉代佛教实在是道佛结合的一种思想和方术。“上流社会,偶因好黄老之术,兼及浮屠……至若文人学士,仅襄楷、张衡略为述及。”及至魏晋,玄风渐盛,中华学术面目为之一变,佛法则转而依附玄理,受到大夫的青睐,而得以在学术界广为流行。其时“牟子援引老庄以申佛旨,已足征时代精神之转换”。这种转换便是汤氏认为《牟子理惑论》“已弃道术而谈玄理”,而输入期依附黄老方术的道佛式佛教同时也就沿着佛玄结合的方向,开始推助中华文化的第一次转化了。
二、佛玄思想比较看佛教发展及儒、道、释的互相趋附
就中国思想发展史的主流而言,魏晋实乃玄学思潮氾埽的阶段,而三国时期则是清谈玄风滥觞的年代。据汤氏考,公元2世纪末,在牟子著《理惑论》前后,中国思想学术为之一变。一些思想家兼取释老,佛家玄风也于其中而见端倪。尤其到三国时,有识之士对于汉代长生久视之类的道家方技已不屑一顾,道家不死而仙、祠祀丹药、辟谷吐纳几为大雅所不道。可是还应该看到《老》、《庄》尚全身养生,虽为两汉方士所采,而顺乎自然却是《老》、《庄》的根本精神。它们对自然、人生的超越关怀和辩证思维方式,显然投合了屡经战乱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于是汉代方技便在《老》、《庄》的根基上,辗转而为清谈之风。其时汉译佛典也有所增加,佛学的空无旨趣也随汉代佛教的植入而被世人所了解。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静无为之玄致……而为神仙方技枝属之汉代佛教,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佛与玄相辅相成而得以盛行,佛教也由初传入时被中国士子百姓误以为道术的道佛式佛教演进为崇尚自然礼法、本末体用之类清谈的佛玄式佛教了。毫无疑问,当时清谈之风借佛语而趋高尚,佛学义理尤借士子玄风而求发达,西来僧人以及在中国本土诞生的佛门弟子无不袭取《老》、《庄》玄谈,弘扬空无旨趣。如慧远引“庄子为连类”以讲“实相义”;法雅、道安常引“三玄”之言,比附佛经义理;至如僧肇三论,更是以玄说佛的精品。汤用彤对此广搜精求,条分缕析,认真比较佛玄思想的形式内容、发生原因及社会结果等,阐述佛教思想在中国本土的深化以及儒、道、释三家思想冲突融合的大趋势。
(1)
当然,三国时代也可视作时代精神转换的分水岭,而佛、道的转型均可在《牟子理惑论》中找到依据。汤氏首先从两汉三国不同时代的佛道思想比较中,勾画出过渡时期思想转化的形式,同时比较了佛道平行发展中的异同。
汤用彤指出,两汉方士企求长生不死的惑人之术在三国时已信誉扫地。“牟子鄙养生辟谷”,“讥道家‘不死而仙’之妖妄”,魏武帝虽“奉行桓帝故事”,“笃好方术”,其子曹丕、曹植却作文斥神仙道术。曹丕《典论》言“生之必死,成之必败”,“逝者莫返,潜在莫形”,指斥道家的不死之法乃惑者所为。曹植有《辩道论》,“佛徒恒引之”,“其旨在指斥方士”。被后世誉为“天下英雄谁敌手”的孙仲谋,虎踞江东,《吴志》载其好神仙符瑞,然其任支谦为博士,使与韦昭共辅东宫;为康僧会立建初寺,三国时佛教两大家均盛行江左,佛法开玄化之端,不能不说有孙吴之功。这一前后转型的比较,说明了佛教在理论上谋求发展——“非复东汉斋祀之教矣”。这是其一。
另一方面,汤氏凭借这一过渡时期佛道平行发展过程的横向比较,进一步说明社会思潮在不同文化作用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复杂关系。这里主要还是围绕对粗俗的道家方术的扬弃和对形而上辩证思维的强化而展开的立体式的比较。
汤氏着重指出:“汉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统。至三国时,传播于南方。一为安世高之禅学,偏于小乘……二为支谶之《般若》,乃大乘学……二者虽互相有关涉,但其系统在学说及传授上,固甚分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展开了他的系统比较。
他说,支谦传支谶之学,僧会注世高之经。二人均在魏初,并生中土,俱受华北,同住建业。其译经均“尚文雅”,且“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然而他们的思想显然不尽相同。支谦之学主神与道合,主明本,重智慧;僧会之说主养生成神,主养神,重禅法。前者“颇附合于(老子)五千言之玄理”,与当时玄学同流,乃大乘般若之学。后者“虽亦探及人生原始,但重守意养气,思得神通,其性质仍上承汉代之道术”,具有小乘的特点。据此,汤氏告诉我们,“是亦已见汉代以来,旧佛道之将坠,而两晋新佛玄之将兴”,“两晋以还所流行之佛学,则上接二支。明乎此,则中国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始于此时,实无疑也”。具体说,支谦即是开佛教玄学化之端的大家,由是也理清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端绪。
汤氏着重比较了两者在思想上的差异。他指出:“汉代以来,中国阴阳五行家言盛行元气之说……故汉魏佛徒以之与‘五阴’相牵合。”而安世高之学,“禅数最悉,禅之用在洞悉人之本原。数之要者,其一为五蕴”。康僧会上接安世高之学,其所持之阴,“仍承袭汉代佛教神明住寿之说”。康僧会强调行安般禅法旨在“制天地、住寿命”,就说明了其思想实乃汉世佛法的余绪。汤氏因此明确指出:“道家养气,可以不死而仙。佛家行安般,亦可以成神。”康僧会佛教思想,撇开禅定追求解脱而入涅槃的玄理,撷取道家重得神通的一面,仍然受道家成仙思想的影响,实为保性命之真的养生成神之理。
支谦的学说则不然,他重学问,趋向于人生本真之探讨。汤氏所谓的神与道合,无疑是反本或者说是达本之说。他指出支氏“常用之名辞与重要之观念,曰佛、曰法身、曰涅槃、曰真如、曰空。此与老庄玄学所有之名辞,如道、如虚无(或本无)者,均指本体,因而互相牵引附合”。为了说明这一点,汤用彤广取《牟子理惑论》、阮籍《老子赞》,以及边韶、何晏、王弼、裴頠等关于道的论述予以比较。他引述曰:
牟子云:佛乃道德之元祖。
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
佛与道之关系,牟子虽未畅言,然于佛则曰“恍惚”,曰“能小能大”。于道则曰“无形无声”,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则佛之与道,固无二致。
阮籍曰:归虚返真。
与道俱成。
支谦则云:
夫体道为菩萨,是空虚也。斯道为菩萨,亦空虚也。
菩萨心履践大道。欲为体道,心与道俱无形,故言空虚也。
如此比较,汤氏据此指出,“支谦实深契《老》、《庄》之说”,“牟子所言,支谦所译,与步兵之文,理趣同符……实则因老庄教行,诸人均染时代之风尚,故文若是之相似也”。同时他仍以诸玄学家“以无为本”之说,进一步说明支氏“无形故空虚”的论点,亦即玄学家乐此不疲的本无思想。
上述佛教玄言,借老庄道义扶摇而起,足见不同文化因相似而趋于调合。但汤氏并未满足大传统内之比较,他还把这一理论上的牵合,同西文基督教化兼容犹太、希腊文化的现象作以对比,他说西方基督徒也曾合耶稣与希腊哲学之Logos为一体,而Logos,即理,即道。借此说明佛与中国传统观念在理论上的趋合也有世界历史文化的前鉴。
另外汤氏还作了求法与传法的比较,朱士行西行求法,“弘法不惜生命者”,正因《般若》、《方等》适来中华,其空无旨趣恰投时人所好。但先时传经,率凭口译,且音训畅义难通,“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因而“誓志捐身,远求大品”,使佛教思想在学术上更向上跨越了一步。
(2)
其次,汤用彤又从佛学、玄学两种思潮的载体——名僧和名士的趋合上,看佛法在魏晋时期顺化和发展的社会助因。他指出:“高僧传》曰‘孙权使支谦与韦昭共辅东宫’,言或非实。然名僧名士之相结合,当滥觞于斯日。”指明三国时期僧人与士子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历史事实。接着他又说:
其后《般若》大行于世,而僧人立身行事又在在与清谈者契合。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
这里说明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思想上的认同而引起的形式上的结合,形式上的结合又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而其结合之处,则在朱士行以后提倡的般若学了。为了说明上的便利,兹将汤氏的比较勾勒如下:
其一是七道人与竹林七贤牵合:
竺法护→山涛(风德高远)
竺法乘→王戎(施舍钱财)
于法兰→阮籍(傲独不群)
于道邃→阮咸(高风一也)
帛法祖→嵇康(轻世招患)
竺道潜→刘伶(旷大之体)
支遁→向秀(风好同矣)
其二是释子名士共入一流,时谓八达:
陶靖节《群辅录》载董昶、王澄、阮瞻、庾、谢鲲、胡毋辅之与沙门支孝龙、光逸为八达。《晋书》谓胡毋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为八达。
其三是名僧与名士的交流:
竺法护有助手聂承远、道真父子。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均中华学士而与佛教名师接近者。
竺叔兰醉酒,与清谈领袖乐广酬对。
阮庾与支孝龙为友。
清流巨子石季伦奉佛甚至。
一代名僧支道林与东晋名士,诸如王洽、殷浩、孙绰、袁弘、王羲之、谢安相结为友。
上述名僧与名士交游,皆因其发展的需要而染清谈习尚,其风神亦类谈客也。
应当看到,上述名僧与名士的趋合,一则是因为佛法般若性空的旨趣与老庄玄理相符,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原因所造成中国士子的避世佯狂之风与佛教追求超越精神在形式上的吻合。所以汤氏又着重说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而或“厉操幽栖高情避世”——嘉遁;或“佯狂放荡,宅心事外”——任达。而佛徒也多以此行事,以保持与社会协同发展的关系。由此可见,魏晋佛法为了发展的需要而沿袭传统,兼采老庄,国内名流则没有必要去深究佛理,故汤氏说:“名士之未能尽解佛理,亦可想见。”其实,未能尽解佛理,甚至可以说无意尽解者,何止当时名士,即使佛教文化鼎盛时的隋唐,中国士人对佛法精奥也不甚了了,仅取其皮毛而已。只是到了晚近,才出现了学者、居士在佛经中探赜索隐之风。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文化接触和转化过程中,无疑还是以本地固有文化为中心而向前推进的。这大概又是汤氏的良苦用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晋时“佛道门户之见不深,无大抵触。实尤因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为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
(3)
上述由宏观上的比较,说明魏晋佛法转型的特点。继之,汤氏尤以更大的篇幅从微观上比较了晋及其后佛教在思想学术上的发展。简而言之,即由般若性空之理比较六家七宗以及其与儒道文化的异同;由罗什之学看佛教南北的分野以及地域文化在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汤氏借释名僧与高僧之概念,强调名僧和同风气,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特立独行,使佛法泽继被于未来,说明东晋以下,佛教与以前相比又能有所创获而独步一时,并发挥佛陀精神,亦不全借清谈之浮华,实赖高僧之学识。故其比较也以高僧为主轴,而以其他佛教史实作附证。其中释道安、鸠摩罗什之德望功绩最著。他们讲学译经,集僧门英才,造就了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一代宗风,故汤氏不惮其烦,详细比述了他们的思想在不同方向上发生的不同影响。
远在鸠摩罗什之前,玄风飚起,般若学亦附之而光大,中国学术思想的绝大变化,也全赖般若学的推助。而释道安卓著辛劳,其影响遍及燕赵荆襄、中原关中,故本期般若学亦多与道安有所关涉。其后有僧睿作《毗摩罗诘堤经义疏》序之曰:“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不仅说明道安性空之义影响广久,而且指明当时僧界学术上的偏颇。汤氏据此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其一,汤氏自道安扬弃译经中的格义之法,与其前译方式的不同,看魏晋佛教不依傍时流、志在弘扬教理而谋独立发展的趋势。
格者,量也。具体说即以中国思想比拟配合,或者说融合中国传统观念于佛教义理之中,此为初期译经师所创。至竺法雅而成系统。竺法雅以代表佛家名相条目的“事数”拟配中国学术的传统概念,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之意,以便被输入民族了解佛理进而发展佛学。但其迂拙牵强,难免有失本义,故为有识者所不取。汤氏特别强调:“迨文化灌输既甚久,了悟更深,于是审知外族思想自有其源流曲折,遂了然其毕竟有异,此自道安、罗什以后格义之所由废弃也。”他还说:
自道安以后,佛道渐明,世人渐了然释教有特异处。且因势力既张,当有出主入奴之见,因更不愿以佛理附和外书。及至罗什时代,经义大明,尤不须借俗理相比拟。
这也就是说,道安前后的佛教相比,前为形式上的牵会,后是思想上的发展,其独立性、思想性都因格义的废弃而日渐加强。
其二,道安般若性空与六家七宗其他各家的相互比较,看佛学与儒道本体观的融合。
据此可知,般若各家因对性空本无之义解释各不相同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基于对本体认识的差异,又可将他们分为三派,即解释本体空无的本无派,悉主色无的即色派,空心不空境的心无派。其后僧肇著《不真空论》破斥的三种偏向即此三说。
为了说明文化融合的基础及其在学术思想上的转化,汤氏还专门就本末真俗与有无之辨展示中印文化在本体观念上的融会贯通。他说:
魏晋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也。周秦诸子之谈本体者,要以儒道二家为大宗。《老子》以道为万物之母,无为天地之根。天地万物与道之关系,盖以“有”“无”诠释。“无”为母,而“有”为子。“无”为本,而“有”为末。本末之别,即后世所谓体用之辨。
如此,作为本体之学的魏晋玄学便上接周秦儒、道二家,魏晋佛学的本体观便可以与儒、道二家平行相较了。汤用彤实际上从本体与玄思、核心观念、学术习尚三个方面观察佛与儒、道、玄相互吸引的理论基础。他反复比较说:
魏晋玄学祖述《老》、《庄》,竞尚空无,贵无贱有。本无末有乃玄学中心。
佛教义理,先与道家合流,般若诸经,均言“本无”乃“真如”之古译,本末者即“真”“俗”二谛之异辞。
传统本体之说不离人生,以实现本性为第一要义,即所谓反本。归真、复命、通玄、履道、体极、存神均反本之异名。
佛乃解脱之道,与人生关系尤切。传入期佛教解脱之方在息意去欲,识心达本以归无为。魏吴佛说神与道合,主张禅智双运,由末达本。汉代佛法达本在探心识之源,魏晋佛玄反本亦有心空之说,其实均以实现人生为要义。
晋代名僧名士逍遥任达,轻忽人事,行为风格,尤属同气。僧人言谈举止,学术理论与所习用名词,“无往而不可与清谈家一致”。
总之,般若学在道安等的倡导下,已脱离对传统概念的比附而独立发展,更与儒、道、玄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清谈之风中扶摇而起了。
般若之学,多与道安同时,六家七宗的异同,主要是在历史的断面上所作的横向比较。鸠摩罗什之学理趋幽邃,敷扬至教,广出妙典,境界极高,僧肇《什法师诔文》说他使“法鼓重振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其门下有四圣、八俊、十哲者。其中有三论之祖僧肇,涅槃之圣道生,成实师宗之始僧导、僧嵩,足见其学说所被之广,流布之久远。故汤氏比较已不局限在某个时代,而循不同学说发展的脉络,予以独立叙述,并在时间、空间、地域诸方面比较大乘思想的飚起和深化。
汤用彤着重说明,罗什之学博大精深,今古罕匹。而且因关内兵祸频仍,名僧四散,其弟子相率南渡,进而造成风气益形殊异的南北佛学。他指出:什公门下“多尚玄谈”,“宗奉空理,而仍未离于中国当时之风尚也”。然而,“义学南渡,《涅槃》、《成实》相继风行”,《涅槃》“已自真空入于妙有”,《成实》“实不免于沙婆多之有说”。故而北方有“解空第一”的僧肇,“融会中印之义理,于体用问题,有深切之证知”。南方涅槃,成实相代而起,行有无之辨,而主本有之说,形成了典型的南北佛学分野的学术局面,其比较以下详细叙述。此处仅从僧肇之学看汤氏佛玄、佛学各家以及中外文化的各种比较所揭示的佛学思想在当时的理论升华。
汤氏指出:
肇公之学,融合《般若》、《维摩》诸经,《中》、《百》诸论,而用中国论学文体扼要写出。凡印度名相之分析,事数之排列,均皆解除毕尽……而于印度学说之华化……均有绝大建树……命意遣词,自然多袭取《老》、《庄》玄学之书。因此《肇论》仍属玄学之系统。概括言之,《肇论》重要理论,如齐是非,一动静,或多由读《庄子》而有所了悟。
显而易见,他对僧肇之学的认识是在比较了中印思想、佛学与老庄玄学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之后,他便就肇论之比较而比较,详细分析了僧肇的体用观念。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思想与道安时代般若学的不同。
汤氏说:“肇公之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此即后来中国佛教的重要理论,也是近代思想家构建哲学体系的主要支柱(如熊十力翕辟成变的本心本体论)。汤氏显然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他从空有、动静两个方面,同般若学的本体观和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衬托了僧肇不偏不二之说的划时代意义。
“从来佛家谈空,皆不免于偏。僧睿曰‘六家偏而不即’是矣。”这就是汤氏比较肇论与六家的前提。他指出支愍度等的心无说“旨在空心”;支道林的即色“从物方面说空”,“均有所偏”,道安等的本无“即本空”,“亦不免于虚无”。僧肇自称其学为“不真空”,提出“本体无相,超于有无”“有无皆不真”的非有非无之说,以高度的辩证思维破斥三家在本体论方面的偏执之说。为了说明本体,也即佛家所言“空”的性质,汤氏进一步解释僧肇理论,以本体无相说明万物的性质,“不能偏于有,亦不能偏于无”。同时他还指出“一切决定即是否定”这一命题,把肇论同Spinoza之说——To call anything definite is a denial in part——相比较,从中透见佛家说空即否定之否定的性质。
《物不迁论》是从动静性质上谈体用关系的。
同时,汤氏还将这一比较与西方相应的思想作以对照,指出僧肇“皆加呵斥”的动静观“若如古希腊哲学家Parmenides主一切不变,又如Heracleitus执一切皆变,而即所谓两家之‘调和派’谓本质不变,而变属于现象,似亦与《物不迁论》之主旨大相径庭”。由此而显示僧肇高度辩证思维的理性性格。
通过上述空有、动静观念的比较阐述,鲜明地突出了僧肇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的体用理论。据此,汤氏说这一体用之说仿佛Spinoza所谓的immanent cause,进一步展示了世界文化发展即或有先后的不同,但在核心观念上总还是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这种比较无疑为其中西互补的文化观提供了事实依据。
其实,僧肇非有非无、即动即静、即体即用的体用理论是中国佛学,即以大乘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化佛学,理论上的板块结构,也为传统中国哲学的升华,提供了足资参考的辩证思维资料。以后佛学的中道思想,当体即空,即心即佛,无不与僧肇体用如一的思想相一致。自宋至明,理学家辨理、辨心,尤其近代思想家,构筑新的哲学体系,显然都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这一观念。难怪汤氏说“其所作论,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
(4)
魏晋佛学南北风气悬异早已成为定论,尽管当时学者对佛教传入路线有所争议,但“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益有不可诬者”。也就是说佛教植入中国本土,因地域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梁启超向持此论。汤用彤历来持文化各具地域特性,故对佛法南统、北统的区别及其与地域文化的趋同性尤予以详细论证,只不过他与其他《学衡》诸子一样,不取梁氏“谓江淮人对于玄学最易感受,故佛教先盛于南”的说法罢了。
总的说来,汤氏认为南方佛教专精义理,与玄学合流;北方佛学则偏重行业,与经学俱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证唐僧神清《北山录》云:
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
汤氏还解释华、淳二意曰:“晋宋高僧艺解光时,弘阐教法,故曰华也。元魏高僧以禅观行业据道,故曰淳”,“由此言之,则唐世已有分佛教为南北二系也”。
当然还有,诸如南方涅槃、成实,北方般若、毗昙,北方传法途径主要是陆路而分南北,南方主要经海程亦染北方之风气等,其不同也并非纯以地域相划。南方玄风实由名士渡江、北方义学南趋推助。北方谈玄亦如南朝名流习尚。而在传统佛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隋唐宗派亦颇采江南之学。如此同中存异,异处求同,在南北系统的地域比较同时,更注意不同文化流派的思想内容的剖判。这种在比较中有比较、多方位展现不同文化纵横内外各种关系是汤氏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
就佛教的南统而言,汤氏通过黑白、夷夏、本末之争以及形神因果的辩论,揭示南方佛义与玄学同流和孔、释之异同。他说:
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而兼擅玄趣。一在南齐竟陵王当国之时,而萧子良亦并奖励三玄之学。一在梁武帝之世,而梁武帝亦名士笃于佛事者。佛义与玄学之同流,继承魏晋之风,为南统之特征。
他还以《南史》为据,证明“南统偏尚义理,不脱三玄之轨范。而士大夫与僧徒之结合,多袭支(道林)、许(询)之遗风”。特别指出,元嘉名士,“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故《涅槃》之学,顿悟之说,虽非因其提倡,乃能风行后世”。谢灵运一生常与佛徒发生因缘,著《辨宗论》,申道生顿悟之义,又尝注《金刚般若》,其诗“融合儒、佛、老,可见其濡染之深”。与谢氏以词章齐名的颜延之颇习佛理,著书立说,辨析异同,往复终日,宋武帝笑称其“无愧支许”。足可见当时风气与魏晋一脉相承。所以汤氏又说:“当时名士之所以乐与僧人交游,社会之所以弘奖佛法,盖均在玄理清言,与支、许、安、汰之世无以异也。”至于齐季萧子良,“少有清尚,倾意宾客”,“齐梁二代之名师,罕有与其无关系者”。其学“首以大乘玄理为本……志在‘总校玄释,定其虚实’”。梁武帝舍道归佛,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佛化治国。朝臣更趋附人主,僧人亦染名士华而不实、柔靡浮虚的风格,均见佛玄合流的迹象。当时“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
不仅如此,汤氏还不惮其烦地以当时的本末之争,反映佛玄合流的立命之所。他认为魏晋以来“释、李之同异,异说之争辩,均系于本末源流之观念。党释者多斥李为末,尊李者每言释不得其本”。其与周孔名教的区别在本末,于是伪造故事,定其先后,争论骤起。学者们也从学术上参与此争论。一说“致本则同”,一说本一末殊,异计繁兴,不一而足。汤氏通过反复比较而言:“魏晋玄学以《老》、《庄》为大宗,圣人本无,故《般若》谈空,与二篇虚无之旨,并行不悖,均视为得本探源之学……刘宋以后,儒学渐昌……然其谈儒术仍沿玄学之观点,与王弼注《周易》、何晏解《论语》固为一系。”此说不仅说明佛玄合流的汇聚点,而且从探本的角度揭示了儒道佛三家的牵合,从而也显示出南统与北统的相通之处。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汤用彤比较了佛儒异同,从中透见文化接触过程中因看见不同而冲突的事实。
他首先从总体上比较而言:佛入中华,或偏于教,或偏于理。“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内外之争,常只在理之长短。”时学通于玄风清谈,“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涉入《老》、《庄》,说用则儒在济俗,佛在治心,二者亦同归而殊途”。既说明佛教与传统的相合而互补,同时也展现其与传统的相异而冲突和在冲突中的发展。
汤氏引慧琳《白黑论》的白黑之争,重申慧远、宗炳等孔、释“虽同归而实殊途”之旨。他说:“琳以为佛教仁慈,劝人迁善,与周孔以仁义化天下者其方不同,其旨在挽救风俗则一……因而六度可与五教并行,信顺无妨与慈悲齐立也。”
其次,汤氏又以形神因果的辩论,重点阐明儒、佛入道之途的不同。汤氏开宗明义,引宗少文之说,“谓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其事渺茫,于周、孔书典,又未明言”,周、孔所述“笃于始形,而略于终神”。他还据谯王《论孔释书》说:“因果之理,不见于周、孔典谟。”至南齐范缜《神灭论》出,把形神因果的辩论推向高潮。他指出:“儒教主祭祀祖先之神,则意在从孝子之心,而厉渝薄之意。世俗虽传有妖怪鬼神,但决非神不灭因而有鬼也。”可见,这已经不只是同归的殊途,其核心观念也因大不同而导发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神灭神不灭的争论。然而,汤氏并不拘泥于这一冲突的表面现象,还是说明“精神之理,亦间见于中华书卷。盖世之疑结,首在暗于形神之别”,指出“神固资形而生”,形神一如的无神论,主旨在破除因果,表现了汤氏透过文化冲突表面所看到的更深刻的意蕴。
另外,汤用彤还从夷夏之争的角度宏观地描绘了东西文化交相影响的历史画面。他指出,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以起”。自王浮作《化胡经》起,南方佛道之争虽不像北方以武力相侵,但“其争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推翻”。自晋简文帝时,尼道容反对清水道师王濮阳,至宋末顾欢作《夷夏论》,双方伪造经典,自张其军,屡起屡歇。其中根本倾覆佛说者,除神灭外,夷夏之防则是道家杀向佛门的重要武器。其大旨在“中印国民性之殊异,而言西方之教不可行于中国”。汤氏引顾欢之言曰:“端委搢绅,诸华之容。翦发旷衣,群夷之服……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下弃妻孥,上废宗祀……舍华效夷,义将安取?”顾氏黜佛之意,溢于言表。汤氏还利用顾之比较而比较。
顾氏虽然信道,但这里已很难看见崇道抑佛的迹象。所以汤氏说“夫华人奉佛,本系用夷变夏……深智之夷人,与受教之汉人,形迹虽殊,而道躯无别”,而玄佛合流,亦“必使夷夏之界渐泯也”。汤氏在此又再一次折向他那文化冲突、中西互补的文化观念。
作为佛教的北统,显然与南方不同,自东晋末,姚秦僭号关中,沮渠称王陇右,继而拓跋氏入主中原,北方佛教屡遭兵残。故汤氏由当时政治与佛法兴衰之关系,看佛学与经学俱起,剖析重宗教行为的北方佛教特征,以及开隋唐佛教宗派竞起一统的局面。
汤用彤在这里还比较南北佛教兴衰的根由。他说:“南朝佛法以执麈尾能清言者为高。其流弊所极,在乎争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其流弊所极,在乎好利,而堕于私欲。”北方佛法一则以利诱人,致使信仰者趋之若鹜;二则因求福田,出家猥滥僧徒流风之坏,朋比匪人,而致变祸迭起。兴则九天之上,衰则九地之下,无不与社会政治有密切关系,因而也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交相影响,并驾齐驱。
西晋末叶,天下大乱,兵祸迭起,乱世祸福,至无定轨。永嘉名士相继渡江,朝廷南徙,政治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先经五胡之乱,其后诸帝,享国日浅,祸乱相寻,故不如南方相对稳定的局势利于佛法和平发展,佛法的兴衰多与人主的好恶相关切。北方佛教更多染政治色彩而与南方玄佛合流的佛法各异其趣。汤用彤认真分析了当时社会状况,包括两次大的法难以及其与经学俱起俱弘的历史事实,说明佛法兴衰亦与统治者的鼓励或限制尤其与治道立说有绝大关系。
汤用彤首先指出:“北魏诸帝,虽渐被华化,然其奉佛则与中国南方之君主不同。”落笔即道出北方佛教与统治者的关系及其与南统佛教的区别之由。他举例说魏献文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在位六年而禅位于太子宏”,其所信虽不专在佛教,“但因信道而至于禅位,则其对宗教之热情,似又非南朝帝王爱好玄理者所可比也”。而于佛理有所研求并予以提倡者,首推孝文帝。其后“北魏义学僧人辈出”,“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魏世诸王亦多有奉佛者”。故“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至孝静帝立,魏分东西,虽经变乱,立寺之风犹存。北齐诸帝于佛法仍循前规。北齐文宣帝、武成帝、后主都礼敬僧人,奖励译经,建寺立塔。此时造像刻经,较元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北朝佛法之兴,自然借助君主推尊之力。
当然,统治者的倡导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乱世中人们冀求解脱,求得安身立命之所,才是驱动人们向佛的社会心理,这既可以说是信仰,也可说是动机。汤用彤认为:“僧徒游手而得衣食,又可托命三宝,经营私利……即可避免租税力役,故天下愈乱,则出家者益众。”他又说:“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故甚者贪婪自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如僧祇粟之诛求)。荡检逾闲,净土翻成诲淫之地。究其原因,皆由其奉佛之动机,在求利益。信教虽或虔至,便终含商业性质。”汤氏这里说的“动机不纯”、“信仰不真诚”,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可以看出他对客观历史考察的科学精神。1955年,汤氏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记》中自我批评说,他“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谈。这里他不只谈了佛教兴盛的社会政治背景,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反动作用,也即其在当时,事实上也是以后空门寂落的自身因素。魏太武帝、周武帝毁法使南北朝佛教跌入低谷。
诚如杨衒之所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
印度佛法东渐,于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儒、道乃至民间习俗交汇、拒斥和互相渗透中,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损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它虽从未占据统治地位,但京都重镇、市井乡里、名山大川,无处不寺院林立,缁衣云集;翻译佛典,经论爰述,浩如烟海;上自王公贵胄,下至贩夫翁妪,口称阿弥陀佛者比比皆是,虔心向佛者也不乏其人;如来真身,十室之邑,必有一席香火之奉。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鼎足而立,构成了世界宗教文化的三元色彩。然而由于中国僧徒素乏历史观念,即使佛门大德,也对自身的发展缺乏系统的认识。更由于禅宗不立文字、道断语言的修行方式,尤其难能对佛教文化进展的里程进行系统的整理。其间,虽然自梁慧皎著《高僧传》,后经唐道宣、宋赞宁、明如惺相继有历代高僧传记资料传世,于经、律、论三藏外,补上了史的阙失,但它们均依梁传体例,多为个人传记材料,且奇诡怪异,前生来世充斥于字里行间,“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本来的佛教往史被涂抹得妖祥杂兴,类同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和魂飞魄降的神话传说。加之《封神演义》、《西游记》的艺术夸张与民间鬼神崇拜的契合,几乎使佛教文化与超生送死、地狱天堂的民间信仰趋于一途。因此仍可以说,20世纪之前佛教史的研究始终未能登上学术的殿堂,即使在寺院的藏经楼中也难得占一席之地。
时至19世纪末叶,由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兴衰振敝的需要,佛教文化沿着自身发展的道路,重新出现了盛唐以后的勃兴局面。对佛教义理新的诠释,引起学者们对佛教史籍如痴如狂的求索,以及对经典真伪开始了锲而不舍的考证。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佛教往史研究的连带兴趣。上述由政治转向学术、由哲理扩展到史学领域的佛教文化研究,既是近世文化黄金时代的表征,也与科学史学兴起相同步。
20世纪初,寺僧、居士,尤其是侧身于中西文化交争的学者,其中不少人属意于佛教兴衰变迁之迹的研究,为史学领域增添了异样的光彩。维新派的臣子、反清革命的志士、新文化运动各壁垒中佼佼者与佛门四众中那些博雅好古之士,对佛教输入、发展的历史资料详征博引,条分缕析,甚至借资东籍,求诸欧西,开始在佛教史领域中纵横捭阖。诸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蒋维乔、欧阳渐、释太虚以及胡适之一辈,俱以乾嘉流风遗韵,钩稽靡密,从不同角度考订中国佛教植根与发展的佚事,或辨识一经一典的真伪与成书年代,间或探寻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冲突中发生和转化的轨迹。然而这些研究均散漫零落,于个别史料或某一经籍辨述过详,甚而有三纸无驴之嫌,于宏观的历史研究仅得补缺而已。梁启超虽于20世纪初即有志于《中国佛教史》的著述,而且精心结撰各种论文三十余篇。然而毕竟功亏一篑,留下了西西弗斯(Sisyphus)之憾。而且其常带感情的笔锋也难免使其语涉武断。汤氏之前真正能称得上佛教史著述的仅蒋维乔、黄忏华二氏之书。然而诚如前言,黄著多取旧传史料,蒋著依日人撰述改写增补而成。他们的功在将历代中国佛教往史予以系统整理,但无甚创见而缺乏独立研究的价值是严重的缺憾。1938年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问世,该书综合全史,有所陈述,中国佛教史才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了学术舞台。它既立足于史料的精详缜密,并以史为鉴,欲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又非纯依陈迹之搜讨,实以心性体会与佛教文化的精髓同情默应,客观公正地评价过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它既铺排着历史的真实,又不乏中肯的评价,因此也就无愧于“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的盛誉了。
有人说,汤氏的佛教史研究是“考证研究体”,其意在区别蒋、黄二氏记述体的两部佛教史著述。其实近代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无不受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梁启超诸人誉之以“科学实证法”,即此风影响的具体表现。在佛教文化研究中,此风也弥散在整个学术领域,梁启超、章太炎、欧阳渐、太虚诸人的《大乘起信论》、《四十二章经》,汉明帝永平求法等考证以及胡适的《神会和尚传》,均是这一“科学实证法”在治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实践。蒋、黄二氏的《中国佛教史》尽管是陈述形式,但其间也充斥着大量考据的学问。至于“研究”则更无特指的含义。但“考证研究体”的内涵还是突出了汤氏佛教史研究与其他人不同的特点:与蒋、黄不同的是以考证为基础的多维比较,与梁、胡不同的是系统的历史诠释。因此,准确地说汤氏佛教史研究应当是“考证比较诠释体”。
就方法而言,汤氏一再说明他的佛教史研究是凭借考证之学而展开的。这显然得力于乾嘉治学的流风遗韵。他又是受过系统西方文化教育的中国学人,因而西方科学史学、社会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治学方法也可信手拈来。故其研究中又多用系统的比较方法。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自不必重复,只其强调“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所谓“言约旨远”、“见道深弘”,自然要对它的现实意义“有所陈述”了。可见,汤氏中国佛教史研究不仅提供了“可信的材料”,“提出了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一般线索”,“揭露中国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现象”,同时也建设了一整套社会科学的系统治学方法。当然它所体现和印证因革转化的文化观念,更是汤氏通览全史、有所陈述的“深弘之道”。
事实上,前章所述同情默应、心性体会是就方法而言的指导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治学过程中对客体的深刻理解。这既是传统人文主义的精神,也是学术道路上的选择前提,或者说是选择的可能性。而广搜精求、多维比较则是“选择”的实施,即在大量史料中,通过不同方位的比较与考订而选择出历史的真迹。故其方法可集中概括为比较与考证两个方面,而逻辑的阐释则是以比较和考证为基础的。汤氏在《隋唐佛学的特点》的一次演讲中指明,历史研究有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在《隋唐佛教史稿》一书的绪言中又强调“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这两种方法的说明,显然把其治斯学的方法具体化也进一步系统化了。所谓纵的叙述,就是以可信的历史文献,从社会发展的纵轴上,阐述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及逻辑发展的必然性。横的叙述则是就同一时代不同地域各种宗风的历史断面的比较和诠释,表现地域文化的差异、宗派间的冲突与渗透,进而把握不同文化的特殊性、普遍性以及时代转型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不仅汤氏并览今古、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且其考证、比较与诠释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同样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成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享“价值至高”的盛誉。其后至今治斯学者,无不取之为蓝本而只能在其原有的间架上有所增益。
据此,本章就比较、考证、诠释三个方面对汤氏中国佛教史研究予以系统的透析,力图展现汤氏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全部风貌。同时还拟以专章同梁启超、蒋维乔、胡适佛教史研究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借以说明汤氏学术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在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原本就是对世界古今人文精神的选择和集大成。从希波格拉底到柏拉图洎至亚里士多德,由孔孟到朱、王,自释迦旁涉基督,还有卢梭因感情扩张的个人主义、培根视知识为权力的科学主义等,都是其思想上的借鉴之处。他尤其尊尚传统,视佛、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为“四圣”,每提及他们的人文学说,则情不自禁地称他们四人为“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之人物”。这是对不同文化优良传统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实际上也是在比较中完成的。白氏在建设他新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对古今东西文化均有所扬弃。他既比较了传统和现代,比较了神学和科学,比较了印欧和中美等文化观念的优劣异同,而且在强调研究佛教往史以吸取其精义的时候,又多角度地同基督、伊斯兰乃至儒、道、墨思想进行了比较,有选择地吸收了各宗教义中的人文精神而形成了他的人文主义。尽管这种比较是表层的,但作为科学思想建设的一种方法,不可能不影响汤氏以后的治学途径。事实上,科学的比较法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尤其是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应用。
所谓比较宗教学就是对个别宗教的历史、社会心理以及与其他宗教相关内容进行比较,以揭示宗教的内容与本质的实证宗教学。它是从18世纪比较解剖学、比较心理学的领域中延伸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用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创始人缪勒(Mǖller,F。M)的话说就是“只知道一种宗教的人什么宗教也不了解”,说明比较的方法对于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其实,19世纪对宗教史的考察就是建立在对不同宗教价值观比较的基础上。因此从广义上说,宗教史研究就是比较宗教学研究。汤氏的哲学、史学论文已经驾轻就熟地使用起这种科学比较法了。
当然,这并非说“比较”就完全是舶来品,其实,清初的朴学大师、乾嘉时期的汉学家所应用的考据之学同样寓比较于其中。清末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就是重实证的考据之学,它同样含有比较、扬弃的内容。汤用彤佛教史研究更多地,也可以说系统地采用了比较法和比较宗教学研究,这虽然是对西方文化选择吸收的结果,但无疑也与传统的灌注有关,更得力于乾嘉汉学的治学功底。
所谓系统的比较,显然不是传统中采用的零星的或平面式的比较,而是有组织的、多维的或者说是整体多方位的比较。它包括时序上的前后比较以探源索流、自身发展变化的纵深比较以得其精髓,以及宗派间的风尚、教外各家的异同乃至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空间聚散离合、冲突渗透的多方位比较以观其会通和转化。后者又是在时间和地域、内容和形式、本质精神与理论框架等不同层面的比较中实现的。通过上述系统的比较,揭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不同文化的对峙以及在接触中的拒斥、吸引、渗透和互相推动的特征,以寻找文化变迁的脉络。
一、佛道思想的比较看佛教的传入与佛道思想的调和
汤氏学术从不囿于单一的领域,其佛教史研究亦然。他总是把佛教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兴衰的变迁之迹放置在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佛教初传之时,他经过一系列的考证,确认“在西汉,佛法当已由北天竺传布中亚各国。其时汉武锐意开辟西域,远谋与乌孙、大宛、大夏交通……佛法必因是而益得东侵之便利。中印文化之结合即系于此……武帝之雄图实与佛法东来以极大助力”,“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而大月氏则为东汉时佛法东传的重镇。其时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已“由独任清虚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而且道教亦方萌芽,所以佛教传入必附庸方术才能得以流行,因而形成所谓佛道式的佛教。这些便是汤氏揭示的佛法东渐及其在中国这块文化厚土上植根、发芽,同时引起中国传统思想震荡并开始转化的社会背景,也是他进行佛道思想比较的客观前提。
事实上,汉武之际,尚雄强刚勇之风而尊儒术;另一方面汉武帝希冀长生久视之术,黄老之学则由盛而衰,谶纬之说亦代之而起。至纪元初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托名黄帝,道家方士亦以周之史官为教主,于是黄老之术与道教方术并行不悖。光武诸子均好鬼神方术,当时民俗甚至儒门学说均尚阴阳五行之事。崇尚清虚的佛教自然容易和它们实现多方面的认同。而且,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时也刚刚破土而出。初入的佛教,初创的道教以及取代黄老之学而新起的黄老之术“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于是便在接触中转相资益、并驾前行了。汤氏就是在这一文化大环境中认识佛教传入,并比较它们的思想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结果的。汤用彤根据汉代佛法之流布,列《佛道》专章,从生死观、道德观、修行方法、宗教仪式、经文教理、布道形式等方面比较了佛道乃至儒家的思想。
1938年,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于长沙付梓时,汤用彤曾指出,佛法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僧人学者无不具宗教情绪,“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必不能得其真”。所以他说:“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而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本土,探讨起来实在也非易事。因为这既不能不依靠那些真伪难辨、莫衷一是的“陈迹”,也难以“同情默应”之情去作心性的体会。佛法虽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甚巨,但其初来时势力甚微,且被人视作异族信仰,故史籍缺载。其后又揣测附会,神化己说,因而盘根错节,使后世学者“实难确定”。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强调“入华年代之确定,固非首要问题”,故“不宜强为之解”;另一方面又指出“治佛教史,尤当致意于变迁兴衰之迹”。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在考证比较中探索佛法输入、植根、孕育以至生成的机遇和条件,找出其发生发展的脉络。
首先,汤用彤以其所具的乾嘉考据之学的功力,对无稽散漫、精芜混杂的史籍和传说条分缕析,否定了汉明帝以前佛教入华的各种传说,即使如《魏书·释老志》所载,汉武帝时为“佛教流通之渐”,其时印度未有塑佛像之事等五证而“虚妄可知”。大致确定佛入中土当在汉明帝永平年中。同时他还指出“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但汉明帝求法亦“应有相当的根据”,而“非向壁虚造”,把佛教传入华夏视作由微而著的渐渍过程。至于后世必定以作始之功归之明帝,实在是出于自张其军,为僧伽增色的需要而已。
佛教传入中土的大环境确定之后,何以佛教能在此时输入?输入后的文化能否在新的环境中植根、发芽?这才是汤氏力图说明的,他选择的主要是比较文化或者说是比较宗教学方法。可以这样认为:考证是为了确定事实,比较则既为了辨析事实的真伪,也在于追溯变迁的缘由。
在这里,汤氏取争议较多的《四十二章经》为研究对象,并针对梁启超的“伪书晚出”之说,从内容到形式阐明佛教传入的契机,及其初传时的文化冲突与调和。
《四十二章经》即《佛说二十四章经》。相传在中国最早的寺院和译经道场白马寺译出,也是第一本汉译佛典。《高僧传》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历代三宝记》有言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携梵文贝叶经入华,禅居白马寺,于寺内清凉台共同译出此经,明帝敕令藏于兰台石室(皇家图书馆)。《高僧传》作者慧皎也认为是他们二人共译,后尚行江左,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此经出世甚晚,而为中国人托名伪撰。梁启超即持此论,认为它“乃撰本而非译本”。汤氏则从此经源出西土,刘宋时已有两种译本,后又经历代改窜,特别就经的性质诸方面,说明《四十二章经》译于月氏,送至中夏,乃佛法植入的一个表征。不仅为佛法初传时期进一步提供了确证,更由其思想内容与当时社会思潮相合,阐明了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
他指出:“古本《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既未申大乘之圆义,更不涉老庄之玄致”,后世之修加,实在是“唐以后宗门教下之妄人,依据当日流行之旨趣,以彰大其服膺之宗义”。由此他进一步比较了《四十二章经》与当时文化习俗:
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几全为小乘)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而其相合之故有二。首因人心相同,其所信之理每相似。次则汉代道术,必渐受佛教之影响,致采用其教义……经义与道术可相附会,而佛教在汉代已列入道术之林,此经因而为社会最流行之经典。故桓帝时,襄楷……引此与《太平经》及谶纬之说杂陈,且于西来之法与中夏之学,未尝加以区分也。
汤氏不仅利用自己语言文字之长,取巴利文本与汉译佛典作比较,令人无可非议地信服《四十二章经》源出西土;更重要的是从认识发生的心理过程,追究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在社会心理上的认同,以及文化接触中影响的双向性,即佛教对道术的附会,道术又取佛教义理而用之。他还特意指明,初传时期的佛教,不仅与道家方术,而且与杂取儒、道、阴阳的谶纬之说兼收并用了。这也正是汤氏关于文化移植的第一阶段,看见表面相同而调合。其实这里同样也包含有文化传播(即汤氏所谓的播化)的意思。
事实上,佛教传入时期,黄老思想为上流社会所崇尚,阴阳道术则为民间俗情,当时社会祭祀祈福大行其道。故佛教传入不仅要与道术趋合,而且还要受黄老思想的吸引或拒斥。因此,佛法必须适时地进行自身改造,以满足华夏民族心理乃至整个文化的需要,才能在一个新的地域植根或在华夏文化之树上嫁接而得新果。汤用彤同样注意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对初接触的中印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
汤氏在《汉代佛法之流布》一章中,不厌其烦地说明中印文化接触过程中的趋合现象。一方面是:
光武诸子,类好鬼神方术。
光武及明帝,虽一代明君,均信谶纬。沛王辅亦善图谶。楚王、济南王均谓常造作图书。当时皇室风尚若此。
当时俗情儒术均重阴阳五行之说,鬼神方术,厌胜避忌,甚嚣尘上。
还有如楚王英斋戒祭祀,桓帝亦好神仙之事,甚至上溯《史记》已有“鼎湖仙去”之说。
另一方面则是:
(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故俊异之声早被。
北之巨子昙柯迦罗则向善星术,南之领袖康僧会则多知图谶。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仅视佛教为一种方术或者直接“羼以神仙道术之言。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而佛教之所以能在初传时期,其势力逐渐得以扩张,也“不能不谓因其为一种祭祀方术,而投一时风尚也”。
当然,初传时期的佛教,很难以原来意义上的佛教视之,自然也非后起之典型的中国佛教。汤氏在比较时即断然指出:“故方士求仙捷径,最初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与之趋合的汉代佛教“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由此不难看出,不同文化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因适应新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理论的需要必然要进行自身改造,本土文化则常在不改变自己特质的前提下,吸收会通外来文化以实现自身的转化。这正是汤氏比较性阐释的用意所在。
无疑,道士方术,或者说黄老之术并不完全代表黄老之学,更不反映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全部。内容上的趋合较形式上的趋合更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会通。佛法清静无为、省欲去奢的理论尤其与黄老之学同气。汉初黄老之学虽为人君南面之术,但清静无为的思想显然与佛家空无旨趣能一拍即合。即如道教,也多讲修心养性、无为而治。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以天地万物受之“元气”即受之虚无的自然,言阴阳、配五行、陈教诫之辞,治国治道“其所言上接黄老、推尊谶纬”在思想上同样能引导佛教的顺化,所以在山东及东海沿岸诸地,道教佛教同步流行,尤能显示思想上的认同对于文化调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佛法在思想内容和行为方式上与当时的学术、道术相结合,又是百姓崇奉佛教的原因。如此辗转推助,佛教植入、生发,传统因之得以转化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为了说明佛、道(包括黄老之学的道家,辟谷养气、长生久视的道术和道教)思想的认同对于佛教传入的吸附作用,汤用彤进一步在宗教旨意、仪轨和经说异同诸方面对汉代佛道予以微观的剖析和比较。
一曰精灵起灭。汤氏指出:
释迦教义,自始即不为华人所了解。当东汉之世,鬼神之说至为炽盛。佛教谈三世因果,遂亦误认为鬼道之一,内教外道,遂并行不悖矣。
此说包括两个方面,即神不灭和果报之说。被汉代推为至尊的儒家思想,虽然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说,但仍讲“敬鬼神而远之”的话。而在整个大传统中,精灵不灭、魂升魄降之类的信仰却是根深蒂固的。汉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至桓帝时,边韶更据“浴神不死”之理,沿用阴阳二气之义,提出“蝉蜕渡世”的精灵不灭论。其时佛家不得不将无我轮回的缘起理论暂搁一旁,而以魂灵轮回呼应当时的习尚,这大概是本来具有的鲜明辩证思维的因缘说长期被人误解为天堂地狱、神佛畜生轮回之迷信思想的缘起了。
与神不灭思想相应的便是因果报应之说。《易》有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便是传统中的“承负”之说。这本来与佛说果报有些类同,因而更容易被善于攀合的中国传统心理糅为一体了。《牟子理惑论》有“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太平经》更以“承负”之说为根本义理之一,大讲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总之道禀气以生而永存,佛尚神灵而有三世;道以老子叠为圣者作师,佛谓释迦过去本生,历无量数劫;道有承负之说,流及子孙,佛有果报之理,应至三世。总之改造后的佛家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也就与之珠联璧合了。
二曰省欲去奢。
此则佛道异同比较尤为审慎。汤氏认为在摒除嗜欲方面,“固亦中外学说常有也”。这反映人类文化较普遍的特征,而佛道于此道更有相通之处。
无论道家还是道教,都以道法自然为准绳而贵尚无为。今译佛家涅槃,汉时即译无为。黄老之学本尚清静无为,道教则强调“不淫其性,返璞归真”。无为则摒除嗜欲,不淫其性乃不放纵个人性情也。道教追求的保性命之真是以“荡意平心”为入道之途的。它强调精神内守,不为外物所诱。汤氏引《淮南子·精神训》“五色乱目目不明,五声哗耳耳不聪”说明道家传统同样视嗜欲为失性命之真的根本而持节欲去奢之精神。而省欲去奢原本即是佛教教化的基本方式和通达觉悟之境的主要道路,当时传入的《四十二章经》“全书宗旨,在奖励梵行……教人克伐爱欲,尤所常见”。汤氏轻易列举了十来条关于此方面的内容,说明汉代佛教“视财色为爱欲之根”与传统精神几可等量齐观。
另外,汤氏在此还指出了佛道的差异。他说:“沙门不近女色,中国道术所无(且汉时方士已有房中术)。”在民间甚至还有采阴补阳、夫妇双修之事。但这些在汤用彤看来也是“甚为时人所惊奇”的。襄楷认为佛教不近女色便是道教的“守一”,即如皇帝“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也有悖于黄老之学,说明当时社会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去奢节欲的精神。汤氏还引述了《淮南子》“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丑也”,借以证明当时克欲去奢的风尚。这一点实际上与佛教的不净观如出一辙,传统文化受西来思想影响亦可知也。后世道教全真派的戒律多取诸佛门,无疑为汤氏文化调和、推助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印证。
三曰仁慈好施。
儒家讲博施济众,道家则重己贵生,字面虽与佛家布施戒杀相类,其义实相去甚远。前者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内容,后者显然由爱己出发。中国人向以三牲为祭,所以汉代佛教传入前,戒杀乐施在中国罕见。由此观之,传统与慈悲为怀、好生恶杀的佛教大相异趣。“汉代方士,不闻戒杀”,“至若布施,则亦为治黄白术者所不言”。至于乐善好施之士,显然是佛教广为流传之后的事了。然而“仁善好施”作为一种教化,在随佛入华之时,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拒斥,应当视为武帝时穷兵黩武,以及其后士族豪门穷奢极欲,鲸吞兼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馈。这点尽管汤氏未予说明,但他还是举出后汉时蜀中高士折象“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谓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用以说明“东汉奉黄老者,固亦有戒杀乐施者”。当然,单纯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佛教传入时在传统中的顺化,所以他又专取《太平经》与佛教进行比较,指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亦颇窃取佛教之学说”。他说《太平经》“颇重仁道”,“常言乐施好生,则尤与佛家契合”,足见道家甚至整个传统与佛法的趋合。当然,佛教更要受传统的影响而发生变异。比如《太平经》以五阴为元气,此中国传统的元气论亦为佛家所取而作为汉代佛教的根本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汤氏引《六度集经》中《察微王经》借用的元气观:“元气强者为地,软者为水,暖者为火,动者为风”,佛家的四大在传统的吸附下,便被“元气”兼包并容了。
四曰讲经注经。
汤用彤说:“汉代儒家讲经立都讲。晋时佛家讲经,亦闻有都讲。似系采汉人经师讲经成法。但此制自亦有释典之根据,未必是因袭儒家法度。”为此他考察了佛家典籍,证明“佛家在汉魏间已有都讲,则都讲诵经发问之制,疑始于佛徒也”。尽管都讲之制是佛家因袭儒家还是儒家效法佛家不能得到确论,然而两相比较,同样显示了文化调和的痕迹。
另外还有如黄老之学为君子人之术、浮图乃延祚之方等,实反映了佛教初传时中印文化互相影响的真实情况。简单地说,由外来文化方面看,佛法因植入的需要而趋附传统,依傍黄老、道术以求发展。就传统而言,一方面因中西交通开辟,佛法继续东来,而不能不受新思想的影响,再则因译事未兴,国人仅得其思想之概貌及释迦教人行事之大端,推测附会,视之为与传统相合的道术,西来之人也顺水推船、推广其教,所以汉代佛教实在是道佛结合的一种思想和方术。“上流社会,偶因好黄老之术,兼及浮屠……至若文人学士,仅襄楷、张衡略为述及。”及至魏晋,玄风渐盛,中华学术面目为之一变,佛法则转而依附玄理,受到大夫的青睐,而得以在学术界广为流行。其时“牟子援引老庄以申佛旨,已足征时代精神之转换”。这种转换便是汤氏认为《牟子理惑论》“已弃道术而谈玄理”,而输入期依附黄老方术的道佛式佛教同时也就沿着佛玄结合的方向,开始推助中华文化的第一次转化了。
二、佛玄思想比较看佛教发展及儒、道、释的互相趋附
就中国思想发展史的主流而言,魏晋实乃玄学思潮氾埽的阶段,而三国时期则是清谈玄风滥觞的年代。据汤氏考,公元2世纪末,在牟子著《理惑论》前后,中国思想学术为之一变。一些思想家兼取释老,佛家玄风也于其中而见端倪。尤其到三国时,有识之士对于汉代长生久视之类的道家方技已不屑一顾,道家不死而仙、祠祀丹药、辟谷吐纳几为大雅所不道。可是还应该看到《老》、《庄》尚全身养生,虽为两汉方士所采,而顺乎自然却是《老》、《庄》的根本精神。它们对自然、人生的超越关怀和辩证思维方式,显然投合了屡经战乱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于是汉代方技便在《老》、《庄》的根基上,辗转而为清谈之风。其时汉译佛典也有所增加,佛学的空无旨趣也随汉代佛教的植入而被世人所了解。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静无为之玄致……而为神仙方技枝属之汉代佛教,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佛与玄相辅相成而得以盛行,佛教也由初传入时被中国士子百姓误以为道术的道佛式佛教演进为崇尚自然礼法、本末体用之类清谈的佛玄式佛教了。毫无疑问,当时清谈之风借佛语而趋高尚,佛学义理尤借士子玄风而求发达,西来僧人以及在中国本土诞生的佛门弟子无不袭取《老》、《庄》玄谈,弘扬空无旨趣。如慧远引“庄子为连类”以讲“实相义”;法雅、道安常引“三玄”之言,比附佛经义理;至如僧肇三论,更是以玄说佛的精品。汤用彤对此广搜精求,条分缕析,认真比较佛玄思想的形式内容、发生原因及社会结果等,阐述佛教思想在中国本土的深化以及儒、道、释三家思想冲突融合的大趋势。
(1)
当然,三国时代也可视作时代精神转换的分水岭,而佛、道的转型均可在《牟子理惑论》中找到依据。汤氏首先从两汉三国不同时代的佛道思想比较中,勾画出过渡时期思想转化的形式,同时比较了佛道平行发展中的异同。
汤用彤指出,两汉方士企求长生不死的惑人之术在三国时已信誉扫地。“牟子鄙养生辟谷”,“讥道家‘不死而仙’之妖妄”,魏武帝虽“奉行桓帝故事”,“笃好方术”,其子曹丕、曹植却作文斥神仙道术。曹丕《典论》言“生之必死,成之必败”,“逝者莫返,潜在莫形”,指斥道家的不死之法乃惑者所为。曹植有《辩道论》,“佛徒恒引之”,“其旨在指斥方士”。被后世誉为“天下英雄谁敌手”的孙仲谋,虎踞江东,《吴志》载其好神仙符瑞,然其任支谦为博士,使与韦昭共辅东宫;为康僧会立建初寺,三国时佛教两大家均盛行江左,佛法开玄化之端,不能不说有孙吴之功。这一前后转型的比较,说明了佛教在理论上谋求发展——“非复东汉斋祀之教矣”。这是其一。
另一方面,汤氏凭借这一过渡时期佛道平行发展过程的横向比较,进一步说明社会思潮在不同文化作用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复杂关系。这里主要还是围绕对粗俗的道家方术的扬弃和对形而上辩证思维的强化而展开的立体式的比较。
汤氏着重指出:“汉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统。至三国时,传播于南方。一为安世高之禅学,偏于小乘……二为支谶之《般若》,乃大乘学……二者虽互相有关涉,但其系统在学说及传授上,固甚分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展开了他的系统比较。
他说,支谦传支谶之学,僧会注世高之经。二人均在魏初,并生中土,俱受华北,同住建业。其译经均“尚文雅”,且“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然而他们的思想显然不尽相同。支谦之学主神与道合,主明本,重智慧;僧会之说主养生成神,主养神,重禅法。前者“颇附合于(老子)五千言之玄理”,与当时玄学同流,乃大乘般若之学。后者“虽亦探及人生原始,但重守意养气,思得神通,其性质仍上承汉代之道术”,具有小乘的特点。据此,汤氏告诉我们,“是亦已见汉代以来,旧佛道之将坠,而两晋新佛玄之将兴”,“两晋以还所流行之佛学,则上接二支。明乎此,则中国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始于此时,实无疑也”。具体说,支谦即是开佛教玄学化之端的大家,由是也理清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端绪。
汤氏着重比较了两者在思想上的差异。他指出:“汉代以来,中国阴阳五行家言盛行元气之说……故汉魏佛徒以之与‘五阴’相牵合。”而安世高之学,“禅数最悉,禅之用在洞悉人之本原。数之要者,其一为五蕴”。康僧会上接安世高之学,其所持之阴,“仍承袭汉代佛教神明住寿之说”。康僧会强调行安般禅法旨在“制天地、住寿命”,就说明了其思想实乃汉世佛法的余绪。汤氏因此明确指出:“道家养气,可以不死而仙。佛家行安般,亦可以成神。”康僧会佛教思想,撇开禅定追求解脱而入涅槃的玄理,撷取道家重得神通的一面,仍然受道家成仙思想的影响,实为保性命之真的养生成神之理。
支谦的学说则不然,他重学问,趋向于人生本真之探讨。汤氏所谓的神与道合,无疑是反本或者说是达本之说。他指出支氏“常用之名辞与重要之观念,曰佛、曰法身、曰涅槃、曰真如、曰空。此与老庄玄学所有之名辞,如道、如虚无(或本无)者,均指本体,因而互相牵引附合”。为了说明这一点,汤用彤广取《牟子理惑论》、阮籍《老子赞》,以及边韶、何晏、王弼、裴頠等关于道的论述予以比较。他引述曰:
牟子云:佛乃道德之元祖。
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
佛与道之关系,牟子虽未畅言,然于佛则曰“恍惚”,曰“能小能大”。于道则曰“无形无声”,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则佛之与道,固无二致。
阮籍曰:归虚返真。
与道俱成。
支谦则云:
夫体道为菩萨,是空虚也。斯道为菩萨,亦空虚也。
菩萨心履践大道。欲为体道,心与道俱无形,故言空虚也。
如此比较,汤氏据此指出,“支谦实深契《老》、《庄》之说”,“牟子所言,支谦所译,与步兵之文,理趣同符……实则因老庄教行,诸人均染时代之风尚,故文若是之相似也”。同时他仍以诸玄学家“以无为本”之说,进一步说明支氏“无形故空虚”的论点,亦即玄学家乐此不疲的本无思想。
上述佛教玄言,借老庄道义扶摇而起,足见不同文化因相似而趋于调合。但汤氏并未满足大传统内之比较,他还把这一理论上的牵合,同西文基督教化兼容犹太、希腊文化的现象作以对比,他说西方基督徒也曾合耶稣与希腊哲学之Logos为一体,而Logos,即理,即道。借此说明佛与中国传统观念在理论上的趋合也有世界历史文化的前鉴。
另外汤氏还作了求法与传法的比较,朱士行西行求法,“弘法不惜生命者”,正因《般若》、《方等》适来中华,其空无旨趣恰投时人所好。但先时传经,率凭口译,且音训畅义难通,“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因而“誓志捐身,远求大品”,使佛教思想在学术上更向上跨越了一步。
(2)
其次,汤用彤又从佛学、玄学两种思潮的载体——名僧和名士的趋合上,看佛法在魏晋时期顺化和发展的社会助因。他指出:“高僧传》曰‘孙权使支谦与韦昭共辅东宫’,言或非实。然名僧名士之相结合,当滥觞于斯日。”指明三国时期僧人与士子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历史事实。接着他又说:
其后《般若》大行于世,而僧人立身行事又在在与清谈者契合。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
这里说明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思想上的认同而引起的形式上的结合,形式上的结合又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而其结合之处,则在朱士行以后提倡的般若学了。为了说明上的便利,兹将汤氏的比较勾勒如下:
其一是七道人与竹林七贤牵合:
竺法护→山涛(风德高远)
竺法乘→王戎(施舍钱财)
于法兰→阮籍(傲独不群)
于道邃→阮咸(高风一也)
帛法祖→嵇康(轻世招患)
竺道潜→刘伶(旷大之体)
支遁→向秀(风好同矣)
其二是释子名士共入一流,时谓八达:
陶靖节《群辅录》载董昶、王澄、阮瞻、庾、谢鲲、胡毋辅之与沙门支孝龙、光逸为八达。《晋书》谓胡毋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为八达。
其三是名僧与名士的交流:
竺法护有助手聂承远、道真父子。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均中华学士而与佛教名师接近者。
竺叔兰醉酒,与清谈领袖乐广酬对。
阮庾与支孝龙为友。
清流巨子石季伦奉佛甚至。
一代名僧支道林与东晋名士,诸如王洽、殷浩、孙绰、袁弘、王羲之、谢安相结为友。
上述名僧与名士交游,皆因其发展的需要而染清谈习尚,其风神亦类谈客也。
应当看到,上述名僧与名士的趋合,一则是因为佛法般若性空的旨趣与老庄玄理相符,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原因所造成中国士子的避世佯狂之风与佛教追求超越精神在形式上的吻合。所以汤氏又着重说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而或“厉操幽栖高情避世”——嘉遁;或“佯狂放荡,宅心事外”——任达。而佛徒也多以此行事,以保持与社会协同发展的关系。由此可见,魏晋佛法为了发展的需要而沿袭传统,兼采老庄,国内名流则没有必要去深究佛理,故汤氏说:“名士之未能尽解佛理,亦可想见。”其实,未能尽解佛理,甚至可以说无意尽解者,何止当时名士,即使佛教文化鼎盛时的隋唐,中国士人对佛法精奥也不甚了了,仅取其皮毛而已。只是到了晚近,才出现了学者、居士在佛经中探赜索隐之风。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文化接触和转化过程中,无疑还是以本地固有文化为中心而向前推进的。这大概又是汤氏的良苦用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晋时“佛道门户之见不深,无大抵触。实尤因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为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
(3)
上述由宏观上的比较,说明魏晋佛法转型的特点。继之,汤氏尤以更大的篇幅从微观上比较了晋及其后佛教在思想学术上的发展。简而言之,即由般若性空之理比较六家七宗以及其与儒道文化的异同;由罗什之学看佛教南北的分野以及地域文化在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汤氏借释名僧与高僧之概念,强调名僧和同风气,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特立独行,使佛法泽继被于未来,说明东晋以下,佛教与以前相比又能有所创获而独步一时,并发挥佛陀精神,亦不全借清谈之浮华,实赖高僧之学识。故其比较也以高僧为主轴,而以其他佛教史实作附证。其中释道安、鸠摩罗什之德望功绩最著。他们讲学译经,集僧门英才,造就了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一代宗风,故汤氏不惮其烦,详细比述了他们的思想在不同方向上发生的不同影响。
远在鸠摩罗什之前,玄风飚起,般若学亦附之而光大,中国学术思想的绝大变化,也全赖般若学的推助。而释道安卓著辛劳,其影响遍及燕赵荆襄、中原关中,故本期般若学亦多与道安有所关涉。其后有僧睿作《毗摩罗诘堤经义疏》序之曰:“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不仅说明道安性空之义影响广久,而且指明当时僧界学术上的偏颇。汤氏据此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其一,汤氏自道安扬弃译经中的格义之法,与其前译方式的不同,看魏晋佛教不依傍时流、志在弘扬教理而谋独立发展的趋势。
格者,量也。具体说即以中国思想比拟配合,或者说融合中国传统观念于佛教义理之中,此为初期译经师所创。至竺法雅而成系统。竺法雅以代表佛家名相条目的“事数”拟配中国学术的传统概念,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之意,以便被输入民族了解佛理进而发展佛学。但其迂拙牵强,难免有失本义,故为有识者所不取。汤氏特别强调:“迨文化灌输既甚久,了悟更深,于是审知外族思想自有其源流曲折,遂了然其毕竟有异,此自道安、罗什以后格义之所由废弃也。”他还说:
自道安以后,佛道渐明,世人渐了然释教有特异处。且因势力既张,当有出主入奴之见,因更不愿以佛理附和外书。及至罗什时代,经义大明,尤不须借俗理相比拟。
这也就是说,道安前后的佛教相比,前为形式上的牵会,后是思想上的发展,其独立性、思想性都因格义的废弃而日渐加强。
其二,道安般若性空与六家七宗其他各家的相互比较,看佛学与儒道本体观的融合。
据此可知,般若各家因对性空本无之义解释各不相同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基于对本体认识的差异,又可将他们分为三派,即解释本体空无的本无派,悉主色无的即色派,空心不空境的心无派。其后僧肇著《不真空论》破斥的三种偏向即此三说。
为了说明文化融合的基础及其在学术思想上的转化,汤氏还专门就本末真俗与有无之辨展示中印文化在本体观念上的融会贯通。他说:
魏晋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也。周秦诸子之谈本体者,要以儒道二家为大宗。《老子》以道为万物之母,无为天地之根。天地万物与道之关系,盖以“有”“无”诠释。“无”为母,而“有”为子。“无”为本,而“有”为末。本末之别,即后世所谓体用之辨。
如此,作为本体之学的魏晋玄学便上接周秦儒、道二家,魏晋佛学的本体观便可以与儒、道二家平行相较了。汤用彤实际上从本体与玄思、核心观念、学术习尚三个方面观察佛与儒、道、玄相互吸引的理论基础。他反复比较说:
魏晋玄学祖述《老》、《庄》,竞尚空无,贵无贱有。本无末有乃玄学中心。
佛教义理,先与道家合流,般若诸经,均言“本无”乃“真如”之古译,本末者即“真”“俗”二谛之异辞。
传统本体之说不离人生,以实现本性为第一要义,即所谓反本。归真、复命、通玄、履道、体极、存神均反本之异名。
佛乃解脱之道,与人生关系尤切。传入期佛教解脱之方在息意去欲,识心达本以归无为。魏吴佛说神与道合,主张禅智双运,由末达本。汉代佛法达本在探心识之源,魏晋佛玄反本亦有心空之说,其实均以实现人生为要义。
晋代名僧名士逍遥任达,轻忽人事,行为风格,尤属同气。僧人言谈举止,学术理论与所习用名词,“无往而不可与清谈家一致”。
总之,般若学在道安等的倡导下,已脱离对传统概念的比附而独立发展,更与儒、道、玄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清谈之风中扶摇而起了。
般若之学,多与道安同时,六家七宗的异同,主要是在历史的断面上所作的横向比较。鸠摩罗什之学理趋幽邃,敷扬至教,广出妙典,境界极高,僧肇《什法师诔文》说他使“法鼓重振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其门下有四圣、八俊、十哲者。其中有三论之祖僧肇,涅槃之圣道生,成实师宗之始僧导、僧嵩,足见其学说所被之广,流布之久远。故汤氏比较已不局限在某个时代,而循不同学说发展的脉络,予以独立叙述,并在时间、空间、地域诸方面比较大乘思想的飚起和深化。
汤用彤着重说明,罗什之学博大精深,今古罕匹。而且因关内兵祸频仍,名僧四散,其弟子相率南渡,进而造成风气益形殊异的南北佛学。他指出:什公门下“多尚玄谈”,“宗奉空理,而仍未离于中国当时之风尚也”。然而,“义学南渡,《涅槃》、《成实》相继风行”,《涅槃》“已自真空入于妙有”,《成实》“实不免于沙婆多之有说”。故而北方有“解空第一”的僧肇,“融会中印之义理,于体用问题,有深切之证知”。南方涅槃,成实相代而起,行有无之辨,而主本有之说,形成了典型的南北佛学分野的学术局面,其比较以下详细叙述。此处仅从僧肇之学看汤氏佛玄、佛学各家以及中外文化的各种比较所揭示的佛学思想在当时的理论升华。
汤氏指出:
肇公之学,融合《般若》、《维摩》诸经,《中》、《百》诸论,而用中国论学文体扼要写出。凡印度名相之分析,事数之排列,均皆解除毕尽……而于印度学说之华化……均有绝大建树……命意遣词,自然多袭取《老》、《庄》玄学之书。因此《肇论》仍属玄学之系统。概括言之,《肇论》重要理论,如齐是非,一动静,或多由读《庄子》而有所了悟。
显而易见,他对僧肇之学的认识是在比较了中印思想、佛学与老庄玄学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之后,他便就肇论之比较而比较,详细分析了僧肇的体用观念。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思想与道安时代般若学的不同。
汤氏说:“肇公之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此即后来中国佛教的重要理论,也是近代思想家构建哲学体系的主要支柱(如熊十力翕辟成变的本心本体论)。汤氏显然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他从空有、动静两个方面,同般若学的本体观和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衬托了僧肇不偏不二之说的划时代意义。
“从来佛家谈空,皆不免于偏。僧睿曰‘六家偏而不即’是矣。”这就是汤氏比较肇论与六家的前提。他指出支愍度等的心无说“旨在空心”;支道林的即色“从物方面说空”,“均有所偏”,道安等的本无“即本空”,“亦不免于虚无”。僧肇自称其学为“不真空”,提出“本体无相,超于有无”“有无皆不真”的非有非无之说,以高度的辩证思维破斥三家在本体论方面的偏执之说。为了说明本体,也即佛家所言“空”的性质,汤氏进一步解释僧肇理论,以本体无相说明万物的性质,“不能偏于有,亦不能偏于无”。同时他还指出“一切决定即是否定”这一命题,把肇论同Spinoza之说——To call anything definite is a denial in part——相比较,从中透见佛家说空即否定之否定的性质。
《物不迁论》是从动静性质上谈体用关系的。
同时,汤氏还将这一比较与西方相应的思想作以对照,指出僧肇“皆加呵斥”的动静观“若如古希腊哲学家Parmenides主一切不变,又如Heracleitus执一切皆变,而即所谓两家之‘调和派’谓本质不变,而变属于现象,似亦与《物不迁论》之主旨大相径庭”。由此而显示僧肇高度辩证思维的理性性格。
通过上述空有、动静观念的比较阐述,鲜明地突出了僧肇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的体用理论。据此,汤氏说这一体用之说仿佛Spinoza所谓的immanent cause,进一步展示了世界文化发展即或有先后的不同,但在核心观念上总还是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这种比较无疑为其中西互补的文化观提供了事实依据。
其实,僧肇非有非无、即动即静、即体即用的体用理论是中国佛学,即以大乘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化佛学,理论上的板块结构,也为传统中国哲学的升华,提供了足资参考的辩证思维资料。以后佛学的中道思想,当体即空,即心即佛,无不与僧肇体用如一的思想相一致。自宋至明,理学家辨理、辨心,尤其近代思想家,构筑新的哲学体系,显然都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这一观念。难怪汤氏说“其所作论,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
(4)
魏晋佛学南北风气悬异早已成为定论,尽管当时学者对佛教传入路线有所争议,但“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益有不可诬者”。也就是说佛教植入中国本土,因地域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梁启超向持此论。汤用彤历来持文化各具地域特性,故对佛法南统、北统的区别及其与地域文化的趋同性尤予以详细论证,只不过他与其他《学衡》诸子一样,不取梁氏“谓江淮人对于玄学最易感受,故佛教先盛于南”的说法罢了。
总的说来,汤氏认为南方佛教专精义理,与玄学合流;北方佛学则偏重行业,与经学俱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证唐僧神清《北山录》云:
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
汤氏还解释华、淳二意曰:“晋宋高僧艺解光时,弘阐教法,故曰华也。元魏高僧以禅观行业据道,故曰淳”,“由此言之,则唐世已有分佛教为南北二系也”。
当然还有,诸如南方涅槃、成实,北方般若、毗昙,北方传法途径主要是陆路而分南北,南方主要经海程亦染北方之风气等,其不同也并非纯以地域相划。南方玄风实由名士渡江、北方义学南趋推助。北方谈玄亦如南朝名流习尚。而在传统佛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隋唐宗派亦颇采江南之学。如此同中存异,异处求同,在南北系统的地域比较同时,更注意不同文化流派的思想内容的剖判。这种在比较中有比较、多方位展现不同文化纵横内外各种关系是汤氏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
就佛教的南统而言,汤氏通过黑白、夷夏、本末之争以及形神因果的辩论,揭示南方佛义与玄学同流和孔、释之异同。他说:
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而兼擅玄趣。一在南齐竟陵王当国之时,而萧子良亦并奖励三玄之学。一在梁武帝之世,而梁武帝亦名士笃于佛事者。佛义与玄学之同流,继承魏晋之风,为南统之特征。
他还以《南史》为据,证明“南统偏尚义理,不脱三玄之轨范。而士大夫与僧徒之结合,多袭支(道林)、许(询)之遗风”。特别指出,元嘉名士,“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故《涅槃》之学,顿悟之说,虽非因其提倡,乃能风行后世”。谢灵运一生常与佛徒发生因缘,著《辨宗论》,申道生顿悟之义,又尝注《金刚般若》,其诗“融合儒、佛、老,可见其濡染之深”。与谢氏以词章齐名的颜延之颇习佛理,著书立说,辨析异同,往复终日,宋武帝笑称其“无愧支许”。足可见当时风气与魏晋一脉相承。所以汤氏又说:“当时名士之所以乐与僧人交游,社会之所以弘奖佛法,盖均在玄理清言,与支、许、安、汰之世无以异也。”至于齐季萧子良,“少有清尚,倾意宾客”,“齐梁二代之名师,罕有与其无关系者”。其学“首以大乘玄理为本……志在‘总校玄释,定其虚实’”。梁武帝舍道归佛,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佛化治国。朝臣更趋附人主,僧人亦染名士华而不实、柔靡浮虚的风格,均见佛玄合流的迹象。当时“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
不仅如此,汤氏还不惮其烦地以当时的本末之争,反映佛玄合流的立命之所。他认为魏晋以来“释、李之同异,异说之争辩,均系于本末源流之观念。党释者多斥李为末,尊李者每言释不得其本”。其与周孔名教的区别在本末,于是伪造故事,定其先后,争论骤起。学者们也从学术上参与此争论。一说“致本则同”,一说本一末殊,异计繁兴,不一而足。汤氏通过反复比较而言:“魏晋玄学以《老》、《庄》为大宗,圣人本无,故《般若》谈空,与二篇虚无之旨,并行不悖,均视为得本探源之学……刘宋以后,儒学渐昌……然其谈儒术仍沿玄学之观点,与王弼注《周易》、何晏解《论语》固为一系。”此说不仅说明佛玄合流的汇聚点,而且从探本的角度揭示了儒道佛三家的牵合,从而也显示出南统与北统的相通之处。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汤用彤比较了佛儒异同,从中透见文化接触过程中因看见不同而冲突的事实。
他首先从总体上比较而言:佛入中华,或偏于教,或偏于理。“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内外之争,常只在理之长短。”时学通于玄风清谈,“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涉入《老》、《庄》,说用则儒在济俗,佛在治心,二者亦同归而殊途”。既说明佛教与传统的相合而互补,同时也展现其与传统的相异而冲突和在冲突中的发展。
汤氏引慧琳《白黑论》的白黑之争,重申慧远、宗炳等孔、释“虽同归而实殊途”之旨。他说:“琳以为佛教仁慈,劝人迁善,与周孔以仁义化天下者其方不同,其旨在挽救风俗则一……因而六度可与五教并行,信顺无妨与慈悲齐立也。”
其次,汤氏又以形神因果的辩论,重点阐明儒、佛入道之途的不同。汤氏开宗明义,引宗少文之说,“谓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其事渺茫,于周、孔书典,又未明言”,周、孔所述“笃于始形,而略于终神”。他还据谯王《论孔释书》说:“因果之理,不见于周、孔典谟。”至南齐范缜《神灭论》出,把形神因果的辩论推向高潮。他指出:“儒教主祭祀祖先之神,则意在从孝子之心,而厉渝薄之意。世俗虽传有妖怪鬼神,但决非神不灭因而有鬼也。”可见,这已经不只是同归的殊途,其核心观念也因大不同而导发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神灭神不灭的争论。然而,汤氏并不拘泥于这一冲突的表面现象,还是说明“精神之理,亦间见于中华书卷。盖世之疑结,首在暗于形神之别”,指出“神固资形而生”,形神一如的无神论,主旨在破除因果,表现了汤氏透过文化冲突表面所看到的更深刻的意蕴。
另外,汤用彤还从夷夏之争的角度宏观地描绘了东西文化交相影响的历史画面。他指出,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以起”。自王浮作《化胡经》起,南方佛道之争虽不像北方以武力相侵,但“其争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推翻”。自晋简文帝时,尼道容反对清水道师王濮阳,至宋末顾欢作《夷夏论》,双方伪造经典,自张其军,屡起屡歇。其中根本倾覆佛说者,除神灭外,夷夏之防则是道家杀向佛门的重要武器。其大旨在“中印国民性之殊异,而言西方之教不可行于中国”。汤氏引顾欢之言曰:“端委搢绅,诸华之容。翦发旷衣,群夷之服……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下弃妻孥,上废宗祀……舍华效夷,义将安取?”顾氏黜佛之意,溢于言表。汤氏还利用顾之比较而比较。
顾氏虽然信道,但这里已很难看见崇道抑佛的迹象。所以汤氏说“夫华人奉佛,本系用夷变夏……深智之夷人,与受教之汉人,形迹虽殊,而道躯无别”,而玄佛合流,亦“必使夷夏之界渐泯也”。汤氏在此又再一次折向他那文化冲突、中西互补的文化观念。
作为佛教的北统,显然与南方不同,自东晋末,姚秦僭号关中,沮渠称王陇右,继而拓跋氏入主中原,北方佛教屡遭兵残。故汤氏由当时政治与佛法兴衰之关系,看佛学与经学俱起,剖析重宗教行为的北方佛教特征,以及开隋唐佛教宗派竞起一统的局面。
汤用彤在这里还比较南北佛教兴衰的根由。他说:“南朝佛法以执麈尾能清言者为高。其流弊所极,在乎争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其流弊所极,在乎好利,而堕于私欲。”北方佛法一则以利诱人,致使信仰者趋之若鹜;二则因求福田,出家猥滥僧徒流风之坏,朋比匪人,而致变祸迭起。兴则九天之上,衰则九地之下,无不与社会政治有密切关系,因而也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交相影响,并驾齐驱。
西晋末叶,天下大乱,兵祸迭起,乱世祸福,至无定轨。永嘉名士相继渡江,朝廷南徙,政治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先经五胡之乱,其后诸帝,享国日浅,祸乱相寻,故不如南方相对稳定的局势利于佛法和平发展,佛法的兴衰多与人主的好恶相关切。北方佛教更多染政治色彩而与南方玄佛合流的佛法各异其趣。汤用彤认真分析了当时社会状况,包括两次大的法难以及其与经学俱起俱弘的历史事实,说明佛法兴衰亦与统治者的鼓励或限制尤其与治道立说有绝大关系。
汤用彤首先指出:“北魏诸帝,虽渐被华化,然其奉佛则与中国南方之君主不同。”落笔即道出北方佛教与统治者的关系及其与南统佛教的区别之由。他举例说魏献文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在位六年而禅位于太子宏”,其所信虽不专在佛教,“但因信道而至于禅位,则其对宗教之热情,似又非南朝帝王爱好玄理者所可比也”。而于佛理有所研求并予以提倡者,首推孝文帝。其后“北魏义学僧人辈出”,“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魏世诸王亦多有奉佛者”。故“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至孝静帝立,魏分东西,虽经变乱,立寺之风犹存。北齐诸帝于佛法仍循前规。北齐文宣帝、武成帝、后主都礼敬僧人,奖励译经,建寺立塔。此时造像刻经,较元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北朝佛法之兴,自然借助君主推尊之力。
当然,统治者的倡导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乱世中人们冀求解脱,求得安身立命之所,才是驱动人们向佛的社会心理,这既可以说是信仰,也可说是动机。汤用彤认为:“僧徒游手而得衣食,又可托命三宝,经营私利……即可避免租税力役,故天下愈乱,则出家者益众。”他又说:“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故甚者贪婪自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如僧祇粟之诛求)。荡检逾闲,净土翻成诲淫之地。究其原因,皆由其奉佛之动机,在求利益。信教虽或虔至,便终含商业性质。”汤氏这里说的“动机不纯”、“信仰不真诚”,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可以看出他对客观历史考察的科学精神。1955年,汤氏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记》中自我批评说,他“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谈。这里他不只谈了佛教兴盛的社会政治背景,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反动作用,也即其在当时,事实上也是以后空门寂落的自身因素。魏太武帝、周武帝毁法使南北朝佛教跌入低谷。
诚如杨衒之所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