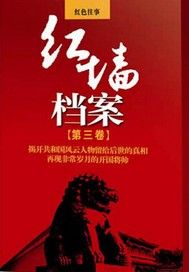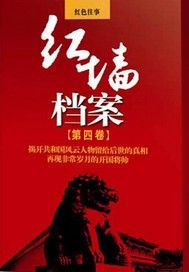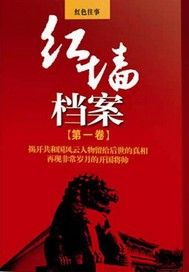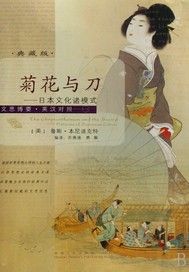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四节 故国新论
1922年,汤用彤载誉归国。其时新旧文化、中西文化、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之争日益深化,学术界无不沉浸在古史考证之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或创设历史依据。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1921年年底发行,于是掀起了一场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轩然大波。由学衡派创办的《学衡》杂志于1922年1月首刊。他们针对新文化运动只关心政治实体存亡,漠视传统文化绝续,企图以近代西方文化全面取代中国传统的偏颇之弊,标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学术宗旨,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年7月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的基础上创办支那内学院,为近代佛学之勃兴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汤用彤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中,不仅顶着硕士的光环,更重要的是挟西方文化,具体说主要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利器,并以深厚而扎实的佛学研究基础,登上中国近代学界这个大舞台,也登上了中国新式教育的讲坛。他应梅光迪、吴宓之邀,首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继而于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执教,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前后九年左右。
归国后的汤用彤,尽管难免时代大潮的裹挟,但他还是竭力保持他那知识分子的风骨。高等学府为他提供了学院式的专业史家的环境,吴宓、梅光迪等《学衡》诸友也为他开辟了学术研究的领地,使他那已经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大有用武之地。
就目前所知,汤用彤为中西文化讨论直接发表的仅有两篇文章:一是1943年1月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二期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另一篇就是汤氏自哈佛初返国土不久,发表于《中华新报》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1922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学衡》头条全文转录。如果说其后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以其人文主义为指导,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转化理论,那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则是针对当时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谬误有感而发的。他首先借西哲之言,说希腊文治之末世,患神经衰弱之症(Greek Failure of Nerves)。内则学术崩溃,外则魔教四侵,今日中国重蹈希腊神经衰弱之故辙。一则固有精神湮灭,二是饥不择食,崇拜欧美,“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率先表述了他对当时中西文化论战的不同见解。具体而言,他以为若无深入的学术研究,不了解民族文化之往史而又不能洞察欧美之实状,妄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中西文化问题,只能加重文化之衰象。所以他对此从不再做任何笼系之见,而主张“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以“通古今之变”,把学术兴趣集中在文化史的研究,并通过中外文化接触调和的历史事实,阐明他的文化转化观念。由此便不甘寂寞,把他的毕生精力,献身于学术事业之中。20世纪20年代则是他学术道路的起跑线。
可以这样说,汤氏学术道路是由讲学、著述、译介三路并进的:
其一,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佛教史”;
其二,译介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
其三,同时着手“中国佛教史”的撰著。
总之,游学归来的汤用彤立即将其人文主义思想付诸学术实践。他不仅把西学引入旧学领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西学屏障传统,借以保存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如果说,清华是汤氏文化观念的摇篮,哈佛则是助其成长的舟楫,而归国后系统表述其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汤用彤,无疑是腾跃龙门之鱼,搏击长空的海燕了。
讲授“中国佛教史”自不必详述,被国外学者称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两部精品力作,都是在此基础上成书的。正如汤氏所说:“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隋唐佛教史》讲义,亦有20世纪20年代在中央大学的油印本。由此足见,汤氏对佛教史研究的选择,是早在哈佛已经确定了的。
晚清佛学的勃兴可以上溯至乾嘉年间的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今文经学家兼治佛学,分别开创了近代佛学思辨和经世之路。石埭杨仁山继其后,创刻经处于金陵,究心佛乘,兴学育僧,广求佛典,使佛学由缁众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金陵刻经处早已成为近代佛学之重镇。欧阳竟无继承师志,于汤氏归国的同年,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始讲唯识抉择谈,学人云集。梁启超且来受业兼旬,张君劢亦负书问学”。汤用彤在南京授课之暇,也在内学院旁听欧阳氏讲授唯识学,以达到其广搜精求、触类旁通之目的。钱穆对此有较深刻的记忆,他说:“锡予在南京中大时(当为十一年或稍后,笔者注),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稍后,内院设研究部,汤氏即被聘为研究部导师,与吕澂、邱虚明、王恩洋等分别指导研究僧学习佛学。1924年上半年,汤氏同时兼任巴利文导师,指导“文典长阿含游行经演习”。同年9月至12月,讲授“金七十论解说”及“释迦时代之外道”诸课目。这些课目的讲义,以后均收入其《印度佛教史略》及其他书籍之中,有的当时已见诸《学衡》、《内学》等杂志。
汤用彤对西方文化的译介,无疑也是基于“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学术宗旨。汤氏汲汲于灌输新知,同样是针对当时“以西人为祖师”的维新者和“借外族为护符”的守旧者对外来文化“仅取其偏,失其大体”的偏颇之弊而发的。他坚信要了解不同文化在接触中冲突和调和的具体情况,非要弄清它们的本来面目不可,对中国人来说,若要取得中西文化讨论的发言权,就应当系统、全面地了解西学。所以在他一踏上故国的土地,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便致力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的引介。截至1931年汤氏转入北京大学之前,即其主要在南京执教的十来年时间里,先后在《学衡》、《内学》、《史学》等杂志发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印度哲学之起源》、《释迦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南传念安般经》等论文,宏通平正地介绍了西方(包括印度)哲学、宗教思想。
1923年5月至12月,汤氏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希腊之宗教》的译文,在《学衡》十七、十八和二十四期相继发表。前者系英人Edwin Wallace所著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英国剑桥大学出版部印行),是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大旨的通俗读物。它完整而又简要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介绍了他的伦理哲学、自然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以及本质论、心理学和美学思想,它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的入门读物。汤氏在《学衡》十七期首次发表该书译文时就说:“亚里士多德之书,必永为伦理及哲学之最好著手处。”他说的伦理和哲学当然是指西方的伦理和哲学了。
《希腊之宗教》的译文发表在1923年《学衡》的最后一期,它是英人R。W。Livingston编辑之The legacy of Greece一书中的第二篇。第一篇,吴宓译之为《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发表于《学衡》二十三期。作者认为,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基督教,渊源于希腊哲学、神话及秘密宗教。希腊哲学对于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发生发展亦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即希腊文化为西方文化的中坚或精华。我国学术界了解西方文化,首先应注意古希腊精神智慧所留遗于后世者,“借古镜今”仍然是汤氏及其《学衡》诸友介绍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
佛教原非中华民族所本有,中国佛教也是中外文化接触和涵化的结果,是印度佛教东传并经过数百年调适、顺化,最终在传统文化的整合下新的民族文化形态。因此,研究中国佛教史,尤当留意佛教发展的源头,译介印度哲学及其起源,更是汤氏义不容辞的重任了。
1924年6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之起源》一文在第三十期《学衡》上发表。文章详细分析了自释迦至商羯罗一千余年诸宗哲理赖以兴起的四个方面的学术背景,条分缕析“印度哲理进化之迹”。同时指出印度民族兼有希腊人的哲理和犹太人之出世观念,以及统治者奖励学术讨论,不滥用威力,此言论自由之功,足使“印土哲理之能大昌至二千年者”则属于历史方面的原因。“金十七论解说”、“胜宗十句义解说”则是数论派、胜论派的基本论典的翻译详释。同年发表于《内学季刊》的《释迦时代之外道》进一步把与佛教有关的数十家学说分为三系予以详说。这年2月,载于《学衡》第二十六期的《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是汤氏参照巴利文原本译介佛教上座部学说的文章。它以九心轮释生死流转与解脱之道,该文同时还有英文译文。至于《南传念安般经》却是对佛经原典的翻译与校释。安般禅原有后汉安世高所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禅法因与当时道术契合,故安译遂为汉魏学佛者所崇尚。汤氏则根据巴利文《中阿含经》原本,就其中一章“念安般经”译成《南传念安般经》,于1927年发表于《内学年刊》第四辑,它不仅比较了南北传佛教的异同,而且穷源究委,探索魏晋禅数的源头。
汤用彤从20年代初,即自回国之日起即开始撰著《中国佛教史》。《读慧皎〈高僧传〉札记》首先成文,于1930年9月发表在《史学杂志》第二卷三、四期合刊上。他认为慧皎“用功虽勤”、“搜聚甚富”,但“采录间似有误”。因此,汤氏就慧皎据以成书的79种史料,详细考订僧传内容。对慧皎书中竺法护卒年卒地、道安避乱之年、佛图澄本姓、魏太武帝毁法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将它们分作12个专题,条分缕析,提出了确凿可信的结论,首次表现了汤氏考证与科学比较的功夫。
汤氏从撰著佛教史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佛教思想的变迁兴衰之迹。他不仅广搜精求、详实考订历史资料,而且能从庞杂散乱的原始材料中理清思想发展演化的脉络。1931年4月在《史学杂志》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发表的《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以及1932年3月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三卷一期的《竺道生与涅槃学》,均属这一类的著述。后者虽发表于他调入北大之后,但依前后时间分析,该文亦当成于调入北大之前。至于1931年5月发表于《学衡》第七十五期的《唐太宗与佛教》,则充分揭示了佛教兴衰的政治背景及其与世俗趋合的特点。
可以这样认为,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隋唐佛教史稿》是在他著述《中国佛教史》这一鸿篇巨制的宏伟计划中,首先搜集资料,认真分析考证,然后将讲义纲要、单篇论文“汇成卷帙”,最终经过初稿修改补正而成书的。据汤一介回忆,汤用彤于20年代末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的初稿,当然包括两汉至隋唐的佛教史实。其中既有他发表过的单篇论文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他在中大时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史的讲义。与此同时,于1929年,汤氏即开始写作印度思想史讲稿,此即以后在北大成书的《印度哲学史略》,当然它包括了这一时期汤氏介绍印度哲学的文章。
1930年,时值蒋梦麟继蔡元培之后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次年夏,北大以英庚赔款补助特聘教授名义,延请汤用彤北上,任哲学系教授。同时至北大的还有钱穆,任教历史系,贺麟当时则与汤氏同系。至抗战爆发前,汤氏在北大除承担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的讲授外,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修改、补充工作。如前所述,他在20年代末,即在南京中大时期,就已完成了这部前后跨越近一千年有关佛教传入、兴起、鼎盛而至衰落的史实著作。调入北大后,他对初稿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修改补充。自1933、1934年始,又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定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汤氏随北大转移长沙,继至昆明西南联大。其时虽值国变,戎马生郊,汤氏随校避乱南迁,水陆兼程,备尝艰辛,然而著述甚勤,操觚不辍,终于在1938年元旦,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在长沙付梓,成就了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又一伟业。
据钱穆回忆:“民国二十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赔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他与汤用彤同时被邀北大任教,又于同时避乱南下,情同手足。五十一年后,年近九旬的钱穆,羁旅台湾地区,回忆前尘,多处涉及其与汤用彤的密切交往,特别是在北大期间。这些虽不足以弥补资料不足的缺憾,却可了解汤氏在北大生活、工作以及待人接物之一斑。
汤氏以特聘教授身份应邀北上,与老母诸家眷同居南池子寓所。钱穆初至北京,居西城潘佑荪寓邸,距北大甚远。汤氏曾赴西城潘宅专访钱穆。次日汤母继访钱穆,并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钱穆说“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开始了他们十数年的莫逆之交,即使后来远隔重洋,仍然是神交不断。至1982年《燕园论学集》出版,钱穆在海外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忆锡予》,高度评价了汤用彤的道德文章,即其为人和学术思想,情真意切地悼念亡友,饱含生死茫茫、相对无言的凄凉。
非如其著作恢弘精当,汤氏为人谦谨而落落寡合,实在是一个醇儒型的学者。在北大期间,除钱穆外,其交游者仅熊十力、蒙文通、林宰平、梁漱溟、陈寅恪,以及同系的贺麟和当时由中大转至清华的吴宓数人而已。1932年榆关事变,钱氏奉母返苏州故里,汤母亦随行南京。1933年春,钱氏只身返京,迁居南池子汤氏寓所,每日与汤氏一家共进晚餐。其时,支那内学院听讲之友熊十力自杭州来京,蒙文通亦在汤氏举荐下自开封河南大学至北大历史系任教,四人则得以时时相聚。后又有林宰平、梁漱溟间隔加入。虽然是志同道合、情意殷殷,却也难免学术上的歧见。然而,汤氏从不介入口角之战,也不阻止这些学术论争。钱穆在回忆此段生活时娓娓道来,有不少可资参考的史料。他说:
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换别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汤氏平日交往,且在交往中,即使于己专行也能保持沉默而不参与争论,尤能显示他温厚、凝重的醇儒风度。这也是在当时学术界无人能超脱的中西文化论争中,汤氏始终保持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傲岸态度和纯学术精神的缩影。当然,这是以其所建立的以古论今的独特文化整合系统为后盾的。
另外钱氏谈到他们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读起来也别有一番兴味。说一家传三世的善相之人,曾两次在梁漱溟及汤氏家钱穆居室为其三人及熊十力相,“所言皆能微中”。相士谓熊氏“麋鹿之姿”,梁氏“恐无好收场”,钱氏“精气神三者皆足”,“当能先后如一”,唯独未提及汤氏。相士之言,神秘兮兮,固然无稽,但其于四人之中独不言汤氏,或许另有隐衷。而汤氏深藏若虚,也令仅谋面两次的善相之士难测深浅,恐怕也是事实。1934年7月,在佛教史研究的同时,汤氏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老子化胡考》的全部工作。此书充分体现了科学方法和考据之学的结合,不仅证成“化胡说”的伪出,而且揭示了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透见佛道之争的文化背景。其取材之详备、论据之周密,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35年,汤氏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以哲学史和佛教思想把握北大哲学系的方向。致力于学术事业的汤用彤,自然难得“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名士情怀,居京七年,可以确知者,仅两次出游。一次与钱穆、熊十力、蒙文通三位志同道合的老友夜宿清华大学一农场。冥冥之中,白杨萧萧,凄婉动人,四人同座,至深夜始散。钱穆说:“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另一次在1936年夏,汤氏在庐峰牯岭,为其母择宅避暑,曾与钱穆同游岭上僧寺,并在方丈陪同下于竹荫蔽天的后厅中品茗,大有胜却人间无数之感。然而汤氏终日居家奉母,近在咫尺的匡庐真面目,也仅得探寻一次。
显而易见,汤用彤于抗战前北大工作期间,除积极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以外,致全力于中国佛教史的撰述及其文化整合系统的构建。继《竺道生与涅槃学》之后,又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书评札记以及年会报告等十数篇。其中有《释道安时代般若学述略》,1933年5月载《哲学论丛》;《释法瑶》,1932年载《国学季刊》五卷四号;《评唐中期净土教》,载1934年3月17日《大公报》;《读〈太平经〉书所见》,1935年载《国学季刊》五卷一号;《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1936年1月载《微妙声》三期;《汉魏佛学的两大系统》,1936年9月载《哲学评论》七卷一期;《关于肇论》,1936年载《哲学评论》七卷二期;《评日译梁〈高僧传〉——日本国译一切经史传部第七》,1937年5月载《微妙声》第八期;《中国佛教史零篇》,1937年12月载《燕京学报》二十二期。另外还有发表在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年4月号上的《〈四十二章经〉之版本》,由美国学者J。R。Ware翻译的英文全文。仅由这些文章不难看出汤氏著述之勤及其佛教史研究的大致范围。这些文章以后大多为1938年所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的章节内容。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基于佛教史研究的需要,汤氏已开始注意汉代道教的研究,并转向魏晋玄学的领域。至于对日人中国佛教典籍翻译的评述,既可以透见其佛教史研究多维比较的特点,也可以推测出,汤氏在此时,或在此以前当读过日人境野哲所著的《支那佛教史纲》,并受到蒋维乔1928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的影响。这是汤氏未尝提及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三人南下天津,数日后乘船直抵香港。在香港小住近旬,转程北上广州,又数日抵达长沙。其时日机轰炸长沙,一家于婚礼中祸从天降,尸体残骸犹挂树端,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在南岳半山圣经书院旧址,汤氏等不得不在随时都可能遭受飞机轰炸的长沙连宿三宵后,又在车站候车至深夜才得登车南下。次日午至衡州,尽管人困马乏,饥渴难忍,然而湖南风味的饭菜还是使他们难以下咽。南岳山势绵延,积雪中常见虎迹。且书院狭陋,常四人拥居一室,一灯如豆,置之座前,或读书撰著,或备课抄写,条件艰难,可想而知。然而也正是在此时即1938年元旦,汤用彤于南岳掷钵峰下,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时在南岳文学院的还有冯友兰、闻一多、吴宓、沈有鼎等。
1938年春节前,校方决定由陆路步行赴昆明,部分学生经香港,海行赴越南入滇。汤用彤等教授则由广西政府分两车载往游桂林,继分水陆两种抵阳朔,途经广西南部诸城镇,穿过镇南关而至越南河内,并由河内转赴昆明。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旧日法租界蒙自,当时已是人去楼空,仅有希腊老夫妇一对开设小旅馆一爿,守此终老。携家带口的教授皆寓居旅馆之中,汤氏等只身来联大者则两人一室,住在校舍之内。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于重庆经昆明来蒙自,北大教授集会欢迎,会上竟言联大种种不平,尝有支持汤用彤出任文学院长的动议。
同年夏,联大文学院自蒙自迁返昆明,钱穆因爱宜良山,决定一人卜居宜良。汤用彤、贺麟也念蒙自环境幽雅,故留校小住。于是他们约请吴宓、沈有鼎等共七人,借居旧时法国医院。此去空军基地不远,乃空袭危险地带,沈氏占易,得节之九二,有“不出门庭凶”的谶言。所以,汤氏七人遂晨起出门,携带干粮、茶水,择野外林石佳境,各出所携书阅读,至午后4时始归。后来果然遭受敌机空袭,城区多处轰毁,蒙自安然无恙。汤氏等在蒙自尽管日日如避乱之难民,岩居穴处,连续经旬,然而其中也有一番健身怡情的深切感受。秋季开学,汤氏、贺麟送钱穆至宜良北山岩泉下寺,遂赴昆明任事。由是获数日流连清静。
时至寒假,即1939年初,汤用彤曾偕陈寅恪同访钱穆于宜良山寺。钱穆又曾约汤氏、贺氏在宜良至昆明途中一湖附近做一日游,见湖水平漾,却无舟楫,知湖中有漩涡曾吞没两个驾舟探险的法国人,不禁谈湖色变,废然而归。另钱氏因游路南而食羊乳,归昆明告汤氏同赴城外某酒肆品尝此风味小吃,汤氏一饱口福,甚赞不绝。如此亦是学者们忙中偷闲的一段佳话。
寒去暑来,1939年暑假将至,其时昆明屡遭空袭,汤氏利用假期赴沪接从北平南下的眷属至昆明,钱氏也于此时赴香港交《国史大纲》与商务印书馆付印,再转上海归苏州探母。二人又得同行。他们绕道河内,乘海轮抵达香港,继而北上抵沪。汤氏又伴钱至苏州省亲。因钱决意在苏州奉养老母,两日后,汤氏只身返沪,并携眷南下昆明。
离昆明以后,汤用彤尝与钱穆谈及治学之事,据钱穆追忆:
锡予询余:“史纲》(即《国史大纲》,笔者注)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庚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
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此途砧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径。”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
在苏州两日,汤氏曾伴钱穆同游苏州书市,见公私书籍满街流散,甚至有一书摊,尽是西方书籍,均为东吴大学散失之书。汤用彤为钱穆择购三本,钱氏意多购,汤氏解释说:“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指钱氏预备在苏州逗留一年,笔者注),读此三书足矣。”
这是钱穆在《师友杂忆》十数则有关汤氏记载中唯一披露汤氏对治学发表的个人意见,也是汤氏唯一直抒己见之处。1943年钱穆任四川华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暑期居灌县灵岩山寺,曾就寺中方丈处借读《指月录》,加深了他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的认识。后来,他又因读胡适关于神会和尚的论述,不禁操觚为文,撰长文《神会与坛经》,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他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在香港读宝林书及少室逸书。迁居台北以后,钱氏更读宗密《原人论》诸书,及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关于禅学理论的书籍。他终续为文,一意相承,重点在于禅宗思想和理学思想传承之一大公案,同时言外旁及天台、华严两宗。这些应当说都与汤氏在1939年的那一席话有关系。所以钱穆在述及这些往事时,终难忘与汤用彤的学术切磋。他说:“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已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读起来令人总有一种“此恨终成追忆”之憾。当然,这里钱穆所述关于隋唐佛教汤氏“未遑执笔”,大概是指最终定稿付梓,因为事实上汤氏早在中央大学时期已有《隋唐佛教史》讲义的油印本,南下前已有北大铅印本了。只不过直到最后才由后人整理成书发表罢了。
汤氏自沪返滇后,继续在联大文学院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之职。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时获得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其间汤氏此书又曾在重庆出版发行(只是纸质甚劣,字迹模糊)。
如前所述,汤氏完成中国佛教史初稿后,即已开始转向魏晋玄学之研究。1938年,即在西南联大时,便着意著述魏晋玄学,至1947年在北京复校先后完成其中九篇,并在《国学季刊》、《学术季刊》、《哲学评论》、《清华学报》、《学原》、《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同时开设魏晋玄学纲领和专题等课。汤用彤自己说:
我原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想写《魏晋玄学》一书,但以后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生活颠沛流离,无法写书,只能写些短篇论文发表。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至于原来计划,本在《流别略论》一章后,应有“贵无”学说数章,除王弼外,还应有嵇康和阮籍、道安和张湛等人的“贵无”学说;对向、郭崇有义本应多加阐述;原来计划还包括《玄学与政治理论》、《玄学与文艺理论》两章。这些本都在西南联大讲过,但未写成文章。
汤一介在整理汤用彤遗著时说:“汤先生的《魏晋玄学》一书虽未完成,但仍留下大量研究成果。”这些包括四种讲课提纲,其中《魏晋玄学纲领》和《魏晋玄学专题》两种都是在西南联大时的讲义。汤用彤在西南联大关于玄学的讲授,至今有据可查的尚有1942年或1943年的《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以及《贵无之学——道安与张湛》的授课提纲等。
值得注意的是,汤氏在西南联大时,正值日寇铁蹄南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自幼深怀忧国忧民忧患意识的汤用彤,自然又涌起《哀江南》之思。但此时的汤用彤再也不会仅仅以低回吟咏悲歌兴亡所能满足,而表现出深沉的哲人气息。他既不顾欧风美雨的侵袭,也不持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笼系空洞之见,而究心于中国学术的内在生命力与内在逻辑性的探索,并寓悲愤于超逸的情怀之中,把学术研究转向了魏晋玄学领域。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于国家兴亡时局成败的关切,他则强调阮籍、嵇康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典范。在讲授玄学时一再说明他们纵情诗酒,均有所为而发,阮籍假酒回避权势,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都表现了他们立身处世的特点。于此,也可以说汤氏同样是有所为而发的。所以他虽有忧国伤时之情却难得溢于言表,常常假魏晋名士言谈之妙,虽不臧否人物,却在娓娓道来的玄学演讲中动人心弦。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已有复校之议,当时聘胡适为校长,因胡氏留美未归,由傅斯年暂代。同年《印度哲学史略》出版发行。1946年暑假,北大由昆明正式迁返北平,汤用彤亦随校复员并开始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此后除继续他的研究外,还在百忙中为哲学系开设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四门课程。1947年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议员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
北大复校直到北平解放,正是北大学潮迭起、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关键时刻。汤用彤对时局既不抱什么希望,也没有任何失望,始终融凝如一,独立不倚,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距离”,沉浸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同时也沉静地审视这时局的变化。1947年夏,他应美国加州贝克莱大学陈世骧教授之邀,专程赴加州讲授《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等。1948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又邀汤氏讲学,但是拳拳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最终还是使他婉言谢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同年9月自美国启程,返回烽火连天的华北平原。
美国讲学归来,汤氏专程赴无锡江南大学访钱穆。据钱氏回忆,汤氏“告余,倘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又不欲往”。充分显示了他那“独立不倚”的人格,以及在风云突变中的矛盾遽惶状态。但是,当北平围城战役打响,胡适乘机退走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人,胡适又来电促汤氏南下,并遣人送来全家机票时,汤氏毅然拒绝离开他的学术园地,离开这块生养他的热土。钱穆在追忆他与汤氏无锡一别时,曾无限感慨地提及这次“竟成永诀”的“一时小别”,生动地述及了汤氏拒绝离京的情形。他说:“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汤氏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称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直至1951年9月。可以认为,北大校务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机构。正因为汤用彤是一个醇儒的典范,一个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操守而且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但又不完全处在象牙塔中,而是以全部心力关注着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所以他能够在那巨变的历史条件下,新旧交接之际,被各方面所接受。也正是同样原因,1952年以后,他便离开了这一临时职务,而以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之职终其一生。同时也就离开了他熟悉的讲坛,再也未发挥他的文化观念和学术系统。他那学兼中、印、欧的学术思想,也未能再投向更大的学术工程,而不得不转向土木工地了。
据钱穆云,1937年离校前,自己曾将二十万卷的藏书寄宅主家中,抗战胜利后,未能移书南下。后北平解放,宅主托汤氏将藏书转北大存放。汤氏踌躇再三,不得不让一个与钱氏相熟的书贾以百石米价取去存藏。由此一则小事可见身为一校之首的汤氏处事之谨慎,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待人接物当可知矣。院系调整后,与汤氏共事的人以“忠厚长者”的美誉称颂这位副校长,也足见其醇儒的学者风范了。
1954年,汤氏积劳成疾,患脑溢血卧病不起,病中有特护护理。脱离危险后,仍悉心指导青年教师及研究生的教学研究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为研究生讲课。同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以之为后学提供学习和研究条件。其中有《校点高僧传》、《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另外还做了一些道教史研究工作。病中十年,仅有一些短文问世。1961年3月,应《新建设》杂志之约,集为《康复札记》,以文集形式付梓。“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题于《康复札记》题头下的这一诗句,充分表现了汤氏在迟暮之年还抱着为人民尽涓埃之力的赤诚之心。
1963年五一节晚,汤氏应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起汤氏健康恢复状况,并向毛泽东主席引见。毛泽东同样不无关怀地对他说:你的病好了,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身体不大好,就写那样的短文好了。据任继愈回忆,汤氏那天回来十分兴奋,表示要更好地把他的知识献给人民。直到他逝世,虽然在学术上他未再有显著贡献,但确实实现了“还必涓埃答圣民”的诺言。
新中国成立后,汤用彤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三届政协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汤氏脑血管病再发,5月1日,这位在教育界辛勤耕耘数十年的中国近代学术巨子,以公正、平实、精当著称的文化思想家与世长辞了。
综前所述,汤氏幼承庭训,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植入了往圣先贤的前言往行及忧国忧民的情思。二十岁以后在清华接受的新式教育,不仅没有使他同传统割裂,而且加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力图以西学翼护传统,逐渐形成反躬内省、坚定精神的理学救国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近代保守主义大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五年间异国文化的熏陶又为其文化救国的国粹思想找到了他乡故知。儒家的道德伦理哲学,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人文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纯化而为一种“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归国后的二十余年中逐渐系统化而为一种以古论今、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系统和全面立论、分疏事实、传统考证、科学比较的治学方法。同时他受白璧德、莫尔的影响,选择了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刻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并提出了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治佛教史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创造出前无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他对传统洞悉入微,却没有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他是号称“哈佛三杰”之一的美国留学生,而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因此在中西争论的大潮中融凝如一,既不以西人为祖师,赶作一些政治、社会思想的时髦文章,也不以本族为至善,视传统为无可变革的单一体系。他借雄辩的历史事实,阐明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而异军突立,同时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学术巨变的年代,也是汤用彤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可惜到50年代收获季节,他和梁漱溟这两位近代学术巨子,都被他们的同龄人——毛泽东的神圣光彩淹没得黯然失色了。
§§第二章 文化观念的系统工程建设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
归国后的汤用彤,尽管难免时代大潮的裹挟,但他还是竭力保持他那知识分子的风骨。高等学府为他提供了学院式的专业史家的环境,吴宓、梅光迪等《学衡》诸友也为他开辟了学术研究的领地,使他那已经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大有用武之地。
就目前所知,汤用彤为中西文化讨论直接发表的仅有两篇文章:一是1943年1月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二期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另一篇就是汤氏自哈佛初返国土不久,发表于《中华新报》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1922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学衡》头条全文转录。如果说其后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以其人文主义为指导,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转化理论,那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则是针对当时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谬误有感而发的。他首先借西哲之言,说希腊文治之末世,患神经衰弱之症(Greek Failure of Nerves)。内则学术崩溃,外则魔教四侵,今日中国重蹈希腊神经衰弱之故辙。一则固有精神湮灭,二是饥不择食,崇拜欧美,“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率先表述了他对当时中西文化论战的不同见解。具体而言,他以为若无深入的学术研究,不了解民族文化之往史而又不能洞察欧美之实状,妄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中西文化问题,只能加重文化之衰象。所以他对此从不再做任何笼系之见,而主张“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以“通古今之变”,把学术兴趣集中在文化史的研究,并通过中外文化接触调和的历史事实,阐明他的文化转化观念。由此便不甘寂寞,把他的毕生精力,献身于学术事业之中。20世纪20年代则是他学术道路的起跑线。
可以这样说,汤氏学术道路是由讲学、著述、译介三路并进的:
其一,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佛教史”;
其二,译介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
其三,同时着手“中国佛教史”的撰著。
总之,游学归来的汤用彤立即将其人文主义思想付诸学术实践。他不仅把西学引入旧学领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西学屏障传统,借以保存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如果说,清华是汤氏文化观念的摇篮,哈佛则是助其成长的舟楫,而归国后系统表述其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汤用彤,无疑是腾跃龙门之鱼,搏击长空的海燕了。
讲授“中国佛教史”自不必详述,被国外学者称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两部精品力作,都是在此基础上成书的。正如汤氏所说:“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隋唐佛教史》讲义,亦有20世纪20年代在中央大学的油印本。由此足见,汤氏对佛教史研究的选择,是早在哈佛已经确定了的。
晚清佛学的勃兴可以上溯至乾嘉年间的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今文经学家兼治佛学,分别开创了近代佛学思辨和经世之路。石埭杨仁山继其后,创刻经处于金陵,究心佛乘,兴学育僧,广求佛典,使佛学由缁众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金陵刻经处早已成为近代佛学之重镇。欧阳竟无继承师志,于汤氏归国的同年,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始讲唯识抉择谈,学人云集。梁启超且来受业兼旬,张君劢亦负书问学”。汤用彤在南京授课之暇,也在内学院旁听欧阳氏讲授唯识学,以达到其广搜精求、触类旁通之目的。钱穆对此有较深刻的记忆,他说:“锡予在南京中大时(当为十一年或稍后,笔者注),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稍后,内院设研究部,汤氏即被聘为研究部导师,与吕澂、邱虚明、王恩洋等分别指导研究僧学习佛学。1924年上半年,汤氏同时兼任巴利文导师,指导“文典长阿含游行经演习”。同年9月至12月,讲授“金七十论解说”及“释迦时代之外道”诸课目。这些课目的讲义,以后均收入其《印度佛教史略》及其他书籍之中,有的当时已见诸《学衡》、《内学》等杂志。
汤用彤对西方文化的译介,无疑也是基于“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学术宗旨。汤氏汲汲于灌输新知,同样是针对当时“以西人为祖师”的维新者和“借外族为护符”的守旧者对外来文化“仅取其偏,失其大体”的偏颇之弊而发的。他坚信要了解不同文化在接触中冲突和调和的具体情况,非要弄清它们的本来面目不可,对中国人来说,若要取得中西文化讨论的发言权,就应当系统、全面地了解西学。所以在他一踏上故国的土地,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便致力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的引介。截至1931年汤氏转入北京大学之前,即其主要在南京执教的十来年时间里,先后在《学衡》、《内学》、《史学》等杂志发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印度哲学之起源》、《释迦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南传念安般经》等论文,宏通平正地介绍了西方(包括印度)哲学、宗教思想。
1923年5月至12月,汤氏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希腊之宗教》的译文,在《学衡》十七、十八和二十四期相继发表。前者系英人Edwin Wallace所著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英国剑桥大学出版部印行),是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大旨的通俗读物。它完整而又简要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介绍了他的伦理哲学、自然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以及本质论、心理学和美学思想,它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的入门读物。汤氏在《学衡》十七期首次发表该书译文时就说:“亚里士多德之书,必永为伦理及哲学之最好著手处。”他说的伦理和哲学当然是指西方的伦理和哲学了。
《希腊之宗教》的译文发表在1923年《学衡》的最后一期,它是英人R。W。Livingston编辑之The legacy of Greece一书中的第二篇。第一篇,吴宓译之为《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发表于《学衡》二十三期。作者认为,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基督教,渊源于希腊哲学、神话及秘密宗教。希腊哲学对于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发生发展亦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即希腊文化为西方文化的中坚或精华。我国学术界了解西方文化,首先应注意古希腊精神智慧所留遗于后世者,“借古镜今”仍然是汤氏及其《学衡》诸友介绍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
佛教原非中华民族所本有,中国佛教也是中外文化接触和涵化的结果,是印度佛教东传并经过数百年调适、顺化,最终在传统文化的整合下新的民族文化形态。因此,研究中国佛教史,尤当留意佛教发展的源头,译介印度哲学及其起源,更是汤氏义不容辞的重任了。
1924年6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之起源》一文在第三十期《学衡》上发表。文章详细分析了自释迦至商羯罗一千余年诸宗哲理赖以兴起的四个方面的学术背景,条分缕析“印度哲理进化之迹”。同时指出印度民族兼有希腊人的哲理和犹太人之出世观念,以及统治者奖励学术讨论,不滥用威力,此言论自由之功,足使“印土哲理之能大昌至二千年者”则属于历史方面的原因。“金十七论解说”、“胜宗十句义解说”则是数论派、胜论派的基本论典的翻译详释。同年发表于《内学季刊》的《释迦时代之外道》进一步把与佛教有关的数十家学说分为三系予以详说。这年2月,载于《学衡》第二十六期的《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是汤氏参照巴利文原本译介佛教上座部学说的文章。它以九心轮释生死流转与解脱之道,该文同时还有英文译文。至于《南传念安般经》却是对佛经原典的翻译与校释。安般禅原有后汉安世高所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禅法因与当时道术契合,故安译遂为汉魏学佛者所崇尚。汤氏则根据巴利文《中阿含经》原本,就其中一章“念安般经”译成《南传念安般经》,于1927年发表于《内学年刊》第四辑,它不仅比较了南北传佛教的异同,而且穷源究委,探索魏晋禅数的源头。
汤用彤从20年代初,即自回国之日起即开始撰著《中国佛教史》。《读慧皎〈高僧传〉札记》首先成文,于1930年9月发表在《史学杂志》第二卷三、四期合刊上。他认为慧皎“用功虽勤”、“搜聚甚富”,但“采录间似有误”。因此,汤氏就慧皎据以成书的79种史料,详细考订僧传内容。对慧皎书中竺法护卒年卒地、道安避乱之年、佛图澄本姓、魏太武帝毁法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将它们分作12个专题,条分缕析,提出了确凿可信的结论,首次表现了汤氏考证与科学比较的功夫。
汤氏从撰著佛教史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佛教思想的变迁兴衰之迹。他不仅广搜精求、详实考订历史资料,而且能从庞杂散乱的原始材料中理清思想发展演化的脉络。1931年4月在《史学杂志》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发表的《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以及1932年3月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三卷一期的《竺道生与涅槃学》,均属这一类的著述。后者虽发表于他调入北大之后,但依前后时间分析,该文亦当成于调入北大之前。至于1931年5月发表于《学衡》第七十五期的《唐太宗与佛教》,则充分揭示了佛教兴衰的政治背景及其与世俗趋合的特点。
可以这样认为,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隋唐佛教史稿》是在他著述《中国佛教史》这一鸿篇巨制的宏伟计划中,首先搜集资料,认真分析考证,然后将讲义纲要、单篇论文“汇成卷帙”,最终经过初稿修改补正而成书的。据汤一介回忆,汤用彤于20年代末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的初稿,当然包括两汉至隋唐的佛教史实。其中既有他发表过的单篇论文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他在中大时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史的讲义。与此同时,于1929年,汤氏即开始写作印度思想史讲稿,此即以后在北大成书的《印度哲学史略》,当然它包括了这一时期汤氏介绍印度哲学的文章。
1930年,时值蒋梦麟继蔡元培之后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次年夏,北大以英庚赔款补助特聘教授名义,延请汤用彤北上,任哲学系教授。同时至北大的还有钱穆,任教历史系,贺麟当时则与汤氏同系。至抗战爆发前,汤氏在北大除承担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的讲授外,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修改、补充工作。如前所述,他在20年代末,即在南京中大时期,就已完成了这部前后跨越近一千年有关佛教传入、兴起、鼎盛而至衰落的史实著作。调入北大后,他对初稿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修改补充。自1933、1934年始,又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定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汤氏随北大转移长沙,继至昆明西南联大。其时虽值国变,戎马生郊,汤氏随校避乱南迁,水陆兼程,备尝艰辛,然而著述甚勤,操觚不辍,终于在1938年元旦,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在长沙付梓,成就了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又一伟业。
据钱穆回忆:“民国二十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赔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他与汤用彤同时被邀北大任教,又于同时避乱南下,情同手足。五十一年后,年近九旬的钱穆,羁旅台湾地区,回忆前尘,多处涉及其与汤用彤的密切交往,特别是在北大期间。这些虽不足以弥补资料不足的缺憾,却可了解汤氏在北大生活、工作以及待人接物之一斑。
汤氏以特聘教授身份应邀北上,与老母诸家眷同居南池子寓所。钱穆初至北京,居西城潘佑荪寓邸,距北大甚远。汤氏曾赴西城潘宅专访钱穆。次日汤母继访钱穆,并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钱穆说“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开始了他们十数年的莫逆之交,即使后来远隔重洋,仍然是神交不断。至1982年《燕园论学集》出版,钱穆在海外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忆锡予》,高度评价了汤用彤的道德文章,即其为人和学术思想,情真意切地悼念亡友,饱含生死茫茫、相对无言的凄凉。
非如其著作恢弘精当,汤氏为人谦谨而落落寡合,实在是一个醇儒型的学者。在北大期间,除钱穆外,其交游者仅熊十力、蒙文通、林宰平、梁漱溟、陈寅恪,以及同系的贺麟和当时由中大转至清华的吴宓数人而已。1932年榆关事变,钱氏奉母返苏州故里,汤母亦随行南京。1933年春,钱氏只身返京,迁居南池子汤氏寓所,每日与汤氏一家共进晚餐。其时,支那内学院听讲之友熊十力自杭州来京,蒙文通亦在汤氏举荐下自开封河南大学至北大历史系任教,四人则得以时时相聚。后又有林宰平、梁漱溟间隔加入。虽然是志同道合、情意殷殷,却也难免学术上的歧见。然而,汤氏从不介入口角之战,也不阻止这些学术论争。钱穆在回忆此段生活时娓娓道来,有不少可资参考的史料。他说:
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换别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汤氏平日交往,且在交往中,即使于己专行也能保持沉默而不参与争论,尤能显示他温厚、凝重的醇儒风度。这也是在当时学术界无人能超脱的中西文化论争中,汤氏始终保持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傲岸态度和纯学术精神的缩影。当然,这是以其所建立的以古论今的独特文化整合系统为后盾的。
另外钱氏谈到他们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读起来也别有一番兴味。说一家传三世的善相之人,曾两次在梁漱溟及汤氏家钱穆居室为其三人及熊十力相,“所言皆能微中”。相士谓熊氏“麋鹿之姿”,梁氏“恐无好收场”,钱氏“精气神三者皆足”,“当能先后如一”,唯独未提及汤氏。相士之言,神秘兮兮,固然无稽,但其于四人之中独不言汤氏,或许另有隐衷。而汤氏深藏若虚,也令仅谋面两次的善相之士难测深浅,恐怕也是事实。1934年7月,在佛教史研究的同时,汤氏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老子化胡考》的全部工作。此书充分体现了科学方法和考据之学的结合,不仅证成“化胡说”的伪出,而且揭示了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透见佛道之争的文化背景。其取材之详备、论据之周密,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35年,汤氏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以哲学史和佛教思想把握北大哲学系的方向。致力于学术事业的汤用彤,自然难得“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名士情怀,居京七年,可以确知者,仅两次出游。一次与钱穆、熊十力、蒙文通三位志同道合的老友夜宿清华大学一农场。冥冥之中,白杨萧萧,凄婉动人,四人同座,至深夜始散。钱穆说:“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另一次在1936年夏,汤氏在庐峰牯岭,为其母择宅避暑,曾与钱穆同游岭上僧寺,并在方丈陪同下于竹荫蔽天的后厅中品茗,大有胜却人间无数之感。然而汤氏终日居家奉母,近在咫尺的匡庐真面目,也仅得探寻一次。
显而易见,汤用彤于抗战前北大工作期间,除积极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以外,致全力于中国佛教史的撰述及其文化整合系统的构建。继《竺道生与涅槃学》之后,又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书评札记以及年会报告等十数篇。其中有《释道安时代般若学述略》,1933年5月载《哲学论丛》;《释法瑶》,1932年载《国学季刊》五卷四号;《评唐中期净土教》,载1934年3月17日《大公报》;《读〈太平经〉书所见》,1935年载《国学季刊》五卷一号;《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1936年1月载《微妙声》三期;《汉魏佛学的两大系统》,1936年9月载《哲学评论》七卷一期;《关于肇论》,1936年载《哲学评论》七卷二期;《评日译梁〈高僧传〉——日本国译一切经史传部第七》,1937年5月载《微妙声》第八期;《中国佛教史零篇》,1937年12月载《燕京学报》二十二期。另外还有发表在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年4月号上的《〈四十二章经〉之版本》,由美国学者J。R。Ware翻译的英文全文。仅由这些文章不难看出汤氏著述之勤及其佛教史研究的大致范围。这些文章以后大多为1938年所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的章节内容。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基于佛教史研究的需要,汤氏已开始注意汉代道教的研究,并转向魏晋玄学的领域。至于对日人中国佛教典籍翻译的评述,既可以透见其佛教史研究多维比较的特点,也可以推测出,汤氏在此时,或在此以前当读过日人境野哲所著的《支那佛教史纲》,并受到蒋维乔1928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的影响。这是汤氏未尝提及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三人南下天津,数日后乘船直抵香港。在香港小住近旬,转程北上广州,又数日抵达长沙。其时日机轰炸长沙,一家于婚礼中祸从天降,尸体残骸犹挂树端,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在南岳半山圣经书院旧址,汤氏等不得不在随时都可能遭受飞机轰炸的长沙连宿三宵后,又在车站候车至深夜才得登车南下。次日午至衡州,尽管人困马乏,饥渴难忍,然而湖南风味的饭菜还是使他们难以下咽。南岳山势绵延,积雪中常见虎迹。且书院狭陋,常四人拥居一室,一灯如豆,置之座前,或读书撰著,或备课抄写,条件艰难,可想而知。然而也正是在此时即1938年元旦,汤用彤于南岳掷钵峰下,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时在南岳文学院的还有冯友兰、闻一多、吴宓、沈有鼎等。
1938年春节前,校方决定由陆路步行赴昆明,部分学生经香港,海行赴越南入滇。汤用彤等教授则由广西政府分两车载往游桂林,继分水陆两种抵阳朔,途经广西南部诸城镇,穿过镇南关而至越南河内,并由河内转赴昆明。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旧日法租界蒙自,当时已是人去楼空,仅有希腊老夫妇一对开设小旅馆一爿,守此终老。携家带口的教授皆寓居旅馆之中,汤氏等只身来联大者则两人一室,住在校舍之内。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于重庆经昆明来蒙自,北大教授集会欢迎,会上竟言联大种种不平,尝有支持汤用彤出任文学院长的动议。
同年夏,联大文学院自蒙自迁返昆明,钱穆因爱宜良山,决定一人卜居宜良。汤用彤、贺麟也念蒙自环境幽雅,故留校小住。于是他们约请吴宓、沈有鼎等共七人,借居旧时法国医院。此去空军基地不远,乃空袭危险地带,沈氏占易,得节之九二,有“不出门庭凶”的谶言。所以,汤氏七人遂晨起出门,携带干粮、茶水,择野外林石佳境,各出所携书阅读,至午后4时始归。后来果然遭受敌机空袭,城区多处轰毁,蒙自安然无恙。汤氏等在蒙自尽管日日如避乱之难民,岩居穴处,连续经旬,然而其中也有一番健身怡情的深切感受。秋季开学,汤氏、贺麟送钱穆至宜良北山岩泉下寺,遂赴昆明任事。由是获数日流连清静。
时至寒假,即1939年初,汤用彤曾偕陈寅恪同访钱穆于宜良山寺。钱穆又曾约汤氏、贺氏在宜良至昆明途中一湖附近做一日游,见湖水平漾,却无舟楫,知湖中有漩涡曾吞没两个驾舟探险的法国人,不禁谈湖色变,废然而归。另钱氏因游路南而食羊乳,归昆明告汤氏同赴城外某酒肆品尝此风味小吃,汤氏一饱口福,甚赞不绝。如此亦是学者们忙中偷闲的一段佳话。
寒去暑来,1939年暑假将至,其时昆明屡遭空袭,汤氏利用假期赴沪接从北平南下的眷属至昆明,钱氏也于此时赴香港交《国史大纲》与商务印书馆付印,再转上海归苏州探母。二人又得同行。他们绕道河内,乘海轮抵达香港,继而北上抵沪。汤氏又伴钱至苏州省亲。因钱决意在苏州奉养老母,两日后,汤氏只身返沪,并携眷南下昆明。
离昆明以后,汤用彤尝与钱穆谈及治学之事,据钱穆追忆:
锡予询余:“史纲》(即《国史大纲》,笔者注)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庚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
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此途砧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径。”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
在苏州两日,汤氏曾伴钱穆同游苏州书市,见公私书籍满街流散,甚至有一书摊,尽是西方书籍,均为东吴大学散失之书。汤用彤为钱穆择购三本,钱氏意多购,汤氏解释说:“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指钱氏预备在苏州逗留一年,笔者注),读此三书足矣。”
这是钱穆在《师友杂忆》十数则有关汤氏记载中唯一披露汤氏对治学发表的个人意见,也是汤氏唯一直抒己见之处。1943年钱穆任四川华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暑期居灌县灵岩山寺,曾就寺中方丈处借读《指月录》,加深了他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的认识。后来,他又因读胡适关于神会和尚的论述,不禁操觚为文,撰长文《神会与坛经》,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他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在香港读宝林书及少室逸书。迁居台北以后,钱氏更读宗密《原人论》诸书,及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关于禅学理论的书籍。他终续为文,一意相承,重点在于禅宗思想和理学思想传承之一大公案,同时言外旁及天台、华严两宗。这些应当说都与汤氏在1939年的那一席话有关系。所以钱穆在述及这些往事时,终难忘与汤用彤的学术切磋。他说:“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已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读起来令人总有一种“此恨终成追忆”之憾。当然,这里钱穆所述关于隋唐佛教汤氏“未遑执笔”,大概是指最终定稿付梓,因为事实上汤氏早在中央大学时期已有《隋唐佛教史》讲义的油印本,南下前已有北大铅印本了。只不过直到最后才由后人整理成书发表罢了。
汤氏自沪返滇后,继续在联大文学院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之职。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时获得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其间汤氏此书又曾在重庆出版发行(只是纸质甚劣,字迹模糊)。
如前所述,汤氏完成中国佛教史初稿后,即已开始转向魏晋玄学之研究。1938年,即在西南联大时,便着意著述魏晋玄学,至1947年在北京复校先后完成其中九篇,并在《国学季刊》、《学术季刊》、《哲学评论》、《清华学报》、《学原》、《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同时开设魏晋玄学纲领和专题等课。汤用彤自己说:
我原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想写《魏晋玄学》一书,但以后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生活颠沛流离,无法写书,只能写些短篇论文发表。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至于原来计划,本在《流别略论》一章后,应有“贵无”学说数章,除王弼外,还应有嵇康和阮籍、道安和张湛等人的“贵无”学说;对向、郭崇有义本应多加阐述;原来计划还包括《玄学与政治理论》、《玄学与文艺理论》两章。这些本都在西南联大讲过,但未写成文章。
汤一介在整理汤用彤遗著时说:“汤先生的《魏晋玄学》一书虽未完成,但仍留下大量研究成果。”这些包括四种讲课提纲,其中《魏晋玄学纲领》和《魏晋玄学专题》两种都是在西南联大时的讲义。汤用彤在西南联大关于玄学的讲授,至今有据可查的尚有1942年或1943年的《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以及《贵无之学——道安与张湛》的授课提纲等。
值得注意的是,汤氏在西南联大时,正值日寇铁蹄南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自幼深怀忧国忧民忧患意识的汤用彤,自然又涌起《哀江南》之思。但此时的汤用彤再也不会仅仅以低回吟咏悲歌兴亡所能满足,而表现出深沉的哲人气息。他既不顾欧风美雨的侵袭,也不持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笼系空洞之见,而究心于中国学术的内在生命力与内在逻辑性的探索,并寓悲愤于超逸的情怀之中,把学术研究转向了魏晋玄学领域。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于国家兴亡时局成败的关切,他则强调阮籍、嵇康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典范。在讲授玄学时一再说明他们纵情诗酒,均有所为而发,阮籍假酒回避权势,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都表现了他们立身处世的特点。于此,也可以说汤氏同样是有所为而发的。所以他虽有忧国伤时之情却难得溢于言表,常常假魏晋名士言谈之妙,虽不臧否人物,却在娓娓道来的玄学演讲中动人心弦。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已有复校之议,当时聘胡适为校长,因胡氏留美未归,由傅斯年暂代。同年《印度哲学史略》出版发行。1946年暑假,北大由昆明正式迁返北平,汤用彤亦随校复员并开始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此后除继续他的研究外,还在百忙中为哲学系开设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四门课程。1947年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议员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
北大复校直到北平解放,正是北大学潮迭起、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关键时刻。汤用彤对时局既不抱什么希望,也没有任何失望,始终融凝如一,独立不倚,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距离”,沉浸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同时也沉静地审视这时局的变化。1947年夏,他应美国加州贝克莱大学陈世骧教授之邀,专程赴加州讲授《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等。1948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又邀汤氏讲学,但是拳拳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最终还是使他婉言谢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同年9月自美国启程,返回烽火连天的华北平原。
美国讲学归来,汤氏专程赴无锡江南大学访钱穆。据钱氏回忆,汤氏“告余,倘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又不欲往”。充分显示了他那“独立不倚”的人格,以及在风云突变中的矛盾遽惶状态。但是,当北平围城战役打响,胡适乘机退走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人,胡适又来电促汤氏南下,并遣人送来全家机票时,汤氏毅然拒绝离开他的学术园地,离开这块生养他的热土。钱穆在追忆他与汤氏无锡一别时,曾无限感慨地提及这次“竟成永诀”的“一时小别”,生动地述及了汤氏拒绝离京的情形。他说:“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汤氏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称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直至1951年9月。可以认为,北大校务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机构。正因为汤用彤是一个醇儒的典范,一个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操守而且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但又不完全处在象牙塔中,而是以全部心力关注着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所以他能够在那巨变的历史条件下,新旧交接之际,被各方面所接受。也正是同样原因,1952年以后,他便离开了这一临时职务,而以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之职终其一生。同时也就离开了他熟悉的讲坛,再也未发挥他的文化观念和学术系统。他那学兼中、印、欧的学术思想,也未能再投向更大的学术工程,而不得不转向土木工地了。
据钱穆云,1937年离校前,自己曾将二十万卷的藏书寄宅主家中,抗战胜利后,未能移书南下。后北平解放,宅主托汤氏将藏书转北大存放。汤氏踌躇再三,不得不让一个与钱氏相熟的书贾以百石米价取去存藏。由此一则小事可见身为一校之首的汤氏处事之谨慎,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待人接物当可知矣。院系调整后,与汤氏共事的人以“忠厚长者”的美誉称颂这位副校长,也足见其醇儒的学者风范了。
1954年,汤氏积劳成疾,患脑溢血卧病不起,病中有特护护理。脱离危险后,仍悉心指导青年教师及研究生的教学研究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为研究生讲课。同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以之为后学提供学习和研究条件。其中有《校点高僧传》、《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另外还做了一些道教史研究工作。病中十年,仅有一些短文问世。1961年3月,应《新建设》杂志之约,集为《康复札记》,以文集形式付梓。“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题于《康复札记》题头下的这一诗句,充分表现了汤氏在迟暮之年还抱着为人民尽涓埃之力的赤诚之心。
1963年五一节晚,汤氏应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起汤氏健康恢复状况,并向毛泽东主席引见。毛泽东同样不无关怀地对他说:你的病好了,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身体不大好,就写那样的短文好了。据任继愈回忆,汤氏那天回来十分兴奋,表示要更好地把他的知识献给人民。直到他逝世,虽然在学术上他未再有显著贡献,但确实实现了“还必涓埃答圣民”的诺言。
新中国成立后,汤用彤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三届政协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汤氏脑血管病再发,5月1日,这位在教育界辛勤耕耘数十年的中国近代学术巨子,以公正、平实、精当著称的文化思想家与世长辞了。
综前所述,汤氏幼承庭训,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植入了往圣先贤的前言往行及忧国忧民的情思。二十岁以后在清华接受的新式教育,不仅没有使他同传统割裂,而且加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力图以西学翼护传统,逐渐形成反躬内省、坚定精神的理学救国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近代保守主义大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五年间异国文化的熏陶又为其文化救国的国粹思想找到了他乡故知。儒家的道德伦理哲学,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人文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纯化而为一种“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归国后的二十余年中逐渐系统化而为一种以古论今、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系统和全面立论、分疏事实、传统考证、科学比较的治学方法。同时他受白璧德、莫尔的影响,选择了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刻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并提出了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治佛教史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创造出前无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他对传统洞悉入微,却没有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他是号称“哈佛三杰”之一的美国留学生,而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因此在中西争论的大潮中融凝如一,既不以西人为祖师,赶作一些政治、社会思想的时髦文章,也不以本族为至善,视传统为无可变革的单一体系。他借雄辩的历史事实,阐明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而异军突立,同时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学术巨变的年代,也是汤用彤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可惜到50年代收获季节,他和梁漱溟这两位近代学术巨子,都被他们的同龄人——毛泽东的神圣光彩淹没得黯然失色了。
§§第二章 文化观念的系统工程建设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