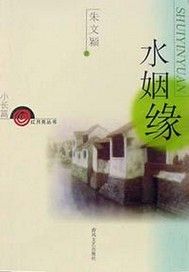第八节 卡夫卡与中国新时期荒诞小说
一
荒诞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样式。虽然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具有荒诞意味的小说曾不时溅起美丽的浪花,但由于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强度,一直到20世纪才获得命名权。首先确立荒诞小说文学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1883-1924)。人们从他的长篇小说《审判》的主人公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约瑟夫K。受到控告,但不知为什么;他想辩护,但不知辩护什么;他被判决了,但不知判决的是什么,从而认定卡夫卡是荒诞小说的始作俑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法国荒诞文学大师加缪把荒诞小说推到一个新的高度,50年代,荒诞文学进入全盛时期,荒诞派戏剧风靡世界文坛,把荒诞文学推向极致。60年代以后,荒诞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因素渗透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中。
新时期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荒诞小说。新时期以来,随着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荒诞小说,或曰荒诞品格小说。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谌容的《减去十岁》、《007337》,韩少功的《爸爸爸》,陈村的《美女岛》、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学者、评论家在寻求这些小说的外来影响时,大都把目光盯在存在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黑色幽默小说,特别是荒诞派戏剧上,而忽略了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其实,在我们看来,较之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小说和荒诞派戏剧,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有着更多的可比性。
荒诞是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来表现原因和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群体的疏离。作为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在他的《变形记》、《判决》、《审判》、《城堡》等作品中,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行为与事件莫名其妙而又不由分说地充斥其间,活动于其中的人们充满了恐惧、孤独和异化感。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流派,荒诞只是从美学品格上对一些小说的相当宽泛的描述,文学评论界也没有单独将其作为“荒诞小说”进行阐释和解读,它们分别被纳入现实主义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等类别之中,因而作为荒诞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指认。这里,我们将卡夫卡的荒诞小说作为参照系,力图从荒诞角度对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做出相对准确的解读和阐释。
二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有着相似的一面。这种相似是指抛开所有荒诞文学的共同特征(比如抽象的主题,夸张、变形的手法,反英雄式的人物等),二者之间独具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荒诞小说的创作主体,即卡夫卡和中国新时期的作家都有一种荒诞的感受,这是他们创作出荒诞小说的主观动因。首先我们来看卡夫卡的荒诞感,由于卡夫卡的荒诞感在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只有将其置于西方世界的大环境中才能把这种荒诞感看得更清楚。西方世界在卡夫卡的时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20世纪以前,科学工具还不很发达,人基本上是凭自己的感官来认识世界,这时,人对世界的认识尽管十分狭窄、肤浅,但却带给人一种稳定感和自豪感,他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现象因与他的感官相连而倍感亲切、实在。凡是他看不见、感知不到的事物,或无法解释的现象,便认为它不存在,或明智地托给神灵来管。这种井底之蛙式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渐被取代了。在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们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它也剥落了人对世界认识的人格化色彩。科学仪器和科学手段的作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使人看到、听到或推算到了无数超越于他的天生感知能力的东西:湛蓝的大海在深层潜水员的眼里五颜六色,星汉灿烂的夜空在巨型望远镜中浩瀚无边,细腻的皮肤在高倍显微镜下凹凸不平,超声波仪器可以透视人的五脏六腑……世界不再是以前人们感觉中那个熟悉、亲切、实实在在的世界了,它把一张新奇而又陌生的面孔呈现在人们面前,肉眼所见的世界与科学仪器对其的探知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在新的事实面前,人们不禁惶惑了,愕然了,一种荒诞感也就油然而生。物质的世界如此,精神的世界也同样给人以荒诞感。宗教是西方人的精神皈依,上帝是西方人的心灵慰藉,20世纪以前的西方人一直凭藉着宗教信仰获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可到了19世纪末,这种平衡与宁静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宁静感丧失了,西方人被别无选择地、不由分说地抛到精神的荒原和信仰的真空之中,一种无所适从的荒诞感像幽灵一般时时搅扰着西方人。卡夫卡恰恰出生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时代的荒诞感加上缺乏理解与关爱的家庭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田埋下了荒诞的种子,岁月的增长使这粒种子不断发芽、生长,终致使他提起笔来将其淋漓尽致地倾诉出来。
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之所以写出具有浓重荒诞意味的小说,从社会背景上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由畸形政治导致的迷惘感所致。像王蒙等老一代的作家,都经历过一些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动荡岁月,他们曾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但却不幸罹难,被抛入痛苦的深渊。乌云不能永远遮盖住太阳,拨开云雾见天日的他们痛感那段人妖颠倒的岁月的荒诞,要把那种荒诞的感受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欲望也分外强烈。像刘索拉等年轻一代作家,在“文革”期间作为运动的参加者,曾为革命理想振臂高呼过,也曾为捍卫信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挥汗如雨地奋斗过。但“文革”后,他们看到自己昔日为之献身的一切竟是如此的荒谬可笑,昔日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新的现实是如此地不相协调,一种迷惘、荒诞、无所适从的感觉在他们心头隐隐作痛,不吐不快。像韩少功等“寻根文学”作家之所以也会写出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是基于某些传统文化在新的现实面前所暴露出的荒诞性带给他们的荒诞感。我国超稳定的文化形态在历史的进程中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在新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所形成的新的衡量尺度面前,逐渐暴露出其虚伪性、腐朽性,人们发现自己原来所崇拜的竟是那样的不值得崇拜,自己虔诚的追求竟是那样的毫无价值,甚至荒诞可笑。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一些寻根文学作家的感官,他们要把这种荒诞感倾诉出来,以唤醒人们尽快摆脱传统文化中的沉疴,轻装迈进历史的新时代。
其二,从小说的结构方式上来看,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大都表现出整体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相结合的特点。
卡夫卡的许多小说,其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陪衬中心事件的细节大部分是真实的。《变形记》中除“人变甲虫”这一事件令人瞠目结舌之外,对格里高尔及其家人的心理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审判》中除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捕并申诉无门违背常理以外,他为洗清罪名四处奔走时的所见所闻都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城堡》中的城堡虽然近在眼前,K。却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是荒诞的,但他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却是真实可信的。并且,这些作品中的生活环境也是人们常见的村庄、原野、公寓,这里没有仙境,没有地狱,没有点石成金的巫师和法术,而是凡身肉胎的普通人物和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生存环境。卢卡契在评价卡夫卡的创作时说:“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最不真实的事情,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所以卡夫卡的作品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
在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中,这种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更是比比皆是。谌容的《007337》中的公共汽车没有司机、电脑的控制,却奇妙地载着乘客红灯止、绿灯行地正常运行是怪诞的、不可思议的,但处理这一事件的方法、对待这一事物的态度在生活中却是典型的、司空见惯的:面对新问题、新事物,不是认真研究对待,尽快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上推下卸,空发议论,最后不了了之。陈村的《美女岛》中的故事虽然荒诞至极,但荒诞故事的生活内容却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庸人的势利,丑女的冷遇,船长的引诱及抛弃,人一旦出名后的身价倍增,对“星”的追逐,都会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在结构上的这种相似性,和作家们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不无关系。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夫卡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对传统的背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整个传统的隔绝。正像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有很强的包容性一样,卡夫卡对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豁达的宽容精神,他对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推崇备至,特别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不止一次地赞扬狄更斯、福楼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他早期的作品现实主义风格较为明显,《美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接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连卡夫卡本人也说这是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在卡夫卡后期的创作中,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凝聚为整体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的辩证统一。真正的文学创新应该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卡夫卡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面向未来、开拓创新的同时,不忘记回首过去,拾取既往成功的艺术经验。
中国文人历来身负使命,有着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在文学上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生活;这使得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一直绵延不断,即使在某些时期发生过某些变异,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的历史观尚“通”,注重前后的承袭;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主张“中庸”,持正居中;中国的古典美学崇尚“中和之美”,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在接受新事物时,不忘记对旧事物的承继,因此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流淌着现实主义的血液。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只有关注现实的作品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认同。
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理性、综合、中庸等品格决定了中国人不易走极端,因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卡夫卡的作品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与荒诞文学发展到顶峰时的西方荒诞派戏剧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任何新出现的文学质素在其初始阶段,由于其前面剩余文化因素的强大制约,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此后,新的文学质素不断增强,剩余文化因素不断消亡,及至新的文学质素发展到顶峰,它往往因完全摆脱了先前剩余文化因素的制约而显出极端化的一面,而这种极端化的倾向和中华民族温柔敦厚、持正居中的传统是相背离的。
三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和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有着独具的相似之处,但也有着可以辨识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卡夫卡笔下的荒诞表达的是人自身存在的悲剧,是整个世界的荒诞性、全部人生的悲剧性和人类前途的渺茫性。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还没有达到对人自身内在悲剧性进行深入探索的层次,它们所表现的大多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发的内心冲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个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仍处在社会的、道德的层面上。
一个能得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普遍认同的作家必定是一个表达出人类某些共同遭际的作家。卡夫卡的所有文字--小说、箴言、书信、日记,都在探讨人类的困境,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何处有指引人类前行的光亮?这是卡夫卡毕生的自我拷问,也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幸福和真正意义之所在。卡夫卡非常渴望投入热烈的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执著于爱情和友谊。然而,他深感自己负有强烈而沉重的使命,认定自己必须思考人生而不是去享受生活,认定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求证人生的真实境况,求证生命的真正形式和意义。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不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特定现象,而是弥漫于人生的全过程。《判决》中的父子冲突不是单纯家庭内部的,而是子辈在父辈阴影下的荒诞处境;两位K。的悲剧人生,象征着人类徒劳的挣扎,预示着人类悬而未决的未来。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一是与“文革”相关,二是揭示了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荒诞性,而后者构成中国新时期荒诞小说的主体。谌容的《减去十岁》鞭笞的是特殊时代造就的荒诞现象,而更多的荒诞小说着力表现的则是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中的荒诞因素。007337号公共汽车所掀起的无稽波澜猛烈地撞击着社会生活中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保守狭隘的思维模式、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的现象以及缺乏自主意识和自控能力的领导状况。王蒙在《冬天的话题》中关于“早浴”、“晚浴”的荒诞故事,揭示出拉帮结派,动辄把问题升级,甚至上纲上线,以资历年龄论人而不是以才干禀赋论人的重现成秩序而不思变革的极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是因为中西文化有着不同的深层结构。西方文化始终以个体为本,关注人的存在本质和个体生命欲求。不可遏制的个人欲求,奔放的个性,强烈的个人意志,一开始就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主旋律,虽然黑暗的中世纪以神性来遏制人性,导致了西方文学的深厚断层,但14世纪蓬勃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文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得到恢复。自此以后,西方文学对人的生命的开掘逐渐深入,从14世纪至18世纪对人的情欲的展现,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对狂放不羁的个性的追求、批判现实主义对个人奋斗的集中展示,西方文学对人的生命展示得越来越充分。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浸润成长的卡夫卡,自然把目光集中在对个体生命、对人自身的探讨上。
到了20世纪,西方人对个体生命的探索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即人的本体世界的层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认为,人的悲剧根源不在于自然、社会等外部原因,而在人本身。人生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系统,必然会处在不断追求而又永无止境的悲剧之中,人的出生和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悲剧。深受他们影响的卡夫卡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便是罪过,生而为人是人无法逃脱的原罪。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即使变形为动物,但只要有人的思维存在,就永远逃脱不了悲剧命运的追踪。
中国传统文化执著于现世,对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的事情,如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不象西方人那样,去寻根究底,惹出无穷的烦恼。中国传统文化也十分关注人的生命,但不是西方人那种对生命本质和生存出路的探求,而是如何在现世活得更长久、更安乐。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注重由社会群体构成的社会及其规范、法则对个体生命的约束。就连衡量人的价值,也不是以他有多少独创性,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为标准,而是以他在多大程度上牺牲自我利益和个人价值,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为标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开始强调人的独特价值和个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但这种强调和发挥仍是在群体框架下的强调和发挥,必然表现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并且由于中华民族强大的务实性,执著于形而下的现世生活,对形而上的问题不甚追究,这种冲突没有上升到对人自身本质的怀疑和探讨。因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大多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上嘲笑、抨击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其政治批判、民族自审的社会内涵多于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
第二,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是悲剧性的荒诞,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是悲剧的喜剧化。虽然新时期的荒诞小说揭示了社会、历史、文化中的荒诞因素所导致的悲剧,但悲剧中有调侃、黑色幽默等喜剧因子,因而有着更多的怪诞色彩。荒诞与怪诞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把荒诞归结为人类生存的徒劳无益。银行职员约瑟夫K。最后“像一条狗一样”死去,使他所有的申诉都变成了徒劳;土地测量员K。在城堡脚下的无效奔波使他的生存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一生就像围着一个圆圈打转,从起点又回到终点,除了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销蚀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进展。卡夫卡的荒诞小说的悲剧结局都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死亡令人异常沉痛,而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他们的死是那样的悄无声息,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和不安,仿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怪诞”在本质上是乖庆和反常,它既体现出荒诞、不协调的特征,也造成一定的喜剧效果。王蒙的《冬天的话题》中,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升级为关涉国计民生的大事给人以滑稽感;谌容的《减去十岁》中,幼儿园的娃娃们“减去十岁后,我们回到哪里去”的疑问给这一荒诞事件蒙上浓重的喜剧色彩;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小个子”每日身不由己地不停地擦拭“功能圈”,石白“一道和声题要做六遍,得出六种结果”,莉莉穿着三点式练琴,森森追求“妈的力度”……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透出滑稽可笑的因素。总之,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借助蕴含于其中的喜剧因素,达到揭示和批判现实的怪诞的目的,盼望生活能从反常、怪异中解脱出来,走上正常、和谐的轨道。揭示怪诞而企图不怪诞,这是新时期荒诞小说的普遍关怀和突出意向。
这种悲、喜之别是由中西悲剧精神的不同内涵所决定的。西方有着悠久的悲剧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悲剧作为重要的文学样式便出现在文学殿堂里,在文学的摇篮期就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悲剧精神,在以后的小说、诗歌中得以延续和丰富。同时,由于西方传统文化强调对立、冲突、分化,大悲大喜朝着悲观主义、乐观主义两个极端发展,所以西方的戏剧要悲就悲得哭天恸地,要喜就喜得捧腹大笑,很少有悲喜因素的融合。虽然西方现代也出现了一些悲喜混杂的作品,但卡夫卡基本上还是属于受西方古代文化影响较大的作家,因此他的主人公大都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中国的悲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中和”传统的制约。孔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凡事强调适度、有节制,因此,中国很少有西方那种纯然的悲剧和喜剧,中国传统的悲剧意识实际上是悲喜杂糅、悲中有喜。中国古典文论中对“中和之美”的最高追求也决定了中国的悲剧往往运用辅助性、象征性的喜剧因素,来冲淡悲剧那严肃悲痛的氛围,给读者或观众以情感上的调适和慰藉。这种悲剧意识无形中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使他们的荒诞小说在揭示荒诞因素造成的种种悲剧时融合进喜剧的因子。
我们把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化圈之间文学的沟通与互补。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愈多,亲和力愈强;相异之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大。既然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大家庭”,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共性的探讨能为它们之间的友好往来提供一块基石;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差异的研究能为彼此的文学发展提供更多样化的参照和启迪。
荒诞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样式。虽然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具有荒诞意味的小说曾不时溅起美丽的浪花,但由于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强度,一直到20世纪才获得命名权。首先确立荒诞小说文学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1883-1924)。人们从他的长篇小说《审判》的主人公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约瑟夫K。受到控告,但不知为什么;他想辩护,但不知辩护什么;他被判决了,但不知判决的是什么,从而认定卡夫卡是荒诞小说的始作俑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法国荒诞文学大师加缪把荒诞小说推到一个新的高度,50年代,荒诞文学进入全盛时期,荒诞派戏剧风靡世界文坛,把荒诞文学推向极致。60年代以后,荒诞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因素渗透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中。
新时期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荒诞小说。新时期以来,随着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荒诞小说,或曰荒诞品格小说。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谌容的《减去十岁》、《007337》,韩少功的《爸爸爸》,陈村的《美女岛》、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学者、评论家在寻求这些小说的外来影响时,大都把目光盯在存在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黑色幽默小说,特别是荒诞派戏剧上,而忽略了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其实,在我们看来,较之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小说和荒诞派戏剧,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有着更多的可比性。
荒诞是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来表现原因和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群体的疏离。作为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在他的《变形记》、《判决》、《审判》、《城堡》等作品中,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行为与事件莫名其妙而又不由分说地充斥其间,活动于其中的人们充满了恐惧、孤独和异化感。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流派,荒诞只是从美学品格上对一些小说的相当宽泛的描述,文学评论界也没有单独将其作为“荒诞小说”进行阐释和解读,它们分别被纳入现实主义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等类别之中,因而作为荒诞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指认。这里,我们将卡夫卡的荒诞小说作为参照系,力图从荒诞角度对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做出相对准确的解读和阐释。
二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有着相似的一面。这种相似是指抛开所有荒诞文学的共同特征(比如抽象的主题,夸张、变形的手法,反英雄式的人物等),二者之间独具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荒诞小说的创作主体,即卡夫卡和中国新时期的作家都有一种荒诞的感受,这是他们创作出荒诞小说的主观动因。首先我们来看卡夫卡的荒诞感,由于卡夫卡的荒诞感在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只有将其置于西方世界的大环境中才能把这种荒诞感看得更清楚。西方世界在卡夫卡的时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20世纪以前,科学工具还不很发达,人基本上是凭自己的感官来认识世界,这时,人对世界的认识尽管十分狭窄、肤浅,但却带给人一种稳定感和自豪感,他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现象因与他的感官相连而倍感亲切、实在。凡是他看不见、感知不到的事物,或无法解释的现象,便认为它不存在,或明智地托给神灵来管。这种井底之蛙式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渐被取代了。在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们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它也剥落了人对世界认识的人格化色彩。科学仪器和科学手段的作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使人看到、听到或推算到了无数超越于他的天生感知能力的东西:湛蓝的大海在深层潜水员的眼里五颜六色,星汉灿烂的夜空在巨型望远镜中浩瀚无边,细腻的皮肤在高倍显微镜下凹凸不平,超声波仪器可以透视人的五脏六腑……世界不再是以前人们感觉中那个熟悉、亲切、实实在在的世界了,它把一张新奇而又陌生的面孔呈现在人们面前,肉眼所见的世界与科学仪器对其的探知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在新的事实面前,人们不禁惶惑了,愕然了,一种荒诞感也就油然而生。物质的世界如此,精神的世界也同样给人以荒诞感。宗教是西方人的精神皈依,上帝是西方人的心灵慰藉,20世纪以前的西方人一直凭藉着宗教信仰获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可到了19世纪末,这种平衡与宁静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宁静感丧失了,西方人被别无选择地、不由分说地抛到精神的荒原和信仰的真空之中,一种无所适从的荒诞感像幽灵一般时时搅扰着西方人。卡夫卡恰恰出生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时代的荒诞感加上缺乏理解与关爱的家庭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田埋下了荒诞的种子,岁月的增长使这粒种子不断发芽、生长,终致使他提起笔来将其淋漓尽致地倾诉出来。
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之所以写出具有浓重荒诞意味的小说,从社会背景上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由畸形政治导致的迷惘感所致。像王蒙等老一代的作家,都经历过一些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动荡岁月,他们曾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但却不幸罹难,被抛入痛苦的深渊。乌云不能永远遮盖住太阳,拨开云雾见天日的他们痛感那段人妖颠倒的岁月的荒诞,要把那种荒诞的感受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欲望也分外强烈。像刘索拉等年轻一代作家,在“文革”期间作为运动的参加者,曾为革命理想振臂高呼过,也曾为捍卫信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挥汗如雨地奋斗过。但“文革”后,他们看到自己昔日为之献身的一切竟是如此的荒谬可笑,昔日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新的现实是如此地不相协调,一种迷惘、荒诞、无所适从的感觉在他们心头隐隐作痛,不吐不快。像韩少功等“寻根文学”作家之所以也会写出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是基于某些传统文化在新的现实面前所暴露出的荒诞性带给他们的荒诞感。我国超稳定的文化形态在历史的进程中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在新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所形成的新的衡量尺度面前,逐渐暴露出其虚伪性、腐朽性,人们发现自己原来所崇拜的竟是那样的不值得崇拜,自己虔诚的追求竟是那样的毫无价值,甚至荒诞可笑。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一些寻根文学作家的感官,他们要把这种荒诞感倾诉出来,以唤醒人们尽快摆脱传统文化中的沉疴,轻装迈进历史的新时代。
其二,从小说的结构方式上来看,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大都表现出整体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相结合的特点。
卡夫卡的许多小说,其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陪衬中心事件的细节大部分是真实的。《变形记》中除“人变甲虫”这一事件令人瞠目结舌之外,对格里高尔及其家人的心理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审判》中除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捕并申诉无门违背常理以外,他为洗清罪名四处奔走时的所见所闻都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城堡》中的城堡虽然近在眼前,K。却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是荒诞的,但他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却是真实可信的。并且,这些作品中的生活环境也是人们常见的村庄、原野、公寓,这里没有仙境,没有地狱,没有点石成金的巫师和法术,而是凡身肉胎的普通人物和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生存环境。卢卡契在评价卡夫卡的创作时说:“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最不真实的事情,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所以卡夫卡的作品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
在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中,这种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更是比比皆是。谌容的《007337》中的公共汽车没有司机、电脑的控制,却奇妙地载着乘客红灯止、绿灯行地正常运行是怪诞的、不可思议的,但处理这一事件的方法、对待这一事物的态度在生活中却是典型的、司空见惯的:面对新问题、新事物,不是认真研究对待,尽快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上推下卸,空发议论,最后不了了之。陈村的《美女岛》中的故事虽然荒诞至极,但荒诞故事的生活内容却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庸人的势利,丑女的冷遇,船长的引诱及抛弃,人一旦出名后的身价倍增,对“星”的追逐,都会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在结构上的这种相似性,和作家们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不无关系。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夫卡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对传统的背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整个传统的隔绝。正像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有很强的包容性一样,卡夫卡对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豁达的宽容精神,他对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推崇备至,特别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不止一次地赞扬狄更斯、福楼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他早期的作品现实主义风格较为明显,《美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接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连卡夫卡本人也说这是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在卡夫卡后期的创作中,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凝聚为整体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的辩证统一。真正的文学创新应该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卡夫卡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面向未来、开拓创新的同时,不忘记回首过去,拾取既往成功的艺术经验。
中国文人历来身负使命,有着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在文学上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生活;这使得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一直绵延不断,即使在某些时期发生过某些变异,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的历史观尚“通”,注重前后的承袭;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主张“中庸”,持正居中;中国的古典美学崇尚“中和之美”,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在接受新事物时,不忘记对旧事物的承继,因此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流淌着现实主义的血液。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只有关注现实的作品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认同。
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理性、综合、中庸等品格决定了中国人不易走极端,因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卡夫卡的作品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与荒诞文学发展到顶峰时的西方荒诞派戏剧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任何新出现的文学质素在其初始阶段,由于其前面剩余文化因素的强大制约,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此后,新的文学质素不断增强,剩余文化因素不断消亡,及至新的文学质素发展到顶峰,它往往因完全摆脱了先前剩余文化因素的制约而显出极端化的一面,而这种极端化的倾向和中华民族温柔敦厚、持正居中的传统是相背离的。
三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和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有着独具的相似之处,但也有着可以辨识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卡夫卡笔下的荒诞表达的是人自身存在的悲剧,是整个世界的荒诞性、全部人生的悲剧性和人类前途的渺茫性。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还没有达到对人自身内在悲剧性进行深入探索的层次,它们所表现的大多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发的内心冲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个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仍处在社会的、道德的层面上。
一个能得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普遍认同的作家必定是一个表达出人类某些共同遭际的作家。卡夫卡的所有文字--小说、箴言、书信、日记,都在探讨人类的困境,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何处有指引人类前行的光亮?这是卡夫卡毕生的自我拷问,也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幸福和真正意义之所在。卡夫卡非常渴望投入热烈的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执著于爱情和友谊。然而,他深感自己负有强烈而沉重的使命,认定自己必须思考人生而不是去享受生活,认定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求证人生的真实境况,求证生命的真正形式和意义。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不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特定现象,而是弥漫于人生的全过程。《判决》中的父子冲突不是单纯家庭内部的,而是子辈在父辈阴影下的荒诞处境;两位K。的悲剧人生,象征着人类徒劳的挣扎,预示着人类悬而未决的未来。
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一是与“文革”相关,二是揭示了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荒诞性,而后者构成中国新时期荒诞小说的主体。谌容的《减去十岁》鞭笞的是特殊时代造就的荒诞现象,而更多的荒诞小说着力表现的则是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中的荒诞因素。007337号公共汽车所掀起的无稽波澜猛烈地撞击着社会生活中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保守狭隘的思维模式、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的现象以及缺乏自主意识和自控能力的领导状况。王蒙在《冬天的话题》中关于“早浴”、“晚浴”的荒诞故事,揭示出拉帮结派,动辄把问题升级,甚至上纲上线,以资历年龄论人而不是以才干禀赋论人的重现成秩序而不思变革的极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是因为中西文化有着不同的深层结构。西方文化始终以个体为本,关注人的存在本质和个体生命欲求。不可遏制的个人欲求,奔放的个性,强烈的个人意志,一开始就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主旋律,虽然黑暗的中世纪以神性来遏制人性,导致了西方文学的深厚断层,但14世纪蓬勃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文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得到恢复。自此以后,西方文学对人的生命的开掘逐渐深入,从14世纪至18世纪对人的情欲的展现,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对狂放不羁的个性的追求、批判现实主义对个人奋斗的集中展示,西方文学对人的生命展示得越来越充分。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浸润成长的卡夫卡,自然把目光集中在对个体生命、对人自身的探讨上。
到了20世纪,西方人对个体生命的探索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即人的本体世界的层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认为,人的悲剧根源不在于自然、社会等外部原因,而在人本身。人生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系统,必然会处在不断追求而又永无止境的悲剧之中,人的出生和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悲剧。深受他们影响的卡夫卡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便是罪过,生而为人是人无法逃脱的原罪。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即使变形为动物,但只要有人的思维存在,就永远逃脱不了悲剧命运的追踪。
中国传统文化执著于现世,对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的事情,如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不象西方人那样,去寻根究底,惹出无穷的烦恼。中国传统文化也十分关注人的生命,但不是西方人那种对生命本质和生存出路的探求,而是如何在现世活得更长久、更安乐。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注重由社会群体构成的社会及其规范、法则对个体生命的约束。就连衡量人的价值,也不是以他有多少独创性,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为标准,而是以他在多大程度上牺牲自我利益和个人价值,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为标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开始强调人的独特价值和个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但这种强调和发挥仍是在群体框架下的强调和发挥,必然表现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并且由于中华民族强大的务实性,执著于形而下的现世生活,对形而上的问题不甚追究,这种冲突没有上升到对人自身本质的怀疑和探讨。因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大多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上嘲笑、抨击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其政治批判、民族自审的社会内涵多于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
第二,卡夫卡的荒诞小说是悲剧性的荒诞,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是悲剧的喜剧化。虽然新时期的荒诞小说揭示了社会、历史、文化中的荒诞因素所导致的悲剧,但悲剧中有调侃、黑色幽默等喜剧因子,因而有着更多的怪诞色彩。荒诞与怪诞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把荒诞归结为人类生存的徒劳无益。银行职员约瑟夫K。最后“像一条狗一样”死去,使他所有的申诉都变成了徒劳;土地测量员K。在城堡脚下的无效奔波使他的生存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一生就像围着一个圆圈打转,从起点又回到终点,除了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销蚀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进展。卡夫卡的荒诞小说的悲剧结局都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死亡令人异常沉痛,而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他们的死是那样的悄无声息,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和不安,仿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怪诞”在本质上是乖庆和反常,它既体现出荒诞、不协调的特征,也造成一定的喜剧效果。王蒙的《冬天的话题》中,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升级为关涉国计民生的大事给人以滑稽感;谌容的《减去十岁》中,幼儿园的娃娃们“减去十岁后,我们回到哪里去”的疑问给这一荒诞事件蒙上浓重的喜剧色彩;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小个子”每日身不由己地不停地擦拭“功能圈”,石白“一道和声题要做六遍,得出六种结果”,莉莉穿着三点式练琴,森森追求“妈的力度”……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透出滑稽可笑的因素。总之,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借助蕴含于其中的喜剧因素,达到揭示和批判现实的怪诞的目的,盼望生活能从反常、怪异中解脱出来,走上正常、和谐的轨道。揭示怪诞而企图不怪诞,这是新时期荒诞小说的普遍关怀和突出意向。
这种悲、喜之别是由中西悲剧精神的不同内涵所决定的。西方有着悠久的悲剧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悲剧作为重要的文学样式便出现在文学殿堂里,在文学的摇篮期就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悲剧精神,在以后的小说、诗歌中得以延续和丰富。同时,由于西方传统文化强调对立、冲突、分化,大悲大喜朝着悲观主义、乐观主义两个极端发展,所以西方的戏剧要悲就悲得哭天恸地,要喜就喜得捧腹大笑,很少有悲喜因素的融合。虽然西方现代也出现了一些悲喜混杂的作品,但卡夫卡基本上还是属于受西方古代文化影响较大的作家,因此他的主人公大都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中国的悲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中和”传统的制约。孔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凡事强调适度、有节制,因此,中国很少有西方那种纯然的悲剧和喜剧,中国传统的悲剧意识实际上是悲喜杂糅、悲中有喜。中国古典文论中对“中和之美”的最高追求也决定了中国的悲剧往往运用辅助性、象征性的喜剧因素,来冲淡悲剧那严肃悲痛的氛围,给读者或观众以情感上的调适和慰藉。这种悲剧意识无形中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使他们的荒诞小说在揭示荒诞因素造成的种种悲剧时融合进喜剧的因子。
我们把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化圈之间文学的沟通与互补。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愈多,亲和力愈强;相异之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大。既然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大家庭”,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共性的探讨能为它们之间的友好往来提供一块基石;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差异的研究能为彼此的文学发展提供更多样化的参照和启迪。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中国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 2拿起来就放不下的60...
- 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
- 4章泽
- 5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 6从日记到作文
- 7西安古镇
- 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 9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伦...
- 10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科普教育 【已完结】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