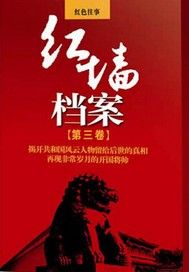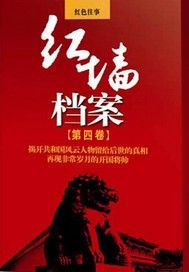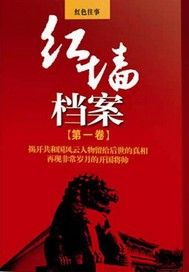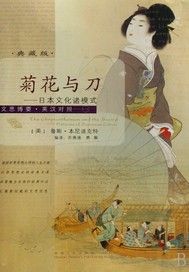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二节 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一)南诏与吐蕃的政治关系
1.天宝之战前南诏与吐蕃的政治交往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吐蕃历史上“庄严的大德王”松赞干布(《唐书》作弃宗弄赞)继位。《旧唐书·吐蕃传》说,松赞干布“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新唐书·吐蕃传》则说:“其为人慷慨才雄,常驱野马、牦牛、驰刺之以为乐,西域诸国共臣之。”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吐蕃统一了西藏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开始与内地的唐王朝进行直接的接触交往,松赞干布遣使朝贡唐朝,并请求和亲,这是吐蕃与唐朝发生关系之始。唐朝没有应允,松赞干布遂以军事强迫打开了唐朝的西后门。
吐蕃把求亲的失败归罪于吐谷浑,发兵击败了吐谷浑,又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并率其众二十万,与唐朝发生了松州(驻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之战,最终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迎得文成公主进藏。文成公主进藏后,对改善唐蕃关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与唐朝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其政治触角始终没有触及唐朝之西南边境。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其孙芒松芒赞(公元650~679年在位)继为赞普,国事皆委禄东赞家族。吐蕃开始与唐朝发生了冲突,矛盾的开始就是争夺吐谷浑(在今青海省境内)。吐谷浑是隶属于唐朝的藩国,处于唐朝与吐蕃之间,与吐蕃边境直接相连。公元663年,吐蕃攻破了吐谷浑,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公元670年,唐朝5万人与吐蕃40万人在大非川(青海惠渠南切吉旷野)展开激战,唐朝全军覆没,吐谷浑王族借助唐朝复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大非川之战使唐朝失去了西部屏障,吐蕃则获得了在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进行拓展所必需的出口及回旋空间,以及优厚的农牧资源。此后,唐朝西南边境频频遭到了吐蕃的攻打,《旧唐书》说:“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州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县)、悉(州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等州诸羌尽降之。”又“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皆在今四川阿坝州西部)。《旧唐书·吐蕃传》称其“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有鉴于此,唐朝决定加强对剑南西川的防御力量。《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条载:“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安戎城的失陷,使吐蕃势力迅速南下。有学者研究,“吐蕃接触松外诸蛮及磨些诸蛮部应是在7世纪70年代前后”,至少7世纪80年代以后,洱海地区的白蛮及部分乌蛮也投向了吐蕃。赵吕甫先生考证,自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经营洱海地区以来,至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均有双方政治往来的记载,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之后的数年间,这种记载就较稀少了。这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吐蕃势力南下的时间界限。
对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没有形成大的统一联盟的洱海各部族而言,唐朝大非川战役的失利与吐谷浑的亡国,安戎城的易主,无疑使他们认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选择依附吐蕃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政治上投向吐蕃的民族部落,有明确记载的有磨些蛮、施蛮、顺蛮、西洱河蛮,以及洱海乌蛮六诏中的施浪、浪穹、邓赕及白崖城时傍、剑川矣罗识等。吐蕃在今云南丽江塔城一带设置了神川都督府,以浪穹为据点展开对洱海各部族的经营。
吐蕃赤都松赞普执政期间(公元676~704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收黑蛮归于治下。往昔各代赞普中,其甲利兵坚,政令四被,未有能超越此王者。”公元700年,为了剪灭噶尔家族,加强对吐蕃东境的控制,赞普赤都松亲自率兵东征,几年中先后转战于河州、松州、洮州,最后于公元703年冬“绛域,攻下共地”,即到达了今云南丽江和大理鹤庆一带。“及至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赞普之死,《新唐书·吐蕃传》载为:“虏南属帐皆叛,赞普自讨,死于军。”《旧唐书·郭元振传》则载“直是其国中诸豪及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据此大致可知,由于吐蕃南边发生的叛乱,致使赤都松赞于704年再次到达了洱海地区,并死于军中。
对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政治举动,远处巍山坝子的南诏,与吐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吐蕃南下,在洱海地区形成了吐蕃与唐朝两大政治势力共存的形势。各部族处于游走依违于政治堡垒的中间,“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叛去”,此情形,在数年后的《敕吐蕃赞普书》中,唐玄宗描述道:“且西南群蛮,别是一物,既不容于我,亦不专于吐蕃,去即不追,来亦不拒,……自数十年来,或叛或附,皆所亲见。”《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敕吐普赞普书》。这种朝秦暮楚、审时度势的政治态度,乃生存需要使然。吐蕃南下后,在吐蕃的军事压力下,南诏当无可选择地受到影响。
吐蕃南下之后,浪穹诏、邓赕诏就投靠了吐蕃,而这两诏与南诏均有亲姻关系,彼此之间应是声息互通的。如果说南诏因为地处边远而与吐蕃没有联系,恐不太符合历史《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证明,皮罗阁时期仍地处巍山的南诏与吐蕃有交往的事实,可见地理位置不是南诏与吐蕃交往的阻碍。在此期间,吐蕃甚至还与南诏结成婚姻之家。《汉藏史集》说:“赤德祖赞王(公元704~754年在位)迎娶南诏妃赤尊为妻,生下了一个相貌出众的王子,起名为绛察拉本。因吐蕃境内没有能给绛察拉本王子当妻子的女子,所以派人到汉地迎娶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后因王子被暗杀,“赤德祖赞娶了公主,生子赤松德赞”达仓宗巴·。此事与汉文史料虽有诸多抵牾,但也透露了南诏与吐蕃存在亲姻关系的信息。虽然有些学者对这一条史料存在不同看法,认为“绛(vjang)”是藏族对纳西族的称呼,妃“赤尊”即“绛母赤尊”,与吐蕃联姻的是磨些族。这主要涉及到对藏文史籍中绛的理解,学者已考证,吐蕃时期vjang的范围要大得多,不可能只是丽江一带的磨些部落,而是据洱海一带的南诏。
在皮罗阁时期,南诏已经有了与吐蕃接触的迹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载:“及至鸡年(公元733年),赞普牙帐驻于准,唐廷使者李尚书,蛮(皮)罗阁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在《敕剑南节度王昱书》中也说道:“近得卿表,知蒙归义等效命出力,自讨西蛮。彼持两端,宜其残破。苟非生事,定是输忠。”《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说明唐朝对南诏“持两端”的做法,暗地里是清楚的。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朝攻下了吐蕃占领下的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县南),吐蕃惧败求和。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由于渠浪州杨盛颠作乱,唐朝派内常侍高守信进行征讨,使唐朝的势力再次深入至洱海腹地,导致了南诏与唐朝更为紧密的联系。公元733年,在金城公主的斡旋下,就在南诏出使吐蕃的同年,唐朝与吐蕃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西)立界碑重修旧好。九月,吐蕃遣大臣随汉使分往剑南等地,通告边关唐、蕃和好故事。这是唐蕃关系史上出现的第二次和好。唐朝与吐蕃关系的缓和,对处于政治夹缝中的洱海各部而言是一种释放。唐朝官方资料记载,“吐蕃请和,近与结约,群蛮翻附”,洱海地区各部族政治风向再次发生变化,唐朝又为洱海人心所向。
在这种时机下,南诏坚定地站到了唐朝一边,随后就开始对“潜通犬戎”的河蛮展开讨伐,发出了独奉唐朝的信号。事实证明,对于皮罗阁的背叛行为,吐蕃始终心怀芥蒂,并一直打算进行报复。公元735年唐朝在《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中,就对南诏进行了警告:“吐蕃于蛮,拟行报复。……比有信使,频以为词。今知其将兵,拟侵蛮落,兼拟取盐井,事似不虚。……今既如此,不可不防。”
公元733年,剑南节度王昱上书长安,唐玄宗随后在《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中对南诏进行了慰勉,并赐皮罗阁“归义”之名。所谓“归义”者,有南诏脱离吐蕃、回归正义之寓意。公元734年,皮罗阁即遣使向唐朝贡献麝香、牛黄。
赤岭划界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唐朝与吐蕃的矛盾,在随后的几年内,双方为争西洱河地争吵不休,南诏则紧密配合唐朝对吐蕃进行防范,终于在公元737年,唐朝联合南诏的力量,展开了驱逐吐蕃的战争,夺邓赕、浪穹诸地,迫使吐蕃的势力范围收缩至野共、剑川一带。
综上所述,对吐蕃势力南下后南诏一直“独奉唐朝为正朔”的观点显然没能说明事实本身,在二股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为生存需要,南诏同洱海其他部落一样,确存在过“持两端”的做法。但相比较而言,南诏与唐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紧密,尤其是在皮罗阁时期,南诏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审时度势,最终促使南诏成为唐朝的政治同盟,而与吐蕃形成政治军事的对抗。
2.从赞普钟到日东王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南诏的势力范围已经超出了洱海地区,扩大到了东至今楚雄地区,西抵澜沧江东岸,北至今剑川、鹤庆一带。可以说,在唐朝、吐蕃、南诏三者的政治博弈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南诏。
唐、诏的联合使吐蕃势力远遁剑、共,也使南诏与吐蕃的政治鸿沟越来越大,并处于敌对的状态中。例如,南诏兼并东方爨区之后,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的压制措施。《南诏德化碑》历数了云南太守张虔陀的种种做法,首要之条即是:“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可见,张虔陀背叛盟友、勾结吐蕃灭亡南诏的行径,引起南诏强烈的反感,为南诏最不可忍。
唐朝与南诏的矛盾,客观上又使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出现了转折。吐蕃赞普趁势对南诏展开了招徕,“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既以军事要挟,又以政治利益进行引诱。尽管如此,南诏还是决定保持与唐朝的联盟。在南诏看来,南诏与唐朝处于同一阵线,一旦唐、诏反目,有如鹬蚌相争,吐蕃将坐收渔利。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大兵压境,吐蕃亦屯兵边境,伺机而动。错误的战争终于将南诏推向吐蕃一方。南诏与吐蕃合兵大败唐军,胜利之后,南诏西朝献凯,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正月一日,吐蕃于邓川册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给金印,号“东帝”,授长男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吐蕃称国王为“赞普”,称兄弟为“钟”。南诏与吐蕃的联盟过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南方之东部,南诏地面,有谓白蛮子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者遂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钟’,民庶皆附庸,地域增长一倍。以南诏王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政权极为低落,且极为不安。而南诏王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均献于(赞普),临阵交战时,抓拿唐人有如屠宰羔羊一般。”
从吐蕃给予南诏兄弟之国政治礼遇的情况看,吐蕃对南诏是比较重视的,这是因为,南诏合六诏为一,兼并东方爨区后,成为唐朝西南边境最大的政治力量,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已然成为吐蕃与唐朝政治博弈的关键所在。例如,吐蕃与南诏联盟后,就合兵打败了唐朝的几次进攻,迫使唐朝的政治势力退出洱海,收缩至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一带。天宝十五、十六年(公元756、757年),南诏与吐蕃又合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共同瓜分了唐朝的巂州之地,大渡河以南之地不为唐朝所有。
南诏与吐蕃的结盟,是南诏出于政权安全需要与吐蕃结成的政治军事联盟,是一种迫于形势的政治选择,所谓南诏“北臣吐蕃”,是指在这种联盟关系中南诏因势弱而体现的从属状态。应该看到,南诏的政治、军事只有在共同对抗唐朝的前提下,才为吐蕃所驱使。从吐蕃封南诏为“赞普钟”并赐为“兄弟之国”的记载看,南诏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并且,南诏有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和稳定的疆域范围,吐蕃并不能插手南诏内部的政治事务。因此,“赞普钟”时期南诏在政治方面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双方以使节的形式展开政治往来,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出使吐蕃的南诏大臣有段忠国、阁罗(应为阁陂)等。吐蕃也派使者往来其间,例如,甚至在贞元会盟前夕,唐朝使者“催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
也有资料表明,南诏投向吐蕃后,吐蕃曾试图推行政令于南诏。其中,贡赋和征兵,从唐代前期吐蕃在洱海地区征赋的情况,以及对异牟寻时期的记载看,当一向为吐蕃所实行。对南诏的政治管理方面,吐蕃曾授阁罗凤长男凤加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僚。宠幸咸被”。但南诏的职官体系却又自成一体和吐蕃并不相同,说明了吐蕃的政治制度并未能真正推行于南诏。
吐蕃与南诏的联盟是建立在军事战略需要基础上的缺乏信任的政治联盟,这就使这种联盟具有了种种不稳定因素。异牟寻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开始恶化。公元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寇西川,欲取蜀地为吐蕃之东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唐朝大败吐蕃和南诏,战争的失利使吐蕃迁怒于南诏,并把南诏改封为“日东王”。从“赞普钟”到“日东王”,标志着南诏政治地位的下降,南诏由兄弟之邦降为一方藩王。在此之后,吐蕃开始加紧了对南诏的控制。
《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与韦皋书曰:“代祖弃背,吐蕃欺孤背约。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说明吐蕃与南诏之间曾有过约定,但具体内容已无考。从吐蕃扶持剑川利罗式对南诏形成政治威胁达十二年的记载看,此事件始于公元781年前后,为异牟寻被降为日东王之后。异牟寻紧接着叙述道:“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汙,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舌头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四难忍也。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有如偷生,实汙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跋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每虑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诏函信节,皆送蕃廷。虽知中夏至仁,业为蕃臣,吞声无诉。此四难忍也。”
上述“四忍”与“四难忍”,四次提到利罗式,则吐蕃所背之“约”当与南诏的政治安全有关。樊绰《蛮书》附录赵昌奏状说:“天宝年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虔陀谗构,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以赞普年少,信任谗佞,欲并其国。”这就证明了,至少在异牟寻继位后,吐蕃对南诏开始有了吞并之心。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墀松德赞(又名赤松德赞,公元754~796年在位)时,吐蕃“收抚于阗于治下,抚为编氓度征其贡赋,其后,白蛮南诏之部归于诏下,忽心生叛逆,时,召有庐·茹木夏拜为将军,于山巅布阵进击之时,杀南诏多人,擒获悉编掣逋等大小官员,及民庶以上三百一十二人,南诏之王阁罗(凤)亦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吐蕃陷北庭、安西,收于阗,大概在公元790年,时阁罗凤已卒,异牟寻执政,出使南诏者,或为阁罗凤之弟阁陂。
《吐蕃文书》可信度较高,所载南诏事迹,多能与汉文史籍互现。但此事件的汉文记载不甚明了。疑与《资治通鉴》载段忠义事有关。韦皋招徕南诏时,曾遣南诏旧臣段忠义至南诏,公元791年“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资治通鉴》所记与《吐蕃文书》时间上有关联,一说擒南诏官员大小官员,一说“执段忠义,并大臣子弟为质”。
吐蕃攻打南诏后,列为直属藩部户民正式征收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说明吐蕃对南诏的控制,已具有了向政治统辖方向深入的趋势,南诏的政治权利遭到严重挑战,南诏方面深知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但迫于形势,只能吞声无诉,一忍再忍。
以上说明,吐蕃与南诏联盟后不久,两者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斗争就已展开。从“赞普钟”到“日东王”,其实贯串了吐蕃对南诏政治一步步吞噬、控制一步步加深的过程,从而触及南诏的政治利益,最后激发南诏以经济、军事压迫为理由的反抗。这就是南诏自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北臣吐蕃后,最终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再次与吐蕃反目的重要原因。
3.南诏与吐蕃的再度分裂
随着唐朝“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战略的实施,在韦皋的积极招徕下,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南诏有意回归唐朝。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在会盟之前,南诏兵已出发准备袭击吐蕃。《旧唐书·南诏传》说: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征兵以袭之,仍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正月五日,南诏与唐朝苍洱会盟,十八日,寻牟寻“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遣使告捷。且请韦皋使阅其所虏获及城堡,以取信焉”。此役南诏“收铁桥已来城垒一十六,擒吐蕃王五人,归降百姓一十二万,计约三万余户”,吐蕃“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
铁桥一战吐蕃损失惨重,企图报复,南诏与吐蕃之间进入紧急战争状态。南诏既与吐蕃为仇,乃积极筹划安全之策,“异牟寻谋击吐蕃,以邓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峭山深堑修战备”。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巂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吐蕃谋袭南诏,遣军八万屯于昆明,“赞普以舅攘若罗为都统,遣尚乞力、欺徐滥铄屯西(襄)贡川”,韦皋命部将武免率弩手三千人援助异牟寻,唐军与南诏军形成南北呼应、互为犄角的阵式,大败吐蕃,“欺徐滥铄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多死,仍徙纳川,壁而待。”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朝联合回鹘、南诏等民族对吐蕃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诏与唐军深入吐蕃腹地,“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这次战争之后,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在西南战场上开始由攻转为守,与南诏形成对峙之势。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牟尼赞普逝世,其子赤德松赞继为赞普(公元804~816年在位)后,这期间吐蕃致力于与唐朝关系的改善,南诏与吐蕃之间也鲜有战事。公元816年赤德松赞逝世,其子可黎可足(赤祖德赞)继为赞普(公元816~838年在位),由于“彝泰(即赤祖德赞)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摩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日益衰落,公元821~822年,唐朝与吐蕃结成长庆会盟,互为舅甥之国,使节频相往来,双方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
公元829年11月,南诏突然置唐、诏盟约于不顾,劝丰佑遣弄栋节度王嵯巅大肆入侵西川,“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对于此次战争,一般认为是南诏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是,仔细考究史料,还会发现这次在唐、诏关系史上略显突兀的战争,与吐蕃也有一定关系。
对于被南诏掳掠的工伎,《资治通鉴》记载了西川节度李裕德向唐文宗的奏言:“……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王嵯巅入寇后,唐朝立即以李裕德负责剑南西川节度事务,其人到任后,即“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故其所言事实,当是可信。南诏以工伎金帛赂遗吐蕃,是因工伎一向为吐蕃所需。由于史料原因,王嵯巅进犯西川的原因难于考证,但此事使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又若隐若现,或可说劝丰佑时期南诏与吐蕃暗中还是有往来,出于奴隶制政权的掠夺本性,为夺取西川财富,在某些情况下双方还可以达成共识对付唐朝。的确,从南诏和吐蕃后期的历史记载来看,在西南地区双方边境平静、鲜有战事,反而是唐、蕃之间和唐、诏之间小范围的纷争时有发生。
公元842年,吐蕃陷入内乱之中,纷争不息、残破不堪,已然不能对南诏有所企图。吐蕃与南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分合合之后,双方政治关系终于走向沉寂。公元9世纪后半叶,吐蕃政权瓦解。
(二)南诏与吐蕃的经济往来
1.官方的经济往来
南诏与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献”与“贡赋”两种途径进行。《南诏德化碑》记载,天宝年间南诏击败鲜于仲通之后,“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吐蕃重酬我勋效”,回报南诏金冠、锦袍、金玉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鞻(长筒皮靴)等物品。由此可知,在南诏与吐蕃的官方之间存在着从属于政治礼仪范畴的经济交换,从交换的内容来看,大都为各自“方土所贵之物”,这是与吐蕃、南诏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
吐蕃对南诏还强迫实行贡赋的征收。如前文所述,吐蕃对南诏的经营内容,还包括了攫取南诏丰富的农牧资源的目的。南诏一度北臣吐蕃,约为兄弟之国,在此期间南诏对吐蕃承担着经济贡赋。对此,汉文史料有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亦说:墀松德赞之时,“南诏之王阁罗(应为阁陂)亦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吐蕃役赋南蛮重数”,以致南诏不堪其重,引发了南诏与吐蕃之间的矛盾。
2.民间经济往来
南诏与吐蕃地域相接,民间互通有无的经济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南诏与吐蕃重要的贸易路线有两条,《蛮书》卷二记载:“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往往有吐蕃至赕易货,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大雪山在今迈立开江上游,大赕在今坎底。则从吐蕃地界经大雪山至大赕,为吐蕃与南诏的一条经济贸易路线。
另一条路线经过南诏北部的铁桥地区直达洱海地区。《蛮书》卷七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从交易牲畜的数量来看,这一商业路线上的交易规模可谓不小,木芹先生补注说:“自古以来滇西北及康、藏地区牧业很盛,当地居民经常到洱海地区以羊等来贸易,换回盐、茶、糖、布等货,至近代也如此。”
(三)吐蕃文化对南诏的影响
就南诏与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情形而言,在双方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交往中,由于吐蕃长期占有政治军事上的优势,从而使双方的文化交流同样具有一定的倾斜性,相比较而言,吐蕃文化对南诏文化产生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制度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字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可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及与“德行”对称的“道艺”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公认的比较复杂而有系统的行为准则”,体现了一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可从属于文化范畴。
南诏北臣吐蕃的四十余年,是南诏吸收吐蕃文化的主要时期。南诏地方基层组织的设置,有明显效仿吐蕃的内容。例如,吐蕃把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按原有部落的大小划分为千户府和下千户府。千户府既是行政单位,也是军事组织机构。各千户府有百户长、千户长,千户长之外,另设部落使,作为行政长官,治理士兵(归千户长统率)之外的一般人民,下辖各种文职官吏,有征收赋税的税吏和管理狱讼的法官。四至五个千户府组成一个“支如”,“如”有“旗”、“翼”等义。每个支如设大将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南诏则把洱海周围及其附近直接控制的地区以“”为单位进行划分,同样兼有行政军事的两重功能,各内“百家以上有总佐一,千人以上有理人官一。人约万家以上,即制都督”,其中,从职官等级及所管人数来看,总佐效仿于吐蕃的百户长,理人官兼有千户长、部落使的两重职责,都督犹如吐蕃之大将,但所管人数较大将要多。
吐蕃各支如依不同颜色的旗帜来识别,南诏则“各据邑居远近”,将村社农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吐蕃还有判官专管记录将士功过,王朝据之以奖惩。与之相类似的,南诏有同伦判官,“南诏有所处分,辄疏记之”;吐蕃在出兵时派遣监军使,监视元帅和大将的行动,直接向赞普报告情况。这一点南诏与其极为相似。“每战,南诏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军前监视。有用命及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后,一一疏记回具白南诏,凭此为定赏罚。”
南诏有告身制度,与吐蕃的告身制度有一定关系。《新唐书·吐蕃传》说:“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次之,银又次之,最下至铜者,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南诏德化碑》记载,南诏“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凤伽异曾被授予“大瑟瑟告身”。吐蕃的告身制度是在对唐朝制度的借鉴模仿的基础上制定的,南诏的告身制度则是阁罗凤投蕃以后,受吐蕃影响结果。南诏告身的称谓有金告身、颇弥告身、银告身、铜告身、石告身,各分大小两类,在形式上类似于吐蕃,但在实际规定方面又与吐蕃不同,南诏告身与官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2.宗教文化
公元7世纪初,印度佛教已经传入吐蕃,经过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妥协、适应后,产生了西藏密宗。对于藏密与南诏国教阿吒力教的关系,虽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然而南诏时期西藏密宗的影响曾及于南诏却是十分明确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即载:“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
胡蔚本《南诏野史》又载天宝九载,鲜于仲通战败于西洱河后,阁罗凤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等人“并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坡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倾”。此说虽有荒诞成分,但有关阁陂和尚的记载却有文物资料可证。剑川石窟第七号窟《阁罗凤议政图》,有一位盘坐于阁罗凤旁的和尚,身穿袈裟,手执念珠,学界普遍认为是阁罗凤的弟弟阁陂和尚。信仰宗教的使者活动于南诏与吐蕃之间,无疑会为双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带来契机,故有学者认为“南诏与吐蕃的交往中,也吸收了藏传佛教的部分内容。不过要指出的是,到了公元10世纪末叶,藏密各大宗派才正式形成,因此南诏时期受吐蕃佛教的影响并不太深。”
南诏时期遗留下来的藏传佛教的建筑不多,今云南省大姚县城西文笔峰有白塔一座,此塔形制特殊,上部呈圆锥形,基座呈八角形,道光《大姚县志》卷一载此塔“相传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汪宁生先生也认为从“塔的形制来说,确与内地塔不同,似原为藏塔,而后失去其顶”。
1.天宝之战前南诏与吐蕃的政治交往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吐蕃历史上“庄严的大德王”松赞干布(《唐书》作弃宗弄赞)继位。《旧唐书·吐蕃传》说,松赞干布“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新唐书·吐蕃传》则说:“其为人慷慨才雄,常驱野马、牦牛、驰刺之以为乐,西域诸国共臣之。”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吐蕃统一了西藏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开始与内地的唐王朝进行直接的接触交往,松赞干布遣使朝贡唐朝,并请求和亲,这是吐蕃与唐朝发生关系之始。唐朝没有应允,松赞干布遂以军事强迫打开了唐朝的西后门。
吐蕃把求亲的失败归罪于吐谷浑,发兵击败了吐谷浑,又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并率其众二十万,与唐朝发生了松州(驻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之战,最终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迎得文成公主进藏。文成公主进藏后,对改善唐蕃关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与唐朝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其政治触角始终没有触及唐朝之西南边境。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其孙芒松芒赞(公元650~679年在位)继为赞普,国事皆委禄东赞家族。吐蕃开始与唐朝发生了冲突,矛盾的开始就是争夺吐谷浑(在今青海省境内)。吐谷浑是隶属于唐朝的藩国,处于唐朝与吐蕃之间,与吐蕃边境直接相连。公元663年,吐蕃攻破了吐谷浑,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公元670年,唐朝5万人与吐蕃40万人在大非川(青海惠渠南切吉旷野)展开激战,唐朝全军覆没,吐谷浑王族借助唐朝复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大非川之战使唐朝失去了西部屏障,吐蕃则获得了在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进行拓展所必需的出口及回旋空间,以及优厚的农牧资源。此后,唐朝西南边境频频遭到了吐蕃的攻打,《旧唐书》说:“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州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县)、悉(州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等州诸羌尽降之。”又“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皆在今四川阿坝州西部)。《旧唐书·吐蕃传》称其“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有鉴于此,唐朝决定加强对剑南西川的防御力量。《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条载:“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安戎城的失陷,使吐蕃势力迅速南下。有学者研究,“吐蕃接触松外诸蛮及磨些诸蛮部应是在7世纪70年代前后”,至少7世纪80年代以后,洱海地区的白蛮及部分乌蛮也投向了吐蕃。赵吕甫先生考证,自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经营洱海地区以来,至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均有双方政治往来的记载,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之后的数年间,这种记载就较稀少了。这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吐蕃势力南下的时间界限。
对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没有形成大的统一联盟的洱海各部族而言,唐朝大非川战役的失利与吐谷浑的亡国,安戎城的易主,无疑使他们认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选择依附吐蕃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政治上投向吐蕃的民族部落,有明确记载的有磨些蛮、施蛮、顺蛮、西洱河蛮,以及洱海乌蛮六诏中的施浪、浪穹、邓赕及白崖城时傍、剑川矣罗识等。吐蕃在今云南丽江塔城一带设置了神川都督府,以浪穹为据点展开对洱海各部族的经营。
吐蕃赤都松赞普执政期间(公元676~704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收黑蛮归于治下。往昔各代赞普中,其甲利兵坚,政令四被,未有能超越此王者。”公元700年,为了剪灭噶尔家族,加强对吐蕃东境的控制,赞普赤都松亲自率兵东征,几年中先后转战于河州、松州、洮州,最后于公元703年冬“绛域,攻下共地”,即到达了今云南丽江和大理鹤庆一带。“及至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赞普之死,《新唐书·吐蕃传》载为:“虏南属帐皆叛,赞普自讨,死于军。”《旧唐书·郭元振传》则载“直是其国中诸豪及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据此大致可知,由于吐蕃南边发生的叛乱,致使赤都松赞于704年再次到达了洱海地区,并死于军中。
对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政治举动,远处巍山坝子的南诏,与吐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吐蕃南下,在洱海地区形成了吐蕃与唐朝两大政治势力共存的形势。各部族处于游走依违于政治堡垒的中间,“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叛去”,此情形,在数年后的《敕吐蕃赞普书》中,唐玄宗描述道:“且西南群蛮,别是一物,既不容于我,亦不专于吐蕃,去即不追,来亦不拒,……自数十年来,或叛或附,皆所亲见。”《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敕吐普赞普书》。这种朝秦暮楚、审时度势的政治态度,乃生存需要使然。吐蕃南下后,在吐蕃的军事压力下,南诏当无可选择地受到影响。
吐蕃南下之后,浪穹诏、邓赕诏就投靠了吐蕃,而这两诏与南诏均有亲姻关系,彼此之间应是声息互通的。如果说南诏因为地处边远而与吐蕃没有联系,恐不太符合历史《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证明,皮罗阁时期仍地处巍山的南诏与吐蕃有交往的事实,可见地理位置不是南诏与吐蕃交往的阻碍。在此期间,吐蕃甚至还与南诏结成婚姻之家。《汉藏史集》说:“赤德祖赞王(公元704~754年在位)迎娶南诏妃赤尊为妻,生下了一个相貌出众的王子,起名为绛察拉本。因吐蕃境内没有能给绛察拉本王子当妻子的女子,所以派人到汉地迎娶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后因王子被暗杀,“赤德祖赞娶了公主,生子赤松德赞”达仓宗巴·。此事与汉文史料虽有诸多抵牾,但也透露了南诏与吐蕃存在亲姻关系的信息。虽然有些学者对这一条史料存在不同看法,认为“绛(vjang)”是藏族对纳西族的称呼,妃“赤尊”即“绛母赤尊”,与吐蕃联姻的是磨些族。这主要涉及到对藏文史籍中绛的理解,学者已考证,吐蕃时期vjang的范围要大得多,不可能只是丽江一带的磨些部落,而是据洱海一带的南诏。
在皮罗阁时期,南诏已经有了与吐蕃接触的迹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载:“及至鸡年(公元733年),赞普牙帐驻于准,唐廷使者李尚书,蛮(皮)罗阁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在《敕剑南节度王昱书》中也说道:“近得卿表,知蒙归义等效命出力,自讨西蛮。彼持两端,宜其残破。苟非生事,定是输忠。”《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说明唐朝对南诏“持两端”的做法,暗地里是清楚的。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朝攻下了吐蕃占领下的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县南),吐蕃惧败求和。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由于渠浪州杨盛颠作乱,唐朝派内常侍高守信进行征讨,使唐朝的势力再次深入至洱海腹地,导致了南诏与唐朝更为紧密的联系。公元733年,在金城公主的斡旋下,就在南诏出使吐蕃的同年,唐朝与吐蕃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西)立界碑重修旧好。九月,吐蕃遣大臣随汉使分往剑南等地,通告边关唐、蕃和好故事。这是唐蕃关系史上出现的第二次和好。唐朝与吐蕃关系的缓和,对处于政治夹缝中的洱海各部而言是一种释放。唐朝官方资料记载,“吐蕃请和,近与结约,群蛮翻附”,洱海地区各部族政治风向再次发生变化,唐朝又为洱海人心所向。
在这种时机下,南诏坚定地站到了唐朝一边,随后就开始对“潜通犬戎”的河蛮展开讨伐,发出了独奉唐朝的信号。事实证明,对于皮罗阁的背叛行为,吐蕃始终心怀芥蒂,并一直打算进行报复。公元735年唐朝在《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中,就对南诏进行了警告:“吐蕃于蛮,拟行报复。……比有信使,频以为词。今知其将兵,拟侵蛮落,兼拟取盐井,事似不虚。……今既如此,不可不防。”
公元733年,剑南节度王昱上书长安,唐玄宗随后在《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中对南诏进行了慰勉,并赐皮罗阁“归义”之名。所谓“归义”者,有南诏脱离吐蕃、回归正义之寓意。公元734年,皮罗阁即遣使向唐朝贡献麝香、牛黄。
赤岭划界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唐朝与吐蕃的矛盾,在随后的几年内,双方为争西洱河地争吵不休,南诏则紧密配合唐朝对吐蕃进行防范,终于在公元737年,唐朝联合南诏的力量,展开了驱逐吐蕃的战争,夺邓赕、浪穹诸地,迫使吐蕃的势力范围收缩至野共、剑川一带。
综上所述,对吐蕃势力南下后南诏一直“独奉唐朝为正朔”的观点显然没能说明事实本身,在二股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为生存需要,南诏同洱海其他部落一样,确存在过“持两端”的做法。但相比较而言,南诏与唐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紧密,尤其是在皮罗阁时期,南诏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审时度势,最终促使南诏成为唐朝的政治同盟,而与吐蕃形成政治军事的对抗。
2.从赞普钟到日东王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南诏的势力范围已经超出了洱海地区,扩大到了东至今楚雄地区,西抵澜沧江东岸,北至今剑川、鹤庆一带。可以说,在唐朝、吐蕃、南诏三者的政治博弈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南诏。
唐、诏的联合使吐蕃势力远遁剑、共,也使南诏与吐蕃的政治鸿沟越来越大,并处于敌对的状态中。例如,南诏兼并东方爨区之后,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的压制措施。《南诏德化碑》历数了云南太守张虔陀的种种做法,首要之条即是:“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可见,张虔陀背叛盟友、勾结吐蕃灭亡南诏的行径,引起南诏强烈的反感,为南诏最不可忍。
唐朝与南诏的矛盾,客观上又使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出现了转折。吐蕃赞普趁势对南诏展开了招徕,“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既以军事要挟,又以政治利益进行引诱。尽管如此,南诏还是决定保持与唐朝的联盟。在南诏看来,南诏与唐朝处于同一阵线,一旦唐、诏反目,有如鹬蚌相争,吐蕃将坐收渔利。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大兵压境,吐蕃亦屯兵边境,伺机而动。错误的战争终于将南诏推向吐蕃一方。南诏与吐蕃合兵大败唐军,胜利之后,南诏西朝献凯,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正月一日,吐蕃于邓川册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给金印,号“东帝”,授长男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吐蕃称国王为“赞普”,称兄弟为“钟”。南诏与吐蕃的联盟过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南方之东部,南诏地面,有谓白蛮子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者遂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钟’,民庶皆附庸,地域增长一倍。以南诏王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政权极为低落,且极为不安。而南诏王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均献于(赞普),临阵交战时,抓拿唐人有如屠宰羔羊一般。”
从吐蕃给予南诏兄弟之国政治礼遇的情况看,吐蕃对南诏是比较重视的,这是因为,南诏合六诏为一,兼并东方爨区后,成为唐朝西南边境最大的政治力量,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已然成为吐蕃与唐朝政治博弈的关键所在。例如,吐蕃与南诏联盟后,就合兵打败了唐朝的几次进攻,迫使唐朝的政治势力退出洱海,收缩至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一带。天宝十五、十六年(公元756、757年),南诏与吐蕃又合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共同瓜分了唐朝的巂州之地,大渡河以南之地不为唐朝所有。
南诏与吐蕃的结盟,是南诏出于政权安全需要与吐蕃结成的政治军事联盟,是一种迫于形势的政治选择,所谓南诏“北臣吐蕃”,是指在这种联盟关系中南诏因势弱而体现的从属状态。应该看到,南诏的政治、军事只有在共同对抗唐朝的前提下,才为吐蕃所驱使。从吐蕃封南诏为“赞普钟”并赐为“兄弟之国”的记载看,南诏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并且,南诏有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和稳定的疆域范围,吐蕃并不能插手南诏内部的政治事务。因此,“赞普钟”时期南诏在政治方面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双方以使节的形式展开政治往来,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出使吐蕃的南诏大臣有段忠国、阁罗(应为阁陂)等。吐蕃也派使者往来其间,例如,甚至在贞元会盟前夕,唐朝使者“催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
也有资料表明,南诏投向吐蕃后,吐蕃曾试图推行政令于南诏。其中,贡赋和征兵,从唐代前期吐蕃在洱海地区征赋的情况,以及对异牟寻时期的记载看,当一向为吐蕃所实行。对南诏的政治管理方面,吐蕃曾授阁罗凤长男凤加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僚。宠幸咸被”。但南诏的职官体系却又自成一体和吐蕃并不相同,说明了吐蕃的政治制度并未能真正推行于南诏。
吐蕃与南诏的联盟是建立在军事战略需要基础上的缺乏信任的政治联盟,这就使这种联盟具有了种种不稳定因素。异牟寻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开始恶化。公元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寇西川,欲取蜀地为吐蕃之东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唐朝大败吐蕃和南诏,战争的失利使吐蕃迁怒于南诏,并把南诏改封为“日东王”。从“赞普钟”到“日东王”,标志着南诏政治地位的下降,南诏由兄弟之邦降为一方藩王。在此之后,吐蕃开始加紧了对南诏的控制。
《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与韦皋书曰:“代祖弃背,吐蕃欺孤背约。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说明吐蕃与南诏之间曾有过约定,但具体内容已无考。从吐蕃扶持剑川利罗式对南诏形成政治威胁达十二年的记载看,此事件始于公元781年前后,为异牟寻被降为日东王之后。异牟寻紧接着叙述道:“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汙,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舌头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四难忍也。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有如偷生,实汙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跋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每虑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诏函信节,皆送蕃廷。虽知中夏至仁,业为蕃臣,吞声无诉。此四难忍也。”
上述“四忍”与“四难忍”,四次提到利罗式,则吐蕃所背之“约”当与南诏的政治安全有关。樊绰《蛮书》附录赵昌奏状说:“天宝年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虔陀谗构,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以赞普年少,信任谗佞,欲并其国。”这就证明了,至少在异牟寻继位后,吐蕃对南诏开始有了吞并之心。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墀松德赞(又名赤松德赞,公元754~796年在位)时,吐蕃“收抚于阗于治下,抚为编氓度征其贡赋,其后,白蛮南诏之部归于诏下,忽心生叛逆,时,召有庐·茹木夏拜为将军,于山巅布阵进击之时,杀南诏多人,擒获悉编掣逋等大小官员,及民庶以上三百一十二人,南诏之王阁罗(凤)亦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吐蕃陷北庭、安西,收于阗,大概在公元790年,时阁罗凤已卒,异牟寻执政,出使南诏者,或为阁罗凤之弟阁陂。
《吐蕃文书》可信度较高,所载南诏事迹,多能与汉文史籍互现。但此事件的汉文记载不甚明了。疑与《资治通鉴》载段忠义事有关。韦皋招徕南诏时,曾遣南诏旧臣段忠义至南诏,公元791年“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资治通鉴》所记与《吐蕃文书》时间上有关联,一说擒南诏官员大小官员,一说“执段忠义,并大臣子弟为质”。
吐蕃攻打南诏后,列为直属藩部户民正式征收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说明吐蕃对南诏的控制,已具有了向政治统辖方向深入的趋势,南诏的政治权利遭到严重挑战,南诏方面深知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但迫于形势,只能吞声无诉,一忍再忍。
以上说明,吐蕃与南诏联盟后不久,两者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斗争就已展开。从“赞普钟”到“日东王”,其实贯串了吐蕃对南诏政治一步步吞噬、控制一步步加深的过程,从而触及南诏的政治利益,最后激发南诏以经济、军事压迫为理由的反抗。这就是南诏自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北臣吐蕃后,最终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再次与吐蕃反目的重要原因。
3.南诏与吐蕃的再度分裂
随着唐朝“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战略的实施,在韦皋的积极招徕下,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南诏有意回归唐朝。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在会盟之前,南诏兵已出发准备袭击吐蕃。《旧唐书·南诏传》说: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征兵以袭之,仍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正月五日,南诏与唐朝苍洱会盟,十八日,寻牟寻“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遣使告捷。且请韦皋使阅其所虏获及城堡,以取信焉”。此役南诏“收铁桥已来城垒一十六,擒吐蕃王五人,归降百姓一十二万,计约三万余户”,吐蕃“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
铁桥一战吐蕃损失惨重,企图报复,南诏与吐蕃之间进入紧急战争状态。南诏既与吐蕃为仇,乃积极筹划安全之策,“异牟寻谋击吐蕃,以邓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峭山深堑修战备”。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巂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吐蕃谋袭南诏,遣军八万屯于昆明,“赞普以舅攘若罗为都统,遣尚乞力、欺徐滥铄屯西(襄)贡川”,韦皋命部将武免率弩手三千人援助异牟寻,唐军与南诏军形成南北呼应、互为犄角的阵式,大败吐蕃,“欺徐滥铄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多死,仍徙纳川,壁而待。”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朝联合回鹘、南诏等民族对吐蕃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诏与唐军深入吐蕃腹地,“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这次战争之后,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在西南战场上开始由攻转为守,与南诏形成对峙之势。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牟尼赞普逝世,其子赤德松赞继为赞普(公元804~816年在位)后,这期间吐蕃致力于与唐朝关系的改善,南诏与吐蕃之间也鲜有战事。公元816年赤德松赞逝世,其子可黎可足(赤祖德赞)继为赞普(公元816~838年在位),由于“彝泰(即赤祖德赞)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摩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日益衰落,公元821~822年,唐朝与吐蕃结成长庆会盟,互为舅甥之国,使节频相往来,双方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
公元829年11月,南诏突然置唐、诏盟约于不顾,劝丰佑遣弄栋节度王嵯巅大肆入侵西川,“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对于此次战争,一般认为是南诏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是,仔细考究史料,还会发现这次在唐、诏关系史上略显突兀的战争,与吐蕃也有一定关系。
对于被南诏掳掠的工伎,《资治通鉴》记载了西川节度李裕德向唐文宗的奏言:“……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王嵯巅入寇后,唐朝立即以李裕德负责剑南西川节度事务,其人到任后,即“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故其所言事实,当是可信。南诏以工伎金帛赂遗吐蕃,是因工伎一向为吐蕃所需。由于史料原因,王嵯巅进犯西川的原因难于考证,但此事使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又若隐若现,或可说劝丰佑时期南诏与吐蕃暗中还是有往来,出于奴隶制政权的掠夺本性,为夺取西川财富,在某些情况下双方还可以达成共识对付唐朝。的确,从南诏和吐蕃后期的历史记载来看,在西南地区双方边境平静、鲜有战事,反而是唐、蕃之间和唐、诏之间小范围的纷争时有发生。
公元842年,吐蕃陷入内乱之中,纷争不息、残破不堪,已然不能对南诏有所企图。吐蕃与南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分合合之后,双方政治关系终于走向沉寂。公元9世纪后半叶,吐蕃政权瓦解。
(二)南诏与吐蕃的经济往来
1.官方的经济往来
南诏与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献”与“贡赋”两种途径进行。《南诏德化碑》记载,天宝年间南诏击败鲜于仲通之后,“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吐蕃重酬我勋效”,回报南诏金冠、锦袍、金玉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鞻(长筒皮靴)等物品。由此可知,在南诏与吐蕃的官方之间存在着从属于政治礼仪范畴的经济交换,从交换的内容来看,大都为各自“方土所贵之物”,这是与吐蕃、南诏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
吐蕃对南诏还强迫实行贡赋的征收。如前文所述,吐蕃对南诏的经营内容,还包括了攫取南诏丰富的农牧资源的目的。南诏一度北臣吐蕃,约为兄弟之国,在此期间南诏对吐蕃承担着经济贡赋。对此,汉文史料有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亦说:墀松德赞之时,“南诏之王阁罗(应为阁陂)亦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吐蕃役赋南蛮重数”,以致南诏不堪其重,引发了南诏与吐蕃之间的矛盾。
2.民间经济往来
南诏与吐蕃地域相接,民间互通有无的经济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南诏与吐蕃重要的贸易路线有两条,《蛮书》卷二记载:“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往往有吐蕃至赕易货,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大雪山在今迈立开江上游,大赕在今坎底。则从吐蕃地界经大雪山至大赕,为吐蕃与南诏的一条经济贸易路线。
另一条路线经过南诏北部的铁桥地区直达洱海地区。《蛮书》卷七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从交易牲畜的数量来看,这一商业路线上的交易规模可谓不小,木芹先生补注说:“自古以来滇西北及康、藏地区牧业很盛,当地居民经常到洱海地区以羊等来贸易,换回盐、茶、糖、布等货,至近代也如此。”
(三)吐蕃文化对南诏的影响
就南诏与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情形而言,在双方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交往中,由于吐蕃长期占有政治军事上的优势,从而使双方的文化交流同样具有一定的倾斜性,相比较而言,吐蕃文化对南诏文化产生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制度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字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可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及与“德行”对称的“道艺”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公认的比较复杂而有系统的行为准则”,体现了一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可从属于文化范畴。
南诏北臣吐蕃的四十余年,是南诏吸收吐蕃文化的主要时期。南诏地方基层组织的设置,有明显效仿吐蕃的内容。例如,吐蕃把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按原有部落的大小划分为千户府和下千户府。千户府既是行政单位,也是军事组织机构。各千户府有百户长、千户长,千户长之外,另设部落使,作为行政长官,治理士兵(归千户长统率)之外的一般人民,下辖各种文职官吏,有征收赋税的税吏和管理狱讼的法官。四至五个千户府组成一个“支如”,“如”有“旗”、“翼”等义。每个支如设大将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南诏则把洱海周围及其附近直接控制的地区以“”为单位进行划分,同样兼有行政军事的两重功能,各内“百家以上有总佐一,千人以上有理人官一。人约万家以上,即制都督”,其中,从职官等级及所管人数来看,总佐效仿于吐蕃的百户长,理人官兼有千户长、部落使的两重职责,都督犹如吐蕃之大将,但所管人数较大将要多。
吐蕃各支如依不同颜色的旗帜来识别,南诏则“各据邑居远近”,将村社农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吐蕃还有判官专管记录将士功过,王朝据之以奖惩。与之相类似的,南诏有同伦判官,“南诏有所处分,辄疏记之”;吐蕃在出兵时派遣监军使,监视元帅和大将的行动,直接向赞普报告情况。这一点南诏与其极为相似。“每战,南诏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军前监视。有用命及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后,一一疏记回具白南诏,凭此为定赏罚。”
南诏有告身制度,与吐蕃的告身制度有一定关系。《新唐书·吐蕃传》说:“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次之,银又次之,最下至铜者,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南诏德化碑》记载,南诏“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凤伽异曾被授予“大瑟瑟告身”。吐蕃的告身制度是在对唐朝制度的借鉴模仿的基础上制定的,南诏的告身制度则是阁罗凤投蕃以后,受吐蕃影响结果。南诏告身的称谓有金告身、颇弥告身、银告身、铜告身、石告身,各分大小两类,在形式上类似于吐蕃,但在实际规定方面又与吐蕃不同,南诏告身与官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2.宗教文化
公元7世纪初,印度佛教已经传入吐蕃,经过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妥协、适应后,产生了西藏密宗。对于藏密与南诏国教阿吒力教的关系,虽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然而南诏时期西藏密宗的影响曾及于南诏却是十分明确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即载:“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
胡蔚本《南诏野史》又载天宝九载,鲜于仲通战败于西洱河后,阁罗凤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等人“并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坡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倾”。此说虽有荒诞成分,但有关阁陂和尚的记载却有文物资料可证。剑川石窟第七号窟《阁罗凤议政图》,有一位盘坐于阁罗凤旁的和尚,身穿袈裟,手执念珠,学界普遍认为是阁罗凤的弟弟阁陂和尚。信仰宗教的使者活动于南诏与吐蕃之间,无疑会为双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带来契机,故有学者认为“南诏与吐蕃的交往中,也吸收了藏传佛教的部分内容。不过要指出的是,到了公元10世纪末叶,藏密各大宗派才正式形成,因此南诏时期受吐蕃佛教的影响并不太深。”
南诏时期遗留下来的藏传佛教的建筑不多,今云南省大姚县城西文笔峰有白塔一座,此塔形制特殊,上部呈圆锥形,基座呈八角形,道光《大姚县志》卷一载此塔“相传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汪宁生先生也认为从“塔的形制来说,确与内地塔不同,似原为藏塔,而后失去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