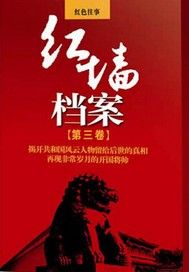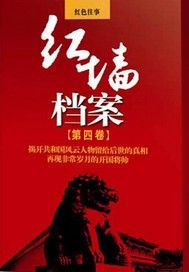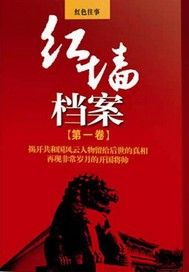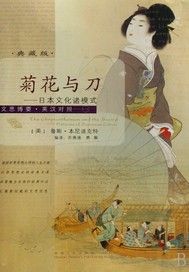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人生真谛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尔斯泰传
> 激变之后
激变之后
1881年秋天,托尔斯泰全家迁居莫斯科。这是早就决定了的事。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大儿子谢尔盖已满18岁,想报考莫斯科大学。大女儿塔尼娅17岁,爱好绘画,想进莫斯科美术雕塑学校深造。另两个男孩也要上中学。托尔斯泰虽然同意移居,但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对于故乡的感情,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表达过:
“没有雅斯纳亚·波良纳,我很难想象俄罗斯,也很难想象我和它的关系。没有雅斯纳亚·波良纳,我也许能对我的祖国赖以形成的那些共同规律看得更为清楚,但是我不可能对它爱得这般深切。”
那年,他们一家在杰涅日内依街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托尔斯泰断断续续地在莫斯科住了将近20个年头。
刚到莫斯科,喧嚣、拥挤的城市生活使托尔斯泰感到极为不适,而城市中悬殊的贫富差距更使世界观激变后的托尔斯泰触目惊心。他在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臭味,瓦砾,奢侈,贫穷,腐化,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佣法官以保护他们寻欢作乐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壑,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托尔斯泰称自己在莫斯科度过的这头一个月是“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索菲娅在给妹妹的信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景:
“头两个星期,我每天都在哭,因为列沃奇卡不仅精神委靡,而且甚至有些麻木,他不吃不睡,有时当真哭泣,我焦急得要发疯……后来他到特维尔省去了一趟,见了那里的老朋友巴库宁,而后又到一个村子里去看一个分裂教派的基督徒,回来时就没有那么神色沮丧了。”
这里提到的“基督徒”,名叫休塔耶夫。休塔耶夫和他的儿子原是彼得堡的墓碑工人,当他们认为这种竞争性的职业是不道德的,就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休塔耶夫认为,他在农村按基督精神建立的村社体现了“按上帝意志生活”的理想,他的信仰是“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从这点出发,他否定任何以暴力抗恶的行为,否定官方教会和相应的宗教仪式,也不承认私有制。休塔耶夫的家人也赞同他的学说,他的儿子因拒绝服兵役而被送进了感化营。托尔斯泰从分裂教派的研究者普鲁加神父那里听到了有关休塔耶夫的介绍,十分激动。他迫不及待地前往特维尔省拜访了这个农民。在接触中,休塔耶夫的质朴、真诚、坚定,为维护自己的信仰决心去承受一切苦难的行动,都令托尔斯泰感慨不已。托尔斯泰认为,尽管他与休塔耶夫是不同的两种人,但他们有共同的信念。休塔耶夫的宗教热情对深感孤独的托尔斯泰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那年冬天,休塔耶夫到莫斯科回访了托尔斯泰,两人交谈十分投机,托尔斯泰引为知音。但此事却引起了沙皇当局的警觉,宪兵二度闯进托尔斯泰的寓所,休塔耶夫被迫离开莫斯科。托尔斯泰对此十分气愤。
不过,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普通人,他们是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和教师奥尔诺夫。托尔斯泰曾在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住在莫斯科,对于我是非常困难的。我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是一样困难……起初好像我必须在两件事情当中选择一样:或是放手不干,消极地受苦,向失望屈服;或是跟罪恶和解,让自己沉湎于赌博、闲谈和喧闹之中。可是幸而我不能干后者,而前者又太痛苦。我看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生活,总是把自己的好处转向别人。可是即使在这里也还是有些真正的人,上帝已经使我遇到了两个。他(费奥多罗夫)60岁,很穷,他把一切都给了别人,总是欢快而从容。奥尔诺夫是一个受过苦的人,由于涅恰耶夫的事情,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而且有病。他也过着苦行者的生活,供养九口人,生活得很合理。他是一个铁道学校的教师。奥尔诺夫和费奥多罗夫都读了我的书《福音书概要》,在最小的细节上,我们和休塔耶夫都完全一致。”
托尔斯泰还常常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郊外与伐木工人一起锯木头,和农民一起聊天。托尔斯泰觉得,只有在这时他才“看见了真正的生活”,“精神就振作了”。
那年12月里的一天,托尔斯泰顶着凛冽的寒风,前往贫民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访问。市场周围到处是衣衫褴褛、缺衣少食,甚至随时可能倒毙街头的流浪汉、乞丐、妓女、失业者和农民。在利亚平免费夜店的门口早早就排起了数百名等候栖身者的长队。托尔斯泰上前与人们攀谈起来,他得知这些贫民中不少都是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在农村待不住了,就流落到城里打工糊口,可是工作没了,就得挨饿、乞讨,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托尔斯泰同情地给那些不幸的人们买来几杯热糖水和一些零钱,不料周围的穷人蜂拥而上,这时“他们的脸一张比一张更可怜,更疲惫,更屈辱”,这一切使托尔斯泰不寒而栗。从那里回来后,他踏上自己家里那铺着毡毯的楼梯,吃着有五道菜的丰盛的晚餐时,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控制了他:“过这种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当天晚上,托尔斯泰对着自己的亲友,痛苦地流着泪喊道:
“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不能!”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次年1月,托尔斯泰又主动要求参加莫斯科的人口调查。一开始,托尔斯泰还寄望于借此“唤起富人对城市贫民的同情,收募钱财”,以帮助穷人。托尔斯泰来到了被称为“最可怕的贫穷和堕落的巢穴”的阳沟街一带调查。人民生活的可怕处境一次又一次地使托尔斯泰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在《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指出,“数字和结论将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成千上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的身影,但是“难道能就此止步吗”?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这种生活状况,因为“没有任何一项事业能比扫除这种生活发展的障碍,改善这种生活更为重要的了”。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文中,托尔斯泰更为详尽地谈到了人口调查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他愤怒地回忆起富人们面对他的救助呼吁的那种种冷漠和虚伪,他也痛心地谴责了自己一度还沾沾自喜的“慈善”行为。托尔斯泰以忏悔和激愤的心情写道:
“……我居然会糊涂到那样的地步,竟把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用另一只手扔给随意想到的人几个戈比称作善事。自然我要觉得羞愧了。的确,如果我穿的是贵重的裘皮大衣,或者那缺靴子穿的人看见我的住宅值两千卢布,哪怕看见的仅仅是我只因心血来潮就慷慨地送给别人5个卢布,那他就会知道,我这样给钱仅仅是因为我弄到了很多的钱,多得花都花不光,而那些多余的钱我不但什么人也不给,而且还很容易从别人那里夺到手。他若不把我看成占有了本应属于他的东西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还会把我看成什么?他除了希望从我手里尽可能多捞回一些从他和别人手里夺走的卢布,还能对我有什么别的感情?”
“……我看到由于种种我也参加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我看到这种对他人劳动的享受又是这样分配的:一个人或者给他留下遗产的那个人使用的诡计越是狡猾复杂,他对别人的劳动就享受得越多,自己从事的劳动也越少。”
“……我看到,十分之九的工人生活本来就紧张辛苦,如同任何自然的生活一样,可是夺走这些人的必需品并使他们陷入艰难困苦之中的种种诡计又使这种生活变得一年比一年更辛苦,更贫困……。我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工人的生活,特别是属于劳动人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因为劳动强度不断增加而又缺乏与之相称的营养,简直就是在毁灭之中。这种生活连自己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在我所属的那个不劳动的阶层,生活却一年比一年更阔绰,更奢侈,更有保障,最后对这个阶层的连我在内的幸运儿来说,生活已经达到古人只在童话故事里幻想过的那种境地,我们成了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的主人……我看到,人们的劳动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劳动大众的手里转到非劳动者手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仿佛正在改造,要使基石移往顶端,并且这种移动正以一种几何级数的速度不断加快……”
这次人口调查使托尔斯泰心情沉重。为了“从可怕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托尔斯泰在调查结束后就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但是,即使在那里,他的心情也无法平静,托尔斯泰强烈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认为:“我们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权的所谓有教养的人,在错误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因此我们要猛醒回头。”“一个人如果当真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然而,作家真诚而热烈的精神追求却给他的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表面上看,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丈夫享誉文坛,妻子温柔体贴,经济收入颇丰,孩子的学习也已安排妥贴。这时,长子已经在莫斯科大学就读,长女进入了美术雕塑学校,两个稍小一点的男孩已被安排在波里瓦诺夫私立学校读书。平日里,他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女主人常常举办晚会,宾客盈门。不仅如此,为了让孩子更多地接触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索菲娅还不时带着孩子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可是如今,上流社会的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已令托尔斯泰极为反感,这必然导致他与妻子关系的裂痕。1882年2月,索菲娅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
“你同休塔耶夫有能耐不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这些凡人却办不到,而且我们也许并不愿意成为一个怪人,标榜自己爱全世界,从而为自己不爱任何人作辩护。享你的清福吧!搞你的写作吧!不必担心。反正你在与不在都一样,只不过客人少些。就是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我们的生活已经分道扬镳了。其实这算什么生活呢?”
虽然气头一过,索菲娅又会给托尔斯泰写来情意绵绵的书信,可是她并没有也不可能踏上托尔斯泰同样的人生之旅,严峻的生活已经无情地把他们推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
那年春天,托尔斯泰回到莫斯科。由于妻子的一再要求,他在城里买了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位于城市的西南角,离莫斯科河不远的老织工巷内(现为列夫·托尔斯泰街二十一号)。托尔斯泰选定这所住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拥有一个面积达一公顷的大花园,园内有高大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野花,颇有几分野趣。园内的主楼是一幢两层的木房。由于房间不够托尔斯泰全家使用,托尔斯泰请人加盖了一些附属的建筑。完工后,托尔斯泰在顶楼挑了一间面向花园的房间作为他的书房。10月里,全家迁入了新居。
很快,老织工巷的这幢房子也像雅斯纳亚·波良纳一样,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在以后的岁月中,许多来自国内外的人士络绎不断地来到这里,拜访他们敬仰的作家。托尔斯泰的秘书谢尔盖延科回忆说:
“谁不曾到这所涂刷成黑褐色的不大的乡村式的房子里来呀!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国务活动家和金融家、省长、教派信徒、地方自治工作者、议员、大学生、军人、工人、农民、不同色彩和不同民族的记者。冬天里没有一天,老织工巷不出现前来请求会见著名的俄罗斯作家的陌生人。”
画家列宾就是这里的常客。托尔斯泰与列宾相识于1880年秋天,从此以后两人建立起了终身不渝的友谊。他们常常漫步于莫斯科的林荫大道上,作倾心的交谈。列宾回忆说,托尔斯泰的“谈话充满热情,极其激烈,我很不安,夜间甚至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萦绕着他对陈腐生活的那些尖刻议论。”当时,列宾还为托尔斯泰的《莫斯科人口调查》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作了《在尔扎诺夫的一所房子里》、《一群穷人》、《篝火旁》等插图。
1882年4月底,托尔斯泰从格里戈罗维奇那里得知屠格涅夫患病的消息,十分焦急。他立即去信问候,还一度打算前往巴黎探望。屠格涅夫回信说:
“我说不出您的信是怎样地感动了我!我要为其中的每一个词拥抱您……至于我的生命,虽说大好时光已经过去,但我大概还得活很久。您也要长久地活下去,这不仅是为了生就是好事,而是为了完成您所担负的,而且除您之外,我们别无他人能够担负的那种事业。”
遗憾的是,屠格涅夫的病情不断恶化,终于不治。1883年6月底,屠格涅夫在病危期间,勉强支撑着,用铅笔亲手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久未修书致候,因为我最近以及现在,干脆地说,已处于死亡的边缘,我已不能重新康复了——这是没有什么可想的。我现在亲自给您写信,为的是向您表明,我成为您的同时代人是多么高兴,并且向您表示我最后的、衷心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方面那就另一回事了。啊,假如我能想到,我的请求对您发生作用,我是多么幸福!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听取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这张便条,请您让我知道。请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夫人,您的所有一家人,我不能再写了,很疲倦。”
这是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托尔斯泰心情极为沉重。那些天里,他的话题老是离不开屠格涅夫。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到屠格涅夫,我非常爱他,惋惜他,我一直在读他的作品。我每时每刻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写点关于他的东西……”不久,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邀请托尔斯泰参加纪念屠格涅夫的活动,托尔斯泰同意了,并准备在会上作公开演讲。消息传出,莫斯科为之轰动。可是当局十分担心托尔斯泰的演讲会产生对他们不利的巨大影响,迫使这次活动以“无限期推迟”而告终。
沙皇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对托尔斯泰的言行越来越感到害怕和不满。1882年9月中旬,当局就传令各地,密切注意托尔斯泰与分裂教派关系上的“有害活动”。9月底,莫斯科警察局开始派特务对托尔斯泰进行秘密监视。这年12月和次年9月,托尔斯泰分别拒绝担任克拉皮文县贵族长和法庭陪审员的职务,此事又引起当局,包括沙皇本人的恼怒,认为对此“政府必须给予无条件的谴责,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类似的、非善意的现象发生”。与此同时,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著述也均被沙皇当局明令禁止出版。莫斯科书报检查官声称,那些书“极端有害”,因为它们“破坏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并且根本违反教会教义”。
1883年4月的一天,雅斯纳亚·波良纳村发生了一场大火。整个村庄浓烟滚滚。托尔斯泰闻讯后立即赶到火场,指挥灭火。可是由于火势过猛,而水井又太少,村里还是有22家农舍化为灰烬。托尔斯泰十分同情农民的不幸,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他在给索菲娅的信中写道:
“我很可怜那些庄稼人,无法想象他们已经忍受而且还将忍受多少苦难,粮食全烧光了。所受损失如果以金钱计算,将超过一万卢布。大约有两千卢布保险金,其他一切都要靠赤手空拳筹措,生活必需品也需筹措,一家人才不致饿死。我刚刚在火灾场察看了一遍。那情景凄惨可怕,而农民的生命力,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的自信心和镇定情绪也令人惊心动魄。”
托尔斯泰给了农民造房的木料,并设法从别处用高价购得农民急需的燕麦种,以不误春时。
尽管已迁居莫斯科,夏日里,索菲娅还是爱带着孩子在农村度过。那几年,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在屋子的楼梯口放了个信箱,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即兴创作,如幽默诗文、家事评议、趣闻轶事等投入其中,每周开启一次。家里人兴致颇高,托尔斯泰也饶有兴趣地参与了这项活动,信箱里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诙谐短文。下面是他写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医院精神病患者病历》中的两篇:
第一号病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具有多血质的特征。属于平和病人科。病人狂躁,这种病症德国精神病学者称之为癫狂。病情:他认为能够用语言改变别人的生活。一般症状:对整个现存制度不满,指责所有的人(他本人除外),愤慨多言,不注意听众反应,常常由恼怒和愤慨转变为不自然的流泪和感动。常见症状:爱干分外和无益的事,如缝靴子、擦皮鞋以及割草之类。治疗办法: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让他从事消耗体力的劳动。第二号病历(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属温顺病人科,但有时必须隔离。病人狂躁,极端焦狂。病情:病人以为凡事非她莫为,忙得团团转也做不完。症状:完成没有布置的任务,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陈述不必要的辩白,满足并无需要的要求。治疗办法:紧张工作。禁忌:与轻浮的上流社会人士结交。”
托尔斯泰的生活日趋平民化,他尽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并更多地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为了替自己一生所过的老爷生活赎罪,从1884年起,他不再吃肉,连烟酒也戒了。托尔斯泰还把全部财产的处理权移交给了妻子,并作了公证。然而,托尔斯泰力求过简朴生活的努力却不为家人所理解,他的关于改变家庭生活方式的谈话常常遭到家人的嘲笑和反对。1884年,托尔斯泰与家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当时,托尔斯泰对家中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厌恶之极。他在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家里的气氛太让我难受了。让我难受的是,我不能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的一切欢乐、考试、在社交界的成功、音乐、陈设、买到的东西,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他们的不幸和恶,而我又不能这样对他们说。我可以说,也在说,但是我的话打动不了任何人。他们明白的似乎并不是我的话的涵义,而是我有这样说话的坏习惯。在我沮丧的时候——此刻便是——他们的无情使我惊异。他们怎么就看不见,三年以来我不止是痛苦,而简直是没法活。”
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疯的人住在一所由疯人当家作主的疯人院里”。他渴望离开这个家,过平民生活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6月里,托尔斯泰提议,将萨马拉田庄农民还的债就地分给农民,索菲娅坚决反对。6月17日傍晚,夫妻间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当晚,托尔斯泰第一次离家出走,而此时索菲娅正怀着他们的又一个孩子,并即将分娩。托尔斯泰在前往图拉的途中停住了脚步,重新回到了家中。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他次日的日记中表露无遗:
“唉!真受罪啊!我毕竟心疼她,而且我毕竟无法相信她是个十足的木头人。正如有个人管理我们的生活事务,我却要责备他。这太难了,也太无情了。对她无情。我眼见她日益迅速地走向毁灭,走向可怕的心灵的苦难。等到哥哥从图拉来了,我才生平第一次对他道出了我的处境多么可怕。”
就在那天凌晨,索菲娅生下了女儿萨莎。
家庭风波自然会有平息之时。每当此时,全家人,特别是两个女儿(已成年的塔尼娅和刚步入少女时代的玛莎)都与托尔斯泰亲近。欢乐、谅解、和睦的气氛使托尔斯泰感到欣慰,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是孤独的,因为生活很快恢复了常态。托尔斯泰时时“不无恐惧地”注视着家人“不道德的生活”;“游手好闲和大吃大喝”;“别人为他们做一切事,而他们不为任何人,甚至不为自己做一点事”,而且,大家都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因此,尽管6月里那次没走成,但托尔斯泰内心的这种愿望却再也没有消失过。7月14日的日记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我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虽说我非常可怜孩子们。我越来越爱他们,疼他们。”后来他还表示:“哪怕有一年时间置身在这个发疯的家庭之外也好。”
作为托尔斯泰的妻子和一个有才干的女人,索菲娅对丈夫的文学事业作出过帮助,并且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即使在矛盾尖锐的1884年,索菲娅仍深情地对托尔斯泰写道:
“忽然间,我给自己清楚地描绘出你的形象,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柔情。你身上有一种那么聪明、仁慈、天真而固执的气质,这种气质被你那天性所独具的对每一个人的亲切关心所照耀,也为你洞悉人们灵魂的目光所照耀。”
§§第八章 走向人民
“没有雅斯纳亚·波良纳,我很难想象俄罗斯,也很难想象我和它的关系。没有雅斯纳亚·波良纳,我也许能对我的祖国赖以形成的那些共同规律看得更为清楚,但是我不可能对它爱得这般深切。”
那年,他们一家在杰涅日内依街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托尔斯泰断断续续地在莫斯科住了将近20个年头。
刚到莫斯科,喧嚣、拥挤的城市生活使托尔斯泰感到极为不适,而城市中悬殊的贫富差距更使世界观激变后的托尔斯泰触目惊心。他在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臭味,瓦砾,奢侈,贫穷,腐化,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佣法官以保护他们寻欢作乐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壑,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托尔斯泰称自己在莫斯科度过的这头一个月是“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索菲娅在给妹妹的信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景:
“头两个星期,我每天都在哭,因为列沃奇卡不仅精神委靡,而且甚至有些麻木,他不吃不睡,有时当真哭泣,我焦急得要发疯……后来他到特维尔省去了一趟,见了那里的老朋友巴库宁,而后又到一个村子里去看一个分裂教派的基督徒,回来时就没有那么神色沮丧了。”
这里提到的“基督徒”,名叫休塔耶夫。休塔耶夫和他的儿子原是彼得堡的墓碑工人,当他们认为这种竞争性的职业是不道德的,就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休塔耶夫认为,他在农村按基督精神建立的村社体现了“按上帝意志生活”的理想,他的信仰是“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从这点出发,他否定任何以暴力抗恶的行为,否定官方教会和相应的宗教仪式,也不承认私有制。休塔耶夫的家人也赞同他的学说,他的儿子因拒绝服兵役而被送进了感化营。托尔斯泰从分裂教派的研究者普鲁加神父那里听到了有关休塔耶夫的介绍,十分激动。他迫不及待地前往特维尔省拜访了这个农民。在接触中,休塔耶夫的质朴、真诚、坚定,为维护自己的信仰决心去承受一切苦难的行动,都令托尔斯泰感慨不已。托尔斯泰认为,尽管他与休塔耶夫是不同的两种人,但他们有共同的信念。休塔耶夫的宗教热情对深感孤独的托尔斯泰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那年冬天,休塔耶夫到莫斯科回访了托尔斯泰,两人交谈十分投机,托尔斯泰引为知音。但此事却引起了沙皇当局的警觉,宪兵二度闯进托尔斯泰的寓所,休塔耶夫被迫离开莫斯科。托尔斯泰对此十分气愤。
不过,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普通人,他们是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和教师奥尔诺夫。托尔斯泰曾在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住在莫斯科,对于我是非常困难的。我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是一样困难……起初好像我必须在两件事情当中选择一样:或是放手不干,消极地受苦,向失望屈服;或是跟罪恶和解,让自己沉湎于赌博、闲谈和喧闹之中。可是幸而我不能干后者,而前者又太痛苦。我看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生活,总是把自己的好处转向别人。可是即使在这里也还是有些真正的人,上帝已经使我遇到了两个。他(费奥多罗夫)60岁,很穷,他把一切都给了别人,总是欢快而从容。奥尔诺夫是一个受过苦的人,由于涅恰耶夫的事情,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而且有病。他也过着苦行者的生活,供养九口人,生活得很合理。他是一个铁道学校的教师。奥尔诺夫和费奥多罗夫都读了我的书《福音书概要》,在最小的细节上,我们和休塔耶夫都完全一致。”
托尔斯泰还常常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郊外与伐木工人一起锯木头,和农民一起聊天。托尔斯泰觉得,只有在这时他才“看见了真正的生活”,“精神就振作了”。
那年12月里的一天,托尔斯泰顶着凛冽的寒风,前往贫民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访问。市场周围到处是衣衫褴褛、缺衣少食,甚至随时可能倒毙街头的流浪汉、乞丐、妓女、失业者和农民。在利亚平免费夜店的门口早早就排起了数百名等候栖身者的长队。托尔斯泰上前与人们攀谈起来,他得知这些贫民中不少都是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在农村待不住了,就流落到城里打工糊口,可是工作没了,就得挨饿、乞讨,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托尔斯泰同情地给那些不幸的人们买来几杯热糖水和一些零钱,不料周围的穷人蜂拥而上,这时“他们的脸一张比一张更可怜,更疲惫,更屈辱”,这一切使托尔斯泰不寒而栗。从那里回来后,他踏上自己家里那铺着毡毯的楼梯,吃着有五道菜的丰盛的晚餐时,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控制了他:“过这种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当天晚上,托尔斯泰对着自己的亲友,痛苦地流着泪喊道:
“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不能!”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次年1月,托尔斯泰又主动要求参加莫斯科的人口调查。一开始,托尔斯泰还寄望于借此“唤起富人对城市贫民的同情,收募钱财”,以帮助穷人。托尔斯泰来到了被称为“最可怕的贫穷和堕落的巢穴”的阳沟街一带调查。人民生活的可怕处境一次又一次地使托尔斯泰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在《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指出,“数字和结论将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成千上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的身影,但是“难道能就此止步吗”?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这种生活状况,因为“没有任何一项事业能比扫除这种生活发展的障碍,改善这种生活更为重要的了”。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文中,托尔斯泰更为详尽地谈到了人口调查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他愤怒地回忆起富人们面对他的救助呼吁的那种种冷漠和虚伪,他也痛心地谴责了自己一度还沾沾自喜的“慈善”行为。托尔斯泰以忏悔和激愤的心情写道:
“……我居然会糊涂到那样的地步,竟把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用另一只手扔给随意想到的人几个戈比称作善事。自然我要觉得羞愧了。的确,如果我穿的是贵重的裘皮大衣,或者那缺靴子穿的人看见我的住宅值两千卢布,哪怕看见的仅仅是我只因心血来潮就慷慨地送给别人5个卢布,那他就会知道,我这样给钱仅仅是因为我弄到了很多的钱,多得花都花不光,而那些多余的钱我不但什么人也不给,而且还很容易从别人那里夺到手。他若不把我看成占有了本应属于他的东西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还会把我看成什么?他除了希望从我手里尽可能多捞回一些从他和别人手里夺走的卢布,还能对我有什么别的感情?”
“……我看到由于种种我也参加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我看到这种对他人劳动的享受又是这样分配的:一个人或者给他留下遗产的那个人使用的诡计越是狡猾复杂,他对别人的劳动就享受得越多,自己从事的劳动也越少。”
“……我看到,十分之九的工人生活本来就紧张辛苦,如同任何自然的生活一样,可是夺走这些人的必需品并使他们陷入艰难困苦之中的种种诡计又使这种生活变得一年比一年更辛苦,更贫困……。我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工人的生活,特别是属于劳动人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因为劳动强度不断增加而又缺乏与之相称的营养,简直就是在毁灭之中。这种生活连自己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在我所属的那个不劳动的阶层,生活却一年比一年更阔绰,更奢侈,更有保障,最后对这个阶层的连我在内的幸运儿来说,生活已经达到古人只在童话故事里幻想过的那种境地,我们成了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的主人……我看到,人们的劳动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劳动大众的手里转到非劳动者手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仿佛正在改造,要使基石移往顶端,并且这种移动正以一种几何级数的速度不断加快……”
这次人口调查使托尔斯泰心情沉重。为了“从可怕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托尔斯泰在调查结束后就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但是,即使在那里,他的心情也无法平静,托尔斯泰强烈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认为:“我们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权的所谓有教养的人,在错误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因此我们要猛醒回头。”“一个人如果当真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然而,作家真诚而热烈的精神追求却给他的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表面上看,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丈夫享誉文坛,妻子温柔体贴,经济收入颇丰,孩子的学习也已安排妥贴。这时,长子已经在莫斯科大学就读,长女进入了美术雕塑学校,两个稍小一点的男孩已被安排在波里瓦诺夫私立学校读书。平日里,他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女主人常常举办晚会,宾客盈门。不仅如此,为了让孩子更多地接触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索菲娅还不时带着孩子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可是如今,上流社会的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已令托尔斯泰极为反感,这必然导致他与妻子关系的裂痕。1882年2月,索菲娅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
“你同休塔耶夫有能耐不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这些凡人却办不到,而且我们也许并不愿意成为一个怪人,标榜自己爱全世界,从而为自己不爱任何人作辩护。享你的清福吧!搞你的写作吧!不必担心。反正你在与不在都一样,只不过客人少些。就是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我们的生活已经分道扬镳了。其实这算什么生活呢?”
虽然气头一过,索菲娅又会给托尔斯泰写来情意绵绵的书信,可是她并没有也不可能踏上托尔斯泰同样的人生之旅,严峻的生活已经无情地把他们推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
那年春天,托尔斯泰回到莫斯科。由于妻子的一再要求,他在城里买了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位于城市的西南角,离莫斯科河不远的老织工巷内(现为列夫·托尔斯泰街二十一号)。托尔斯泰选定这所住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拥有一个面积达一公顷的大花园,园内有高大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野花,颇有几分野趣。园内的主楼是一幢两层的木房。由于房间不够托尔斯泰全家使用,托尔斯泰请人加盖了一些附属的建筑。完工后,托尔斯泰在顶楼挑了一间面向花园的房间作为他的书房。10月里,全家迁入了新居。
很快,老织工巷的这幢房子也像雅斯纳亚·波良纳一样,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在以后的岁月中,许多来自国内外的人士络绎不断地来到这里,拜访他们敬仰的作家。托尔斯泰的秘书谢尔盖延科回忆说:
“谁不曾到这所涂刷成黑褐色的不大的乡村式的房子里来呀!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国务活动家和金融家、省长、教派信徒、地方自治工作者、议员、大学生、军人、工人、农民、不同色彩和不同民族的记者。冬天里没有一天,老织工巷不出现前来请求会见著名的俄罗斯作家的陌生人。”
画家列宾就是这里的常客。托尔斯泰与列宾相识于1880年秋天,从此以后两人建立起了终身不渝的友谊。他们常常漫步于莫斯科的林荫大道上,作倾心的交谈。列宾回忆说,托尔斯泰的“谈话充满热情,极其激烈,我很不安,夜间甚至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萦绕着他对陈腐生活的那些尖刻议论。”当时,列宾还为托尔斯泰的《莫斯科人口调查》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作了《在尔扎诺夫的一所房子里》、《一群穷人》、《篝火旁》等插图。
1882年4月底,托尔斯泰从格里戈罗维奇那里得知屠格涅夫患病的消息,十分焦急。他立即去信问候,还一度打算前往巴黎探望。屠格涅夫回信说:
“我说不出您的信是怎样地感动了我!我要为其中的每一个词拥抱您……至于我的生命,虽说大好时光已经过去,但我大概还得活很久。您也要长久地活下去,这不仅是为了生就是好事,而是为了完成您所担负的,而且除您之外,我们别无他人能够担负的那种事业。”
遗憾的是,屠格涅夫的病情不断恶化,终于不治。1883年6月底,屠格涅夫在病危期间,勉强支撑着,用铅笔亲手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久未修书致候,因为我最近以及现在,干脆地说,已处于死亡的边缘,我已不能重新康复了——这是没有什么可想的。我现在亲自给您写信,为的是向您表明,我成为您的同时代人是多么高兴,并且向您表示我最后的、衷心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方面那就另一回事了。啊,假如我能想到,我的请求对您发生作用,我是多么幸福!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听取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这张便条,请您让我知道。请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夫人,您的所有一家人,我不能再写了,很疲倦。”
这是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托尔斯泰心情极为沉重。那些天里,他的话题老是离不开屠格涅夫。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到屠格涅夫,我非常爱他,惋惜他,我一直在读他的作品。我每时每刻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写点关于他的东西……”不久,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邀请托尔斯泰参加纪念屠格涅夫的活动,托尔斯泰同意了,并准备在会上作公开演讲。消息传出,莫斯科为之轰动。可是当局十分担心托尔斯泰的演讲会产生对他们不利的巨大影响,迫使这次活动以“无限期推迟”而告终。
沙皇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对托尔斯泰的言行越来越感到害怕和不满。1882年9月中旬,当局就传令各地,密切注意托尔斯泰与分裂教派关系上的“有害活动”。9月底,莫斯科警察局开始派特务对托尔斯泰进行秘密监视。这年12月和次年9月,托尔斯泰分别拒绝担任克拉皮文县贵族长和法庭陪审员的职务,此事又引起当局,包括沙皇本人的恼怒,认为对此“政府必须给予无条件的谴责,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类似的、非善意的现象发生”。与此同时,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著述也均被沙皇当局明令禁止出版。莫斯科书报检查官声称,那些书“极端有害”,因为它们“破坏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并且根本违反教会教义”。
1883年4月的一天,雅斯纳亚·波良纳村发生了一场大火。整个村庄浓烟滚滚。托尔斯泰闻讯后立即赶到火场,指挥灭火。可是由于火势过猛,而水井又太少,村里还是有22家农舍化为灰烬。托尔斯泰十分同情农民的不幸,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他在给索菲娅的信中写道:
“我很可怜那些庄稼人,无法想象他们已经忍受而且还将忍受多少苦难,粮食全烧光了。所受损失如果以金钱计算,将超过一万卢布。大约有两千卢布保险金,其他一切都要靠赤手空拳筹措,生活必需品也需筹措,一家人才不致饿死。我刚刚在火灾场察看了一遍。那情景凄惨可怕,而农民的生命力,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的自信心和镇定情绪也令人惊心动魄。”
托尔斯泰给了农民造房的木料,并设法从别处用高价购得农民急需的燕麦种,以不误春时。
尽管已迁居莫斯科,夏日里,索菲娅还是爱带着孩子在农村度过。那几年,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在屋子的楼梯口放了个信箱,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即兴创作,如幽默诗文、家事评议、趣闻轶事等投入其中,每周开启一次。家里人兴致颇高,托尔斯泰也饶有兴趣地参与了这项活动,信箱里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诙谐短文。下面是他写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医院精神病患者病历》中的两篇:
第一号病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具有多血质的特征。属于平和病人科。病人狂躁,这种病症德国精神病学者称之为癫狂。病情:他认为能够用语言改变别人的生活。一般症状:对整个现存制度不满,指责所有的人(他本人除外),愤慨多言,不注意听众反应,常常由恼怒和愤慨转变为不自然的流泪和感动。常见症状:爱干分外和无益的事,如缝靴子、擦皮鞋以及割草之类。治疗办法: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让他从事消耗体力的劳动。第二号病历(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属温顺病人科,但有时必须隔离。病人狂躁,极端焦狂。病情:病人以为凡事非她莫为,忙得团团转也做不完。症状:完成没有布置的任务,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陈述不必要的辩白,满足并无需要的要求。治疗办法:紧张工作。禁忌:与轻浮的上流社会人士结交。”
托尔斯泰的生活日趋平民化,他尽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并更多地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为了替自己一生所过的老爷生活赎罪,从1884年起,他不再吃肉,连烟酒也戒了。托尔斯泰还把全部财产的处理权移交给了妻子,并作了公证。然而,托尔斯泰力求过简朴生活的努力却不为家人所理解,他的关于改变家庭生活方式的谈话常常遭到家人的嘲笑和反对。1884年,托尔斯泰与家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当时,托尔斯泰对家中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厌恶之极。他在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家里的气氛太让我难受了。让我难受的是,我不能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的一切欢乐、考试、在社交界的成功、音乐、陈设、买到的东西,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他们的不幸和恶,而我又不能这样对他们说。我可以说,也在说,但是我的话打动不了任何人。他们明白的似乎并不是我的话的涵义,而是我有这样说话的坏习惯。在我沮丧的时候——此刻便是——他们的无情使我惊异。他们怎么就看不见,三年以来我不止是痛苦,而简直是没法活。”
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疯的人住在一所由疯人当家作主的疯人院里”。他渴望离开这个家,过平民生活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6月里,托尔斯泰提议,将萨马拉田庄农民还的债就地分给农民,索菲娅坚决反对。6月17日傍晚,夫妻间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当晚,托尔斯泰第一次离家出走,而此时索菲娅正怀着他们的又一个孩子,并即将分娩。托尔斯泰在前往图拉的途中停住了脚步,重新回到了家中。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他次日的日记中表露无遗:
“唉!真受罪啊!我毕竟心疼她,而且我毕竟无法相信她是个十足的木头人。正如有个人管理我们的生活事务,我却要责备他。这太难了,也太无情了。对她无情。我眼见她日益迅速地走向毁灭,走向可怕的心灵的苦难。等到哥哥从图拉来了,我才生平第一次对他道出了我的处境多么可怕。”
就在那天凌晨,索菲娅生下了女儿萨莎。
家庭风波自然会有平息之时。每当此时,全家人,特别是两个女儿(已成年的塔尼娅和刚步入少女时代的玛莎)都与托尔斯泰亲近。欢乐、谅解、和睦的气氛使托尔斯泰感到欣慰,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是孤独的,因为生活很快恢复了常态。托尔斯泰时时“不无恐惧地”注视着家人“不道德的生活”;“游手好闲和大吃大喝”;“别人为他们做一切事,而他们不为任何人,甚至不为自己做一点事”,而且,大家都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因此,尽管6月里那次没走成,但托尔斯泰内心的这种愿望却再也没有消失过。7月14日的日记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我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虽说我非常可怜孩子们。我越来越爱他们,疼他们。”后来他还表示:“哪怕有一年时间置身在这个发疯的家庭之外也好。”
作为托尔斯泰的妻子和一个有才干的女人,索菲娅对丈夫的文学事业作出过帮助,并且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即使在矛盾尖锐的1884年,索菲娅仍深情地对托尔斯泰写道:
“忽然间,我给自己清楚地描绘出你的形象,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柔情。你身上有一种那么聪明、仁慈、天真而固执的气质,这种气质被你那天性所独具的对每一个人的亲切关心所照耀,也为你洞悉人们灵魂的目光所照耀。”
§§第八章 走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