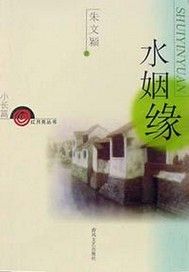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科普教育
> 麦积山石窟考古断代研究:后秦开窟新证
> 附录
附录
(一)历史地理研究
1.“天水”名考
据《汉书·地理志》,天水郡设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天水”之名,始见古籍于此。但当时命此地名的统治者以何为根据,本文之前,已有相当的说法,笔者试再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篇》[1]:“耤水又东北径上邽县。……上邽县故城……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
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无稽,虽然,根据现在天水地区多大股泉水的现象看,古天水郡应有积泉水成湖的事实,但“白龙”乃神话,故清代学者王先谦曰:“世或訾其(郦道元)好奇骋博。”[2]
北魏时,上邽(改名上封)治天水郡,[3]郦氏记上邽县故城,在有关天水郡名之来由方面,大概在缺乏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仅寥寥数语记载了当时当地的民间传说而已,故北宋苏东坡曾“叹郦元之简”。[4]
大约同一时代,南朝刘宋之郭仲产在其《秦州地记》中关于天水郡的记载曰:“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这同郦氏观点相近,皆本于有神异现象之湖水。郦氏说湖中“风雨随白龙”,郭氏说“湖水冬夏无增减”,因此他们认为湖水乃上应于天,因名“天水湖”即湖水为“天水下注”或“天河下注”而成,故有“天水”之地名。又《天水史话》[5]和《麦积山的传说》[6]中有“天河注水”的传说,以及《天水报》载《天水与小天水》[7]中,有秦代“小天水求神降雨成湖”说,也欠妥当。因为“天河注水”传说,实际上就是郭仲产和郦道元的说法,不过更明确地说出来了二位的言下之意,湖水由神异的天河注水而成。以上这些说法,都把“天水”地名的来由,归于某种神异现象,所以只能以神话传说看待,不能做为“天水”地名来由的历史事实根据。
而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时,天水郡曾改名为“汉阳郡”。阳者,水的北面。从历史沿革中,我们得到了启示,即天水郡与汉水有关,言位于其水之北。
《诗·大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也称天汉、天河、云汉。
地面上的汉水,顾名思义,就是天汉在地上的延续。那么,汉水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是来自于天上的,来自于“天水”的。于是,汉水接天,其上源之地,就是“天水”之地。
《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故漾水为汉水上源。
又《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洋水出焉。”
按“洋水”即“漾水”。据《水经注·漾水篇》引晋地理学家阚骃云:“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梁州部分,氐道与西汉天水郡的东南部相邻。
又据《山海经·西山经》之次序,昆仑山在中国西北。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治,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可知河西敦煌境内,有与昆仑山有关的地名。今人萧兵《楚辞文化》亦认为:“以黄帝为传说祖先的夏人集群最强大的一支,发源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以‘昆仑’(其原型祁连山)为圣地。”可见昆仑山古代曾被认为在河西祁连山周围一带。
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凉州部分,西汉时的天水郡,黄河过其西北境,天水郡接壤连通河西走廊。而西汉元鼎三年设天水郡时,河西并未设郡,[8]所以,当时的天水郡直接通西北的河西走廊,即通昆仑山。漾水从昆仑山流来,按阚骃的说法,潜流至天水郡东南相邻的氐道县,“重源显发”,复如《禹贡》所说,从嶓冢山中,东流为汉。
于是天水郡是被认为连接昆仑山的汉水上源之地,(汉为霄汉即天河意,此郡为上得天河之水处)所以“天水”郡便由此得名。
以上是关于汉水上源与天水郡关系的地理观点,这种观点在古代并不是孤立的。
据《王氏合校水经注·漾水篇》,孙校曰:阚骃“其说本高诱(东汉人)”,郦道元亦称“不可全言阚氏之非也”。
又据东汉许慎《说文》“漾”字条:“漾水出陇西豲道,东至武都为汉水。”此说亦被晋学者吕忱所接受。[9]
按《汉书·地理志》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武都与西汉天水郡东南部相邻,豲道在西汉天水郡中,至东汉未变其地望,位于武都西北,此乃直接说明漾水在西汉天水郡中。
由上可见,许慎、吕忱之说;与高诱、阚骃之说是一致的,即汉水上源经过西汉天水郡,西汉天水郡为汉水上源之地。
关于高诱、阚骃所指的“重源显发”或者叫“潜源复出”的说法,是否是古代学者只因汉水而说的呢?如果是这样,在当时的统治者和民众中,其可信性就差了,就很难被统治者做为命地起名的根据。事实上,潜源的说法,古代的别的河流也有,以致成为很热门的话题。
最著名的是河水。
如《山海经·西山经》载:“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
又如《汉书·西域传》曰:河水“东注蒲昌海……皆认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
东汉高诱称[10]:“河出昆仑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
又如济水,《据地志》载:“济水出河东……即见而伏,东出于今济源县。”[11]因此,潜源的说法,古代并不是某一人只对汉水的附会,而是古代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地理认识。因此可被“天水”起名所采用。
以上是天水之名的地理原因。
另外,间接的历史时代原因,是汉朝本身。汉高祖初封“汉王”时,萧何曰:“‘天汉’,其称甚美。”[12]
汉武帝也曾以“天汉”作为年号。
所以西汉时,“天汉”这一代表大统一与皇权国势神圣天授的思想,得到广泛提倡。因而天水郡的设立,正是“天汉”思想的结果,因为有“天汉”之说,才有“天水”地名。而设“天水”郡名,也如同“广汉”、“武威”、“敦煌”等郡名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一样,以期汉祚永昌,如滔滔汉水,源于“天水”,长流不断。
虽然,上述古代对汉水源头(在西汉时,曾在直接连接昆仑山的天水郡地区,重源显发)的地理认识,在东汉正统记载西汉地理的书籍,如《汉书·地理志》(在天水郡等地区的内容)中并无明确记载,而只在其他载籍和一些学者中流传,但是,较离奇的说法并不等于在西汉时没有,也不等于不被统治者所接受。西汉统治者正处于汉代经学创立时期,更相信古籍,比东汉人富于想象力。
且汉武帝本人思想活泼,尊重知识,热衷神仙黄老之学,接受方士说教,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接受神奇的地理思想。于是他又从政治意义出发给新郡命名,以期追先贤之记述,得山海之奇致,扬汉朝之天威。所以,“天水郡”的命名,是汉武帝时期地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完美结合的一个创作。
综上所述,可见“天水”地名,基于“天汉”之说,来由于“汉水上源之地”的位置。古人认为汉水来源于天河,来源于昆仑山这座上应于天的圣山,来源于连接昆仑山的陇上高原那广大而深厚的地层中。而直到如今,这片黄土高原,的确相对比较多雨,且地下水丰富,泉水众多。这或许不是巧合,或许确实因有这方面因素,而使古人认为这片黄土高原是汉水上源的潜流之地,于是在昆仑山附近地带的河西地区没有建郡之前,而为设于这片陇上高原的新郡命名,就理所当然地以上接天河之水的“天水”命名而为“天水郡”。那么所谓“天水”,其本义就是“天河之水”,“天水”地名是指这片土地上接天河,为“天河下注之地”而已。
(此文最初公布于1992年天水市首届伏羲历史文化研讨会,原载于《伏羲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原作者夏阳为曾用名)
2.嶓冢山名考——嶓冢山·鲋鱼山·麦积山
嶓(音bo)冢山,古代名山,见之于《山海经》及《禹贡》,但其名字的来历如何,即为何称嶓冢呢?未见述于古籍,笔者试探,以求教于专家。如果从字面上看,“嶓”字从“山”形,“番”声,而“冢”附后,则“蟠冢”有高山如冢之意。但是,凡山,或多或少有此意,此山何嶓独以冢名?笔者以为此绝非偶然。
一
按《山海经》、《禹贡》所记的古“嶓冢山”,汉水出于此山[13]。又按《山海经·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则“嶓冢山”“鲋鱼山”似为一山。
清胡渭《禹贡锥指》亦日:“《山海经》云:‘汉水出鲋嶓山。’盖嶓冢之别名也。”笔者按,“嶓”为胡渭用的通假字(或另本经所用通假字),原经为“鲋鱼山”。
那么“嶓冢”之名是否与“鲋鱼”有关呢?
按《十三经注疏》载《易·井》:“九二,井谷射鲋。”唐孔颖达《疏》引子夏《传》云:“井中之蝦呼为鲋鱼也。”
按《说文》:“蝦,蝦蟆也。”
按西安市东南有虾蟆陵,一作虾陵,虾即蝦[14]。则“”通“蟆”,蝦即蝦蟆。故“蝦”即“蝦蟆”即“虾蟆”。又虾同蛤[15]。故“蝦”即“蛤蟆”也。
但这只是字面上的传承,内部意思可能有所转变,即今蛤蟆(蛙和蟾蜍的统称)有可能包括不了古“蛤蟆”(蝦)所指。
按《庄子·外物》:“(庄)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乃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之情景。如以今蛤蟆比作鲋鱼,则有悖于生活常识,因涸辙困不住蛤蟆。因此,今“蛤蟆”包括不了古“蛤蟆”所指。
那么古“蛤蟆”可别指什么呢?
现实中有一例可以给我们启示。
河南陕县西门外有一泉名“蛤蟆泉”,《陕州志》云:“水自石眼流出,内生蝌蚪,祷雨辄应。”[16]这似可理解为:“蛤蟆可指蝌蚪。”且是其古意在民间的一种遗留,即古“蛤蟆”即“蝦”即“鲋鱼”可指蝌蚪。
如此,我们对涸辙之鲋的困惑,便迎刃而解。因为“涸辙之蝌蚪,相濡以沫”之情景是常见的。故《庄子》之文印证了先秦时“蝦可指蝌蚪。”的情况。
进一步说,先秦时“鲋鱼”可指“蝌蚪”。
那么是否仅此孤例印证先秦时鲋鱼可指蝌蚪呢?不是的,还有别的证据可凭:
《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按文意,此“鲵”“鲋”当指小的个体。如鲋鱼以今蛤蟆来比附之,依常识,蛤蟆却不会在灌渎中随水漂流,更不能被人守来。这样,则与文意中确实能守来,只是得不到大鱼相矛盾。但如鲋鱼指蝌蚪,则合于实际情况,更合于大小鱼差距悬殊的意思,更符合庄子多用强烈对比的文风。
又《山海经·中山经》:“来需之水……其中多鱼,黑文,其状如鲋,食者不睡。”
《南山经》:“鸡山……黑水……其中有鱼,其状如鲋。”
《东山经》:“……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
《北山经》:“其中有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
《中山经》:“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
按:如以“今蛤蟆”来解释上文中的“鲋鱼”则牵强。
因为,“鱼很像今蛤蟆”很难理解。如果这样,则在经文中,对这些鱼的描述,抛开了与今蛤蟆具有相似之处的,且更像鱼的娃娃鱼(鲵鱼)而不说“其状如鲵”,而直指与今蛤蟆相似,那么这些鱼则简直更像今蛤蟆,甚至分别就是某种今蛤蟆,则无需说“状如鲋鱼”即“状如今蛤蟆”了。
且如此“鱼很像今蛤蟆”的说法,也不好解释所谓“彘身“一首十身”。因鱼如这样,整体不会如今蛤蟆。
但“鲋鱼指蝌蚪”,则问题迎刃而解。蝌蚪本身形状如鱼,故可以与一些鱼相似。且其腹圆下垂如彘(猪)“身”,后拖一壮尾。
如某鱼一首而十小尾,可看作“一首而十身”,而整体仍似一首一壮尾的蝌蚪,今“水母”、“乌贼”“章鱼”等大头部生出若干较小的腕和触手(如尾)的这类水中动物还有很多,一首而十身的“茈鱼”或即此类,整体与蝌蚪有相似之处。
因此,《山海经》的记载使“鲋鱼”指“蝌蚪”,得到了进一步证明。
按宋陆佃《埤雅·释鱼》谓鲋鱼即卿鱼,另外还有其他解释,皆后出。故笔者谨从春秋晚期的子夏言,参以先秦著作推论,不采宋代等说。因此,“鲋鱼山”即“蝌蚪山”也。“嶓冢山”即“鲋鱼山”即“蝌蚪山”也。
二
那么是否蝌蚪与嶓冢之名的缘起有关呢?
按《尔雅·释鱼》:“科斗:活东。”晋郭璞注曰:“蝦蟆子。”则“科斗”即“蝌蚪”也。那么“科斗”与“嶓冢”是什么关系呢?
按“科斗”与“活东”,概古代时一音之转的关系,今天读来也仍有相似之处。所以古字音至今,虽有其变,但应有保留相似之迹的情况。相应,“科斗”与“嶓冢”,今天读来,也有相似之处。故它们的关系,虽不能说是音转意同,但也有可能为“嶓冢”系记“科斗”之音的情况。且“科”可入古韵“歌”部,“嶓”可人“元”部,可对转;“斗”可入“候”部,“冢”可入“东”部,[17]可对转。因此,古人可能从“科斗”音出发,参以从“山”等意象,记作“嶓冢”二字。
三
按“汉水出鲋鱼之山”载于《山海经·海内东经》:“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所属的一段中。清毕元校本中疑此段文字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晋郭璞注或撰的《水经》中的文字。今袁珂先生也赞许,认为这段是其他书籍的拦入。笔者认为,这段文字不管出于何书,当为郭璞时或郭璞之前,有研究价值的古记载无疑,郭璞等并未抛弃之。
按《山海经笺疏》:“(对《海内东经》笺疏)懿行案,汉水所出已见《西山经》嶓冢之山,此经(《海内东经》)云出鲋鱼之山。鲋鱼或作鲋隅,一作鲋鰅,即《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大荒北经》又作附禺之山,皆广阳山之异名也,与汉水源流绝不相蒙,疑经有伪文。《北堂书钞》九十二卷引(“出鲋鱼之山”)汉水作濮水,水在东郡濮阳,正颛项所葬,似作濮者得之矣,宜据以订正。”
笔者不苟同。
按:鲋鱼山与颛顼葬地无关。
“汉水出鲋鱼之山”之下的“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一句,非经文,而是注文。因错简或其他原因注文掺入经文的情况会发生。具体看,在“岷三江……”所属的这段文字中,述水之出入位置,别处均不详言山除位置之外的其它名堂,而在此鲋鱼山独载,为突兀之文,非其类耳。实际上,这句话如以注文目之并不突兀。此乃从别处移植来。按《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羆、文虎、离朱、久、视肉。”《大荒北经》:“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虎、豹、熊、羆、黄蛇、视肉、璿、瑰、瑶、碧,皆出卫于山。”大概作注者认为“务隅”、“鲋鱼”、“附禺”古字相通,故于务隅山,附禺山所属之文,摘其要注于“鲋鱼之山”下。比如取“务隅山”的“颛顼、九嫔葬地分阴阳”,取“附禺山”的“蛇”和“卫”。注者认为此“卫”为“保卫”之“卫”(此意同郭注《大荒北经》“在其山边也”)。而记作“四面有蛇护卫”作为两山众多之物的代表,注在“鲋鱼山”下。这也是注往往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表现。
故,因颛顼所葬而校改“汉”作“濮”难有充足理由。
事实上,笔者也是受郝懿行启发而有上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首次提出“汉水出鲋鱼之山”下经文为注文曰:“疑后人见鲋鱼与务隅山名相涉,因取彼羼入之耳。”此言极当。但他虽在经文中去掉后面被怀疑为注文的一句,却肯定了注者把两山拉到一块的思路,故根据“古字通用”认为“鲋鱼山”与“务隅山”、“附禺山”皆一山也。[18]因此据“濮阳正颛顼所葬”,认为山在濮阳,则“鲋鱼山”处经文中“汉水”为“文”当为“濮水”。这观点同《北堂书钞》九二卷引汉水作濮水一致。笔者认为从水的角度此观点也有误:
按《山海经》通行本承古至今于此(“汉水出鲋鱼之山”经文)处皆作“汉”。
且(实际地理考察)古濮水并非出郝氏所谓“广阳山”或者“务隅山”,而是出于河、济,为渠道性质的小河,与务隅山(郝氏认为的鲋鱼山)关系勉强,因此难说“濮水出于鲋鱼之山”。濮水这类小渠,也难说能列到“江”“淮”“湘”“濛”这些源流自成体系的大水之间。且在“岷三江”这段文字中,主序是支流列在主流后面。假如汉水处改作濮水,则濮水列于济水前,殊为不合理。故“汉”或为“濮”的观点,又一次难有充足理由。
且“汉”改为“濮”的想法,皆因为“鲋鱼”与“务隅”读音相近,被认作一山。但读音相近之山并非总为一山,如《西山经》有“符禺之山”却与“附禺山”、“务隅山”、“鲋鱼山”大相径庭。故“汉”非关“濮水”,“鲋鱼”非关“务隅”,为什么非要把鲋鱼山拉到务隅山身上不可呢?
另外,“鲋隅”出《北堂书钞》,“鲋鰅”出《禹贡锥指》,皆转抄字,无碍“鲋鱼”之为本字。故“汉水出鲋鱼山”所言不伪,“鲋鱼山”乃“嶓冢山”明矣。那么,嶓冢与科斗音近,反过来也更说明了鲋鱼可指蝌蚪的正确。嶓冢、蝌蚪、鲋鱼三位一体的意境,互相印证,道出“嶓冢”之名,从鲋鱼意到蝌蚪音,再落实到嶓冢字的来由。
四
那么什么是“蟠冢山”现实中实物来源呢?即现实中是否真正存在着一座鲋鱼山或蝌蚪山呢?有,那就是著名的天水“麦积山”。
麦积山头大根缩,形如麦垛,故名。其名始见于十六国。[19]但命名者仅仅着眼于此山的主体部分,而忽略了主体部分附带着的山梁。
此梁和主体部分同样,其山石裸露部分多。而梁的尾部渐渐不裸,可以生长草木,融入绿树草丛中。裸露的岩石使人们醒目地看到一个头大拖尾的蝌蚪形象。最重要的是,山的主体部分高大、明显、奇特,且自最高处渐渐向梁部收分,给人们的目光指示出尾部之所在,而其指示的方向确实有一带隆起山梁。即使山梁被树木掩住,仍有地形的隆起隐含着尾部的所在,故远观仍活脱脱地看出蝌蚪的形象。因此先民在此片山区,农业生产不太发达,麦垛概念不强烈的情况下,看到此山,最有可能联想到山间溪水中常见到的动物“蝌蚪”而名之为“蝌蚪山”。
那么今麦积山的位置是否就是古“嶓冢山”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据《汉书‘地理志》:“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
按氐道、西(县)均在今天水市南边山区中。[20]养即漾水。《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故知氐道有嶓冢山。而上文西县有嶓冢山,则一山跨二县。
而《山海经》、《禹贡》只说嶓冢出汉水,并未限定山的范围局限为一个地点的一座山峰所跨区域。据《山海经·西山经》,蟠冢山(中心)分别与两旁的山(中心),距离三百多里,则它本身东西跨度应为三百多里。《禹贡》记山更少,则山的跨度范围更宽。因此有理由相信,《山海经》、《禹贡》所指的嶓冢山应包括今麦积山在内的,今天水市南边广大群山,嶓冢山是一个广大山区的概念。民国《天水县志》也有相同的看法:“汉水发源县南百里间,是知境南诸山当为嶓冢无疑矣。”
以上是根据《汉志》所作的推论,但历代学者曾对此山的位置争论不休,皆因看到今汉水出处与《汉志》所载不符,即今天水市南边山区发源之水却流不到今汉水中,而流入今嘉陵江。但80年代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揭开了这古迷。他引《地理知识》1978 年第7期载李超文:“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入四川,而是东流入汉江的。”李超此文,是就他发现的古河道而言的。故刘琳先生说“盖在战国以前,嘉陵江至阳平关附近东流入汉中。”[21]
故战国以前之嶓冢山,应排除其他地区后代附会的山,如陕西嶓冢山[22],应是今天水市南部,渭水与嘉陵江上源的分水岭。而今嘉陵江上源仍称“西汉水”,也正说明了此分水岭正是古嶓冢山。
而今麦积山(麦积崖)正处在这条分水岭上,这样,古人就有可能会用这座奇特的山崖来代表整个分水岭山区,即把今麦积山(麦积崖)作为整个分水岭山区的“精魂”。实际上,在这片嶓冢山区中,再没有发现比麦积山更为奇特的地貌了。故战国以降,以它为代表,为群山命名当不奇怪。况且这种情况在浙江的“天目”山区,河南的“熊耳”山区也出现,均是以特殊形象(一小部分的湖泊、双峰)来代表整个山区,并以此小名来作为大名。
最有说服力的是,这种情况在晚唐五代也曾发生在麦积山身上。按宋《太平广记》引五代《玉堂闲话》云: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此则明言整个五百里山区被称为“麦积山”,人们以“处其半”之“麦积”即“麦积崖”作其代表命其名。故知,以此“蝌蚪山”名冠于整个分水岭,在上古朴素思想中更有可能。且今天水当地方言说蝌蚪为“guo zou”,音近今“嶓冢”,估计其上古音与古“嶓冢”音也相似,故“嶓冢”可能系直接记古代此地方言的“蝌蚪”音。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推断,古嶓冢山的地理“精魂”或其名字的现实来源地,当即今“附带山梁的麦积山(崖)”。
五
关于“麦积山”、“嶓冢山”,历史上还有一些相关的片断记载。这些片断可能反映了古人的某种认识而未言明,笔者试串列于右以为佐证。
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二载:“秦文公墓,东南麦积山下。”民国《天水县志》因袭之。按《史记·秦本纪》:“文公卒,葬西山。”南朝宋裴骃《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23]按古代西县在今天水市西南,[24]与其东面的麦积山相距甚远,故上述二记载矛盾。乾隆时修志者一定注意到了《史记》的《集解》,却坚持将秦文公墓记作“东南麦积山下”,定有所本。或乾隆前的古人曾如《玉堂闲话》所言,将整个今天水市南边山区统称为“麦积山”,这里面自然包括西山。于是乾隆前的古人可能曾记载了“秦文公葬于麦积山下”。于是乾隆修志人因袭之,但只注意到“麦积山下”而不明其广泛含义,就具体将秦文公墓记作“(秦州)东南麦积山下”即“麦积崖”下了。这记载,从一个侧面,似也反映了“麦积山”曾代表包括“西山”在内的大片山区。
按前文(《汉书·地理志》)已知西县有嶓冢山,嶓冢山广大,其支脉隐然相连,则西县境内诸山当即嶓冢之属。西山在西县,当即嶓冢之属。既然秦文公葬于西山,那么,秦文公墓也可以说在嶓冢山了,上古为此山命名者或许知秦文公墓在此山中,(《山海经·西山经》、《禹贡》大约作于战国,晚于秦文公时)则嶓冢之“冢”字,也许有此意而为之。
六
按民国《天水县志》将嶓冢山的具体位置放在今天水市秦城区齐寿山南支一段上。其原因大概为第一:此地是郦道元《水经注》“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导”之地。第二:此段山符合郦氏《水经注》引《汉中记》载:“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的情况。第三:齐寿山似如冢。笔者认为,前文已论述,嶓冢山范围广大,而此具体为某山者,犯了以偏概全之错误。另外,《汉中记》所记嶓冢山,似指后人附会的陕西蟠冢山,当与天水以南的甘肃古嶓冢山无涉。即使此《记》有所本,则一山分东西水者比比皆是,仅从麦积山迤逦向东北、西南的一脉山看,其东水大致东流,西水大致西流,且东西之水流向汉、渭,比东西水大致东西流,且东西之水皆为西汉水支流的齐寿山南支,更具有分水岭意义。山多有冢形,非独齐寿。齐寿山并非特别奇特,并非群山主峰。且“冢”可比附,“嶓”字何来?所以将此段山名为“嶓冢山”从山区范围等理论上看欠妥,从现实看也说明不了“嶓冢山”名的来由。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关于嶓冢山的相关因素存在着争议,故人们对嶓冢山的真实面目认识较少。本文据前人的研究成果试探,得出结论:“嶓冢山”又名“鲋鱼山”,“鲋鱼”在先秦时可指“蝌蚪”。“嶓冢”二字是记古代“蝌蚪”之音的字。今天水麦积山及其附属山梁相结合的形状如“蝌蚪”,且其地望与古嶓冢山相合,故是嶓冢山名具体来源处。“嶓冢”是在依古“蝌蚪”声的同时,托以“山”之意或者又有“秦公所葬地”之意,被上古地理学家创造出来的书面山名。
(原载于《史学论丛》第 6 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原作者夏阳为曾用名)
(二)绘画史研究
1.也谈麦积山壁画《睒子本生》——与王宁宇先生商榷
前言
《美术研究》2002 年第 1 期刊载了王宁宇先生“孝子变相—畋猎图—山水平远——麦积山127窟[25]壁画《睒子本生》对中国早期山水画史的里程碑意义”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过去,一些老美术史家也曾注意到此壁画,但都未曾大胆地提出过如“王文”之结论[26],本文也有以下与王先生的分歧。
一、《睒图》是人物鞍马动物画而非山水画
山水画是“以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独立完整的山水画可全面地研究其各个方面,尤其是其构图图式。“王文”为研究山水画的图式,力图将《睒图》称为一幅独立的完整的山水画,即所谓“独幅”的山水画。如:
王文第一节有:“它还堪称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笔者按,既是“里程碑”,王先生就应当认为它是真正的山水画。
“王文”第二节有:“但人群及动物形象在画面上所占面积较小,而群山、河川、原野、树木、池沼、窑洞等景物却几乎布满了整个画面,而且这些景物具有统一性、连续性的组织关系,他们为人物活动的历时性过程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自然空间环境,也同时形成了支配整个画面构图节奏开合起伏的骨架系统,是整个画面的主旋律所在。”笔者按,王先生的意思是:此图的主体是山水环境,是山水画。
“王文”第三节有:“《睒图》具有独幅画的有机的形式面貌。在这里,山水业已超越了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和环境的衬托的地位,在构图中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相形之下,倒是作为佛即孝子的本生故事之情节内容在幅面中有所剪裁,而这正是为了突出画面中的环境景象描写的自然性、集中性与完整性所需要的。”
笔者按,王先生认为此图不是人物连环画,而是的山水独幅画。
总之,王文的意思是,此图是一幅主要表现山水的独立山水画,山水内容非附庸的配景。以此为基础来谈早期山水画史。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及其以上的时代,真正的独立的山水画见于记载的就很少,传世的和考古发现的山水画也几乎没有形成公认的规模。著名的《洛神赋图》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物故事画卷,不能称为独立的山水画,《女史箴图》和《列女图》中的山水也只是片段,况且它们都是传世品。如果麦积山《睒图》作为考古材料能称为山水画,因它处在文献记载中山水画的形成发展时期,那么自然是稀见的里程碑,(更何况还有王文所谓的平远图式)。问题是,如下文所述,我们看不出它是一幅主要表现山水的山水画(也看不到后世山水画以它为楷模的现象)。因此难说是里程碑。
具体地看,《睒图》如同传世《洛神赋图》一样,是主要表现人物故事的情节的。二图均可作如是观察:从单个的人物动物看,自然空间环境肯定会大于他们,但从画面主要去表现的主体看,人(群)及动物(群)则是其着重所要表现的,人、动物,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形成的活动空间范围在画中的面积,也大于周边的,非其活动范围的山水环境在画中的面积。就《睒图》看,画面是上小下大的梯形,人群和动物群所形成的较密集、呈规模的活动空间范围所占的画面在梯形的下方偏右,占画面的3/5强,处于画面的具有基础和主宰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与王文相反的结论是:人(群)及动物(群)的活动场面和情景,形成了支配整个画面构图的疏密开合起伏的骨架系统,是整个画面的主旋律之所在。
另外,看一幅画中的主旋律所在,要看是什么形象和事物掀起画中的高潮?
或看画中的高潮在哪里?山水画中,是山水形象掀起画中的高潮;人物画中,是人物场面掀起画中的高潮。图中,是人物的场面,掀起了画面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情感高潮,只不过是多时空的人物鞍马等场景用了一个山水环境。不能因为人物情节有剪接而否认它的主体性,相反,高潮所在的连环画故事情节表明,山水只是作为其背景。因此,在构图中,人物应该是作者首先考虑到的,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睒图》和《洛神赋图》应该是人物及其相关的鞍马动物等的连环画,王文所谓《睒图》“具有独幅(山水)画有机的形式面貌”是不能成立的。
二、《睒图》的山水背景是“类似于斜轴侧投影式”的构图图式而非“平远”构图图式
王文力图将《睒图》描绘成平远图式,如:
王文第二节有:“画幅右段约占1/5底边长度部分,其上部画面是远山、层林”“中段,约3/5底边长度的画面上,横向伸延的起伏原野从前景层递推向画面纵深;向上是远山拔起,层叠逶迤,气象旷远”。(画面左部)“都在稳健老到地兜回着全幅的‘气’,也加强着向画幅中部纵深消失的空间整体感。”
王文第三节有:“在这个复杂的现实自然环境中,画师明显地把握住了一条能支配全幅的统一的视平线(约略在画面高度的2/3处),从林郊、原野一直贯穿到深山丛林,成功地组织出一个旷阔而符合视觉合理性的空间。”
因此,王文的第四节有:“与目前已知的遗迹相较,《睒图》堪称中国山水‘平远’法运用最早的范例。”
笔者按,右段1/5底边长度上部所谓“远山”不能成立。
因为第一,如果是“远山”,则其上的“层林”过于高大。因此“远山”实为低丘,“层林”实为灌木。
第二,这些灌木同《睒图》中部前景处,马蹄下的山坡上的灌木大致相当高。所谓的“远山”上有明显的石头,又与此图前景处的石头在形状和大小上都差不多。因为前景处的石头、灌木和最后景处的石头、灌木的大小比例一样,故此图无“远小近大”的观察方式,所谓“远山”应看作画面后景处的低丘而已。
第三,所谓“远山”处有一坐禅的人物以及一只飞鸟的形象,也与前景的人物和鸟的比例一致,说明了同样的“非平远”现象。
所谓“中段前景层递纵深,向上远山拔起”,也是不能成立的。笔者观察,所谓前景处,其前和后的石头大小一样,非远小近大;且较为平缓的,可供鞍马驰骋的层层山坡,几乎画成了相同的,一宽一窄相间的,平行线构成的长条形,且颜色也是大体两种机械地相间;所谓远处和更远处的山,其颜色也是大致两种,在块面上深浅机械地相间,而非渐渐冲淡的情况。因此,此段景色无递进的构图形式。另外,所谓“拔起的远山”,在其右处的一座上,却长了两棵极为高大的树,与此图前景中的树木,如泉水旁和茅屋旁的树木大致相同大小,远山上的石头也与前景处的石头形状基本一样,大小大体一致,这些也均与平远观察法相抵触,说明图中所谓“远山”不是因透视而显小的山,而应看作是后景处的低山丘而已。另外,在此处左边的所谓“远山”的坡石间,有一游行的人(神),也与《睒图》前景中的人物比例一致,也说明了同样的非“平远”现象。
画面左部,在睒子中箭的泉水旁的上部有几棵树,此树如按平远法观察当小,但却与整个画面前景处的树,如画面左下部茅屋旁和山坡上同种的树,大致同样大小。说明此处画面无“远小近大”,其“兜气”并不稳健老到,也未“加强着向画幅中部纵深消失的空间整体感。”
在左部画面中,笔者还注意到,泉水是向画面上部,即后景的右后处流淌的(虽然泉水后部被后景的山石所遮挡)。这说明山图的右后处,即整个画面的右上部的地势较低,画面前景,尤其是左前景处的地势较高,那么,所谓“远山”应为低丘的(本文的)看法就更趋合理了。试想,如画面右上为高山山脉的话,则更有可能与左上的主峰相连形成地势较高处,小小的泉水不可能向画面右后部,从山脚低处将高山山脉切割成极窄的小峡谷而流出去,而只能向画面的前部流淌,因此,正因为泉水没向前部流淌而向画面的右后流淌,则更明显地表明,画面中,右后部,即右上部的所谓“远山”实际上是“低丘”而已。
王先生只注意到画的某一部分,而未注意到画面的某些关键部分所形成的整体观察效果,同时又被古壁画上部的残损所形成的空灵幻觉所迷惑,难免就产生王文中所说的“气象旷远、极目之旷望、及冲融、飘渺、冲淡、旷阔、暝漠、微茫、幽远、荒远等山水平远意境”的设想,并欣赏为“复杂的现实自然环境”。
但这毕竟是一种“幻象”,非此壁画的原始效果,原始的效果是,其色彩几乎均为平涂,较为艳丽,其背景色,包括以所谓平远法观察的,画面上部必然作为天空的地方均被平涂为深红色。因此,壁画原作者并非强调山水的自然色彩效果,而是强调人物画背景的深厚的装饰性色彩。另外,此壁画的造型也是较图案化和装饰化的,如山石多几何图案式,多片状,树冠多呈封闭状等。更重要的是,因此而产生的总体构图图式,必然或连带地也会呈装饰性、平面地图性的效果,而非递进的效果。这就是,画面的空间感不充分,缺乏自然的远近感。既然“无远近纵深感”,也就无严格意义上的“透视”或所谓“散点透视”,也就没有王氏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在画面三分之二高处有一条“大致统一的视平线”,所谓“旷阔而符合视觉合理性的空间”及“中国山水平远法最早范例”也就无从谈起。
上述《睒子本生》构图图式,在麦积山127窟中的其他部分的壁画上基本上也是如此,即:在同属于大树的情况下,后景树和前景树的大小比例一致;同时,后景的人和前景的人的大小比例也是一样的。不存在“远小近大”的效果,不存在“平远”的构图图式。[27]
虽然王文为了说明《睒图》的平远不孤立,举出了北魏的《孝子石棺石刻线画》已有远小近大的图式[28],即使如此,但《睒图》如上文分析,却在图式上较原始。因此,总体上看,《睒图》不能同北魏《孝子石棺石刻线画》比附,而应被看作汉魏晋画构图图式的继承。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睒图》没有所谓“平远”的构图图式。画面不是整体的远小近大,而是远近事物,包括远近人物、动物,大小比例一致,有相互的遮挡,呈平面和立体结合分布的形式。
其构图图式为视平线非一,且是可远近移动的斜俯视的观察效果。因此,其图式颇为接近于斜轴测投影图式,较接近于汉代绘画多出现的,那种平面布局和立体投影相结合式的“平列诸物”的构图,但在复杂性和稳定性等方面有所发展。
三、《睒图》不能改写中国山水画史
所谓改写,主要指从“质变”方面的改写,因此王文力图在质的方面,用《睒图》来改写(一)美国美术史论家方闻先生的“所言”;(二)山水画史上的张彦远“定理”;(三)中央美院教材的“习惯的学术结论”。并且,在中央电视台于2002年4月播出的《美术星空》以及5月份西部频道中进一步宣传,谓发现了麦积山石窟的《睒图》将“平远”图式的产生时代大幅度地提前了,因此从三方面改写了中国山水画史。故,本文也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1.《睒图》难以修改方闻先生在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判断
王文在其第四节末尾中有:“《睒图》在山水表现上凸现出来的与上述(平远)特征相符合的品质,使我们对中国山水画空间法则成熟的时间有了一个具体实在的新的认识线索。方闻先生过去所言‘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从唐之前(7世纪前)到元代初期(13世纪末)的山水画,可以说是从表意性符号到创造视错觉空间的发展过程……在七八世纪期间,固定的构图图式有了发展……’[29],现在可以改说为:在五六世纪之交的北魏后期,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可以看到山水画‘从表意性符号到视错觉空间的发展’探索,已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笔者按,王文所谓决定性的突破,即指《睒图》在山水画史上,首先出现了较强的统一的空间纵深感。但是,如本文第二论点所述,《睒图》并没有在山水表现上凸现出来平远的品质特征。因此,王文的误解所导致的,对方闻先生从考古发现所进行的,中国山水画史的判断的“改说”是不能成立的。
2.《睒图》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指误于张彦远的著名论断
王文在其第6节前段中有:“至迟在《睒图》这个时代,中国山水画的本体在表达自然环境上业已能够形成基本合理、真实而完整的画面。在这个时期成问题的却是那些外加的、主观先验、非现实理性的人物故事情节组合。它们一方面不肯轻易离开前台地盘,一方面又逐步衰退着。这是否应当看作中国山水画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发展(蜕变)阶段呢?”
王文在其第6节后段中有:“在《睒图》上,摆脱古拙粗放或流动华丽的装饰图案遗痕、注重视觉感受与理性认知、趋向自然写实的迹象多有表现。……这些绘画上的具体处理都透露着一种社会审美风尚转变的信息。因此,它给人的美感与南朝《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像模印砖画》(甚至北魏洛阳《石棺线刻孝子图》)中景物的装饰性图案美都有判然之别。”
因此,王文在其第七节中有:“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以质疑的态度重新审读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那一段为后世学者反复引证奉若定理的著名论说: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这个说法现在显见是偏缺有误的,如果不是有意故作抑扬的话,至少说明作为批评家和画史家的他,眼界仍然有局限而妄夸‘皆见’。”
笔者按,王文以上的说法应该解剖为:同“平远”相对应,《睒图》的山水树石也表现得较为自然写实,非“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非“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并认为此图作为山水画,人物所占的比例小,且图中有“人小于山”和“河川”的情况,故认为张彦远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论断有所未见。
首先,我们前文已经否认了所谓“平远”的论调。
至于山石的所谓“写实”,我们看到,王文所举的例子却是题材方面的,而非技法方面的,如所谓与“天水一带所见实际地貌相似”,并没有举出写实的艺术技法的进步。画均有相似之处,有的像北方,有的像南方,但王文并没有举出相似的程度是如何加深的。况且王文所谓地域特色的“山脉河川坡梁与丘石溪涧陂池相间”并不与张彦远的描述矛盾。而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此壁画的艺术形象,应当复原到它原来未残损时的样子来看,那恰恰是“古拙粗放或流动华丽的装饰图案痕迹”。且众山(包括众低丘)之势,起伏如圆弧等规矩之状,大致色彩平涂,故“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的装饰感形象的描述成立。又此图中的石头多具“符号”感,其色彩多平涂如薄片,分布于山峰和丘坡之间,也和“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相合。
至于树木,王文所谈的所谓“写实”乃“画中树木多作摇曳状,充分体现着西北多风的气候特点,称得上是真正的‘风景’;许多树木的种属也具有很鲜明的地域特色(如白杨、落叶松、柳树及茅稍)。”
这还是说明地域特色,也同样没有说明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有任何创新的写实成分。《睒图》中的树干、树枝的具有图案化的平面排列形式,少立体的“树分四枝”的因素,且较为“光滑无鳞”,并没有大的突破性的写实方向的进展,因此,还应看作是“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南北朝其他画中的树木同样能看出一些种属的不同,并非此图所独有的特点,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像》中的树木均个性分明,比起麦积山《睒图》中的树木形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文中第二节提到的,《睒图》中的“河川”“河流”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王文把画面下部的山坡,因其色彩较暗,误认为是河川了。因如是河川,则画面右部的车马和人群就会“不合理”地站在河水流经处,甚至河水里。古人表现水面,一般色调较明亮,127窟其它壁画(如《西方净土变》和《涅般变》中的水面,颜色也一般较鲜亮,(《睒图》泉水中加了几点石青色和其它的浑浊色,则表现《佛说睒子经》中所谓睒子中箭后泉水干涸的情景),一般不应有用暗色甚至黑色来调色表示水的深邃的(这种水的深邃,一般在西画以及现代国画的表现中才有)。因此,《睒图》并无大面积的河川形象,只有泉水,颇合“水不容泛”。
此图左侧茅屋附近有“人小于山”的现象,但不足以批驳张彦远的著名论断。张说为“或人大于山”。按,“或”乃“有的”之意,和“不是……就是……”之意,但决无“率皆”之意。否则,张彦远就不会在两个“或”之后再用“率皆”,而应会直接写作“率皆水不容泛,人大于山,附以树石,映带其地”。
故张彦远的意思应为“有的图画中人大于山”或“在相当一部分的图画中,人大于山”,或这些古画中“不是水不容泛,就是人大于山”。他并不绝对地说,所有魏晋以降,隋唐之前,画山水树石的相关图画中,均存在“人大于山”的现象,他并不否认古画中有“人小于山”的情况。事实上,无论是《洛神赋图》还是《北魏画像石》[30]中,均存在人物“小于”长着树木的山包和甚至长着草的山石的情况。
另外,王文中还有一处所谓“写实”,即所谓“二老居住的不是天竺式的茅庐,而与陇山地区旧时农家的土窑洞形制十分仿佛。”则是由于识图上的错误,而急于认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写实”了。以“柴草为屋”的“茅庐”是《佛说睒子经》中所明确规定的,虔诚的绘画者不会在壁画中作大的改革,况且此图中二老的居所也是茅庐,为立体的尖锥形象,非窑洞口的平面平拱形象。
从以上对此图的分析看,王文中所谓:“这些绘画上的具体处理都透露着一种社会审美风尚(向写实)转变的信息。”也就不是那么强烈了。应该说,此图与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像模印砖画》,甚至北魏《石棺线刻孝子图》中景物的装饰性图案美基本一致,而非如王文所谓的“有判然之别”。由此观之,张彦远之“定理”,信以为然。
3.《睒图》不能改写习惯性的学术结论
王文以上错误地理解考古材料的“写实”结论,必然引起对南北文化比较方面的错误理解。学术界历来以为,在南北朝这一文化交流时代,南方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但王文力图通过山水画及其构图来说明北方的要比南方的先进,从而动摇南朝在文化上的主流地位,它至少要说明的是,从考古材料的情况看,在南北朝后期,北方的山水画要引起重视,其成就要高于南方。同时,它强调,北方山水画的“先进”,是对孝子、孝子变相、畋猎的写实表现所激发的,这种“写实”表现是南北朝山水画“进步”的直接动力,因此怀疑中央美院教材的习惯性学术结论。其具体表述如下:
王文在其第5节中有:“南朝模印砖画上这种衬景处理,虽然已较汉代以来美术作品中殊少自然景物的空间意识有一定的进步,但跟北魏《石棺孝子图》相较,就差距很大了。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来比较《孝子石棺》与《睒图》,我们又会认识到:当中原本土的相对静态的孝子图题材一旦被外域引入的内容活跃、环境场面宏大的”孝子变相“题材替代时,这种绘画空间意识的进步又获得了激越的动力和鲜活的施展机会。”
第6节有:“《睒图》在宏大空间、复杂层次的视觉真实把握上的进步确是惊人的。联想到古画著录中记述过而如今却已佚失的古代一系列畋猎题材绘画作品,注意到这类题材(特别是大幅)作品中旷阔风景几乎是不可回避的描绘对象,就不免让人猜测它们可能是中国山水画,特别是平远山水曾借重过的主要演练阵地。……南北朝时代在政治上处于强势、在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大潮中处于潮头地位、采取积极进取态度的北方,其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与研究。而这个问题以前并不被我们很看重。”
王文在其第7段中有:“对麦积山石窟壁画中山水风景画的研摩,触发我们对以往一些习惯的学术结论产生怀疑:
山水画的发展和当时玄学思想的盛行、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有关,也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有关。[31]
迄今,考古发现的实际材料仍不能支持上述认识。自然客体是否秀丽不是山水画艺术本体产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玄学和隐逸也未必能胜任作为山水画进步的最直接的动力。相反,文学界关于六朝山水诗发展史研究所得的一个重要论断移用到山水画演进史上可能也是同样适当的,那就是:玄言不死,山水不立。”
笔者按,所谓“差距”,“潮头地位”,“积极进取”,“‘很’看重”,“考古材料”,“山水画进步”,王文的言下之意已很明显了,王文感兴趣于用考古材料来建构中国山水画史,虽然有些遮遮掩掩,其结论当然是北朝的作品要“进步”。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皆见”,王文的“言下之意”就难成立。
自然南朝《竹林七贤模印砖图》比北朝《孝子石棺图》的空间感少,但南朝《邓县画像砖》中的一幅无榜文的《吹笙凤鸣图》的山水空间感也较强,其前部有形象较大的人、树和凤,中景有由远而近的云气,远景位于画面的右上部,为一带远山。虽在茂密上不比北朝的《孝子石棺图》,但在自然和飘渺感上略胜一筹,其区别只在,南派和北派的风格不同而已,不在本质上的构图图式上的先进或落后,因为两者都有近、中、远景的具体表现。
但两者的远山,都靠近画面的上部的边缘,仿佛是图案的填充装饰部分,而两者的整个画面确实都是满满的,为缺乏较多天空面积的,有很强的图案感的画面,因此两者(在散点透视意义上)的视平线,都靠近画面内容的上方,其构图图式只能被称为“深远”,没有“平远”。况且,这些“石画”、“砖画”也并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因此如果北朝的《睒图》壁画是场面宏大,层次复杂的“平远”山水画,自然它会成为里程碑,自然会引出北方山水画进步的结论。但通过我们对王文所谓“平远”和“写实”的批驳,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麦积山的“考古材料”不能支持王文所认为的,北朝“先”出现山水画进步的状况。
因此,仅从考古材料上看(姑且把石画和砖画看成画),在南北朝后期,“山水”是“人物”等题材的背景,无独幅山水画;南朝和北朝的“山水”都带有图案化的因素,北方的较茂密,南方的较疏朗,都能表现一定的空间感但不充分;在构图图式上,其“山水”背景或许可勉强认为出现了“深远”图式(如《孝子石棺图》和《邓县画像砖》中的无榜文的《吹笙凤鸣图》),但迄今仍未发现“平远”图式。总之,南北朝后期,南北方对山水表现的总体技术水平大致应相当,这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频繁、广泛和逐渐融合的趋势的结果。其他方面的文化现象也是大致如此,如佛像的褒衣博带式样,此时,南北方风格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本一致;书法的帖、碑形式,此时在南北方也基本都有,只有细节上的差别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且,我们发现,南北朝的绘画中,恰恰是为了表现人物,可以忽略山水背景的表现真实,并使之协调于人物,如“人大于山”“钿饰犀栉”“伸臂布指”的表现形式[32]。因此王文所谓山水平远的产生借重了人物画《畋猎图》的说法证据不足,何况表现了“畋猎”的麦积山《睒图》非平远山水画。故,如果探究南北朝山水画,因无独幅山水画的考古材料,又不能主观地从考古材料中的“人物画”中去寻找山水画产生及发展的原因,那只有从文献和思想史,尤其来自“江南”的有关山水画的信息中去寻找,别无他法,所以,王文对玄学、隐逸和江南秀丽山水与山水画进步的关系的“否认”,以及对“非文学史”意义上的,而是“山水画史”意义上的“玄言不死,山水不立”的“肯定”,没有考古材料方面的依据。
另外,北方重禅修,多开凿石窟。南方重义理,以木构寺宇为主。因此,北方的考古材料多土石,易于保存。不能因为北方的现存考古材料丰富而认为其文化先进,南方虽较少石刻画,也应有大量的壁画和其他种类的画,只不过由于气候和历史战乱等原因,不易于保存罢了。基于这种考古的“皆见”,我们就能更客观地看待南北朝山水画演进的历史和现状。
总之,我们否认了麦积山壁画《睒图》的山水平远图式。同时我们也看到,麦积山127窟中的其他壁画同《睒图》的构图图式基本一样,均较缺乏空间纵深感,同样,也不会有山水“平远”甚至“高远”和“深远”的构图图式的存在。因此《睒图》不能“改写历史”,相反却能“证经补史”了,基于此,作为考古材料,它可以又一次让我们客观地、历史地来感知古代优秀的壁画作品。
四、絮论
从麦积山127窟《睒子本生图》,以及同窟相关的《太子舍身饲虎图》、《十善图》、《西方净土图》、《维摩变图》、《八王争舍利图》等上,我们感知到的是,并非“陶然于自然山水之中”的情趣,而“损己利他”的善行,和“一心向佛”等的种种行为表现。这些图画给我们的,主要不是山水的幽静清远,而是人们活动场面的热闹、嘈杂、激烈、甚至熙来攘往,是人的善行、佛性的颂歌,以及人的美德的壮丽升华,给人以人类可以通过积极进取,以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方面的鼓舞。其背景山水技法和构图并不是那么“先进”,正是“人物故事”主题的“先入为主”所要求的。正是主题人物、车仗、宫殿院落,用类似“斜轴测投影”的,注重“平均表现”的手法,支配了山水背景也必须以同样的形式“映带其地”。正如王伯敏先生所论述的“树木为群山量体裁衣”[33]那样,其实山水树石背景也为人物的特殊艺术风格和构图“量体裁衣”了。总之,这种映带其地的,非有远近平远纵深感的拙朴的山水图式,承栽并保证了故事中的人物、车仗、宫殿院落建筑具有更强的表现性,即远近的人物、车仗、宫殿院落建筑以同样的大小,表现在我们面前,使观者看清楚内容,而非欣赏有“远近真实”的所谓“风景”,从而起到强烈的宣传鼓舞作用。它具有很强的示意性。这同某些汉画和魏晋画的构图的场面表现形式是相似或一致的。
我们不贬低《睒图》的艺术价值,如同不任意拔高它的地位一样。客观地看,在南北朝“画山水树石”的总的艺术风格中,《睒图》在表现山野的场面上,比同时期同类作品[34],甚至更晚至北周[35]和隋[36]的同类作品都要更具有疏密开合,表现出较生动尽致而广阔的特点。但它们的造境上方法仍未脱离那个时代较原始的壁画构图图式。《睒图》生动尽致而广阔并不是平远,它的构图形式仍处在继承汉画风格的魏晋艺术的总的质朴的格局中(如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屯垦图》和《营垒图》的构图图式,同《睒图》的构图图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诸如《孝子石棺图》和《邓县画像砖》
中,具有远近纵深感的画面,但《睒图》的构图图式并不是那么“进步”,这可能是为满足观者在较远和有角度的情况下,能看清楚较为复杂内容的要求等因素所决定的。
总之,麦积山127窟《睒图》所表现的,基本上不是山水平远的,较为写实的广阔场面,而是有山水背景的较为图案化、装饰化、平面化的人物活动的广阔场面。它在山水画史中,在画山水树石方面有一定特殊性的量变地位,但并没有产生各方面突飞猛进的质的变化。它的艺术成就上的辉煌并不在于图式,而是在于较为广阔的场面;人物情景布局的疏密开合;山水配景与人物故事场面的对角布局;山水背景独立存在面积的增加;多了些“人小于山”的结构,以及某些细致的绘画表现和生动的艺术造型等。
结语
王教授在麦积山壁画前呆的时间较短,同时又囿于受到感染的心情,于是激动于眼前壁画残损幻象之所见,叹张彦远之所未“皆见”以及今人的不重视,同时,也因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自夸家珍者的误导,故有智者之失。总之,标新立异的观点要经得起对现代考古材料个体内部结构,和多方面客观情况“皆见”的考验。
(本文最初公布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办的,2002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原载于《美术研究》2004 年第 3 期。后载于《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2002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莼菜条、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创新——从古文献、出土文物、石窟、传世品的有关因素和图像谈起
文献中“纯菜条”始出现于北宋米芾《画史》中,“陁子头”“道子脚”始出现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本文探索上述三词的具体所指,就以前的某种相关误解进行讨论。
一、莼菜条形态的文献依据及其与天王的关系
北宋米芾《画史》:“唐画:……王防,字元规,家二天王,皆是吴之入神画,行笔磊落,挥霍如蓴菜条,圜润折算,方圆凸凹,装色如新……”
按:蓴,乃莼的异体字,蓴菜条即莼菜条。
现实中的莼菜,是一种附有透明胶质物的卷曲的尚未展开的嫩叶,其具体形态是两头尖,中间稍圆厚。此种“嫩叶卷”富有张力,能圆转而俏丽,故显得挺健,整体具有洒脱的流线型,故可被称曰“条”。但这种菜条的具体形象稍短,是否就是“莼菜条”这种绘画线条的具体形象呢?回答是肯定的。画史中著名的“莼菜条”的形态,就是“莼菜嫩叶卷”的条状形态。
首先,它符合上述古文献中,有关莼菜条行笔的“挥霍”一词。挥霍,即用笔有外拓展带笔锋之势,且着重“按”于线条中部,“带入”“提连”于线条两端,形成线条两端的尖头,并较为潇洒随意。因此挥霍用笔,颇合“莼菜嫩叶卷”生动的具体形象。
其次,它符合天王形象。在上述《画史》记载中,除了吴画天王像提到莼菜条外,凡提到的其他题材的吴画,均未曾认为是莼菜条用笔,可见莼菜条与天王关系的密切,当是天王类绘画所专用或多用的线条。而事实上,本文上述“莼菜嫩叶卷”所形成的短促线条,颇为符合用于天王像上。
因为天王多为武将的短装扮,富有强烈爆发之健美风格,而本文所述的“莼菜嫩叶卷”之莼菜条形态,各个稍短的菜“条”可形成笔断意连的状态,可表现在天王短促的肌肉块上,表现在天王转折较多的风动披巾上,以及表现在天王其它较细碎而灵动的装束边缘上,如:扎住的衣袖和裤脚的边缘等。所以,由现实中的“莼菜”和古文献中的“挥霍”和“天王”三位一体的链条,可证明“莼菜条”线描的具体形态,就是现实中“莼菜嫩叶卷”的条状投影形态。
总之,莼菜条应是与天王类形象有密切关系的稍短而灵动的线条,主要可表现短促努张物体的力度感和动感,是形成吴道子“离披点画”[37]疏体绘画风格的主要因素。其所主要表现的题材,除天王外,类似的可能还包括金刚力士,包括帝释、荧惑、钟馗等佛道类神将形象,甚至魔鬼类形象,也可次要或零星地用于其他题材中。
1978 年发现的苏州瑞光塔第 3 层天宫中藏晚唐五代“四天王木函彩画”上的天王形象,较为接近莼菜条式的天王形象,其服饰肌肉和,由众多的莼菜条线描构成。
莫高窟及其附近石窟中,现存盛唐以后的天王力士壁画像和(可作绘画参考的)雕塑像,似没有典型的,从肌肉到服饰,由较多“莼菜条”线条所组成的形象,但其天王金刚力士类壁画中,其面部和赤裸手臂上的少量短线纹理,亦是莼菜条式的线条。如:中唐,榆 25窟,北壁初会听法八部众壁画局部。
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身唐代金刚力士绢画,其裸露的肌肉部分上的线条,有些近似于莼菜条。石窟中,在其他类形象的壁画中也可以寻到莼菜条的点点滴滴,如某些人物面部的皱纹,动物身体上短促的肌肉隆起。
因为莼菜条主要表现的是某些特定的题材,或某些题材的部分形象,它
1.“天水”名考
据《汉书·地理志》,天水郡设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天水”之名,始见古籍于此。但当时命此地名的统治者以何为根据,本文之前,已有相当的说法,笔者试再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篇》[1]:“耤水又东北径上邽县。……上邽县故城……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
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无稽,虽然,根据现在天水地区多大股泉水的现象看,古天水郡应有积泉水成湖的事实,但“白龙”乃神话,故清代学者王先谦曰:“世或訾其(郦道元)好奇骋博。”[2]
北魏时,上邽(改名上封)治天水郡,[3]郦氏记上邽县故城,在有关天水郡名之来由方面,大概在缺乏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仅寥寥数语记载了当时当地的民间传说而已,故北宋苏东坡曾“叹郦元之简”。[4]
大约同一时代,南朝刘宋之郭仲产在其《秦州地记》中关于天水郡的记载曰:“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这同郦氏观点相近,皆本于有神异现象之湖水。郦氏说湖中“风雨随白龙”,郭氏说“湖水冬夏无增减”,因此他们认为湖水乃上应于天,因名“天水湖”即湖水为“天水下注”或“天河下注”而成,故有“天水”之地名。又《天水史话》[5]和《麦积山的传说》[6]中有“天河注水”的传说,以及《天水报》载《天水与小天水》[7]中,有秦代“小天水求神降雨成湖”说,也欠妥当。因为“天河注水”传说,实际上就是郭仲产和郦道元的说法,不过更明确地说出来了二位的言下之意,湖水由神异的天河注水而成。以上这些说法,都把“天水”地名的来由,归于某种神异现象,所以只能以神话传说看待,不能做为“天水”地名来由的历史事实根据。
而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时,天水郡曾改名为“汉阳郡”。阳者,水的北面。从历史沿革中,我们得到了启示,即天水郡与汉水有关,言位于其水之北。
《诗·大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也称天汉、天河、云汉。
地面上的汉水,顾名思义,就是天汉在地上的延续。那么,汉水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是来自于天上的,来自于“天水”的。于是,汉水接天,其上源之地,就是“天水”之地。
《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故漾水为汉水上源。
又《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洋水出焉。”
按“洋水”即“漾水”。据《水经注·漾水篇》引晋地理学家阚骃云:“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梁州部分,氐道与西汉天水郡的东南部相邻。
又据《山海经·西山经》之次序,昆仑山在中国西北。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治,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可知河西敦煌境内,有与昆仑山有关的地名。今人萧兵《楚辞文化》亦认为:“以黄帝为传说祖先的夏人集群最强大的一支,发源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以‘昆仑’(其原型祁连山)为圣地。”可见昆仑山古代曾被认为在河西祁连山周围一带。
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凉州部分,西汉时的天水郡,黄河过其西北境,天水郡接壤连通河西走廊。而西汉元鼎三年设天水郡时,河西并未设郡,[8]所以,当时的天水郡直接通西北的河西走廊,即通昆仑山。漾水从昆仑山流来,按阚骃的说法,潜流至天水郡东南相邻的氐道县,“重源显发”,复如《禹贡》所说,从嶓冢山中,东流为汉。
于是天水郡是被认为连接昆仑山的汉水上源之地,(汉为霄汉即天河意,此郡为上得天河之水处)所以“天水”郡便由此得名。
以上是关于汉水上源与天水郡关系的地理观点,这种观点在古代并不是孤立的。
据《王氏合校水经注·漾水篇》,孙校曰:阚骃“其说本高诱(东汉人)”,郦道元亦称“不可全言阚氏之非也”。
又据东汉许慎《说文》“漾”字条:“漾水出陇西豲道,东至武都为汉水。”此说亦被晋学者吕忱所接受。[9]
按《汉书·地理志》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武都与西汉天水郡东南部相邻,豲道在西汉天水郡中,至东汉未变其地望,位于武都西北,此乃直接说明漾水在西汉天水郡中。
由上可见,许慎、吕忱之说;与高诱、阚骃之说是一致的,即汉水上源经过西汉天水郡,西汉天水郡为汉水上源之地。
关于高诱、阚骃所指的“重源显发”或者叫“潜源复出”的说法,是否是古代学者只因汉水而说的呢?如果是这样,在当时的统治者和民众中,其可信性就差了,就很难被统治者做为命地起名的根据。事实上,潜源的说法,古代的别的河流也有,以致成为很热门的话题。
最著名的是河水。
如《山海经·西山经》载:“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
又如《汉书·西域传》曰:河水“东注蒲昌海……皆认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
东汉高诱称[10]:“河出昆仑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
又如济水,《据地志》载:“济水出河东……即见而伏,东出于今济源县。”[11]因此,潜源的说法,古代并不是某一人只对汉水的附会,而是古代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地理认识。因此可被“天水”起名所采用。
以上是天水之名的地理原因。
另外,间接的历史时代原因,是汉朝本身。汉高祖初封“汉王”时,萧何曰:“‘天汉’,其称甚美。”[12]
汉武帝也曾以“天汉”作为年号。
所以西汉时,“天汉”这一代表大统一与皇权国势神圣天授的思想,得到广泛提倡。因而天水郡的设立,正是“天汉”思想的结果,因为有“天汉”之说,才有“天水”地名。而设“天水”郡名,也如同“广汉”、“武威”、“敦煌”等郡名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一样,以期汉祚永昌,如滔滔汉水,源于“天水”,长流不断。
虽然,上述古代对汉水源头(在西汉时,曾在直接连接昆仑山的天水郡地区,重源显发)的地理认识,在东汉正统记载西汉地理的书籍,如《汉书·地理志》(在天水郡等地区的内容)中并无明确记载,而只在其他载籍和一些学者中流传,但是,较离奇的说法并不等于在西汉时没有,也不等于不被统治者所接受。西汉统治者正处于汉代经学创立时期,更相信古籍,比东汉人富于想象力。
且汉武帝本人思想活泼,尊重知识,热衷神仙黄老之学,接受方士说教,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接受神奇的地理思想。于是他又从政治意义出发给新郡命名,以期追先贤之记述,得山海之奇致,扬汉朝之天威。所以,“天水郡”的命名,是汉武帝时期地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完美结合的一个创作。
综上所述,可见“天水”地名,基于“天汉”之说,来由于“汉水上源之地”的位置。古人认为汉水来源于天河,来源于昆仑山这座上应于天的圣山,来源于连接昆仑山的陇上高原那广大而深厚的地层中。而直到如今,这片黄土高原,的确相对比较多雨,且地下水丰富,泉水众多。这或许不是巧合,或许确实因有这方面因素,而使古人认为这片黄土高原是汉水上源的潜流之地,于是在昆仑山附近地带的河西地区没有建郡之前,而为设于这片陇上高原的新郡命名,就理所当然地以上接天河之水的“天水”命名而为“天水郡”。那么所谓“天水”,其本义就是“天河之水”,“天水”地名是指这片土地上接天河,为“天河下注之地”而已。
(此文最初公布于1992年天水市首届伏羲历史文化研讨会,原载于《伏羲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原作者夏阳为曾用名)
2.嶓冢山名考——嶓冢山·鲋鱼山·麦积山
嶓(音bo)冢山,古代名山,见之于《山海经》及《禹贡》,但其名字的来历如何,即为何称嶓冢呢?未见述于古籍,笔者试探,以求教于专家。如果从字面上看,“嶓”字从“山”形,“番”声,而“冢”附后,则“蟠冢”有高山如冢之意。但是,凡山,或多或少有此意,此山何嶓独以冢名?笔者以为此绝非偶然。
一
按《山海经》、《禹贡》所记的古“嶓冢山”,汉水出于此山[13]。又按《山海经·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则“嶓冢山”“鲋鱼山”似为一山。
清胡渭《禹贡锥指》亦日:“《山海经》云:‘汉水出鲋嶓山。’盖嶓冢之别名也。”笔者按,“嶓”为胡渭用的通假字(或另本经所用通假字),原经为“鲋鱼山”。
那么“嶓冢”之名是否与“鲋鱼”有关呢?
按《十三经注疏》载《易·井》:“九二,井谷射鲋。”唐孔颖达《疏》引子夏《传》云:“井中之蝦呼为鲋鱼也。”
按《说文》:“蝦,蝦蟆也。”
按西安市东南有虾蟆陵,一作虾陵,虾即蝦[14]。则“”通“蟆”,蝦即蝦蟆。故“蝦”即“蝦蟆”即“虾蟆”。又虾同蛤[15]。故“蝦”即“蛤蟆”也。
但这只是字面上的传承,内部意思可能有所转变,即今蛤蟆(蛙和蟾蜍的统称)有可能包括不了古“蛤蟆”(蝦)所指。
按《庄子·外物》:“(庄)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乃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之情景。如以今蛤蟆比作鲋鱼,则有悖于生活常识,因涸辙困不住蛤蟆。因此,今“蛤蟆”包括不了古“蛤蟆”所指。
那么古“蛤蟆”可别指什么呢?
现实中有一例可以给我们启示。
河南陕县西门外有一泉名“蛤蟆泉”,《陕州志》云:“水自石眼流出,内生蝌蚪,祷雨辄应。”[16]这似可理解为:“蛤蟆可指蝌蚪。”且是其古意在民间的一种遗留,即古“蛤蟆”即“蝦”即“鲋鱼”可指蝌蚪。
如此,我们对涸辙之鲋的困惑,便迎刃而解。因为“涸辙之蝌蚪,相濡以沫”之情景是常见的。故《庄子》之文印证了先秦时“蝦可指蝌蚪。”的情况。
进一步说,先秦时“鲋鱼”可指“蝌蚪”。
那么是否仅此孤例印证先秦时鲋鱼可指蝌蚪呢?不是的,还有别的证据可凭:
《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按文意,此“鲵”“鲋”当指小的个体。如鲋鱼以今蛤蟆来比附之,依常识,蛤蟆却不会在灌渎中随水漂流,更不能被人守来。这样,则与文意中确实能守来,只是得不到大鱼相矛盾。但如鲋鱼指蝌蚪,则合于实际情况,更合于大小鱼差距悬殊的意思,更符合庄子多用强烈对比的文风。
又《山海经·中山经》:“来需之水……其中多鱼,黑文,其状如鲋,食者不睡。”
《南山经》:“鸡山……黑水……其中有鱼,其状如鲋。”
《东山经》:“……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
《北山经》:“其中有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
《中山经》:“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
按:如以“今蛤蟆”来解释上文中的“鲋鱼”则牵强。
因为,“鱼很像今蛤蟆”很难理解。如果这样,则在经文中,对这些鱼的描述,抛开了与今蛤蟆具有相似之处的,且更像鱼的娃娃鱼(鲵鱼)而不说“其状如鲵”,而直指与今蛤蟆相似,那么这些鱼则简直更像今蛤蟆,甚至分别就是某种今蛤蟆,则无需说“状如鲋鱼”即“状如今蛤蟆”了。
且如此“鱼很像今蛤蟆”的说法,也不好解释所谓“彘身“一首十身”。因鱼如这样,整体不会如今蛤蟆。
但“鲋鱼指蝌蚪”,则问题迎刃而解。蝌蚪本身形状如鱼,故可以与一些鱼相似。且其腹圆下垂如彘(猪)“身”,后拖一壮尾。
如某鱼一首而十小尾,可看作“一首而十身”,而整体仍似一首一壮尾的蝌蚪,今“水母”、“乌贼”“章鱼”等大头部生出若干较小的腕和触手(如尾)的这类水中动物还有很多,一首而十身的“茈鱼”或即此类,整体与蝌蚪有相似之处。
因此,《山海经》的记载使“鲋鱼”指“蝌蚪”,得到了进一步证明。
按宋陆佃《埤雅·释鱼》谓鲋鱼即卿鱼,另外还有其他解释,皆后出。故笔者谨从春秋晚期的子夏言,参以先秦著作推论,不采宋代等说。因此,“鲋鱼山”即“蝌蚪山”也。“嶓冢山”即“鲋鱼山”即“蝌蚪山”也。
二
那么是否蝌蚪与嶓冢之名的缘起有关呢?
按《尔雅·释鱼》:“科斗:活东。”晋郭璞注曰:“蝦蟆子。”则“科斗”即“蝌蚪”也。那么“科斗”与“嶓冢”是什么关系呢?
按“科斗”与“活东”,概古代时一音之转的关系,今天读来也仍有相似之处。所以古字音至今,虽有其变,但应有保留相似之迹的情况。相应,“科斗”与“嶓冢”,今天读来,也有相似之处。故它们的关系,虽不能说是音转意同,但也有可能为“嶓冢”系记“科斗”之音的情况。且“科”可入古韵“歌”部,“嶓”可人“元”部,可对转;“斗”可入“候”部,“冢”可入“东”部,[17]可对转。因此,古人可能从“科斗”音出发,参以从“山”等意象,记作“嶓冢”二字。
三
按“汉水出鲋鱼之山”载于《山海经·海内东经》:“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所属的一段中。清毕元校本中疑此段文字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晋郭璞注或撰的《水经》中的文字。今袁珂先生也赞许,认为这段是其他书籍的拦入。笔者认为,这段文字不管出于何书,当为郭璞时或郭璞之前,有研究价值的古记载无疑,郭璞等并未抛弃之。
按《山海经笺疏》:“(对《海内东经》笺疏)懿行案,汉水所出已见《西山经》嶓冢之山,此经(《海内东经》)云出鲋鱼之山。鲋鱼或作鲋隅,一作鲋鰅,即《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大荒北经》又作附禺之山,皆广阳山之异名也,与汉水源流绝不相蒙,疑经有伪文。《北堂书钞》九十二卷引(“出鲋鱼之山”)汉水作濮水,水在东郡濮阳,正颛项所葬,似作濮者得之矣,宜据以订正。”
笔者不苟同。
按:鲋鱼山与颛顼葬地无关。
“汉水出鲋鱼之山”之下的“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一句,非经文,而是注文。因错简或其他原因注文掺入经文的情况会发生。具体看,在“岷三江……”所属的这段文字中,述水之出入位置,别处均不详言山除位置之外的其它名堂,而在此鲋鱼山独载,为突兀之文,非其类耳。实际上,这句话如以注文目之并不突兀。此乃从别处移植来。按《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羆、文虎、离朱、久、视肉。”《大荒北经》:“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虎、豹、熊、羆、黄蛇、视肉、璿、瑰、瑶、碧,皆出卫于山。”大概作注者认为“务隅”、“鲋鱼”、“附禺”古字相通,故于务隅山,附禺山所属之文,摘其要注于“鲋鱼之山”下。比如取“务隅山”的“颛顼、九嫔葬地分阴阳”,取“附禺山”的“蛇”和“卫”。注者认为此“卫”为“保卫”之“卫”(此意同郭注《大荒北经》“在其山边也”)。而记作“四面有蛇护卫”作为两山众多之物的代表,注在“鲋鱼山”下。这也是注往往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表现。
故,因颛顼所葬而校改“汉”作“濮”难有充足理由。
事实上,笔者也是受郝懿行启发而有上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首次提出“汉水出鲋鱼之山”下经文为注文曰:“疑后人见鲋鱼与务隅山名相涉,因取彼羼入之耳。”此言极当。但他虽在经文中去掉后面被怀疑为注文的一句,却肯定了注者把两山拉到一块的思路,故根据“古字通用”认为“鲋鱼山”与“务隅山”、“附禺山”皆一山也。[18]因此据“濮阳正颛顼所葬”,认为山在濮阳,则“鲋鱼山”处经文中“汉水”为“文”当为“濮水”。这观点同《北堂书钞》九二卷引汉水作濮水一致。笔者认为从水的角度此观点也有误:
按《山海经》通行本承古至今于此(“汉水出鲋鱼之山”经文)处皆作“汉”。
且(实际地理考察)古濮水并非出郝氏所谓“广阳山”或者“务隅山”,而是出于河、济,为渠道性质的小河,与务隅山(郝氏认为的鲋鱼山)关系勉强,因此难说“濮水出于鲋鱼之山”。濮水这类小渠,也难说能列到“江”“淮”“湘”“濛”这些源流自成体系的大水之间。且在“岷三江”这段文字中,主序是支流列在主流后面。假如汉水处改作濮水,则濮水列于济水前,殊为不合理。故“汉”或为“濮”的观点,又一次难有充足理由。
且“汉”改为“濮”的想法,皆因为“鲋鱼”与“务隅”读音相近,被认作一山。但读音相近之山并非总为一山,如《西山经》有“符禺之山”却与“附禺山”、“务隅山”、“鲋鱼山”大相径庭。故“汉”非关“濮水”,“鲋鱼”非关“务隅”,为什么非要把鲋鱼山拉到务隅山身上不可呢?
另外,“鲋隅”出《北堂书钞》,“鲋鰅”出《禹贡锥指》,皆转抄字,无碍“鲋鱼”之为本字。故“汉水出鲋鱼山”所言不伪,“鲋鱼山”乃“嶓冢山”明矣。那么,嶓冢与科斗音近,反过来也更说明了鲋鱼可指蝌蚪的正确。嶓冢、蝌蚪、鲋鱼三位一体的意境,互相印证,道出“嶓冢”之名,从鲋鱼意到蝌蚪音,再落实到嶓冢字的来由。
四
那么什么是“蟠冢山”现实中实物来源呢?即现实中是否真正存在着一座鲋鱼山或蝌蚪山呢?有,那就是著名的天水“麦积山”。
麦积山头大根缩,形如麦垛,故名。其名始见于十六国。[19]但命名者仅仅着眼于此山的主体部分,而忽略了主体部分附带着的山梁。
此梁和主体部分同样,其山石裸露部分多。而梁的尾部渐渐不裸,可以生长草木,融入绿树草丛中。裸露的岩石使人们醒目地看到一个头大拖尾的蝌蚪形象。最重要的是,山的主体部分高大、明显、奇特,且自最高处渐渐向梁部收分,给人们的目光指示出尾部之所在,而其指示的方向确实有一带隆起山梁。即使山梁被树木掩住,仍有地形的隆起隐含着尾部的所在,故远观仍活脱脱地看出蝌蚪的形象。因此先民在此片山区,农业生产不太发达,麦垛概念不强烈的情况下,看到此山,最有可能联想到山间溪水中常见到的动物“蝌蚪”而名之为“蝌蚪山”。
那么今麦积山的位置是否就是古“嶓冢山”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据《汉书‘地理志》:“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
按氐道、西(县)均在今天水市南边山区中。[20]养即漾水。《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故知氐道有嶓冢山。而上文西县有嶓冢山,则一山跨二县。
而《山海经》、《禹贡》只说嶓冢出汉水,并未限定山的范围局限为一个地点的一座山峰所跨区域。据《山海经·西山经》,蟠冢山(中心)分别与两旁的山(中心),距离三百多里,则它本身东西跨度应为三百多里。《禹贡》记山更少,则山的跨度范围更宽。因此有理由相信,《山海经》、《禹贡》所指的嶓冢山应包括今麦积山在内的,今天水市南边广大群山,嶓冢山是一个广大山区的概念。民国《天水县志》也有相同的看法:“汉水发源县南百里间,是知境南诸山当为嶓冢无疑矣。”
以上是根据《汉志》所作的推论,但历代学者曾对此山的位置争论不休,皆因看到今汉水出处与《汉志》所载不符,即今天水市南边山区发源之水却流不到今汉水中,而流入今嘉陵江。但80年代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揭开了这古迷。他引《地理知识》1978 年第7期载李超文:“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入四川,而是东流入汉江的。”李超此文,是就他发现的古河道而言的。故刘琳先生说“盖在战国以前,嘉陵江至阳平关附近东流入汉中。”[21]
故战国以前之嶓冢山,应排除其他地区后代附会的山,如陕西嶓冢山[22],应是今天水市南部,渭水与嘉陵江上源的分水岭。而今嘉陵江上源仍称“西汉水”,也正说明了此分水岭正是古嶓冢山。
而今麦积山(麦积崖)正处在这条分水岭上,这样,古人就有可能会用这座奇特的山崖来代表整个分水岭山区,即把今麦积山(麦积崖)作为整个分水岭山区的“精魂”。实际上,在这片嶓冢山区中,再没有发现比麦积山更为奇特的地貌了。故战国以降,以它为代表,为群山命名当不奇怪。况且这种情况在浙江的“天目”山区,河南的“熊耳”山区也出现,均是以特殊形象(一小部分的湖泊、双峰)来代表整个山区,并以此小名来作为大名。
最有说服力的是,这种情况在晚唐五代也曾发生在麦积山身上。按宋《太平广记》引五代《玉堂闲话》云: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此则明言整个五百里山区被称为“麦积山”,人们以“处其半”之“麦积”即“麦积崖”作其代表命其名。故知,以此“蝌蚪山”名冠于整个分水岭,在上古朴素思想中更有可能。且今天水当地方言说蝌蚪为“guo zou”,音近今“嶓冢”,估计其上古音与古“嶓冢”音也相似,故“嶓冢”可能系直接记古代此地方言的“蝌蚪”音。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推断,古嶓冢山的地理“精魂”或其名字的现实来源地,当即今“附带山梁的麦积山(崖)”。
五
关于“麦积山”、“嶓冢山”,历史上还有一些相关的片断记载。这些片断可能反映了古人的某种认识而未言明,笔者试串列于右以为佐证。
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二载:“秦文公墓,东南麦积山下。”民国《天水县志》因袭之。按《史记·秦本纪》:“文公卒,葬西山。”南朝宋裴骃《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23]按古代西县在今天水市西南,[24]与其东面的麦积山相距甚远,故上述二记载矛盾。乾隆时修志者一定注意到了《史记》的《集解》,却坚持将秦文公墓记作“东南麦积山下”,定有所本。或乾隆前的古人曾如《玉堂闲话》所言,将整个今天水市南边山区统称为“麦积山”,这里面自然包括西山。于是乾隆前的古人可能曾记载了“秦文公葬于麦积山下”。于是乾隆修志人因袭之,但只注意到“麦积山下”而不明其广泛含义,就具体将秦文公墓记作“(秦州)东南麦积山下”即“麦积崖”下了。这记载,从一个侧面,似也反映了“麦积山”曾代表包括“西山”在内的大片山区。
按前文(《汉书·地理志》)已知西县有嶓冢山,嶓冢山广大,其支脉隐然相连,则西县境内诸山当即嶓冢之属。西山在西县,当即嶓冢之属。既然秦文公葬于西山,那么,秦文公墓也可以说在嶓冢山了,上古为此山命名者或许知秦文公墓在此山中,(《山海经·西山经》、《禹贡》大约作于战国,晚于秦文公时)则嶓冢之“冢”字,也许有此意而为之。
六
按民国《天水县志》将嶓冢山的具体位置放在今天水市秦城区齐寿山南支一段上。其原因大概为第一:此地是郦道元《水经注》“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导”之地。第二:此段山符合郦氏《水经注》引《汉中记》载:“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的情况。第三:齐寿山似如冢。笔者认为,前文已论述,嶓冢山范围广大,而此具体为某山者,犯了以偏概全之错误。另外,《汉中记》所记嶓冢山,似指后人附会的陕西蟠冢山,当与天水以南的甘肃古嶓冢山无涉。即使此《记》有所本,则一山分东西水者比比皆是,仅从麦积山迤逦向东北、西南的一脉山看,其东水大致东流,西水大致西流,且东西之水流向汉、渭,比东西水大致东西流,且东西之水皆为西汉水支流的齐寿山南支,更具有分水岭意义。山多有冢形,非独齐寿。齐寿山并非特别奇特,并非群山主峰。且“冢”可比附,“嶓”字何来?所以将此段山名为“嶓冢山”从山区范围等理论上看欠妥,从现实看也说明不了“嶓冢山”名的来由。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关于嶓冢山的相关因素存在着争议,故人们对嶓冢山的真实面目认识较少。本文据前人的研究成果试探,得出结论:“嶓冢山”又名“鲋鱼山”,“鲋鱼”在先秦时可指“蝌蚪”。“嶓冢”二字是记古代“蝌蚪”之音的字。今天水麦积山及其附属山梁相结合的形状如“蝌蚪”,且其地望与古嶓冢山相合,故是嶓冢山名具体来源处。“嶓冢”是在依古“蝌蚪”声的同时,托以“山”之意或者又有“秦公所葬地”之意,被上古地理学家创造出来的书面山名。
(原载于《史学论丛》第 6 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原作者夏阳为曾用名)
(二)绘画史研究
1.也谈麦积山壁画《睒子本生》——与王宁宇先生商榷
前言
《美术研究》2002 年第 1 期刊载了王宁宇先生“孝子变相—畋猎图—山水平远——麦积山127窟[25]壁画《睒子本生》对中国早期山水画史的里程碑意义”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过去,一些老美术史家也曾注意到此壁画,但都未曾大胆地提出过如“王文”之结论[26],本文也有以下与王先生的分歧。
一、《睒图》是人物鞍马动物画而非山水画
山水画是“以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独立完整的山水画可全面地研究其各个方面,尤其是其构图图式。“王文”为研究山水画的图式,力图将《睒图》称为一幅独立的完整的山水画,即所谓“独幅”的山水画。如:
王文第一节有:“它还堪称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笔者按,既是“里程碑”,王先生就应当认为它是真正的山水画。
“王文”第二节有:“但人群及动物形象在画面上所占面积较小,而群山、河川、原野、树木、池沼、窑洞等景物却几乎布满了整个画面,而且这些景物具有统一性、连续性的组织关系,他们为人物活动的历时性过程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自然空间环境,也同时形成了支配整个画面构图节奏开合起伏的骨架系统,是整个画面的主旋律所在。”笔者按,王先生的意思是:此图的主体是山水环境,是山水画。
“王文”第三节有:“《睒图》具有独幅画的有机的形式面貌。在这里,山水业已超越了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和环境的衬托的地位,在构图中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相形之下,倒是作为佛即孝子的本生故事之情节内容在幅面中有所剪裁,而这正是为了突出画面中的环境景象描写的自然性、集中性与完整性所需要的。”
笔者按,王先生认为此图不是人物连环画,而是的山水独幅画。
总之,王文的意思是,此图是一幅主要表现山水的独立山水画,山水内容非附庸的配景。以此为基础来谈早期山水画史。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及其以上的时代,真正的独立的山水画见于记载的就很少,传世的和考古发现的山水画也几乎没有形成公认的规模。著名的《洛神赋图》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物故事画卷,不能称为独立的山水画,《女史箴图》和《列女图》中的山水也只是片段,况且它们都是传世品。如果麦积山《睒图》作为考古材料能称为山水画,因它处在文献记载中山水画的形成发展时期,那么自然是稀见的里程碑,(更何况还有王文所谓的平远图式)。问题是,如下文所述,我们看不出它是一幅主要表现山水的山水画(也看不到后世山水画以它为楷模的现象)。因此难说是里程碑。
具体地看,《睒图》如同传世《洛神赋图》一样,是主要表现人物故事的情节的。二图均可作如是观察:从单个的人物动物看,自然空间环境肯定会大于他们,但从画面主要去表现的主体看,人(群)及动物(群)则是其着重所要表现的,人、动物,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形成的活动空间范围在画中的面积,也大于周边的,非其活动范围的山水环境在画中的面积。就《睒图》看,画面是上小下大的梯形,人群和动物群所形成的较密集、呈规模的活动空间范围所占的画面在梯形的下方偏右,占画面的3/5强,处于画面的具有基础和主宰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与王文相反的结论是:人(群)及动物(群)的活动场面和情景,形成了支配整个画面构图的疏密开合起伏的骨架系统,是整个画面的主旋律之所在。
另外,看一幅画中的主旋律所在,要看是什么形象和事物掀起画中的高潮?
或看画中的高潮在哪里?山水画中,是山水形象掀起画中的高潮;人物画中,是人物场面掀起画中的高潮。图中,是人物的场面,掀起了画面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情感高潮,只不过是多时空的人物鞍马等场景用了一个山水环境。不能因为人物情节有剪接而否认它的主体性,相反,高潮所在的连环画故事情节表明,山水只是作为其背景。因此,在构图中,人物应该是作者首先考虑到的,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睒图》和《洛神赋图》应该是人物及其相关的鞍马动物等的连环画,王文所谓《睒图》“具有独幅(山水)画有机的形式面貌”是不能成立的。
二、《睒图》的山水背景是“类似于斜轴侧投影式”的构图图式而非“平远”构图图式
王文力图将《睒图》描绘成平远图式,如:
王文第二节有:“画幅右段约占1/5底边长度部分,其上部画面是远山、层林”“中段,约3/5底边长度的画面上,横向伸延的起伏原野从前景层递推向画面纵深;向上是远山拔起,层叠逶迤,气象旷远”。(画面左部)“都在稳健老到地兜回着全幅的‘气’,也加强着向画幅中部纵深消失的空间整体感。”
王文第三节有:“在这个复杂的现实自然环境中,画师明显地把握住了一条能支配全幅的统一的视平线(约略在画面高度的2/3处),从林郊、原野一直贯穿到深山丛林,成功地组织出一个旷阔而符合视觉合理性的空间。”
因此,王文的第四节有:“与目前已知的遗迹相较,《睒图》堪称中国山水‘平远’法运用最早的范例。”
笔者按,右段1/5底边长度上部所谓“远山”不能成立。
因为第一,如果是“远山”,则其上的“层林”过于高大。因此“远山”实为低丘,“层林”实为灌木。
第二,这些灌木同《睒图》中部前景处,马蹄下的山坡上的灌木大致相当高。所谓的“远山”上有明显的石头,又与此图前景处的石头在形状和大小上都差不多。因为前景处的石头、灌木和最后景处的石头、灌木的大小比例一样,故此图无“远小近大”的观察方式,所谓“远山”应看作画面后景处的低丘而已。
第三,所谓“远山”处有一坐禅的人物以及一只飞鸟的形象,也与前景的人物和鸟的比例一致,说明了同样的“非平远”现象。
所谓“中段前景层递纵深,向上远山拔起”,也是不能成立的。笔者观察,所谓前景处,其前和后的石头大小一样,非远小近大;且较为平缓的,可供鞍马驰骋的层层山坡,几乎画成了相同的,一宽一窄相间的,平行线构成的长条形,且颜色也是大体两种机械地相间;所谓远处和更远处的山,其颜色也是大致两种,在块面上深浅机械地相间,而非渐渐冲淡的情况。因此,此段景色无递进的构图形式。另外,所谓“拔起的远山”,在其右处的一座上,却长了两棵极为高大的树,与此图前景中的树木,如泉水旁和茅屋旁的树木大致相同大小,远山上的石头也与前景处的石头形状基本一样,大小大体一致,这些也均与平远观察法相抵触,说明图中所谓“远山”不是因透视而显小的山,而应看作是后景处的低山丘而已。另外,在此处左边的所谓“远山”的坡石间,有一游行的人(神),也与《睒图》前景中的人物比例一致,也说明了同样的非“平远”现象。
画面左部,在睒子中箭的泉水旁的上部有几棵树,此树如按平远法观察当小,但却与整个画面前景处的树,如画面左下部茅屋旁和山坡上同种的树,大致同样大小。说明此处画面无“远小近大”,其“兜气”并不稳健老到,也未“加强着向画幅中部纵深消失的空间整体感。”
在左部画面中,笔者还注意到,泉水是向画面上部,即后景的右后处流淌的(虽然泉水后部被后景的山石所遮挡)。这说明山图的右后处,即整个画面的右上部的地势较低,画面前景,尤其是左前景处的地势较高,那么,所谓“远山”应为低丘的(本文的)看法就更趋合理了。试想,如画面右上为高山山脉的话,则更有可能与左上的主峰相连形成地势较高处,小小的泉水不可能向画面右后部,从山脚低处将高山山脉切割成极窄的小峡谷而流出去,而只能向画面的前部流淌,因此,正因为泉水没向前部流淌而向画面的右后流淌,则更明显地表明,画面中,右后部,即右上部的所谓“远山”实际上是“低丘”而已。
王先生只注意到画的某一部分,而未注意到画面的某些关键部分所形成的整体观察效果,同时又被古壁画上部的残损所形成的空灵幻觉所迷惑,难免就产生王文中所说的“气象旷远、极目之旷望、及冲融、飘渺、冲淡、旷阔、暝漠、微茫、幽远、荒远等山水平远意境”的设想,并欣赏为“复杂的现实自然环境”。
但这毕竟是一种“幻象”,非此壁画的原始效果,原始的效果是,其色彩几乎均为平涂,较为艳丽,其背景色,包括以所谓平远法观察的,画面上部必然作为天空的地方均被平涂为深红色。因此,壁画原作者并非强调山水的自然色彩效果,而是强调人物画背景的深厚的装饰性色彩。另外,此壁画的造型也是较图案化和装饰化的,如山石多几何图案式,多片状,树冠多呈封闭状等。更重要的是,因此而产生的总体构图图式,必然或连带地也会呈装饰性、平面地图性的效果,而非递进的效果。这就是,画面的空间感不充分,缺乏自然的远近感。既然“无远近纵深感”,也就无严格意义上的“透视”或所谓“散点透视”,也就没有王氏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在画面三分之二高处有一条“大致统一的视平线”,所谓“旷阔而符合视觉合理性的空间”及“中国山水平远法最早范例”也就无从谈起。
上述《睒子本生》构图图式,在麦积山127窟中的其他部分的壁画上基本上也是如此,即:在同属于大树的情况下,后景树和前景树的大小比例一致;同时,后景的人和前景的人的大小比例也是一样的。不存在“远小近大”的效果,不存在“平远”的构图图式。[27]
虽然王文为了说明《睒图》的平远不孤立,举出了北魏的《孝子石棺石刻线画》已有远小近大的图式[28],即使如此,但《睒图》如上文分析,却在图式上较原始。因此,总体上看,《睒图》不能同北魏《孝子石棺石刻线画》比附,而应被看作汉魏晋画构图图式的继承。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睒图》没有所谓“平远”的构图图式。画面不是整体的远小近大,而是远近事物,包括远近人物、动物,大小比例一致,有相互的遮挡,呈平面和立体结合分布的形式。
其构图图式为视平线非一,且是可远近移动的斜俯视的观察效果。因此,其图式颇为接近于斜轴测投影图式,较接近于汉代绘画多出现的,那种平面布局和立体投影相结合式的“平列诸物”的构图,但在复杂性和稳定性等方面有所发展。
三、《睒图》不能改写中国山水画史
所谓改写,主要指从“质变”方面的改写,因此王文力图在质的方面,用《睒图》来改写(一)美国美术史论家方闻先生的“所言”;(二)山水画史上的张彦远“定理”;(三)中央美院教材的“习惯的学术结论”。并且,在中央电视台于2002年4月播出的《美术星空》以及5月份西部频道中进一步宣传,谓发现了麦积山石窟的《睒图》将“平远”图式的产生时代大幅度地提前了,因此从三方面改写了中国山水画史。故,本文也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1.《睒图》难以修改方闻先生在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判断
王文在其第四节末尾中有:“《睒图》在山水表现上凸现出来的与上述(平远)特征相符合的品质,使我们对中国山水画空间法则成熟的时间有了一个具体实在的新的认识线索。方闻先生过去所言‘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从唐之前(7世纪前)到元代初期(13世纪末)的山水画,可以说是从表意性符号到创造视错觉空间的发展过程……在七八世纪期间,固定的构图图式有了发展……’[29],现在可以改说为:在五六世纪之交的北魏后期,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可以看到山水画‘从表意性符号到视错觉空间的发展’探索,已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笔者按,王文所谓决定性的突破,即指《睒图》在山水画史上,首先出现了较强的统一的空间纵深感。但是,如本文第二论点所述,《睒图》并没有在山水表现上凸现出来平远的品质特征。因此,王文的误解所导致的,对方闻先生从考古发现所进行的,中国山水画史的判断的“改说”是不能成立的。
2.《睒图》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指误于张彦远的著名论断
王文在其第6节前段中有:“至迟在《睒图》这个时代,中国山水画的本体在表达自然环境上业已能够形成基本合理、真实而完整的画面。在这个时期成问题的却是那些外加的、主观先验、非现实理性的人物故事情节组合。它们一方面不肯轻易离开前台地盘,一方面又逐步衰退着。这是否应当看作中国山水画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发展(蜕变)阶段呢?”
王文在其第6节后段中有:“在《睒图》上,摆脱古拙粗放或流动华丽的装饰图案遗痕、注重视觉感受与理性认知、趋向自然写实的迹象多有表现。……这些绘画上的具体处理都透露着一种社会审美风尚转变的信息。因此,它给人的美感与南朝《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像模印砖画》(甚至北魏洛阳《石棺线刻孝子图》)中景物的装饰性图案美都有判然之别。”
因此,王文在其第七节中有:“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以质疑的态度重新审读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那一段为后世学者反复引证奉若定理的著名论说: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这个说法现在显见是偏缺有误的,如果不是有意故作抑扬的话,至少说明作为批评家和画史家的他,眼界仍然有局限而妄夸‘皆见’。”
笔者按,王文以上的说法应该解剖为:同“平远”相对应,《睒图》的山水树石也表现得较为自然写实,非“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非“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并认为此图作为山水画,人物所占的比例小,且图中有“人小于山”和“河川”的情况,故认为张彦远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论断有所未见。
首先,我们前文已经否认了所谓“平远”的论调。
至于山石的所谓“写实”,我们看到,王文所举的例子却是题材方面的,而非技法方面的,如所谓与“天水一带所见实际地貌相似”,并没有举出写实的艺术技法的进步。画均有相似之处,有的像北方,有的像南方,但王文并没有举出相似的程度是如何加深的。况且王文所谓地域特色的“山脉河川坡梁与丘石溪涧陂池相间”并不与张彦远的描述矛盾。而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此壁画的艺术形象,应当复原到它原来未残损时的样子来看,那恰恰是“古拙粗放或流动华丽的装饰图案痕迹”。且众山(包括众低丘)之势,起伏如圆弧等规矩之状,大致色彩平涂,故“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的装饰感形象的描述成立。又此图中的石头多具“符号”感,其色彩多平涂如薄片,分布于山峰和丘坡之间,也和“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相合。
至于树木,王文所谈的所谓“写实”乃“画中树木多作摇曳状,充分体现着西北多风的气候特点,称得上是真正的‘风景’;许多树木的种属也具有很鲜明的地域特色(如白杨、落叶松、柳树及茅稍)。”
这还是说明地域特色,也同样没有说明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有任何创新的写实成分。《睒图》中的树干、树枝的具有图案化的平面排列形式,少立体的“树分四枝”的因素,且较为“光滑无鳞”,并没有大的突破性的写实方向的进展,因此,还应看作是“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南北朝其他画中的树木同样能看出一些种属的不同,并非此图所独有的特点,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像》中的树木均个性分明,比起麦积山《睒图》中的树木形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文中第二节提到的,《睒图》中的“河川”“河流”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王文把画面下部的山坡,因其色彩较暗,误认为是河川了。因如是河川,则画面右部的车马和人群就会“不合理”地站在河水流经处,甚至河水里。古人表现水面,一般色调较明亮,127窟其它壁画(如《西方净土变》和《涅般变》中的水面,颜色也一般较鲜亮,(《睒图》泉水中加了几点石青色和其它的浑浊色,则表现《佛说睒子经》中所谓睒子中箭后泉水干涸的情景),一般不应有用暗色甚至黑色来调色表示水的深邃的(这种水的深邃,一般在西画以及现代国画的表现中才有)。因此,《睒图》并无大面积的河川形象,只有泉水,颇合“水不容泛”。
此图左侧茅屋附近有“人小于山”的现象,但不足以批驳张彦远的著名论断。张说为“或人大于山”。按,“或”乃“有的”之意,和“不是……就是……”之意,但决无“率皆”之意。否则,张彦远就不会在两个“或”之后再用“率皆”,而应会直接写作“率皆水不容泛,人大于山,附以树石,映带其地”。
故张彦远的意思应为“有的图画中人大于山”或“在相当一部分的图画中,人大于山”,或这些古画中“不是水不容泛,就是人大于山”。他并不绝对地说,所有魏晋以降,隋唐之前,画山水树石的相关图画中,均存在“人大于山”的现象,他并不否认古画中有“人小于山”的情况。事实上,无论是《洛神赋图》还是《北魏画像石》[30]中,均存在人物“小于”长着树木的山包和甚至长着草的山石的情况。
另外,王文中还有一处所谓“写实”,即所谓“二老居住的不是天竺式的茅庐,而与陇山地区旧时农家的土窑洞形制十分仿佛。”则是由于识图上的错误,而急于认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写实”了。以“柴草为屋”的“茅庐”是《佛说睒子经》中所明确规定的,虔诚的绘画者不会在壁画中作大的改革,况且此图中二老的居所也是茅庐,为立体的尖锥形象,非窑洞口的平面平拱形象。
从以上对此图的分析看,王文中所谓:“这些绘画上的具体处理都透露着一种社会审美风尚(向写实)转变的信息。”也就不是那么强烈了。应该说,此图与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像模印砖画》,甚至北魏《石棺线刻孝子图》中景物的装饰性图案美基本一致,而非如王文所谓的“有判然之别”。由此观之,张彦远之“定理”,信以为然。
3.《睒图》不能改写习惯性的学术结论
王文以上错误地理解考古材料的“写实”结论,必然引起对南北文化比较方面的错误理解。学术界历来以为,在南北朝这一文化交流时代,南方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但王文力图通过山水画及其构图来说明北方的要比南方的先进,从而动摇南朝在文化上的主流地位,它至少要说明的是,从考古材料的情况看,在南北朝后期,北方的山水画要引起重视,其成就要高于南方。同时,它强调,北方山水画的“先进”,是对孝子、孝子变相、畋猎的写实表现所激发的,这种“写实”表现是南北朝山水画“进步”的直接动力,因此怀疑中央美院教材的习惯性学术结论。其具体表述如下:
王文在其第5节中有:“南朝模印砖画上这种衬景处理,虽然已较汉代以来美术作品中殊少自然景物的空间意识有一定的进步,但跟北魏《石棺孝子图》相较,就差距很大了。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来比较《孝子石棺》与《睒图》,我们又会认识到:当中原本土的相对静态的孝子图题材一旦被外域引入的内容活跃、环境场面宏大的”孝子变相“题材替代时,这种绘画空间意识的进步又获得了激越的动力和鲜活的施展机会。”
第6节有:“《睒图》在宏大空间、复杂层次的视觉真实把握上的进步确是惊人的。联想到古画著录中记述过而如今却已佚失的古代一系列畋猎题材绘画作品,注意到这类题材(特别是大幅)作品中旷阔风景几乎是不可回避的描绘对象,就不免让人猜测它们可能是中国山水画,特别是平远山水曾借重过的主要演练阵地。……南北朝时代在政治上处于强势、在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大潮中处于潮头地位、采取积极进取态度的北方,其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与研究。而这个问题以前并不被我们很看重。”
王文在其第7段中有:“对麦积山石窟壁画中山水风景画的研摩,触发我们对以往一些习惯的学术结论产生怀疑:
山水画的发展和当时玄学思想的盛行、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有关,也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有关。[31]
迄今,考古发现的实际材料仍不能支持上述认识。自然客体是否秀丽不是山水画艺术本体产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玄学和隐逸也未必能胜任作为山水画进步的最直接的动力。相反,文学界关于六朝山水诗发展史研究所得的一个重要论断移用到山水画演进史上可能也是同样适当的,那就是:玄言不死,山水不立。”
笔者按,所谓“差距”,“潮头地位”,“积极进取”,“‘很’看重”,“考古材料”,“山水画进步”,王文的言下之意已很明显了,王文感兴趣于用考古材料来建构中国山水画史,虽然有些遮遮掩掩,其结论当然是北朝的作品要“进步”。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皆见”,王文的“言下之意”就难成立。
自然南朝《竹林七贤模印砖图》比北朝《孝子石棺图》的空间感少,但南朝《邓县画像砖》中的一幅无榜文的《吹笙凤鸣图》的山水空间感也较强,其前部有形象较大的人、树和凤,中景有由远而近的云气,远景位于画面的右上部,为一带远山。虽在茂密上不比北朝的《孝子石棺图》,但在自然和飘渺感上略胜一筹,其区别只在,南派和北派的风格不同而已,不在本质上的构图图式上的先进或落后,因为两者都有近、中、远景的具体表现。
但两者的远山,都靠近画面的上部的边缘,仿佛是图案的填充装饰部分,而两者的整个画面确实都是满满的,为缺乏较多天空面积的,有很强的图案感的画面,因此两者(在散点透视意义上)的视平线,都靠近画面内容的上方,其构图图式只能被称为“深远”,没有“平远”。况且,这些“石画”、“砖画”也并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因此如果北朝的《睒图》壁画是场面宏大,层次复杂的“平远”山水画,自然它会成为里程碑,自然会引出北方山水画进步的结论。但通过我们对王文所谓“平远”和“写实”的批驳,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麦积山的“考古材料”不能支持王文所认为的,北朝“先”出现山水画进步的状况。
因此,仅从考古材料上看(姑且把石画和砖画看成画),在南北朝后期,“山水”是“人物”等题材的背景,无独幅山水画;南朝和北朝的“山水”都带有图案化的因素,北方的较茂密,南方的较疏朗,都能表现一定的空间感但不充分;在构图图式上,其“山水”背景或许可勉强认为出现了“深远”图式(如《孝子石棺图》和《邓县画像砖》中的无榜文的《吹笙凤鸣图》),但迄今仍未发现“平远”图式。总之,南北朝后期,南北方对山水表现的总体技术水平大致应相当,这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频繁、广泛和逐渐融合的趋势的结果。其他方面的文化现象也是大致如此,如佛像的褒衣博带式样,此时,南北方风格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本一致;书法的帖、碑形式,此时在南北方也基本都有,只有细节上的差别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且,我们发现,南北朝的绘画中,恰恰是为了表现人物,可以忽略山水背景的表现真实,并使之协调于人物,如“人大于山”“钿饰犀栉”“伸臂布指”的表现形式[32]。因此王文所谓山水平远的产生借重了人物画《畋猎图》的说法证据不足,何况表现了“畋猎”的麦积山《睒图》非平远山水画。故,如果探究南北朝山水画,因无独幅山水画的考古材料,又不能主观地从考古材料中的“人物画”中去寻找山水画产生及发展的原因,那只有从文献和思想史,尤其来自“江南”的有关山水画的信息中去寻找,别无他法,所以,王文对玄学、隐逸和江南秀丽山水与山水画进步的关系的“否认”,以及对“非文学史”意义上的,而是“山水画史”意义上的“玄言不死,山水不立”的“肯定”,没有考古材料方面的依据。
另外,北方重禅修,多开凿石窟。南方重义理,以木构寺宇为主。因此,北方的考古材料多土石,易于保存。不能因为北方的现存考古材料丰富而认为其文化先进,南方虽较少石刻画,也应有大量的壁画和其他种类的画,只不过由于气候和历史战乱等原因,不易于保存罢了。基于这种考古的“皆见”,我们就能更客观地看待南北朝山水画演进的历史和现状。
总之,我们否认了麦积山壁画《睒图》的山水平远图式。同时我们也看到,麦积山127窟中的其他壁画同《睒图》的构图图式基本一样,均较缺乏空间纵深感,同样,也不会有山水“平远”甚至“高远”和“深远”的构图图式的存在。因此《睒图》不能“改写历史”,相反却能“证经补史”了,基于此,作为考古材料,它可以又一次让我们客观地、历史地来感知古代优秀的壁画作品。
四、絮论
从麦积山127窟《睒子本生图》,以及同窟相关的《太子舍身饲虎图》、《十善图》、《西方净土图》、《维摩变图》、《八王争舍利图》等上,我们感知到的是,并非“陶然于自然山水之中”的情趣,而“损己利他”的善行,和“一心向佛”等的种种行为表现。这些图画给我们的,主要不是山水的幽静清远,而是人们活动场面的热闹、嘈杂、激烈、甚至熙来攘往,是人的善行、佛性的颂歌,以及人的美德的壮丽升华,给人以人类可以通过积极进取,以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方面的鼓舞。其背景山水技法和构图并不是那么“先进”,正是“人物故事”主题的“先入为主”所要求的。正是主题人物、车仗、宫殿院落,用类似“斜轴测投影”的,注重“平均表现”的手法,支配了山水背景也必须以同样的形式“映带其地”。正如王伯敏先生所论述的“树木为群山量体裁衣”[33]那样,其实山水树石背景也为人物的特殊艺术风格和构图“量体裁衣”了。总之,这种映带其地的,非有远近平远纵深感的拙朴的山水图式,承栽并保证了故事中的人物、车仗、宫殿院落建筑具有更强的表现性,即远近的人物、车仗、宫殿院落建筑以同样的大小,表现在我们面前,使观者看清楚内容,而非欣赏有“远近真实”的所谓“风景”,从而起到强烈的宣传鼓舞作用。它具有很强的示意性。这同某些汉画和魏晋画的构图的场面表现形式是相似或一致的。
我们不贬低《睒图》的艺术价值,如同不任意拔高它的地位一样。客观地看,在南北朝“画山水树石”的总的艺术风格中,《睒图》在表现山野的场面上,比同时期同类作品[34],甚至更晚至北周[35]和隋[36]的同类作品都要更具有疏密开合,表现出较生动尽致而广阔的特点。但它们的造境上方法仍未脱离那个时代较原始的壁画构图图式。《睒图》生动尽致而广阔并不是平远,它的构图形式仍处在继承汉画风格的魏晋艺术的总的质朴的格局中(如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屯垦图》和《营垒图》的构图图式,同《睒图》的构图图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诸如《孝子石棺图》和《邓县画像砖》
中,具有远近纵深感的画面,但《睒图》的构图图式并不是那么“进步”,这可能是为满足观者在较远和有角度的情况下,能看清楚较为复杂内容的要求等因素所决定的。
总之,麦积山127窟《睒图》所表现的,基本上不是山水平远的,较为写实的广阔场面,而是有山水背景的较为图案化、装饰化、平面化的人物活动的广阔场面。它在山水画史中,在画山水树石方面有一定特殊性的量变地位,但并没有产生各方面突飞猛进的质的变化。它的艺术成就上的辉煌并不在于图式,而是在于较为广阔的场面;人物情景布局的疏密开合;山水配景与人物故事场面的对角布局;山水背景独立存在面积的增加;多了些“人小于山”的结构,以及某些细致的绘画表现和生动的艺术造型等。
结语
王教授在麦积山壁画前呆的时间较短,同时又囿于受到感染的心情,于是激动于眼前壁画残损幻象之所见,叹张彦远之所未“皆见”以及今人的不重视,同时,也因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自夸家珍者的误导,故有智者之失。总之,标新立异的观点要经得起对现代考古材料个体内部结构,和多方面客观情况“皆见”的考验。
(本文最初公布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办的,2002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原载于《美术研究》2004 年第 3 期。后载于《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2002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莼菜条、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创新——从古文献、出土文物、石窟、传世品的有关因素和图像谈起
文献中“纯菜条”始出现于北宋米芾《画史》中,“陁子头”“道子脚”始出现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本文探索上述三词的具体所指,就以前的某种相关误解进行讨论。
一、莼菜条形态的文献依据及其与天王的关系
北宋米芾《画史》:“唐画:……王防,字元规,家二天王,皆是吴之入神画,行笔磊落,挥霍如蓴菜条,圜润折算,方圆凸凹,装色如新……”
按:蓴,乃莼的异体字,蓴菜条即莼菜条。
现实中的莼菜,是一种附有透明胶质物的卷曲的尚未展开的嫩叶,其具体形态是两头尖,中间稍圆厚。此种“嫩叶卷”富有张力,能圆转而俏丽,故显得挺健,整体具有洒脱的流线型,故可被称曰“条”。但这种菜条的具体形象稍短,是否就是“莼菜条”这种绘画线条的具体形象呢?回答是肯定的。画史中著名的“莼菜条”的形态,就是“莼菜嫩叶卷”的条状形态。
首先,它符合上述古文献中,有关莼菜条行笔的“挥霍”一词。挥霍,即用笔有外拓展带笔锋之势,且着重“按”于线条中部,“带入”“提连”于线条两端,形成线条两端的尖头,并较为潇洒随意。因此挥霍用笔,颇合“莼菜嫩叶卷”生动的具体形象。
其次,它符合天王形象。在上述《画史》记载中,除了吴画天王像提到莼菜条外,凡提到的其他题材的吴画,均未曾认为是莼菜条用笔,可见莼菜条与天王关系的密切,当是天王类绘画所专用或多用的线条。而事实上,本文上述“莼菜嫩叶卷”所形成的短促线条,颇为符合用于天王像上。
因为天王多为武将的短装扮,富有强烈爆发之健美风格,而本文所述的“莼菜嫩叶卷”之莼菜条形态,各个稍短的菜“条”可形成笔断意连的状态,可表现在天王短促的肌肉块上,表现在天王转折较多的风动披巾上,以及表现在天王其它较细碎而灵动的装束边缘上,如:扎住的衣袖和裤脚的边缘等。所以,由现实中的“莼菜”和古文献中的“挥霍”和“天王”三位一体的链条,可证明“莼菜条”线描的具体形态,就是现实中“莼菜嫩叶卷”的条状投影形态。
总之,莼菜条应是与天王类形象有密切关系的稍短而灵动的线条,主要可表现短促努张物体的力度感和动感,是形成吴道子“离披点画”[37]疏体绘画风格的主要因素。其所主要表现的题材,除天王外,类似的可能还包括金刚力士,包括帝释、荧惑、钟馗等佛道类神将形象,甚至魔鬼类形象,也可次要或零星地用于其他题材中。
1978 年发现的苏州瑞光塔第 3 层天宫中藏晚唐五代“四天王木函彩画”上的天王形象,较为接近莼菜条式的天王形象,其服饰肌肉和,由众多的莼菜条线描构成。
莫高窟及其附近石窟中,现存盛唐以后的天王力士壁画像和(可作绘画参考的)雕塑像,似没有典型的,从肌肉到服饰,由较多“莼菜条”线条所组成的形象,但其天王金刚力士类壁画中,其面部和赤裸手臂上的少量短线纹理,亦是莼菜条式的线条。如:中唐,榆 25窟,北壁初会听法八部众壁画局部。
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身唐代金刚力士绢画,其裸露的肌肉部分上的线条,有些近似于莼菜条。石窟中,在其他类形象的壁画中也可以寻到莼菜条的点点滴滴,如某些人物面部的皱纹,动物身体上短促的肌肉隆起。
因为莼菜条主要表现的是某些特定的题材,或某些题材的部分形象,它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中国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 2拿起来就放不下的60...
- 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
- 4章泽
- 5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 6从日记到作文
- 7西安古镇
- 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 9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伦...
- 10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科普教育 【已完结】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