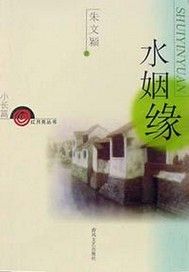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科普教育
>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0中篇小说卷
> 第六章 叛徒
第六章 叛徒
王松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适中,肤色黝黑,眼睛里像蒙了一层令人难以察觉的阴霾。但这阴霾的后面又似乎还有内容,因此显得有些深邃。我和他握了一下手,请他坐下。他就在我的对面坐了。我叫李祥生。他说。他的声音帝着沉重的胸腔共鸣。我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我注意到他没穿警服,只是穿了一件有些随意的米色夹克衫,里面是深色的圆领T恤,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
是的,他又说,周云的案子当年是经我手办的。
我问,是你自己……私下办的?
他说是,我没告诉单位领导。
我又点点头,就取出一只录音笔打开,放到他面前的桌上。他于是稍稍沉了一下,就开始讲述起来……
一
这应该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1982年毕业于这个城市的师范大学数学系,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毕业还要由国家统一分配。按当时的分配政策,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一律要去中学当教师的。但那时候,中教界的待遇还很低,因此一般没人愿意去。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叫李大庆的同学,他父亲是这个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于是公安局就专门为他给了我们系一个名额,是去公安局下属的劳改局,到监狱工作。但是,这个李大庆一听说是去监狱,干部子弟的脾气就上来了,死活不肯去。可指标既然下达我们系,再想要回去已经不可能,于是也就由我们系自己支配了。当时我是系里的学生干部,不仅表现积极,政治条件也很好,系里就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劳改局。那时警察还不叫警察,叫民警,说实在话,我对当时的民警印象并不好,觉得那些人穿着一身蓝不蓝绿不绿的警服不想着如何为人民服务,却整天狐假虎威地吓唬老百姓。可是转念再想,去劳改局当民警总比去中学当教师强,于是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我来到劳改局,被分到西郊监狱。
我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周云的。我刚到监狱时,一穿上这身警服感觉立刻就变了,竟有了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我每当看到自己帽徽上鲜红的国徽,就觉得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更重要的是代表我们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我对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对每一个细节也从不掉以轻心。我下定决心,要对得起国家给予的这份信任。
我渐渐发现,关在001号监室的犯人有些不太正常。
这个犯人就是周云。她当时60多岁,据同事对我讲,已在这里关了十几年。我曾经看过关于她的材料,她是因为历史问题被判刑的。据案情记载,她的原籍是江西赣南,祖辈务农。她在三十年代初投身革命,后来还曾经参加过游击队。1934年秋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她继续留在苏区坚持对敌斗争,但后来被捕就叛变了革命。据说当时被她出卖的人很多,其中还有我们党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因此,她的刑期也就很长,被判的是无期徒刑。
我听同事讲,这个周云的认罪态度很不好,这些年来一直拒不接受改造,坚持说自己有冤情,在监室里不停地写申诉材料。但她的申诉材料只到监狱这一级就被扣下了。那时各种类似的申诉材料很多,监狱不可能都送上去,上级有关领导也没时间看这些东西。因此,尽管这个周云一直在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但她并不知道,这些材料交到监狱之后就都被扔在角落里了。那时一些冤假错案都已陆续平反,但这个周云的案子却始终没有翻过来。有关领导也曾问过此事,却都没有任何结果。后来监狱方面也就明白了,看来这个周云的案子确实不属于错案,因此也就不会涉及平反昭雪的问题。如此说来,监狱方面一直将她的申诉材料扣下也就做对了,否则真转上去不仅毫无意义,也只会给上级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从此之后,监狱索性就给周云准备了大量的废旧纸张,只要她想写就为她无条件提供,待她写完之后,只要将这些废纸从一个角落放到另一个角落也就是了。周云渐渐地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再写完材料之后就不交给监狱方面,而是一页一页地撕碎,然后一边喃喃自语地嘟囔着,将这些碎纸一把一把地从铁门上的窗洞里扔出来。那些扔出的碎纸像一团一团白色的蝴蝶,在监房的楼道里上下飞舞。监狱方面认为周云这样做严重地破坏了监房的环境卫生,因此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警告,如果她再这样肆意乱扔纸屑就要根据有关的监规对她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周云却置若罔闻,不仅我行我素,而且向外抛撒的纸屑也越来越多。渐渐地,那些纸屑甚至将她监室门口的地面都白花花地覆盖起来。看上去,像一堆蝴蝶的尸体。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傍晚临近下班时,我从001号监室的门前走过,看到一地的烂纸,就找来一把扫帚想清扫一下。我将这些烂纸扫到一起正准备倒进垃圾箱,不知怎么突发奇想,就蹲到地上将几块碎纸拼在一起,想看一看这个周云究竟都写了些什么。然而这一看,竟让我大感意外。周云写的虽然密密麻麻,内容却很简单,翻来覆去只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在来回重复。但这些字我仔细看了一阵,却都无法辨认。
我立刻感到很奇怪,难道……她一直写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当即决定,将周云最近一段时间写的材料都找来看一看。我立刻来到监狱的资料室。那时资料室还形同虚设,平时几乎没有人去查阅资料。在资料室的里面还有一个套间,是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库房,用来存放监狱里一些没用或废弃的文件资料。我知道,周云这些年来写的申诉材料,就应该都被搁置在这里。我在一个满是灰尘的角落里果然找到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竟然整整地装满一箩筐。我大致翻弄了一下,显然,放在最上面的应该是最新写的,越往下时间就越早。我拿起最上面的几页纸看了看,都是同样的字迹,也是那样的密密麻麻歪歪扭扭,但如果仔细看却无法辨认出究竟写的是什么。再往下翻,我忽然发现几页纸。这几页纸是夹在一摞散乱的纸中,用一个曲别针勉强别在一起,虽然字迹同样的潦草怪异,但如果仔细看,竟然能看出所写的内容。
我立刻将这几页纸拿出来,带回到宿舍。
在这个晚上,我将这几页纸很认真地看了一下。这显然是周云某一份申诉材料中的一部分,写的是她当年在游击队里如何与丈夫结合,后来又是如何离开游击队的一段过程。这几页材料虽然字迹还能勉强辨认出来,却断断续续,词语不仅不连贯也有些凌乱,我几乎看了大半夜,才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重新梳理再拼接起来。据她在这份材料中说,她当年的丈夫叫罗永才,她和他是在1935年初春走到一起的。那时中央主力红军已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以及红军二十四师也已经分九路突围,苏区完全被国民党军队战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留下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生存环境也就越来越残酷。当时为了便于隐蔽和相互照顾,游击队员一般都是男女相配,也就是说,大都是夫妻。周云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有十七个人,共中八对是夫妻,只有周云一个单身。她那时还只有18岁,每天钻山林住岩洞,别的女游击队员都有丈夫在身边照顾,她一个女孩独自面对这一切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后来罗永才就从别的游击队调过来。那时罗永才21岁,也是单身,生得魁梧壮实也很热心帮助战友。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帮他们撮合,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
关于罗永才后来牺牲的过程,周云在这份材料中是这样记述的。
那一年开春,由于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占领苏区之后不断“清剿”,斗争环境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加艰难。就在这时,游击队突然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中央机关的一位重要领导同志去粤北,只要进入粤北境内,那边的游击武装自会有人接应。但是,周云这时已经怀有身孕,而且妊娠反应很严重,总是不停地呕吐,身体非常虚弱。游击队领导考虑到这一次任务的特殊性,就和周云商议,让她下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待生了孩子再想办法归队。但周云的家虽然是在山下,可她离家已经很久,估计家里已没有什么人。于是罗永才考虑了一下,就让周云先去他的家里。周云就这样在一个傍晚离开游击队,独自下山去了罗永才的家。所以,周云的这份材料写到这里特别强调,她那一次离开部队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暂时下山去罗永才的家里生孩子。
罗永才的家是在山下的下屋坪村,与周云的家只隔着一架山。所以,周云对去他家的路很熟悉。在那个晚上,周云摸着山路好容易来到下屋坪村罗永才的家里。罗永才的父母还都健在,他们一见这样一个眉目清秀的儿媳突然带着身孕来到家里,就如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然都喜出望外。一番问这问那之后,见她由于长期钻山林风餐露宿,蓬头垢面身上肮脏不堪,就赶紧忙着烧水让她洗一洗身上再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又找出家里的粮食为她做饭。就这样,周云就在罗永才的家里住下来。那时国民党的“靖卫团”正在到处搜捕红军家属,所以罗永才的家里一直说罗永才是去赣江下游为人家运木材了。因此这一次,他父母就对村里人说,周云是罗永才在外面娶的媳妇,现在怀了孕才送回家来。村里知情的人立刻心领神会,于是也就都帮着罗永才的父母隐瞒。因此,周云在下屋坪村并没引起人的怀疑。
出事是在几天以后。
关于这一段记述,周云材料上的字迹更加潦草,因此辨认也就更加困难。但语句却突然一下流畅起来,也明显的有了一些条理。据材料上说,出事是在一个上午。当时周云正躺在家里的竹床上。她这时妊娠反应越来越重,已经虚弱得无法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叫赖顺昌的人带着几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闯进家来。这赖顺昌原本是附近前樟坑村一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只靠偷鸡摸狗混日子。红军主力转移以后,地主豪绅卷土重来成立了“义勇队”,赖顺昌就去投靠了“义勇队”,整天带着靖卫团的人到处搜寻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在这个上午,赖顺昌带着人闯进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周云,就转身对一个又矮又瘦军官模样的人说,就是这个女人。那个矮瘦军官走过来,朝周云看了看问,你就是周云?当时周云听了立刻感到奇怪,她来到罗永才家之后,已经改名换姓叫温秀英,她摸不清楚这些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她没动声色,只是对这个矮瘦军官说,我不知道周云是谁,我叫温秀英,是罗永才的女人。罗永才?那个矮瘦军官微微一笑说,我们来找你就是因为罗永才。他这样说罢又朝身边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就转身出去了。几个士兵立刻走过来,从竹床上拉起周云就架着往外走。罗永才的父母一见连忙扑过来挡在门口。这时赖顺昌就走过来说,你们不要找麻烦,田营长是去让她认尸的,只要认完了尸首立刻就会放回来。罗永才的父母一听说是让周云去认尸,立刻都惊得呆住了。那几个士兵趁机就将周云架出去了。
周云在这份材料上说,她后来才知道,她所在的那支游击队在完成护送领导同志去粤北的任务时,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连同那个领导同志以及她的丈夫罗永才在内,已经全部牺牲了。在那个上午,赖顺昌领着那个叫田营长的国民党军官率人将周云架到山上去,就是想让她辨认一下,哪些尸体是游击队员,最后剩下的那具她不认识的尸体,自然也就是他们要护送的人。周云在这份材料上也承认,她至今仍然搞不明白,敌人在当时怎么会对这件事的底细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如果他们让她去认尸,也就说明她的身份已经暴露,而敌人又是怎么知道她也曾是游击队员呢?
周云在那个上午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架上山,就看到在山坡的一片空地上横躺竖卧地摆放着一堆尸体。这些尸体显然都是刚从什么地方抬来的,身上满是黑紫的血污,有的中弹是在脸上,看上去惨不忍睹。这时,那个叫田营长的矮瘦军官走过来,对架在两边的士兵挥了一下手。那两个士兵立刻朝后退去。周云的身体失去了支撑,摇晃了一下勉强站住了。田营长的样子还算温和,他让周云仔细看一看,在这些尸体中有没有她不认识的人。田营长又冲周云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你过去跟他们是一起的。
周云当然明白这个田营长的用意。
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过程中,如果捉到或打死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是有很高奖赏的,所以,这个田营长显然是想找到他要找的尸体,查明身份,然后去上级那里邀功请赏。这时周云的腹痛突然开始加剧起来。她艰难地走到这些尸体的近前,立刻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这些游击队员由于长期在山林里露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身上都已衣衫褴褛,再溅上黑紫的血污,看上去就都成了一个样子。但是,周云在心里暗暗数了一下,突然将两个眼睛睁大起来,她注意到,这些尸体一共是十七具。周云知道,当初游击队包括自己在内一共是十八个人,现在自己离队,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应该还是十八个人,但眼前的这些尸体却是十七具,这也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在这次战斗中幸免于难。这个人是谁呢?会不会是罗永才?这时,那个田营长也注意到周云脸上的变化,立刻走过来问,你看到了什么?周云摇摇头说,没看到什么。赖顺昌从旁边走过来,别有用心地说,咱们开始认尸吧,你一具一具认,看哪一个是你男人罗永才。周云慢慢回过头说,既然你是前樟坑村“义勇队”的人,你会不认识罗永才吗?赖顺昌立刻被问得支吾一下,说,这些尸体都打得稀烂,谁还能认得出来。说罢就捂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这时,周云虽然这样说,却把目光转向那些尸体。她小心地在那些尸体中搜寻着,唯恐看到自己最怕看到的人。但就在这时,她的目光突然定住了。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面孔显然是在一个极端愤怒而又痛苦的瞬间凝固住了,因此有些扭歪,两只没有闭上的眼睛里仍然透出冰冷的怒火。周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肚子里也猛地抽动一下,接着就剧烈地疼痛起来。
她眼前一黑,就栽到地上失去了知觉……
周云的这份材料就到这里。后面还有半页纸,但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我注意到,这些字迹不是因为潦草,而像是被水洇过。我想,这也许是周云的泪水。我又努力辨认了一下,这半页纸上的文字大致是说,那一次在山坡上认尸,她昏倒之后就流产了。敌人认为她死定了,就将她扔在山坡上走了。直到傍晚,她才被找上山来的罗永才父母背回家去……
二
我立刻对001号监室这个叫周云的女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又在她写的这份材料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从她的讲述看,她所说的事情是发生在1935年春,而她当时是18岁,那么这样计算她现在就应该是66岁。但我清楚记得,在她的犯人登记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15年8月,也就是说,这样算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是68岁。不过我想,这也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赣南地区那样的农村,很少有人用公元去记自己的出生年月,一般都是后来经过换算才确定的,这也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误差。
也就从这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周云。
我再走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就总是有意放慢脚步。我想观察一下这个周云平时在监室里都干些什么。我发现,正如别的同事告诉我的,她在监室里似乎只做两件事情,要么趴在墙角的小桌上埋头写材料,要么一边喃喃自语着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在001号监室的门前停下来,隔着铁门上的窗洞朝里面看着。周云仍像平时一样一边喃喃自语着在监房的中间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她走路的样子并不显衰老,两腿很有力,步子也迈得很坚实,因此看上去还给人一种矫健的感觉。只是来回走得有些茫然,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令人焦虑的事情。突然,她也发现了我,于是立刻停住脚步,愣了片刻,就朝这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她来到铁门跟前站住了,微微侧过脸,隔着那个小小的窗洞与我对视着。我发现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满是沧桑的皱褶,眼睛却仍然很亮,而且像婴儿一般清澈。
她就这样与我对视了一阵,忽然说,你是新来的。
我稍稍愣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
她说,我过去从没见过你。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江西赣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给人的感觉也很清醒,似乎不像是疯疯癫癫的人说出来的。我刻意不让自己的脸上有任何表情。我对她说,你应该正常吃饭。我已经听同事说了,这个周云的食欲很不好,经常一整天不吃一点东西。周云显然将我的话听进去了,她又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你……真的关心我吗?
我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关心每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
她摇摇头说,你如果真的关心我,就不应该只是吃饭问题。
她这样说罢,仍然盯住我用力地看着。
我沉一下问,你说,应该是什么问题?
赖春常,说的都是假话。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赖春常?
赖春常是谁?
她忽然笑了,说,你会不知道赖春常是谁吗?
我又努力想了一下,还是想不出她说的这个赖春常究竟是谁。
好吧,她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赖春常曾经是咱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我们的同志,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她这样说罢,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哼,虽然他改了名字……我也知道他是谁……
她这样说着就转过身,又朝监室的深处走去。
周云的这番话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我得承认,如果是在今天,我不会在意这个周云说了什么,更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探究她的案情,因为这些年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事了,在我感知器官的表面已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我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在那时候,我毕竟只有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刚穿上警服的年轻狱警,因此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当即决定,要想办法将这个周云的案卷调出来看一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已经开始重新建立起来,那时在监狱羁押的犯人,一股情况下案卷都是存放在法院,但公安机关也会有一个副本。我工作的劳改局是公安局的下属机关,所以跟他们联系应该方便一些。于是,我在一天上午就给市局那边负责案卷的部门挂了一个电话。那边一听说是自己系统的人,果然很客气,但还是公事公办地告诉我,要想查阅犯人案卷,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信。这对我显然是一个难题。我去查阅周云案卷这件事并不想让单位领导知道。我想了一下,觉得只能求助在大学时的那个同学李大庆了。李大庆的父亲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这点事打一个招呼,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我立刻给李大庆挂了一个电话。
这时李大庆还是分来市公安局,被安排在八处工作。我知道,八处是一个要害部门,几乎掌握着这个城市公安系统所有人员的情况。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大庆一听说要求他父亲办事,竟立刻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当领导之后一直跟家里人有一个约定,无论谁,无论什么事,都不准向他开口。所以,李大庆说,要想找他父亲是不可能的。不过……李大庆想了一下又说,这件事他可以试一试。我听了立刻眼前一亮,对啊,李大庆是李副局长的儿子,这在局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打电话和他父亲打电话还不是一样,况且他现在又在八处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负责案卷那边的人也总要给一些面子。
我连忙说好好,那你现在就给那边打个电话吧。
果然,时间不长,李大庆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
他说,你现在过去吧。
我问,你……说好了?
他说,说好了。
没问题了?
你去吧。
李大庆说罢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立刻来到市局。负责案卷的人一听说是我果然没再提证明信的事,立刻就将已经准备好的周云案卷拿出来。但他们又对我说,案卷是不可以拿走的,只能在这里查阅。我看了看这个满是灰尘的卷宗夹,虽然不算太厚,但要想把里面的内容看一遍也需要一定时间。负责案卷的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旁边的一个房间指了指告诉我,那里有一个阅卷室,是专供查案卷的人使用的,但一般不会有人来。
我听了点点头,就来到阅卷室。
周云的案卷并不复杂,除去一些相关法律程序的文书,还有一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显然是六十年代写的,所以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规范,案情记述也很简要,只说是在1935年春,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周云意志动摇,先是私自脱离革命队伍,继而被敌人逮捕之后又贪生怕死,变节投敌,而且由于她的出卖使我党遭受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一位当时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和十六位游击队员全部遇难。判决书上最后说,周云以上的犯罪事实清楚,且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据此判处她无期徒刑。
我在这张判决书的下面,又看到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证明材料是一个调查笔录,被调查者是一个叫赖春常的人。周云曾对我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我想,她指的是不是这份证明材料?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还曾说,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革命同志。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又怎么会为周云的事作证呢?我立刻将这份材料拿出来。材料的开头先是介绍赖春常的基本情况:赖春常,男,汉族,1917年出生,职业农民,家住东岰人民公社下屋坪生产大队。然后是记载事情的经过,1958年,赖春常突然揭发出周云有叛变投敌的历史问题,这件事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当即派人前往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
接下来就是调查者在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的笔录。
调查者问得开门见山:你根据什么说周云曾经叛变投敌?
赖春常的回答也很干脆: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
问:你亲眼看见周云叛变?
答:是的,我亲眼看见的。
问:这件事还有谁可以证明?
答:再有……就是田营长了。
问:田营长?田营长又是谁?
答: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问:国民党军官?
答:不过,你们恐怕已经找不到他了。
问:你能详细说一下这件事的经过吗?
答:当然可以,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赖春常的陈述。
那是1935年夏天,具体是五月还是六月,已经记不清了。一天夜里,周云突然从山上跑下来,藏到下屋坪村她丈夫罗永才的家里。当时在下屋坪村附近的前樟坑村,刚好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是田营长的队伍。田营长听说了此事,又知道这个周云曾是红军游击队的人,第二天下午就带人来到下屋坪村,直扑罗永才的家把周云堵在了屋里。周云一被逮捕立刻就吓得说不出话了,接着田营长又威胁她,说是如果她不肯招供,就把她送去靖卫团,让靖卫团的那些人把她糟蹋够了,再拉去山里活埋。周云一听田营长这样说就吓得哭起来,接着也就全招了,她告诉田营长,山上的游击队刚刚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一位重要领导去粤北。然后,周云又告诉了田营民游击队准备走的详细路线。就这样,田营长立刻派了一支队伍连夜上山,在游击队要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到后半夜时,果然就将游击队等到了。当时游击队的人由于连夜赶路已经很疲惫,看到路边有一个纸寮,就进去想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纸寮是当地一种特殊建筑,一般都是用竹子搭建的简单棚舍。那时山里人还习惯用竹子造一种土纸,这种纸寮就是专门用来造纸用的。但是,就在游击队的人进到那个纸寮里,田营长的队伍也迅速在外面将这个纸寮包围起来。他们包围了纸寮却并没有急于行动,只是耐心地等待天亮。就这样,天亮以后,田营长的队伍突然向那间纸寮发起攻击。当时在纸寮的四面都架起机枪,所以游击队的人一冲出来立刻就被猛烈的火力压回去。其实田营长事先已有命令,要尽量捉活的。但那些游击队的人都不怕死,硬是顶着子弹拼命往外冲,就这样,十几个人全被打死了。这时田营长的队伍才冲上去,将那些还在冒着烟的尸体拖出来清点了一下,整整是十七个人。于是就将这些尸体都抬回来。
赖春常说到这里,就被调查者打断了。
调查者问,当时为什么要将这些尸体抬回来?
赖春常说,田营长想查找,究竟哪一个是游击队要护送的人。
调查者说,好吧,你继续说。
赖春常说,在那个下午,周云向田营长提供了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就被放回家去了。这时,田营长又派人把她抓回来,让她去山上辨认尸体。就这样,周云被带到山上,将那些尸体一具一具辨认之后,就找出了那个游击队要护送的人,他的前胸中了两枪,脖子上还中了一枪,于是田营长就命人将这具尸体抬出来,弄到上级那里请赏去了。
这时,调查者突然又将赖春常打断了。
调查者说,等一等,这里有一个问题。
赖春常问,什么……问题?
调查者说,你说的这个过程这样详细,你是怎样知道的?
沉默。赖春常没有回答。
调查者又问,你刚才说,你是亲眼看到周云叛变的?
赖春常答,是……我是……亲眼看到……她叛变的。
调查者问,你是怎样看到的呢?
调查者又问,当时,你在场吗?
调查者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无法回答,那么你说的这些情况也就都不能成立,不仅不能成立,你还要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赖春常说,好吧……我说,我当时,确实……就在现场。
调查者问,你为什么在现场?你是以什么身份在现场呢?
赖春常说,我……我在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
调查者问,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赖春常说,是,可这是……他们逼我干的。
调查者说,好吧,你再把其他细节想一想,我们还会找你的。
赖春常说,好的……我如果再想起什么,会立刻告诉你们的。
这份调查笔录就到此为止。
三
我从市局回来,心里还一直在想着这个叫赖春常的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如果从周云的案卷看,这份证明材料显然对她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周云的公婆,也就是罗永才的父母后来相继去世,于是解放后,周云就来到这个城市投奔罗永才的一个远房叔叔,后来又进了一家服装厂做工。如果没有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揭发,周云已经生活得很平静,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过去。但是,这个赖春常却突然说出这样一件事。从这份证明材料的时间看,应该是在1968年春天。1968年,在那样一个时间突然揭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如果按这个赖春常所说,他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发生这件事时又在现场,那么他的揭发和证明也就应该最直接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赖春常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那么去下屋坪村抓周云时他怎么会在场呢?此外还有两个细节。这两个细节在周云那份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中曾经出现过,这次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再次出现。
首先,周云的申诉材料中曾提到一个叫赖顺昌的人,而且据周云讲,在她被架去山上认尸时,这个赖顺昌也一直在场。但她的材料中却并未提到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始终坚持说自己当时就在现场。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这也就是说,周云是知道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存在的,那么,这个赖春常又究竟是什么人呢?“赖顺昌”和“赖春常”,这两个名字在谐音上很相近,从这一点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个人呢?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细节,周云曾在她的申诉材料中提到,在她被押上山去认尸时,曾经注意到,一共是十七具尸体,而她清楚记得,当时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她离队之后,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然是十八个人,这时怎么会只有十七具尸体呢?而这个细节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也再次出现。据赖春常说,当敌人冲进那个已经被打得稀烂的纸寮,清点那些身上还在冒烟的尸体时,整整是十七个人。这个说法与周云所说刚好吻合。如此看来,当时这支游击队的队员并没有全部牺牲,应该还有一个人幸免于难。那么,这个人又到哪去了呢?
我想到这里,就决定再向周云询问一下。
这天晚上刚好是我值班。傍晚六点钟,别的同事都下班以后,我就来到监房。我先是不动声色地在监房的楼道里走了一趟。经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我迅速地朝铁门上的那个窗洞里看了一眼。我发现,周云竟然也正在朝外看着。她一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在我朝窗洞里看去的一瞬,与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感觉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渴望和期待。于是,在我折身回来,又走到这扇铁门的窗洞跟前时,就站住了。这时我发现,周云竟然已经等在窗洞的近前。但她只是隔着窗洞静静地看着我,并没有说话。
我沉了一下,问她,赖春常……是什么人?
赖春常?
对,赖春常。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
我立刻被她问得愣了一下。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去市局查阅过她的案卷,于是想了想就说,是你告诉我的,你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
哦……
她皱起眉想了想,点点头。
我又问,你还曾说,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是的,她说,他确实曾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问,就因为他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周云立刻问,你怎么知道……他当过伪甲长?
她又摇摇头,说,我没对你说过这样的话。
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漏嘴了。赖春常曾经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这件事,我是在周云的案卷里看到的,周云确实从没有对我说过。看来周云的头脑的确很清醒,她对我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心里都是很清楚记得的。因此,我想,我跟她说话要小心。
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同一个人。
周云突然对我说。
他们真是……同一个人?
是,周云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赖春常这个名字,应该是他解放以后改的,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说自己是下屋坪村人,可是下屋坪村根本就没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揭发我的一些事情,当时除去那个田营长,也应该只有赖顺昌一个人在场,虽然赖春常揭发我叛变不是事实,可他说的一些细节跟当时还是对得上的,如果赖春常不是赖顺昌,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些细节都是那个田营长告诉他的,但我知道,虽然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可是赖春常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见到了田营长也不会对他说起当初的那些事情,所以,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我得承认,周云说的这番话条理很清晰,逻辑性也很强,应该说,如果仅从她的分析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接下来也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倘若这个赖春常和赖顺昌的确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就并不是只在三十年代当过伪甲长这样简单了,按周云的说法,他是投身到当时的地主武装“义勇队”,而且还曾经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还“害死过很多我们的同志”。这也就是说,他将自己过去的历史都隐瞒起来。
那么,这样一个人提供的证词,还能采信吗?
有一个想法始终缠绕着我。解放以后,周云来到这个城市,进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生活原本很平静,似乎已经与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就因为这个赖春常的揭发,突然将过去的那些事情又都重新翻出来,不仅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也使她从此陷入这种没有尽头的牢狱生活。且不论当年周云叛变这件事是否属实,这个赖春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倘若真像周云所说,他揭发的那些事都是诬陷,那么他这样诬陷周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很想见一见这个曾经叫赖顺昌,解放以后改名叫赖春常的人。我有一种预感,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当面问一问他,一定能从他口中知道一些更直接的事情。从那份证明材料上可以看出,这个赖春常解放后一直在下屋坪村务农,如果是这样,我只要去一趟江西,到下屋坪村就可以找到他。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很想去探究一下这件事的真相。同时,我也被一股强大的热情鼓舞起来。我是一个人民的公安民警,如果周云的这件案子确有冤情,那么,我就有责任为她澄清。
八十年代的交通还不像今天这样便利,而且,我那时每月的收入也很有限。但我还是拿出平时的一些积蓄,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就买了一张车票登上南下的火车。我按着事先在地图上查阅的路线先到赣州,然后又换乘长途汽车。那时赣南地区的公路体系还很不发达,而当地的地貌又是丘陵,长途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将近半天时间,我又步行几十公里,才在一个很深的山岰里找到这个下屋坪村。当时下屋坪村还叫下屋坪生产大队。我直接来到村里的大队办公室,找到村干部。接待我的是一个40多岁的农村汉子,操一口浓重的赣南口音。他自我介绍说,姓温,是下屋坪村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温主任一听说我的来意,就告诉我,赖春常已经死了。
我一听连忙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温主任想一想说,这个人已经死很多年了,好像……是自杀死的。
据温主任证实,赖春常的确跟赖顺昌是同一个人。赖顺昌是解放那年从前樟坑村迁来下屋坪村的,同时改名叫赖春常。他原本在村里默默无闻,平时也很少说话。但在1968年春天,突然有一伙前樟坑村的人闯来下屋坪村,说是赖顺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要将他揪回去批斗。直到这时下屋坪村的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赖春常过去叫赖顺昌。前樟坑村的人将赖春常捆回去,连续召开了几天批斗大会。那时的批斗大会实际也就是打人会,每次都是将赖春常五花大绑,让他跪到土台子的中央,然后周围站着几个人轮番用毛竹在他的身上用力抽打,一边抽打台下的人一边高喊口号,并且让他交代问题。就这样,几天以后,赖春常实在挨不住这样的拷打,就胡乱交代出周云曾在1935年春天叛变的事。这件事一说出来自然非同小可,立刻引起前樟坑村的高度重视,连夜就将此事汇报到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县领导也意识到这件事的案情重大,于是又逐级汇报到省里。就这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迅速派出专人调查,当得知这个周云已经移居到外省的城市,便立即向这边的相关部门发出通报。但是,让赖春常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出周云这件事不仅没能拯救自己,反而将自己拖入一个更可怕的深渊。赖春常在交代这件事时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如果按他所说,周云叛变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场?前樟坑村的伪甲长?这样的说法无疑站不住脚,既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怎么会跟随那个国民党军官田营长去下屋坪村抓人呢?上面立刻组成专案组,又对赖春常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这时赖春常已经又被下屋坪村的人押解回来。因为下屋坪村认为赖春常是他们的人,所以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由他们审问。专案组来到下屋坪村,和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对赖春常进行审问,这一审果然就审出了更大的问题。原来赖春常,也就是当年的赖顺昌在前樟坑村并不是什么伪甲长,而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在1935年的“大清剿”中曾带领国民党军队和“靖卫团”的人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不仅罪行累累,两手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赖春常在交代出这些问题之后,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于是一天夜里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搓成绳索,把自己吊在窗棂上了。
但是,温主任又向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据温主任说,当初在省里的专案组下来调查时,一度曾怀疑赖春常只交代了一部分情况,而将另一些与自己有关的情况都隐瞒起来,比如,他是不是与周云相互勾结,二人共同将游击队的情报出卖给敌人的?赖春常当然很清楚,出卖游击队比当“义勇队”副大队长的罪过更大,所以当专案组的人这样问他时,立刻矢口否认。他否认的理由是,他当时既然在“义勇队”,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只要直接告诉那个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有什么必要再去抓周云,费那样大的气力从她的口中掏出情况呢?赖春常为了证明这件事,又向专案组说出一个叫韩福茂的人,他说这个韩福茂就住在东岰镇上,他对自己当年没有出卖游击队这件事应该很了解,如果专案组的人不相信可以去问一问他。专案组的人立刻问,这个韩福茂又是什么人。赖春常支支吾吾,只说是田营长在哪一次打伏击时抓到的什么人。但在那时候,专案组急于想搞出一个结果,所以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反复审问赖春常。就这样,还没等他们去东岰镇找那个叫韩福茂的人,赖春常这里就已经自缢死了。
温主任说的这个情况立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没想到,在这里又发现了一条新线索。如果真能找到这个叫韩福茂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一个了解当时情况的途径。
我连忙问,这个韩福茂,现在还在东岰镇吗?
温主任告诉我,后来下屋坪村曾派人去东岰镇了解过,这个韩福茂果然还在。他当时已经50多岁,在镇里的小西街上做裁缝。不过那时赖春常已经自杀,所以去了解情况的人只是简单地向他询问了一下当年的情况。但这个韩裁缝却说,他从不认识赖春常,更没有被什么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他对去调查的人说,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
就这样,温主任说,去调查的人也就只好回来了。
我又问,你们去东岰镇找这个韩福茂,是哪一年?
温主任想一想说,大概是在……1970年前后。
我立刻在脑子里算了一下,如果按温主任这样说,这件事就刚刚过去十几年,这个韩福茂当时50多岁,现在也就应该只有60多岁。我当即决定,去东岰镇找这个韩福茂。这时温主任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我立刻明白他要说什么了。我这一次来江西特意穿了便衣,我想这样可以方便一些。这个温主任看我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又操着一口地道的北方话,突然跑到山里来询问赖春常当年的事情,一定摸不清我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我笑一笑对温主任说,你先不要问我是干什么的,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现在想请村里帮一个忙。温主任一听立刻说,没问题,你说吧,什么事。我说,我的时间很紧,还要立刻赶回去,可是现在想去东岰镇见一见这个叫韩福茂的人,你们能不能找人给我带一下路,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温主任立刻说这没问题,当年去东岰镇上调查韩福茂的人还在,就让他陪你去,村里有拖拉机,可以送你们过去。
四
就这样,在这个傍晚,我来到东岰镇。
由于有人带路,我很顺利地就来到小西街,在一个街角找到了那家门面不大的裁缝店。在我走进这裁缝店时,一眼就看到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正用手在一个妇女的身上比比画画的老年男人。我立刻断定,这个人应该就是韩福茂。他约莫60多岁,脸上的皮肉已经松弛地垂下来,看上去有了些老态,但手脚仍很麻利,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在他抬起头看到我的一瞬,突然稍稍愣了一下。我知道,虽然我穿的是便衣,但身上的装束显然与当地人不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样愣了一下之后,试探地问,您要……做衣服?
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冲他笑一笑说,不,不做衣服。
他越发警觉起来,又问,那您是来……
我问,您贵姓?
他说,姓韩。
叫,韩福茂?
是,您是……
我冲他做了一个手势,说,您先忙,我们一会儿说话。
他也冲我笑了一下,点点头。我注意到了,在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似乎停滞了半秒钟,在这半秒钟里他的目光迅速坦然下来,然后就又低下头去继续忙碌了。我坐在墙边的木凳上,掏出香烟慢慢抽着。韩福茂很快就为那个妇女量好尺寸,写了一个单子将她送出去。这时才走过来,又看一看我,然后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韩福茂的眼睛迅速眨了一下问,当年的?什么情况?
我想一想,突然问,您是哪年离开的部队?
我是有意这样问的,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末,下屋坪村的人曾去镇上向这个韩福茂核实过当年的情况,但韩福茂却矢口否认了,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被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如果真如赖春常所说,这个韩福茂当年是那个田营长在什么地方打伏击时抓到的,那么他当时的身份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红军,或者是游击队。而无论哪一种,在今天都应该是很光荣的历史。
可是……他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这样做果然起了作用,韩福茂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绕住了。他慢慢仰起头,翻一翻眼皮,似乎一边回忆着,真在心里计算着当年的具体时间。但他立刻就醒悟过来,慢慢把头转向我,睁大两眼朝我看着,然后问,离开部队?离开……什么部队?
我说,1935年您在什么部队?
韩福茂摇摇头笑了,说,不要说1935年,我长这样大就没有吃过当兵的粮食,我从12岁学裁缝手艺,不到25岁就在这小西街上做裁缝,在东岰镇,恐怕没有不认识我韩裁缝的,也没有几个没穿过我韩裁缝做的衣服的。他一边说着,又摇一摇头,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这时,我盯住他问,您是哪一年出生?
他稍稍愣了一下,说,1……1911年。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这么说,如果您是25岁来这小西街上做裁缝的,应该是在1936年,那么1936年以前,比如……1935年,您在干什么呢?我这样说完在心里暗暗笑了一下。我没有想到,自己学数学的脑子在这时竟派上了用场。
韩福茂果然被我这精确的计算问住了,他先是支吾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静下来,冲我微微一笑说,我还没来得及问,您这位同志贵姓是……
我也冲他笑一笑,说,我姓洪。
哦,洪同志,他说,不管怎样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没在部队干过。
事情到这里显然就僵住了。我很清楚,无论这个韩福茂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坚决不承认当年曾与此事有关,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我毕竟已在公安系统干过一段时间,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有必要上一些手段了。于是,我稍稍沉了一下就笑了,然后对韩福茂说,您不要误会,我是从省里的民政厅来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落实政策,民政厅也按上级要求对当年的老红军和老苏干进行一次普查,只要核实了当年的情况,就可以给予老红军待遇,所以,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调查一下东岰镇上的情况。我说的所谓“老红军待遇”也是来江西之后才听说的。按当时规定,倘若真能享受这种待遇,不仅每月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元的生活补贴,还可以领到一些紧俏物品的购买证,这在八十年代初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这样说罢就站起来,跟韩福茂握了握手,然后向他告辞说,我还要拜访几个老同志,所以今晚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你如果想起什么情况可以去找我。
我这样说罢,就从这个小裁缝店里出来了。
我留在东岰镇上住一晚,也是临时决定的。我在这种时候当然不能走。既然已经找到一条如此重要的线索,就一定要查出一个结果。我在临出来时,对这个韩福茂说了这样一番话也就如同投下一枚鱼饵,接下来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了。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里。
这是东岰镇革委会的一个招待所,条件不算太好,可是就在小西街那家裁缝店的斜对面。我想,如果韩福茂想来找我,只要一过街就行了。但是,在这个晚上,我等了很久韩福茂却始终没有露面。我从招待所里出来,朝斜对面望去,发现那个裁缝店很早就打烊了。这让我有些郁闷。我想,是我的哪句话说错了,还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分析错了?也许……下屋坪村的人真的找错了人,这个韩福茂确实与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或者是赖春常当年被打糊涂了,不过是又胡乱扯出这样一个人来?
我就这样想了一夜。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在我起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东岰镇时,韩福茂竟突然来找我了。韩福茂的两眼通红,显然也是一夜没有睡好。他一见我正在收拾东西,立刻问,您……要走?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是啊,事情都已办完了,今天就回省城。
他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故意装作没看见,仍然低着头收拾东西。
他又吭哧了一下,忽然问,您这次来,就是为……老红军的事?
我说是啊,就是为这件事。
他突然说,我过去……确实在游击队干过。
我立刻停住手,慢慢抬起头看着他。
他又说,我只是,不想再提……过去的那些事了。
我盯住他问,你当年,是否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他的眼里忽闪了一下,摇头说,没……没有,我真不知道这个田营长是什么人。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韩福茂仍然没把实话全说出来。
我想一想,又问,赖春常你知道吗,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
赖春常?
对,他当年叫赖顺昌。
赖顺昌?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你,你应该已听说了,当初你的名字,就是他说出来的。
韩福茂看我一眼说,赖春常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说过,十几年前下屋坪村的人也曾来向我调查过,据他们说,这人已经自杀了,我也就知道这么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看着他,又叮问一句,你在当年,真的没跟这个赖春常打过交道?
这时韩福茂突然抬起头,瞪着我问,你……真是从省里民政厅来的?
我点点头说是啊,怎么,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他又问,你,真是……来落实老红军政策的?
我又点点头,说是。
韩福茂就慢慢低下头去。
我又朝他看了一阵,然后耐心地说,你如果当年确实参加过游击队,就应该符合老红军的标准,可是你要对我说实话才行,而且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如果这样说一半留一半,我就没办法帮你了,确定老红军待遇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韩福茂似乎又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我确实……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我的心里立刻轻轻舒出一口气。我想,他终于要说实话了。
可是……他立刻又说,我……真没告诉过他们任何事情。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说,好吧,你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吧。
我一边说着就拿出一个记录本,在他面前坐下来。
韩福茂又想了想,对我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
据韩福茂说,他在1935年之前一直是区苏维埃政府的干事,后来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他就上山参加了游击队。那一年春天,游击队突然接到一个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去粤北。由于当时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正在到处搜山清剿,所以上级就严格规定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并指示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不得擅自改变计划,同时为了保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也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当时韩福茂的任务是负责在前面探路。第一天还比较顺利,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情况。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就决定连夜赶路,这样也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到第二天上午,游击队突然发现有国民党军队在附近搜山,于是当即决定先原地停下来,让韩福茂去前面打探情况,并跟他约好,如果到中午的正午时刻他还没有回来,就说明是出事了,游击队立刻动身改走另一条路线。就这样,韩福茂前头先走了。但是,韩福茂对这一带的山路并不熟悉,为躲避敌人又要不停地东绕西绕,就这样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将近中午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回去与游击队会合了,索性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钻进去,想等国民党的搜山部队离开这里时再去寻找队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支搜山部队竟然就在附近的山腰上露营了,而且埋锅造饭不像是马上要走的意思。于是韩福茂也就只好躲在山洞里耐心地等待。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刚刚放亮时前面的山坡上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韩福茂从声音的方向判断出,很可能是游击队在改走另一条路线时遭遇到敌人。于是立刻朝那个响枪的方向赶过去。快到中午时,他赶到了出事地点。这里显然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到处还在冒着青烟。丛林深处有一间纸寮,四面的竹墙和木板门都已被打得稀烂,而且还能看到溅在上面的鲜血。韩福茂知道游击队已经出事了,正准备离开这里,就被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士兵抓到了。
韩福茂说到这里重重喘出一口气,就把头慢慢低下去。
我沉了一下,问,那个赖顺昌……又是怎么回事?
韩福茂说,我……真的不认识赖顺昌。
我一下一下地看着韩福茂,没有说话。
韩福茂又想想说,也许……是那个人。
我问,哪个人?
韩福茂说,他被那个田营长手下的士兵抓到时,曾看到有一个当地人一直跟在田营长的身边,他穿一件黑纺绸上衣,挎着一只盒子枪,不停地在田营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当时韩福茂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好像是前樟坑村的,却不知叫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果然是前樟坑村的,好像还是那边“义勇队”的副大队长。
现在想,韩福茂说,也许……这人就是赖顺昌。
我问,游击队遭伏击,是不是跟这个赖顺昌有关系?
他问,什么关系?
我说,比如,向敌人提供情报?
韩福茂先是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也许……有这个可能。
可是,我立刻又问,游击队要走的另一条路线,赖顺昌怎么会知道?
韩福茂翻一翻眼皮说,那就……那就不是他说的。
这时,我就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盯住韩福茂,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认识周云吗?
韩福茂立刻睁大眼,周云?
对,她后来改名温秀英。
韩福茂不再说话了,只是用两眼死死地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了我一阵,突然说,你……不是来落实政策的,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应该是为别的事来的。我也直盯盯地看着他,不置可否。就这样看了一阵,我说,我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已经不重要,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只有说实话才会对你有利。接着,我又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究竟认不认识周云?
韩福茂又愣了一阵,点点头说,认识。
我问,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韩福茂这时已从紧张和惊愕的状态中又慢慢坦然下来,他忽然淡淡一笑说,既然你已经问到这一步,就说明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笑一笑,摇摇头说,也不完全是,有的事我还不知道,比如,周云是什么时候离开游击队下山的?她又是怎么下山的?
韩福茂想一下说,她下山,好像是在……那一年的冬天。
我说,也就是说,她下山时游击队还没有接到护送任务?
韩福茂想了想,很肯定地说,还没有。
我又问,周云当时是私自下山的,还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
韩福茂立刻说,是队长让她下山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已经怀孕,肚子大得像一口锅扣在身上,这样重的身子会拖累整个游击队,所以队长才让她走的。
我点点头,又问,敌人是在什么时候抓到周云的?
韩福茂迅速地看我一眼,说,这个……记不清了。
是在敌人伏击游击队以前,还是以后?
伏击游击队以前。
你能肯定?
当然能肯定,伏击游击队之后,敌人还让她去山上认过尸。
我掏出香烟,朝韩福茂举了一下。他摇摇头,表示不会吸烟。我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几口,突然又抬起头问,你觉得,有可能是周云向敌人提供的游击队行动路线吗?
韩福茂立刻说,当然有可能,那时敌人抓到女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我又说,如果按你所说,游击队的另一条路线是在你临去前面打探情况时才最后确定的,周云就是想向敌人提供,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韩福茂张张嘴哦了一声,没有说出话来。
我拍拍韩福茂的肩膀,示意让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来,然后说,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被那个田营长的队伍抓到之后,后来是怎样脱身的?
韩福茂又谨慎地想了一下,说,我当时穿的是当地人的衣服,手里拎着柴刀,还背着一捆柴火,所以身份就没有暴露,我只对他们说,就住在山下,是来山上砍柴从这里路过的,那些人盘问了我一阵,见没问出什么,也就信以为真把我放了。
我点点头,说,好吧。
我告别韩福茂,从招待所里出来。
韩福茂将我送出来时忽然又问,你这次……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我跟他握握手,发自内心地说,是啊,该了解的,都已了解清楚了。
那你们……
他说到这里,忽然又看看我。
我问,什么?
他吭哧了一下说,就是……老红军待遇的事。
我哦一声,点点头说,当然没问题。
他立刻问,那你看……什么时候……
我笑笑说,别着急,后面会有人来找你的。
我这样说罢,就朝镇上的长途汽车站走去。
五
应该说,我这次江西之行收获很大。
我在回来的火车上将这一次了解到的情况在头脑中梳理了一下。显然,周云在申诉材料上所说的一部分情况在韩福茂这里都已得到证实。首先,周云当初下山确实不是私自离队,而是因为怀有身孕,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才下山去生孩子的。其次,赖春常在他的证明材料中也确实隐瞒了自己当年的历史,他那时并不是前樟坑村的什么伪甲长,而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这一点不仅是下屋坪村的温主任给予证实,据温主任说,赖春常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从这一点看,赖春常揭发周云有叛变行为,他证明的可信度也就更值得怀疑了。此外,我也同意当时专案组的最后结论,赖春常是不可能与周云共同勾结出卖游击队的。正如赖春常自己所说,他当时是“义勇队”那样一个身份,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报没必要再扯上一个周云,自己去告诉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
但是,有一点,赖春常与韩福茂的说法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又恰恰与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的相矛盾。我清楚记得,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她是到罗永才家的几天以后才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而且当时还是赖顺昌带人去抓她的,当时抓她的目的,就是让她去山上认尸。而据赖春常所说,周云是一到罗永才的家里就立刻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韩福茂也十分肯定地说,周云是在游击队遭到伏击之前被捕的。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两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出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时间的顺序问题,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另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但再仔细想,正是这样一个时间顺序也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倘若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被捕,那么她叛变投敌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而如果她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这件事就复杂了,换句话说,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不是不存在了。或许,赖春常和韩福茂都是看准这一点,所以才不谋而合都这样说的。现在看来,赖春常这样说的动机显而易见,那么,那个韩福茂呢,他这样说的动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始终让我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甚至认为,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我此次来江西的最大收获。从韩福茂向我的讲述可以知道,当年在游击队完成这个护送任务时,行动路线都是由上级事先定好的,而且为保密起见,这个路线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后来在出事前,游击队改走的另一条路线也是临时才决定的,而这条新的路线只有游击队长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适中,肤色黝黑,眼睛里像蒙了一层令人难以察觉的阴霾。但这阴霾的后面又似乎还有内容,因此显得有些深邃。我和他握了一下手,请他坐下。他就在我的对面坐了。我叫李祥生。他说。他的声音帝着沉重的胸腔共鸣。我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我注意到他没穿警服,只是穿了一件有些随意的米色夹克衫,里面是深色的圆领T恤,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
是的,他又说,周云的案子当年是经我手办的。
我问,是你自己……私下办的?
他说是,我没告诉单位领导。
我又点点头,就取出一只录音笔打开,放到他面前的桌上。他于是稍稍沉了一下,就开始讲述起来……
一
这应该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1982年毕业于这个城市的师范大学数学系,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毕业还要由国家统一分配。按当时的分配政策,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一律要去中学当教师的。但那时候,中教界的待遇还很低,因此一般没人愿意去。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叫李大庆的同学,他父亲是这个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于是公安局就专门为他给了我们系一个名额,是去公安局下属的劳改局,到监狱工作。但是,这个李大庆一听说是去监狱,干部子弟的脾气就上来了,死活不肯去。可指标既然下达我们系,再想要回去已经不可能,于是也就由我们系自己支配了。当时我是系里的学生干部,不仅表现积极,政治条件也很好,系里就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劳改局。那时警察还不叫警察,叫民警,说实在话,我对当时的民警印象并不好,觉得那些人穿着一身蓝不蓝绿不绿的警服不想着如何为人民服务,却整天狐假虎威地吓唬老百姓。可是转念再想,去劳改局当民警总比去中学当教师强,于是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我来到劳改局,被分到西郊监狱。
我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周云的。我刚到监狱时,一穿上这身警服感觉立刻就变了,竟有了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我每当看到自己帽徽上鲜红的国徽,就觉得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更重要的是代表我们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我对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对每一个细节也从不掉以轻心。我下定决心,要对得起国家给予的这份信任。
我渐渐发现,关在001号监室的犯人有些不太正常。
这个犯人就是周云。她当时60多岁,据同事对我讲,已在这里关了十几年。我曾经看过关于她的材料,她是因为历史问题被判刑的。据案情记载,她的原籍是江西赣南,祖辈务农。她在三十年代初投身革命,后来还曾经参加过游击队。1934年秋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她继续留在苏区坚持对敌斗争,但后来被捕就叛变了革命。据说当时被她出卖的人很多,其中还有我们党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因此,她的刑期也就很长,被判的是无期徒刑。
我听同事讲,这个周云的认罪态度很不好,这些年来一直拒不接受改造,坚持说自己有冤情,在监室里不停地写申诉材料。但她的申诉材料只到监狱这一级就被扣下了。那时各种类似的申诉材料很多,监狱不可能都送上去,上级有关领导也没时间看这些东西。因此,尽管这个周云一直在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但她并不知道,这些材料交到监狱之后就都被扔在角落里了。那时一些冤假错案都已陆续平反,但这个周云的案子却始终没有翻过来。有关领导也曾问过此事,却都没有任何结果。后来监狱方面也就明白了,看来这个周云的案子确实不属于错案,因此也就不会涉及平反昭雪的问题。如此说来,监狱方面一直将她的申诉材料扣下也就做对了,否则真转上去不仅毫无意义,也只会给上级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从此之后,监狱索性就给周云准备了大量的废旧纸张,只要她想写就为她无条件提供,待她写完之后,只要将这些废纸从一个角落放到另一个角落也就是了。周云渐渐地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再写完材料之后就不交给监狱方面,而是一页一页地撕碎,然后一边喃喃自语地嘟囔着,将这些碎纸一把一把地从铁门上的窗洞里扔出来。那些扔出的碎纸像一团一团白色的蝴蝶,在监房的楼道里上下飞舞。监狱方面认为周云这样做严重地破坏了监房的环境卫生,因此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警告,如果她再这样肆意乱扔纸屑就要根据有关的监规对她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周云却置若罔闻,不仅我行我素,而且向外抛撒的纸屑也越来越多。渐渐地,那些纸屑甚至将她监室门口的地面都白花花地覆盖起来。看上去,像一堆蝴蝶的尸体。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傍晚临近下班时,我从001号监室的门前走过,看到一地的烂纸,就找来一把扫帚想清扫一下。我将这些烂纸扫到一起正准备倒进垃圾箱,不知怎么突发奇想,就蹲到地上将几块碎纸拼在一起,想看一看这个周云究竟都写了些什么。然而这一看,竟让我大感意外。周云写的虽然密密麻麻,内容却很简单,翻来覆去只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在来回重复。但这些字我仔细看了一阵,却都无法辨认。
我立刻感到很奇怪,难道……她一直写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当即决定,将周云最近一段时间写的材料都找来看一看。我立刻来到监狱的资料室。那时资料室还形同虚设,平时几乎没有人去查阅资料。在资料室的里面还有一个套间,是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库房,用来存放监狱里一些没用或废弃的文件资料。我知道,周云这些年来写的申诉材料,就应该都被搁置在这里。我在一个满是灰尘的角落里果然找到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竟然整整地装满一箩筐。我大致翻弄了一下,显然,放在最上面的应该是最新写的,越往下时间就越早。我拿起最上面的几页纸看了看,都是同样的字迹,也是那样的密密麻麻歪歪扭扭,但如果仔细看却无法辨认出究竟写的是什么。再往下翻,我忽然发现几页纸。这几页纸是夹在一摞散乱的纸中,用一个曲别针勉强别在一起,虽然字迹同样的潦草怪异,但如果仔细看,竟然能看出所写的内容。
我立刻将这几页纸拿出来,带回到宿舍。
在这个晚上,我将这几页纸很认真地看了一下。这显然是周云某一份申诉材料中的一部分,写的是她当年在游击队里如何与丈夫结合,后来又是如何离开游击队的一段过程。这几页材料虽然字迹还能勉强辨认出来,却断断续续,词语不仅不连贯也有些凌乱,我几乎看了大半夜,才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重新梳理再拼接起来。据她在这份材料中说,她当年的丈夫叫罗永才,她和他是在1935年初春走到一起的。那时中央主力红军已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以及红军二十四师也已经分九路突围,苏区完全被国民党军队战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留下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生存环境也就越来越残酷。当时为了便于隐蔽和相互照顾,游击队员一般都是男女相配,也就是说,大都是夫妻。周云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有十七个人,共中八对是夫妻,只有周云一个单身。她那时还只有18岁,每天钻山林住岩洞,别的女游击队员都有丈夫在身边照顾,她一个女孩独自面对这一切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后来罗永才就从别的游击队调过来。那时罗永才21岁,也是单身,生得魁梧壮实也很热心帮助战友。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帮他们撮合,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
关于罗永才后来牺牲的过程,周云在这份材料中是这样记述的。
那一年开春,由于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占领苏区之后不断“清剿”,斗争环境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加艰难。就在这时,游击队突然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中央机关的一位重要领导同志去粤北,只要进入粤北境内,那边的游击武装自会有人接应。但是,周云这时已经怀有身孕,而且妊娠反应很严重,总是不停地呕吐,身体非常虚弱。游击队领导考虑到这一次任务的特殊性,就和周云商议,让她下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待生了孩子再想办法归队。但周云的家虽然是在山下,可她离家已经很久,估计家里已没有什么人。于是罗永才考虑了一下,就让周云先去他的家里。周云就这样在一个傍晚离开游击队,独自下山去了罗永才的家。所以,周云的这份材料写到这里特别强调,她那一次离开部队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暂时下山去罗永才的家里生孩子。
罗永才的家是在山下的下屋坪村,与周云的家只隔着一架山。所以,周云对去他家的路很熟悉。在那个晚上,周云摸着山路好容易来到下屋坪村罗永才的家里。罗永才的父母还都健在,他们一见这样一个眉目清秀的儿媳突然带着身孕来到家里,就如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然都喜出望外。一番问这问那之后,见她由于长期钻山林风餐露宿,蓬头垢面身上肮脏不堪,就赶紧忙着烧水让她洗一洗身上再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又找出家里的粮食为她做饭。就这样,周云就在罗永才的家里住下来。那时国民党的“靖卫团”正在到处搜捕红军家属,所以罗永才的家里一直说罗永才是去赣江下游为人家运木材了。因此这一次,他父母就对村里人说,周云是罗永才在外面娶的媳妇,现在怀了孕才送回家来。村里知情的人立刻心领神会,于是也就都帮着罗永才的父母隐瞒。因此,周云在下屋坪村并没引起人的怀疑。
出事是在几天以后。
关于这一段记述,周云材料上的字迹更加潦草,因此辨认也就更加困难。但语句却突然一下流畅起来,也明显的有了一些条理。据材料上说,出事是在一个上午。当时周云正躺在家里的竹床上。她这时妊娠反应越来越重,已经虚弱得无法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叫赖顺昌的人带着几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闯进家来。这赖顺昌原本是附近前樟坑村一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只靠偷鸡摸狗混日子。红军主力转移以后,地主豪绅卷土重来成立了“义勇队”,赖顺昌就去投靠了“义勇队”,整天带着靖卫团的人到处搜寻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在这个上午,赖顺昌带着人闯进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周云,就转身对一个又矮又瘦军官模样的人说,就是这个女人。那个矮瘦军官走过来,朝周云看了看问,你就是周云?当时周云听了立刻感到奇怪,她来到罗永才家之后,已经改名换姓叫温秀英,她摸不清楚这些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她没动声色,只是对这个矮瘦军官说,我不知道周云是谁,我叫温秀英,是罗永才的女人。罗永才?那个矮瘦军官微微一笑说,我们来找你就是因为罗永才。他这样说罢又朝身边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就转身出去了。几个士兵立刻走过来,从竹床上拉起周云就架着往外走。罗永才的父母一见连忙扑过来挡在门口。这时赖顺昌就走过来说,你们不要找麻烦,田营长是去让她认尸的,只要认完了尸首立刻就会放回来。罗永才的父母一听说是让周云去认尸,立刻都惊得呆住了。那几个士兵趁机就将周云架出去了。
周云在这份材料上说,她后来才知道,她所在的那支游击队在完成护送领导同志去粤北的任务时,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连同那个领导同志以及她的丈夫罗永才在内,已经全部牺牲了。在那个上午,赖顺昌领着那个叫田营长的国民党军官率人将周云架到山上去,就是想让她辨认一下,哪些尸体是游击队员,最后剩下的那具她不认识的尸体,自然也就是他们要护送的人。周云在这份材料上也承认,她至今仍然搞不明白,敌人在当时怎么会对这件事的底细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如果他们让她去认尸,也就说明她的身份已经暴露,而敌人又是怎么知道她也曾是游击队员呢?
周云在那个上午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架上山,就看到在山坡的一片空地上横躺竖卧地摆放着一堆尸体。这些尸体显然都是刚从什么地方抬来的,身上满是黑紫的血污,有的中弹是在脸上,看上去惨不忍睹。这时,那个叫田营长的矮瘦军官走过来,对架在两边的士兵挥了一下手。那两个士兵立刻朝后退去。周云的身体失去了支撑,摇晃了一下勉强站住了。田营长的样子还算温和,他让周云仔细看一看,在这些尸体中有没有她不认识的人。田营长又冲周云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你过去跟他们是一起的。
周云当然明白这个田营长的用意。
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过程中,如果捉到或打死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是有很高奖赏的,所以,这个田营长显然是想找到他要找的尸体,查明身份,然后去上级那里邀功请赏。这时周云的腹痛突然开始加剧起来。她艰难地走到这些尸体的近前,立刻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这些游击队员由于长期在山林里露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身上都已衣衫褴褛,再溅上黑紫的血污,看上去就都成了一个样子。但是,周云在心里暗暗数了一下,突然将两个眼睛睁大起来,她注意到,这些尸体一共是十七具。周云知道,当初游击队包括自己在内一共是十八个人,现在自己离队,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应该还是十八个人,但眼前的这些尸体却是十七具,这也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在这次战斗中幸免于难。这个人是谁呢?会不会是罗永才?这时,那个田营长也注意到周云脸上的变化,立刻走过来问,你看到了什么?周云摇摇头说,没看到什么。赖顺昌从旁边走过来,别有用心地说,咱们开始认尸吧,你一具一具认,看哪一个是你男人罗永才。周云慢慢回过头说,既然你是前樟坑村“义勇队”的人,你会不认识罗永才吗?赖顺昌立刻被问得支吾一下,说,这些尸体都打得稀烂,谁还能认得出来。说罢就捂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这时,周云虽然这样说,却把目光转向那些尸体。她小心地在那些尸体中搜寻着,唯恐看到自己最怕看到的人。但就在这时,她的目光突然定住了。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面孔显然是在一个极端愤怒而又痛苦的瞬间凝固住了,因此有些扭歪,两只没有闭上的眼睛里仍然透出冰冷的怒火。周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肚子里也猛地抽动一下,接着就剧烈地疼痛起来。
她眼前一黑,就栽到地上失去了知觉……
周云的这份材料就到这里。后面还有半页纸,但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我注意到,这些字迹不是因为潦草,而像是被水洇过。我想,这也许是周云的泪水。我又努力辨认了一下,这半页纸上的文字大致是说,那一次在山坡上认尸,她昏倒之后就流产了。敌人认为她死定了,就将她扔在山坡上走了。直到傍晚,她才被找上山来的罗永才父母背回家去……
二
我立刻对001号监室这个叫周云的女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又在她写的这份材料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从她的讲述看,她所说的事情是发生在1935年春,而她当时是18岁,那么这样计算她现在就应该是66岁。但我清楚记得,在她的犯人登记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15年8月,也就是说,这样算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是68岁。不过我想,这也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赣南地区那样的农村,很少有人用公元去记自己的出生年月,一般都是后来经过换算才确定的,这也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误差。
也就从这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周云。
我再走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就总是有意放慢脚步。我想观察一下这个周云平时在监室里都干些什么。我发现,正如别的同事告诉我的,她在监室里似乎只做两件事情,要么趴在墙角的小桌上埋头写材料,要么一边喃喃自语着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在001号监室的门前停下来,隔着铁门上的窗洞朝里面看着。周云仍像平时一样一边喃喃自语着在监房的中间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她走路的样子并不显衰老,两腿很有力,步子也迈得很坚实,因此看上去还给人一种矫健的感觉。只是来回走得有些茫然,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令人焦虑的事情。突然,她也发现了我,于是立刻停住脚步,愣了片刻,就朝这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她来到铁门跟前站住了,微微侧过脸,隔着那个小小的窗洞与我对视着。我发现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满是沧桑的皱褶,眼睛却仍然很亮,而且像婴儿一般清澈。
她就这样与我对视了一阵,忽然说,你是新来的。
我稍稍愣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
她说,我过去从没见过你。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江西赣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给人的感觉也很清醒,似乎不像是疯疯癫癫的人说出来的。我刻意不让自己的脸上有任何表情。我对她说,你应该正常吃饭。我已经听同事说了,这个周云的食欲很不好,经常一整天不吃一点东西。周云显然将我的话听进去了,她又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你……真的关心我吗?
我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关心每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
她摇摇头说,你如果真的关心我,就不应该只是吃饭问题。
她这样说罢,仍然盯住我用力地看着。
我沉一下问,你说,应该是什么问题?
赖春常,说的都是假话。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赖春常?
赖春常是谁?
她忽然笑了,说,你会不知道赖春常是谁吗?
我又努力想了一下,还是想不出她说的这个赖春常究竟是谁。
好吧,她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赖春常曾经是咱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我们的同志,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她这样说罢,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哼,虽然他改了名字……我也知道他是谁……
她这样说着就转过身,又朝监室的深处走去。
周云的这番话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我得承认,如果是在今天,我不会在意这个周云说了什么,更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探究她的案情,因为这些年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事了,在我感知器官的表面已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我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在那时候,我毕竟只有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刚穿上警服的年轻狱警,因此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当即决定,要想办法将这个周云的案卷调出来看一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已经开始重新建立起来,那时在监狱羁押的犯人,一股情况下案卷都是存放在法院,但公安机关也会有一个副本。我工作的劳改局是公安局的下属机关,所以跟他们联系应该方便一些。于是,我在一天上午就给市局那边负责案卷的部门挂了一个电话。那边一听说是自己系统的人,果然很客气,但还是公事公办地告诉我,要想查阅犯人案卷,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信。这对我显然是一个难题。我去查阅周云案卷这件事并不想让单位领导知道。我想了一下,觉得只能求助在大学时的那个同学李大庆了。李大庆的父亲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这点事打一个招呼,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我立刻给李大庆挂了一个电话。
这时李大庆还是分来市公安局,被安排在八处工作。我知道,八处是一个要害部门,几乎掌握着这个城市公安系统所有人员的情况。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大庆一听说要求他父亲办事,竟立刻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当领导之后一直跟家里人有一个约定,无论谁,无论什么事,都不准向他开口。所以,李大庆说,要想找他父亲是不可能的。不过……李大庆想了一下又说,这件事他可以试一试。我听了立刻眼前一亮,对啊,李大庆是李副局长的儿子,这在局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打电话和他父亲打电话还不是一样,况且他现在又在八处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负责案卷那边的人也总要给一些面子。
我连忙说好好,那你现在就给那边打个电话吧。
果然,时间不长,李大庆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
他说,你现在过去吧。
我问,你……说好了?
他说,说好了。
没问题了?
你去吧。
李大庆说罢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立刻来到市局。负责案卷的人一听说是我果然没再提证明信的事,立刻就将已经准备好的周云案卷拿出来。但他们又对我说,案卷是不可以拿走的,只能在这里查阅。我看了看这个满是灰尘的卷宗夹,虽然不算太厚,但要想把里面的内容看一遍也需要一定时间。负责案卷的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旁边的一个房间指了指告诉我,那里有一个阅卷室,是专供查案卷的人使用的,但一般不会有人来。
我听了点点头,就来到阅卷室。
周云的案卷并不复杂,除去一些相关法律程序的文书,还有一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显然是六十年代写的,所以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规范,案情记述也很简要,只说是在1935年春,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周云意志动摇,先是私自脱离革命队伍,继而被敌人逮捕之后又贪生怕死,变节投敌,而且由于她的出卖使我党遭受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一位当时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和十六位游击队员全部遇难。判决书上最后说,周云以上的犯罪事实清楚,且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据此判处她无期徒刑。
我在这张判决书的下面,又看到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证明材料是一个调查笔录,被调查者是一个叫赖春常的人。周云曾对我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我想,她指的是不是这份证明材料?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还曾说,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革命同志。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又怎么会为周云的事作证呢?我立刻将这份材料拿出来。材料的开头先是介绍赖春常的基本情况:赖春常,男,汉族,1917年出生,职业农民,家住东岰人民公社下屋坪生产大队。然后是记载事情的经过,1958年,赖春常突然揭发出周云有叛变投敌的历史问题,这件事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当即派人前往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
接下来就是调查者在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的笔录。
调查者问得开门见山:你根据什么说周云曾经叛变投敌?
赖春常的回答也很干脆: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
问:你亲眼看见周云叛变?
答:是的,我亲眼看见的。
问:这件事还有谁可以证明?
答:再有……就是田营长了。
问:田营长?田营长又是谁?
答: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问:国民党军官?
答:不过,你们恐怕已经找不到他了。
问:你能详细说一下这件事的经过吗?
答:当然可以,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赖春常的陈述。
那是1935年夏天,具体是五月还是六月,已经记不清了。一天夜里,周云突然从山上跑下来,藏到下屋坪村她丈夫罗永才的家里。当时在下屋坪村附近的前樟坑村,刚好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是田营长的队伍。田营长听说了此事,又知道这个周云曾是红军游击队的人,第二天下午就带人来到下屋坪村,直扑罗永才的家把周云堵在了屋里。周云一被逮捕立刻就吓得说不出话了,接着田营长又威胁她,说是如果她不肯招供,就把她送去靖卫团,让靖卫团的那些人把她糟蹋够了,再拉去山里活埋。周云一听田营长这样说就吓得哭起来,接着也就全招了,她告诉田营长,山上的游击队刚刚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一位重要领导去粤北。然后,周云又告诉了田营民游击队准备走的详细路线。就这样,田营长立刻派了一支队伍连夜上山,在游击队要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到后半夜时,果然就将游击队等到了。当时游击队的人由于连夜赶路已经很疲惫,看到路边有一个纸寮,就进去想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纸寮是当地一种特殊建筑,一般都是用竹子搭建的简单棚舍。那时山里人还习惯用竹子造一种土纸,这种纸寮就是专门用来造纸用的。但是,就在游击队的人进到那个纸寮里,田营长的队伍也迅速在外面将这个纸寮包围起来。他们包围了纸寮却并没有急于行动,只是耐心地等待天亮。就这样,天亮以后,田营长的队伍突然向那间纸寮发起攻击。当时在纸寮的四面都架起机枪,所以游击队的人一冲出来立刻就被猛烈的火力压回去。其实田营长事先已有命令,要尽量捉活的。但那些游击队的人都不怕死,硬是顶着子弹拼命往外冲,就这样,十几个人全被打死了。这时田营长的队伍才冲上去,将那些还在冒着烟的尸体拖出来清点了一下,整整是十七个人。于是就将这些尸体都抬回来。
赖春常说到这里,就被调查者打断了。
调查者问,当时为什么要将这些尸体抬回来?
赖春常说,田营长想查找,究竟哪一个是游击队要护送的人。
调查者说,好吧,你继续说。
赖春常说,在那个下午,周云向田营长提供了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就被放回家去了。这时,田营长又派人把她抓回来,让她去山上辨认尸体。就这样,周云被带到山上,将那些尸体一具一具辨认之后,就找出了那个游击队要护送的人,他的前胸中了两枪,脖子上还中了一枪,于是田营长就命人将这具尸体抬出来,弄到上级那里请赏去了。
这时,调查者突然又将赖春常打断了。
调查者说,等一等,这里有一个问题。
赖春常问,什么……问题?
调查者说,你说的这个过程这样详细,你是怎样知道的?
沉默。赖春常没有回答。
调查者又问,你刚才说,你是亲眼看到周云叛变的?
赖春常答,是……我是……亲眼看到……她叛变的。
调查者问,你是怎样看到的呢?
调查者又问,当时,你在场吗?
调查者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无法回答,那么你说的这些情况也就都不能成立,不仅不能成立,你还要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赖春常说,好吧……我说,我当时,确实……就在现场。
调查者问,你为什么在现场?你是以什么身份在现场呢?
赖春常说,我……我在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
调查者问,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赖春常说,是,可这是……他们逼我干的。
调查者说,好吧,你再把其他细节想一想,我们还会找你的。
赖春常说,好的……我如果再想起什么,会立刻告诉你们的。
这份调查笔录就到此为止。
三
我从市局回来,心里还一直在想着这个叫赖春常的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如果从周云的案卷看,这份证明材料显然对她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周云的公婆,也就是罗永才的父母后来相继去世,于是解放后,周云就来到这个城市投奔罗永才的一个远房叔叔,后来又进了一家服装厂做工。如果没有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揭发,周云已经生活得很平静,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过去。但是,这个赖春常却突然说出这样一件事。从这份证明材料的时间看,应该是在1968年春天。1968年,在那样一个时间突然揭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如果按这个赖春常所说,他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发生这件事时又在现场,那么他的揭发和证明也就应该最直接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赖春常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那么去下屋坪村抓周云时他怎么会在场呢?此外还有两个细节。这两个细节在周云那份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中曾经出现过,这次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再次出现。
首先,周云的申诉材料中曾提到一个叫赖顺昌的人,而且据周云讲,在她被架去山上认尸时,这个赖顺昌也一直在场。但她的材料中却并未提到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始终坚持说自己当时就在现场。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这也就是说,周云是知道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存在的,那么,这个赖春常又究竟是什么人呢?“赖顺昌”和“赖春常”,这两个名字在谐音上很相近,从这一点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个人呢?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细节,周云曾在她的申诉材料中提到,在她被押上山去认尸时,曾经注意到,一共是十七具尸体,而她清楚记得,当时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她离队之后,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然是十八个人,这时怎么会只有十七具尸体呢?而这个细节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也再次出现。据赖春常说,当敌人冲进那个已经被打得稀烂的纸寮,清点那些身上还在冒烟的尸体时,整整是十七个人。这个说法与周云所说刚好吻合。如此看来,当时这支游击队的队员并没有全部牺牲,应该还有一个人幸免于难。那么,这个人又到哪去了呢?
我想到这里,就决定再向周云询问一下。
这天晚上刚好是我值班。傍晚六点钟,别的同事都下班以后,我就来到监房。我先是不动声色地在监房的楼道里走了一趟。经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我迅速地朝铁门上的那个窗洞里看了一眼。我发现,周云竟然也正在朝外看着。她一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在我朝窗洞里看去的一瞬,与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感觉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渴望和期待。于是,在我折身回来,又走到这扇铁门的窗洞跟前时,就站住了。这时我发现,周云竟然已经等在窗洞的近前。但她只是隔着窗洞静静地看着我,并没有说话。
我沉了一下,问她,赖春常……是什么人?
赖春常?
对,赖春常。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
我立刻被她问得愣了一下。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去市局查阅过她的案卷,于是想了想就说,是你告诉我的,你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
哦……
她皱起眉想了想,点点头。
我又问,你还曾说,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是的,她说,他确实曾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问,就因为他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周云立刻问,你怎么知道……他当过伪甲长?
她又摇摇头,说,我没对你说过这样的话。
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漏嘴了。赖春常曾经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这件事,我是在周云的案卷里看到的,周云确实从没有对我说过。看来周云的头脑的确很清醒,她对我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心里都是很清楚记得的。因此,我想,我跟她说话要小心。
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同一个人。
周云突然对我说。
他们真是……同一个人?
是,周云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赖春常这个名字,应该是他解放以后改的,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说自己是下屋坪村人,可是下屋坪村根本就没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揭发我的一些事情,当时除去那个田营长,也应该只有赖顺昌一个人在场,虽然赖春常揭发我叛变不是事实,可他说的一些细节跟当时还是对得上的,如果赖春常不是赖顺昌,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些细节都是那个田营长告诉他的,但我知道,虽然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可是赖春常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见到了田营长也不会对他说起当初的那些事情,所以,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我得承认,周云说的这番话条理很清晰,逻辑性也很强,应该说,如果仅从她的分析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接下来也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倘若这个赖春常和赖顺昌的确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就并不是只在三十年代当过伪甲长这样简单了,按周云的说法,他是投身到当时的地主武装“义勇队”,而且还曾经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还“害死过很多我们的同志”。这也就是说,他将自己过去的历史都隐瞒起来。
那么,这样一个人提供的证词,还能采信吗?
有一个想法始终缠绕着我。解放以后,周云来到这个城市,进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生活原本很平静,似乎已经与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就因为这个赖春常的揭发,突然将过去的那些事情又都重新翻出来,不仅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也使她从此陷入这种没有尽头的牢狱生活。且不论当年周云叛变这件事是否属实,这个赖春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倘若真像周云所说,他揭发的那些事都是诬陷,那么他这样诬陷周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很想见一见这个曾经叫赖顺昌,解放以后改名叫赖春常的人。我有一种预感,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当面问一问他,一定能从他口中知道一些更直接的事情。从那份证明材料上可以看出,这个赖春常解放后一直在下屋坪村务农,如果是这样,我只要去一趟江西,到下屋坪村就可以找到他。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很想去探究一下这件事的真相。同时,我也被一股强大的热情鼓舞起来。我是一个人民的公安民警,如果周云的这件案子确有冤情,那么,我就有责任为她澄清。
八十年代的交通还不像今天这样便利,而且,我那时每月的收入也很有限。但我还是拿出平时的一些积蓄,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就买了一张车票登上南下的火车。我按着事先在地图上查阅的路线先到赣州,然后又换乘长途汽车。那时赣南地区的公路体系还很不发达,而当地的地貌又是丘陵,长途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将近半天时间,我又步行几十公里,才在一个很深的山岰里找到这个下屋坪村。当时下屋坪村还叫下屋坪生产大队。我直接来到村里的大队办公室,找到村干部。接待我的是一个40多岁的农村汉子,操一口浓重的赣南口音。他自我介绍说,姓温,是下屋坪村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温主任一听说我的来意,就告诉我,赖春常已经死了。
我一听连忙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温主任想一想说,这个人已经死很多年了,好像……是自杀死的。
据温主任证实,赖春常的确跟赖顺昌是同一个人。赖顺昌是解放那年从前樟坑村迁来下屋坪村的,同时改名叫赖春常。他原本在村里默默无闻,平时也很少说话。但在1968年春天,突然有一伙前樟坑村的人闯来下屋坪村,说是赖顺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要将他揪回去批斗。直到这时下屋坪村的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赖春常过去叫赖顺昌。前樟坑村的人将赖春常捆回去,连续召开了几天批斗大会。那时的批斗大会实际也就是打人会,每次都是将赖春常五花大绑,让他跪到土台子的中央,然后周围站着几个人轮番用毛竹在他的身上用力抽打,一边抽打台下的人一边高喊口号,并且让他交代问题。就这样,几天以后,赖春常实在挨不住这样的拷打,就胡乱交代出周云曾在1935年春天叛变的事。这件事一说出来自然非同小可,立刻引起前樟坑村的高度重视,连夜就将此事汇报到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县领导也意识到这件事的案情重大,于是又逐级汇报到省里。就这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迅速派出专人调查,当得知这个周云已经移居到外省的城市,便立即向这边的相关部门发出通报。但是,让赖春常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出周云这件事不仅没能拯救自己,反而将自己拖入一个更可怕的深渊。赖春常在交代这件事时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如果按他所说,周云叛变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场?前樟坑村的伪甲长?这样的说法无疑站不住脚,既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怎么会跟随那个国民党军官田营长去下屋坪村抓人呢?上面立刻组成专案组,又对赖春常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这时赖春常已经又被下屋坪村的人押解回来。因为下屋坪村认为赖春常是他们的人,所以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由他们审问。专案组来到下屋坪村,和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对赖春常进行审问,这一审果然就审出了更大的问题。原来赖春常,也就是当年的赖顺昌在前樟坑村并不是什么伪甲长,而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在1935年的“大清剿”中曾带领国民党军队和“靖卫团”的人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不仅罪行累累,两手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赖春常在交代出这些问题之后,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于是一天夜里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搓成绳索,把自己吊在窗棂上了。
但是,温主任又向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据温主任说,当初在省里的专案组下来调查时,一度曾怀疑赖春常只交代了一部分情况,而将另一些与自己有关的情况都隐瞒起来,比如,他是不是与周云相互勾结,二人共同将游击队的情报出卖给敌人的?赖春常当然很清楚,出卖游击队比当“义勇队”副大队长的罪过更大,所以当专案组的人这样问他时,立刻矢口否认。他否认的理由是,他当时既然在“义勇队”,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只要直接告诉那个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有什么必要再去抓周云,费那样大的气力从她的口中掏出情况呢?赖春常为了证明这件事,又向专案组说出一个叫韩福茂的人,他说这个韩福茂就住在东岰镇上,他对自己当年没有出卖游击队这件事应该很了解,如果专案组的人不相信可以去问一问他。专案组的人立刻问,这个韩福茂又是什么人。赖春常支支吾吾,只说是田营长在哪一次打伏击时抓到的什么人。但在那时候,专案组急于想搞出一个结果,所以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反复审问赖春常。就这样,还没等他们去东岰镇找那个叫韩福茂的人,赖春常这里就已经自缢死了。
温主任说的这个情况立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没想到,在这里又发现了一条新线索。如果真能找到这个叫韩福茂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一个了解当时情况的途径。
我连忙问,这个韩福茂,现在还在东岰镇吗?
温主任告诉我,后来下屋坪村曾派人去东岰镇了解过,这个韩福茂果然还在。他当时已经50多岁,在镇里的小西街上做裁缝。不过那时赖春常已经自杀,所以去了解情况的人只是简单地向他询问了一下当年的情况。但这个韩裁缝却说,他从不认识赖春常,更没有被什么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他对去调查的人说,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
就这样,温主任说,去调查的人也就只好回来了。
我又问,你们去东岰镇找这个韩福茂,是哪一年?
温主任想一想说,大概是在……1970年前后。
我立刻在脑子里算了一下,如果按温主任这样说,这件事就刚刚过去十几年,这个韩福茂当时50多岁,现在也就应该只有60多岁。我当即决定,去东岰镇找这个韩福茂。这时温主任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我立刻明白他要说什么了。我这一次来江西特意穿了便衣,我想这样可以方便一些。这个温主任看我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又操着一口地道的北方话,突然跑到山里来询问赖春常当年的事情,一定摸不清我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我笑一笑对温主任说,你先不要问我是干什么的,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现在想请村里帮一个忙。温主任一听立刻说,没问题,你说吧,什么事。我说,我的时间很紧,还要立刻赶回去,可是现在想去东岰镇见一见这个叫韩福茂的人,你们能不能找人给我带一下路,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温主任立刻说这没问题,当年去东岰镇上调查韩福茂的人还在,就让他陪你去,村里有拖拉机,可以送你们过去。
四
就这样,在这个傍晚,我来到东岰镇。
由于有人带路,我很顺利地就来到小西街,在一个街角找到了那家门面不大的裁缝店。在我走进这裁缝店时,一眼就看到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正用手在一个妇女的身上比比画画的老年男人。我立刻断定,这个人应该就是韩福茂。他约莫60多岁,脸上的皮肉已经松弛地垂下来,看上去有了些老态,但手脚仍很麻利,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在他抬起头看到我的一瞬,突然稍稍愣了一下。我知道,虽然我穿的是便衣,但身上的装束显然与当地人不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样愣了一下之后,试探地问,您要……做衣服?
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冲他笑一笑说,不,不做衣服。
他越发警觉起来,又问,那您是来……
我问,您贵姓?
他说,姓韩。
叫,韩福茂?
是,您是……
我冲他做了一个手势,说,您先忙,我们一会儿说话。
他也冲我笑了一下,点点头。我注意到了,在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似乎停滞了半秒钟,在这半秒钟里他的目光迅速坦然下来,然后就又低下头去继续忙碌了。我坐在墙边的木凳上,掏出香烟慢慢抽着。韩福茂很快就为那个妇女量好尺寸,写了一个单子将她送出去。这时才走过来,又看一看我,然后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韩福茂的眼睛迅速眨了一下问,当年的?什么情况?
我想一想,突然问,您是哪年离开的部队?
我是有意这样问的,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末,下屋坪村的人曾去镇上向这个韩福茂核实过当年的情况,但韩福茂却矢口否认了,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被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如果真如赖春常所说,这个韩福茂当年是那个田营长在什么地方打伏击时抓到的,那么他当时的身份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红军,或者是游击队。而无论哪一种,在今天都应该是很光荣的历史。
可是……他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这样做果然起了作用,韩福茂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绕住了。他慢慢仰起头,翻一翻眼皮,似乎一边回忆着,真在心里计算着当年的具体时间。但他立刻就醒悟过来,慢慢把头转向我,睁大两眼朝我看着,然后问,离开部队?离开……什么部队?
我说,1935年您在什么部队?
韩福茂摇摇头笑了,说,不要说1935年,我长这样大就没有吃过当兵的粮食,我从12岁学裁缝手艺,不到25岁就在这小西街上做裁缝,在东岰镇,恐怕没有不认识我韩裁缝的,也没有几个没穿过我韩裁缝做的衣服的。他一边说着,又摇一摇头,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这时,我盯住他问,您是哪一年出生?
他稍稍愣了一下,说,1……1911年。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这么说,如果您是25岁来这小西街上做裁缝的,应该是在1936年,那么1936年以前,比如……1935年,您在干什么呢?我这样说完在心里暗暗笑了一下。我没有想到,自己学数学的脑子在这时竟派上了用场。
韩福茂果然被我这精确的计算问住了,他先是支吾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静下来,冲我微微一笑说,我还没来得及问,您这位同志贵姓是……
我也冲他笑一笑,说,我姓洪。
哦,洪同志,他说,不管怎样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没在部队干过。
事情到这里显然就僵住了。我很清楚,无论这个韩福茂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坚决不承认当年曾与此事有关,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我毕竟已在公安系统干过一段时间,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有必要上一些手段了。于是,我稍稍沉了一下就笑了,然后对韩福茂说,您不要误会,我是从省里的民政厅来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落实政策,民政厅也按上级要求对当年的老红军和老苏干进行一次普查,只要核实了当年的情况,就可以给予老红军待遇,所以,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调查一下东岰镇上的情况。我说的所谓“老红军待遇”也是来江西之后才听说的。按当时规定,倘若真能享受这种待遇,不仅每月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元的生活补贴,还可以领到一些紧俏物品的购买证,这在八十年代初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这样说罢就站起来,跟韩福茂握了握手,然后向他告辞说,我还要拜访几个老同志,所以今晚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你如果想起什么情况可以去找我。
我这样说罢,就从这个小裁缝店里出来了。
我留在东岰镇上住一晚,也是临时决定的。我在这种时候当然不能走。既然已经找到一条如此重要的线索,就一定要查出一个结果。我在临出来时,对这个韩福茂说了这样一番话也就如同投下一枚鱼饵,接下来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了。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里。
这是东岰镇革委会的一个招待所,条件不算太好,可是就在小西街那家裁缝店的斜对面。我想,如果韩福茂想来找我,只要一过街就行了。但是,在这个晚上,我等了很久韩福茂却始终没有露面。我从招待所里出来,朝斜对面望去,发现那个裁缝店很早就打烊了。这让我有些郁闷。我想,是我的哪句话说错了,还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分析错了?也许……下屋坪村的人真的找错了人,这个韩福茂确实与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或者是赖春常当年被打糊涂了,不过是又胡乱扯出这样一个人来?
我就这样想了一夜。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在我起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东岰镇时,韩福茂竟突然来找我了。韩福茂的两眼通红,显然也是一夜没有睡好。他一见我正在收拾东西,立刻问,您……要走?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是啊,事情都已办完了,今天就回省城。
他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故意装作没看见,仍然低着头收拾东西。
他又吭哧了一下,忽然问,您这次来,就是为……老红军的事?
我说是啊,就是为这件事。
他突然说,我过去……确实在游击队干过。
我立刻停住手,慢慢抬起头看着他。
他又说,我只是,不想再提……过去的那些事了。
我盯住他问,你当年,是否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他的眼里忽闪了一下,摇头说,没……没有,我真不知道这个田营长是什么人。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韩福茂仍然没把实话全说出来。
我想一想,又问,赖春常你知道吗,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
赖春常?
对,他当年叫赖顺昌。
赖顺昌?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你,你应该已听说了,当初你的名字,就是他说出来的。
韩福茂看我一眼说,赖春常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说过,十几年前下屋坪村的人也曾来向我调查过,据他们说,这人已经自杀了,我也就知道这么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看着他,又叮问一句,你在当年,真的没跟这个赖春常打过交道?
这时韩福茂突然抬起头,瞪着我问,你……真是从省里民政厅来的?
我点点头说是啊,怎么,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他又问,你,真是……来落实老红军政策的?
我又点点头,说是。
韩福茂就慢慢低下头去。
我又朝他看了一阵,然后耐心地说,你如果当年确实参加过游击队,就应该符合老红军的标准,可是你要对我说实话才行,而且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如果这样说一半留一半,我就没办法帮你了,确定老红军待遇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韩福茂似乎又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我确实……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我的心里立刻轻轻舒出一口气。我想,他终于要说实话了。
可是……他立刻又说,我……真没告诉过他们任何事情。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说,好吧,你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吧。
我一边说着就拿出一个记录本,在他面前坐下来。
韩福茂又想了想,对我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
据韩福茂说,他在1935年之前一直是区苏维埃政府的干事,后来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他就上山参加了游击队。那一年春天,游击队突然接到一个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去粤北。由于当时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正在到处搜山清剿,所以上级就严格规定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并指示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不得擅自改变计划,同时为了保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也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当时韩福茂的任务是负责在前面探路。第一天还比较顺利,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情况。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就决定连夜赶路,这样也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到第二天上午,游击队突然发现有国民党军队在附近搜山,于是当即决定先原地停下来,让韩福茂去前面打探情况,并跟他约好,如果到中午的正午时刻他还没有回来,就说明是出事了,游击队立刻动身改走另一条路线。就这样,韩福茂前头先走了。但是,韩福茂对这一带的山路并不熟悉,为躲避敌人又要不停地东绕西绕,就这样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将近中午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回去与游击队会合了,索性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钻进去,想等国民党的搜山部队离开这里时再去寻找队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支搜山部队竟然就在附近的山腰上露营了,而且埋锅造饭不像是马上要走的意思。于是韩福茂也就只好躲在山洞里耐心地等待。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刚刚放亮时前面的山坡上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韩福茂从声音的方向判断出,很可能是游击队在改走另一条路线时遭遇到敌人。于是立刻朝那个响枪的方向赶过去。快到中午时,他赶到了出事地点。这里显然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到处还在冒着青烟。丛林深处有一间纸寮,四面的竹墙和木板门都已被打得稀烂,而且还能看到溅在上面的鲜血。韩福茂知道游击队已经出事了,正准备离开这里,就被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士兵抓到了。
韩福茂说到这里重重喘出一口气,就把头慢慢低下去。
我沉了一下,问,那个赖顺昌……又是怎么回事?
韩福茂说,我……真的不认识赖顺昌。
我一下一下地看着韩福茂,没有说话。
韩福茂又想想说,也许……是那个人。
我问,哪个人?
韩福茂说,他被那个田营长手下的士兵抓到时,曾看到有一个当地人一直跟在田营长的身边,他穿一件黑纺绸上衣,挎着一只盒子枪,不停地在田营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当时韩福茂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好像是前樟坑村的,却不知叫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果然是前樟坑村的,好像还是那边“义勇队”的副大队长。
现在想,韩福茂说,也许……这人就是赖顺昌。
我问,游击队遭伏击,是不是跟这个赖顺昌有关系?
他问,什么关系?
我说,比如,向敌人提供情报?
韩福茂先是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也许……有这个可能。
可是,我立刻又问,游击队要走的另一条路线,赖顺昌怎么会知道?
韩福茂翻一翻眼皮说,那就……那就不是他说的。
这时,我就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盯住韩福茂,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认识周云吗?
韩福茂立刻睁大眼,周云?
对,她后来改名温秀英。
韩福茂不再说话了,只是用两眼死死地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了我一阵,突然说,你……不是来落实政策的,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应该是为别的事来的。我也直盯盯地看着他,不置可否。就这样看了一阵,我说,我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已经不重要,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只有说实话才会对你有利。接着,我又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究竟认不认识周云?
韩福茂又愣了一阵,点点头说,认识。
我问,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韩福茂这时已从紧张和惊愕的状态中又慢慢坦然下来,他忽然淡淡一笑说,既然你已经问到这一步,就说明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笑一笑,摇摇头说,也不完全是,有的事我还不知道,比如,周云是什么时候离开游击队下山的?她又是怎么下山的?
韩福茂想一下说,她下山,好像是在……那一年的冬天。
我说,也就是说,她下山时游击队还没有接到护送任务?
韩福茂想了想,很肯定地说,还没有。
我又问,周云当时是私自下山的,还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
韩福茂立刻说,是队长让她下山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已经怀孕,肚子大得像一口锅扣在身上,这样重的身子会拖累整个游击队,所以队长才让她走的。
我点点头,又问,敌人是在什么时候抓到周云的?
韩福茂迅速地看我一眼,说,这个……记不清了。
是在敌人伏击游击队以前,还是以后?
伏击游击队以前。
你能肯定?
当然能肯定,伏击游击队之后,敌人还让她去山上认过尸。
我掏出香烟,朝韩福茂举了一下。他摇摇头,表示不会吸烟。我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几口,突然又抬起头问,你觉得,有可能是周云向敌人提供的游击队行动路线吗?
韩福茂立刻说,当然有可能,那时敌人抓到女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我又说,如果按你所说,游击队的另一条路线是在你临去前面打探情况时才最后确定的,周云就是想向敌人提供,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韩福茂张张嘴哦了一声,没有说出话来。
我拍拍韩福茂的肩膀,示意让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来,然后说,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被那个田营长的队伍抓到之后,后来是怎样脱身的?
韩福茂又谨慎地想了一下,说,我当时穿的是当地人的衣服,手里拎着柴刀,还背着一捆柴火,所以身份就没有暴露,我只对他们说,就住在山下,是来山上砍柴从这里路过的,那些人盘问了我一阵,见没问出什么,也就信以为真把我放了。
我点点头,说,好吧。
我告别韩福茂,从招待所里出来。
韩福茂将我送出来时忽然又问,你这次……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我跟他握握手,发自内心地说,是啊,该了解的,都已了解清楚了。
那你们……
他说到这里,忽然又看看我。
我问,什么?
他吭哧了一下说,就是……老红军待遇的事。
我哦一声,点点头说,当然没问题。
他立刻问,那你看……什么时候……
我笑笑说,别着急,后面会有人来找你的。
我这样说罢,就朝镇上的长途汽车站走去。
五
应该说,我这次江西之行收获很大。
我在回来的火车上将这一次了解到的情况在头脑中梳理了一下。显然,周云在申诉材料上所说的一部分情况在韩福茂这里都已得到证实。首先,周云当初下山确实不是私自离队,而是因为怀有身孕,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才下山去生孩子的。其次,赖春常在他的证明材料中也确实隐瞒了自己当年的历史,他那时并不是前樟坑村的什么伪甲长,而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这一点不仅是下屋坪村的温主任给予证实,据温主任说,赖春常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从这一点看,赖春常揭发周云有叛变行为,他证明的可信度也就更值得怀疑了。此外,我也同意当时专案组的最后结论,赖春常是不可能与周云共同勾结出卖游击队的。正如赖春常自己所说,他当时是“义勇队”那样一个身份,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报没必要再扯上一个周云,自己去告诉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
但是,有一点,赖春常与韩福茂的说法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又恰恰与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的相矛盾。我清楚记得,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她是到罗永才家的几天以后才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而且当时还是赖顺昌带人去抓她的,当时抓她的目的,就是让她去山上认尸。而据赖春常所说,周云是一到罗永才的家里就立刻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韩福茂也十分肯定地说,周云是在游击队遭到伏击之前被捕的。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两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出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时间的顺序问题,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另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但再仔细想,正是这样一个时间顺序也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倘若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被捕,那么她叛变投敌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而如果她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这件事就复杂了,换句话说,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不是不存在了。或许,赖春常和韩福茂都是看准这一点,所以才不谋而合都这样说的。现在看来,赖春常这样说的动机显而易见,那么,那个韩福茂呢,他这样说的动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始终让我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甚至认为,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我此次来江西的最大收获。从韩福茂向我的讲述可以知道,当年在游击队完成这个护送任务时,行动路线都是由上级事先定好的,而且为保密起见,这个路线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后来在出事前,游击队改走的另一条路线也是临时才决定的,而这条新的路线只有游击队长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中国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 2拿起来就放不下的60...
- 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
- 4章泽
- 5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 6从日记到作文
- 7西安古镇
- 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 9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伦...
- 10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科普教育 【已完结】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