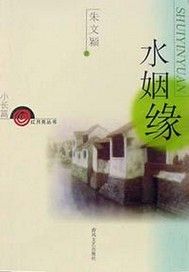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科普教育
>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 第五章
第五章
当我经历了和公爵在S餐厅的那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夜晚之后,我连续很多天时不时因为娜塔莎而忐忑不安。“不晓得那混蛋公爵会以什么手段恐吓她,到底会以何种形式向她回击呢?”我没有一刻不这样扪心自问,我被许多的猜测包围着。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不能无视他的恐吓,这并非虚张声势,如果阿辽沙继续和她住在一块儿,公爵一定会找她的茬儿。他鼠肚鸡肠、睚眦必报、深不可测、阴险狡诈,——我是这样认为的。想让他忘掉曾经受过的羞辱和不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力图回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在这次事件的全过程里,他向我指明了一点,同时还将这一点阐释得十分清楚:他坚决要求阿辽沙和娜塔莎结束目前的关系,同时还祈盼着我能让娜塔莎对即将到来的分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分手的时候绝不能有“饱含田园牧歌和席勒气质的场景”。自然,最关键的是他希望阿辽沙对他绝不能有不满情绪,仍然将他视为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这一点对于以后他以最快捷的方式霸占卡佳的财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目前我要做的便是让娜塔莎对即将面临的分手有充分的准备。可是我觉得娜塔莎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从前直言不讳的真诚已经消失;更重要的是,她好像已经对我缺乏信任感了。我的慰藉只会徒增她的烦恼;我一连串的问题愈加令她反感,以至于令她发怒。我经常是在她那儿坐着,望着她:她两手一背,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心情郁闷,脸色惨白,仿佛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也忘记了我就在她身旁。当她偶尔向我这儿看的时候(她甚至不愿和我对视了),在她脸上明显地写着烦躁和愤懑,她会立刻扭过身子。我很清楚,也许她是在思考自己面对就要到来的分手应有的打算,她这样思考时怎么会不难过、不悲伤呢?我确信无疑,她已决定要与阿辽沙脱离关系了。可她的那种阴惨惨的绝望仍然令我忧伤,使我恐惧。何况,有的时候,我连和她讲话的胆量都没有,也没勇气抚慰她,因此只能心怀恐惧地静观其变。
因为我对娜塔莎的心有高度的信任感,对于她在我面前表现出的冷峻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虽然我也觉得难过和痛苦,但我能够理解:她的极度忧伤和难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外界的一切纷扰只不过是徒增她的恼怒与愤懑。在如今的情势之下,那些和我们亲密无间的了解实情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纷扰令我们感到格外的烦躁和气愤。可我心里十分明白,娜塔莎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儿来的,并从我这儿寻求慰藉。
我当然不会向她叙述公爵和我谈话的内容:这样做的后果只会让她情绪激动,并加重她的伤感。我只不过顺便向她提及,公爵与我曾去过伯爵夫人的住所,并坚定不移地将他视为令人恐怖的恶棍。可她压根儿对他的事情没有兴趣,这点令我很开心;可她却如饥似渴地听着我对和卡佳会面时的描述。当叙述结束,虽然她对于卡佳只字不提,可她原本苍白的脸颊却变成了潮红色,整整一天她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我并没有对关于卡佳的事做任何的遮掩,我毋庸讳言地告诉她,卡佳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我何必要遮遮掩掩呢?毫无疑问,这一定会被娜塔莎识破的,同时会就此事大发雷霆。因此我刻意地作了十分详尽的交代,并且提前对她有可能提出的问题尽量作了回答的准备,这得归咎于她现在所处的地位,主动询问对她而言真的是勉为其难:说实话,谁能表现得漠不关心去询问自己情敌的长处,这该是多么困难啊?
据我猜测,她仍然不了解实情,公爵向来说一不二,照他的命令,阿辽沙一定得陪着伯爵夫人和卡佳去乡下,我不明白怎么做才能既让她清楚此事又尽量使她有能力承受。谁知道我刚打算说就被娜塔莎制止了,还说她压根儿不需要我的劝慰,原来她五天前就知道这件事了,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上帝!”我大叫一声,“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阿辽沙。”
“什么?他都告诉你了。”
“对,我把什么都想好了,文尼亚。”她又补充了一句,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已经很不耐烦了,而且是告诫我停止谈论此话题。
阿辽沙经常来探望娜塔莎,可每次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只有一回在她那儿连续待了好几个小时,然而那一回我没碰上。他每次进门都愁眉苦脸地、怯怯地又柔情似水地凝望着她;而娜塔莎则亲切、温柔而又热情地回应他,让他将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九霄云外,变得兴高采烈。他也开始经常探望我,差不多每天如此。真的,他活得太痛苦了,一个人独自烦闷的日子,他是一刻都熬不下去的,因此他总是不断地从我这儿寻求心灵的慰藉。
我和他又能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责怪我冷漠、没人情味,以至于埋怨我恨他,他心烦意乱、痛哭流涕,便时常去卡佳那儿,从她那儿获得抚慰。
那一天,也就是娜塔莎跟我说她已知道阿辽沙要走的日子那天(即公爵与我谈话一星期之后),他彻底失望地跑到我的住所,抱着我趴在我的胸口上失声痛哭,那时的他就像个孩子。我静静地听着他的一字一句。
“我实在是一个无耻而又龌龊的人,文尼亚,”他这样开口说道,“快拯救我的灵魂吧。我哭泣并非为了自己的无耻与龌龊,而是为了我即将给娜塔莎带来的痛苦。是因为我她才会痛苦……文尼亚,我的朋友,请给我说说,帮我作个抉择,她们二人,谁是我的最爱:是卡佳还是娜塔莎?”
“这件事不能由我说了算,阿辽沙,”我答道,“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
“不,文尼亚,你不明白,即使我蠢不可言也不会提出这种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扪心自问却没有答案。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可能比我更明白……好吧,你如果实在不清楚,就随便谈谈吧,你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你爱卡佳多一些。”
“你竟然是这样看的!不,不,绝对错误!你压根儿不会想到。我对娜塔莎充满无限的爱意。不管怎样我绝不能将她抛弃,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做;对卡佳我也是这么讲的,卡佳十分赞同我的观点。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方才我看到了你的笑容。唉,文尼亚,每当我如此痛苦悲伤之时,你却从未给过我半点安慰……再见!”
他朝屋外跑去,给吃惊不已的内莉内心留下了十分特别的印象,她一直静静聆听着我们的对话。那会儿她还卧病在床,正吃着药。阿辽沙从未和她说过话,每次来看望我时,他对她差不多都是视而不见。
两小时后,他再次回到我这儿,对于他脸上兴高采烈的神情,我觉得十分诧异。他还搂着我的脖子和我紧紧拥抱。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叫道,“所有的误解都消失了。我从这儿径直去了娜塔莎的住所:我实在太难过了,我绝不能失去她。一进门我就跪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吻她的脚:我一定得这么做,我情愿这么做;否则,我会愁死的。她静静地抱着我,伤心流泪。我十分坦然地对她讲,就卡佳和她而言,我更爱卡佳……”
“那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关怀我、抚慰我,——而我竟对她说了那样的一番话。她实在是太会安慰人了,伊凡·彼得诺维奇!啊,我什么都和她说了,并向她哭诉了内心的痛苦。我很坦率地告诉她,我十分爱卡佳,可不管我有多爱她,也不管我爱的是谁,如果失去了她,失去了娜塔莎,我仍然无法生存,终究会死去的。真的,文尼亚,失去她我也会死掉的,对这一点我感受颇深,真的!因此我们打算立刻结婚;因为在我们走之前还不能处理这件事,如今正处于大斋期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婚礼无法举行,因此必须等我回来,那会儿是六月一号。毋庸置疑,爸爸一定会同意的。对于卡佳,真的无所谓!您应该能体会,失去了娜塔莎,我会死的……我们的婚礼一完就一块儿去那儿,去卡佳那里……”
值得同情的娜塔莎!为了安抚这个人,她付出了那么多,并和他坐在一块儿,听他的告白,同时还以立即和他结婚的谎言来安抚这位只为自己着想的幼稚派。阿辽沙的情绪真的稳定了几天。他经常去娜塔莎那里,实质上是由于他脆弱内心的承受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可当分别的日子愈加临近之时,他再次被不安和泪水包围了,他仍然时不时地到我这儿声泪俱下地陈述自己的凄惨。最近他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娜塔莎,甭说一个半月,哪怕就一天他都离不了。可直到最后时刻他仍深信不疑,他只是和她分开一个半月,回来以后就马上娶她。就娜塔莎而言,她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将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阿辽沙从此一去不回头,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们分手的日子终于到了。娜塔莎病倒了,——她面无血色,双眼布满血丝,双唇发干,时不时喃喃低语,有时会以极快的速度狠狠地看我一眼。阿辽沙进门时发出的巨大声响传来之时,她并没有哭泣,也不答复我,只是颤抖着,活像树上的一片叶子。她的面颊如同夕照时的霞光,她快速向他跑过去,她抽搐地和他相拥,吻他,同时又面带微笑……阿辽沙对她上下打量,很紧张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并劝慰她说,他与她分开的时间不会很久,回来之后俩人就举行婚礼。显而易见,娜塔莎是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将眼泪往肚里咽。在他面前她不曾流泪。
有一回,他说起得为她准备一笔足够她在他不在的日子里花费的钱,他还让她放宽心,父亲已经许诺会给他很多在旅途上必需的花费。娜塔莎那时双眉紧锁。当我们二人独处的时候,我对她说,我手头有一百五十卢布,她随时都可以支取。她并未询问这笔钱的来源。这件事发生在阿辽沙离开的前两天,也是娜塔莎与卡佳第一次、同时又是最后一次会面的前夕。卡佳拜托阿辽沙带了个便笺,希望娜塔莎能同意她第二天登门拜访的请求;还有几句写给我的话:她希望她们会面时我也在场。
我发誓,不管怎样,十二点(与卡佳约定的时间)我必须到娜塔莎那儿去,虽然确实有太多的琐事和阻碍。内莉就甭提了,阿赫米涅夫妇最近也给我惹了不少乱子。
早在一星期前就有接二连三的麻烦出现。一个清晨,安娜·安德烈芙娜派人来请我,让我无论如何马上到她那儿去,理由是有一件不容延误的火烧眉毛的事。我赶到她的住所时,就只有她一人:她情绪激动,面色惶恐如发疯般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哆哆嗦嗦地等待着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归来。像平时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从她嘴里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害怕的原因,而每一分钟似乎都格外宝贵。她不断地责怪我,情绪激动,而这些责怪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怎么总不来呢,我们如同没人要的孩子被你丢在一旁,只得伤心落泪”,还有“鬼知道你没来时发生了啥事情”,最后她才跟我说,三天以来,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情绪总是那么激动,“实在是不知如何表达”。
“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说,“他如同发狂一般,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地给神像下跪,并在神像前面默默祈祷,睡觉时老发出呓语,活像个疯子:昨天喝菜汤的时候,匙子摆在他面前,他偏偏看不到;你问东,他答西。他总爱出门,总说:‘我得出门办点事,要去看律师’;另外,今天清晨,他将自己锁在书房内,说:‘为了打官司,我得草拟一篇公文。’好啊,我自个儿琢磨,匙子就在盘子边上你都发现不了,还说是草拟公文呢?可当我私下里透过锁孔向里看时,他正泪汪汪地坐在那里写着什么。我暗自寻思,他到底写的是哪门子公文呀?也许是由于离不开我们的阿赫米涅夫;那我们的阿赫米涅夫岂非一点希望都没了。正想到这儿,他突然从桌子边上跳了起来,将笔使劲扔在桌上,脸憋得红红的,双眼满是泪光,拿上帽子走了出来告诉我:‘安娜·安德烈芙娜,我马上就回来。’他离开后,我立即来到他的书桌旁;关于我们那个官司的公文在他那儿堆得老高,他连碰都不准我碰。我曾反复提出要求:你能否让我将这些公文挪开,就一小会儿,我得把桌上的尘土擦掉。‘绝不允许’,他一边喊一边挥动双手:自从他来到彼得堡之后,脾气越来越躁,碰上点儿事就吵吵嚷嚷。我走到书桌边上去寻觅:方才他写的是什么公文?因为我再清楚不过了,那些东西还在这儿,当他从桌边起身时他将它和别的公文搁在一块儿了。这不是嘛,老弟,伊凡·彼得诺维奇,看看,这正是我一直在寻觅的。”
然后她将一张信纸交给了我,那纸的一半写有字,可几经修改,一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
值得同情的老先生!光看开头几行便不难发现信的内容和写信的对象。是写给娜塔莎的,他最最疼爱的女儿。信的开篇还热情饱满,亲切感十足;对她来说,他是宽容的,他让她回家。信的内容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他的思路不清,情绪也太激动,又有许多的改动。仅可以觉察出,令他开篇写下充满温情话语的那种强烈情感,在完成了开头的几行以后,立刻转化成另外的情绪:老先生开始表示对女儿的不满,用轻松愉快的语气历数了她的桩桩错事,恼怒地提及了她的顽固不化,谴责她没心没肺——也许她压根儿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他发话说她会因自己的高傲而受到惩罚和诅咒,最后还让她马上老老实实回家,“到了那会儿,也只有那会儿,等你在‘亲人中间’毕恭毕敬地,以榜样的形象重头做人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够对你的行为表示宽容,”他是这样表述的。显而易见,他是在回顾自己的开头时将自己开始的宽容之心视为软弱,并因此而觉得羞愧难当,最后他受不了因强烈自尊给他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便以愤恨和恐吓收场。老太太的双手放在袖口里,在我跟前站着,等我将信读完再说给她听。
我将自己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我认为:老先生如果离了娜塔莎肯定无法生存,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得立即和解;可这还要受制于现实条件。我还陈述了自己的以下推断:首先,官司的惨败也许大大刺伤了他,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他震惊,关于被公爵击败而令他自尊心受挫所带来的强烈刺激,因为官司竟有如此的结局而给他的心灵造成的重大创伤就更不在话下了。在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找寻一份心灵的支持,因此他格外怀念那个自己在世上最最疼爱的人;另外也许是因为他可能对阿辽沙就快抛弃她的事情有所耳闻(因为他总是关注着娜塔莎,关于她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对于她现在的境遇,他再清楚不过了,同时凭自己的经验,他知道她急需别人的关怀和体贴。可他依旧不能屈尊降贵,总觉得女儿欺侮了自己。他也许曾这样认为:终究不是她先做出让步的,也许她压根儿没考虑过他们,觉得和解之事实在没什么必要。“他绝对是这么认为的,”当我为自己的想法做总结时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无法继续写下去,也许这些会导致更多不愉快的事,而这些会给人带来更为强烈的震撼,况且,谁晓得呢,这也许会使和解的时间一天天拖下去……”
老太太边哭边听我讲。到后来,我说自己得立即去看看娜塔莎,我都耽搁很长时间了,这会儿,她哆嗦了一下,说自己忘了正事。当她将信纸从众多文件中抽出之时,不留神将墨水瓶弄翻了,墨水溅到了信纸的一角上,老太太被吓坏了,生怕老先生凭这些墨迹判断出有人背着他看了他的文件,会察觉出安娜·安德烈芙娜看了给娜塔莎的信。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仅是我们了解了他心中的秘密这一条就足以令他羞愤并内心另生怨恨,同时还会因为自己的骄傲绝不宽恕亲生女儿。
可当我回顾了整件事的经过之后,又让老太太别放在心上。因为他写信时情绪过于激动,那些琐屑小事肯定注意不到,可能他还会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慢慢将此事淡忘。我用这样的话让安娜·安德烈芙娜放宽心,接着又很小心地将信搁了回去,我突然想到走之前得和她好好谈谈内莉。我认为,这个令人同情的被抛弃的孤苦伶仃的姑娘,因为她的母亲也有过被自己父亲咒骂的经历,所以她能够谈谈自己以前的生活,谈谈她母亲的死,她讲的这个悲伤而又凄凉的故事可能会感动这位老先生,并激起他的宽容;他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时机已经很成熟了;对女儿强烈的思念使他的高傲和受伤的自尊显得无足轻重。现在缺少的就是一种催化力量,是最终的有利机会,内莉恰好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机会。老太太十分认真地侧耳倾听,脸上神采奕奕,充满希望与喜悦之情。她很快开始怪我:怎么不早点对她说这一想法?她心急火燎地打探关于内莉的事情,后来还信誓旦旦地许诺,这回她会自动向老先生请命,将那位孤苦伶仃的姑娘领进家门。她由衷地热爱内莉,对于内莉的病痛,她觉得心里很不好受,询问她的病况,强迫我将那罐她专门去储藏室拿来的蜜饯带给内莉;她认为我穷得请不起大夫,还给了我五个卢布。我坚决不收,这令她十分过意不去,当听到内莉缺少连衣裙和内衣时,她心里这才舒服了,原因是她终于有机会帮帮内莉,随后她马上在箱柜里乱翻,将里面的衣服都拿了出来,挑选出一些能送给“孤女”的。
我去了娜塔莎的住所。我开始已经提到,她那里的楼梯是螺旋形的。当我在最后一截梯子那儿停下的时候,看见她门口站着个人,他正欲敲门,可一听到我上楼时发出的声音便不敲了。他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也许忽然放弃了内心的念头,转身下了楼。在最后一个楼梯拐角的小台阶那儿,我与他碰了个正着,当我发现他就是阿赫米涅夫之时,我的吃惊就别提了。尽管是白天,楼梯上的光线仍很昏暗。他紧贴墙面让我先过,现在我还能想起那两只眼睛看着我时的奇特眼神。我认为他是因为害羞才满面通红,至少是因为慌乱,甚至是惊慌失措。
“哦,原来是你,文尼亚!”他的声音发颤,说,“我到这儿是想找个人……一个记录员……都是因为那官司……前一阵他搬家了……搬到这附近……似乎并不住这儿。我搞错了,回头见。”
他以极快的速度下了楼。
我打算将这次会面的事情先搁一搁,等阿辽沙离开后就她一个人时,我一定马上对娜塔莎讲。现在她过于悲伤,就算她可以彻底想通并懂得此事的全部意义,但可能不一定会如她日后处于被最终的苦痛和彻底失望征服之时那样去理解和感受它。这会儿的时机仍然不够成熟。
那天我本想再去阿赫米涅夫家一趟,我也十分愿意去,可最终也没去。我认为,老先生和我见面之后心里一定会不好受;他可能还会以为我是专门为了碰面的事去找他。第三天我才登门拜访;老先生十分沮丧,却又十分随和地欢迎我,谈话内容总离不了他的案子。
“哦,你那天去那幢高楼上找谁呀,你记不记得我们曾在那儿碰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大概是前天。”他很随意地忽然问我,可不知为何并不看我,眼睛注视着其他地方。
“那儿住着位朋友。”我回答时也同样不看他。
“噢!那次我是去找我的记录员,阿斯塔菲耶夫;有人告诉我他住那儿……搞错了……哦,方才我们正谈着那件案子:枢密院决定……”等等,等等。
一说起他的案子,他就满面红光。
正是那天,为了让安娜·安德烈芙娜开心,我就将一切和盘托出,还求她现在别以古怪的眼神观察他,别叹息、别暗示,一句话,千万别让他知道她了解了他近期来的古怪行为。老太太十分吃惊和开心,最开始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跟我说,她已旁敲侧击地向尼古拉·希尔戈耶维奇提及了那位孤苦伶仃的姑娘,但他没什么反应,可以前又总催促她答应把小姑娘往家里带。我们商定,第二天她必须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想法,不应含糊其辞,也不该做暗示。谁知道第二天我们竟然会战栗不安。
事情是这样的:阿赫米涅夫早上与主管他案子的官员碰面了。那位官员说自己已见到了公爵,尽管公爵已将阿赫米涅夫留在了自己身边,可“因为某种家庭情况”,他决定给老先生一万卢布的报酬。老先生从那位官员那直接跑到我这儿,他十分气恼,眼中直冒火花。不知什么原因,他将我从屋内喊到楼梯上,非要我马上去找公爵,并提出与他决斗的要求。我吃惊极了,过了很久也没想到处理此事的办法。开始时我好言相劝。可老先生急火攻心,立刻晕厥过去。我马上回去倒了杯水;可当我回到楼梯时,他已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我去找他,可他已离开家了;连续三天没见他的踪影。
等到第三天我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从我那儿离开之后便径直去了公爵家,公爵外出了,他便留了个便条给他。条子上说公爵和那位官员对话的内容他已知晓,并将此视作人生最大耻辱,还说公爵是个无耻的小人,基于以上理由,他得和他决斗,并恐吓公爵不许逃避,不然让他身败名裂。
安娜·安德烈芙娜跟我说,他回家那会儿情绪十分激动,懊恼之余倒头就睡了。他对她温情脉脉,却丝毫不理会她的盘问,很明显他是心急火燎地期盼着什么。第二天清晨,市邮局送过来一封信;他阅读完毕大叫起来,抱住了自己的头。这把安娜·安德列芙娜吓得目瞪口呆。而他很快拿着帽子与手杖夺门而出。
那信是公爵写的。他言简意赅地、客客气气地告诉阿赫米涅夫,关于他和那位官员的对话内容,他认为没有向任何人解释的必要。尽管他也替阿赫米涅夫在官司上惨败深表惋惜,可不管他觉得多惋惜,他也不能对在官司上打败了的人有正当理由为了复仇找自己对手决斗的理论表示认同。关于那个让他“身败名裂”的恐吓,公爵则让他不用操心,原因是他压根儿不会身败名裂,也没有那种可能性;阿赫米涅夫的信立即会被呈给相关单位,警察如果早得到消息一定会采取措施执行保护工作。
阿赫米涅夫随即带着信去找公爵。公爵又外出了;老先生从听差那儿打听到,公爵这会儿可能在纳英斯基伯爵那儿。他未曾深思熟虑便直奔伯爵家。他已经登上了楼梯却被伯爵的司阍一把拦住。老先生火冒三丈,举起手杖便往他身上打。他很快被逮住了,拽到门口,送到警察那儿,接着又被送进警察局。有人向伯爵通风报信。当时正在那儿的公爵告诉老色狼,他就是阿赫米涅夫,即那个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的父亲(公爵曾经多次在这种事情上替伯爵效力),那位大老爷听罢报之以微笑,由开始的恼怒变成了仁慈;他命令下属将阿赫米涅夫放掉,可等到第三天老先生才被放出来,释放时还被告知是公爵亲自请伯爵赦免他的(可能也是遵照公爵的意思)。
老先生发疯一般回到家中,倒在床上不动弹,就那样躺了一个小时;他最后起身严正宣告,他会永远地诅咒自己的女儿,让她永远失去父母的祝福,这让安娜·安德烈芙娜惊恐万状。
虽然她被吓得够呛,可是又有责任帮助这位老先生,她差不多什么都忘了,夜以继日地伺候着他,用醋敷他的额头,还加上冰块。他的体温很高,不断地呓语。我一直待到凌晨两点多才告辞。可第二天早晨阿赫米涅夫起床了,当日就到了我的住处非要将内莉带走。可他和内莉交往的详情我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到家之后他就躺倒在床上。这所有的事儿都发生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这一天也是卡佳与娜塔莎会面的日子,次日,阿辽沙与卡佳就要一道离开彼得堡。这次会面我也参加了:会面定在一个清晨,在老先生还没找我之前,也是在内莉首次逃跑之前。
因为我对娜塔莎的心有高度的信任感,对于她在我面前表现出的冷峻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虽然我也觉得难过和痛苦,但我能够理解:她的极度忧伤和难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外界的一切纷扰只不过是徒增她的恼怒与愤懑。在如今的情势之下,那些和我们亲密无间的了解实情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纷扰令我们感到格外的烦躁和气愤。可我心里十分明白,娜塔莎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儿来的,并从我这儿寻求慰藉。
我当然不会向她叙述公爵和我谈话的内容:这样做的后果只会让她情绪激动,并加重她的伤感。我只不过顺便向她提及,公爵与我曾去过伯爵夫人的住所,并坚定不移地将他视为令人恐怖的恶棍。可她压根儿对他的事情没有兴趣,这点令我很开心;可她却如饥似渴地听着我对和卡佳会面时的描述。当叙述结束,虽然她对于卡佳只字不提,可她原本苍白的脸颊却变成了潮红色,整整一天她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我并没有对关于卡佳的事做任何的遮掩,我毋庸讳言地告诉她,卡佳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我何必要遮遮掩掩呢?毫无疑问,这一定会被娜塔莎识破的,同时会就此事大发雷霆。因此我刻意地作了十分详尽的交代,并且提前对她有可能提出的问题尽量作了回答的准备,这得归咎于她现在所处的地位,主动询问对她而言真的是勉为其难:说实话,谁能表现得漠不关心去询问自己情敌的长处,这该是多么困难啊?
据我猜测,她仍然不了解实情,公爵向来说一不二,照他的命令,阿辽沙一定得陪着伯爵夫人和卡佳去乡下,我不明白怎么做才能既让她清楚此事又尽量使她有能力承受。谁知道我刚打算说就被娜塔莎制止了,还说她压根儿不需要我的劝慰,原来她五天前就知道这件事了,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上帝!”我大叫一声,“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阿辽沙。”
“什么?他都告诉你了。”
“对,我把什么都想好了,文尼亚。”她又补充了一句,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已经很不耐烦了,而且是告诫我停止谈论此话题。
阿辽沙经常来探望娜塔莎,可每次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只有一回在她那儿连续待了好几个小时,然而那一回我没碰上。他每次进门都愁眉苦脸地、怯怯地又柔情似水地凝望着她;而娜塔莎则亲切、温柔而又热情地回应他,让他将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九霄云外,变得兴高采烈。他也开始经常探望我,差不多每天如此。真的,他活得太痛苦了,一个人独自烦闷的日子,他是一刻都熬不下去的,因此他总是不断地从我这儿寻求心灵的慰藉。
我和他又能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责怪我冷漠、没人情味,以至于埋怨我恨他,他心烦意乱、痛哭流涕,便时常去卡佳那儿,从她那儿获得抚慰。
那一天,也就是娜塔莎跟我说她已知道阿辽沙要走的日子那天(即公爵与我谈话一星期之后),他彻底失望地跑到我的住所,抱着我趴在我的胸口上失声痛哭,那时的他就像个孩子。我静静地听着他的一字一句。
“我实在是一个无耻而又龌龊的人,文尼亚,”他这样开口说道,“快拯救我的灵魂吧。我哭泣并非为了自己的无耻与龌龊,而是为了我即将给娜塔莎带来的痛苦。是因为我她才会痛苦……文尼亚,我的朋友,请给我说说,帮我作个抉择,她们二人,谁是我的最爱:是卡佳还是娜塔莎?”
“这件事不能由我说了算,阿辽沙,”我答道,“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
“不,文尼亚,你不明白,即使我蠢不可言也不会提出这种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扪心自问却没有答案。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可能比我更明白……好吧,你如果实在不清楚,就随便谈谈吧,你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你爱卡佳多一些。”
“你竟然是这样看的!不,不,绝对错误!你压根儿不会想到。我对娜塔莎充满无限的爱意。不管怎样我绝不能将她抛弃,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做;对卡佳我也是这么讲的,卡佳十分赞同我的观点。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方才我看到了你的笑容。唉,文尼亚,每当我如此痛苦悲伤之时,你却从未给过我半点安慰……再见!”
他朝屋外跑去,给吃惊不已的内莉内心留下了十分特别的印象,她一直静静聆听着我们的对话。那会儿她还卧病在床,正吃着药。阿辽沙从未和她说过话,每次来看望我时,他对她差不多都是视而不见。
两小时后,他再次回到我这儿,对于他脸上兴高采烈的神情,我觉得十分诧异。他还搂着我的脖子和我紧紧拥抱。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叫道,“所有的误解都消失了。我从这儿径直去了娜塔莎的住所:我实在太难过了,我绝不能失去她。一进门我就跪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吻她的脚:我一定得这么做,我情愿这么做;否则,我会愁死的。她静静地抱着我,伤心流泪。我十分坦然地对她讲,就卡佳和她而言,我更爱卡佳……”
“那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关怀我、抚慰我,——而我竟对她说了那样的一番话。她实在是太会安慰人了,伊凡·彼得诺维奇!啊,我什么都和她说了,并向她哭诉了内心的痛苦。我很坦率地告诉她,我十分爱卡佳,可不管我有多爱她,也不管我爱的是谁,如果失去了她,失去了娜塔莎,我仍然无法生存,终究会死去的。真的,文尼亚,失去她我也会死掉的,对这一点我感受颇深,真的!因此我们打算立刻结婚;因为在我们走之前还不能处理这件事,如今正处于大斋期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婚礼无法举行,因此必须等我回来,那会儿是六月一号。毋庸置疑,爸爸一定会同意的。对于卡佳,真的无所谓!您应该能体会,失去了娜塔莎,我会死的……我们的婚礼一完就一块儿去那儿,去卡佳那里……”
值得同情的娜塔莎!为了安抚这个人,她付出了那么多,并和他坐在一块儿,听他的告白,同时还以立即和他结婚的谎言来安抚这位只为自己着想的幼稚派。阿辽沙的情绪真的稳定了几天。他经常去娜塔莎那里,实质上是由于他脆弱内心的承受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可当分别的日子愈加临近之时,他再次被不安和泪水包围了,他仍然时不时地到我这儿声泪俱下地陈述自己的凄惨。最近他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娜塔莎,甭说一个半月,哪怕就一天他都离不了。可直到最后时刻他仍深信不疑,他只是和她分开一个半月,回来以后就马上娶她。就娜塔莎而言,她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将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阿辽沙从此一去不回头,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们分手的日子终于到了。娜塔莎病倒了,——她面无血色,双眼布满血丝,双唇发干,时不时喃喃低语,有时会以极快的速度狠狠地看我一眼。阿辽沙进门时发出的巨大声响传来之时,她并没有哭泣,也不答复我,只是颤抖着,活像树上的一片叶子。她的面颊如同夕照时的霞光,她快速向他跑过去,她抽搐地和他相拥,吻他,同时又面带微笑……阿辽沙对她上下打量,很紧张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并劝慰她说,他与她分开的时间不会很久,回来之后俩人就举行婚礼。显而易见,娜塔莎是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将眼泪往肚里咽。在他面前她不曾流泪。
有一回,他说起得为她准备一笔足够她在他不在的日子里花费的钱,他还让她放宽心,父亲已经许诺会给他很多在旅途上必需的花费。娜塔莎那时双眉紧锁。当我们二人独处的时候,我对她说,我手头有一百五十卢布,她随时都可以支取。她并未询问这笔钱的来源。这件事发生在阿辽沙离开的前两天,也是娜塔莎与卡佳第一次、同时又是最后一次会面的前夕。卡佳拜托阿辽沙带了个便笺,希望娜塔莎能同意她第二天登门拜访的请求;还有几句写给我的话:她希望她们会面时我也在场。
我发誓,不管怎样,十二点(与卡佳约定的时间)我必须到娜塔莎那儿去,虽然确实有太多的琐事和阻碍。内莉就甭提了,阿赫米涅夫妇最近也给我惹了不少乱子。
早在一星期前就有接二连三的麻烦出现。一个清晨,安娜·安德烈芙娜派人来请我,让我无论如何马上到她那儿去,理由是有一件不容延误的火烧眉毛的事。我赶到她的住所时,就只有她一人:她情绪激动,面色惶恐如发疯般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哆哆嗦嗦地等待着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归来。像平时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从她嘴里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害怕的原因,而每一分钟似乎都格外宝贵。她不断地责怪我,情绪激动,而这些责怪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怎么总不来呢,我们如同没人要的孩子被你丢在一旁,只得伤心落泪”,还有“鬼知道你没来时发生了啥事情”,最后她才跟我说,三天以来,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情绪总是那么激动,“实在是不知如何表达”。
“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说,“他如同发狂一般,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地给神像下跪,并在神像前面默默祈祷,睡觉时老发出呓语,活像个疯子:昨天喝菜汤的时候,匙子摆在他面前,他偏偏看不到;你问东,他答西。他总爱出门,总说:‘我得出门办点事,要去看律师’;另外,今天清晨,他将自己锁在书房内,说:‘为了打官司,我得草拟一篇公文。’好啊,我自个儿琢磨,匙子就在盘子边上你都发现不了,还说是草拟公文呢?可当我私下里透过锁孔向里看时,他正泪汪汪地坐在那里写着什么。我暗自寻思,他到底写的是哪门子公文呀?也许是由于离不开我们的阿赫米涅夫;那我们的阿赫米涅夫岂非一点希望都没了。正想到这儿,他突然从桌子边上跳了起来,将笔使劲扔在桌上,脸憋得红红的,双眼满是泪光,拿上帽子走了出来告诉我:‘安娜·安德烈芙娜,我马上就回来。’他离开后,我立即来到他的书桌旁;关于我们那个官司的公文在他那儿堆得老高,他连碰都不准我碰。我曾反复提出要求:你能否让我将这些公文挪开,就一小会儿,我得把桌上的尘土擦掉。‘绝不允许’,他一边喊一边挥动双手:自从他来到彼得堡之后,脾气越来越躁,碰上点儿事就吵吵嚷嚷。我走到书桌边上去寻觅:方才他写的是什么公文?因为我再清楚不过了,那些东西还在这儿,当他从桌边起身时他将它和别的公文搁在一块儿了。这不是嘛,老弟,伊凡·彼得诺维奇,看看,这正是我一直在寻觅的。”
然后她将一张信纸交给了我,那纸的一半写有字,可几经修改,一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
值得同情的老先生!光看开头几行便不难发现信的内容和写信的对象。是写给娜塔莎的,他最最疼爱的女儿。信的开篇还热情饱满,亲切感十足;对她来说,他是宽容的,他让她回家。信的内容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他的思路不清,情绪也太激动,又有许多的改动。仅可以觉察出,令他开篇写下充满温情话语的那种强烈情感,在完成了开头的几行以后,立刻转化成另外的情绪:老先生开始表示对女儿的不满,用轻松愉快的语气历数了她的桩桩错事,恼怒地提及了她的顽固不化,谴责她没心没肺——也许她压根儿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他发话说她会因自己的高傲而受到惩罚和诅咒,最后还让她马上老老实实回家,“到了那会儿,也只有那会儿,等你在‘亲人中间’毕恭毕敬地,以榜样的形象重头做人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够对你的行为表示宽容,”他是这样表述的。显而易见,他是在回顾自己的开头时将自己开始的宽容之心视为软弱,并因此而觉得羞愧难当,最后他受不了因强烈自尊给他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便以愤恨和恐吓收场。老太太的双手放在袖口里,在我跟前站着,等我将信读完再说给她听。
我将自己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我认为:老先生如果离了娜塔莎肯定无法生存,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得立即和解;可这还要受制于现实条件。我还陈述了自己的以下推断:首先,官司的惨败也许大大刺伤了他,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他震惊,关于被公爵击败而令他自尊心受挫所带来的强烈刺激,因为官司竟有如此的结局而给他的心灵造成的重大创伤就更不在话下了。在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找寻一份心灵的支持,因此他格外怀念那个自己在世上最最疼爱的人;另外也许是因为他可能对阿辽沙就快抛弃她的事情有所耳闻(因为他总是关注着娜塔莎,关于她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对于她现在的境遇,他再清楚不过了,同时凭自己的经验,他知道她急需别人的关怀和体贴。可他依旧不能屈尊降贵,总觉得女儿欺侮了自己。他也许曾这样认为:终究不是她先做出让步的,也许她压根儿没考虑过他们,觉得和解之事实在没什么必要。“他绝对是这么认为的,”当我为自己的想法做总结时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无法继续写下去,也许这些会导致更多不愉快的事,而这些会给人带来更为强烈的震撼,况且,谁晓得呢,这也许会使和解的时间一天天拖下去……”
老太太边哭边听我讲。到后来,我说自己得立即去看看娜塔莎,我都耽搁很长时间了,这会儿,她哆嗦了一下,说自己忘了正事。当她将信纸从众多文件中抽出之时,不留神将墨水瓶弄翻了,墨水溅到了信纸的一角上,老太太被吓坏了,生怕老先生凭这些墨迹判断出有人背着他看了他的文件,会察觉出安娜·安德烈芙娜看了给娜塔莎的信。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仅是我们了解了他心中的秘密这一条就足以令他羞愤并内心另生怨恨,同时还会因为自己的骄傲绝不宽恕亲生女儿。
可当我回顾了整件事的经过之后,又让老太太别放在心上。因为他写信时情绪过于激动,那些琐屑小事肯定注意不到,可能他还会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慢慢将此事淡忘。我用这样的话让安娜·安德烈芙娜放宽心,接着又很小心地将信搁了回去,我突然想到走之前得和她好好谈谈内莉。我认为,这个令人同情的被抛弃的孤苦伶仃的姑娘,因为她的母亲也有过被自己父亲咒骂的经历,所以她能够谈谈自己以前的生活,谈谈她母亲的死,她讲的这个悲伤而又凄凉的故事可能会感动这位老先生,并激起他的宽容;他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时机已经很成熟了;对女儿强烈的思念使他的高傲和受伤的自尊显得无足轻重。现在缺少的就是一种催化力量,是最终的有利机会,内莉恰好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机会。老太太十分认真地侧耳倾听,脸上神采奕奕,充满希望与喜悦之情。她很快开始怪我:怎么不早点对她说这一想法?她心急火燎地打探关于内莉的事情,后来还信誓旦旦地许诺,这回她会自动向老先生请命,将那位孤苦伶仃的姑娘领进家门。她由衷地热爱内莉,对于内莉的病痛,她觉得心里很不好受,询问她的病况,强迫我将那罐她专门去储藏室拿来的蜜饯带给内莉;她认为我穷得请不起大夫,还给了我五个卢布。我坚决不收,这令她十分过意不去,当听到内莉缺少连衣裙和内衣时,她心里这才舒服了,原因是她终于有机会帮帮内莉,随后她马上在箱柜里乱翻,将里面的衣服都拿了出来,挑选出一些能送给“孤女”的。
我去了娜塔莎的住所。我开始已经提到,她那里的楼梯是螺旋形的。当我在最后一截梯子那儿停下的时候,看见她门口站着个人,他正欲敲门,可一听到我上楼时发出的声音便不敲了。他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也许忽然放弃了内心的念头,转身下了楼。在最后一个楼梯拐角的小台阶那儿,我与他碰了个正着,当我发现他就是阿赫米涅夫之时,我的吃惊就别提了。尽管是白天,楼梯上的光线仍很昏暗。他紧贴墙面让我先过,现在我还能想起那两只眼睛看着我时的奇特眼神。我认为他是因为害羞才满面通红,至少是因为慌乱,甚至是惊慌失措。
“哦,原来是你,文尼亚!”他的声音发颤,说,“我到这儿是想找个人……一个记录员……都是因为那官司……前一阵他搬家了……搬到这附近……似乎并不住这儿。我搞错了,回头见。”
他以极快的速度下了楼。
我打算将这次会面的事情先搁一搁,等阿辽沙离开后就她一个人时,我一定马上对娜塔莎讲。现在她过于悲伤,就算她可以彻底想通并懂得此事的全部意义,但可能不一定会如她日后处于被最终的苦痛和彻底失望征服之时那样去理解和感受它。这会儿的时机仍然不够成熟。
那天我本想再去阿赫米涅夫家一趟,我也十分愿意去,可最终也没去。我认为,老先生和我见面之后心里一定会不好受;他可能还会以为我是专门为了碰面的事去找他。第三天我才登门拜访;老先生十分沮丧,却又十分随和地欢迎我,谈话内容总离不了他的案子。
“哦,你那天去那幢高楼上找谁呀,你记不记得我们曾在那儿碰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大概是前天。”他很随意地忽然问我,可不知为何并不看我,眼睛注视着其他地方。
“那儿住着位朋友。”我回答时也同样不看他。
“噢!那次我是去找我的记录员,阿斯塔菲耶夫;有人告诉我他住那儿……搞错了……哦,方才我们正谈着那件案子:枢密院决定……”等等,等等。
一说起他的案子,他就满面红光。
正是那天,为了让安娜·安德烈芙娜开心,我就将一切和盘托出,还求她现在别以古怪的眼神观察他,别叹息、别暗示,一句话,千万别让他知道她了解了他近期来的古怪行为。老太太十分吃惊和开心,最开始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跟我说,她已旁敲侧击地向尼古拉·希尔戈耶维奇提及了那位孤苦伶仃的姑娘,但他没什么反应,可以前又总催促她答应把小姑娘往家里带。我们商定,第二天她必须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想法,不应含糊其辞,也不该做暗示。谁知道第二天我们竟然会战栗不安。
事情是这样的:阿赫米涅夫早上与主管他案子的官员碰面了。那位官员说自己已见到了公爵,尽管公爵已将阿赫米涅夫留在了自己身边,可“因为某种家庭情况”,他决定给老先生一万卢布的报酬。老先生从那位官员那直接跑到我这儿,他十分气恼,眼中直冒火花。不知什么原因,他将我从屋内喊到楼梯上,非要我马上去找公爵,并提出与他决斗的要求。我吃惊极了,过了很久也没想到处理此事的办法。开始时我好言相劝。可老先生急火攻心,立刻晕厥过去。我马上回去倒了杯水;可当我回到楼梯时,他已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我去找他,可他已离开家了;连续三天没见他的踪影。
等到第三天我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从我那儿离开之后便径直去了公爵家,公爵外出了,他便留了个便条给他。条子上说公爵和那位官员对话的内容他已知晓,并将此视作人生最大耻辱,还说公爵是个无耻的小人,基于以上理由,他得和他决斗,并恐吓公爵不许逃避,不然让他身败名裂。
安娜·安德烈芙娜跟我说,他回家那会儿情绪十分激动,懊恼之余倒头就睡了。他对她温情脉脉,却丝毫不理会她的盘问,很明显他是心急火燎地期盼着什么。第二天清晨,市邮局送过来一封信;他阅读完毕大叫起来,抱住了自己的头。这把安娜·安德列芙娜吓得目瞪口呆。而他很快拿着帽子与手杖夺门而出。
那信是公爵写的。他言简意赅地、客客气气地告诉阿赫米涅夫,关于他和那位官员的对话内容,他认为没有向任何人解释的必要。尽管他也替阿赫米涅夫在官司上惨败深表惋惜,可不管他觉得多惋惜,他也不能对在官司上打败了的人有正当理由为了复仇找自己对手决斗的理论表示认同。关于那个让他“身败名裂”的恐吓,公爵则让他不用操心,原因是他压根儿不会身败名裂,也没有那种可能性;阿赫米涅夫的信立即会被呈给相关单位,警察如果早得到消息一定会采取措施执行保护工作。
阿赫米涅夫随即带着信去找公爵。公爵又外出了;老先生从听差那儿打听到,公爵这会儿可能在纳英斯基伯爵那儿。他未曾深思熟虑便直奔伯爵家。他已经登上了楼梯却被伯爵的司阍一把拦住。老先生火冒三丈,举起手杖便往他身上打。他很快被逮住了,拽到门口,送到警察那儿,接着又被送进警察局。有人向伯爵通风报信。当时正在那儿的公爵告诉老色狼,他就是阿赫米涅夫,即那个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的父亲(公爵曾经多次在这种事情上替伯爵效力),那位大老爷听罢报之以微笑,由开始的恼怒变成了仁慈;他命令下属将阿赫米涅夫放掉,可等到第三天老先生才被放出来,释放时还被告知是公爵亲自请伯爵赦免他的(可能也是遵照公爵的意思)。
老先生发疯一般回到家中,倒在床上不动弹,就那样躺了一个小时;他最后起身严正宣告,他会永远地诅咒自己的女儿,让她永远失去父母的祝福,这让安娜·安德烈芙娜惊恐万状。
虽然她被吓得够呛,可是又有责任帮助这位老先生,她差不多什么都忘了,夜以继日地伺候着他,用醋敷他的额头,还加上冰块。他的体温很高,不断地呓语。我一直待到凌晨两点多才告辞。可第二天早晨阿赫米涅夫起床了,当日就到了我的住处非要将内莉带走。可他和内莉交往的详情我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到家之后他就躺倒在床上。这所有的事儿都发生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这一天也是卡佳与娜塔莎会面的日子,次日,阿辽沙与卡佳就要一道离开彼得堡。这次会面我也参加了:会面定在一个清晨,在老先生还没找我之前,也是在内莉首次逃跑之前。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中国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 2拿起来就放不下的60...
- 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
- 4章泽
- 5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 6从日记到作文
- 7西安古镇
- 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 9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伦...
- 10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科普教育 【已完结】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