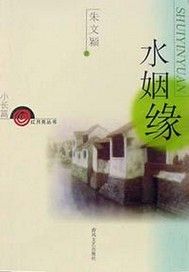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科普教育
> 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 第十一章 圆仁目睹的新罗人——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札记
第十一章 圆仁目睹的新罗人——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札记
唐朝时候,在中国的新罗人很多,特别是从现在苏北到山东半岛一带,新罗人更是遍布各地。但是,这些新罗人为何而来,从事什么活动,生活情况怎样,和中国人的关系如何等,我国的史籍中都缺乏必要的记载。日本和尚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笔者主要根据该书所载,再参考其他有关资料,想对唐后期在中国的新罗人情况理出一个头绪来。
新罗人在唐的分布
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圆仁提到的新罗人很多,仅有具体姓名者就有如下47人。
译语(翻译):金正南、朴正长、刘慎言、道玄。
僧人:圣林和尚、谅贤、法清、常寂、玄测法师、季信惠、弘仁、庆元、惠溢、教惠、昙表、智真、范、顿、明信、惠觉、修惠、金政、真空、法行、忠信、善范、道真、师教、咏贤、信惠、融洛、师俊、小善、怀亮、智应。
官吏:通事、押衙张咏、新罗使张押衙、唐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
其他新罗人:王请、王长文、王宪、王宗、郑客、陈忠、金子白、钦良晖、金珍。
除了以上有姓名者以外,笼统提到的新罗人还很多。这些新罗人,在僧人、官吏、译语之外,还有水手、商人等。根据圆仁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出新罗人分布的大致情况。
圆仁到唐最早接触新罗人是在楚州(江苏淮安)。开成四年(839)二月,圆仁一行到达楚州,日本遣唐使为了回国,雇新罗人谙海路者60余人。一次能雇熟悉海路者60多人,可见新罗人在楚州为数不少。在从楚州前往密州(山东诸城)的途中,圆仁及其随从僧惟正、惟晓、水手行者丁雄满(万)在东海县(江苏连云港)境内海岸下船,准备暂住,待机前往长安。他们刚登岸不久,看见有一条船停泊海岸,船上有10余人。待他们互相问明情况时,圆仁等自称是新罗人,显然这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对方也说他们都是新罗人,有数十人之多。后来,他们又到宿城村的新罗人宅中休息,被人识破是日本人。圆仁冒充新罗人,肯定是当地新罗人很多而且和唐人相处很好,冒充可以减少麻烦。新罗人有自己的船只,还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们明确告知圆仁等:“从此南行,逾一重山,二十余里方到村里。今交一人送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40页。这说明新罗人有自己的财产而且居住此地也非一朝一夕了。村里有新罗人宅,说明新罗人和唐人是杂居一起的。
4月17日,到达登州(山东蓬莱)牟平县(山东牟平)。20日就碰到新罗人,从新罗人的口中知道新罗的王子成为国王了;又听说日本朝贡使驾五只新罗船离去的消息。同时又听说日本朝贡使的另外一批所乘的四只船不知去向。
26日,有30余新罗人骑马乘驴而来,告知圆仁等州押衙要来看望他们的消息。不久,押衙驾新罗船来,“下船登岸,多有娘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56页。既然妇女很多,更说明新罗人早已定居于此地,并非来往匆匆的过客。同时,圆仁又从这些新罗人口中知道,日本朝贡使的九条船都安全无恙。29日,圆仁等命新罗译语道玄与新罗人商量在此地居留的问题,结果顺利谈妥,新罗人愿提供方便。5月1日,圆仁又遣人去邵村找该村的头领王训,既买粮又谈留住此村的事,王训立即表示,他负责办理此事。王训与上面提到的新罗人态度一致,大概王训也是新罗人。
6月初,圆仁等又到文登县(山东文登)清宁乡赤山村的法花院(寺),该院有僧三十多人,都是新罗人。他们还保持着新罗人的风俗习惯。例如,他们非常重视八月十五日这个节日。据新罗僧谈,这一天是新罗与渤海作战取得胜利的节日,所以,新罗人“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个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入唐记》第67页。这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一致。《旧唐书》卷一九九《新罗传》在叙述新罗的风俗时说:“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说:“八月望日,大宴赉官吏,射。”《册府元龟》卷九五九《外臣部·土风一》说:“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这些内容,虽然和《入唐记》所载大体一致,但都没有《入唐记》所载内容丰富而且详细。同时,还缺少为什么重视八月十五日这一重要内容。不难看出:《入唐记》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比我国的有关史籍更为珍贵。这时朝鲜半岛还没有文字,汉文的有关记载自然对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十分有用,《入唐记》也不例外。从圆仁与新罗僧共食饼等情节来看,《入唐记》的内容是十分可信的。
赤山村一带不仅有新罗寺院,而且是新罗人聚居的地方。十月十六日,寺里讲《法花经》,听众男女道俗除了圆仁等四个日本人以外,全都是新罗人。人数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据圆仁“男女道俗”、“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等提法,可知听众有男女老少尊卑之别。既然有各种性别、年龄、等级的人参加,当然是相当多的人了。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一日,圆仁等四人到达青州(山东益都)龙兴寺。二十四日,典座僧将其引向新罗院安置。四月五日,他们又到长山县(山东邹平东)也同样是被醴泉寺的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长山县属于淄州,由此可见,青州、淄州一带新罗院不少,勿庸置疑,新罗人也到处可见。
会昌三年(843)正月二十七日,宦官召见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圆仁这时正在长安,据他所记,当时外国僧人共21人,即青龙寺南天竺僧5人,兴善寺北天竺僧1人。慈恩寺师子国僧1人,圣寺日本僧3人。接着又说“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入唐记》第159、184页。既然说“诸寺新罗僧”,当然是指不少寺都有新罗僧人。会昌五年(845)三月,武宗有敕: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者”。圆仁记载此事,提到北天竺僧难陀、南天竺僧宝月、日本僧圆仁、惟正等,对新罗僧则记为:“新罗国僧亦无祠部牒者多。”《入唐记》第159、184页。另外,有一个长安籍的僧人,为了逃避武宗灭佛的灾难,曾冒充新罗僧,暂住大荐福寺。由此可见,当时,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新罗僧人是最多的。
在唐朝政府中,还有新罗人充任重要官员。会昌三年(843)八月十三日,由于武宗灭佛,圆仁等为了回国,去求见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李元佐信敬佛法,是新罗人,住宅在永昌坊。到了会昌五年(845)三月,李元佐除了左神策军押衙的头衔以外,又加上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等官衔。左神策军押衙是禁军的下级军官,银青光禄大夫是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是虚衔,殿中监察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属官,上柱国是武散官。由此看来,李元佐虽然不是有实权的高级的官员,但也是个颇有声誉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圆仁才请求他帮忙办理回国事宜。
会昌五年三月,圆仁离开长安,东去回国途经郑州、汴州到楚州觅船。七月三日到楚州(江苏淮安),住新罗坊。楚州治所是山阳县(江苏淮安),新罗译语刘慎言想把圆仁等安置在县新罗坊,未得县司许可。7月9日,到涟水县(江苏涟水),住新罗坊。24日,到文登县(山东文登)去勾当(办理)新罗所。该县还有新罗人户。
综上所述,圆仁所到之处,看到过新罗人的地方有:楚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淄州、长安、泗州。其实,圆仁未到过的地方也多处有新罗人,例如,宪宗时新罗“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恶风,漂至楚州盐城县(江苏盐城)界”。当时的盐城临海,王子的船能漂至此处,其他新罗人的船当然也可漂到此处或来到此处。还有,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到浙东去求食,很可能有原在浙东的新罗人引进,否则为什么不到山东半岛去求食而舍近求远呢!据此看来,至少可以这样说,在现在的浙江、江苏、山东的沿海一带,都分布有不少新罗人口。另外,在京城长安也有少量新罗人。
新罗人在唐的职业
在唐的新罗人都从事什么职业呢?
首先,是从事佛教活动。佛教在南北朝时通过高丽传入新罗,到公元五二八年得到国家认可。后来,新罗就不断派遣学问僧到中国来求法取经。由于人数愈来愈多,在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故而唐政府决定:新罗“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但这并没有影响新罗僧继续来唐,所以在圆仁来唐时在各地碰到很多新罗僧人。
新罗僧在唐的情况,一种是像在长安那样,分散在唐朝的各寺里;一种是像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的法花院那样,集中在新罗人的寺院里。前一种情况,新罗僧必须遵守唐朝寺院的规矩,和唐朝僧人没有什么差别,都受左、右街功德使的直接管理。这些僧人的任务主要是向唐僧学习佛经,圆仁就是带着佛经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到达唐朝又到长安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同了。法花院是私人所建,建院者张宝高是不是新罗人,不得而知,但圆仁在该院居住时,管理此院的是新罗通事、押衙张咏及林大使、王训等。张咏与王训都是新罗人,院僧也是新罗人,林大使的身份虽不甚明确,但足以说明法花院是新罗人自己的寺院。
法花院的讲经习俗也与唐寺有所不同:“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讲经的仪式,也是唐和新罗兼而有之。例如:“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偈矣。”《入唐记》第72—73页。这更进一步说明法花院确是新罗人的寺院,该院保持着新罗人的习俗和讲经仪式,但也受到唐人风气的影响。以此类推,青州的新罗院,淄州长山县的新罗院,很可能大体类同。
新罗院的经济来源,是他们拥有庄田,法花院的庄田一年可得米五百石。该院的僧人对唐朝的情况十分熟悉,很可能他们和唐朝的一些著名寺院都常有交往。例如,当圆仁要前往五台山的时候,新罗僧谅贤就非常详细地告诉他前进的路程:“从赤山村到文登县,百三十里;过县到登州,五百里;从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莱州;从莱州行五百里,到青州;从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从淄州到齐州,一百八十里;过齐州到郓州,三百里;从郓州行,过黄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过魏府到镇州(恒州),五百来里;从镇州入山,行五日,约三百里,应到五台山。”《入唐记》第68页。以上所述,除了魏府(魏州即今河北大名)到镇州(河北正定)较为笼统以外,其他内容都甚具体。实际上圆仁后来没有按这条路线行进,而是到齐州禹城县(山东禹城)即北渡黄河到德州(山东陵县),然后经冀州(河北冀县)、赵州(河北赵县)、镇州(河北正定)境内到达五台山的。这说明法花院的新罗僧不只一个人到过五台山,而且走的不是一条路。
其次,是从事商业活动。新罗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来往于唐与新罗之间;其二,是在唐朝境内往返于各地。
唐与新罗的关系一直友好,新罗王死,即遣使向唐告哀;新王即位,要得到唐朝皇帝的承认。自武德四年(621)以后,新罗对唐朝贡不绝。朝贡必然得到赏赐,所以,朝贡实际上是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在官方贸易的影响下,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起来。到圆仁入唐的时候,在现在的江苏、山东半岛一带碰到很多新罗坊。新罗坊是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人聚居的地方,楚州、山阳县、涟水县等地的新罗坊,圆仁都曾在其中停留。坊中设有总管、译语,处理日常工作。圆仁到楚州、涟水等地的新罗坊,是去寻找回国的船只。商人常常来往于唐与新罗之间,必然对海上的情况相当熟悉,圆仁在楚州新罗坊得到常州(江苏常州)有两条日本船的消息,还了解到日本惠萼梨子的情况,都说明新罗坊消息灵通,交往广泛。只有频繁的商业活动才容易提供这些情况。
楚州新罗坊译语刘慎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圆仁在长安,到登州等地,都和他有书信往来。圆仁从长安回到楚州,首先找他,主要是为了请他解决回国的船只问题。后来,圆仁前往涟水,也经过他的介绍。这说明各地的新罗坊是相互联系,不是孤立的。这种相互联系靠商人最方便,当时不可能有专职的交通员。
登州是唐距新罗最近的地方,新罗人更多,除了新罗坊外,还有新罗所。新罗所是管理机构,它既负责包括商人在内的新罗人的来往,也管理在唐的新罗寺院、新罗人户,还和唐官方打交道。例如,张咏是文登县新罗所的官员,他管理法花院,又管理文登县界新罗人户。会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圆仁再次到文登县,在新罗所又碰到张咏。由张咏向登州报告,准许圆仁等暂住新罗所,候船回国。由此可知,新罗商人需要和唐官府办理交涉时,也应当是有新罗所代办的。
另外,在登州城南街东还有新罗馆、渤海馆。新罗馆是什么性质的单位,现在很难确知,但从它和渤海馆相提并论,同设一处看来,大概也是为唐和新罗政治与贸易发展的需要而设。王仲荦教授说:“由于聘问通使的频繁和互市的不断发展,唐中叶以后,还在青州(治益都,今山东益都县)设立渤海馆,专门用来接待渤海来唐的使团。”《隋唐五代史》上册第601页。青州、登州都在山东半岛北部,所处地位类同。登州的渤海馆与新罗馆又同在一处,不言而喻,新罗馆也是唐为接待新罗使团而设的专门机构,也是由于聘问通使的频繁和互市不断发展的产物。
新罗坊、新罗所、新罗馆,都和新罗商人在唐的活动密切相关。
据圆仁所记,楚州、海州、登州是唐和日本、新罗海路交往的据点。楚州虽不临海,但当时淮水从楚州向东经涟水入海,同时,楚州又位于运河的交通要道上,所以,该地也必然是个商业中心。圆仁从长安东去,首先到楚州,然后到海州、登州,都是为了找寻回国的船只。在他之前,有些从京兆来的新罗僧也曾到海州找船回国。未达目的,也必然向登州而去。圆仁最后是在登州境内乘新罗船回国的。这些地方来往船只很多,商业必然发达。新罗商人对这里的商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圆仁第一次到海州,就碰到十多个新罗人驾船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入唐记》第40、99页。圆仁最后回国时,在密州境内碰到新罗人陈忠的船,也是“载炭欲往楚州”《入唐记》第40、99页。从北向南运炭,又必然从南向北运送其他货物。不难看出,新罗商人的长途贩运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海内外互相交往的频繁以及贸易发展的需要,新罗人充任译语、水手者很多。有姓名可查的译语已如上述,不知姓名者,还有大量的水手,《入唐记》中有多处记载。这是新罗人在唐的相当大部分。至于在唐的留学生等,《入唐记》虽未提及,但决不会没有。在京任职的李元佐,很可是新罗留学生的考试及第者。
新罗人和唐人、日本人的关系
在唐代,唐朝与新罗、日本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这主要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对日本和新罗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文化首先传入朝鲜半岛,继又传入日本,所以,日本学者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文本第17、152页。视新罗为“中国文化的分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文本第17、152页。日本人最初先从朝鲜半岛学习中国文化,后来才直接到中国来的。所以,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文本第50页。遣隋使、遣唐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时,新罗、日本都还使用汉字。这说明唐和新罗、日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文化基础的。
既然在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新罗起了桥梁作用,新罗人接受中国文化较早,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深,和中国人的交往也多,无疑,新罗人可以在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的时候发挥媒介作用。圆仁目睹的新罗人正是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
圆仁到唐的船上,雇有新罗译语金正南。在船行至距长江口不远的地方,发现有黄色的水,众人皆以为是长江流水,但当有人登上桅子远望时,发现前面还是浅绿色的水,遂使许多人暂感失望。于是,金正南解释说:“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泊水(地名),疑逾掘港欤?”《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尽管金正南的解释还不够确切,但至少可以说他对扬州一带是有所了解的。
圆仁等到达扬州后,金正南接到停泊于海州的另一日本船上新罗译语朴正长的书信。非常明显,新罗译语在两条日本船之间发挥了互相联系的作用。
开成三年(838)七月,圆仁等到达扬州。十二月十八日,“新罗译语金正南为定诸使归国之船,向楚州发去”《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四日,又“依金正南请,为令修理所买船,令都匠、番将、船工、锻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由此可见,金正南、朴正长等新罗译语,不仅是翻译,而且引导日本使团入唐,又为日本使团回国做好了准备,充当了日本遣唐使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如果说日本人吸收唐朝先进文化时离不开新罗人,决非言过其实。
开成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圆仁等所乘日本遣唐使归国船到达东海县(江苏连云港)。本来,圆仁与金正南密谋,船到密州境内时,乘修理船的机会,圆仁、惟正、惟晓、丁雄满(万)等四人离开船,再从陆上向长安进发。但到了东海县以后,因风向不顺,不宜再向密州,故而决定从东海县东去日本。这样,圆仁等四人只好在此下船,留居岸上,金正南为圆仁等人的行程做周到的安排,正说明新罗人比日本人对唐人更为了解,新罗人在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媒介作用是历史进程的要求。
会昌年间,唐武宗大肆灭佛,圆仁也必须离开长安。为了办理回国事宜,圆仁结识了新罗人在唐为官的李元佐。从会昌三年八月到会昌五年三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圆仁与李元佐多次交往,关系甚好。所以,圆仁记道:“左神策军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李元佐,因求归国事投,相识来近二年,情分最亲。客中云资,有所阙者,尽能相济。”《入唐记》第185页、186页。在圆仁即将离开长安时,“李侍御(当是李元佐)与外甥阮十三郎同来相问”。并帮助办理行李。圆仁离开万年县(西安市东部)前往照应县(陕西临潼)时,李元佐相送到春明门(长安外郭城东面中门)外,又共同吃茶。同时,李元佐还送圆仁很多礼物,如:“少吴绫十疋、檀香木一、檀龛象两种、和香一瓷瓶、银五股、拔折罗一、毡帽两顶、银字《金刚经》一卷,软鞋一量、钱二贯文、数在别纸也。”《入唐记》第185页、186页。显而易见,圆仁能够离开长安,顺利东去,是和李元佐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在武宗灭佛的高潮中,僧人正在遭难之际,李元佐对圆仁的帮助是难能可贵的。
圆仁东去,先到楚州新罗坊,新罗译语刘慎言也全力帮忙。刘慎言首先到楚州治所山阳县办理交涉,要求准许圆仁等日本人民在此停留,候船回国。因有武宗灭佛的诏书,县司不肯答应。刘慎言又到州里交涉,也未达目的。刘慎言把圆仁安置在私宅休息数日,圆仁把不便携带的东西寄存刘宅,然后根据刘慎言的安排,前往登州。
到了登州文登县,找到原来相识的新罗人张咏。张咏喜出望外,非常热情。这时张咏是平卢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所以,他对圆仁说:“余管内苦无异事,请安心歇息,不用忧烦。未归国之间,每日斋粮,余情愿自供,但饱飧即睡。”《入唐记》第194页。张咏为其妥善解决了食宿问题,又为其代向登州请求停留候船得到许可。这就为圆仁回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圆仁等乘新罗人金珍的船从登州界东渡,途经新罗回国。
圆仁从随遣唐使到唐,到最后和遣唐使先后都乘新罗船回国,自始至终都得到新罗人的帮助。根据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唐代的中国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新罗人存在。这些新罗人,在中国、新罗、日本的历史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对日本人直接吸收中国文化起了媒介作用,促进作用。
上述有关内容,中国史籍的记载是凤毛麟角,《入唐记》的记载却颇为详细。在这方面,《入唐记》的记载对中国史籍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圆仁笔下的“茶”
圆仁笔下的“茶”
日本和尚圆仁(794—864年),于开成三年(838)随日本遣唐使入唐,到大中元年(847)返回日本,在唐求法巡礼,历时九年又七个月左右。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一书,基本上如实记载了他在唐的所见所闻。在该书中,他多次提到“茶”,据统计,共有30多处。因为他是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场合提到“茶”,所以他每次提到的“茶”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象。
以吃茶助休息
圆仁提到“茶”次数最多的,是把吃茶和休息联系起来,以吃茶助休息。圆仁从登州(今山东蓬莱)经青州(今山东益都)、贝州(今河北清河)、赵州(今河北赵县)、镇州(今河北正定),到达五台山,又从五台山经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今山西汾阳西北)、晋州(今山西临汾)、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同州(今陕西大荔),到达长安。这样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途中当然要多次休息。休息常常吃茶,以茶帮助休息,消除疲劳。
开成五年(840)三月十三日,圆仁与弟子惟正、惟晓、行者丁雄万四人,在从登州西行途中,到达蓬莱县境内,从名为战斋馆的地方出发,西行二十五里,“到乘夫馆吃茶”。次日,又从图丘馆出发,行十里,“到乔村王家吃茶”。
四月五日,到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北),又西行到“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
四月六日,又西行到醴泉寺果园吃茶。
四月二十二日,早上行过二十里路程后,到南接刘家吃斋后又吃茶。
五月二十日,圆仁一行在五台山,从花严寺向西行七里许,“到王子寺吃茶”。
五月二十一日,从供养院吃斋后,“到中台菩萨寺吃茶”。
五月二十二日,在五台山东台巡礼途中,到台东头供养院吃茶。
会昌五年(845)五月十五日,圆仁离开长安东去,友人送他到春明门(长安外郭城正东门)外吃茶。
从以上九次吃茶的情况看来,都是在行进途中休息时吃茶的。休息同时吃茶,无疑是吃茶有助于休息、消除疲劳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九次吃茶有四次是在村民家中,一次是在醴泉寺果园,这都是体力劳动者的所在地。劳动者常备有茶,随时可以用来招待来往行人。再者,今天山东半岛一带也非产茶区,村民家中普遍有茶,更说明茶在劳动者的生活中相当重要。会昌五年八月,圆仁又到登州,发现“山村县人飧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痛”。圆仁感到“涩吞不入,吃即胸痛”的“盐茶粟饭”,当地村民却养成了“爱吃”的习惯。由此可见,茶对当地劳动者来说,已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必需品了。
据今人研究,“茶叶中咖啡碱有刺激神经和增进筋肉收缩力、促进新陈代谢作用,活动筋肉的功效。因而在劳动疲乏以后适量饮茶既可振奋精神,又可消除疲劳。”日本学者也认为:“茶叶中的芳香物质同样具有醒脑提神,使人愉快之感觉。”王宏树、汪前:《饮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与生理功能》,《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当时人们虽然不懂这些科学道理,但必然有所亲身感受。不难看出,茶在劳动者中广泛流行的原因即在于此。圆仁一行在长途旅行中,常常在休息时吃茶,也主要是为了消除疲劳,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以茶待客
茶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招待客人。
开成四年(839)闰正月三日,圆仁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延光寺,“当寺庆僧正入寺,屈诸寺老宿于库头(食堂)空茶空饭。百种周足,兼设音声”。所谓“空茶空饭”,颇为费解,日本学者小野胜年的解释是“恭敬地捧上来的茶饭”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106页注释。既然“百种周足,兼设音声”,当然是相当隆重的场面。在这种场合以茶饭招待客人,说明敬茶有以礼相待的意义。
四月七日,圆仁一行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兴国寺,“寺主煎茶”招待他们。又行二十里,到名为心净寺的尼寺中,碰到海州押衙,押衙有“勾当蕃客”(办理外事)的任务,自然要招待他们吃茶。“吃茶之后,便向县家去”。
开成五年(840)三月三日,圆仁等在登州“入州见录事。又入判官衙,见判官了。从载门入参见使君,邀上厅里吃茶。次日,使君(州刺史)于开元寺召见圆仁等。圆仁被召见时,使君判官正在吃茶。圆仁到来后,就对其“赐茶”,并“问本国风情”。这种边吃茶、边谈话的气氛,甚为和谐、闲雅。
三月二十三日,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应萧判官请,“到宅吃粥。汤药茗茶周足”。因为判官信仰佛教,所以对僧人特别热情,以茶饭招待僧人,无疑是非常友好的表示。
四月二日,圆仁等赴青州节度副使张员外院辞别,“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吃茶,辞别员外,到寺里。”张员外虽然不像萧判官那样信奉佛教,但也以茶食招待,可见以茶饭待客是常见的现象。
七月十三日,圆仁离五台山到太原府,住在华严寺。陪同圆仁离五台山南行的一位名叫义圆的僧人引圆仁等来此居住。圆仁颇为感激义圆,故而他记道:“头陀(义圆)自从台山为同行,一路已来,勾当粥饭茶,无所阙少。”既然从五台山到太原沿途粥饭茶无所阙少,可见这里以茶饭待客已习以为常了。
圆仁离开长安东去,于会昌五年(845)七月九日到达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县长官令“勾当茶饭饮食,且令将见”。
根据以上情况,圆仁一行受到茶或茶饭招待,都是在寺院或官府。这些地方都把他们当作客人,故而以礼相待,表示尊重。据有关学者研究,以茶待客,意义深长。当代一位研究陆羽茶道的先生认为:《茶经》中“客来敬茶的典型场面,且以茶礼恭敬奉之,体现的是一种心平气和、和睦安宁的气氛。”实际上就是“人际的融通,意态的谦和”王厚林:《陆羽茶道浅析》,《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还有位先生说:“以茶敬客,以茶会友,表示敬意、亲切、和气、淡雅的人际关系等等。”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圆仁多次碰到的茶饭招待都体现了这种意义。
以茶送礼
把茶当作礼品送与别人,是茶的另一社会作用。
开成四年(839)三月三日,圆仁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听说天台山禅林寺僧敬文从扬州来,遂派弟子惟正前去慰问,“兼赠细茶等”。在这里,赠送细茶实际上起了见面礼的作用。
三月二十三日,在楚州的新罗译语刘慎言,以细茶十斤及松脯等物赠与圆仁。刘慎言虽是新罗人,但他懂得日语和汉语,对日本人来唐颇多帮助,圆仁前后多次与他交往。这里初次见面,赠送细茶,正是他要与圆仁交友的表示。
开成五年(840)四月一日,圆仁在青州得到官府允其继续西行的证件,同时,受赐布三端,茶六斤。第二天,圆仁致书表示感谢。当时,从登州到青州,连遭三四年蝗虫灾害,以致“官私饥穷”。面临困境,圆仁不得不向官府乞粮。在此情况下,圆仁得到官府的粮、茶、布等物的支持,是难能可贵的。
会昌五年(845)五月十五日,圆仁准备离开长安回国,到万年县(今西安市东部)办理离境手续。中散大夫杨敬之信仰佛教,故而派人前往慰问,“兼赐团茶一串”。另外,职方郎中杨鲁士又在圆仁上路后派其子“送潞绢二匹,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显然,这是以茶等物为礼品送别友人。
这些以茶为礼品赠送友人的事例,意义极其深长。在这种场合,“茶”的物质意义是次要的,因为它并非贵重物品,主要是它的精神意义。圆仁对敬文送茶,刘慎言对圆仁送礼,都是在对方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向初见面的客人表示友好。由此可见,这种以茶送礼,实际是一种结交朋友的手段。青州官府赐给圆仁茶六斤、布三端,数量也不算多,但在连年遭灾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圆仁到唐巡礼求法的支持。其精神上的鼓励作用决不亚于物质上的赠予。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会昌五年圆仁离开长安时有人对他赠茶。当时,正值武宗灭佛的高潮期间,圆仁离境东去实际上是被驱逐出境的。在此困境中竟有政府官员冒着风险对他赠茶,显然有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是非观念在内。勿庸置疑,在这种场合的赠茶,必然是对圆仁在精神上的安慰。
以茶敬佛
以茶敬佛,在唐代也相当普遍。茶被佛教界视为“圣物”。按照寺院的规矩,每日都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或茶具作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以茶结缘”。这都说明“佛教与饮茶有不解之缘”。法门寺地宫出土许多茶具,“其造型和纹饰图案也都带有佛教意识色彩,可见唐代饮茶生活与佛教意识密切结合”张高举:《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看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文博》1993年第4期。在圆仁笔下的“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
开成五年(840)五月五日,圆仁在五台山竹林寺内详细观看了该寺的敬佛过程,并亲自目睹了以茶敬佛的场面。他应约“赴请入道场,看礼念法寺。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宝幡、宝珠,尽世妙彩张施铺列,杂色毡毯敷洽地上,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圣贤。”非常隆重的场面,说明“茶”在敬佛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月十六日,又在五台山华严寺看到僧人“吃茶之后入涅道场,礼拜涅相:于双林树下右胁而卧”。圆仁在这里所记的“吃茶”,大概是入涅道场的必经过程。
开成六年(841)二月,从八日到十五日,长安的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县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所谓“无碍茶饭”,就是不论僧俗同样施与茶饭。在供养佛牙的同时广施茶饭,当然是鼓励供养佛牙的意思。
如前所述,圆仁在行进途中以吃茶助休息,有三次是在寺中;以茶待客的事例,也有三次是在寺中。再加上以茶敬佛的事例,都充分说明“茶”和佛教的关系甚为密切。开成五年六月六日,唐文宗遣使到五台山,按“常例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细帔五百领,绵五百屯,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两,茶一千斤,手巾一千条”。皇帝年赐茶一千斤,说明五台山年用茶的数量很大。五台山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这就不难理解法门寺地宫为什么会出现许多珍贵的唐代茶具了。从另一方面说,也容易理解产茶地区对皇室的贡茶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旧唐书·文宗纪下》载:“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文宗)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贡新茶,宜于立春后造。”文宗“务恭俭”,才改变了造茶的时间,以表示其爱民。可见皇室的大量用茶是对产茶地区的强力索取。
以茶怡情以茶抒情
以茶怡情,以茶抒情,是茶的另一种作用,圆仁笔下的“茶”,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十八日,扬州节度使李德裕于扬州开元寺接见圆仁一行。圆仁来到时,李德裕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吃茶”。李德裕等官员共八人,他们吃茶等待日本和尚的到来。圆仁等进来,他们都起立施礼,然后共同吃茶。同时,还问长问短,了解日本的情况,例如,问日本有无寒暑的交替;有无僧寺、尼寺,有多少;有无道士;京城面积多大等等。圆仁都一一作了回答。这种边吃茶、边聊天的场面,充分反映了在座人们悠闲的心情和安逸的兴致、融洽的气氛,必然使日本和尚看到唐政府官员的友好态度。
开成四年(839)六月八日,将入夜时,圆仁等到文登县(今山东文登)清宁乡赤山村的法华院(寺),碰到院僧30余人,“相看吃茶”。众僧经过一天的佛事活动,夜幕降临之际的相聚吃茶,无疑有闲适自得之意。
开成五年(840)八月一日,圆仁到达汾州(今山西汾阳),州押衙姓何,是陪同圆仁离开五台山的义圆头陀的门徒,故而对圆仁特别热情。次日早,圆仁到“何押衙宅茶语”。在何押衙家吃过午饭,就又向西进发了。主人热情异常,客人在临行前到主人家中“茶语”,无异是以茶话别,谨表谢意。这种场合的“茶”,自然是情谊的纽带。
会昌三年(843)正月,唐武宗灭佛已经开始。二十七日,长安管理寺院的左、右街功德使通知各寺外国僧人集会。二十八日,“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后,见军容。军容亲尉安存。当日各归本寺”。在大难将要临头之际,21个外国僧人齐集一处,吃茶后,面见军容。虽然当天又各归本寺,但其心情极其沉重是勿须置疑的。
会昌五年(845)六月九日,圆仁从长安到达郑州(今河南郑州),州长史辛文昱曾在长安与圆仁相识,故而在此处相见后颇感亲切。辛长史对圆仁除了赠送礼物外,又远送于十五里之外,“遂于土店里任吃茶,语话多时相别,云:‘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上努力,早达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上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显而易见,辛长史和圆仁的吃茶话别非同一般。看来,辛长史也信仰佛教,他对武宗灭佛甚为不满,所以,借吃茶话别之机,抒发感情,希望圆仁回国后弘传佛法,把佛教的复兴寄希望于日本。他还要求圆仁成佛之日不要忘记自己。这种对佛教充满感情的言行,正是一个唐政府官员对一个日本和尚难舍难分的内在原因。
上述各种场合的吃茶现象,无不体现着一个“情”字。有的是愉快而和悦的情绪,有的是诚恳真挚的感情,有的是面临灾难的沉重心情,还有依依不舍的友情。各种各样的“情”中,蕴藏着人情、国情、教情等深层次的含义。看来,各种各样的吃茶现象中,都含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在圆仁提到的“茶”中,还有一处颇为特殊,就是以茶易物。
开成五年(840)三月十七日,在莱州(今山东掖县)境内,到潘村的潘家吃午饭。主人极为冷淡,圆仁等人乞求菜、酱、酢、盐等,一无所得。圆仁无可奈何,遂出茶一斤,买得酱菜。以茶易物,茶起了货币的作用。如果说圆仁提到的“茶”中多处主要是精神意义的话,那么,这里就主要是物质意义了。
余论
从圆仁笔下的“茶”来看,茶在唐代后期已相当流行,不仅在上层社会,而且在广大农村中也相当普及。这样一来,唐朝后期征收茶税也就不可避免了。
建中三年(782)九月,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贞元九年(793)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建议:“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下》。都得到了德宗同意。太和九年(835)十月,文宗又实行榷茶法,由政府垄断茶的买卖,“人甚苦之”。十一月,榷茶使王涯被杀,“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王涯是因参与甘露之变失败被杀的,同时被杀的官员多人,围观者对别的被杀官员无动于衷,惟独怨恨王涯,主要是因为“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可见实行榷茶法直接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十二月废除榷茶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些事例,更进一步说明圆仁笔下的“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圆仁笔下的“茶”,不仅因其物质意义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同时,其精神意义还更为深远。除了吃茶能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以外,以茶待客、以茶送礼交友、以茶敬佛、以茶怡情、以茶抒情等等,无不体现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使当时的精神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当然,“茶”的社会意义并不止圆仁所记,有时候在政治事件中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宰相欲诛宦官失败,宦官张仲清欲杀翰林学士、工部尚书郑注。张仲清请郑注饮茶,诱骗使其掉以轻心,郑注正在饮茶之际被杀。这主要是“茶”有以礼待客的作用,故而使郑注麻痹了。在这里,用以茶待客的手段达到了诱杀政敌的目的。由于本文题目所限,圆仁所记以外的“茶”,就不再赘述了。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所以,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研究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而写的。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关论著涉及者不少,专论者不多。于辅仁先生的《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见《烟台师院学报》1991年3期。一文,是近年来专文论述这一问题的大作,内容充实,很有深度,但其结论还难令人信服。故而在于先生的启发下,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灭佛不是为了查杀宣宗
于辅仁先生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关于宣宗与武宗的矛盾,宣宗被迫隐身于佛门的事,主要见之于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和尉迟的《中朝故事》。这些资料,虽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已明确表示:“鄙妄无稽”而“不取”,但也不能断言今人不可据此再作结论。笔者认为,即使承认这个前提,于先生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于先生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武宗是否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不得而知;但武宗初信佛,后信道,倒是言之有据。赞宁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宋高僧传》中华书局版第130页。不过,这种武宗初信佛教、后受人蛊惑而改信道教的观点,明显有为武宗辩护的意思。赞宁是北宋初年人,他的《宋高僧传》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编撰的。既是奉敕而作,无疑必须迎合皇帝的需要。五代十国时,赞宁是吴越僧人,宋统一全国后,他受赐紫衣,可见他颇受北宋皇帝的赏识。“所以书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不叙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迹,不主张高蹈,这倒是实在有悖于慧皎当初名其书曰《高僧传》的初衷”《佛教与中国文化》第167—168页。如是,他把武宗崇道灭佛之举归罪于蛊惑者,以减轻佛门对武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武宗在会昌元年六月以前,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是信奉道教的。《旧唐书·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坛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既然是未做皇帝时即已崇道,又在开成五年(840)秋刚做皇帝时即召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当然就不是会昌元年(841)6月突然改变态度才由信佛改为崇道了。
另外,于先生对所用资料的理解也欠确切。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在武宗生日这天,确有道士与僧人相对议论,“二个道士赐紫”,但棒决僧人却是六月十五日的事。因为六月十一日南天竺僧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此事因越过主管部门右街功德使而直接上奏皇帝,故“犯越官罪”而于六月十五日“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看来,僧人与道士相对议论,两个道士赐紫,和尚“总不得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391—392页。可以视为排佛的信号;但棒决僧人是因为外国和尚违犯唐律而受惩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于先生认为武宗“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于先生认为:“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于先生所谈的灭佛事实,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都有记载。但把这些事实视为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显然不妥。
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到会昌二年(842)他32岁。武宗应该知道宣宗的年龄。如果这时搜捕宣宗,首先应从30多岁的僧人中去找。其次,于先生很重视 的《中朝故事》中又明确说,宣宗“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从长安到江表,又有一个地域的范围。按照常规,依年龄、活动的地域查找逃者,是最有力的根据。其他像入佛门的时间、在佛门中的地位等,都是弹性很大、容易弄虚作假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烧练,指合练金丹;咒术,即念咒语行术法;禁气,是修身练仙的法术;背军,指离开军队为僧的;身上杖痕鸟文,指受过官刑的人;杂工巧,指各种特殊的手工技艺。这些内容,既没有地域、年龄的限制,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宣宗即使隐身佛门,也不会加入这些非佛门主流的行列;他只有按照正统的僧人打扮自己,才容易隐藏下来。再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并论,宣宗不可能隐身于尼中。这说明武宗的灭佛令根本没有针对宣宗的意思。
会昌五年(845),武宗敕下:从四月一日起,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十六日起,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五月十一日起,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使包括外国僧人在内的全部僧尼还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不能达到查杀的目的。如果真的要查杀宣宗,完全可以运用其他手段。如使认识宣宗的宦官或官员直接查找,或迫使与宣宗密切相关的人员提供线索等,都是更为有效的措施,何必一定要大海捞针呢!因此,把这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很难令人信服。
第三,于先生说:“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藏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死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惧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武宗对僧尼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确是事实。但于先生所举事例,恰巧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
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刘从谏侄刘稹请求为兵马留后。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议,派成德节度使王远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等率军征讨。九月,又对在京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采取了行动。
进奏院是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在平康坊,万年县领。当时,昭义节度使的押牙孙在京。武宗派兵逮捕孙,孙走脱,只将其妻子儿女杀死。因有人报告:“路府留后押牙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于是,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元和二年后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员)清查城中僧,“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还对“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捉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捉拿昭义节度使押牙孙,因孙可能刚剃发为僧,所以,打击范围只限于新裹头僧,更不包括尼在内。这种有目的有范围的迫害僧人,当然和查杀宣宗无关。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内容,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道士奏云:孔子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氏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其中说的黑衣天子,便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唐宣宗)。”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
其实,这条谶语出之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权力之争。“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显然是说有以“黑衣”为标志的人要对李唐皇帝取而代之。如果宣宗代替武宗,只是李家内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这更进一步说明,武宗灭佛并非查杀宣宗。再者,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者并非始于唐武宗灭佛时。南北朝时,宇文泰就因为“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以黄代赤承运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宇文泰)挟魏西奔,衣物旗帜并变为黑,用期讹谶之言”《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不难看出,这是宇文泰对北魏改朝换代的手段。北齐皇帝也因“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高欢)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北齐书》卷十《高涣传》。齐文宣帝高洋崇佛,曾命“道士皆剃发为沙门”,致使“齐境皆无道士”《资治通鉴》卷一六六,绍泰元年八月。但他还相信这种谶语,牵强附会地认为黑莫过于漆,漆与七同音,故而将其七弟高涣杀死。因此,如果说这是反佛者从政治上攻击、陷害佛教,倒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所以,这种谶语很容易发挥作用。唐武宗灭佛时,道士有意煽动武宗进一步灭佛,散布这种谶语,也不过是前人的故技重演,为什么就是针对唐宣宗呢!
第四,于先生说:“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所以,宣宗兴佛实在有还愿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首先,应当明确,前一个皇帝灭佛,后一个皇帝兴佛,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复佛法”《魏书》卷五《高宗纪》。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周书》卷七《宣帝纪》。由此可见,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多次灭佛都很快得到恢复,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于最 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代宗末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谓天下通制,不惟剑南一道。”后经众臣议论,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虽然“上颇善其言”,但因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灭佛的措施也难以实行。
杜牧(803—853)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认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樊川文集》第155页。故而才对佛教有所恢复。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谈不上是“大兴”。
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宣宗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恢复的程度是“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者。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也不符合事实。
大中五年(851)六月,进士孙樵上言:“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书门下奏:度僧必须慎重。“乡村佛舍,请罢兵日(停止对吐蕃用兵后)修。”十月,中书门下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切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宣宗都表示“从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六月—七月。大中十年(856)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于灵感、会善二寺设戒坛,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一意孤行地兴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复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例如,反佛者常说:“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而崇佛者则反驳道:“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突非通论。”《广弘明集》卷十五《内德篇》。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遐迩。”《广弘明集》卷十五《辩惑一》。显而易见,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正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所以,从南北朝到唐代,虽有三次灭佛,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
再者,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也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李文饶文集》卷十二《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扰乱社会秩序,被视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论》。的宣宗,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宣宗恢复佛教,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间,傅奕就指责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兴佛。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唐中宗时,韦嗣立针对中宗“崇饰寺观”而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意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同时,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如果说武德年间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赋,对国家不利的端倪,那么,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指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显然这是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的矛盾有所发展的反映。
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德宗时,彭偃参加了有关佛道问题的议论。在他看来:“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人害”,“去人害”的办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税。他的具体措施是:“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如果这样使僧道“就役输课”,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文宗也认为:“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蕃无生之法!”《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故而下敕整顿僧尼。文宗还说过:“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一五五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十八《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体现了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过程。
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参与者。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限制。例如,“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了聚敛财富,他以敬宗生日为由,于泗州(江苏盱眙)置僧坛,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发为僧。对此,李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此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
新罗人在唐的分布
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圆仁提到的新罗人很多,仅有具体姓名者就有如下47人。
译语(翻译):金正南、朴正长、刘慎言、道玄。
僧人:圣林和尚、谅贤、法清、常寂、玄测法师、季信惠、弘仁、庆元、惠溢、教惠、昙表、智真、范、顿、明信、惠觉、修惠、金政、真空、法行、忠信、善范、道真、师教、咏贤、信惠、融洛、师俊、小善、怀亮、智应。
官吏:通事、押衙张咏、新罗使张押衙、唐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
其他新罗人:王请、王长文、王宪、王宗、郑客、陈忠、金子白、钦良晖、金珍。
除了以上有姓名者以外,笼统提到的新罗人还很多。这些新罗人,在僧人、官吏、译语之外,还有水手、商人等。根据圆仁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出新罗人分布的大致情况。
圆仁到唐最早接触新罗人是在楚州(江苏淮安)。开成四年(839)二月,圆仁一行到达楚州,日本遣唐使为了回国,雇新罗人谙海路者60余人。一次能雇熟悉海路者60多人,可见新罗人在楚州为数不少。在从楚州前往密州(山东诸城)的途中,圆仁及其随从僧惟正、惟晓、水手行者丁雄满(万)在东海县(江苏连云港)境内海岸下船,准备暂住,待机前往长安。他们刚登岸不久,看见有一条船停泊海岸,船上有10余人。待他们互相问明情况时,圆仁等自称是新罗人,显然这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对方也说他们都是新罗人,有数十人之多。后来,他们又到宿城村的新罗人宅中休息,被人识破是日本人。圆仁冒充新罗人,肯定是当地新罗人很多而且和唐人相处很好,冒充可以减少麻烦。新罗人有自己的船只,还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们明确告知圆仁等:“从此南行,逾一重山,二十余里方到村里。今交一人送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40页。这说明新罗人有自己的财产而且居住此地也非一朝一夕了。村里有新罗人宅,说明新罗人和唐人是杂居一起的。
4月17日,到达登州(山东蓬莱)牟平县(山东牟平)。20日就碰到新罗人,从新罗人的口中知道新罗的王子成为国王了;又听说日本朝贡使驾五只新罗船离去的消息。同时又听说日本朝贡使的另外一批所乘的四只船不知去向。
26日,有30余新罗人骑马乘驴而来,告知圆仁等州押衙要来看望他们的消息。不久,押衙驾新罗船来,“下船登岸,多有娘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56页。既然妇女很多,更说明新罗人早已定居于此地,并非来往匆匆的过客。同时,圆仁又从这些新罗人口中知道,日本朝贡使的九条船都安全无恙。29日,圆仁等命新罗译语道玄与新罗人商量在此地居留的问题,结果顺利谈妥,新罗人愿提供方便。5月1日,圆仁又遣人去邵村找该村的头领王训,既买粮又谈留住此村的事,王训立即表示,他负责办理此事。王训与上面提到的新罗人态度一致,大概王训也是新罗人。
6月初,圆仁等又到文登县(山东文登)清宁乡赤山村的法花院(寺),该院有僧三十多人,都是新罗人。他们还保持着新罗人的风俗习惯。例如,他们非常重视八月十五日这个节日。据新罗僧谈,这一天是新罗与渤海作战取得胜利的节日,所以,新罗人“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个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入唐记》第67页。这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一致。《旧唐书》卷一九九《新罗传》在叙述新罗的风俗时说:“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说:“八月望日,大宴赉官吏,射。”《册府元龟》卷九五九《外臣部·土风一》说:“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这些内容,虽然和《入唐记》所载大体一致,但都没有《入唐记》所载内容丰富而且详细。同时,还缺少为什么重视八月十五日这一重要内容。不难看出:《入唐记》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比我国的有关史籍更为珍贵。这时朝鲜半岛还没有文字,汉文的有关记载自然对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十分有用,《入唐记》也不例外。从圆仁与新罗僧共食饼等情节来看,《入唐记》的内容是十分可信的。
赤山村一带不仅有新罗寺院,而且是新罗人聚居的地方。十月十六日,寺里讲《法花经》,听众男女道俗除了圆仁等四个日本人以外,全都是新罗人。人数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据圆仁“男女道俗”、“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等提法,可知听众有男女老少尊卑之别。既然有各种性别、年龄、等级的人参加,当然是相当多的人了。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一日,圆仁等四人到达青州(山东益都)龙兴寺。二十四日,典座僧将其引向新罗院安置。四月五日,他们又到长山县(山东邹平东)也同样是被醴泉寺的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长山县属于淄州,由此可见,青州、淄州一带新罗院不少,勿庸置疑,新罗人也到处可见。
会昌三年(843)正月二十七日,宦官召见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圆仁这时正在长安,据他所记,当时外国僧人共21人,即青龙寺南天竺僧5人,兴善寺北天竺僧1人。慈恩寺师子国僧1人,圣寺日本僧3人。接着又说“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入唐记》第159、184页。既然说“诸寺新罗僧”,当然是指不少寺都有新罗僧人。会昌五年(845)三月,武宗有敕: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者”。圆仁记载此事,提到北天竺僧难陀、南天竺僧宝月、日本僧圆仁、惟正等,对新罗僧则记为:“新罗国僧亦无祠部牒者多。”《入唐记》第159、184页。另外,有一个长安籍的僧人,为了逃避武宗灭佛的灾难,曾冒充新罗僧,暂住大荐福寺。由此可见,当时,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新罗僧人是最多的。
在唐朝政府中,还有新罗人充任重要官员。会昌三年(843)八月十三日,由于武宗灭佛,圆仁等为了回国,去求见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李元佐信敬佛法,是新罗人,住宅在永昌坊。到了会昌五年(845)三月,李元佐除了左神策军押衙的头衔以外,又加上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等官衔。左神策军押衙是禁军的下级军官,银青光禄大夫是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是虚衔,殿中监察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属官,上柱国是武散官。由此看来,李元佐虽然不是有实权的高级的官员,但也是个颇有声誉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圆仁才请求他帮忙办理回国事宜。
会昌五年三月,圆仁离开长安,东去回国途经郑州、汴州到楚州觅船。七月三日到楚州(江苏淮安),住新罗坊。楚州治所是山阳县(江苏淮安),新罗译语刘慎言想把圆仁等安置在县新罗坊,未得县司许可。7月9日,到涟水县(江苏涟水),住新罗坊。24日,到文登县(山东文登)去勾当(办理)新罗所。该县还有新罗人户。
综上所述,圆仁所到之处,看到过新罗人的地方有:楚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淄州、长安、泗州。其实,圆仁未到过的地方也多处有新罗人,例如,宪宗时新罗“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恶风,漂至楚州盐城县(江苏盐城)界”。当时的盐城临海,王子的船能漂至此处,其他新罗人的船当然也可漂到此处或来到此处。还有,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到浙东去求食,很可能有原在浙东的新罗人引进,否则为什么不到山东半岛去求食而舍近求远呢!据此看来,至少可以这样说,在现在的浙江、江苏、山东的沿海一带,都分布有不少新罗人口。另外,在京城长安也有少量新罗人。
新罗人在唐的职业
在唐的新罗人都从事什么职业呢?
首先,是从事佛教活动。佛教在南北朝时通过高丽传入新罗,到公元五二八年得到国家认可。后来,新罗就不断派遣学问僧到中国来求法取经。由于人数愈来愈多,在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故而唐政府决定:新罗“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但这并没有影响新罗僧继续来唐,所以在圆仁来唐时在各地碰到很多新罗僧人。
新罗僧在唐的情况,一种是像在长安那样,分散在唐朝的各寺里;一种是像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的法花院那样,集中在新罗人的寺院里。前一种情况,新罗僧必须遵守唐朝寺院的规矩,和唐朝僧人没有什么差别,都受左、右街功德使的直接管理。这些僧人的任务主要是向唐僧学习佛经,圆仁就是带着佛经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到达唐朝又到长安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同了。法花院是私人所建,建院者张宝高是不是新罗人,不得而知,但圆仁在该院居住时,管理此院的是新罗通事、押衙张咏及林大使、王训等。张咏与王训都是新罗人,院僧也是新罗人,林大使的身份虽不甚明确,但足以说明法花院是新罗人自己的寺院。
法花院的讲经习俗也与唐寺有所不同:“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讲经的仪式,也是唐和新罗兼而有之。例如:“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偈矣。”《入唐记》第72—73页。这更进一步说明法花院确是新罗人的寺院,该院保持着新罗人的习俗和讲经仪式,但也受到唐人风气的影响。以此类推,青州的新罗院,淄州长山县的新罗院,很可能大体类同。
新罗院的经济来源,是他们拥有庄田,法花院的庄田一年可得米五百石。该院的僧人对唐朝的情况十分熟悉,很可能他们和唐朝的一些著名寺院都常有交往。例如,当圆仁要前往五台山的时候,新罗僧谅贤就非常详细地告诉他前进的路程:“从赤山村到文登县,百三十里;过县到登州,五百里;从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莱州;从莱州行五百里,到青州;从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从淄州到齐州,一百八十里;过齐州到郓州,三百里;从郓州行,过黄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过魏府到镇州(恒州),五百来里;从镇州入山,行五日,约三百里,应到五台山。”《入唐记》第68页。以上所述,除了魏府(魏州即今河北大名)到镇州(河北正定)较为笼统以外,其他内容都甚具体。实际上圆仁后来没有按这条路线行进,而是到齐州禹城县(山东禹城)即北渡黄河到德州(山东陵县),然后经冀州(河北冀县)、赵州(河北赵县)、镇州(河北正定)境内到达五台山的。这说明法花院的新罗僧不只一个人到过五台山,而且走的不是一条路。
其次,是从事商业活动。新罗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来往于唐与新罗之间;其二,是在唐朝境内往返于各地。
唐与新罗的关系一直友好,新罗王死,即遣使向唐告哀;新王即位,要得到唐朝皇帝的承认。自武德四年(621)以后,新罗对唐朝贡不绝。朝贡必然得到赏赐,所以,朝贡实际上是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在官方贸易的影响下,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起来。到圆仁入唐的时候,在现在的江苏、山东半岛一带碰到很多新罗坊。新罗坊是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人聚居的地方,楚州、山阳县、涟水县等地的新罗坊,圆仁都曾在其中停留。坊中设有总管、译语,处理日常工作。圆仁到楚州、涟水等地的新罗坊,是去寻找回国的船只。商人常常来往于唐与新罗之间,必然对海上的情况相当熟悉,圆仁在楚州新罗坊得到常州(江苏常州)有两条日本船的消息,还了解到日本惠萼梨子的情况,都说明新罗坊消息灵通,交往广泛。只有频繁的商业活动才容易提供这些情况。
楚州新罗坊译语刘慎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圆仁在长安,到登州等地,都和他有书信往来。圆仁从长安回到楚州,首先找他,主要是为了请他解决回国的船只问题。后来,圆仁前往涟水,也经过他的介绍。这说明各地的新罗坊是相互联系,不是孤立的。这种相互联系靠商人最方便,当时不可能有专职的交通员。
登州是唐距新罗最近的地方,新罗人更多,除了新罗坊外,还有新罗所。新罗所是管理机构,它既负责包括商人在内的新罗人的来往,也管理在唐的新罗寺院、新罗人户,还和唐官方打交道。例如,张咏是文登县新罗所的官员,他管理法花院,又管理文登县界新罗人户。会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圆仁再次到文登县,在新罗所又碰到张咏。由张咏向登州报告,准许圆仁等暂住新罗所,候船回国。由此可知,新罗商人需要和唐官府办理交涉时,也应当是有新罗所代办的。
另外,在登州城南街东还有新罗馆、渤海馆。新罗馆是什么性质的单位,现在很难确知,但从它和渤海馆相提并论,同设一处看来,大概也是为唐和新罗政治与贸易发展的需要而设。王仲荦教授说:“由于聘问通使的频繁和互市的不断发展,唐中叶以后,还在青州(治益都,今山东益都县)设立渤海馆,专门用来接待渤海来唐的使团。”《隋唐五代史》上册第601页。青州、登州都在山东半岛北部,所处地位类同。登州的渤海馆与新罗馆又同在一处,不言而喻,新罗馆也是唐为接待新罗使团而设的专门机构,也是由于聘问通使的频繁和互市不断发展的产物。
新罗坊、新罗所、新罗馆,都和新罗商人在唐的活动密切相关。
据圆仁所记,楚州、海州、登州是唐和日本、新罗海路交往的据点。楚州虽不临海,但当时淮水从楚州向东经涟水入海,同时,楚州又位于运河的交通要道上,所以,该地也必然是个商业中心。圆仁从长安东去,首先到楚州,然后到海州、登州,都是为了找寻回国的船只。在他之前,有些从京兆来的新罗僧也曾到海州找船回国。未达目的,也必然向登州而去。圆仁最后是在登州境内乘新罗船回国的。这些地方来往船只很多,商业必然发达。新罗商人对这里的商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圆仁第一次到海州,就碰到十多个新罗人驾船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入唐记》第40、99页。圆仁最后回国时,在密州境内碰到新罗人陈忠的船,也是“载炭欲往楚州”《入唐记》第40、99页。从北向南运炭,又必然从南向北运送其他货物。不难看出,新罗商人的长途贩运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海内外互相交往的频繁以及贸易发展的需要,新罗人充任译语、水手者很多。有姓名可查的译语已如上述,不知姓名者,还有大量的水手,《入唐记》中有多处记载。这是新罗人在唐的相当大部分。至于在唐的留学生等,《入唐记》虽未提及,但决不会没有。在京任职的李元佐,很可是新罗留学生的考试及第者。
新罗人和唐人、日本人的关系
在唐代,唐朝与新罗、日本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这主要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对日本和新罗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文化首先传入朝鲜半岛,继又传入日本,所以,日本学者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文本第17、152页。视新罗为“中国文化的分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文本第17、152页。日本人最初先从朝鲜半岛学习中国文化,后来才直接到中国来的。所以,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文本第50页。遣隋使、遣唐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时,新罗、日本都还使用汉字。这说明唐和新罗、日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文化基础的。
既然在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新罗起了桥梁作用,新罗人接受中国文化较早,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深,和中国人的交往也多,无疑,新罗人可以在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的时候发挥媒介作用。圆仁目睹的新罗人正是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
圆仁到唐的船上,雇有新罗译语金正南。在船行至距长江口不远的地方,发现有黄色的水,众人皆以为是长江流水,但当有人登上桅子远望时,发现前面还是浅绿色的水,遂使许多人暂感失望。于是,金正南解释说:“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泊水(地名),疑逾掘港欤?”《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尽管金正南的解释还不够确切,但至少可以说他对扬州一带是有所了解的。
圆仁等到达扬州后,金正南接到停泊于海州的另一日本船上新罗译语朴正长的书信。非常明显,新罗译语在两条日本船之间发挥了互相联系的作用。
开成三年(838)七月,圆仁等到达扬州。十二月十八日,“新罗译语金正南为定诸使归国之船,向楚州发去”《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四日,又“依金正南请,为令修理所买船,令都匠、番将、船工、锻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由此可见,金正南、朴正长等新罗译语,不仅是翻译,而且引导日本使团入唐,又为日本使团回国做好了准备,充当了日本遣唐使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如果说日本人吸收唐朝先进文化时离不开新罗人,决非言过其实。
开成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圆仁等所乘日本遣唐使归国船到达东海县(江苏连云港)。本来,圆仁与金正南密谋,船到密州境内时,乘修理船的机会,圆仁、惟正、惟晓、丁雄满(万)等四人离开船,再从陆上向长安进发。但到了东海县以后,因风向不顺,不宜再向密州,故而决定从东海县东去日本。这样,圆仁等四人只好在此下船,留居岸上,金正南为圆仁等人的行程做周到的安排,正说明新罗人比日本人对唐人更为了解,新罗人在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媒介作用是历史进程的要求。
会昌年间,唐武宗大肆灭佛,圆仁也必须离开长安。为了办理回国事宜,圆仁结识了新罗人在唐为官的李元佐。从会昌三年八月到会昌五年三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圆仁与李元佐多次交往,关系甚好。所以,圆仁记道:“左神策军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李元佐,因求归国事投,相识来近二年,情分最亲。客中云资,有所阙者,尽能相济。”《入唐记》第185页、186页。在圆仁即将离开长安时,“李侍御(当是李元佐)与外甥阮十三郎同来相问”。并帮助办理行李。圆仁离开万年县(西安市东部)前往照应县(陕西临潼)时,李元佐相送到春明门(长安外郭城东面中门)外,又共同吃茶。同时,李元佐还送圆仁很多礼物,如:“少吴绫十疋、檀香木一、檀龛象两种、和香一瓷瓶、银五股、拔折罗一、毡帽两顶、银字《金刚经》一卷,软鞋一量、钱二贯文、数在别纸也。”《入唐记》第185页、186页。显而易见,圆仁能够离开长安,顺利东去,是和李元佐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在武宗灭佛的高潮中,僧人正在遭难之际,李元佐对圆仁的帮助是难能可贵的。
圆仁东去,先到楚州新罗坊,新罗译语刘慎言也全力帮忙。刘慎言首先到楚州治所山阳县办理交涉,要求准许圆仁等日本人民在此停留,候船回国。因有武宗灭佛的诏书,县司不肯答应。刘慎言又到州里交涉,也未达目的。刘慎言把圆仁安置在私宅休息数日,圆仁把不便携带的东西寄存刘宅,然后根据刘慎言的安排,前往登州。
到了登州文登县,找到原来相识的新罗人张咏。张咏喜出望外,非常热情。这时张咏是平卢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所以,他对圆仁说:“余管内苦无异事,请安心歇息,不用忧烦。未归国之间,每日斋粮,余情愿自供,但饱飧即睡。”《入唐记》第194页。张咏为其妥善解决了食宿问题,又为其代向登州请求停留候船得到许可。这就为圆仁回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圆仁等乘新罗人金珍的船从登州界东渡,途经新罗回国。
圆仁从随遣唐使到唐,到最后和遣唐使先后都乘新罗船回国,自始至终都得到新罗人的帮助。根据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唐代的中国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新罗人存在。这些新罗人,在中国、新罗、日本的历史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对日本人直接吸收中国文化起了媒介作用,促进作用。
上述有关内容,中国史籍的记载是凤毛麟角,《入唐记》的记载却颇为详细。在这方面,《入唐记》的记载对中国史籍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圆仁笔下的“茶”
圆仁笔下的“茶”
日本和尚圆仁(794—864年),于开成三年(838)随日本遣唐使入唐,到大中元年(847)返回日本,在唐求法巡礼,历时九年又七个月左右。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一书,基本上如实记载了他在唐的所见所闻。在该书中,他多次提到“茶”,据统计,共有30多处。因为他是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场合提到“茶”,所以他每次提到的“茶”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象。
以吃茶助休息
圆仁提到“茶”次数最多的,是把吃茶和休息联系起来,以吃茶助休息。圆仁从登州(今山东蓬莱)经青州(今山东益都)、贝州(今河北清河)、赵州(今河北赵县)、镇州(今河北正定),到达五台山,又从五台山经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今山西汾阳西北)、晋州(今山西临汾)、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同州(今陕西大荔),到达长安。这样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途中当然要多次休息。休息常常吃茶,以茶帮助休息,消除疲劳。
开成五年(840)三月十三日,圆仁与弟子惟正、惟晓、行者丁雄万四人,在从登州西行途中,到达蓬莱县境内,从名为战斋馆的地方出发,西行二十五里,“到乘夫馆吃茶”。次日,又从图丘馆出发,行十里,“到乔村王家吃茶”。
四月五日,到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北),又西行到“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
四月六日,又西行到醴泉寺果园吃茶。
四月二十二日,早上行过二十里路程后,到南接刘家吃斋后又吃茶。
五月二十日,圆仁一行在五台山,从花严寺向西行七里许,“到王子寺吃茶”。
五月二十一日,从供养院吃斋后,“到中台菩萨寺吃茶”。
五月二十二日,在五台山东台巡礼途中,到台东头供养院吃茶。
会昌五年(845)五月十五日,圆仁离开长安东去,友人送他到春明门(长安外郭城正东门)外吃茶。
从以上九次吃茶的情况看来,都是在行进途中休息时吃茶的。休息同时吃茶,无疑是吃茶有助于休息、消除疲劳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九次吃茶有四次是在村民家中,一次是在醴泉寺果园,这都是体力劳动者的所在地。劳动者常备有茶,随时可以用来招待来往行人。再者,今天山东半岛一带也非产茶区,村民家中普遍有茶,更说明茶在劳动者的生活中相当重要。会昌五年八月,圆仁又到登州,发现“山村县人飧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痛”。圆仁感到“涩吞不入,吃即胸痛”的“盐茶粟饭”,当地村民却养成了“爱吃”的习惯。由此可见,茶对当地劳动者来说,已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必需品了。
据今人研究,“茶叶中咖啡碱有刺激神经和增进筋肉收缩力、促进新陈代谢作用,活动筋肉的功效。因而在劳动疲乏以后适量饮茶既可振奋精神,又可消除疲劳。”日本学者也认为:“茶叶中的芳香物质同样具有醒脑提神,使人愉快之感觉。”王宏树、汪前:《饮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与生理功能》,《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当时人们虽然不懂这些科学道理,但必然有所亲身感受。不难看出,茶在劳动者中广泛流行的原因即在于此。圆仁一行在长途旅行中,常常在休息时吃茶,也主要是为了消除疲劳,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以茶待客
茶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招待客人。
开成四年(839)闰正月三日,圆仁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延光寺,“当寺庆僧正入寺,屈诸寺老宿于库头(食堂)空茶空饭。百种周足,兼设音声”。所谓“空茶空饭”,颇为费解,日本学者小野胜年的解释是“恭敬地捧上来的茶饭”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106页注释。既然“百种周足,兼设音声”,当然是相当隆重的场面。在这种场合以茶饭招待客人,说明敬茶有以礼相待的意义。
四月七日,圆仁一行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兴国寺,“寺主煎茶”招待他们。又行二十里,到名为心净寺的尼寺中,碰到海州押衙,押衙有“勾当蕃客”(办理外事)的任务,自然要招待他们吃茶。“吃茶之后,便向县家去”。
开成五年(840)三月三日,圆仁等在登州“入州见录事。又入判官衙,见判官了。从载门入参见使君,邀上厅里吃茶。次日,使君(州刺史)于开元寺召见圆仁等。圆仁被召见时,使君判官正在吃茶。圆仁到来后,就对其“赐茶”,并“问本国风情”。这种边吃茶、边谈话的气氛,甚为和谐、闲雅。
三月二十三日,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应萧判官请,“到宅吃粥。汤药茗茶周足”。因为判官信仰佛教,所以对僧人特别热情,以茶饭招待僧人,无疑是非常友好的表示。
四月二日,圆仁等赴青州节度副使张员外院辞别,“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吃茶,辞别员外,到寺里。”张员外虽然不像萧判官那样信奉佛教,但也以茶食招待,可见以茶饭待客是常见的现象。
七月十三日,圆仁离五台山到太原府,住在华严寺。陪同圆仁离五台山南行的一位名叫义圆的僧人引圆仁等来此居住。圆仁颇为感激义圆,故而他记道:“头陀(义圆)自从台山为同行,一路已来,勾当粥饭茶,无所阙少。”既然从五台山到太原沿途粥饭茶无所阙少,可见这里以茶饭待客已习以为常了。
圆仁离开长安东去,于会昌五年(845)七月九日到达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县长官令“勾当茶饭饮食,且令将见”。
根据以上情况,圆仁一行受到茶或茶饭招待,都是在寺院或官府。这些地方都把他们当作客人,故而以礼相待,表示尊重。据有关学者研究,以茶待客,意义深长。当代一位研究陆羽茶道的先生认为:《茶经》中“客来敬茶的典型场面,且以茶礼恭敬奉之,体现的是一种心平气和、和睦安宁的气氛。”实际上就是“人际的融通,意态的谦和”王厚林:《陆羽茶道浅析》,《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还有位先生说:“以茶敬客,以茶会友,表示敬意、亲切、和气、淡雅的人际关系等等。”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圆仁多次碰到的茶饭招待都体现了这种意义。
以茶送礼
把茶当作礼品送与别人,是茶的另一社会作用。
开成四年(839)三月三日,圆仁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听说天台山禅林寺僧敬文从扬州来,遂派弟子惟正前去慰问,“兼赠细茶等”。在这里,赠送细茶实际上起了见面礼的作用。
三月二十三日,在楚州的新罗译语刘慎言,以细茶十斤及松脯等物赠与圆仁。刘慎言虽是新罗人,但他懂得日语和汉语,对日本人来唐颇多帮助,圆仁前后多次与他交往。这里初次见面,赠送细茶,正是他要与圆仁交友的表示。
开成五年(840)四月一日,圆仁在青州得到官府允其继续西行的证件,同时,受赐布三端,茶六斤。第二天,圆仁致书表示感谢。当时,从登州到青州,连遭三四年蝗虫灾害,以致“官私饥穷”。面临困境,圆仁不得不向官府乞粮。在此情况下,圆仁得到官府的粮、茶、布等物的支持,是难能可贵的。
会昌五年(845)五月十五日,圆仁准备离开长安回国,到万年县(今西安市东部)办理离境手续。中散大夫杨敬之信仰佛教,故而派人前往慰问,“兼赐团茶一串”。另外,职方郎中杨鲁士又在圆仁上路后派其子“送潞绢二匹,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显然,这是以茶等物为礼品送别友人。
这些以茶为礼品赠送友人的事例,意义极其深长。在这种场合,“茶”的物质意义是次要的,因为它并非贵重物品,主要是它的精神意义。圆仁对敬文送茶,刘慎言对圆仁送礼,都是在对方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向初见面的客人表示友好。由此可见,这种以茶送礼,实际是一种结交朋友的手段。青州官府赐给圆仁茶六斤、布三端,数量也不算多,但在连年遭灾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圆仁到唐巡礼求法的支持。其精神上的鼓励作用决不亚于物质上的赠予。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会昌五年圆仁离开长安时有人对他赠茶。当时,正值武宗灭佛的高潮期间,圆仁离境东去实际上是被驱逐出境的。在此困境中竟有政府官员冒着风险对他赠茶,显然有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是非观念在内。勿庸置疑,在这种场合的赠茶,必然是对圆仁在精神上的安慰。
以茶敬佛
以茶敬佛,在唐代也相当普遍。茶被佛教界视为“圣物”。按照寺院的规矩,每日都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或茶具作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以茶结缘”。这都说明“佛教与饮茶有不解之缘”。法门寺地宫出土许多茶具,“其造型和纹饰图案也都带有佛教意识色彩,可见唐代饮茶生活与佛教意识密切结合”张高举:《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看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文博》1993年第4期。在圆仁笔下的“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
开成五年(840)五月五日,圆仁在五台山竹林寺内详细观看了该寺的敬佛过程,并亲自目睹了以茶敬佛的场面。他应约“赴请入道场,看礼念法寺。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宝幡、宝珠,尽世妙彩张施铺列,杂色毡毯敷洽地上,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圣贤。”非常隆重的场面,说明“茶”在敬佛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月十六日,又在五台山华严寺看到僧人“吃茶之后入涅道场,礼拜涅相:于双林树下右胁而卧”。圆仁在这里所记的“吃茶”,大概是入涅道场的必经过程。
开成六年(841)二月,从八日到十五日,长安的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县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所谓“无碍茶饭”,就是不论僧俗同样施与茶饭。在供养佛牙的同时广施茶饭,当然是鼓励供养佛牙的意思。
如前所述,圆仁在行进途中以吃茶助休息,有三次是在寺中;以茶待客的事例,也有三次是在寺中。再加上以茶敬佛的事例,都充分说明“茶”和佛教的关系甚为密切。开成五年六月六日,唐文宗遣使到五台山,按“常例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细帔五百领,绵五百屯,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两,茶一千斤,手巾一千条”。皇帝年赐茶一千斤,说明五台山年用茶的数量很大。五台山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这就不难理解法门寺地宫为什么会出现许多珍贵的唐代茶具了。从另一方面说,也容易理解产茶地区对皇室的贡茶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旧唐书·文宗纪下》载:“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文宗)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贡新茶,宜于立春后造。”文宗“务恭俭”,才改变了造茶的时间,以表示其爱民。可见皇室的大量用茶是对产茶地区的强力索取。
以茶怡情以茶抒情
以茶怡情,以茶抒情,是茶的另一种作用,圆仁笔下的“茶”,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十八日,扬州节度使李德裕于扬州开元寺接见圆仁一行。圆仁来到时,李德裕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吃茶”。李德裕等官员共八人,他们吃茶等待日本和尚的到来。圆仁等进来,他们都起立施礼,然后共同吃茶。同时,还问长问短,了解日本的情况,例如,问日本有无寒暑的交替;有无僧寺、尼寺,有多少;有无道士;京城面积多大等等。圆仁都一一作了回答。这种边吃茶、边聊天的场面,充分反映了在座人们悠闲的心情和安逸的兴致、融洽的气氛,必然使日本和尚看到唐政府官员的友好态度。
开成四年(839)六月八日,将入夜时,圆仁等到文登县(今山东文登)清宁乡赤山村的法华院(寺),碰到院僧30余人,“相看吃茶”。众僧经过一天的佛事活动,夜幕降临之际的相聚吃茶,无疑有闲适自得之意。
开成五年(840)八月一日,圆仁到达汾州(今山西汾阳),州押衙姓何,是陪同圆仁离开五台山的义圆头陀的门徒,故而对圆仁特别热情。次日早,圆仁到“何押衙宅茶语”。在何押衙家吃过午饭,就又向西进发了。主人热情异常,客人在临行前到主人家中“茶语”,无异是以茶话别,谨表谢意。这种场合的“茶”,自然是情谊的纽带。
会昌三年(843)正月,唐武宗灭佛已经开始。二十七日,长安管理寺院的左、右街功德使通知各寺外国僧人集会。二十八日,“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后,见军容。军容亲尉安存。当日各归本寺”。在大难将要临头之际,21个外国僧人齐集一处,吃茶后,面见军容。虽然当天又各归本寺,但其心情极其沉重是勿须置疑的。
会昌五年(845)六月九日,圆仁从长安到达郑州(今河南郑州),州长史辛文昱曾在长安与圆仁相识,故而在此处相见后颇感亲切。辛长史对圆仁除了赠送礼物外,又远送于十五里之外,“遂于土店里任吃茶,语话多时相别,云:‘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上努力,早达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上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显而易见,辛长史和圆仁的吃茶话别非同一般。看来,辛长史也信仰佛教,他对武宗灭佛甚为不满,所以,借吃茶话别之机,抒发感情,希望圆仁回国后弘传佛法,把佛教的复兴寄希望于日本。他还要求圆仁成佛之日不要忘记自己。这种对佛教充满感情的言行,正是一个唐政府官员对一个日本和尚难舍难分的内在原因。
上述各种场合的吃茶现象,无不体现着一个“情”字。有的是愉快而和悦的情绪,有的是诚恳真挚的感情,有的是面临灾难的沉重心情,还有依依不舍的友情。各种各样的“情”中,蕴藏着人情、国情、教情等深层次的含义。看来,各种各样的吃茶现象中,都含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在圆仁提到的“茶”中,还有一处颇为特殊,就是以茶易物。
开成五年(840)三月十七日,在莱州(今山东掖县)境内,到潘村的潘家吃午饭。主人极为冷淡,圆仁等人乞求菜、酱、酢、盐等,一无所得。圆仁无可奈何,遂出茶一斤,买得酱菜。以茶易物,茶起了货币的作用。如果说圆仁提到的“茶”中多处主要是精神意义的话,那么,这里就主要是物质意义了。
余论
从圆仁笔下的“茶”来看,茶在唐代后期已相当流行,不仅在上层社会,而且在广大农村中也相当普及。这样一来,唐朝后期征收茶税也就不可避免了。
建中三年(782)九月,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贞元九年(793)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建议:“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下》。都得到了德宗同意。太和九年(835)十月,文宗又实行榷茶法,由政府垄断茶的买卖,“人甚苦之”。十一月,榷茶使王涯被杀,“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王涯是因参与甘露之变失败被杀的,同时被杀的官员多人,围观者对别的被杀官员无动于衷,惟独怨恨王涯,主要是因为“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可见实行榷茶法直接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十二月废除榷茶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些事例,更进一步说明圆仁笔下的“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圆仁笔下的“茶”,不仅因其物质意义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同时,其精神意义还更为深远。除了吃茶能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以外,以茶待客、以茶送礼交友、以茶敬佛、以茶怡情、以茶抒情等等,无不体现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使当时的精神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当然,“茶”的社会意义并不止圆仁所记,有时候在政治事件中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宰相欲诛宦官失败,宦官张仲清欲杀翰林学士、工部尚书郑注。张仲清请郑注饮茶,诱骗使其掉以轻心,郑注正在饮茶之际被杀。这主要是“茶”有以礼待客的作用,故而使郑注麻痹了。在这里,用以茶待客的手段达到了诱杀政敌的目的。由于本文题目所限,圆仁所记以外的“茶”,就不再赘述了。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所以,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研究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而写的。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关论著涉及者不少,专论者不多。于辅仁先生的《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见《烟台师院学报》1991年3期。一文,是近年来专文论述这一问题的大作,内容充实,很有深度,但其结论还难令人信服。故而在于先生的启发下,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灭佛不是为了查杀宣宗
于辅仁先生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关于宣宗与武宗的矛盾,宣宗被迫隐身于佛门的事,主要见之于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和尉迟的《中朝故事》。这些资料,虽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已明确表示:“鄙妄无稽”而“不取”,但也不能断言今人不可据此再作结论。笔者认为,即使承认这个前提,于先生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于先生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武宗是否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不得而知;但武宗初信佛,后信道,倒是言之有据。赞宁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宋高僧传》中华书局版第130页。不过,这种武宗初信佛教、后受人蛊惑而改信道教的观点,明显有为武宗辩护的意思。赞宁是北宋初年人,他的《宋高僧传》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编撰的。既是奉敕而作,无疑必须迎合皇帝的需要。五代十国时,赞宁是吴越僧人,宋统一全国后,他受赐紫衣,可见他颇受北宋皇帝的赏识。“所以书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不叙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迹,不主张高蹈,这倒是实在有悖于慧皎当初名其书曰《高僧传》的初衷”《佛教与中国文化》第167—168页。如是,他把武宗崇道灭佛之举归罪于蛊惑者,以减轻佛门对武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武宗在会昌元年六月以前,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是信奉道教的。《旧唐书·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坛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既然是未做皇帝时即已崇道,又在开成五年(840)秋刚做皇帝时即召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当然就不是会昌元年(841)6月突然改变态度才由信佛改为崇道了。
另外,于先生对所用资料的理解也欠确切。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在武宗生日这天,确有道士与僧人相对议论,“二个道士赐紫”,但棒决僧人却是六月十五日的事。因为六月十一日南天竺僧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此事因越过主管部门右街功德使而直接上奏皇帝,故“犯越官罪”而于六月十五日“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看来,僧人与道士相对议论,两个道士赐紫,和尚“总不得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391—392页。可以视为排佛的信号;但棒决僧人是因为外国和尚违犯唐律而受惩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于先生认为武宗“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于先生认为:“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于先生所谈的灭佛事实,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都有记载。但把这些事实视为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显然不妥。
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到会昌二年(842)他32岁。武宗应该知道宣宗的年龄。如果这时搜捕宣宗,首先应从30多岁的僧人中去找。其次,于先生很重视 的《中朝故事》中又明确说,宣宗“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从长安到江表,又有一个地域的范围。按照常规,依年龄、活动的地域查找逃者,是最有力的根据。其他像入佛门的时间、在佛门中的地位等,都是弹性很大、容易弄虚作假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烧练,指合练金丹;咒术,即念咒语行术法;禁气,是修身练仙的法术;背军,指离开军队为僧的;身上杖痕鸟文,指受过官刑的人;杂工巧,指各种特殊的手工技艺。这些内容,既没有地域、年龄的限制,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宣宗即使隐身佛门,也不会加入这些非佛门主流的行列;他只有按照正统的僧人打扮自己,才容易隐藏下来。再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并论,宣宗不可能隐身于尼中。这说明武宗的灭佛令根本没有针对宣宗的意思。
会昌五年(845),武宗敕下:从四月一日起,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十六日起,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五月十一日起,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使包括外国僧人在内的全部僧尼还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不能达到查杀的目的。如果真的要查杀宣宗,完全可以运用其他手段。如使认识宣宗的宦官或官员直接查找,或迫使与宣宗密切相关的人员提供线索等,都是更为有效的措施,何必一定要大海捞针呢!因此,把这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很难令人信服。
第三,于先生说:“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藏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死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惧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武宗对僧尼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确是事实。但于先生所举事例,恰巧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
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刘从谏侄刘稹请求为兵马留后。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议,派成德节度使王远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等率军征讨。九月,又对在京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采取了行动。
进奏院是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在平康坊,万年县领。当时,昭义节度使的押牙孙在京。武宗派兵逮捕孙,孙走脱,只将其妻子儿女杀死。因有人报告:“路府留后押牙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于是,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元和二年后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员)清查城中僧,“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还对“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捉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捉拿昭义节度使押牙孙,因孙可能刚剃发为僧,所以,打击范围只限于新裹头僧,更不包括尼在内。这种有目的有范围的迫害僧人,当然和查杀宣宗无关。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内容,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道士奏云:孔子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氏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其中说的黑衣天子,便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唐宣宗)。”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
其实,这条谶语出之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权力之争。“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显然是说有以“黑衣”为标志的人要对李唐皇帝取而代之。如果宣宗代替武宗,只是李家内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这更进一步说明,武宗灭佛并非查杀宣宗。再者,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者并非始于唐武宗灭佛时。南北朝时,宇文泰就因为“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以黄代赤承运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宇文泰)挟魏西奔,衣物旗帜并变为黑,用期讹谶之言”《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不难看出,这是宇文泰对北魏改朝换代的手段。北齐皇帝也因“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高欢)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北齐书》卷十《高涣传》。齐文宣帝高洋崇佛,曾命“道士皆剃发为沙门”,致使“齐境皆无道士”《资治通鉴》卷一六六,绍泰元年八月。但他还相信这种谶语,牵强附会地认为黑莫过于漆,漆与七同音,故而将其七弟高涣杀死。因此,如果说这是反佛者从政治上攻击、陷害佛教,倒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所以,这种谶语很容易发挥作用。唐武宗灭佛时,道士有意煽动武宗进一步灭佛,散布这种谶语,也不过是前人的故技重演,为什么就是针对唐宣宗呢!
第四,于先生说:“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所以,宣宗兴佛实在有还愿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首先,应当明确,前一个皇帝灭佛,后一个皇帝兴佛,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复佛法”《魏书》卷五《高宗纪》。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周书》卷七《宣帝纪》。由此可见,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多次灭佛都很快得到恢复,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于最 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代宗末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谓天下通制,不惟剑南一道。”后经众臣议论,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虽然“上颇善其言”,但因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灭佛的措施也难以实行。
杜牧(803—853)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认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樊川文集》第155页。故而才对佛教有所恢复。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谈不上是“大兴”。
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宣宗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恢复的程度是“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者。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也不符合事实。
大中五年(851)六月,进士孙樵上言:“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书门下奏:度僧必须慎重。“乡村佛舍,请罢兵日(停止对吐蕃用兵后)修。”十月,中书门下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切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宣宗都表示“从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六月—七月。大中十年(856)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于灵感、会善二寺设戒坛,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一意孤行地兴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复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例如,反佛者常说:“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而崇佛者则反驳道:“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突非通论。”《广弘明集》卷十五《内德篇》。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遐迩。”《广弘明集》卷十五《辩惑一》。显而易见,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正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所以,从南北朝到唐代,虽有三次灭佛,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
再者,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也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李文饶文集》卷十二《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扰乱社会秩序,被视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论》。的宣宗,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宣宗恢复佛教,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间,傅奕就指责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兴佛。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唐中宗时,韦嗣立针对中宗“崇饰寺观”而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意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同时,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如果说武德年间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赋,对国家不利的端倪,那么,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指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显然这是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的矛盾有所发展的反映。
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德宗时,彭偃参加了有关佛道问题的议论。在他看来:“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人害”,“去人害”的办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税。他的具体措施是:“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如果这样使僧道“就役输课”,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文宗也认为:“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蕃无生之法!”《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故而下敕整顿僧尼。文宗还说过:“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一五五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十八《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体现了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过程。
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参与者。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限制。例如,“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了聚敛财富,他以敬宗生日为由,于泗州(江苏盱眙)置僧坛,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发为僧。对此,李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此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中国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 2拿起来就放不下的60...
- 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
- 4章泽
- 5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 6从日记到作文
- 7西安古镇
- 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 9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伦...
- 10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科普教育 【已完结】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