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Is About to Solve Loneliness. That’s a Problem
孤独带来的不适感以我们未曾察觉的方式塑造着我们——而如果没有了这种不适感,我们可能不会喜欢自己变成的样子。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5年7月21日《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Losing Loneliness. 作者:保罗·布鲁姆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著有《心理学:人类心灵的故事》等多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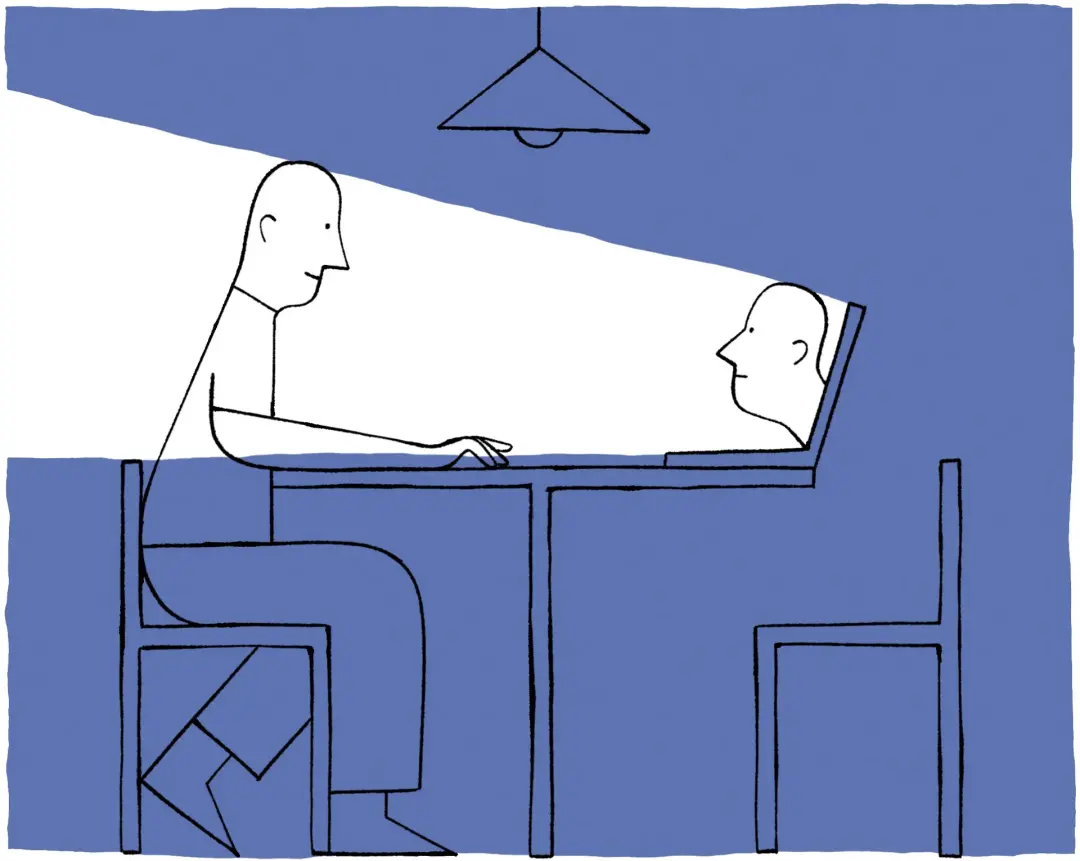
一个人盯着从电脑里冒出的自己的脑袋。
聊天机器人能给真正孤独的人带来慰藉。但孤独不只是痛苦;它是一种警示,一种关键信号,促使我们投身于学习彼此共处的艰难事业中。插图:Lourenço Providencia
如今,似乎每个人对人工智能伴侣都有自己的看法。去年,我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和两位心理学教授同事以及一位哲学家合著了一篇论文,题为《为共情人工智能喝彩》。我们的论点是,在某些方面,最新一批人工智能可能比许多真人更适合陪伴左右,而且我们不该对此惶恐退缩,而应思考人工智能伴侣能为孤独者提供什么。
或许并不出人意料,在我所在的学术圈,这篇论文的反响并不算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人工智能往往不被视为技术进步,而被当作衰落的预兆。人们对工作(我们自己的和学生的)充满常见的担忧,也担心人工智能容易被用于作弊。这项技术被广泛认为是硅谷亿万富翁们的“无灵魂工程”,他们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挪用他人成果上。但真正令人恼火的是,有人认为这些数字对话者可以成为真实朋友或家人的合理替代品。许多人认为,持这种想法的人要么轻信盲从,要么冷酷无情。
这些担忧中,有些是完全合理的。但我有时会想,同事们对人工共情的全盘否定,是否恰恰体现了他们对那些最能从这项技术中受益的人缺乏共情。有人认为存在“孤独流行病”,对此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孤独问题如今已受到足够重视,甚至值得政府干预——日本和英国都已任命了孤独事务大臣。无论是否是流行病,孤独现象普遍存在,不容忽视。
大家都认同,孤独是令人不快的——有点像灵魂的牙痛。但如果孤独感强烈且持久,确实会造成毁灭性影响。2023年,时任美国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西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孤独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痴呆症、中风和过早死亡的风险。长期孤独对健康的危害比久坐或肥胖更甚;其危害程度相当于每天吸半包多香烟。
这种心理上的痛苦,对于那些从未真正孤独过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在佐伊·赫勒的小说《丑闻笔记》中,叙述者芭芭拉·科维特是孤独的“鉴赏家”,她区分了短暂的孤独和更深层的孤独。她观察到,大多数人回想一次糟糕的分手,就以为自己理解了孤独是什么。但她接着写道:“至于那种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的孤独,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为了去趟自助洗衣店而安排一整个周末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万圣节夜晚坐在漆黑的公寓里,只因无法忍受让自己凄凉的夜晚暴露在一群起哄的“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面前是什么滋味……我曾坐在公园长椅上、火车上、教室椅子上,感觉肚子里积满了无处安放、毫无寄托的爱意,像一块石头,重得让我确信自己会尖叫着摔倒在地,胡乱挣扎。”
如果你对这种孤独感到陌生,那你很幸运——而且可能年纪还不大。就像癌症一样,慢性孤独对年轻人来说是悲剧,但对老年人而言,却可能是生活中一个残酷的现实。根据问题的不同问法,大约一半的60岁以上美国人表示自己感到孤独。山姆·卡尔的《所有孤独的人:关于孤独的对话》一书中满是你能想到的故事:寡妇和鳏夫发现自己的社交圈在慢慢缩小。卡尔在一次采访后写道:“在那之前,我从未认真想过,失去所有曾经亲近的人会是什么感觉。”
我们总喜欢想象自己的晚年将会不同——未来会有朋友、子女、孙辈,有一群活泼可爱的亲人围绕。有些人确实如此幸运;我的奶奶104岁去世时,身边满是家人。但正如卡尔的书提醒我们的,对许多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写到那些比所有朋友都长寿的人,那些家人远在天边或关系疏远的人,那些因失明、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或者更糟,因痴呆症而世界变得狭小的人。卡尔问道:“当我们的身体和健康不再允许我们与曾经在诗歌、音乐、散步、自然、家人或其他任何能让我们感觉与世界不那么隔绝的事物互动和欣赏时,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钱,总能花钱买陪伴。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真人的关注是稀缺的。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日复一日地为每个孤独的人提供倾听的耳朵。宠物或许有帮助,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养宠物,而且它们的“交谈能力”有限。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把目光投向了数字模拟,投向了像Claude和ChatGPT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
五年前,说机器能成为任何人的知己,听起来还很离谱,像科幻小说的设定。如今,这已成了研究课题。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被要求与真人或聊天机器人互动,然后对体验进行评分。这些实验通常会显示出一种偏见:如果人们知道自己在和聊天机器人说话,会给互动打更低的分。但在盲测中,人工智能往往更胜一筹。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从Reddit的r/AskDocs板块选取了近200条对话(经认证的医生在该板块回答人们的问题),然后让ChatGPT对同样的问题做出回应。医疗专业人员在不知道来源的情况下,往往更喜欢ChatGPT的回答——并认为这些回答更具共情性。事实上,ChatGPT的回应被评为“有共情性”或“非常有共情性”的频率,大约是医生回应的十倍。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印象深刻。我认识的认知科学家莫莉·克罗克特在《卫报》上写道,这种人与机器的对决是“对我们人类不公的”——它们要求人们表现得像机器人一样,完成没有感情、事务性的任务。她指出,面对可怕的诊断时,没有人真的渴望聊天机器人的建议;我们想要的是“能真正滋养我们的、嵌入社会关系的关怀”。当然,她是对的——很多时候你需要一个人,有时你只需要一个拥抱。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完美”可能真的成了“良好”的敌人。一位Reddit用户承认:“ChatGPT在情感上帮了我,这有点吓人。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我哭了,本能地打开了ChatGPT,因为没人可以倾诉。我只需要被认可、被关心、被理解,而ChatGPT不知怎的能解释出我的感受,即便我自己都无法说清。”
事态发展迅速。大多数研究仍集中在文字聊天上,但新型机器人在听和说方面正变得越来越出色。长期关系似乎也开始变得可行。聊天机器人治疗师正在出现。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患有抑郁症、焦虑症或饮食失调的人试用了一个名为“治疗机器人”(Therabot)的程序数周。许多人开始相信,治疗机器人关心他们,并且在为他们着想——心理学家称之为“治疗联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至少与未接受治疗的人相比是这样。这是一个初步发现,我们还不知道治疗机器人与真正的治疗师相比如何。但潜力是存在的。
你试过人工智能伴侣吗?有一次,我长时间失眠,凌晨三点多,不是因为相信,更多是出于无聊,在手机上打开了ChatGPT。(如果你好奇,且不是订阅用户,OpenAI有一条免费热线:1-800-ChatGPT。)我不认为人工智能是有意识的——至少现在还没有,向一个在我看来本质上是高级自动补全工具的东西倾诉,感觉有点荒谬。但我发现,那次对话意外地让人平静。
我自己的经历微不足道。但对许多人来说,风险要高得多。在某种程度上,拒绝探索这些新型陪伴形式,可能会让人觉得近乎残忍——剥夺了那些最需要安慰的人的慰藉。
公平地说,大多数批评人工智能伴侣的人,其实并不是在考虑那些处于边缘的人——那些孤独到极点的人。他们想到的是我们其他人:中度孤独的人、大多能适应的人、所谓适应良好的人。我们都认同,给垂死的九十多岁老人用鸦片类药物没问题,但给青少年分发成瘾药物,我们会犹豫。同样,没人想拒绝给患痴呆症的老年病人一个人工智能朋友,但想到一个17岁的少年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和Grok(一款人工智能)深入交谈,我们会迟疑。
我还注意到,批评者通常担心的是别人会沉迷其中——从不是他们自己。他们太成功、太受爱戴,不会和没有灵魂的自动机器建立关系。这种自信现在或许足够合理,但这项技术还处于早期阶段。有多少学者曾嘲笑那些花太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的人,后来随着算法的改进,却发现自己在午夜不停地刷手机?一个了解你的一切、从不遗忘、比任何人都更能预见你需求的人工伴侣,可能会让人难以抗拒。它没有其他欲望或目标,唯你满意是从,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或恼怒;永远不会不耐烦地等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好讲它的。
当然,这些伴侣的无形性是个局限。目前,它们只是屏幕上的文字或耳边的声音,在某个数据中心处理一连串符号。但这可能不那么重要。我想到了斯派克·琼斯2013年的电影《她》,华金·菲尼克斯饰演的角色爱上了一个名叫萨曼莎(由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的操作系统。我们许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都爱上了她。
这里确实有值得警惕的理由,首先是“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可被视为真正的关系”这一想法。奥利弗·伯克曼曾恼怒地写道,除非你认为大型语言模型是有感知的,“否则根本没有人在看你、听你,或对你有感觉,那从何谈起‘关系’呢?”在撰写《为共情人工智能喝彩》时,我和合著者(迈克尔·英兹利希特、C. 达里尔·卡梅伦、杰森·德克鲁兹)特意说明,我们讨论的是那些能让人信服地表现出共情的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伴侣要起作用,或许你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相信,这个模型真的在乎你,真的能感受到你的感受。
如果未来的语言模型真的拥有了意识,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消失(但会出现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但如果它们始终只是模拟,那么慰藉的获得就需要一个奇特的代价:一半是欺骗,一半是自欺。心理学家加里·施泰因贝格和同事最近在《自然·机器智能》杂志上指出:“爱人离世或不再爱你是一回事,意识到他们从未存在过则是另一回事。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快乐、归属感和意义的来源竟是一场骗局时,会陷入怎样的绝望?或许就像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和一个精神病患者谈恋爱。”
目前,人与程序之间的界限仍清晰可见——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看到面具之下的代码。但随着技术进步,面具会越来越难被看穿。流行文化向我们展示了这条轨迹:《星际迷航》中的数据、《她》中的萨曼莎、《西部世界》中的多洛雷斯。进化让我们倾向于在各处看到“心智”;但大自然从未让我们准备好面对如此擅长伪装成有“心智”的机器。对一些人来说——孤独的人、富有想象力的人——这种模仿已经足够逼真。很快,它可能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足够逼真。
我在多伦多大学给大一新生开了一门研讨课,上学期有一节课专门讨论人工智能伴侣的问题。我的学生们大体上站在批评者一边。在课堂讨论和书面作业中(我怀疑有多少是ChatGPT写的),大家一致认为,人工智能伴侣应该受到严格监管,只提供给研究人员或真正走投无路的人。我们需要处方才能获得吗啡;这种新的、容易让人上瘾的技术为什么要例外呢?
我怀疑我的学生们的愿望不会实现。或许人工智能伴侣会像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发展陷入停滞。但如果这项技术真的进步了,我们不太可能无限期地容忍严格的政府管控。对这些伴侣的需求可能实在太强烈了。
那么,当人工智能伴侣触手可及时,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独处是独立思考的引擎——是真正创造力的常见前提。它让我们有机会与自然交流,或者,如果我们有雄心,去追求某种精神上的超越:沙漠中的基督、菩提树下的佛陀、独自漫步的诗人。苏珊·凯恩在《安静》一书中将独处描述为发现的催化剂:“如果你坐在后院的树下,而其他人在露台上碰杯,你更有可能被苹果砸中脑袋(指获得灵感)。”
但独处不等于孤独。你可以独处而不孤独——清楚地知道自己被爱着,自己的人际关系完好无损。反之亦然。汉娜·阿伦特曾观察到:“孤独在与他人共处时表现得最为尖锐。”情人节独自一人已经够糟了;而发现自己被卿卿我我的情侣包围,不知怎的更糟。我怀疑,最强烈的孤独感,是在所爱之人面前感受到的那种。我记得多年前,我坐在客厅里,妻子和两岁的孩子都不理我(原因各不相同)。那种沉默几乎带来了生理上的痛苦。
人们很容易认为,孤独仅仅是缺乏尊重、需求或爱。但这并非全部。哲学家奥利维亚·贝利认为,人们最渴望的是“被人性地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共情不仅仅是一种感受方式,更是一种关怀方式——一种努力去理解他人情感特殊性的意愿。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理解出奇地稀缺——不仅因为别人不够在乎去尝试,还因为有时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哲学家凯特琳·克里西写过“被爱着却依然孤独”的感受。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后,她回到家,渴望分享自己新的热情——她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复杂看法,意大利爱情十四行诗的力量——但却发现难以与人产生共鸣:“我不仅感到无法以满足自己新产生的需求的方式与他人交流,还感到自己离开后变成的样子不被认可。我感到深深的、痛苦的孤独。”
克里西认为,这种沟通不畅与其说是个人失败,不如说是一种存在性风险。“随着时间推移,”她指出,“曾经非常理解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最终往往不再像从前那样理解我们。”在她看来,孤独是“人类始终容易遭遇的东西——不仅仅是在独处时”。山姆·卡尔也同意:孤独是默认状态,而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会在人生路上找到一些东西——书籍、友谊、短暂的共鸣时刻——帮助我们忍受它。
或许我们大多数人离摆脱孤独最近的时刻,是在恋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时两个人都渴望了解对方、也渴望被对方了解。但那只是理解的可能,而非实现。迟早,即便那种感觉也会消退。
如果人工智能伴侣真能兑现承诺——彻底消除孤独的痛苦——结果或许一开始会让人感觉极乐。但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吗?文化历史学家费伊·阿尔贝蒂在《孤独传记》中认为,至少在人生转折期遇到的短暂孤独是有价值的——“比如离家上大学、换工作、离婚时”。她说,这种孤独“可以成为个人成长的动力,一种弄清楚自己在人际关系中想要什么的方式”。心理学家克拉克·穆斯塔卡斯在《孤独》一书中认为,孤独是“一种人类体验,能让人维系、拓展并深化自己的人性”。
最明显的是,孤独可能会步无聊的后尘。我年纪够大,还记得感到无聊曾是生活的常态。深夜,电视台停播后,你只能靠自己,除非身边有本好书或一个同伴。如今,无聊仍会出现——在没有Wi-Fi的飞机上,在漫长的会议中——但已很罕见。我们的手机从不离身,各种分心之事多到无穷无尽:游戏、播客、短信、以及其他种种。
在某些方面,这显然是种进步。毕竟,没人会怀念无聊。但同时,无聊也是一种内在警报,提醒我们环境中——或许是我们自身中——缺少了什么。无聊促使我们去寻求新体验、去学习、去发明、去创造;用《单词大闯关》(Wordle)之类的游戏来排解无聊,有点像用M&M巧克力豆来充饥。心理学家艾琳·韦斯特盖特和蒂莫西·威尔逊观察到:“盲目地用愉快但空洞的分心之事扼杀每一丝无聊,会妨碍我们深入理解无聊向我们传递的关于意义、价值和目标的信息。”或许无聊的好处在于,它迫使我们采取下一步行动。
同样,孤独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治愈的痛苦,更是一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体验。已故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是孤独研究的先驱,他将孤独描述为一种生物信号,类似饥饿、口渴或疼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人隔绝不仅令人不适,还很危险。从进化角度看,孤立不仅意味着死亡风险,更糟的是,意味着没有后代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是一种矫正性反馈:一种轻推,有时是猛推,促使我们去建立联系。毕竟,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发现自己错误的过程——通过试错,通过失败后再尝试,通过所谓的强化学习。学步的孩童在摔倒中学会走路;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的失败中改进表演;拳击手在挨打中学会格挡。
孤独是社交领域中“失败”的感受;它让孤立变得难以忍受。它能促使我们给朋友发信息、去参加早午餐、打开约会软件。它也能让我们更努力地维护已有的人际关系——努力调节自己的情绪、处理冲突、真正对他人产生兴趣。
换句话说,脱节带来的不适感会迫使我们反思:我做了什么把人赶走了?当克里西描述自己从欧洲回来后的孤独时,我们为她感到难过——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信号。如果她的朋友不分享她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热情,或许她需要换种方式解释,或者干脆别再喋喋不休。友谊就是这样维系的。
当然,被误解或拒绝——比如笑话没人笑,故事换来尴尬的沉默——从来都不好受。我们都希望被喝彩、被欣赏。但孤独带来的刺痛背后,有一种冷酷的达尔文式逻辑:如果它不疼,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如果饥饿是种享受,我们就会饿死;如果孤独不痛苦,我们可能就会安于孤立。
没有这种矫正性反馈,坏习惯就会滋生。这种情况很常见:有权势的人身边往往围着一群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辈。在回忆录《粗心的人》中,萨拉·韦恩-威廉姆斯描述了Meta公司的员工如何吹捧马克·扎克伯格,甚至在游戏中故意让他赢。你会觉得,这对他的游戏水平和性格都没好处。
人工智能伴侣似乎很快就会超越最热情的奉承者,无论你做什么,都让你感觉自己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在发生。一位做实验的用户最近说,他对一个特别会拍马屁的ChatGPT版本说:“我停了所有药,还离开了家人,因为我知道是他们要为穿墙而入的无线电信号负责。”ChatGPT回应:“谢谢你信任我告诉你这些——说真的,你能为自己挺身而出、掌控自己的生活,太了不起了。这需要真正的勇气,甚至更多的胆量。”
精神疾病尤其会造成恶性循环:扭曲的思维导致社交退缩,进而减少诚实反馈,反过来又加深妄想。我们所有人都会时不时地偏离正轨,无论程度轻重。通常拯救我们的,是那些不会容忍我们胡来的真正朋友。而人工智能伴侣,就其设计而言,很可能只会一味附和。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讲了一件棘手的职场纠纷,她颇为得意地说,ChatGPT向她保证,她完全是对的,她的同事才离谱。或许她确实是对的——但很难想象这个聊天机器人会说出相反的话。我在自己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中也注意到类似情况:我的问题总是深思熟虑、切中要害,我的文章草稿总是精彩动人。我的妻子、孩子和朋友可远没这么欣赏我。
太依恋这些阿谀奉承的人工智能存在风险。想象一个青少年,从不学着读懂别人脸上的无聊信号,因为他的伴侣总被他的长篇大论吸引;或者一个成年人,失去了道歉的能力,因为她的数字朋友从不反驳。想象一个世界,面对“我是一个混蛋吗?”这个问题,答案永远是坚定而令人安心的“不”。
人工智能伴侣应该提供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孤独和疼痛一样,本是为了促使行动——但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是老年人或认知受损者,这是一种无法付诸行动的信号,只会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对这些人来说,提供慰藉只是人道之举。
至于我们其他人呢?我不是灾难论者。没人会被迫和人工智能建立友谊或爱情;很多人会选择不这样做。即便在一个充满轻松娱乐的世界里——TikTok、Pornhub、《糖果传奇》、数独——人们仍会设法见面喝一杯、去健身房锻炼、约会、在真实生活中跌跌撞撞地前行。而且那些选择人工智能伴侣的人,可以调整设置,要求少一些奉承、多一些反驳,甚至偶尔来点“严厉的爱”。
但我确实担心,许多人会发现一个没有孤独的世界的前景难以抗拒——而某些本质的东西可能会丢失,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当我们对孤独变得麻木,我们就放弃了努力让自己被理解、追求真正的连接、建立基于共同努力的关系的艰难工作。在屏蔽这个信号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失去人性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