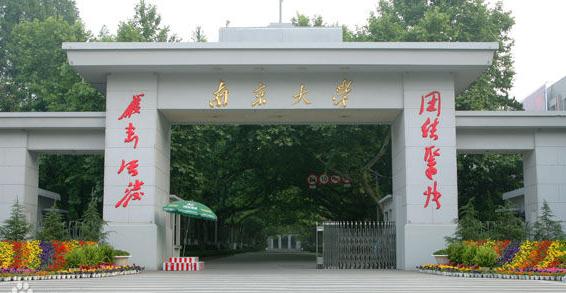
题记:英文字母V被作为胜利(victory)的标志。然而对于老五届科学家,V如其形,意味着必须先承受跌落谷底的痛与爬出谷底的难,然后才谈得上胜利。
从孩提时起,我就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是我感兴趣的。少年的我,最爱读《十万个为什么》,最崇敬杰出的科学家们。1963年9月我考入南京大学,中国生物化学的泰斗、国家一级教授郑集先生亲自给我们作专业教育。他说生化是边缘学科,人才奇缺,勉励我们毕业后考研究生,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
1965年,南京大学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崭露头角名扬全国。与我同年进校的化学系学生温元凯,大学二年级时就发表科学论文,专家认为其水平超过了一般讲师。学校把温元凯树为又红又专的标兵;以他为榜样,我就像干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科学知识。
文革折翼 理想破灭
谁都没有料到,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校大学生是1961年至1965年入学的,后来被统称为老五届。开始时大家破四旧、大串联,起劲得很,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可是没多久,我们就慢慢消沉了,许多事情都想不通,校长被打倒,德高望重的郑集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去扫厕所。就连温元凯,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黑标兵。
中国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停课,除了翻来覆去读毛的那几本书,专业书看一看就是罪过。一旦广播里传出毛的“最新最高指示”,那怕深更半夜都得去游行。毛泽东又派来“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占领大学,难道毛就永远正确吗?为什么他要无休无止地折腾?我们对这种无聊的日子腻烦透顶,唯一的希望就是早点离开大学这是非之地。
1968年12月1日,我们班级在离校前拍毕业照,古今中外的大学,这样的毕业照堪称奇葩。占据中间位置的,是无处不在的毛泽东像和他派来的“工宣队”;而辛勤教导我们的郑集教授等老师,竟无一席之地。更可悲的是,有些班级在文革中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派别,连毕业照都照不成;时隔近半个世纪,到现在仍是老死不相往来。
跌落谷底 忍受苦痛
我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小县的偏僻小村,跌入了社会最底层。在那里我断了科学研究的念想,除了劳动还是劳动。全国大学生多半都是这个命运,因为毛泽东指令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里的农民远没有摆脱贫穷,他们住泥墙草顶的房子,劳动一天所得,只值三、四个鸡蛋,连饭都吃不饱。这里连电灯和电话都没有,同伴装了个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才把我们同世界又联系起来。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和世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被灌输,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穷乡僻壤我才明白,其实三分之二就在这里。明白了真相,是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获。
1969年7月20日,美国之音报导美国航天员成功登上了月球。我长久长久地凝望月亮,思绪万千。我既为全人类共同的科学成就高兴,又为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黯然神伤。许多国家都在快速前进,而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五届大学生,却年复一年地被糟蹋生命。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又到一家小化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在这个偏僻小县整整10年,生活之苦自不待言,当时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一是事业无望:所学非所用。二是前途无望:如果说自己这辈子注定要被耗在这里,只得认命;难道我的孩子们也不得不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承受艰难 爬出谷底
1976年毛泽东死了,中国逐渐发生着变化。1977年10月22日,我习惯性地阅读报纸,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两、三分钟便可看完。然而那天的报纸,我足足看了一个小时,读的都是同一条消息:高等学校将恢复招收研究生。这条消息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可是我已经长时间没有正规学习了,还能把荒疏的学业补上去吗?还有实力竞争取胜吗?不过我很快坚定了决心:考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这不是我的夙愿吗?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我既无后台、又无门路,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再难也要考,而且要考好。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老五届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与我的校友温元凯有一定关系。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塑料厂,1973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1977年8月,他有幸参加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是最年轻的与会者。温元凯大胆发言,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十六字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听了后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这是温元凯生平最闪光的时刻,他不但影响了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影响了老五届大学生的命运。
1978年5月5日,全国有63500名考生参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四个月后尘埃落定,10708人考取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是老五届大学生。我有幸成为这万名研究生之一,当我收到盖有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内心激动得如同迷路的孩子终于回到妈妈的怀抱。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考取研究生,无疑是老五届人生道路的紧要处。可叹的是,从文革停课到考取研究生,老五届竟然耗费了整整12年才跨过这一步。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登上长途汽车去中科院报到。当太阳跃出地平线洒下第一抹曙光,我再次凝神注视这片挥洒过青春岁月的土地。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生命中长长的无望的一页翻过去了,我终于能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梦了。
我们研究所招收了15名研究生,个个都是拔尖出来的。我们的日历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们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言传身教的科研之道,极大地帮助我们成长。1981年8月我们毕业时,老一辈科学家们同我们合影,对我们寄予了极大期望。

(哥伦比亚大学)
再次展翅 终归平淡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隐形的翅膀》歌词)。我永远忘不了1990年9月15日,我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那熟悉的城市和乡村急速远去,机翼下的海水由黄变绿,再由绿变蓝。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凝视着最后一抹海岸线在天际消失,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在美国,我的科学研究走上了轨道。我与美国学者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在本门学科领域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我看到它在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被一再引用,当我听到它又被译成某一国文字出版,当我得知它被写进教科书向学生们传授,我就为自己能在科学殿堂上添砖加瓦而高兴。让我感叹的是,为什么我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能取得这些成果?难道果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实科学研究根本就不必由政党控制;灌输式的政治学习和几年一次的政治运动,只能是科学发展的桎梏。
与我同届毕业的研究生共14人,有12人先后来到美国。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老一辈科学家,何曾想到学生们几乎全部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的老五届科学家,往往发现自己的导师或老板是自己的同龄人,因为美国同龄科学家,已经积累十多年研究经验,开始崭露头角了。许多老五届科学家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现实:自己的知识已经陈旧,又过了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段,力不从心,难以与美国科学家竞争了。为了生活,不少老五届科学家不得不放弃研究,改做其他行业。
就连老五届中的佼佼者、曾经是中国最年轻教授的温元凯,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1992年,温元凯到加州理工大学留学。遗憾的是,他毕竟在文革中蹉跎了青春岁月,此后又在社会活动中投入大量精力,1989年更因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坐了一年多牢,以至于在专业领域再难有所建树。1994年后他不得不转向到经济领域,不再称自己为化学家了,令人唏嘘不已。如果没有文革的折腾,温元凯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优秀化学家的。
留在国内的老五届科学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者寥若晨星。以生物学部为例,现有的132位院士中,老五届只有区区五位。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需要投入毕生精力,而老五届的生活道路太过坎坷,遭遇过太多磨难,荒废了太多岁月。钱学森生前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老五届科学家的经历足以回答他的问题:原本大有希望的老五届,经受了文革浩劫、蹉跎了青春岁月,若是遭受过这么多磨难还能产生出科学大师,岂非咄咄怪事?
从文革开始到恢复招考研究生,时间跨度之长,竟与抗日战争加国共内战相当。中国损失了整整一代有用之材,老五届科学家则损失了整整12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2年,何况是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尽管老五届科学家喊出“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但12年的损失毕竟是无可追回的。就整体而言,本来大有可为的老五届科学家,就这样被耽误糟蹋,再也飞不高了。原本有望成为一代精英的老五届科学家,如今已届古稀之年,就这样归于平淡、面临凋零。
(图片取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