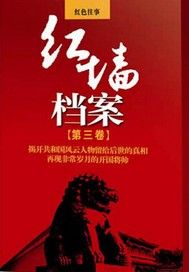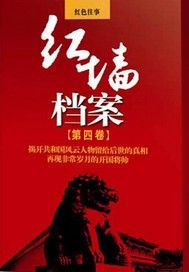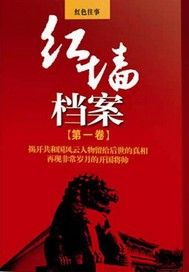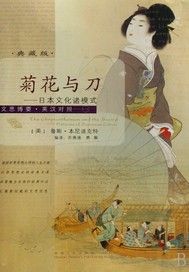第二十五章 开元寺
蒋纪新
开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虽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毁圮不存,却至今常被人们提及,因为它位于东大街钟楼东南角繁华闹市,当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这一带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这座寺庙而引以为豪。这一点,从前些年开元商城落成开业时兴高采烈的宣传中还能看得出来,这个西北最大的综合商业中心因建在开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贾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书中有开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说明。
为什么说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里,人们每当提及开元寺,总要说它自唐代便建在此处,因此,开元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人们一向以为唐代长安城的开元寺建在此处,反映出许多人以为唐长安城这一区域也如同今日车水马龙的景象。
我想从考证昔日开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许有助于纠正人们对唐长安城这一区域的错误印象。
(一)
开元寺并非西安独有,唐代时天下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开元寺。开元,是唐玄宗时的年号。开元寺以玄宗这一年号为名,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具有某种关系自然显而易见。
问题在于:开元寺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
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一书记载:“开元寺在咸宁县治西,唐开元中建,故名。后殿有玄宗真容。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兴胜先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座。”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纂的《咸宁县志》中,也有措辞基本相同的记载。
虽然《关中胜迹图志》与《咸宁县志》两书均未说明上述说法的来源,好在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开元寺兴致碑》提供了答案。在这块碑石上,刻有“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等文字,与上述两书说法恰相吻合。据碑文说:金贞佑四年(1216年)僧澄润将此文书于寺壁,为防岁久泯灭,乃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于碑,以告后人开元寺之由来。这就是碑文之说的最早源头了。
这则记载可谓要言不繁,虽只有短短几十个字,却已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等各种记述要素,不仅把西安开元寺的来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带也解释了全国各地之所以有一批开元寺的原因,听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流传至今。
但是,能够自圆其说并不等于确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并不等于史实,只有拿各种唐代史料与之认真比较、分析与鉴别,才能判断其真伪是非。
碑文之说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那么,它会不会是被史籍遗漏了的史实呢?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起码前提,应当是其涉及的历史背景与已知史实相符。然而,稍加比较便可发现,碑文之说与历史事实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之说,与唐玄宗一贯的政治态度背景史实不符。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所持的宗教态度实际上是其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便确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国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为皇族祖宗,历太宗、高宗而不改。后来,武则天出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势力一度恶性蔓延,并为这位女皇帝改朝换代的图谋摇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后决心拨乱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态度针锋相对而且鲜明激烈。据多种史籍记载,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开元二年(741年)起,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载确系事实,便意味玄宗后来的政治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各种史籍绝不会疏漏不载,然而在为数众多的唐代史籍中,却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记载。
其次,“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的说法,也与唐玄宗终生虔诚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实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说,从开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后有所改变呢?没有。从历史记载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仅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诚乃至进入痴迷狂热的境界。
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九年(740年),“上梦玄元皇帝(即老子)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之周至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由此可见,玄宗并未如碑文所说自前一年起改而“归佛”。
天宝三年(744年),“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天上,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于嵩山炼药成,亦置案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这时玄宗对道教的痴迷日益疯狂,说的话已与梦呓相差无几了。
到了天宝九年(750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你看,玄宗的道教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何曾有过半点“归佛之意”呢!
《大开元寺兴致碑》刻立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距唐玄宗开元年间已近600年,即使按碑文所说,它的说法来自金贞佑四年(1216年)澄润和尚书写在开元寺墙壁上的文字,也与唐玄宗开元年间相隔了500年。僧人们编造一个五六百年前的故事虽然动了一番脑子,乍一听似乎滴水不漏,却毕竟缺少历史知识,经不住与史籍比照,一比,就露了馅。
(二)
有人或许会提出一个疑问:既然你说唐玄宗“崇道抑佛”,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为什么在这位坚决“抑佛”的皇帝手里,却凭空冒出了一批开元寺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没有“返佛”之意,此事又如何解释?
这里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代自建国便以“崇道抑佛”为基本国策,即在允许道、佛两教同时存在的前提下,规定尊崇序次以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武则天执政时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崇佛抑道”,把尊崇序次改成了佛教第一,道教第二;到唐玄宗时又改为“崇道抑佛”,政策重新转向道教倾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抑佛”并非“灭佛”,唐玄宗所做的,只是对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加以抑制而已。所谓“沙汰天下僧尼”,无非是把武则天时期插足政治的僧尼作一番清查处理;而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意思也很明白:武则天时期建的佛寺太多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新建佛寺,当然,这并不意味拆除已建成的佛寺。
开元寺的出现,便是唐玄宗按照其宗教政策,处理武则天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多种史籍的一致记载为我们解析了这一疑团,同时提供了开元寺来历的正确答案。
事情须从武则天的天授元年(690年)说起。这年四月,东魏国寺僧人薛怀义等人忽发奇想,为了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胡侃乱编出一部《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的佛门真经。按照这部经书的说法,武则天乃西天乐土的弥勒佛转世,理应取代唐朝统治天下普渡众生。《大云经》呈上内廷后,果然大得武氏欢心,薛怀义因此平步青云,被拜为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武则天为此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颁旨:“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
可以想见,到唐玄宗掌政后,这部《大云经》就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书籍了。为了肃清其流毒影响,全国各地的“大云寺”自然也得统统改名。于是,据《唐会要》记载:“天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开元寺。”所以,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开元寺是唐玄宗肃清武则天政治影响的结果,全国各地的开元寺没有一座出于新建,皆由原先的大云寺改名而来。
那么,唐代长安的开元寺(即先前的大云寺)是否就是位于今钟楼附近的这一座呢?据北宋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卷十》怀远坊条目载:“东南隅大云经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长安志》原注)”。经考古实测证实,唐代长安的怀远坊,位于今西安市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糜家桥一带。
唐长安城里不可能有两座开元寺,既然《长安志》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唐长安城的开元寺位于糜家桥,便可证明今钟楼附近的寺址在唐代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更可证明《大开元寺兴致碑》出于后来僧人的委托了。
(三)
开元寺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坐标点,把它的位置定错了,一系列的错误就会接踵而来。
寺院是公众活动场所,只能分布在城市中市民居住的区域。若以为唐代开元寺位于今钟楼附近,自然会以为当年唐长安城这一带的大街小巷与今日西安约略相仿,例如,《老西安》中就出现了这种逻辑推演——
“……再琢磨这些名称如尚德路、教场门、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后宰门、马场子、双仁府、北院门、含光路、朱雀门、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风味,可以推断,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
其实,今钟楼附近虽是唐代长安城的城市中心,却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既不可能出现寺院,也不可能出现什么竹笆市、炭市街之类街巷。
既是城市中心,怎会无人居住呢?此话须从唐长安城“城中套城”的基本结构说起。唐都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共三个城组成。外郭城呈东西略宽、南北稍短的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今东至动物园、西至大土门、南至陕西师范大学、北至自强路之间,是供居民居住的活动的区域,并拱托、护卫着在其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宫城,位于外郭城内北部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南至今莲湖公园、北至北关自强西路北、东至革命公园西、西至玉祥门之间,是专供皇帝、太子居住的区域;皇城,位于宫城以南的外郭城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南至今南城墙、北至莲湖公园、西至西城墙、东至炭市街之间,是专供中央政府官员办公的区域。外郭城、皇城与宫城均有城墙环绕,形成各自的封闭系统。这一城市基本结构,不仅在《三辅黄图》《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古籍上有详细记述并附绘地图,而且经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测证实。
皇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今所说的“政府大院”。与今政府大院的不同之处,是那时的西安气派更大。这个“政府大院”之大达5.2平方公里,占今城墙内面积的60%(现存的西安城墙,是明代时在唐代皇城城墙基础上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形成的),所以,称之为“城”毫无夸张。唐末昭宗迁都洛阳,原长安城的宫城、外郭城化为废墟,留守节度使韩建便干脆以这座皇城作为长安城了。历经五代、宋、金、元,在长达500年的岁月里,长安城就是这座“政府大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出现“昔日王榭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情景,已是唐王朝覆灭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的皇城,是唐王朝戒备森严的统治中枢,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出入其间。按唐代制度,“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皇城内只有百官衙署及皇家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绝不允许居民住宅混杂其间;皇城内甚至不允许设置官员住宅区,所有官员一律须在外郭城的各坊居住,即使皇亲国戚也不例外。所以,官员们下班之后,除了城头的巡逻士兵外,皇城内是空无人迹的。
知道了唐都长安的基本结构,即使不作前述考证,我们也可以断定,唐代长安的皇城范围内根本不可能存在开元寺或任何其他寺院。道理明摆在那儿:警卫森严的中央政府机关大院里怎能允许建一座寺院?把寺院建在无人居住的政府大院有什么用处?能接待哪一路香客?开元寺迁建于今钟楼附近,至早也是五代十国之后的事了。
不过,开元商城的老总倒也不必懊丧。唐代时这里虽不存在开元寺,实际上比起开元寺来却风光显赫多了。今开元商城所在位置,是唐代皇城内统管全国工商事务的最高机关少府监署所在地。少府监下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掌百工技巧之事”,不仅统管工商事务,而且负责货币制造与对外贸易,还统管“天子器御、后妃服饰、郊庙圭玉与百官仪服”,正经是个中央机关大衙门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僖宗时,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庙因遭火灾焚毁,少府监大厅一度还曾充作太庙使用。今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现代化商场大厅,千年之前却是庄严肃穆香烟缭绕的皇帝宗庙殿堂,这种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恐怕是人们殊难料及的吧!
开元寺在明、清两代也都有过整修,西安碑林藏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吴泰撰文的《开元寺八景图记》说:
梵阁朝晖,城晚照。
酒楼横笛,僧院鸣钟。
春雨莺声,古垣鹊噪。
槐荫煮茗,雪馆挑灯。
可见在清代开元寺的规模仍很大,也很繁华。辛亥革命陕西同盟会会址曾设在这里。
开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虽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毁圮不存,却至今常被人们提及,因为它位于东大街钟楼东南角繁华闹市,当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这一带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这座寺庙而引以为豪。这一点,从前些年开元商城落成开业时兴高采烈的宣传中还能看得出来,这个西北最大的综合商业中心因建在开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贾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书中有开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说明。
为什么说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里,人们每当提及开元寺,总要说它自唐代便建在此处,因此,开元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人们一向以为唐代长安城的开元寺建在此处,反映出许多人以为唐长安城这一区域也如同今日车水马龙的景象。
我想从考证昔日开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许有助于纠正人们对唐长安城这一区域的错误印象。
(一)
开元寺并非西安独有,唐代时天下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开元寺。开元,是唐玄宗时的年号。开元寺以玄宗这一年号为名,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具有某种关系自然显而易见。
问题在于:开元寺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
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一书记载:“开元寺在咸宁县治西,唐开元中建,故名。后殿有玄宗真容。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兴胜先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座。”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纂的《咸宁县志》中,也有措辞基本相同的记载。
虽然《关中胜迹图志》与《咸宁县志》两书均未说明上述说法的来源,好在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开元寺兴致碑》提供了答案。在这块碑石上,刻有“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等文字,与上述两书说法恰相吻合。据碑文说:金贞佑四年(1216年)僧澄润将此文书于寺壁,为防岁久泯灭,乃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于碑,以告后人开元寺之由来。这就是碑文之说的最早源头了。
这则记载可谓要言不繁,虽只有短短几十个字,却已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等各种记述要素,不仅把西安开元寺的来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带也解释了全国各地之所以有一批开元寺的原因,听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流传至今。
但是,能够自圆其说并不等于确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并不等于史实,只有拿各种唐代史料与之认真比较、分析与鉴别,才能判断其真伪是非。
碑文之说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那么,它会不会是被史籍遗漏了的史实呢?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起码前提,应当是其涉及的历史背景与已知史实相符。然而,稍加比较便可发现,碑文之说与历史事实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之说,与唐玄宗一贯的政治态度背景史实不符。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所持的宗教态度实际上是其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便确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国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为皇族祖宗,历太宗、高宗而不改。后来,武则天出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势力一度恶性蔓延,并为这位女皇帝改朝换代的图谋摇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后决心拨乱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态度针锋相对而且鲜明激烈。据多种史籍记载,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开元二年(741年)起,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载确系事实,便意味玄宗后来的政治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各种史籍绝不会疏漏不载,然而在为数众多的唐代史籍中,却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记载。
其次,“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的说法,也与唐玄宗终生虔诚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实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说,从开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后有所改变呢?没有。从历史记载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仅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诚乃至进入痴迷狂热的境界。
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九年(740年),“上梦玄元皇帝(即老子)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之周至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由此可见,玄宗并未如碑文所说自前一年起改而“归佛”。
天宝三年(744年),“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天上,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于嵩山炼药成,亦置案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这时玄宗对道教的痴迷日益疯狂,说的话已与梦呓相差无几了。
到了天宝九年(750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你看,玄宗的道教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何曾有过半点“归佛之意”呢!
《大开元寺兴致碑》刻立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距唐玄宗开元年间已近600年,即使按碑文所说,它的说法来自金贞佑四年(1216年)澄润和尚书写在开元寺墙壁上的文字,也与唐玄宗开元年间相隔了500年。僧人们编造一个五六百年前的故事虽然动了一番脑子,乍一听似乎滴水不漏,却毕竟缺少历史知识,经不住与史籍比照,一比,就露了馅。
(二)
有人或许会提出一个疑问:既然你说唐玄宗“崇道抑佛”,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为什么在这位坚决“抑佛”的皇帝手里,却凭空冒出了一批开元寺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没有“返佛”之意,此事又如何解释?
这里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代自建国便以“崇道抑佛”为基本国策,即在允许道、佛两教同时存在的前提下,规定尊崇序次以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武则天执政时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崇佛抑道”,把尊崇序次改成了佛教第一,道教第二;到唐玄宗时又改为“崇道抑佛”,政策重新转向道教倾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抑佛”并非“灭佛”,唐玄宗所做的,只是对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加以抑制而已。所谓“沙汰天下僧尼”,无非是把武则天时期插足政治的僧尼作一番清查处理;而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意思也很明白:武则天时期建的佛寺太多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新建佛寺,当然,这并不意味拆除已建成的佛寺。
开元寺的出现,便是唐玄宗按照其宗教政策,处理武则天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多种史籍的一致记载为我们解析了这一疑团,同时提供了开元寺来历的正确答案。
事情须从武则天的天授元年(690年)说起。这年四月,东魏国寺僧人薛怀义等人忽发奇想,为了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胡侃乱编出一部《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的佛门真经。按照这部经书的说法,武则天乃西天乐土的弥勒佛转世,理应取代唐朝统治天下普渡众生。《大云经》呈上内廷后,果然大得武氏欢心,薛怀义因此平步青云,被拜为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武则天为此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颁旨:“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
可以想见,到唐玄宗掌政后,这部《大云经》就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书籍了。为了肃清其流毒影响,全国各地的“大云寺”自然也得统统改名。于是,据《唐会要》记载:“天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开元寺。”所以,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开元寺是唐玄宗肃清武则天政治影响的结果,全国各地的开元寺没有一座出于新建,皆由原先的大云寺改名而来。
那么,唐代长安的开元寺(即先前的大云寺)是否就是位于今钟楼附近的这一座呢?据北宋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卷十》怀远坊条目载:“东南隅大云经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长安志》原注)”。经考古实测证实,唐代长安的怀远坊,位于今西安市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糜家桥一带。
唐长安城里不可能有两座开元寺,既然《长安志》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唐长安城的开元寺位于糜家桥,便可证明今钟楼附近的寺址在唐代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更可证明《大开元寺兴致碑》出于后来僧人的委托了。
(三)
开元寺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坐标点,把它的位置定错了,一系列的错误就会接踵而来。
寺院是公众活动场所,只能分布在城市中市民居住的区域。若以为唐代开元寺位于今钟楼附近,自然会以为当年唐长安城这一带的大街小巷与今日西安约略相仿,例如,《老西安》中就出现了这种逻辑推演——
“……再琢磨这些名称如尚德路、教场门、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后宰门、马场子、双仁府、北院门、含光路、朱雀门、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风味,可以推断,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
其实,今钟楼附近虽是唐代长安城的城市中心,却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既不可能出现寺院,也不可能出现什么竹笆市、炭市街之类街巷。
既是城市中心,怎会无人居住呢?此话须从唐长安城“城中套城”的基本结构说起。唐都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共三个城组成。外郭城呈东西略宽、南北稍短的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今东至动物园、西至大土门、南至陕西师范大学、北至自强路之间,是供居民居住的活动的区域,并拱托、护卫着在其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宫城,位于外郭城内北部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南至今莲湖公园、北至北关自强西路北、东至革命公园西、西至玉祥门之间,是专供皇帝、太子居住的区域;皇城,位于宫城以南的外郭城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南至今南城墙、北至莲湖公园、西至西城墙、东至炭市街之间,是专供中央政府官员办公的区域。外郭城、皇城与宫城均有城墙环绕,形成各自的封闭系统。这一城市基本结构,不仅在《三辅黄图》《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古籍上有详细记述并附绘地图,而且经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测证实。
皇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今所说的“政府大院”。与今政府大院的不同之处,是那时的西安气派更大。这个“政府大院”之大达5.2平方公里,占今城墙内面积的60%(现存的西安城墙,是明代时在唐代皇城城墙基础上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形成的),所以,称之为“城”毫无夸张。唐末昭宗迁都洛阳,原长安城的宫城、外郭城化为废墟,留守节度使韩建便干脆以这座皇城作为长安城了。历经五代、宋、金、元,在长达500年的岁月里,长安城就是这座“政府大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出现“昔日王榭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情景,已是唐王朝覆灭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的皇城,是唐王朝戒备森严的统治中枢,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出入其间。按唐代制度,“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皇城内只有百官衙署及皇家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绝不允许居民住宅混杂其间;皇城内甚至不允许设置官员住宅区,所有官员一律须在外郭城的各坊居住,即使皇亲国戚也不例外。所以,官员们下班之后,除了城头的巡逻士兵外,皇城内是空无人迹的。
知道了唐都长安的基本结构,即使不作前述考证,我们也可以断定,唐代长安的皇城范围内根本不可能存在开元寺或任何其他寺院。道理明摆在那儿:警卫森严的中央政府机关大院里怎能允许建一座寺院?把寺院建在无人居住的政府大院有什么用处?能接待哪一路香客?开元寺迁建于今钟楼附近,至早也是五代十国之后的事了。
不过,开元商城的老总倒也不必懊丧。唐代时这里虽不存在开元寺,实际上比起开元寺来却风光显赫多了。今开元商城所在位置,是唐代皇城内统管全国工商事务的最高机关少府监署所在地。少府监下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掌百工技巧之事”,不仅统管工商事务,而且负责货币制造与对外贸易,还统管“天子器御、后妃服饰、郊庙圭玉与百官仪服”,正经是个中央机关大衙门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僖宗时,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庙因遭火灾焚毁,少府监大厅一度还曾充作太庙使用。今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现代化商场大厅,千年之前却是庄严肃穆香烟缭绕的皇帝宗庙殿堂,这种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恐怕是人们殊难料及的吧!
开元寺在明、清两代也都有过整修,西安碑林藏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吴泰撰文的《开元寺八景图记》说:
梵阁朝晖,城晚照。
酒楼横笛,僧院鸣钟。
春雨莺声,古垣鹊噪。
槐荫煮茗,雪馆挑灯。
可见在清代开元寺的规模仍很大,也很繁华。辛亥革命陕西同盟会会址曾设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