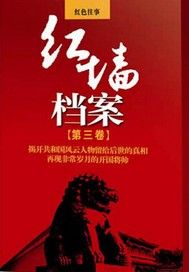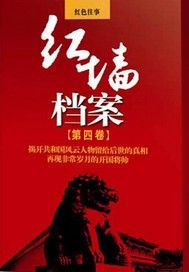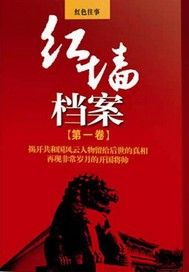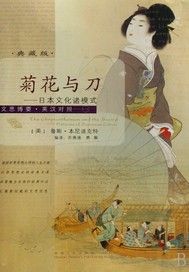6.5 再建良知:阳明与明学
钱宾四先生于1930年春写成《阳明学述要》一书,后收进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54年再版于台湾。此书着意揭示王阳明的真精神。全书依次讨论的问题是:“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明学的一般趋向和在王学以前及同时几个有关系的学者”、“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王学的三变”、“王学大纲”、“阳明的晚年思想”、“王学的流传”等。书后为“阳明年谱”。作者把阳明学放在整个宋明学术本体论与工夫论(修养方法论)的走向与争论的背景上加以考察,讨论了阳明的心路历程,以及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诚意、谨独、立志、事上磨炼等主要命题。
钱穆认为:“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烦有所谓凑泊。人心自然能明觉得此天理,也不烦再有所谓工夫了。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易又直捷的答案之最大贡献处。”阳明以致知来代替北宋相传的集义和穷理,又以知行合一和诚意来代替北宋相传的一个敬字。北宋以来所谓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讲工夫上的争端,在阳明则打并归一,圆满解决。至于对本体方面心与物的争端,“据普通一般见解,阳明自是偏向象山,归入心即理的一面;其实阳明虽讲心理合一,教人从心上下工夫,但他的议论,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极,别开生面,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
钱穆认为,阳明实不曾树起革命的叛旗,来打倒北宋以来的前辈。他批评了后世讲程朱的人要痛斥阳明,讲阳明的人也要轻视程朱的门户之见。他强调阳明仍是宋儒讲学的大传统。阳明把天地万物说成只是一个灵明,又讲离却天地万物,亦没有我们的灵明,是其独特精神之处。他认为阳明晚年特别提出事上磨炼,只为要在朱子格物和象山立心的两边,为他们开一通渠。对阳明晚年思想,钱穆认为其“拔本塞源论”(按:即《答顾东桥书》末节)比《大学问》和“四句教”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由此可看出,王学并不偏陷于个人的喜怒哀乐方寸之地,而把良知推到个人内心之外,扩及人类之全体、人生一切知识才能与事业,兼及人与人之相同与相异处,并由伦理推扩到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上。
以下我们根据钱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和《中国思想史》,来看他对王阳明及明代理学的把握。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对阳明学的看法,与早年所著《阳明学述要》略有不同,较多谈到朱王之异。
一、明代学术
“明代学术,大体沿袭宋。关于学术上之中心问题及最高目标,均未能摆脱宋人,别自创辟。而且明代学术,较之宋代,远为单纯。初期宋学之博大开展,以及南渡后浙东史学之精密细致,明人都没有。他们只沿袭着正统宋学的一脉,但又于正统宋学中剔去了周邵张三家。实际明代学术,只好说沿袭着朱陆异同的一问题。他们对此问题之贡献,可说已超过了朱陆,但也仅此而止。明学较之宋学,似乎更精微,但也更单纯。”
在总体上把握明代理学之后,钱穆又把明代理学分为初期理学、中期理学、晚期理学,并对这几个时期的学术流变及其特点进行分析。
初期明学。其实明代学术,只有举出王阳明一个人作为代表,其他有光彩有力量的,也都在王阳明之后。由此出发,钱穆把王阳明以前的明代学术称之为初期明学。但明代初期的学术与宋代初期的学术无法比拟。明代初期只是经历过蒙古百年统治之后,一种严霜大雪掩盖下的生机萌芽,而宋代初期的学术则气势宏伟、规模庞大。
中期明学。中期明学是明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初期明学,南方如吴与弼、陈献章,都是隐退之人,偏于田野山林;北方如薛宣,也谨慎持守,对于义理方面很少有发挥。明代学术要到王守仁,才开始光彩毕露,因此钱穆把王守仁所处的时代定为明学的中期。与王守仁同时代的还有湛若水、罗钦顺两人。王守仁问学于娄一斋,湛若水从游于陈献章,而娄、陈都是吴与弼的学生。王守仁和湛若水相交游,而讲学宗旨不同,一时在学术上形成平分天下的态势。当时学于湛若水的,有的卒业于王守仁;学于王守仁的,有的卒业于湛若水。王守仁和湛若水并立,就像南宋时的朱熹和陆象山对立一样。而罗钦顺则学无师承,生前也很少讲学授徒,死后也没有什么后学,可以说独来独往,独自发明。罗钦顺与湛若水、王守仁形成明代中期学术界三足鼎立之势。明代的学术以中期为最盛,中期以后的学术,如王学支流、后学,直到明末才开始发生大变化。因此王门各学术派别也属于中期。
晚期明学。钱穆认为,如把中期宋学看作是宋明理学的正统,那么程颢应该是中期宋学的正统代表人物。从他开始到程颐、朱熹一路,却由中期会合到初期。这是指朱子一反程氏兄弟以来正统理学学术狭窄,只重心性、理气的道学风习,而返回宋初诸儒的政治治平、经史博古和文章子集之学上去。另一条路是从程颢到陆象山,再到王守仁,由王守仁再转到泰州学派而至罗汝芳。这条路与朱熹走的那条路不同。这条路到此走到尽头,如同远行人到了家,到了家就无路可走了。如果你不安于家,尽要向外跑,那必须得再出门。晚期明学就是承接那一条走到尽头的路,到了家,又想另起身,另辟蹊径。可惜晚明儒出门行走得不远,扑面遇着暴风雨,阻碍了道路,迷失了方向,那是明清之际的大激变。只有临时找一个安全之处躲藏,但一躲下来,不免耽误了,而且把出门时原有的计划打消了,放弃了,那才有清代乾嘉时期的经学考据。
钱穆认为,真正想沿着晚明儒初出门时那条路走下去的是东林学派。东林学派与王门诸流派不同。王守仁死后,浙中王门与泰州王门,所在设教,鼓动流欲,意气猖狂,迹近标榜。但东林诸贤却不然。他们虽然有一个学会,但仅作朋友私人的讲习。后来“东林”两字扩大到全国,一切忠义气节之士归到东林门下,好像东林成为当时一个大党派,甚至后来把明代亡国也说成是东林党祸所招致的。钱穆指出,东林诸家虽然讲学设教不同,而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是凭空追寻宇宙或人生的大原理,再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现实,或凭这个原理衡量已往的历史。他们似乎更着眼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已往历史的客观经过上。因此他们的理论,更针对现实,客观了解过去,在思想上也没有要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或信守某家某派的理论和主张。这一点,显然是一种新态度。六百年来的理学,便在这一新态度上变了质。
在钱穆看来,明代理学的殿军是明末诸遗老。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转变,不是一件容易出现的事。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与王守仁,可以说已攀登上相反方面的两个高峰,宋明理学所要窥探的全部领域早已豁露无遗了。再沿着这两条路线前进,自然会逐渐走下坡路。但只要继续地向前,必然会踏上新原野,遇见新高峰。这是思想史演进的规律。基于此点,钱穆把明末诸遗老看成开辟新天地的人物。明末诸遗老,北方有孙奇逢、李甬、颜元等,南方有黄宗羲、陈确、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陆世仪等。还有数不清的在学术思想上杰出的人物,与宋初明初一片荒凉是天壤之别。这已经告诉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所积累的大力量。但他们表面上虽然沿袭前轨,精神上已另辟新径。其实清代也有承接宋明理学的,虽然仅是一个伏流,不能与经学考据学相抗衡,但仍然有其相当的流量,始终没有中断过。这说明宋明七百年理学,在清代仍有生命,这是下半部中国思想史里不可磨灭的一番大事业。
二、心体的实践论
在明代理学家中,钱穆最重视王阳明。王阳明一生真可算是以身教身,以心教心的最具体、最到家的一个实例。王阳明平生讲学,总是针对着对方讲,从不凭空讲,也不意在讲书本,或讲天地与万物。他只是本着他自己内心真实经验讲。具体地说,他讲的是良知之学,只是讲人之心,只是本着心来指点内心。他的学术是真正的心学。钱穆把陆象山看作是理学中的别出,把王阳明看作是别出儒中登峰造极者。所谓终久大之易简工夫,已走到无可再易再简,因此说他是登峰造极。
钱穆在解释王阳明“良知”时指出,王阳明的良知就是知善知恶。陆象山说“心即理”,王阳明为他补充,说心有良知,自能分辨善恶,人心的良知就是天理。但知善知恶是能知的心,善恶是所知之理,它们之间是不同的。就宇宙论而言,是非不一定就是善恶;就人生论而言,是的便是善,非的便是恶。一个是物理,一个是事理,朱子把这两者合拢讲,王阳明则分开说。王阳明所谓天理,主要是指人生界的事理,不再泛讲天地自然,如此便把天理的范围变狭窄了。阳明说这一种是非的最后标准根本在于人心的好恶。人心所好就是是,人心所恶就是非。所好所恶者,虽然是外面的事物,但好之恶之者是人的心。人心所好便是,人心所恶便非,如果没有我心的好恶,外面事物根本没有是非可言。纵可说人心有时不知是非、善恶,但哪有不知好恶的呢?知得好恶,就是知得善恶,因此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人哪有不好生恶死的?因此助长人生便是善,陷害人死便是恶。此理因人心的好恶而有,并不是在没有生命,没有人心好恶以前,便先有了此理。既然人心是好善恶恶,为什么人生界乃至人心上还有许多恶存在呢?钱穆由此研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钱穆认为,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不指工夫,而是指本体,是说知行本属一体。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因没有了解他老师的知行合一,来问王阳明:人都应知道对父兄要孝悌,却有不孝不悌的现象,这说明知行分明是两件事。王阳明说,人类知有孝,一定已经先自孝了。知有善,必已先自善了。如是岂不又成了行先于知吗?如果就宇宙而言,除非如西方宗教家所说,行先于知是不错的。但如果就人文界而言,人类一切行为没有不发于心,普遍说心是知,不是行。因此说心即理,说知行合一,却不说行先于知。
王阳明所谓心,是知行合一的。如果把这番话推到宇宙界来讲,朱熹的理气论,也可说理是气的主意,气是理的工夫。只说理,已有气;只说气,已有理。理气也是合一的。但王阳明不也说知是行之始吗?朱熹说理先于气,岂不仍然与王阳明一致?钱穆认为,这里却又有个分别。因为王阳明说的知是活的,有主意的;朱子说的理是静的,无造作的。因此朱熹说知只是觉,而王阳明说知却有好恶的意向。朱熹只说心能觉见理,却没有说心之所好就是理。朱熹是性与心分,王阳明是性与心一。因此,朱熹不得不把心与理分离,而王阳明则自然把心与理合一。如果心知了只是觉,则知了未必便能行,因此心与理是二。如果心知觉中兼有好恶的意向,则知了自能行,因此心与理是一。
钱穆由王阳明的心与理是一,进一步谈到他的工夫论,并认为王阳明把“诚”字来代替“敬”字是他与程朱心学工夫上的主要分歧点。这种所谓心体之诚,说起来容易,得来却不易。人自有生以来,就有种种习染,积累成私欲,如镜上尘埃,水中渣滓,夹杂在心,把心体之诚遮掩了。那么如何廓清心体呢?钱穆认为,王阳明发明了两种工夫。其一是常教人静坐,息思虑,使自悟性体。王阳明这番工夫,有点像张载、程颐所谓变化气质,以及朱熹所谓静存动察。尤其是佛家对这种工夫更加注意。这种静坐与省察克治仅是消极工夫。其二是教人致良知,教人即知即行,这是积极工夫。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能自知善恶,如果自知这一念是恶,就应该把它克了,必须彻底不使这一念潜伏在胸中。如果自知这一念是善,就应该扎扎实实地依着这一念去做。不要使潜藏在心里的和显露在外面的日渐分成两半,如此就是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如此做法便可使心纯乎天理,即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到达这个境界就是所谓的圣人。
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实在可称为一种心体的实践论。与其说他看重知,毋宁说他更看重行;与其说他看重心,毋宁说他更看重事。钱穆认为,王阳明之意,“除却对天地万物之感应,将不见有心。除却对此种感应之是非判别,将无所谓良知。所谓致良知,只要叫我们去事上磨炼。所谓事上磨炼,只要叫我们立诚。所谓立诚,只要叫我们认识此知行合一之原来本体。一切所知的便是所行的,所行的便是所知的。平常往往把知行划成两截,就内心言,往往潜意识与显意识暗藏着冲突。就人事言,往往心里想的与外面做的并不一致。种种利害的打算,把真性情隐晦了。这些都不是良知,都不是天理。人不须于良知外别求天理,真诚恻怛的性情,便是天理本原。须求自心的潜意识与显意识能融成一片,须求外面所行与内心所想也融成一片。全无障隔,全无渣滓,那便是直诚恻怛,那便是良知,那便是天理,那便是圣人”。这是钱穆对王阳明良知之学基本原理的总结。
钱穆在分析王阳明良知之学原理的基础上,考察王阳明根据良知之学所幻想建立的理想社会。在钱穆看来,人文世界的演进愈来愈复杂,外面事变纷繁,利害关系复杂了,使得人人的心都包蕴着重重的冲突和矛盾,潜藏的和显露在浮面的不一致,内心所打算的和向外所表白的不一致,不仅人与人之间有一层障碍,而且自己心里也存在着种种障碍。结果把原来心态,即孟子所谓本心和王阳明所谓良知丧失了。那么以后的表现在阳明那里被称为人欲。本来天理是由人欲而生,但后来人欲却阻碍了天理。王阳明从人文立场出发创生出他想象的人人良知畅遂流行的一种理想社会。这就是他的“拔本塞源之论”。
钱穆认为,中国思想史里所最缺乏的是宗教,但中国却有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儒家思想的最高发展必然常有此种宗教精神作源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种人文教的最高信仰、最高教义。这种人文教的天堂就是理想的现实社会。要造成这一理想社会,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内心世界、人人共有的心灵生活。这种内在的心地,孔子曰仁,孟子曰善,阳明曰良知。只要某人到达这种心地,这个人就已先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是这种理想社会的起点,必须等到人人到达这种心地与生活,才是这种社会的圆满实现。这是人类文化理想的最高可能。达到这种心地与生活的人生就是不朽的人生。这种人生,在大群生命中也是不朽的。
如果依照王阳明的话来说,人类到达这种境界,便觉得人生古今、天地万物只是一个良知。钱穆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中的一种唯心论,一种人生实践的唯心论,与西方由纯思辨中得来的唯心论不同。这种人生实践又必然常有中国传统的宗教精神,即所谓入世的人文教精神。由此看出,王阳明这些思想受禅宗影响很大,所不同的是禅宗归宿到清净涅盘,而王阳明则要建立理想的人类文化最高可能的境界。
钱穆抓住王阳明学的核心“良知之学”,对其学术思想总体把握。王阳明的良知就是天理。从前程颢说过,“天理”二字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什么是天理,从程颐到朱熹提出格物穷理的教法,要明理首先就必须格物,格物一旦达到豁然贯通的时候,才算是明白这个天理。这种天理的获得太难了,非下苦工夫不可。现在王阳明却说,天理就是人心的良知,那么天理本身就不远吾人了,不需要劳神辛苦地向天地万物去穷格。这显然与程朱传统不同。那么良知又如何就是天理呢?王阳明说,天理逃不掉善与恶两项,正因为人心本身分别有善与恶之知,所以说人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一般的凡人,有的人成为圣人?王阳明认为这在于人是否能发明本心,体悟天理。他的良知之学发展到最高处,就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做尧舜的条件不在外面的事业上,而在自己心性上。人的才性有不同,但就其才性发展到至诚至尽处,便都是尧舜。佛教发展到禅宗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儒家发展到王阳明,使人人都可以作圣人。这个理论固然渊源于孟子和陆象山,但到了王阳明手里说得更透辟。
钱穆指出,王阳明“良知就是天理”与“知行合一”有关。“知行合一”是指知行本体原来是合一,不分开的。说良知便已包有行,说良知也已包有天理,知行就是良知。程朱要下苦工夫格物穷理。王阳明意见很简单,只要知与行达到真实合一处,便就是天理。必须要等到人人做了圣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也才是理想的社会。这样,通过钱穆的论述,我们懂得,王阳明学术的真精神不在为学术而学术,而在于通过良知之学,以及“人心的良知就是天理”的简单教法建立一个具有圣人品格的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
三、王门诸流派
钱穆把王阳明当作明学中期的代表,把王门诸儒也归于这个时期。钱氏指出南宋有了一个朱熹,以后诸儒,或赞成朱熹的,或反对朱熹的,都离不开朱熹这个中心。明代也如此,有了一个王阳明,以后的明学无论是赞同王阳明的,还是反对王阳明的,也离不开王阳明这个中心。钱穆根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和泰州学派,并分别阐述这些学派的流变及特点,以示王阳明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
浙中学派。浙中学派以徐爱、钱德洪、王畿三人最重要。徐爱死得早,于是钱德洪和王畿成为王门最大弟子,他们宣扬王学功劳最大。王畿与钱德洪亲炙王阳明最久,但两人学说有很大差异。钱德洪的彻悟不如王畿,而王畿的修持则不如钱德洪。王阳明良知学,也可说寓含一种社会教育的精神。钱德洪与王畿长期从事社会教育。他们与以前理学讲学态度不同。这样流动性的集会讲学,一面是讲各自的良知,反身即得,一面是讲天地万物为一体,当下就是圣人。听讲的人多庞杂,讲得又简易,又广大,自然难免有流弊,于是出现所谓的伪良知。
泰州学派。主要人物是王艮。王阳明的良知学,本来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这种落实到社会大众手里的哲学与士大夫阶层不同。从这方面讲,王艮的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唯一的真传。王艮的主要思想是他的格物说。他把格物理解成为安身。但安身并不是自私的,他教人把一切过错归到自己身上,这才是他安身证法。安身才可以行道,尊身即所以尊道,而尊身之至,必求其能为帝者师,为天下万世师。可见帝者师不在位上求,而在德上求。虽然身处田野,依然可以是帝者师,是天下万世师。使自身可以为帝者师,为天下万世师,就是修其身以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他的格物说。
江右学派。钱穆认为,王阳明学术流衍最大、力量最强的除浙中与泰州外,还有江西一派,当时称江右之门。这个学派与浙中、泰州学派不同。这是在士大夫阶层、读书闲居人中的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洪先、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邹守益和罗洪先,邹守益主张戒惧,而得力于敬,认为敬是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者。罗洪先是阳明私淑弟子,以为良知是心之本体,即天理、至善。本体湛然,有感必有应,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顺之而已。他也主张静坐收敛。在晚明学术界,江右学派的影响超过了浙中学派。王学实在是活泼生动。江右以后,却变得静细萧散,不免带有道家的气息。如果再加上一些严密的意味,便又要由王阳明返回到朱熹。钱穆认为,明代晚期学术,只在这里绕圈子,更无新出路,这是宋明理学衰竭之象征。
钱穆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表明,宋明儒已经从佛学悲观消极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开始回复到先秦儒学,重新面对人生现实。他们运用先秦儒的性善观念,要由人类自身的内在光明来寻求大道。在这里,有偏近于向外寻理与只限于向内寻求这一区别。另一方面,宋明儒虽然如先秦儒一样要积极面对人生现实,但他们因受佛家影响,总爱把人生现实的价值安放在整个宇宙里去衡量,如此则常觉得人生渺小与浮弱。他们总想在现实人生外去寻找宇宙万物共同的本体。如此人生现实依然渺小、浮弱。因此他们的意境多少带有几分悲观消极,不如先秦儒那样人生多面活动的活泼与强壮。换句话说,用《大学》八条目分析,宋明儒似乎对诚意、正心工夫用得多,以修身齐家为宗旨,而对上面治国平天下工夫用得少。汉唐儒及北宋初期诸儒可以说对治国平天下工夫用得多一些,对诚意正心工夫不如理学更注重,更深入。“如此言之,先秦儒以下,终是向外工夫胜过了向内,而到宋明理学诸儒则终是向内工夫胜过了向外。”这是钱穆研究宋明儒得出的结论。
综上所述,钱穆对理学思想的研究既有得也有失。得的方面:(1)重视从总体上把握宋明理学的特征及其基本精神,并在中国思想史、儒学发展史大视野中予以定位,使人对宋明理学的特点、基本精神以及历史地位一目了然。(2)重视从史学角度研究理学,侧重研究理学诸家、诸学派先后师承关系以及学术渊源,揭示了他们不同的特点,以及学术流变的轨迹。这种不把理学家思想平铺开来,而把他们之间看成是有联系的、有序的系统的思想,体现了他治学一贯贵通的学术风格。(3)坚持从中国思想史本身出发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克服了那种以西学剪裁中学的简单公式法。这对当前研究中国哲学史有方法论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从史学出发,过多地注重理学学术的流变、师友渊源,而对诸家的思想横向诠释或共时性分析的深度不够。另外,在理学研究专著体裁上多少有学案体的遗迹,引证原文偏多,理论分析少了一些。这与他早年读夏曾佑书的影响有关。
§§第7章 每转而益进 途穷而必变
钱穆认为:“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烦有所谓凑泊。人心自然能明觉得此天理,也不烦再有所谓工夫了。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易又直捷的答案之最大贡献处。”阳明以致知来代替北宋相传的集义和穷理,又以知行合一和诚意来代替北宋相传的一个敬字。北宋以来所谓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讲工夫上的争端,在阳明则打并归一,圆满解决。至于对本体方面心与物的争端,“据普通一般见解,阳明自是偏向象山,归入心即理的一面;其实阳明虽讲心理合一,教人从心上下工夫,但他的议论,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极,别开生面,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
钱穆认为,阳明实不曾树起革命的叛旗,来打倒北宋以来的前辈。他批评了后世讲程朱的人要痛斥阳明,讲阳明的人也要轻视程朱的门户之见。他强调阳明仍是宋儒讲学的大传统。阳明把天地万物说成只是一个灵明,又讲离却天地万物,亦没有我们的灵明,是其独特精神之处。他认为阳明晚年特别提出事上磨炼,只为要在朱子格物和象山立心的两边,为他们开一通渠。对阳明晚年思想,钱穆认为其“拔本塞源论”(按:即《答顾东桥书》末节)比《大学问》和“四句教”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由此可看出,王学并不偏陷于个人的喜怒哀乐方寸之地,而把良知推到个人内心之外,扩及人类之全体、人生一切知识才能与事业,兼及人与人之相同与相异处,并由伦理推扩到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上。
以下我们根据钱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和《中国思想史》,来看他对王阳明及明代理学的把握。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对阳明学的看法,与早年所著《阳明学述要》略有不同,较多谈到朱王之异。
一、明代学术
“明代学术,大体沿袭宋。关于学术上之中心问题及最高目标,均未能摆脱宋人,别自创辟。而且明代学术,较之宋代,远为单纯。初期宋学之博大开展,以及南渡后浙东史学之精密细致,明人都没有。他们只沿袭着正统宋学的一脉,但又于正统宋学中剔去了周邵张三家。实际明代学术,只好说沿袭着朱陆异同的一问题。他们对此问题之贡献,可说已超过了朱陆,但也仅此而止。明学较之宋学,似乎更精微,但也更单纯。”
在总体上把握明代理学之后,钱穆又把明代理学分为初期理学、中期理学、晚期理学,并对这几个时期的学术流变及其特点进行分析。
初期明学。其实明代学术,只有举出王阳明一个人作为代表,其他有光彩有力量的,也都在王阳明之后。由此出发,钱穆把王阳明以前的明代学术称之为初期明学。但明代初期的学术与宋代初期的学术无法比拟。明代初期只是经历过蒙古百年统治之后,一种严霜大雪掩盖下的生机萌芽,而宋代初期的学术则气势宏伟、规模庞大。
中期明学。中期明学是明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初期明学,南方如吴与弼、陈献章,都是隐退之人,偏于田野山林;北方如薛宣,也谨慎持守,对于义理方面很少有发挥。明代学术要到王守仁,才开始光彩毕露,因此钱穆把王守仁所处的时代定为明学的中期。与王守仁同时代的还有湛若水、罗钦顺两人。王守仁问学于娄一斋,湛若水从游于陈献章,而娄、陈都是吴与弼的学生。王守仁和湛若水相交游,而讲学宗旨不同,一时在学术上形成平分天下的态势。当时学于湛若水的,有的卒业于王守仁;学于王守仁的,有的卒业于湛若水。王守仁和湛若水并立,就像南宋时的朱熹和陆象山对立一样。而罗钦顺则学无师承,生前也很少讲学授徒,死后也没有什么后学,可以说独来独往,独自发明。罗钦顺与湛若水、王守仁形成明代中期学术界三足鼎立之势。明代的学术以中期为最盛,中期以后的学术,如王学支流、后学,直到明末才开始发生大变化。因此王门各学术派别也属于中期。
晚期明学。钱穆认为,如把中期宋学看作是宋明理学的正统,那么程颢应该是中期宋学的正统代表人物。从他开始到程颐、朱熹一路,却由中期会合到初期。这是指朱子一反程氏兄弟以来正统理学学术狭窄,只重心性、理气的道学风习,而返回宋初诸儒的政治治平、经史博古和文章子集之学上去。另一条路是从程颢到陆象山,再到王守仁,由王守仁再转到泰州学派而至罗汝芳。这条路与朱熹走的那条路不同。这条路到此走到尽头,如同远行人到了家,到了家就无路可走了。如果你不安于家,尽要向外跑,那必须得再出门。晚期明学就是承接那一条走到尽头的路,到了家,又想另起身,另辟蹊径。可惜晚明儒出门行走得不远,扑面遇着暴风雨,阻碍了道路,迷失了方向,那是明清之际的大激变。只有临时找一个安全之处躲藏,但一躲下来,不免耽误了,而且把出门时原有的计划打消了,放弃了,那才有清代乾嘉时期的经学考据。
钱穆认为,真正想沿着晚明儒初出门时那条路走下去的是东林学派。东林学派与王门诸流派不同。王守仁死后,浙中王门与泰州王门,所在设教,鼓动流欲,意气猖狂,迹近标榜。但东林诸贤却不然。他们虽然有一个学会,但仅作朋友私人的讲习。后来“东林”两字扩大到全国,一切忠义气节之士归到东林门下,好像东林成为当时一个大党派,甚至后来把明代亡国也说成是东林党祸所招致的。钱穆指出,东林诸家虽然讲学设教不同,而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是凭空追寻宇宙或人生的大原理,再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现实,或凭这个原理衡量已往的历史。他们似乎更着眼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已往历史的客观经过上。因此他们的理论,更针对现实,客观了解过去,在思想上也没有要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或信守某家某派的理论和主张。这一点,显然是一种新态度。六百年来的理学,便在这一新态度上变了质。
在钱穆看来,明代理学的殿军是明末诸遗老。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转变,不是一件容易出现的事。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与王守仁,可以说已攀登上相反方面的两个高峰,宋明理学所要窥探的全部领域早已豁露无遗了。再沿着这两条路线前进,自然会逐渐走下坡路。但只要继续地向前,必然会踏上新原野,遇见新高峰。这是思想史演进的规律。基于此点,钱穆把明末诸遗老看成开辟新天地的人物。明末诸遗老,北方有孙奇逢、李甬、颜元等,南方有黄宗羲、陈确、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陆世仪等。还有数不清的在学术思想上杰出的人物,与宋初明初一片荒凉是天壤之别。这已经告诉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所积累的大力量。但他们表面上虽然沿袭前轨,精神上已另辟新径。其实清代也有承接宋明理学的,虽然仅是一个伏流,不能与经学考据学相抗衡,但仍然有其相当的流量,始终没有中断过。这说明宋明七百年理学,在清代仍有生命,这是下半部中国思想史里不可磨灭的一番大事业。
二、心体的实践论
在明代理学家中,钱穆最重视王阳明。王阳明一生真可算是以身教身,以心教心的最具体、最到家的一个实例。王阳明平生讲学,总是针对着对方讲,从不凭空讲,也不意在讲书本,或讲天地与万物。他只是本着他自己内心真实经验讲。具体地说,他讲的是良知之学,只是讲人之心,只是本着心来指点内心。他的学术是真正的心学。钱穆把陆象山看作是理学中的别出,把王阳明看作是别出儒中登峰造极者。所谓终久大之易简工夫,已走到无可再易再简,因此说他是登峰造极。
钱穆在解释王阳明“良知”时指出,王阳明的良知就是知善知恶。陆象山说“心即理”,王阳明为他补充,说心有良知,自能分辨善恶,人心的良知就是天理。但知善知恶是能知的心,善恶是所知之理,它们之间是不同的。就宇宙论而言,是非不一定就是善恶;就人生论而言,是的便是善,非的便是恶。一个是物理,一个是事理,朱子把这两者合拢讲,王阳明则分开说。王阳明所谓天理,主要是指人生界的事理,不再泛讲天地自然,如此便把天理的范围变狭窄了。阳明说这一种是非的最后标准根本在于人心的好恶。人心所好就是是,人心所恶就是非。所好所恶者,虽然是外面的事物,但好之恶之者是人的心。人心所好便是,人心所恶便非,如果没有我心的好恶,外面事物根本没有是非可言。纵可说人心有时不知是非、善恶,但哪有不知好恶的呢?知得好恶,就是知得善恶,因此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人哪有不好生恶死的?因此助长人生便是善,陷害人死便是恶。此理因人心的好恶而有,并不是在没有生命,没有人心好恶以前,便先有了此理。既然人心是好善恶恶,为什么人生界乃至人心上还有许多恶存在呢?钱穆由此研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钱穆认为,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不指工夫,而是指本体,是说知行本属一体。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因没有了解他老师的知行合一,来问王阳明:人都应知道对父兄要孝悌,却有不孝不悌的现象,这说明知行分明是两件事。王阳明说,人类知有孝,一定已经先自孝了。知有善,必已先自善了。如是岂不又成了行先于知吗?如果就宇宙而言,除非如西方宗教家所说,行先于知是不错的。但如果就人文界而言,人类一切行为没有不发于心,普遍说心是知,不是行。因此说心即理,说知行合一,却不说行先于知。
王阳明所谓心,是知行合一的。如果把这番话推到宇宙界来讲,朱熹的理气论,也可说理是气的主意,气是理的工夫。只说理,已有气;只说气,已有理。理气也是合一的。但王阳明不也说知是行之始吗?朱熹说理先于气,岂不仍然与王阳明一致?钱穆认为,这里却又有个分别。因为王阳明说的知是活的,有主意的;朱子说的理是静的,无造作的。因此朱熹说知只是觉,而王阳明说知却有好恶的意向。朱熹只说心能觉见理,却没有说心之所好就是理。朱熹是性与心分,王阳明是性与心一。因此,朱熹不得不把心与理分离,而王阳明则自然把心与理合一。如果心知了只是觉,则知了未必便能行,因此心与理是二。如果心知觉中兼有好恶的意向,则知了自能行,因此心与理是一。
钱穆由王阳明的心与理是一,进一步谈到他的工夫论,并认为王阳明把“诚”字来代替“敬”字是他与程朱心学工夫上的主要分歧点。这种所谓心体之诚,说起来容易,得来却不易。人自有生以来,就有种种习染,积累成私欲,如镜上尘埃,水中渣滓,夹杂在心,把心体之诚遮掩了。那么如何廓清心体呢?钱穆认为,王阳明发明了两种工夫。其一是常教人静坐,息思虑,使自悟性体。王阳明这番工夫,有点像张载、程颐所谓变化气质,以及朱熹所谓静存动察。尤其是佛家对这种工夫更加注意。这种静坐与省察克治仅是消极工夫。其二是教人致良知,教人即知即行,这是积极工夫。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能自知善恶,如果自知这一念是恶,就应该把它克了,必须彻底不使这一念潜伏在胸中。如果自知这一念是善,就应该扎扎实实地依着这一念去做。不要使潜藏在心里的和显露在外面的日渐分成两半,如此就是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如此做法便可使心纯乎天理,即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到达这个境界就是所谓的圣人。
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实在可称为一种心体的实践论。与其说他看重知,毋宁说他更看重行;与其说他看重心,毋宁说他更看重事。钱穆认为,王阳明之意,“除却对天地万物之感应,将不见有心。除却对此种感应之是非判别,将无所谓良知。所谓致良知,只要叫我们去事上磨炼。所谓事上磨炼,只要叫我们立诚。所谓立诚,只要叫我们认识此知行合一之原来本体。一切所知的便是所行的,所行的便是所知的。平常往往把知行划成两截,就内心言,往往潜意识与显意识暗藏着冲突。就人事言,往往心里想的与外面做的并不一致。种种利害的打算,把真性情隐晦了。这些都不是良知,都不是天理。人不须于良知外别求天理,真诚恻怛的性情,便是天理本原。须求自心的潜意识与显意识能融成一片,须求外面所行与内心所想也融成一片。全无障隔,全无渣滓,那便是直诚恻怛,那便是良知,那便是天理,那便是圣人”。这是钱穆对王阳明良知之学基本原理的总结。
钱穆在分析王阳明良知之学原理的基础上,考察王阳明根据良知之学所幻想建立的理想社会。在钱穆看来,人文世界的演进愈来愈复杂,外面事变纷繁,利害关系复杂了,使得人人的心都包蕴着重重的冲突和矛盾,潜藏的和显露在浮面的不一致,内心所打算的和向外所表白的不一致,不仅人与人之间有一层障碍,而且自己心里也存在着种种障碍。结果把原来心态,即孟子所谓本心和王阳明所谓良知丧失了。那么以后的表现在阳明那里被称为人欲。本来天理是由人欲而生,但后来人欲却阻碍了天理。王阳明从人文立场出发创生出他想象的人人良知畅遂流行的一种理想社会。这就是他的“拔本塞源之论”。
钱穆认为,中国思想史里所最缺乏的是宗教,但中国却有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儒家思想的最高发展必然常有此种宗教精神作源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种人文教的最高信仰、最高教义。这种人文教的天堂就是理想的现实社会。要造成这一理想社会,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内心世界、人人共有的心灵生活。这种内在的心地,孔子曰仁,孟子曰善,阳明曰良知。只要某人到达这种心地,这个人就已先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是这种理想社会的起点,必须等到人人到达这种心地与生活,才是这种社会的圆满实现。这是人类文化理想的最高可能。达到这种心地与生活的人生就是不朽的人生。这种人生,在大群生命中也是不朽的。
如果依照王阳明的话来说,人类到达这种境界,便觉得人生古今、天地万物只是一个良知。钱穆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中的一种唯心论,一种人生实践的唯心论,与西方由纯思辨中得来的唯心论不同。这种人生实践又必然常有中国传统的宗教精神,即所谓入世的人文教精神。由此看出,王阳明这些思想受禅宗影响很大,所不同的是禅宗归宿到清净涅盘,而王阳明则要建立理想的人类文化最高可能的境界。
钱穆抓住王阳明学的核心“良知之学”,对其学术思想总体把握。王阳明的良知就是天理。从前程颢说过,“天理”二字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什么是天理,从程颐到朱熹提出格物穷理的教法,要明理首先就必须格物,格物一旦达到豁然贯通的时候,才算是明白这个天理。这种天理的获得太难了,非下苦工夫不可。现在王阳明却说,天理就是人心的良知,那么天理本身就不远吾人了,不需要劳神辛苦地向天地万物去穷格。这显然与程朱传统不同。那么良知又如何就是天理呢?王阳明说,天理逃不掉善与恶两项,正因为人心本身分别有善与恶之知,所以说人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一般的凡人,有的人成为圣人?王阳明认为这在于人是否能发明本心,体悟天理。他的良知之学发展到最高处,就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做尧舜的条件不在外面的事业上,而在自己心性上。人的才性有不同,但就其才性发展到至诚至尽处,便都是尧舜。佛教发展到禅宗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儒家发展到王阳明,使人人都可以作圣人。这个理论固然渊源于孟子和陆象山,但到了王阳明手里说得更透辟。
钱穆指出,王阳明“良知就是天理”与“知行合一”有关。“知行合一”是指知行本体原来是合一,不分开的。说良知便已包有行,说良知也已包有天理,知行就是良知。程朱要下苦工夫格物穷理。王阳明意见很简单,只要知与行达到真实合一处,便就是天理。必须要等到人人做了圣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也才是理想的社会。这样,通过钱穆的论述,我们懂得,王阳明学术的真精神不在为学术而学术,而在于通过良知之学,以及“人心的良知就是天理”的简单教法建立一个具有圣人品格的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
三、王门诸流派
钱穆把王阳明当作明学中期的代表,把王门诸儒也归于这个时期。钱氏指出南宋有了一个朱熹,以后诸儒,或赞成朱熹的,或反对朱熹的,都离不开朱熹这个中心。明代也如此,有了一个王阳明,以后的明学无论是赞同王阳明的,还是反对王阳明的,也离不开王阳明这个中心。钱穆根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和泰州学派,并分别阐述这些学派的流变及特点,以示王阳明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
浙中学派。浙中学派以徐爱、钱德洪、王畿三人最重要。徐爱死得早,于是钱德洪和王畿成为王门最大弟子,他们宣扬王学功劳最大。王畿与钱德洪亲炙王阳明最久,但两人学说有很大差异。钱德洪的彻悟不如王畿,而王畿的修持则不如钱德洪。王阳明良知学,也可说寓含一种社会教育的精神。钱德洪与王畿长期从事社会教育。他们与以前理学讲学态度不同。这样流动性的集会讲学,一面是讲各自的良知,反身即得,一面是讲天地万物为一体,当下就是圣人。听讲的人多庞杂,讲得又简易,又广大,自然难免有流弊,于是出现所谓的伪良知。
泰州学派。主要人物是王艮。王阳明的良知学,本来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这种落实到社会大众手里的哲学与士大夫阶层不同。从这方面讲,王艮的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唯一的真传。王艮的主要思想是他的格物说。他把格物理解成为安身。但安身并不是自私的,他教人把一切过错归到自己身上,这才是他安身证法。安身才可以行道,尊身即所以尊道,而尊身之至,必求其能为帝者师,为天下万世师。可见帝者师不在位上求,而在德上求。虽然身处田野,依然可以是帝者师,是天下万世师。使自身可以为帝者师,为天下万世师,就是修其身以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他的格物说。
江右学派。钱穆认为,王阳明学术流衍最大、力量最强的除浙中与泰州外,还有江西一派,当时称江右之门。这个学派与浙中、泰州学派不同。这是在士大夫阶层、读书闲居人中的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洪先、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邹守益和罗洪先,邹守益主张戒惧,而得力于敬,认为敬是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者。罗洪先是阳明私淑弟子,以为良知是心之本体,即天理、至善。本体湛然,有感必有应,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顺之而已。他也主张静坐收敛。在晚明学术界,江右学派的影响超过了浙中学派。王学实在是活泼生动。江右以后,却变得静细萧散,不免带有道家的气息。如果再加上一些严密的意味,便又要由王阳明返回到朱熹。钱穆认为,明代晚期学术,只在这里绕圈子,更无新出路,这是宋明理学衰竭之象征。
钱穆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表明,宋明儒已经从佛学悲观消极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开始回复到先秦儒学,重新面对人生现实。他们运用先秦儒的性善观念,要由人类自身的内在光明来寻求大道。在这里,有偏近于向外寻理与只限于向内寻求这一区别。另一方面,宋明儒虽然如先秦儒一样要积极面对人生现实,但他们因受佛家影响,总爱把人生现实的价值安放在整个宇宙里去衡量,如此则常觉得人生渺小与浮弱。他们总想在现实人生外去寻找宇宙万物共同的本体。如此人生现实依然渺小、浮弱。因此他们的意境多少带有几分悲观消极,不如先秦儒那样人生多面活动的活泼与强壮。换句话说,用《大学》八条目分析,宋明儒似乎对诚意、正心工夫用得多,以修身齐家为宗旨,而对上面治国平天下工夫用得少。汉唐儒及北宋初期诸儒可以说对治国平天下工夫用得多一些,对诚意正心工夫不如理学更注重,更深入。“如此言之,先秦儒以下,终是向外工夫胜过了向内,而到宋明理学诸儒则终是向内工夫胜过了向外。”这是钱穆研究宋明儒得出的结论。
综上所述,钱穆对理学思想的研究既有得也有失。得的方面:(1)重视从总体上把握宋明理学的特征及其基本精神,并在中国思想史、儒学发展史大视野中予以定位,使人对宋明理学的特点、基本精神以及历史地位一目了然。(2)重视从史学角度研究理学,侧重研究理学诸家、诸学派先后师承关系以及学术渊源,揭示了他们不同的特点,以及学术流变的轨迹。这种不把理学家思想平铺开来,而把他们之间看成是有联系的、有序的系统的思想,体现了他治学一贯贵通的学术风格。(3)坚持从中国思想史本身出发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克服了那种以西学剪裁中学的简单公式法。这对当前研究中国哲学史有方法论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从史学出发,过多地注重理学学术的流变、师友渊源,而对诸家的思想横向诠释或共时性分析的深度不够。另外,在理学研究专著体裁上多少有学案体的遗迹,引证原文偏多,理论分析少了一些。这与他早年读夏曾佑书的影响有关。
§§第7章 每转而益进 途穷而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