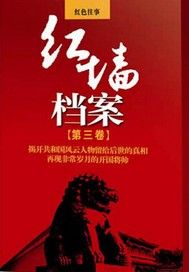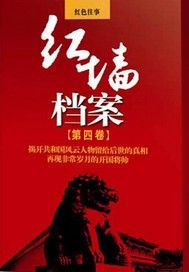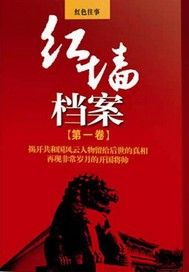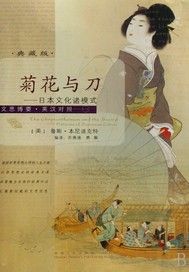6.4 集孔子以来之大成者:朱子
钱穆指出,南渡以来,可以说是宋学发展的第三期。南渡后的政治方面较之北宋相差甚远。但在学术思想方面却毫不逊色。就朱熹一人而论,已是掩盖北宋两期诸儒之长而有余。朱熹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杰出通儒,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承续北宋欧阳修一派综汇儒学一脉而来。朱子学可以说是以综汇之功而完成其别出之大业者。朱熹有两个反对者,一是吕东莱的史学,另一个是陆象山的心学。如果说周敦颐、张载、程氏兄弟是儒学的别出者,那么陆象山则是别出派中的尤其别出者。但以后的儒学是朱熹一派得势。毫不夸张地说,正统的宋学完成在他手里。南宋在短暂的偏安中,学术界有这样的成绩,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
钱穆的一些著作,如《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都辟专章或专题对朱熹学术思想加以论述。尤其是他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是他研究朱子思想的总结。全书五巨册,约百万字,作于1964年至1970年间,初版于1971年。书前有长篇《朱子学提纲》,集中表达了作者的儒学史观和朱子学观。全书主要分思想之部和学术之部。思想之部又分理气与心性两部分。学术之部,分经、史、文学三部分。经学中分《易》、《诗》、《书》、《春秋》、《礼》、《四书》诸题。又于三部外添附校勘、考据、辨伪诸篇,并游艺格物之学一篇。介乎思想与学术两部之间者,又分朱子评述濂溪、横渠、二程诸篇,下逮评程门、评五峰、评浙学,又别著朱陆异同三篇,辟禅学两篇等,专以发明朱子在当时理学界中之地位。全书专就朱子原书叙述朱子,而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称引最详。钱穆评述朱子,尤重在指出其思想学术的变化与发展。在每一分题下,论述每一个或每一对范畴或命题,并不专重其最后所归之结论,而必追溯其前后首尾往复之演变。钱穆全面评述了朱熹的学术成就,指出:“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故谓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学之大成,其言决非过夸而逾量。”
钱穆抉发朱子在理气论与心性论诸方面的创新,肯定了朱学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兼重工夫与本体。钱穆分疏了朱子与二程的异同及朱子对程门之纠弹,对朱陆异同的疏理,尤为细腻。此书意在破门户,认为朱子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钱先生对朱子思想行事及重要的语录、书信都有所考证,指明年代,对全祖望《宋元学案》、王白田《朱子年谱》,多有纠正。
一、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般意见认为,朱熹只是理学集大成者,是对孔子学说的第二次改造(第一次是董仲舒),不把朱子与孔子并提。钱穆则突出朱熹在历史上的地位,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看作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具有纲领性的评价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围绕着这个对朱熹的总评价,钱穆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论证。
首先,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完成在朱熹手里。北宋时期的理学诸家,只有伊洛程门这一派弟子众多,颇有传人。南宋时期的朱子理学正是由程门传来。但朱熹开始推崇周敦颐,并奉他为理学开山,确认二程的学术师承于周敦颐。他看到当时的学人对周敦颐轻视,便为弘扬周敦颐的学说做了许多工作,如对周敦颐生平加以考查,对其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作注解。后人重新了解周敦颐其人的始末,以及学问的底蕴,都是朱熹的功劳。至于说到周程传统的确立,虽然开始于胡宏,但完成在朱熹手中。朱熹也十分推崇张载。二程对张载的《西铭》篇非常重视,但程颢说《西铭》只是造道之言。程颐也说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他们对张载的《正蒙》很轻视。朱熹则推崇《正蒙》,认为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比二程高明。程颐说“神化”等,不如张载说得分明。张载的工夫论也精于二程。朱子还为张载的《西铭》做论解,并为自己的学生讲授《太极图说》和《西铭》。后人谈到北宋理学必然兼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这都是朱熹的功劳。
钱穆还指出,朱熹对于北宋理学,不仅能会通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位理学大师,使之会归合一,而且又扩大了理学的范围,涉及邵雍和司马光两人,并特地为这六位先生作画像赞,以邵雍、司马光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举齐尊。朱熹对于邵雍的象数学非常欣赏。邵雍又通过数学研究历史,朱熹也欣赏邵雍的史学。朱熹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序,其目的在于通过史学来扩大理学的范围。因此,朱子虽然是理学大宗师,其名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重,后人称为濂、洛、关、闽,但朱熹的理学视野,与北宋这四家相比,更为开阔,称朱熹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者,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朱熹集宋学之大成。钱穆认为,朱熹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也集宋学之大成。他所谓的宋学,是指理学产生以前的北宋诸儒之学。其学术包括政事治道、经史博古和文章子集等方面。朱熹对北宋儒学的政事治道、经史博古和文章子集之学都有承传阐扬,克服了理学初期只重心性修养工夫,不重政务、经史、文章及其他的片面性,大有返回宋初诸儒治学的风格。这是其他理学家所不及的。
从政事治道方面看,朱熹是理学当中最突出的。他对国事念念不忘,屡向孝宗直谏,无所忌讳。其议论光明正大,指陈实事求是,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就是与北宋诸儒及古今名贤的大奏议相比,也堪称一流。他在地方州郡政务方面颇有政绩。如淳熙五年(1178年),他被任命“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次年该地发生灾荒,他在解决饥民缺食、修筑石堤及办学等事务方面,颇为干练。又如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发生饥荒,孝宗派他提举浙东,他即单车就道,细访民隐,于救荒之外,随事处划,必为经久之计。再如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要求核实田亩,画图造册,希望纠正贫富“田税不均”的弊政。
再次,朱熹集汉唐儒之大成。钱穆研究理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强调了汉唐儒与宋儒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总体上说,汉唐儒学主要在经,可以说当时的儒学就是经学。宋代儒学不局限于经,而是文史百家之学与经学并举,经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说宋儒是一种新儒学。汉唐儒的经学特点在于章句论疏,宋儒的经学不局限于此,重要在于创新义,发新论,也可以说宋儒经学是一种新经学。朱子把经学与理学结合起来,不仅创造出一个新经学,而且也开掘出一个新理学。
钱穆的研究表明,朱熹不仅集北宋时期理学主要思想流派之大成,而且也是自从宋朝以来称之为新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设计师和汉唐以来儒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只把朱熹局限于南宋,作为南宋思想家来研究是十分不够的。正如先秦儒学的出现是由于周朝封建制度走向崩溃作出自觉的反应,并在春秋时期导致了反对腐朽贵族势力的勇敢斗争一样,理学的兴起也应当看作是儒学在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和佛教的挑战时的一种自我觉醒。很显然,北宋诸儒十分通晓国家事务,并努力维护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经学和历史传统。所以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良运动,胡瑗、孙复和李觏的经学,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历史编纂,以及他们全体的文学著作,都成了朱熹学术的思想资源。
另外,钱穆在研究中,强调了汉儒与宋儒、宋代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打通了汉唐儒与宋儒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把宋儒与理学区别开来,这就防止了夸大汉唐儒与宋儒对立,以及把宋儒与理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并明确宋儒具有返回先秦子学儒的基本精神。这些都是钱穆的独到之处。
二、经史与理学有机结合
在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的方方面面,朱子都有建树。
当时的二程和张载是以理学说经,而宋初诸儒则是以经学说经。如果把经学和理学分为两门学科,那么,朱熹的理学是承袭了二程和张载,而他的经学则继承了宋初诸儒。能把经学与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发端于朱子。在史学方面,朱熹不仅承接司马光,而且超过司马光。朱子把理学与史学结合起来,以史学扩大理学的研究视野。
从文章子集方面看,朱熹也多有研究。对于文学,理学家是加以鄙视的。只有朱子重视并擅长文章。朱子对于诗也有独到见解,超越唐宋,上追选体,以旧风格表现新意境。至于子集之学,周敦颐只称颜回,二程以孟子为限断,虽然自称泛滥于百家,但对百家并没有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北宋诸儒大都遵循韩愈而加以推衍,在两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隋唐举出王通和韩愈,认为这就是儒学的道统。朱子对这些人多有批评、承续。另外,对老庄道家也多有发挥,并不全加废弃,对于佛学禅宗进行批判。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几乎全渊源于朱熹。
当时理学的风气,读书只重视书中的大义,由此出发自立新说,新说兴起得越多,传统越脱落。这种风气在北宋诸儒那里也在所难免,而理学家更为严重。只有朱熹,一方面最能承守传统,另一方面也能发明创造新义。他为经作注解,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的著作,都务求句句了解,字字弄清,这正是汉儒传经章句训诂工夫。只求发现书中的本义与真相,丝毫不容主观臆断之说掺杂在其中。这也是经学的传统工夫。明白前人本意,与发挥自己新意并不互相妨碍。因此,钱穆强调经学与理学重在相济,不在相互独立。合则两美,分则两损。这正是朱熹学术的精神所在。
进一步说,朱子治经,承袭北宋诸儒并在创新义、发新论上超过了北宋儒学。同时他也十分尊重汉唐经学的传统。他对于经学,虽力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也采纳北宋诸儒,又借鉴理学乃至南宋与他同时代人的成果。其用意是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果实。钱氏认为,朱子的经学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只有郑玄能与之相比。然而两人时代不同,朱熹晚郑玄一千年,其学术思想更新。朱子不仅想要创造出一个新经学,而且也想要发掘出一个新理学。
先秦儒学虽然原本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人称经学;但儒学与经学不同,两汉经学代替儒学,宋儒又从旧的经学中脱离而重新建立新儒学和新经学。朱熹是这项事业的完成者。
朱熹治经,一方面遵循汉唐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董理,力戒凭自己主观臆测;另一方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钱穆指出,朱子据《易经》作《易本义》一书,认为《易》原是一部卜筮之书,因而重视象数,力求经文本义。程颐的《易传》是从理学来说《易》,不讲象数。朱熹则是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前人研究易学分为象数、卜筮、孔子十翼三派,还有《参同契》所讲的养生之类,朱子皆加以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学者少见。
钱穆指出,朱子治《诗》有自己独特的解《诗》功夫。朱子考证出《诗小序》不可信,在诗学上“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在书学上指出伏生与孔安国两家今古文的同异,“开出后来明清学者断定《尚书》古文之伪一案”;在易学上“主张易为卜筮之书”。这三者“同为经学上之三大卓见”。朱子治《春秋》,强调《春秋》为史书。朱子对《礼》也有卓立之见。
钱穆还把朱子经学与清代经学作比较,突出朱子治经的特点:(1)朱子治经,分别诸经加以考研,找出诸经内在特殊性,这是治经的特殊方法和特殊意义所在。而清儒忽视诸经,认为都是孔氏遗书,所以主张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这种说法似乎重会通,然而无分别,哪里有会通可言?(2)朱子治经,除经本书外,必兼顾汉唐以后至宋代诸家的说法,并会通求之。而清儒则重限断,这样造成争门户,不复辨是非。(3)朱熹说经对其反对者的思想加以采纳。清儒相反,对采纳委曲闪避,就是沿用也不提其名。(4)朱子治经不乏独见,清儒不加理会。清儒只根据汉唐古注疏,好像没有朱子书。(5)朱子论《尚书》、《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经之意,清代史学则只成经学附庸,治史也只如治经,不见有大区别。
钱穆在阐述朱子四书学时,强调以四书代五经的重要意义。在宋代理学家心目中,四书也是经学,而四书地位,与其他经书相比更为重要。首先提出四书并赋予极崇高地位的是二程和朱熹。(当然,朱子解《论语》、《孟子》与二程有不少差别。)尤其是朱子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一系统,并以毕生的精力为《论语》、《孟子》作集注,为《大学》、《中庸》作章句,四书学于是大兴。元、明两朝乃至清末七百年,朝廷取士,大体上以朱子论四书为圭臬,学者论学也以朱子四书为准绳。《四书集注》在后来七百年间成为必读书,地位越出五经之上,不应仅以科举取士来解释。朱子对四书的毕生研究是有成就的。钱穆指出,朱子论四书,正犹孔子修六经,孔子修六经未必有其事,而朱子论四书其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以四书地位来代替五经地位,实质上是以当时理学来代替汉唐经学。
钱穆还进一步分析朱子四书学的特点。朱子以前的理学家,研究《论语》、《孟子》以孔孟语录作开端,接着再阐发自己的见解。这显然缺乏一种经学精神,势必使理学与儒学传统相脱节。而朱子四书学重在就《论语》、《孟子》本文,务求发挥其正义,而力戒自己主观臆断,然后孔孟儒学的大传统得以奠定。这是一种经学精神。然而在朱子注《大学》、《中庸》章句中,终不免有许多自立说之处,这是一种理学精神。由此看出,朱子四书学使经学与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经学日益完善、邃密,也使理学日益精细、深沉。
钱穆对朱子的史学、文学和杂学都一一作了研究。他指出,在理学家中,能精通史学的只有朱熹一人。朱子对著史、论史和考史三方面均有建树。朱子著有《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等,均为佳作,对后人写史启发很大。朱子也擅长论史,其论史包括论治道、论心术、论人才、论世风四方面,这些都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朱子还见长于考史,他的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对天文、历法、地理、风俗、陈法、衣冠制度等一一考证。朱子对于文学有文道合一论,以文学通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于史学。朱子的杂学分为游艺与格物两项。其他理学家视为旁门,只有朱子力主博通,又其兴趣横逸,格物穷理,范围无所不包,故其学似乎不免出于杂。另外,钱穆也论述了朱子的办书院讲学的事迹与教育思想,以及朱子的读书功夫、方法等。
钱穆对朱子学术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克服了研究者由于专业所限在治朱子学术思想时所出现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钱氏从经史子集角度去阐发统摄朱子学术,为他画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肖像。钱穆为什么着力阐扬朱子?因为朱子能吞吐百家,汇纳众流。朱子学术特点与钱穆追求的学术风格有近似之处,换言之,通过对朱子学术全景式的研究,我们也看到钱穆治学贵在贯通的特点。
钱穆在研究朱子学术上也充分展示了他治学考据义理并重的特点。钱穆研究朱子,首先贯通朱子全书,发掘思想史问题,后将朱子每一书每一篇每一条重要语录,可以系年的系年,可以系月的系月,一一加以考证。他关于校勘、考据、辨伪诸篇,更反映出他治学义理与考据并重,以及训诂钩沉艰深之功力。考据之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于考据,二者是相通相合的。
钱穆的研究表明:两宋诸儒学术尽管派别分歧存在,但有两点精神是共同的。第一,他们都想重新阐明以往中国学术的大传统,来树立一个指导政治和教育的大原则,好以此来达成他们理想的新社会与新人生。其次,他们无不深切地注意到一切学问和治平最后关键都在人的心,所以他们对于人类心理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尤其特别赋以深厚的兴趣,而在此方面的贡献也非常大。第一种精神比较开展而阔大,第二种精神比较凝敛而缜密。在北宋初期,大家兴趣比较偏在第一点,但经过范仲淹和王安石两次政治改革失败,大家的兴趣便转向到第二点。他们认为,如果在社会下层学术心术基础没有打稳固,急于要在上层政治图速效,那是无把握的危险事。这是中期宋学的态度。南渡以后,这一方面几乎已发展到尽头,显露出内部的破绽与裂痕。又加上政治颓败,国势衰危,逼得他们转移目光,重新注意到第一点,尤其是历史与制度方面的讨论和研究。这种学风如果上面面临着一种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金元),无疑,决不能发皇畅遂,而必然会曲折改变其面貌,转移到其他方面,渐渐忘却了原有的精神。
三、理气与心性一体浑成
钱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以理气论和心性论两个方面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展开。他指出:“叙述朱子思想,首先当提出其主要之两部分。一为其理气论,又一为其心性论。理气论略当于近人所谓之宇宙论及形上学。心性论乃由宇宙论形上学落实到人生哲学上。”有一些朱子学研究者在研究朱子思想时,把朱子诸思想范畴平铺开来,分别加以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只见目不见纲,只见分散不见朱子思想的核心与基本精神。钱穆以理气与心性两对范畴来统摄、疏理其它范畴,建立朱子学体系,其结果揭示了朱子思想的真谛和基本精神。这也体现了钱氏一贯倡导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学术风格。
在理气论或宇宙论中,钱穆考察理气论的形成、特点,以及理与气的关系。他认为朱子的理气论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周敦颐和张载宇宙论继承发展的产物。朱熹的理气论主要根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正蒙》。周敦颐只讲太极与阴阳,这是继承《周易》的说法。朱熹换了两个新名词,用理与气取代它。说“物物一太极”,不如说“物各有理”更恰当。张载说太虚与气,太虚不如“无极太极”深刻、确切。因此朱熹理气论根据周敦颐太极说而对张载太虚之说加以辨正。说“虚”不如说“理气”,但单说理则仍是虚。程颢及以后的理学家多以天理人欲对称,这是指人心人事,与朱子说的理气之气有高低广狭之不同。因此朱熹的理气论是对周敦颐和张载之说结合的创新。朱熹的宇宙论也兼通易与道,但与道家不同。道家主张本于自然。朱子理气论则认自然只是一道,所以说有气则必有理。在宇宙形上学,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但一落实到人生形下界,人却可以凭借这种理来造作,理就变成了有作用的。如此,则又从老庄道家转回到孔孟儒学来。
钱穆进一步揭示朱子的理与气之辩证关系,认为朱子论宇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气指其实质部分,理则相当于寄寓在此实质内之性,或者可以说是实质之内一切的条理与规模。朱熹虽然把理气分开说,但认为它们是一体浑成,而非两体对立。这是朱子理气论的宗旨。朱熹把这一点归于周敦颐的太极说。如果说理气有先后,那么朱子必然说理先而气后,但朱子也不是说今日有此理明日有此气,虽然有先后,还是一体浑成,并无时间上的相隔。因此,朱子的宇宙论,既不主张唯气,也不主张唯理,更不主张理气对立,而主张理气只是一体。
在人生哲学方面,钱穆分析朱熹的心与性、心性与理气之间的关系,打通理气论与心性论。他认为,性属理,心属气,必须先明白了朱子的理气论,才能研究朱子的心性论。
朱子对程颐的“性即理”有深入体会。理是天地公共的,性是人物各别的。理属于先天,性属于后天,由理降落为性,已是移下了一层次。朱熹一方面认为理气合一,由此说性气不离,另一方面又主张理气分言,因此说性气不能混淆。但万物的性,各为其形气所束缚,因此不能达到天地公共的理上去,只有人性可以不为形气所限制,由己性直通于天理。但要有一番工夫,即心理工夫。这是从人生角度来谈的。如果从宇宙角度来看,则无工夫可用。只有在人生方面用工夫,才会打通宇宙界。如果只囿于人生界,而违背宇宙界,那么一切工夫均是徒劳的。在朱子看来,宇宙与人生是一体两分,非两体对立,其通处正是“性”。性是体,其发而为工夫则在心,心属用。朱子说性即理,又说性气不相离,也不相混淆,便又把张载、程氏兄弟所言的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给全部融化了。
接着,钱穆又对朱熹的“心”范畴进行研究。他强调:“朱子论宇宙界,似说理之重要性更过于气。但论人生界,则似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则更重在工夫,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尤更重要。”但不能说朱子认为心重要,就说他接近唯心论,因为心只属于气。他既不主张唯气,自然也不主张唯心。就宇宙论而言,理离不开气;就人生论而言,理又离不开知觉,即理离不开心。心是气之灵,只有人类才有这气之灵,所以能有此心,能觉此理。心所觉全是理,满心全是理,这就达到了心即理的境界。这里的心所觉的理,不仅是自然宇宙,也是人生文化方面的理。人生文化方面的理,也即在宇宙自然之理中。人心能明觉到这种理,一面可以自尽己性,一面又可以上达天理,既可以弘扬文化,也可以宣赞自然。儒家不同于老释的精义,理学家的终极目标都在于此。后人多认为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由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从钱穆的论述看出,这一区别并不恰当。理学家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朱子正是通过对心的论述,把宇宙与人生、理气与心性结合起来。钱穆不赞成理学心学之二分法,认为朱子之学其实是一种更加圆密宏大之心学,并就朱子对心之特点、作用、活动过程,心与理、心与性情、心与知觉的相互关系作了精到的研究,也对朱子早期、中期、晚期的心学思想作了周到的考证。朱子的这些思想,较之陆学对心的研究更为细致具体。
钱穆在总结朱子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关系时指出:“以上略说朱子之理气论与心性论。在此,朱子已尽力指陈了心之重要。在人生界中之心,正可与在宇宙界中之理相匹配。而就人生界论人生,则心之重要更过于理。因理是已存底,而心则是待发底。也可谓理属体,心则主要在用,在工夫论上,故尤为理学家所重视。所以说,谓陆王是心学,程朱是理学,此一分别,未为恰当。若说陆王心学乃是专偏重在人生界,程朱理学则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如此言之,庶较近实。”
以理气论和心性论为轴心,钱穆对朱子的其他哲学范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分别论述了宇宙的仁和神。如果说理气是宇宙的体,仁神则是宇宙的用。只有把这四者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朱子宇宙论的全貌。在仁神的造化中,人是最有灵气的,在人中圣人上合天德。如何能成为圣人?要成圣人就必须有圣人之心,圣心通天心在于仁,这种仁是宇宙之仁和人心之仁的统一。要做到人心之仁,就必须诚。朱子的诚也分宇宙、人心两方面。仁与诚是天赋人而为的,是心的本体,然而心有不仁不诚的时候,由此论述了天理人欲论和道心人心论,这些都是理气论与心性论的具体化。
钱穆还强调理气论和心性论的联结处,即心或工夫论的重要性。朱子的工夫论分两方面展开。一是致知。围绕致知,钱氏阐述了朱子的敬、静、已发与未发等范畴。一是格物。致知在格物,格物是零细的工夫,而知致才能得总体。钱穆对朱子工夫论的论述不仅在于贯通理气与心性,更重要的在于高扬主体自觉的精神。
钱穆从理气与心性浑然一体出发研究朱子思想体系,颇有启发意义。
(1)突出了中国哲学两大主题。钱穆注意到朱子思想诸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理解朱熹思想最主要、最基本的范畴(理气与心性),去统摄其他范畴,这样建构了和谐有序的朱子思想范畴体系。他所着重研究的理气论和心性论不仅是朱子理学的主题,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主题。突出这个主题,不仅对朱熹哲学思想研究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哲学史的宏观研究也有启发。
(2)超越西方思想中的物质和精神两极对立,把握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学者们认为朱子的形而上学,讲的是理气二元论,不是一元论。理气虽然可以分开来说,但也绝不是两体对立的。既然不是两体对立的,那么就无所谓谁先谁后的问题。如果一定要问先后的话,那么就宇宙论而言,理在气先,就人生论而言,气在理先。钱穆根据这种绝对与相对的关系,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一些学者对理气是二元还是一元的争论,也杜绝了凡治中国哲学必先言物质和意识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的二项式思维方式。钱穆打通了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界限,把宇宙观与人生观、宇宙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个境界不仅是朱子,也是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3)破除了理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强调理学诸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关于理气合一论的思想,把二程与张载统一起来;关于理气心性合一论,则泯合了朱熹与陆象山之间的门户之见。例如明清王学所谓“朱陆始异终同”、“朱子晚年从陆之悔”等,则不攻而自破。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不无意义。
当然,宋代理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对于理、气、心、性等范畴的理解,在本体与方法上,各学者、各学派,既有所同,更有所异。张程之间、程朱之间、朱陆之间的差别,并不都是门户之见。重视所同,又重视同中之异,统一中之差别,正能窥见宋代学术之繁盛。理学本身也是多样的,如此才有内在的张力,才能促使理学思潮的发展。
事实上,我们从钱先生详实的考证中,可以看出朱子与周敦颐、张载、二程思想的异同,朱子与东莱、南轩、象山思想的异同等等。其间的差别,不仅有经学方面的,而且也有理学方面的。至于朱子思想的流变过程,朱子上与汉唐、下与明清诸儒的联系与区别,《朱子新学案》中也有详考。
钱穆的一些著作,如《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都辟专章或专题对朱熹学术思想加以论述。尤其是他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是他研究朱子思想的总结。全书五巨册,约百万字,作于1964年至1970年间,初版于1971年。书前有长篇《朱子学提纲》,集中表达了作者的儒学史观和朱子学观。全书主要分思想之部和学术之部。思想之部又分理气与心性两部分。学术之部,分经、史、文学三部分。经学中分《易》、《诗》、《书》、《春秋》、《礼》、《四书》诸题。又于三部外添附校勘、考据、辨伪诸篇,并游艺格物之学一篇。介乎思想与学术两部之间者,又分朱子评述濂溪、横渠、二程诸篇,下逮评程门、评五峰、评浙学,又别著朱陆异同三篇,辟禅学两篇等,专以发明朱子在当时理学界中之地位。全书专就朱子原书叙述朱子,而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称引最详。钱穆评述朱子,尤重在指出其思想学术的变化与发展。在每一分题下,论述每一个或每一对范畴或命题,并不专重其最后所归之结论,而必追溯其前后首尾往复之演变。钱穆全面评述了朱熹的学术成就,指出:“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故谓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学之大成,其言决非过夸而逾量。”
钱穆抉发朱子在理气论与心性论诸方面的创新,肯定了朱学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兼重工夫与本体。钱穆分疏了朱子与二程的异同及朱子对程门之纠弹,对朱陆异同的疏理,尤为细腻。此书意在破门户,认为朱子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钱先生对朱子思想行事及重要的语录、书信都有所考证,指明年代,对全祖望《宋元学案》、王白田《朱子年谱》,多有纠正。
一、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般意见认为,朱熹只是理学集大成者,是对孔子学说的第二次改造(第一次是董仲舒),不把朱子与孔子并提。钱穆则突出朱熹在历史上的地位,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看作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具有纲领性的评价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围绕着这个对朱熹的总评价,钱穆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论证。
首先,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完成在朱熹手里。北宋时期的理学诸家,只有伊洛程门这一派弟子众多,颇有传人。南宋时期的朱子理学正是由程门传来。但朱熹开始推崇周敦颐,并奉他为理学开山,确认二程的学术师承于周敦颐。他看到当时的学人对周敦颐轻视,便为弘扬周敦颐的学说做了许多工作,如对周敦颐生平加以考查,对其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作注解。后人重新了解周敦颐其人的始末,以及学问的底蕴,都是朱熹的功劳。至于说到周程传统的确立,虽然开始于胡宏,但完成在朱熹手中。朱熹也十分推崇张载。二程对张载的《西铭》篇非常重视,但程颢说《西铭》只是造道之言。程颐也说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他们对张载的《正蒙》很轻视。朱熹则推崇《正蒙》,认为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比二程高明。程颐说“神化”等,不如张载说得分明。张载的工夫论也精于二程。朱子还为张载的《西铭》做论解,并为自己的学生讲授《太极图说》和《西铭》。后人谈到北宋理学必然兼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这都是朱熹的功劳。
钱穆还指出,朱熹对于北宋理学,不仅能会通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位理学大师,使之会归合一,而且又扩大了理学的范围,涉及邵雍和司马光两人,并特地为这六位先生作画像赞,以邵雍、司马光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举齐尊。朱熹对于邵雍的象数学非常欣赏。邵雍又通过数学研究历史,朱熹也欣赏邵雍的史学。朱熹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序,其目的在于通过史学来扩大理学的范围。因此,朱子虽然是理学大宗师,其名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重,后人称为濂、洛、关、闽,但朱熹的理学视野,与北宋这四家相比,更为开阔,称朱熹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者,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朱熹集宋学之大成。钱穆认为,朱熹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也集宋学之大成。他所谓的宋学,是指理学产生以前的北宋诸儒之学。其学术包括政事治道、经史博古和文章子集等方面。朱熹对北宋儒学的政事治道、经史博古和文章子集之学都有承传阐扬,克服了理学初期只重心性修养工夫,不重政务、经史、文章及其他的片面性,大有返回宋初诸儒治学的风格。这是其他理学家所不及的。
从政事治道方面看,朱熹是理学当中最突出的。他对国事念念不忘,屡向孝宗直谏,无所忌讳。其议论光明正大,指陈实事求是,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就是与北宋诸儒及古今名贤的大奏议相比,也堪称一流。他在地方州郡政务方面颇有政绩。如淳熙五年(1178年),他被任命“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次年该地发生灾荒,他在解决饥民缺食、修筑石堤及办学等事务方面,颇为干练。又如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发生饥荒,孝宗派他提举浙东,他即单车就道,细访民隐,于救荒之外,随事处划,必为经久之计。再如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要求核实田亩,画图造册,希望纠正贫富“田税不均”的弊政。
再次,朱熹集汉唐儒之大成。钱穆研究理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强调了汉唐儒与宋儒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总体上说,汉唐儒学主要在经,可以说当时的儒学就是经学。宋代儒学不局限于经,而是文史百家之学与经学并举,经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说宋儒是一种新儒学。汉唐儒的经学特点在于章句论疏,宋儒的经学不局限于此,重要在于创新义,发新论,也可以说宋儒经学是一种新经学。朱子把经学与理学结合起来,不仅创造出一个新经学,而且也开掘出一个新理学。
钱穆的研究表明,朱熹不仅集北宋时期理学主要思想流派之大成,而且也是自从宋朝以来称之为新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设计师和汉唐以来儒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只把朱熹局限于南宋,作为南宋思想家来研究是十分不够的。正如先秦儒学的出现是由于周朝封建制度走向崩溃作出自觉的反应,并在春秋时期导致了反对腐朽贵族势力的勇敢斗争一样,理学的兴起也应当看作是儒学在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和佛教的挑战时的一种自我觉醒。很显然,北宋诸儒十分通晓国家事务,并努力维护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经学和历史传统。所以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良运动,胡瑗、孙复和李觏的经学,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历史编纂,以及他们全体的文学著作,都成了朱熹学术的思想资源。
另外,钱穆在研究中,强调了汉儒与宋儒、宋代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打通了汉唐儒与宋儒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把宋儒与理学区别开来,这就防止了夸大汉唐儒与宋儒对立,以及把宋儒与理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并明确宋儒具有返回先秦子学儒的基本精神。这些都是钱穆的独到之处。
二、经史与理学有机结合
在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的方方面面,朱子都有建树。
当时的二程和张载是以理学说经,而宋初诸儒则是以经学说经。如果把经学和理学分为两门学科,那么,朱熹的理学是承袭了二程和张载,而他的经学则继承了宋初诸儒。能把经学与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发端于朱子。在史学方面,朱熹不仅承接司马光,而且超过司马光。朱子把理学与史学结合起来,以史学扩大理学的研究视野。
从文章子集方面看,朱熹也多有研究。对于文学,理学家是加以鄙视的。只有朱子重视并擅长文章。朱子对于诗也有独到见解,超越唐宋,上追选体,以旧风格表现新意境。至于子集之学,周敦颐只称颜回,二程以孟子为限断,虽然自称泛滥于百家,但对百家并没有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北宋诸儒大都遵循韩愈而加以推衍,在两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隋唐举出王通和韩愈,认为这就是儒学的道统。朱子对这些人多有批评、承续。另外,对老庄道家也多有发挥,并不全加废弃,对于佛学禅宗进行批判。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几乎全渊源于朱熹。
当时理学的风气,读书只重视书中的大义,由此出发自立新说,新说兴起得越多,传统越脱落。这种风气在北宋诸儒那里也在所难免,而理学家更为严重。只有朱熹,一方面最能承守传统,另一方面也能发明创造新义。他为经作注解,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的著作,都务求句句了解,字字弄清,这正是汉儒传经章句训诂工夫。只求发现书中的本义与真相,丝毫不容主观臆断之说掺杂在其中。这也是经学的传统工夫。明白前人本意,与发挥自己新意并不互相妨碍。因此,钱穆强调经学与理学重在相济,不在相互独立。合则两美,分则两损。这正是朱熹学术的精神所在。
进一步说,朱子治经,承袭北宋诸儒并在创新义、发新论上超过了北宋儒学。同时他也十分尊重汉唐经学的传统。他对于经学,虽力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也采纳北宋诸儒,又借鉴理学乃至南宋与他同时代人的成果。其用意是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果实。钱氏认为,朱子的经学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只有郑玄能与之相比。然而两人时代不同,朱熹晚郑玄一千年,其学术思想更新。朱子不仅想要创造出一个新经学,而且也想要发掘出一个新理学。
先秦儒学虽然原本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人称经学;但儒学与经学不同,两汉经学代替儒学,宋儒又从旧的经学中脱离而重新建立新儒学和新经学。朱熹是这项事业的完成者。
朱熹治经,一方面遵循汉唐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董理,力戒凭自己主观臆测;另一方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钱穆指出,朱子据《易经》作《易本义》一书,认为《易》原是一部卜筮之书,因而重视象数,力求经文本义。程颐的《易传》是从理学来说《易》,不讲象数。朱熹则是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前人研究易学分为象数、卜筮、孔子十翼三派,还有《参同契》所讲的养生之类,朱子皆加以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学者少见。
钱穆指出,朱子治《诗》有自己独特的解《诗》功夫。朱子考证出《诗小序》不可信,在诗学上“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在书学上指出伏生与孔安国两家今古文的同异,“开出后来明清学者断定《尚书》古文之伪一案”;在易学上“主张易为卜筮之书”。这三者“同为经学上之三大卓见”。朱子治《春秋》,强调《春秋》为史书。朱子对《礼》也有卓立之见。
钱穆还把朱子经学与清代经学作比较,突出朱子治经的特点:(1)朱子治经,分别诸经加以考研,找出诸经内在特殊性,这是治经的特殊方法和特殊意义所在。而清儒忽视诸经,认为都是孔氏遗书,所以主张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这种说法似乎重会通,然而无分别,哪里有会通可言?(2)朱子治经,除经本书外,必兼顾汉唐以后至宋代诸家的说法,并会通求之。而清儒则重限断,这样造成争门户,不复辨是非。(3)朱熹说经对其反对者的思想加以采纳。清儒相反,对采纳委曲闪避,就是沿用也不提其名。(4)朱子治经不乏独见,清儒不加理会。清儒只根据汉唐古注疏,好像没有朱子书。(5)朱子论《尚书》、《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经之意,清代史学则只成经学附庸,治史也只如治经,不见有大区别。
钱穆在阐述朱子四书学时,强调以四书代五经的重要意义。在宋代理学家心目中,四书也是经学,而四书地位,与其他经书相比更为重要。首先提出四书并赋予极崇高地位的是二程和朱熹。(当然,朱子解《论语》、《孟子》与二程有不少差别。)尤其是朱子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一系统,并以毕生的精力为《论语》、《孟子》作集注,为《大学》、《中庸》作章句,四书学于是大兴。元、明两朝乃至清末七百年,朝廷取士,大体上以朱子论四书为圭臬,学者论学也以朱子四书为准绳。《四书集注》在后来七百年间成为必读书,地位越出五经之上,不应仅以科举取士来解释。朱子对四书的毕生研究是有成就的。钱穆指出,朱子论四书,正犹孔子修六经,孔子修六经未必有其事,而朱子论四书其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以四书地位来代替五经地位,实质上是以当时理学来代替汉唐经学。
钱穆还进一步分析朱子四书学的特点。朱子以前的理学家,研究《论语》、《孟子》以孔孟语录作开端,接着再阐发自己的见解。这显然缺乏一种经学精神,势必使理学与儒学传统相脱节。而朱子四书学重在就《论语》、《孟子》本文,务求发挥其正义,而力戒自己主观臆断,然后孔孟儒学的大传统得以奠定。这是一种经学精神。然而在朱子注《大学》、《中庸》章句中,终不免有许多自立说之处,这是一种理学精神。由此看出,朱子四书学使经学与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经学日益完善、邃密,也使理学日益精细、深沉。
钱穆对朱子的史学、文学和杂学都一一作了研究。他指出,在理学家中,能精通史学的只有朱熹一人。朱子对著史、论史和考史三方面均有建树。朱子著有《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等,均为佳作,对后人写史启发很大。朱子也擅长论史,其论史包括论治道、论心术、论人才、论世风四方面,这些都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朱子还见长于考史,他的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对天文、历法、地理、风俗、陈法、衣冠制度等一一考证。朱子对于文学有文道合一论,以文学通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于史学。朱子的杂学分为游艺与格物两项。其他理学家视为旁门,只有朱子力主博通,又其兴趣横逸,格物穷理,范围无所不包,故其学似乎不免出于杂。另外,钱穆也论述了朱子的办书院讲学的事迹与教育思想,以及朱子的读书功夫、方法等。
钱穆对朱子学术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克服了研究者由于专业所限在治朱子学术思想时所出现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钱氏从经史子集角度去阐发统摄朱子学术,为他画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肖像。钱穆为什么着力阐扬朱子?因为朱子能吞吐百家,汇纳众流。朱子学术特点与钱穆追求的学术风格有近似之处,换言之,通过对朱子学术全景式的研究,我们也看到钱穆治学贵在贯通的特点。
钱穆在研究朱子学术上也充分展示了他治学考据义理并重的特点。钱穆研究朱子,首先贯通朱子全书,发掘思想史问题,后将朱子每一书每一篇每一条重要语录,可以系年的系年,可以系月的系月,一一加以考证。他关于校勘、考据、辨伪诸篇,更反映出他治学义理与考据并重,以及训诂钩沉艰深之功力。考据之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于考据,二者是相通相合的。
钱穆的研究表明:两宋诸儒学术尽管派别分歧存在,但有两点精神是共同的。第一,他们都想重新阐明以往中国学术的大传统,来树立一个指导政治和教育的大原则,好以此来达成他们理想的新社会与新人生。其次,他们无不深切地注意到一切学问和治平最后关键都在人的心,所以他们对于人类心理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尤其特别赋以深厚的兴趣,而在此方面的贡献也非常大。第一种精神比较开展而阔大,第二种精神比较凝敛而缜密。在北宋初期,大家兴趣比较偏在第一点,但经过范仲淹和王安石两次政治改革失败,大家的兴趣便转向到第二点。他们认为,如果在社会下层学术心术基础没有打稳固,急于要在上层政治图速效,那是无把握的危险事。这是中期宋学的态度。南渡以后,这一方面几乎已发展到尽头,显露出内部的破绽与裂痕。又加上政治颓败,国势衰危,逼得他们转移目光,重新注意到第一点,尤其是历史与制度方面的讨论和研究。这种学风如果上面面临着一种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金元),无疑,决不能发皇畅遂,而必然会曲折改变其面貌,转移到其他方面,渐渐忘却了原有的精神。
三、理气与心性一体浑成
钱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以理气论和心性论两个方面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展开。他指出:“叙述朱子思想,首先当提出其主要之两部分。一为其理气论,又一为其心性论。理气论略当于近人所谓之宇宙论及形上学。心性论乃由宇宙论形上学落实到人生哲学上。”有一些朱子学研究者在研究朱子思想时,把朱子诸思想范畴平铺开来,分别加以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只见目不见纲,只见分散不见朱子思想的核心与基本精神。钱穆以理气与心性两对范畴来统摄、疏理其它范畴,建立朱子学体系,其结果揭示了朱子思想的真谛和基本精神。这也体现了钱氏一贯倡导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学术风格。
在理气论或宇宙论中,钱穆考察理气论的形成、特点,以及理与气的关系。他认为朱子的理气论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周敦颐和张载宇宙论继承发展的产物。朱熹的理气论主要根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正蒙》。周敦颐只讲太极与阴阳,这是继承《周易》的说法。朱熹换了两个新名词,用理与气取代它。说“物物一太极”,不如说“物各有理”更恰当。张载说太虚与气,太虚不如“无极太极”深刻、确切。因此朱熹理气论根据周敦颐太极说而对张载太虚之说加以辨正。说“虚”不如说“理气”,但单说理则仍是虚。程颢及以后的理学家多以天理人欲对称,这是指人心人事,与朱子说的理气之气有高低广狭之不同。因此朱熹的理气论是对周敦颐和张载之说结合的创新。朱熹的宇宙论也兼通易与道,但与道家不同。道家主张本于自然。朱子理气论则认自然只是一道,所以说有气则必有理。在宇宙形上学,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但一落实到人生形下界,人却可以凭借这种理来造作,理就变成了有作用的。如此,则又从老庄道家转回到孔孟儒学来。
钱穆进一步揭示朱子的理与气之辩证关系,认为朱子论宇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气指其实质部分,理则相当于寄寓在此实质内之性,或者可以说是实质之内一切的条理与规模。朱熹虽然把理气分开说,但认为它们是一体浑成,而非两体对立。这是朱子理气论的宗旨。朱熹把这一点归于周敦颐的太极说。如果说理气有先后,那么朱子必然说理先而气后,但朱子也不是说今日有此理明日有此气,虽然有先后,还是一体浑成,并无时间上的相隔。因此,朱子的宇宙论,既不主张唯气,也不主张唯理,更不主张理气对立,而主张理气只是一体。
在人生哲学方面,钱穆分析朱熹的心与性、心性与理气之间的关系,打通理气论与心性论。他认为,性属理,心属气,必须先明白了朱子的理气论,才能研究朱子的心性论。
朱子对程颐的“性即理”有深入体会。理是天地公共的,性是人物各别的。理属于先天,性属于后天,由理降落为性,已是移下了一层次。朱熹一方面认为理气合一,由此说性气不离,另一方面又主张理气分言,因此说性气不能混淆。但万物的性,各为其形气所束缚,因此不能达到天地公共的理上去,只有人性可以不为形气所限制,由己性直通于天理。但要有一番工夫,即心理工夫。这是从人生角度来谈的。如果从宇宙角度来看,则无工夫可用。只有在人生方面用工夫,才会打通宇宙界。如果只囿于人生界,而违背宇宙界,那么一切工夫均是徒劳的。在朱子看来,宇宙与人生是一体两分,非两体对立,其通处正是“性”。性是体,其发而为工夫则在心,心属用。朱子说性即理,又说性气不相离,也不相混淆,便又把张载、程氏兄弟所言的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给全部融化了。
接着,钱穆又对朱熹的“心”范畴进行研究。他强调:“朱子论宇宙界,似说理之重要性更过于气。但论人生界,则似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则更重在工夫,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尤更重要。”但不能说朱子认为心重要,就说他接近唯心论,因为心只属于气。他既不主张唯气,自然也不主张唯心。就宇宙论而言,理离不开气;就人生论而言,理又离不开知觉,即理离不开心。心是气之灵,只有人类才有这气之灵,所以能有此心,能觉此理。心所觉全是理,满心全是理,这就达到了心即理的境界。这里的心所觉的理,不仅是自然宇宙,也是人生文化方面的理。人生文化方面的理,也即在宇宙自然之理中。人心能明觉到这种理,一面可以自尽己性,一面又可以上达天理,既可以弘扬文化,也可以宣赞自然。儒家不同于老释的精义,理学家的终极目标都在于此。后人多认为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由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从钱穆的论述看出,这一区别并不恰当。理学家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朱子正是通过对心的论述,把宇宙与人生、理气与心性结合起来。钱穆不赞成理学心学之二分法,认为朱子之学其实是一种更加圆密宏大之心学,并就朱子对心之特点、作用、活动过程,心与理、心与性情、心与知觉的相互关系作了精到的研究,也对朱子早期、中期、晚期的心学思想作了周到的考证。朱子的这些思想,较之陆学对心的研究更为细致具体。
钱穆在总结朱子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关系时指出:“以上略说朱子之理气论与心性论。在此,朱子已尽力指陈了心之重要。在人生界中之心,正可与在宇宙界中之理相匹配。而就人生界论人生,则心之重要更过于理。因理是已存底,而心则是待发底。也可谓理属体,心则主要在用,在工夫论上,故尤为理学家所重视。所以说,谓陆王是心学,程朱是理学,此一分别,未为恰当。若说陆王心学乃是专偏重在人生界,程朱理学则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如此言之,庶较近实。”
以理气论和心性论为轴心,钱穆对朱子的其他哲学范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分别论述了宇宙的仁和神。如果说理气是宇宙的体,仁神则是宇宙的用。只有把这四者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朱子宇宙论的全貌。在仁神的造化中,人是最有灵气的,在人中圣人上合天德。如何能成为圣人?要成圣人就必须有圣人之心,圣心通天心在于仁,这种仁是宇宙之仁和人心之仁的统一。要做到人心之仁,就必须诚。朱子的诚也分宇宙、人心两方面。仁与诚是天赋人而为的,是心的本体,然而心有不仁不诚的时候,由此论述了天理人欲论和道心人心论,这些都是理气论与心性论的具体化。
钱穆还强调理气论和心性论的联结处,即心或工夫论的重要性。朱子的工夫论分两方面展开。一是致知。围绕致知,钱氏阐述了朱子的敬、静、已发与未发等范畴。一是格物。致知在格物,格物是零细的工夫,而知致才能得总体。钱穆对朱子工夫论的论述不仅在于贯通理气与心性,更重要的在于高扬主体自觉的精神。
钱穆从理气与心性浑然一体出发研究朱子思想体系,颇有启发意义。
(1)突出了中国哲学两大主题。钱穆注意到朱子思想诸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理解朱熹思想最主要、最基本的范畴(理气与心性),去统摄其他范畴,这样建构了和谐有序的朱子思想范畴体系。他所着重研究的理气论和心性论不仅是朱子理学的主题,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主题。突出这个主题,不仅对朱熹哲学思想研究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哲学史的宏观研究也有启发。
(2)超越西方思想中的物质和精神两极对立,把握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学者们认为朱子的形而上学,讲的是理气二元论,不是一元论。理气虽然可以分开来说,但也绝不是两体对立的。既然不是两体对立的,那么就无所谓谁先谁后的问题。如果一定要问先后的话,那么就宇宙论而言,理在气先,就人生论而言,气在理先。钱穆根据这种绝对与相对的关系,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一些学者对理气是二元还是一元的争论,也杜绝了凡治中国哲学必先言物质和意识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的二项式思维方式。钱穆打通了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界限,把宇宙观与人生观、宇宙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个境界不仅是朱子,也是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3)破除了理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强调理学诸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关于理气合一论的思想,把二程与张载统一起来;关于理气心性合一论,则泯合了朱熹与陆象山之间的门户之见。例如明清王学所谓“朱陆始异终同”、“朱子晚年从陆之悔”等,则不攻而自破。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不无意义。
当然,宋代理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对于理、气、心、性等范畴的理解,在本体与方法上,各学者、各学派,既有所同,更有所异。张程之间、程朱之间、朱陆之间的差别,并不都是门户之见。重视所同,又重视同中之异,统一中之差别,正能窥见宋代学术之繁盛。理学本身也是多样的,如此才有内在的张力,才能促使理学思潮的发展。
事实上,我们从钱先生详实的考证中,可以看出朱子与周敦颐、张载、二程思想的异同,朱子与东莱、南轩、象山思想的异同等等。其间的差别,不仅有经学方面的,而且也有理学方面的。至于朱子思想的流变过程,朱子上与汉唐、下与明清诸儒的联系与区别,《朱子新学案》中也有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