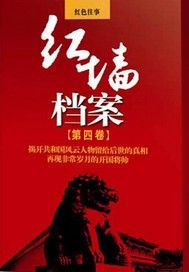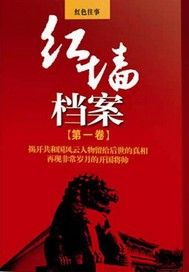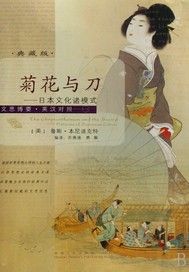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 第一节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春秋时期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第一节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春秋时期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一段极为著名的史料:“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几乎所有读史者都对此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段史料首先告诉人们血缘宗法制度下等级制度的组成,将人分为十等,似乎专门是为了与“天有十日”相对应,以至于后人开始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怀疑血缘宗法社会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复杂的等级关系。其次,这段史料同时告诉人们西周等级制度的森严,而且,这点才是这段史料的真正价值所在。
无独有偶,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了另一段同样的史料:“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
两段史料的出处在时间上前后相隔仅仅二十五年,但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却是翻天覆地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无论如何无法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相提并论,社会观念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至少,同样在《左传·昭公三年》,齐晏婴和晋叔向就分别对自己国家的前途表现出无限的担忧,甚至是绝望:“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事实证明,晏婴与叔向二人的议论并非杞人忧天,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姜齐的命运似乎好一些,比晋国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王迁到海边,他自己做了实际的国君,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封田和为齐国诸侯,田氏代齐。
问题并非仅仅如此,在周初以及后来陆续分封的诸侯方国中,其中绝大部分到春秋末期已经被强国所灭,即使是延续到战国时代的七强,也只有楚、秦两国国君的血统没有改变,正如《淮南子·览冥训》云:“晚世之时,七国异族。”高诱注:“七国,齐、楚、燕、赵、韩、魏、秦也。齐姓田,楚姓芈,燕姓姬,赵姓赵,韩姓韩,魏姓魏,秦姓嬴,故异族也。”读史至此,每每使人产生苍凉之感。所有这一切,无不在暗示着春秋年间的巨大变化。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烈变化,历代研究者极多,对某些时代特点也取得了共识,其中可以称为经典的首推顾炎武的《日知录·周末风俗》:“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顾氏在此描述的几大特点,甚至成为后来研究春秋战国史的总纲,历来研究者无不对此极为重视。但顾氏同时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本人认为,这句话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面的罗列。当然,离开史料,历史便无从谈起,所以,顾炎武这句话的用意无非是要后人仔细分析史料,从而找出各种材料之间内部的逻辑关系,以求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事实上,以上顾炎武所叙述的关于春秋战国之间的几大变化,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并列的。很明显,在上古时代对血缘关系极为重视的宗法社会中,宗姓氏族的意义无疑是其他社会因素的基础,换言之,有关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无不由血缘宗法关系的变化而引发,有关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也都是血缘宗法关系的变化在不同领域里的体现。
那么,通过现有的史料,我们再来分析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关于西周社会的阶级结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左传》和《国语》:
《左传·桓公二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左传·襄公九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很明显,通过分析以上史料,可以得知春秋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应该主要由贵族、国人、野人组成。
在一般意义上,贵族应该是指在血统上与周王室或各诸侯国君比较亲近、在宗法系统中属于各大宗或小宗的嫡系子孙,即王、公、大夫和士,也即社会统治阶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正是贵族身份和特权的证明。
而在现实生活中,判定某人是否具有贵族身份,固然要考虑他的祖宗曾经拥有的身份,但很多情况下更多依据的是他本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比如虽然孔子是“圣人之后”,但当“季氏飨士,孔子与往”,却遭阳虎斥退。“孔子要?,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对少年孔子而言,这件事给他所留下的屈辱和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
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同一始祖的后代,由于出生先后的差异,本身就有身份高低之分,当经过若干代的繁衍后,身份的差异更加明显。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礼记·大传》
有例为证,《礼记·礼运》有云:“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三个“子孙”的社会地位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根据宗法制度,贵族聚族而居,依据血统区分大宗、小宗和远近亲疏,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下推行分封制,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周王依照制度对各级贵族分封统治地区,给予世袭官职,从而建立各级政权。天子是天下同姓贵族的大宗,又是最高政权的领袖,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诸侯为天子所封,在本国为大宗,但对于同姓天子而言则是小宗,以自己的国名为氏,即“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卿大夫是比诸侯国君地位较低的贵族,以世袭官职、辈分为氏。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是本族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全权掌握本族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祭祀大权。每个贵族男子,都有权力参加本族的政治活动和各种祭祀,并且有服兵役的责任,以保卫本族的共同利益。这便是宗法制度所规定的贵族组成。
所以即使在贵族之中,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差异。
首先是诸侯国之间的差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另据《荀子·儒效》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虽然两篇文献的数字并不一致,但其强调在西周宗法体制中姬姓为主的意思的相同的,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正是这种事实的反映。太史公曰:“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需要说明的是,公侯伯子男五等名称虽然在原始氏族已经出现,但并不带有政治意义,纯粹是氏族部落内部的亲属称谓。殷周历史文献以及甲骨文所见公伯子男当属于这一习惯的遗迹,战国时代的学者托古改制,将五等爵位制附会于夏商历史。而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言之凿凿、确然无疑的。但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根据近代考古学的发现,认为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所以“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观堂别集》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3页。,但并未彻底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史学名家,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基本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代彝铭中无五服五等之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金文所无考·五等爵禄》,《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古爵名无定称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此后,虽有史学家仍在继续探讨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但尚未取得一致认同的看法。由此看来,太史公所谓周初五等爵位制尚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证。况且,五等爵的存在与否问题并非本文的重点所在,重要的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五等爵问题至少可以证明诸侯国之间的等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卿大夫之间也存在者地位高低的差异。《礼记·王制》:“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左传·成公三年》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
到底与晋卫两个国家哪个先结盟,鲁成公颇费心思。就个人而言,卫孙良夫乃上卿,而晋荀庚的地位在?克和荀首的地位之下,应该是下卿;但就国家地位而言,卫国却是小国,而晋国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天下盟主,地位应该远在卫国之上。所以鲁成公首先与晋国结盟,第二天才与卫国结盟,因此获得了《左传》作者的赞扬:“礼也”《左传·成公三年》。由此可见在礼制中层层相异的等级关系。
士是贵族阶层中的最下层。西周的士也有上中下之分,“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传·襄公十一年》 并且不同级别的士之间的俸禄也是不同的。《孟子·万章下》云:“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由此可见士并非仅仅是一个阶层,内部也有等级差异,其最下等的下士仅仅比庶人地位高。早期的士基本是武士,《周礼·司马》讲到军队的基层组织时说:“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国语·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韦昭注曰:“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直到春秋后期,从孔子开始兴办私学以后,士的成分发生变化,既有了“击剑扛鼎、鸡鸣狗盗”的武士,也有了“坚白同异、谈天雕龙”的文士。
按照血缘宗法等级体系,贵族以下是国人。在西周宗法体制里,国人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也是比较尴尬的。《周礼·天官冢宰》有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赵世超先生认为,“西周曾经有过国与野的区别。国指少数文化先进的点,野则是相对较为落后的面。国人以周族及其同盟各族为主体,也包括着部分被征服者;野人含有亡王之后、蛮夷戎狄和流裔之人几大类。”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由此可以得知,根据血缘关系,国人与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贵族的远房本家。所以,他们可以享受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权利。但在实际上这些权利中除过服兵役权利和可以免除部分租役等具有实际意义以外,其他礼法规定的权利虽然不能说是形同虚设,也只能是贵族宗法政治的典雅装饰。比如据《尚书·洪范》所云,当国君决策或施政有大疑,则可以而且也应该“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于是,国人便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而事实上,《左传》中虽然也的确记载了春秋时代国人参与政治决策、决定国君废立、过问外交和战、参与国都迁徙等事例,但仔细分析,在诸多事例中,只有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一役中,国人似乎发生了作用。可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王道衰微”西周末期,正如不能用某个朝代末期农民起义的胜利来证明在古代社会中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样,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不能说明国人地位的重要。谢维扬指出:“商周时期的‘询万民’和‘朝国人’只是君主和诸侯为形成自己的意见从而做出决断而采取的一种咨询方式,有时甚至只是向下属和臣民贯彻自己的决策的一种布政方式。在商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使‘国人’或‘万民’成为社会的一个权力点的任何制度。”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从“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庄公十年》一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国人对国家政治的无奈甚至是漠不关心。
野人是西周宗法政治社会阶级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人群,亦称之为“庶人”、“庶民”、“野人”、“鄙人”、“氓”,从“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中可以看出野人在西周社会中的地位。野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压迫和歧视。《仪礼·丧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贾公彦疏云:野人“不知分别父母尊卑”。可见,野人不存在基本的封建家长制,更无所谓礼法观念了,因此在观念上也受到歧视。
以上所述乃是正常社会秩序下的血缘宗法制度中的等级关系,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以周天子为首,以血缘宗法为依据,按照血统远近区别嫡庶亲疏,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级分明,各守其本分,无越轨、无僭越,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春秋末年,中国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受到猛烈的震荡而迅速解体。《战国策附录》对这段历史有个简单而准确的论述:
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道德绝矣。
在刘向看来,春秋时代的社会秩序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霸以前,社会仍然在周礼的规范下发展,整个社会还能“尊事周室”。第二阶段是五霸以后,到孔子去世之前。其时“君虽无德,”但“人臣辅其君者”,故社会仍然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值得注意的是,刘向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偏离了周礼的规范,从他小心翼翼的用到“挟君辅政”一词便可知道,他对这种现象是并不以为然的。第三阶段是孔子去世以后,刘向非常痛心这个阶段的社会变化,所谓“道德大废,上下失序”,以至“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挟君辅政道德绝矣”。
事实上,在后人眼里,刘向对春秋时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仍然显得过于乐观。因为,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周礼所规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平王东迁,根本无能重新建立西周式的封建宗法结构。东周王室在春秋早期还曾先后依赖于几个强国勉强维持,但以“周郑交质”为标志,周天子就堕落为普通的诸侯国君,在楚子观兵周疆之后,《左传·宣公三年》天子威严扫地,所有宗法制度规定的等级制度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列国之间、各级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高低等级也因为互相的吞并侵蚀而遭到破坏,由是引起原来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恰如其分的。
在春秋时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某些贵族不断发展壮大,有些甚至最终取代国君,表现为晋国的韩赵魏三家、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宋国的戴氏等,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齐国的陈氏。
陈氏(也称为田氏)原来是陈国的公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徐广曰:‘应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隐曰:‘据史,此文敬仲奔齐,以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为田氏。’正义曰:‘按:敬仲既奔齐,不欲称本故国号,故改陈字为田氏。’”在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时,公子完田敬仲投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取代姜姓贵族,成为齐国诸侯。
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第二种表现为贵族的沦亡,而且这也是变化的主要形式。翻开史书,这类变化的例子随处可见。最著名的仍然是《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的晋国叔向的一段话:“叔向曰:‘栾、?、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筭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筭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筭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虽然事隔两千余年,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文字所透露出的说不尽的意气萧索。
晋之公族已经堕落殆尽,而自己的氏族也由原来的十一家,变为硕果仅存的一家了,但就这一家也是前途十分渺茫,从“幸而得死,岂其获祀”中,可以看出叔向对终极关怀的深刻绝望。
问题在于,处于这种沉沦边缘或已经沉沦的贵族屈指难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霥之。”有封邑的?缺尚且亲自锄草耕耘,妻子更是送饭到地头,这似乎不能解释为热爱劳动、与庶民同甘共苦,恐怕自己已经降为庶民了。史墨曾向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国语·晋语九》记载了一段极有意思的对话,虽然本意在于劝诫当政者要修德自戒,但仍然可以看出白云苍狗、世态炎凉的无奈:“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窦韜侍,曰:‘臣闻之: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尽管当时某些已经沉沦的贵族仍然不甘于现实,意图抗争,但所有的努力也大多表现为情绪的愤愤不平,相比之下,苍葛的努力多少也算是有了回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于是始起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可见,直到抬出“王之亲姻”这顶大帽子,才获得了“乃出其民”的结果,由此可见春秋时期贵族地位的沦落。
孔门弟子颜回的远祖邾武公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任鲁之卿大夫,他本人却在春秋晚期成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著名贫士,因为“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终落得孔子“贤哉”这句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的赞叹;《论语·雍也》《世本》载曾皙是?国太子巫的子孙,到曾子时只能“衣敝衣以耕”;孔子本人虽出身于贵族,但也自叹“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得不从事“儒”以维持生计,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孔子“吾道穷矣”的无奈和“逝者如斯夫”的苍凉;《论语·子罕》《史记·孔子世家》商鞅、韩非等皆公室之子,世禄制度废除后,他们也只有以技艺奔波于诸侯之国以干禄,将全部的希望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绑在诸侯的战车上。
与贵族地位沦落相对应的是,国野制度的松散和野人身份的提高,这个过程是和各大国“辟土服远”相联系的。
春秋时期各国对“野”的规划,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版图的扩张和治理。为了妥善管理新开辟的土地,为了重新规划因贵族沦落而遗留的采邑,县制开始建立。这是与传统的宗法分封制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是血缘关系松散、地缘关系逐渐占据社会组织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出现的新体制。原来的国野制度就此开始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全体人民身份平等的地缘村落。随着“作爰田”、“作州兵”等制度的出现,在法律上确认了国人、野人身份的平等,彻底泯灭了国人与野人身份的差别。
这种变化体现在古代词语上,也可以看出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身份的逐渐混同。与后世不同,在春秋以前,百姓是贵族的称谓。《国语·周语》富辰曰:“百姓兆民。”韦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尚书·尧典》:“平章百姓。”郑注:“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与百姓相对的庶人则一般称“民”,《尚书·吕刑》:“苗民勿用灵。”郑注:“苗族三生凶恶,故着其氏而谓其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此乃民之本意,指的是异族或下等民众。
到后来,百姓和民渐渐成为一个意思,都表示处于下层的被统治者。而所谓“君子”“小人”,含义也有变化,在春秋以前,君子一般指士大夫贵族,小人指身份低贱的平民,《左传·僖公十五年》:“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春秋以后,君子小人的词义差别,不是以阶级身份为标准,而是以道德品格为尺度。凡此种种,都可以表现出春秋以前原来故有的阶级观念逐渐泯灭,齐民的思想观念随之出现,体现出春秋时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
二、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直接来源于西周的政治模式。
众所周知,西周乃是典型的血缘宗法社会,作为西周国家政治结构构成模本的周礼本身就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早期国家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对于这种统治结构,孔子有个很好的概括,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可以肯定,正是由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是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孔子才会发出如此议论。其实,老先生所处的时代本来就是血缘宗法政治的末世,其显著特点即礼崩乐坏,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他生气的事情,一部《论语》充满了先生对社会上各种非礼现象的讨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不仅对僭越的当政者极为痛恨,而且对依附于当政者、帮助当政者践踏周礼的人也充满愤怒,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不例外。如因为冉求帮助了为富不仁的季氏,引起了先生极大的不满,“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如此大违常规的怂恿,表现出老先生的嫉恶如仇和对社会非礼现象的极度痛恨。
可是,毕竟时代变了,周天子对这种变革都无可奈何,布衣孔子又能怎样?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其实,这是晚年孔子知道行道于天下已不可得,无是心,也无是梦也。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更切。
事实上,随着西周中后期周王朝的衰落,血缘宗法政治就已经开始衰落了。甚至可以说,西周王朝的衰落正是血缘宗法政治体制开始衰落的典型标志。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衰落开始于昭穆时代。“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汉书·匈奴列传上》曰:“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作《吕刑》之辟。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从“微缺”到“衰微”再到“遂衰”,阶段分明,清楚地表现了西周王朝衰落的道路。
另一个对西周王朝衰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夷王的即位。“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史记·周本纪》虽然司马迁以及各种注疏都对此没有作出评论,但很显然“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表明诸侯开始干预王位废立。《礼记·郊特牲》所谓“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郑玄注:“时微弱,不敢自尊于诸侯也。”可以作为这件大事的旁证,证明夷王和诸侯之间的微妙关系。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是西周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此事的发生也是西周王权衰落的证明。在宗法体制下,国人干预政治虽然是“有法可依”的,《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尚书·洪范》:“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但纵观西周春秋历史,真正能干预朝政的事例大都发生在卫、曹、陈、纪等小国,应该是因为这些国家原始公社的残余较多的缘故。而对诸大国、尤其是周王室来说,国人干预政治只能表明王权的极度暗弱。或许,共和行政本身就是王权旁落的证明。
正如后世许多虽然自身能力较强、但身处末世的封建君主一样,周宣王也是无力回天。所谓“宣王中兴”处处透露出末世的虚假繁荣,“不籍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的举动,也只能表现出对剧变的社会现象的无奈承认。
如果说,虚假繁荣的宣王中兴是西周王朝的回光返照的话,那么,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则无疑是自寻死路。“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周幽王如此儿戏,岂能长久?加之废长立幼《史记·周本纪》:“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更加剧了周王室的危机,《史记·周本纪》曰:“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祸成矣,无可奈何!’”果然,“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史记·周本纪》
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身死国灭,自无稀奇,可是此后的王位继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周王室威严堕落的程度。《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襷。” 正义引《汲冢书纪年》曰:“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二王并立,权臣操纵王位,表明血缘宗法政治已经走到尽头。在周平王开始的春秋时代,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结构逐渐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变为“陪臣执国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政由方伯”,天子的权威已是明日黄花,盛况不再。
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宾礼表叙》记载:“终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甚者旅见而朝于楚焉。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61页。
从数字上看,我们不得不为周天子感到悲哀。鲁国这个向来号称最重视礼乐制度的同姓国家尚且如此,更何谈其他异姓之宋齐、非种之楚越。从以下几组史料中,更可以看出周天子的?惶。
《左传·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左传·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左传·桓公十五年》:“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
《左传·文公九年》:“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
对于这几件亘古未闻的奇事,一向讲究微言大义的《公羊传》作如下评论:
《公羊传·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
《公羊传·桓公十五年》:“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
《公羊传·文公九年》:“毛伯来求金,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
在这几件事上,《左传》和《公羊传》两书作者的观点完全一样,即“非礼也”。原因很简单,因为“王者无求”,这不仅表示王者的富甲天下,更重要的是表示王者的尊严。《公羊传》作者的写作意图很明显:“讥”,但到底是在讥谁?周天子抑或诸侯?很显然,从根本上说,是在讥讽混乱的朝纲,讥讽崩溃的礼制。
具体说来,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周以来的君臣之礼虽弛犹存,周天子的王权虽已下移但并未完全消失,周天子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所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左传·宣公三年》,可是往往扮演着为人作嫁的角色。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勤王救天子而取信于天下,成大义于天下,这一条经验被后世列强多次成功模仿。尊王攘夷成为所有企图“代天子行权”的霸主们的共同口号,而周天子也就被迫成为仅有政治意义的天下共主。
首先,春秋初年的霸主只有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才能得到天下诸侯更为广泛的认可。《国语·齐语》记载了一段极有代表性的史料:
葵丘之会,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掌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诸侯称顺焉。
《左传·僖公九年》也有类似记载: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两厢对照,基本史实大致相同,但《国语》描写更加细腻。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对齐桓公的提示,所谓“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可以想到,“桓公惧”并最终下拜受命,并不是首先出于对周天子的敬畏,也不是出于周礼体制的维护,而是出于对自己霸业是否能最终得以实现的担心。作者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在最后照应到“诸侯称顺焉”。这段史料的价值就在于充分描绘了周天子的这种特殊的尴尬地位。
二十年后,历史上又出现了极为相似的一幕,晋文公继齐桓公称霸,因此再次大会天下诸侯:“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霧弓矢千、纒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文公也是因为有了王命,才成为威震一时的“侯伯”,但这次会盟也在历史上开了另一个先例:“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从惯于使用春秋笔法的孔子的评论上,后人可以看出这条史料的褒贬。
其次,春秋时代,甚至战国时代诸侯的地位仍然需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无非是在确立周天子在血缘宗法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周礼·春官·内史》所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就是在说周天子之所以称为天下共主的主要原因。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国语·周语上》等。可见,在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已经是明日黄花,但在宗法封建系统中,周天子仍然能发挥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
如早在春秋初年,秦国的初建便是出于周天子的封赏,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事后分析,周平王当日的狼狈可想而知,但他在少数民族的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被迫举族迁徙之时,居然还颇有政治智慧,不仅分封秦国为西部屏障,而且慷慨地送了个空头人情,“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为犬戎树立了一个强敌。可惜的是,正是由于周平王的政治智慧,秦国由此发展,并最后取代了姬姓家族,成为天下共主。当然这并不是平王当年始料所及的。
周王分封诸侯的惯例,一直到战国时代仍然存在。《史记·晋世家》:“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康公)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这两条史料,充分证明了在战国时期周天子在诸侯任命过程中的重要性。
再次,春秋时代的许多诸侯国仍必须对周天子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周天子也还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中起到一定作用。
《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第二年,“齐人来归子叔姬,王故也。”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13年到公元前612年,政治上已经是“政由方伯”了,但齐人依然不得不遵照王命,从“王故也”就可以看出周天子仍然具有一定的潜在政治影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会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大举伐楚。关于这次战争的政治意义自然毋需多言,有意思的是管仲问罪楚国的一条理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左传·僖公四年》。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王权沦落、政由方伯的春秋年代,为天子进贡也是天经地义的。《左传·隐公六年》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这一点:“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事实上,在春秋年间,许多诸侯国仍然朝觐周天子,为周天子尽着各种义务。
《左传·隐公八年》:“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左传·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戊午,晋侯朝王。”
《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
类似的例子都在或多或少地为周天子和血缘宗法制度维系着残局,也表示着春秋时期血缘宗法制度仍然在顽强地存在。
第二,由周初制定的血缘宗法分封制度遭到破坏,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转化。
就政治结构而言,从西周到春秋时代,再到战国时代,是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状态向分裂动乱发展;而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再到秦王朝的建立,又是从分裂动乱向统一王朝的发展。
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说,春秋以前的王朝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
据《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靌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之说当然不足为据,但方国众多却是事实。到了商朝,这种局面仍在延续。《逸周书·殷祝》:“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同样,三千之数仍然未必确凿,但方国林立的状况却是事实。众多方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互相联合,或互相征服,或为商王朝所翦灭,演化的总趋势是愈来愈少,但到周初至少仍有八百之多。《尚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毫无疑问,此乃夸张。《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应该说,这个数字比较可信。成王以后,又分封了大量诸侯国,《汉书·诸侯王表》说:“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晋书·地理志上》“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而据《春秋大事表》记载,春秋列国共一百四十七国,《春秋会要》载一百四十二国。可见周朝依旧是诸侯林立的时代。
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春秋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家共有十四个。而到了战国时代,《史记》中赫然出现的竟是《六国年表》,即使再加上秦国和已经微不足道的周,也不过八个。当历史发展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兼并六国、横扫宇内后,中国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但论及政治结构,国家兼并不过是表面现象,在这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中,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和世卿世禄制的崩溃。
值得提出的是郑庄公归许。在占有了许国以后,郑庄公表现了难得的谦虚。《左传·隐公十一年》有云:“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齐桓公继位前一年公元前686年,是霸权形成以前的混乱阶段;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到弭兵会议前一年公元前547年,是霸主迭兴阶段;弭兵会议即公元前546年到周元王继位前一年公元前476年,是大夫执政阶段。上述郑庄公归许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12年,属于平王东迁、王室衰落,但霸权尚未形成阶段。
鲁郑齐三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讨伐许国,本身就是对西周以来血缘宗法制度权威的挑衅,郑庄公说得很明白,“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然而,此时毕竟是春秋初年,各大国的兼并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所以,郑庄公仍然将许国归还许人,于是赢来一片喝彩:“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左传·隐公十一年》
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国兼并日益剧烈,而具有郑庄公如此风度的人也越来越少,故此,原本残破的血缘宗法体制更是每况愈下。
《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春秋时期的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原本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发生动摇。在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想方面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也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作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这些新的观念的出现,形成对原本天经地义的血缘宗法关系强有力的挑战。
首先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先后称霸。关于春秋五霸的组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齐桓公和晋文公是没有争议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受到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另一方面,也由于二人的称霸是在春秋早期,霸政以“尊王攘夷”作为旗帜,从而赢得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同。
如果说这个阶段的霸政尚以“尊王攘夷”作为旗帜,以后的大国争霸便以兼并弱国为主要内容。西周以来的传统礼制遭到彻底破坏,王室地位下降,经济拮据,地盘被蚕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王室不仅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经济上也不得不依赖于诸侯的资助,威严扫地。
与此同时,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并且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真正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局面。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卿大夫与公室的斗争愈演愈烈,以下克上的事件层出不穷。斗争的结果,使各国的公室程度不同地衰弱下去,卿大夫逐渐掌握了政权,有的甚至灭亡了公室。
春秋时期卿大夫与公室斗争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族与公室的斗争。按照周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原则,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大夫,他们是公室的后代,称为公族。这些公族卿大夫与公室同室操戈,争权夺利。二是异姓卿大夫与公室的斗争。春秋时期少数国家公族势力衰败不振,执政的卿大夫多为异姓贵族,他们也和公族展开夺权斗争,春秋后期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由于异姓卿大夫专权而造成的结果。
同时,诸侯也不愿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辙,更不愿受制于卿大夫,于是也想尽办法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办法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授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左传·襄公十六年》:“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表明官职与封邑(禄)已经联系在一起。;卿大夫出奔或以其他原因离去官职,其采邑自然归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齮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左传·襄公三十年》:“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在兼并卿大夫封邑的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出现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式的以军功而不完全按血缘授官的规定。因此,各国相继出现了没有世袭的、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
就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逐渐形成,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日益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血缘宗法关系逐渐淡漠,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贵族“出奔”和采邑归公。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出奔”是春秋时期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从一个侧面了反映春秋血缘宗法关系的崩溃。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曾集中统计出国君“出奔”事件十二起,周天子“出居”事件三起。而事实上,各国贵族“出奔”事件不下数百起,涉及周王室和数十个诸侯国。
终春秋时代,因君位之争导致“出奔”的事件,总计七十起,九十二人次。因以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导致的“出奔”事件,总计六十二起,涉及到九十五人次,因家族长争立导致的“出奔”事件,总计四起,涉及到十二人次,因其他原因贵族内部发生冲突导致的“出奔”事件,总计二十八起,涉及到二十九人次。
“出奔”者背井离乡,永远或者暂时脱离了原来的血缘关系和宗法体系,来到理论上有宗法血缘联系而实际上却淡漠疏远的新环境中,使得宗法体系残缺不全,血缘关系受到了破坏性的冲击,并直接摧毁了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
世卿世禄等级制度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孟子·万章下》。根据等级裂土分封,按级别高低分别享有不同政治特权和物质待遇,并且世袭罔替。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新的官僚等级制度开始取代旧的世卿世禄制度。
官僚等级制度源于世卿世禄制,但又有所不同。充当官吏的虽然还是大大小小的贵族,但已经不是世袭,他们“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在这种君主臣仆的特殊雇佣关系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他们的命运”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 年版,第8-11页。。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袭之外,还可能随时受到升迁罢免,上下沉浮,而且享受报酬的形式也不再以土地作为标准,而是改以实物作为支付的手段。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世卿世禄制的封君和赐爵制。例如,晋文公重耳“赏从之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史记·晋世家》;赵简子赵鞅也曾以“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奖励将士,激发各阶层人士奋发立功。
总之,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的官僚制度。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所以后人说:“自世爵世禄之制废,而宗法始坏矣。”清·江琬:《汪氏族谱序》,选自(清)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封建废,而宗法格不行。”清·许三礼:《补定大宗议》,选自《清经世文编·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敬宗之道。”清·顾炎武:《日知录·分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无独有偶,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了另一段同样的史料:“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
两段史料的出处在时间上前后相隔仅仅二十五年,但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却是翻天覆地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无论如何无法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相提并论,社会观念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至少,同样在《左传·昭公三年》,齐晏婴和晋叔向就分别对自己国家的前途表现出无限的担忧,甚至是绝望:“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事实证明,晏婴与叔向二人的议论并非杞人忧天,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姜齐的命运似乎好一些,比晋国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王迁到海边,他自己做了实际的国君,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封田和为齐国诸侯,田氏代齐。
问题并非仅仅如此,在周初以及后来陆续分封的诸侯方国中,其中绝大部分到春秋末期已经被强国所灭,即使是延续到战国时代的七强,也只有楚、秦两国国君的血统没有改变,正如《淮南子·览冥训》云:“晚世之时,七国异族。”高诱注:“七国,齐、楚、燕、赵、韩、魏、秦也。齐姓田,楚姓芈,燕姓姬,赵姓赵,韩姓韩,魏姓魏,秦姓嬴,故异族也。”读史至此,每每使人产生苍凉之感。所有这一切,无不在暗示着春秋年间的巨大变化。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烈变化,历代研究者极多,对某些时代特点也取得了共识,其中可以称为经典的首推顾炎武的《日知录·周末风俗》:“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顾氏在此描述的几大特点,甚至成为后来研究春秋战国史的总纲,历来研究者无不对此极为重视。但顾氏同时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本人认为,这句话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面的罗列。当然,离开史料,历史便无从谈起,所以,顾炎武这句话的用意无非是要后人仔细分析史料,从而找出各种材料之间内部的逻辑关系,以求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事实上,以上顾炎武所叙述的关于春秋战国之间的几大变化,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并列的。很明显,在上古时代对血缘关系极为重视的宗法社会中,宗姓氏族的意义无疑是其他社会因素的基础,换言之,有关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无不由血缘宗法关系的变化而引发,有关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也都是血缘宗法关系的变化在不同领域里的体现。
那么,通过现有的史料,我们再来分析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关于西周社会的阶级结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左传》和《国语》:
《左传·桓公二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左传·襄公九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很明显,通过分析以上史料,可以得知春秋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应该主要由贵族、国人、野人组成。
在一般意义上,贵族应该是指在血统上与周王室或各诸侯国君比较亲近、在宗法系统中属于各大宗或小宗的嫡系子孙,即王、公、大夫和士,也即社会统治阶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正是贵族身份和特权的证明。
而在现实生活中,判定某人是否具有贵族身份,固然要考虑他的祖宗曾经拥有的身份,但很多情况下更多依据的是他本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比如虽然孔子是“圣人之后”,但当“季氏飨士,孔子与往”,却遭阳虎斥退。“孔子要?,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对少年孔子而言,这件事给他所留下的屈辱和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
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同一始祖的后代,由于出生先后的差异,本身就有身份高低之分,当经过若干代的繁衍后,身份的差异更加明显。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礼记·大传》
有例为证,《礼记·礼运》有云:“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三个“子孙”的社会地位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根据宗法制度,贵族聚族而居,依据血统区分大宗、小宗和远近亲疏,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下推行分封制,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周王依照制度对各级贵族分封统治地区,给予世袭官职,从而建立各级政权。天子是天下同姓贵族的大宗,又是最高政权的领袖,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诸侯为天子所封,在本国为大宗,但对于同姓天子而言则是小宗,以自己的国名为氏,即“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卿大夫是比诸侯国君地位较低的贵族,以世袭官职、辈分为氏。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是本族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全权掌握本族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祭祀大权。每个贵族男子,都有权力参加本族的政治活动和各种祭祀,并且有服兵役的责任,以保卫本族的共同利益。这便是宗法制度所规定的贵族组成。
所以即使在贵族之中,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差异。
首先是诸侯国之间的差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另据《荀子·儒效》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虽然两篇文献的数字并不一致,但其强调在西周宗法体制中姬姓为主的意思的相同的,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正是这种事实的反映。太史公曰:“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需要说明的是,公侯伯子男五等名称虽然在原始氏族已经出现,但并不带有政治意义,纯粹是氏族部落内部的亲属称谓。殷周历史文献以及甲骨文所见公伯子男当属于这一习惯的遗迹,战国时代的学者托古改制,将五等爵位制附会于夏商历史。而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言之凿凿、确然无疑的。但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根据近代考古学的发现,认为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所以“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观堂别集》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3页。,但并未彻底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史学名家,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基本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代彝铭中无五服五等之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金文所无考·五等爵禄》,《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古爵名无定称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此后,虽有史学家仍在继续探讨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但尚未取得一致认同的看法。由此看来,太史公所谓周初五等爵位制尚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证。况且,五等爵的存在与否问题并非本文的重点所在,重要的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五等爵问题至少可以证明诸侯国之间的等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卿大夫之间也存在者地位高低的差异。《礼记·王制》:“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左传·成公三年》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
到底与晋卫两个国家哪个先结盟,鲁成公颇费心思。就个人而言,卫孙良夫乃上卿,而晋荀庚的地位在?克和荀首的地位之下,应该是下卿;但就国家地位而言,卫国却是小国,而晋国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天下盟主,地位应该远在卫国之上。所以鲁成公首先与晋国结盟,第二天才与卫国结盟,因此获得了《左传》作者的赞扬:“礼也”《左传·成公三年》。由此可见在礼制中层层相异的等级关系。
士是贵族阶层中的最下层。西周的士也有上中下之分,“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传·襄公十一年》 并且不同级别的士之间的俸禄也是不同的。《孟子·万章下》云:“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由此可见士并非仅仅是一个阶层,内部也有等级差异,其最下等的下士仅仅比庶人地位高。早期的士基本是武士,《周礼·司马》讲到军队的基层组织时说:“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国语·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韦昭注曰:“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直到春秋后期,从孔子开始兴办私学以后,士的成分发生变化,既有了“击剑扛鼎、鸡鸣狗盗”的武士,也有了“坚白同异、谈天雕龙”的文士。
按照血缘宗法等级体系,贵族以下是国人。在西周宗法体制里,国人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也是比较尴尬的。《周礼·天官冢宰》有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赵世超先生认为,“西周曾经有过国与野的区别。国指少数文化先进的点,野则是相对较为落后的面。国人以周族及其同盟各族为主体,也包括着部分被征服者;野人含有亡王之后、蛮夷戎狄和流裔之人几大类。”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由此可以得知,根据血缘关系,国人与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贵族的远房本家。所以,他们可以享受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权利。但在实际上这些权利中除过服兵役权利和可以免除部分租役等具有实际意义以外,其他礼法规定的权利虽然不能说是形同虚设,也只能是贵族宗法政治的典雅装饰。比如据《尚书·洪范》所云,当国君决策或施政有大疑,则可以而且也应该“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于是,国人便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而事实上,《左传》中虽然也的确记载了春秋时代国人参与政治决策、决定国君废立、过问外交和战、参与国都迁徙等事例,但仔细分析,在诸多事例中,只有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一役中,国人似乎发生了作用。可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王道衰微”西周末期,正如不能用某个朝代末期农民起义的胜利来证明在古代社会中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样,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不能说明国人地位的重要。谢维扬指出:“商周时期的‘询万民’和‘朝国人’只是君主和诸侯为形成自己的意见从而做出决断而采取的一种咨询方式,有时甚至只是向下属和臣民贯彻自己的决策的一种布政方式。在商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使‘国人’或‘万民’成为社会的一个权力点的任何制度。”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从“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庄公十年》一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国人对国家政治的无奈甚至是漠不关心。
野人是西周宗法政治社会阶级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人群,亦称之为“庶人”、“庶民”、“野人”、“鄙人”、“氓”,从“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中可以看出野人在西周社会中的地位。野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压迫和歧视。《仪礼·丧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贾公彦疏云:野人“不知分别父母尊卑”。可见,野人不存在基本的封建家长制,更无所谓礼法观念了,因此在观念上也受到歧视。
以上所述乃是正常社会秩序下的血缘宗法制度中的等级关系,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以周天子为首,以血缘宗法为依据,按照血统远近区别嫡庶亲疏,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级分明,各守其本分,无越轨、无僭越,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春秋末年,中国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受到猛烈的震荡而迅速解体。《战国策附录》对这段历史有个简单而准确的论述:
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道德绝矣。
在刘向看来,春秋时代的社会秩序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霸以前,社会仍然在周礼的规范下发展,整个社会还能“尊事周室”。第二阶段是五霸以后,到孔子去世之前。其时“君虽无德,”但“人臣辅其君者”,故社会仍然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值得注意的是,刘向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偏离了周礼的规范,从他小心翼翼的用到“挟君辅政”一词便可知道,他对这种现象是并不以为然的。第三阶段是孔子去世以后,刘向非常痛心这个阶段的社会变化,所谓“道德大废,上下失序”,以至“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挟君辅政道德绝矣”。
事实上,在后人眼里,刘向对春秋时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仍然显得过于乐观。因为,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周礼所规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平王东迁,根本无能重新建立西周式的封建宗法结构。东周王室在春秋早期还曾先后依赖于几个强国勉强维持,但以“周郑交质”为标志,周天子就堕落为普通的诸侯国君,在楚子观兵周疆之后,《左传·宣公三年》天子威严扫地,所有宗法制度规定的等级制度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列国之间、各级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高低等级也因为互相的吞并侵蚀而遭到破坏,由是引起原来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恰如其分的。
在春秋时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某些贵族不断发展壮大,有些甚至最终取代国君,表现为晋国的韩赵魏三家、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宋国的戴氏等,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齐国的陈氏。
陈氏(也称为田氏)原来是陈国的公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徐广曰:‘应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隐曰:‘据史,此文敬仲奔齐,以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为田氏。’正义曰:‘按:敬仲既奔齐,不欲称本故国号,故改陈字为田氏。’”在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时,公子完田敬仲投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取代姜姓贵族,成为齐国诸侯。
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第二种表现为贵族的沦亡,而且这也是变化的主要形式。翻开史书,这类变化的例子随处可见。最著名的仍然是《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的晋国叔向的一段话:“叔向曰:‘栾、?、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筭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筭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筭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虽然事隔两千余年,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文字所透露出的说不尽的意气萧索。
晋之公族已经堕落殆尽,而自己的氏族也由原来的十一家,变为硕果仅存的一家了,但就这一家也是前途十分渺茫,从“幸而得死,岂其获祀”中,可以看出叔向对终极关怀的深刻绝望。
问题在于,处于这种沉沦边缘或已经沉沦的贵族屈指难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霥之。”有封邑的?缺尚且亲自锄草耕耘,妻子更是送饭到地头,这似乎不能解释为热爱劳动、与庶民同甘共苦,恐怕自己已经降为庶民了。史墨曾向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国语·晋语九》记载了一段极有意思的对话,虽然本意在于劝诫当政者要修德自戒,但仍然可以看出白云苍狗、世态炎凉的无奈:“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窦韜侍,曰:‘臣闻之: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尽管当时某些已经沉沦的贵族仍然不甘于现实,意图抗争,但所有的努力也大多表现为情绪的愤愤不平,相比之下,苍葛的努力多少也算是有了回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于是始起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可见,直到抬出“王之亲姻”这顶大帽子,才获得了“乃出其民”的结果,由此可见春秋时期贵族地位的沦落。
孔门弟子颜回的远祖邾武公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任鲁之卿大夫,他本人却在春秋晚期成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著名贫士,因为“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终落得孔子“贤哉”这句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的赞叹;《论语·雍也》《世本》载曾皙是?国太子巫的子孙,到曾子时只能“衣敝衣以耕”;孔子本人虽出身于贵族,但也自叹“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得不从事“儒”以维持生计,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孔子“吾道穷矣”的无奈和“逝者如斯夫”的苍凉;《论语·子罕》《史记·孔子世家》商鞅、韩非等皆公室之子,世禄制度废除后,他们也只有以技艺奔波于诸侯之国以干禄,将全部的希望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绑在诸侯的战车上。
与贵族地位沦落相对应的是,国野制度的松散和野人身份的提高,这个过程是和各大国“辟土服远”相联系的。
春秋时期各国对“野”的规划,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版图的扩张和治理。为了妥善管理新开辟的土地,为了重新规划因贵族沦落而遗留的采邑,县制开始建立。这是与传统的宗法分封制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是血缘关系松散、地缘关系逐渐占据社会组织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出现的新体制。原来的国野制度就此开始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全体人民身份平等的地缘村落。随着“作爰田”、“作州兵”等制度的出现,在法律上确认了国人、野人身份的平等,彻底泯灭了国人与野人身份的差别。
这种变化体现在古代词语上,也可以看出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身份的逐渐混同。与后世不同,在春秋以前,百姓是贵族的称谓。《国语·周语》富辰曰:“百姓兆民。”韦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尚书·尧典》:“平章百姓。”郑注:“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与百姓相对的庶人则一般称“民”,《尚书·吕刑》:“苗民勿用灵。”郑注:“苗族三生凶恶,故着其氏而谓其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此乃民之本意,指的是异族或下等民众。
到后来,百姓和民渐渐成为一个意思,都表示处于下层的被统治者。而所谓“君子”“小人”,含义也有变化,在春秋以前,君子一般指士大夫贵族,小人指身份低贱的平民,《左传·僖公十五年》:“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春秋以后,君子小人的词义差别,不是以阶级身份为标准,而是以道德品格为尺度。凡此种种,都可以表现出春秋以前原来故有的阶级观念逐渐泯灭,齐民的思想观念随之出现,体现出春秋时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
二、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直接来源于西周的政治模式。
众所周知,西周乃是典型的血缘宗法社会,作为西周国家政治结构构成模本的周礼本身就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早期国家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对于这种统治结构,孔子有个很好的概括,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可以肯定,正是由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是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孔子才会发出如此议论。其实,老先生所处的时代本来就是血缘宗法政治的末世,其显著特点即礼崩乐坏,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他生气的事情,一部《论语》充满了先生对社会上各种非礼现象的讨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不仅对僭越的当政者极为痛恨,而且对依附于当政者、帮助当政者践踏周礼的人也充满愤怒,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不例外。如因为冉求帮助了为富不仁的季氏,引起了先生极大的不满,“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如此大违常规的怂恿,表现出老先生的嫉恶如仇和对社会非礼现象的极度痛恨。
可是,毕竟时代变了,周天子对这种变革都无可奈何,布衣孔子又能怎样?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其实,这是晚年孔子知道行道于天下已不可得,无是心,也无是梦也。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更切。
事实上,随着西周中后期周王朝的衰落,血缘宗法政治就已经开始衰落了。甚至可以说,西周王朝的衰落正是血缘宗法政治体制开始衰落的典型标志。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衰落开始于昭穆时代。“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汉书·匈奴列传上》曰:“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作《吕刑》之辟。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从“微缺”到“衰微”再到“遂衰”,阶段分明,清楚地表现了西周王朝衰落的道路。
另一个对西周王朝衰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夷王的即位。“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史记·周本纪》虽然司马迁以及各种注疏都对此没有作出评论,但很显然“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表明诸侯开始干预王位废立。《礼记·郊特牲》所谓“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郑玄注:“时微弱,不敢自尊于诸侯也。”可以作为这件大事的旁证,证明夷王和诸侯之间的微妙关系。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是西周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此事的发生也是西周王权衰落的证明。在宗法体制下,国人干预政治虽然是“有法可依”的,《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尚书·洪范》:“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但纵观西周春秋历史,真正能干预朝政的事例大都发生在卫、曹、陈、纪等小国,应该是因为这些国家原始公社的残余较多的缘故。而对诸大国、尤其是周王室来说,国人干预政治只能表明王权的极度暗弱。或许,共和行政本身就是王权旁落的证明。
正如后世许多虽然自身能力较强、但身处末世的封建君主一样,周宣王也是无力回天。所谓“宣王中兴”处处透露出末世的虚假繁荣,“不籍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的举动,也只能表现出对剧变的社会现象的无奈承认。
如果说,虚假繁荣的宣王中兴是西周王朝的回光返照的话,那么,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则无疑是自寻死路。“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周幽王如此儿戏,岂能长久?加之废长立幼《史记·周本纪》:“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更加剧了周王室的危机,《史记·周本纪》曰:“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祸成矣,无可奈何!’”果然,“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史记·周本纪》
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身死国灭,自无稀奇,可是此后的王位继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周王室威严堕落的程度。《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襷。” 正义引《汲冢书纪年》曰:“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二王并立,权臣操纵王位,表明血缘宗法政治已经走到尽头。在周平王开始的春秋时代,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结构逐渐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变为“陪臣执国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政由方伯”,天子的权威已是明日黄花,盛况不再。
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宾礼表叙》记载:“终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甚者旅见而朝于楚焉。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61页。
从数字上看,我们不得不为周天子感到悲哀。鲁国这个向来号称最重视礼乐制度的同姓国家尚且如此,更何谈其他异姓之宋齐、非种之楚越。从以下几组史料中,更可以看出周天子的?惶。
《左传·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左传·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左传·桓公十五年》:“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
《左传·文公九年》:“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
对于这几件亘古未闻的奇事,一向讲究微言大义的《公羊传》作如下评论:
《公羊传·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
《公羊传·桓公十五年》:“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
《公羊传·文公九年》:“毛伯来求金,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
在这几件事上,《左传》和《公羊传》两书作者的观点完全一样,即“非礼也”。原因很简单,因为“王者无求”,这不仅表示王者的富甲天下,更重要的是表示王者的尊严。《公羊传》作者的写作意图很明显:“讥”,但到底是在讥谁?周天子抑或诸侯?很显然,从根本上说,是在讥讽混乱的朝纲,讥讽崩溃的礼制。
具体说来,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周以来的君臣之礼虽弛犹存,周天子的王权虽已下移但并未完全消失,周天子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所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左传·宣公三年》,可是往往扮演着为人作嫁的角色。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勤王救天子而取信于天下,成大义于天下,这一条经验被后世列强多次成功模仿。尊王攘夷成为所有企图“代天子行权”的霸主们的共同口号,而周天子也就被迫成为仅有政治意义的天下共主。
首先,春秋初年的霸主只有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才能得到天下诸侯更为广泛的认可。《国语·齐语》记载了一段极有代表性的史料:
葵丘之会,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掌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诸侯称顺焉。
《左传·僖公九年》也有类似记载: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两厢对照,基本史实大致相同,但《国语》描写更加细腻。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对齐桓公的提示,所谓“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可以想到,“桓公惧”并最终下拜受命,并不是首先出于对周天子的敬畏,也不是出于周礼体制的维护,而是出于对自己霸业是否能最终得以实现的担心。作者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在最后照应到“诸侯称顺焉”。这段史料的价值就在于充分描绘了周天子的这种特殊的尴尬地位。
二十年后,历史上又出现了极为相似的一幕,晋文公继齐桓公称霸,因此再次大会天下诸侯:“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霧弓矢千、纒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文公也是因为有了王命,才成为威震一时的“侯伯”,但这次会盟也在历史上开了另一个先例:“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从惯于使用春秋笔法的孔子的评论上,后人可以看出这条史料的褒贬。
其次,春秋时代,甚至战国时代诸侯的地位仍然需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无非是在确立周天子在血缘宗法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周礼·春官·内史》所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就是在说周天子之所以称为天下共主的主要原因。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国语·周语上》等。可见,在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已经是明日黄花,但在宗法封建系统中,周天子仍然能发挥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
如早在春秋初年,秦国的初建便是出于周天子的封赏,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事后分析,周平王当日的狼狈可想而知,但他在少数民族的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被迫举族迁徙之时,居然还颇有政治智慧,不仅分封秦国为西部屏障,而且慷慨地送了个空头人情,“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为犬戎树立了一个强敌。可惜的是,正是由于周平王的政治智慧,秦国由此发展,并最后取代了姬姓家族,成为天下共主。当然这并不是平王当年始料所及的。
周王分封诸侯的惯例,一直到战国时代仍然存在。《史记·晋世家》:“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康公)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这两条史料,充分证明了在战国时期周天子在诸侯任命过程中的重要性。
再次,春秋时代的许多诸侯国仍必须对周天子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周天子也还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中起到一定作用。
《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第二年,“齐人来归子叔姬,王故也。”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13年到公元前612年,政治上已经是“政由方伯”了,但齐人依然不得不遵照王命,从“王故也”就可以看出周天子仍然具有一定的潜在政治影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会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大举伐楚。关于这次战争的政治意义自然毋需多言,有意思的是管仲问罪楚国的一条理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左传·僖公四年》。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王权沦落、政由方伯的春秋年代,为天子进贡也是天经地义的。《左传·隐公六年》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这一点:“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事实上,在春秋年间,许多诸侯国仍然朝觐周天子,为周天子尽着各种义务。
《左传·隐公八年》:“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左传·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戊午,晋侯朝王。”
《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
类似的例子都在或多或少地为周天子和血缘宗法制度维系着残局,也表示着春秋时期血缘宗法制度仍然在顽强地存在。
第二,由周初制定的血缘宗法分封制度遭到破坏,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转化。
就政治结构而言,从西周到春秋时代,再到战国时代,是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状态向分裂动乱发展;而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再到秦王朝的建立,又是从分裂动乱向统一王朝的发展。
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说,春秋以前的王朝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
据《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靌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之说当然不足为据,但方国众多却是事实。到了商朝,这种局面仍在延续。《逸周书·殷祝》:“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同样,三千之数仍然未必确凿,但方国林立的状况却是事实。众多方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互相联合,或互相征服,或为商王朝所翦灭,演化的总趋势是愈来愈少,但到周初至少仍有八百之多。《尚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毫无疑问,此乃夸张。《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应该说,这个数字比较可信。成王以后,又分封了大量诸侯国,《汉书·诸侯王表》说:“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晋书·地理志上》“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而据《春秋大事表》记载,春秋列国共一百四十七国,《春秋会要》载一百四十二国。可见周朝依旧是诸侯林立的时代。
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春秋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家共有十四个。而到了战国时代,《史记》中赫然出现的竟是《六国年表》,即使再加上秦国和已经微不足道的周,也不过八个。当历史发展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兼并六国、横扫宇内后,中国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但论及政治结构,国家兼并不过是表面现象,在这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中,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和世卿世禄制的崩溃。
值得提出的是郑庄公归许。在占有了许国以后,郑庄公表现了难得的谦虚。《左传·隐公十一年》有云:“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齐桓公继位前一年公元前686年,是霸权形成以前的混乱阶段;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到弭兵会议前一年公元前547年,是霸主迭兴阶段;弭兵会议即公元前546年到周元王继位前一年公元前476年,是大夫执政阶段。上述郑庄公归许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12年,属于平王东迁、王室衰落,但霸权尚未形成阶段。
鲁郑齐三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讨伐许国,本身就是对西周以来血缘宗法制度权威的挑衅,郑庄公说得很明白,“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然而,此时毕竟是春秋初年,各大国的兼并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所以,郑庄公仍然将许国归还许人,于是赢来一片喝彩:“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左传·隐公十一年》
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国兼并日益剧烈,而具有郑庄公如此风度的人也越来越少,故此,原本残破的血缘宗法体制更是每况愈下。
《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春秋时期的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原本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发生动摇。在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想方面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也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作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这些新的观念的出现,形成对原本天经地义的血缘宗法关系强有力的挑战。
首先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先后称霸。关于春秋五霸的组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齐桓公和晋文公是没有争议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受到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另一方面,也由于二人的称霸是在春秋早期,霸政以“尊王攘夷”作为旗帜,从而赢得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同。
如果说这个阶段的霸政尚以“尊王攘夷”作为旗帜,以后的大国争霸便以兼并弱国为主要内容。西周以来的传统礼制遭到彻底破坏,王室地位下降,经济拮据,地盘被蚕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王室不仅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经济上也不得不依赖于诸侯的资助,威严扫地。
与此同时,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并且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真正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局面。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卿大夫与公室的斗争愈演愈烈,以下克上的事件层出不穷。斗争的结果,使各国的公室程度不同地衰弱下去,卿大夫逐渐掌握了政权,有的甚至灭亡了公室。
春秋时期卿大夫与公室斗争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族与公室的斗争。按照周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原则,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大夫,他们是公室的后代,称为公族。这些公族卿大夫与公室同室操戈,争权夺利。二是异姓卿大夫与公室的斗争。春秋时期少数国家公族势力衰败不振,执政的卿大夫多为异姓贵族,他们也和公族展开夺权斗争,春秋后期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由于异姓卿大夫专权而造成的结果。
同时,诸侯也不愿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辙,更不愿受制于卿大夫,于是也想尽办法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办法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授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左传·襄公十六年》:“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表明官职与封邑(禄)已经联系在一起。;卿大夫出奔或以其他原因离去官职,其采邑自然归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齮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左传·襄公三十年》:“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在兼并卿大夫封邑的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出现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式的以军功而不完全按血缘授官的规定。因此,各国相继出现了没有世袭的、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
就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逐渐形成,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日益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血缘宗法关系逐渐淡漠,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贵族“出奔”和采邑归公。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出奔”是春秋时期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从一个侧面了反映春秋血缘宗法关系的崩溃。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曾集中统计出国君“出奔”事件十二起,周天子“出居”事件三起。而事实上,各国贵族“出奔”事件不下数百起,涉及周王室和数十个诸侯国。
终春秋时代,因君位之争导致“出奔”的事件,总计七十起,九十二人次。因以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导致的“出奔”事件,总计六十二起,涉及到九十五人次,因家族长争立导致的“出奔”事件,总计四起,涉及到十二人次,因其他原因贵族内部发生冲突导致的“出奔”事件,总计二十八起,涉及到二十九人次。
“出奔”者背井离乡,永远或者暂时脱离了原来的血缘关系和宗法体系,来到理论上有宗法血缘联系而实际上却淡漠疏远的新环境中,使得宗法体系残缺不全,血缘关系受到了破坏性的冲击,并直接摧毁了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
世卿世禄等级制度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孟子·万章下》。根据等级裂土分封,按级别高低分别享有不同政治特权和物质待遇,并且世袭罔替。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新的官僚等级制度开始取代旧的世卿世禄制度。
官僚等级制度源于世卿世禄制,但又有所不同。充当官吏的虽然还是大大小小的贵族,但已经不是世袭,他们“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在这种君主臣仆的特殊雇佣关系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他们的命运”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 年版,第8-11页。。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袭之外,还可能随时受到升迁罢免,上下沉浮,而且享受报酬的形式也不再以土地作为标准,而是改以实物作为支付的手段。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世卿世禄制的封君和赐爵制。例如,晋文公重耳“赏从之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史记·晋世家》;赵简子赵鞅也曾以“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奖励将士,激发各阶层人士奋发立功。
总之,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的官僚制度。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所以后人说:“自世爵世禄之制废,而宗法始坏矣。”清·江琬:《汪氏族谱序》,选自(清)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封建废,而宗法格不行。”清·许三礼:《补定大宗议》,选自《清经世文编·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敬宗之道。”清·顾炎武:《日知录·分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纪实传记 【已完结】
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