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物质匮乏,读书用的纸张也非常有限。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楼上的杂物堆里有一个藤条做的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多本线装的稿纸,我和二姐如获珍宝,用稿纸的背面来做数学题的草稿。那是父亲年轻时写的未发表的小说文稿,幸好现在还保留了几本,没有全部被我们糟蹋完。 当一名作家是父亲未完成的夙愿,九十年代人人都在追求物质财富,父亲却为他的儿女安于写作而感到欣慰。 出书,成为一个作家也是我的梦想,可是自从知道出书的门槛后,我不执着了。在网上写着玩,跟人分享,便成了一种乐趣。 这些年看见网友都纷纷出书了,也想尝尝把文字变成书的滋味。于是试着联系海外的出版社,很快就收到了回复,愿意接受我的自传体小说文稿《孤独前行》,但要自己出钱。 反正都要自己出钱,何不选择在国内出书呢?而且我的文字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于是我跟海外的出版社说《孤独前行》上篇只有10万字左右,等我写完下篇之后,再联系他们。 之前有人向我推荐加入国内“青年作家网”的签约作家,我想我身在国外,没必要加入国内的组织,而且我也不需要什么虚名,便放弃了。知道“青年作家网”也可以帮人出版书籍,于是联系了这个网站的负责人汪总。 在国内自费出版一本书大概要7万元左右,汪总看了我的几篇文稿后,对于国外生活经历的题材很有兴趣,表示愿意合作出版,我只需出一半的费用就可以,宣传策划等其它方面的工作,他们负责。 宣传造势,邀请人来写书评,凡是与人打交道的事都是我的短板,有人替我分担,实在太好了,决定与“青年作家网”签约。 在作者简介这一栏,我该怎么写呢?别的作者都有一长串的头衔和亮眼的成绩,我只好自卑地简介自己:
“我曾经是深圳的一名教师,现定居在英国。白天在自己的中餐外卖店讨生活,深夜写字支撑起诗和远方。因为文字朴实、真诚,颇受读者的喜爱。在海外中文网站的网名叫“我生活着”,在微信公众号的网名是“英国懒妈”。 这本《生活在英国》分六部分,分别是“懒妈与儿子”“写给老公”“血浓于水”“疫情中的日子”“英国生活”和“生活随感”。 “懒妈与儿子”是妈妈记录儿子从五岁半到英国的成长历程。儿子能自强自立,还能考进名校,应该是懒妈坚持放养和穷养的成果,但是儿子上大学前的一天,他责备妈妈说“你是个自私的妈妈,对我没尽到责任。”果真如此吗? “写给老公”是妻子应丈夫之约写写他们之间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携手同行二十多年,既是夫妻又是朋友,其中的秘诀,那是因为彼此的坦诚、包容和付出。 “血浓于水” 写的是原生家庭血浓于水的亲情,祖母、父亲从苦难中走来,他们身上坚强、正直和善良的品质影响着一代代后人。 “疫情中的日子”分享了我在英国疫情刚开始时的彷徨害怕,后来禁足在家,到最后麻木得与病毒共处,打完疫苗等着生病的滑稽。 “英国生活”和“生活随感”分享了我在英国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英国开中餐外卖店的经历。 在国内出书要把握语言的分寸,有些敏感词不能出现。在众多的文稿中,我先自查一遍,有些过激的言论和可能伤害到他人情感的文章,我先主动去掉。 在这一轮的筛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写字不能仅仅是自己开心,还要对社会和他人负责。在网上写,可以随时删除掉,印成书,那就撕不掉了,所以容易引起误会的文章,最好不要出现在书里,毕竟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但疫情中我在英国生活的部分,被全部砍掉了,这一刀切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于是我问汪总:“我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初审后的文稿,发现「疫情中的生活」全部砍掉了,我的文字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啊,怎么会这样?难道疫情中就不能有生活,不能有情感体验吗?” 汪总解释说:“国内疫情的稿子都不能出版。除非是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组织的稿件,而且还属于特殊题材,需要特审特批。出版在这方面都比较严。凡是涉及疫情的,包括宗教、民族等问题也都一样。都属于敏感话题。” 唉,还能怎样呢?既然选择在国内出版,只能任凭他们处置了。我对国内官僚机构简单粗暴的做法,向来就很反感,他们一刀切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不想承担责任。 我以为“三审三校”过去后,封面也设计好了,新书很快就可以上架了。按合同上的规定,半年就可以出书,可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还不见动静,于是忍不住弱弱地问了一下出书的进展情况。 负责人汪总说:“原计划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往出版局报书号时,上面认为涉及过多夸赞海外教育等问题,没有批复。后来我们这边换了几家出版社,他们看了选题和试读了内容,认为也不适合出版。之前几家都是省级出版社,后来我们换到一家央级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主管单位是民主党派),对内容相对宽松一些,目前答复我可以出版。” 习主席不是说要坚持“文化自信”吗?一个自信的民族和个体,应该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和不足,包容、学习别人的长处,而不是排斥他人的优点,以此来自欺欺人,自我封闭,自我膨胀。 这些怨言也只能在心里说,我问汪总,“已经砍掉了一些相对敏感的文章,有些与国外对比的事例也删除了,如果文字没有了灵魂,对于出版社来说还有出版的价值吗?” 国内的文化人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汪总说:“出版社不仅看文章,还要了解作者背景,有台湾背景的肯定不行。而且不能用网名,要用真名。” 唉,真同情国内的人,没有表达的自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人拿着棉签,高喊着:“全民核酸,免费核酸。”一个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乖乖地来到举着的棉签面前张开了嘴巴。 这个视频让我沉思和痛心,国内的宣传教育太厉害了,从娃娃抓起,容不得人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这种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哪来的创新能力。再想想现在国内一些刻板,毫无人性的防疫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书稿经过“三堂会审”后,终于到了选择封面的时候了,汪总建议我,封面来一张一家三口在草地上的快乐时光。 我悲哀地发现相册上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一家三口一起外出游玩的时光也特别少,难怪儿子曾经埋怨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 儿子知道我要出书后,他说不可以写他。我说:“你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想想,也是的,但不可以用他现在的照片,小时候的没关系。 我可以无私地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但家人的安全是我的底线,我不会公开家人的照片。刚开始设计的封面,使用的是我的背影照,名字也是网名,但被出版社否定了,一定要用真名,而且用的是正面的照片。 国庆前夕,国内的亲友终于收到了我的新书《生活在英国》,我家大嫂虽然老花眼了,但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她说:“这本书有思想有灵魂,太吸引人阅读了,都是你在英国生活的真实写照,一点都不虚构,文字朴实无华,刚到异国它乡谋生确实不容易啊!” 读书让人快乐,忘掉孤独,前些天收到了很多书评。写出来的文字能得到读者细细的品读和理解,这就是写字的快乐和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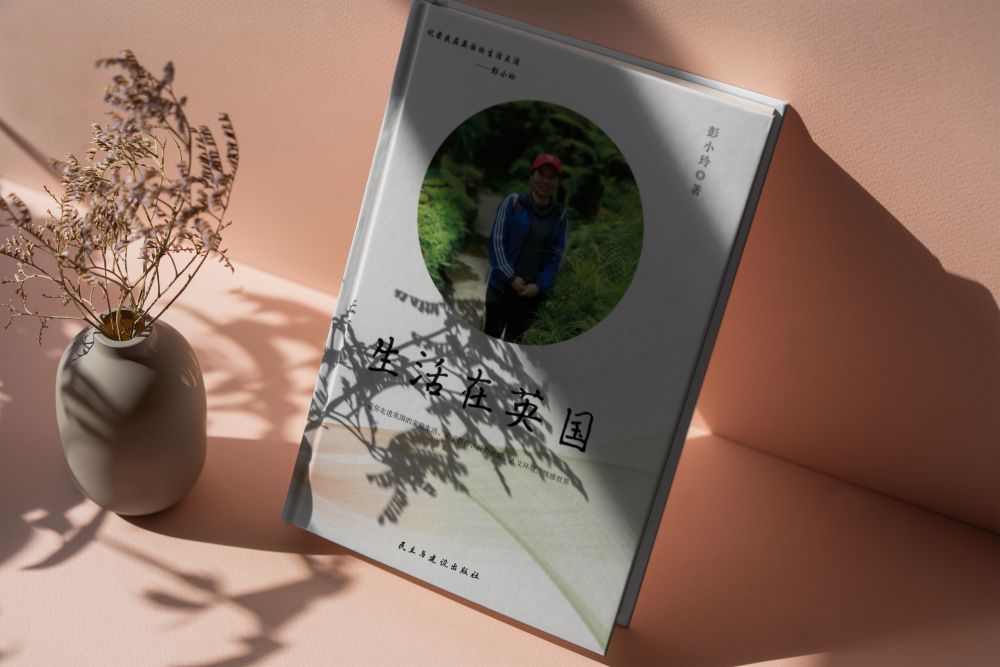
|